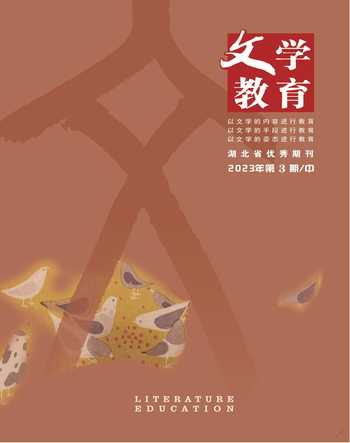丛林深处
虞文婕

A
北纬10°的热带雨林。
晨光熹微,和煦的光芒细密地散布在浓密繁茂的雨林那偌大层叠的叶盖之上,大片大片的苍翠绿得油亮。微风宛若蚍蜉撼树般温柔地拂过丛林发梢,带动微弱的碰撞,发出如私语般的沙沙作响。在茂密交叠的阔叶之下,雨林尚未苏醒。青蛇阖着满是褶皱的眼皮依旧盘缠在枯槁得即将剥离的老树皮上浅浅呼吸,泛白的腹部有隐隐的律动。成群的蝴蝶依旧合拢了双翼,依傍在低矮的灌木丛中拟作枯叶。
“唰——”一只赤裸的身子从幽绿的阴影之中迅速地腾飞摇荡而过,轻盈地落在地上。积久而又蓬松的落叶在任何生物的足下都是如此低微沉潜地匍匐着,默默地隐去了一切声响。这只身子的双足已经大有被落叶淹没之势,一双前肢如兽一般前伏,微微蜷曲双爪,躯干上于丛林生物而言极具保护意义的毛发并不旺盛,却是泥泞斑驳得早已看不出原状。脖颈之上的发丝凌乱地缠绕交杂在一起,微微抬首,依稀可以看清模糊的面庞之上分明的五官。口部因颌骨的前倾趋势而微微张开,露出尖锐的侧牙,一双乌黑的眼睛在暗处隐隐闪烁着绿光。如果此时生物学家或是社会学家出现在此,或许会就此下定论道,它是一个狼孩。可对于这里的每一个物种而言,它只是这片密林里狼王的孩子之一,也是母亲的孩子。
“嗷呜——”一道凛冽又带着召唤意味的嚎叫撕开了丛林的宁静,惊起了隐匿在林中的鸟雀四下扑棱,惊得安逸在枝桠上的蛇群纷纷昂首,“丝丝”的吐着信子,如潮水般群涌而起,缓缓退去,蛇皮与老旧的树皮相互摩挲,发出窸窸窣窣的轻响。蝶群舒展开双翼,抖落簌簌的磷粉,在丛林间舞出一条迷迭炫彩的柔软绸缎。它也抬起了头,慵懒的四肢微微撑起躯干,脖颈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偏转,眼睛里闪烁着幽邃的绿光,旋即撒开四肢,往狼穴疾驰而去。
B
北纬30°的江南小镇里的列车站候车室。
迁徙的本性总是在人类的骨髓里流浪,攒动。不断行走,不断游移,从一座城到一个镇,一路风尘。这里仿佛是候鸟的集散地,有些人归家,有些人远行,但终究都生活在路上。麻木和疲倦是时常浮现在候车室里的神色,带着地域特色的面庞和杂乱的方言交织在一起。婴孩焦躁的啼哭与压抑的交谈声此起彼落,仿佛南北东西就此在这小小的空间里沉默又喧嚣的化成了一片缩影。人们的目光不住地落在频频闪动的车号牌上,手心是被汗水微微浸湿的车票,仿佛总是记不住自己的车号,时不时便看上几眼。
进了站,车尚未来。人们拖着行李箱在大理石的候车台前缓缓踱步,紧紧倚在地上的安全黄线旁,头总是不自觉地跃出黄线,远眺漫长轨道上那洁白纤长的身影,又或是掏空了耳朵细听着从幽远的地方传来的轨道与车轮厮磨的声响。
在稀疏的人群之中,一对形容枯槁衣着陈旧的夫妻仿佛有着异于常人的不安与焦虑。他们时不时地越过安全黄线,在原地不自觉地晃动,打转。在管理人员一次又一次将他们劝解至安全地带后,妻子微微有些神经衰弱地倚在了丈夫肩头,低声抽泣,话语支离破碎:“这……这是第七年了啊……我多希望能够找到她,可如果……如果真的是她,那该怎么办,我……我都不敢想……”啜泣声掩去了剩下的言语。
“没事……没事,会好的……会好的……”丈夫瘦削的手紧紧地搂住妻子的肩膀,轻声呢喃,像是安慰,更多的宛若一种祈祷。他的目光发散向无尽的远方,那是他们将要抵达的远方,又或许他们永远也抵达不了自己的远方。他已经快要忘记自己在路上行走了多久,摩挲过多少片干涸或湿润的土地,叩开过多少扇落了漆的门墙,看过多少双空茫的眼。列车在他身后缓缓停下,风微微扬起他们挂着线头的衣摆,没有片刻地发怔,踏上下一条路已然成为一种条件发射,他们再次坐上了动车。
A
狼穴处。
生物之间总是看起来并没有如同人类一般的生存界限。一棵看起来并不壮实的树上也许居住了数不清的昆虫与寄生植物以及偶尔驻足的各色动物。但它们大多体格渺小,拥有大多的亲族却往往茕茕孑立。狼,成群结队的出没,生存空间也是异于其他渺小生物的固定。这里的狼王将它的一大家子安置在一片乱石林中,这里植被稀少,阳光正好可以透过槎桠的罅隙散落在横七竖八的怪石之上。此刻,每一块石头上都屹立着一匹年幼的小狼,目光直勾勾地盯着正中央那块巨石之上正在分割几头喘息的鹿的母狼。
它,狂奔而至,渐渐放慢了步伐,喘息声有节律地响动,鼻息伴着喷薄而出的热气。行至外围时,弥散的浓烈的血腥味灵巧地钻进它的鼻子,勾起了它腹间萦回曲折的欲望,它轻盈地挪动到母狼身侧,亲昵地用头蹭了蹭母狼的背。母狼回头,将刚从鹿腹上撕咬下来的肉吐在它身前,伸出湿濡的长舌舔了舔它的脸,它微微抬首,舒适地微阖双眼接受了来自母亲的爱抚。其他小狼见状也纷纷像母狼挨近,前赴后继地扑向苟延残喘的鹿,它则叼着自己的肉飞快地脱离了包围圈。
饱食之后,它缓慢地踱步至一块被阳光照射地微微发烫的巨石之上,侧身躺下,将脊背暴露于随时间流逝已然直射这片土地的阳光之下。阖上双眼,懒倦地休憩一番。其他小狼满足于口腹之欲后彼此交尾戏耍一番后也各自于乱石中寻一块匍匐其上,享受阳光的温存。母狼和狼王在石堆上亲昵的交颈戏耍,依偎着躺下。
B
列车上。
旅人们瘫软在舒适的靠椅中静默着,目光有时落在窗外一闪而过的光影之中。那是途径的城市,鳞次栉比的高楼屹立在高架旁的田野间,突兀而又孤单。那又是整齐划一的绿色方块,依稀可辨其中划分的田垄和人工水渠,渐变的绿,盎然又无力地点缀在灰白的天空与灰白的城市之间。那也是远处不断靠近的绵延山丘,浓密的枝叶在上端拼命地向上生长,肢体末端却禁不住裸露在土层之外,隐隐偷着土壤腐朽又无助的气息,亦掩盖不住那杂乱无章的不时冒头的小土包。
那对夫妻并没有这般的闲情掠过窗外的种种世界。妻子因长途奔波的劳累而昏睡着,那紧蹙的眉心,未干的泪渍,轻声的梦呓,都显现出梦中的不安宁。她的头倚在丈夫的肩上,发丝散乱。双手交指垂落于膝上,指尖紧扣,关节因用力而微微泛白,似乎想要抓住什么却又是求而不得。丈夫无心留意妻子这般的异样与梦中的苦痛,他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手机屏幕上。那是一张来自边境丛林里的老猎人的照片,模糊的圖像上隐隐有一个身影。他们从很多渠道了解到了些许零散的讯息,丝丝缕缕的线索都与他们找寻了七年的骨肉不谋而合,可是在经历了这么多次的失望之后,他似乎对这一次的找寻生出了隐隐的恐惧,在那无人之境,他们的女儿怎样活着呢,他不敢想。
他还记得七年前,她刚刚降临人间,在医院里,他第一次见到她,白嫩的皮肤和水光泛滥的眼睛让他移不开眼,他觉得自己仿佛看见了天使。那一双乌黑的眼睛直盯着他看,小嘴一咧一咧似乎在对他笑。他俯身轻柔地吻了吻她,对妻子说:“谢谢你,让我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老公,你……”不知何时,妻子已经醒了,亦不知何时,他已经泪流满面了,他拭了拭眼角,哑声道:“没事,我就是想起了从前,你生她那会儿的事了。”妻子一怔,捂住嘴偏过头去,肩头耸动。
A
丛林里。
度过了晨间分食的喧闹,丛林里又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寂静。所有的狼都安静地阖上眼,舒展了四肢,沐浴在阳光之中,肚皮微微鼓起,随呼吸一起一伏。其他大型生物也沉默着,没有嬉笑追逐的嚎叫与啼鸣,没有肉体冲撞的闷响与嘶鸣。依旧只有风,无力而又虚张声势地从丛林的最顶层呼啸而过,沾染上几片绿得油亮的叶子,却没有一丝办法打破下方的安宁。在偌大的叶子笼罩的阴影之下,细小的昆虫依旧安静地生活着,它们匍匐着,蠕动或是飞翔,倾巢而出又或是单枪匹马地在落叶上,在树干上,在丛林沉闷的空气里,卷起微乎及微的浪潮与动静,一霎时吸引了侧旁生物的目光,旋即又被丛林惯有的沉默覆盖。在这个庞大的体系里,仿佛没有什么能够逃离融合的命运,它宛若一块海绵,能将所有水化为填充自己体积的无辜事物。
所有的狼依旧安眠着,而它,睁着眼出神已久。它有些不耐于此刻的安静,用手抓了抓头发,偏头看看和狼王并排倚躺着的母狼,一如既往地溜了出去。
它在丛林里无所事事地游荡着,这片林子的深处是狼穴的势力范围,它早已溜达完了。她攀上一棵树,又借着枯藤荡到另一棵树上,时而惊扰了航线平稳的鸟雀,时而与树上的松鼠对上两眼,更多的时候,会踩到各式各样的昆虫,然后在身上留下花花绿绿的汁液。晃悠了许久,它思索了片刻,撒开腿往外围奔去。
这是一片竹林,已经趋向于丛林的外沿,竹林是难以遮挡视线的,透过竹林它甚至可以看见外面的村庄与那种直立行走的生物。母狼在平时是不允许它们到这里来的。它告诫过它们,那对于它们是一种极其危险的物种。它曾经透过这片竹林窥探过那些直立行走的生物,这是一种毛发比它还要稀少的物种,它不明白,他们是如何生存的。
它鲜少有机会在这片竹林里享受这般安逸的时光,它在在林子里缓慢地移动着,从这一方到那一方,时而仰视头顶竹叶的沙沙作响,时而俯视足边悠闲的昆虫。兜兜转转,它突然发现了一株与众不同的竹子。它通體碧绿,没有竹节。这一新奇的发现让它围着这株竹子兴奋地打转了许久,抬腿踢了踢,竹竿连带着竹叶轻轻颤动,一团绿油油的东西落了下来,它定睛一看,是一条竹叶青。这条纤瘦的蛇并未因它惊扰了它的美梦而回首攻击,只是微微抬起与身体并不分明的头部,一双细小的眼睛慵懒又清明的看了看它,又缓缓蠕动着身子,重新攀上了那棵竹子,待到了适当的高度又重新盘缠上去,安详的继续它的美梦。她觉得眼前的景十分新奇,决意返回狼穴分享给它们。
C
丛林外。
马不停蹄赶到的夫妻俩行色匆匆地穿梭在破败老旧的村庄内。来到老猎户家,表明来意,老猎户沉默着“吧嗒吧嗒”抽了几口旱烟,抬起黝黑的满是褶皱的脸,缓缓道:“你们可要想清楚,这枪是不长眼的,如果里头真是你娃娃,有些记忆终究会不太美好。何不找了专业的机关人员,反倒来我这小村子里找我。”
“老爷子,我们等不了啊,再者说如果找了国家的人来,我们怎么把她留在身边啊。”妻子心急如焚,早已泪眼婆娑。
老猎户从口中取出旱烟,在檀木桌上敲了敲,站起身来,对着站在身边的一个黝黑的汉子道:“把他们都叫过来,上林子里去。”夫妻俩止不住的感谢,手紧紧地握在一起。
出发时,老猎户告诫过,狼穴都应当在深处,一路势必艰难无疑,可当他们在外缘的竹林中发现了零星的小狼的身影时,老猎户心底的诧异迭起。他阻止了所有人前进的步伐,拿出望远镜细细观瞻,发现竹林深处聚集了众多的狼崽,由外向内形成一个包围圈,而包围圈的内侧仿佛有一个不同于狼的身影。
他把望远镜递给这位丈夫。男人看了许久,双手颤抖道:“一定是,一定是!”老猎户拍了拍他的肩:“放心,它们不会伤害她的。”然后举起猎枪对身后的后生使了个眼色,所有人噤声前进。
竹林里,她正和母狼眉飞色舞地描述着她发现它的过程,所有小狼也全神贯注地听着,浑然不觉危险正在逼近。“呜——”一只受伤落跑的小狼冲进了包围圈,所有狼齐刷刷地回头,才发现外围玩耍的小狼已经倒下得七零八落了,而举着猎枪的人类还在步步紧逼。母狼的眼睛发出了幽邃的绿光,扬起脖子发出一声凄厉的嘶鸣,仿佛在唤醒所有狼崽灵魂深处的野性。它一下子如闪电般冲出包围圈,向人类扑去,其他小狼也随母亲加入了与人类的搏斗之中。她游移在包围圈最中央,有些无措地看身边自小的玩伴一一倒在血泊之中,她在战局中闪躲着无眼的子弹,身上沾染了小狼的血液,每一次跳起与落下时都能感受到血液的飞溅。有时候母狼在千钧一发之际飞扑过来让她躲过一劫,而这般便又有更多的小狼死在猎枪之下,她的耳畔充斥着枪声和狼群的悲鸣与呜咽,可她从未突破包围与小狼一般去战斗。她在原地踌躇也彷徨,连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无法如其他小狼一般扑上去撕咬,它们仿佛出于一种天性,而她却似乎忘了自己的天性。又或许,她本来就没有这种天性。
当最后一匹小狼倒下,浓烈的血腥味中屹立着的只剩下她与母狼,以及那群人类。她被血糊住了四肢,那是母狼的血,也是众多狼崽的血。母狼看了看她又看了看人类,似乎也意识到了人类的意图,可当猎枪再一次被举起,母狼仍然毫不犹豫地挡在了她的前面。那对夫妻早已泣不成声了,妻子道:“放过它吧。”猎人们放下了枪。可当母狼护着她缓缓后退时,在那个女人的尖声叫唤之中,对面的人类又重新举起了猎枪。这一次,她毫不犹豫地站在了母狼的面前,那一瞬间,她敏锐地觉察到人类的脸色一下子变了,所有的猎枪都一下子放了下来。
她护着母狼步步后退,那群人类步步紧逼,但却始终没有在举起猎枪。她与母狼都渐渐察觉到人类并不打算伤害她,却也明白了人类并不打算放走她。它们退到竹林尽头,最终决定让母狼离开。母狼最后用舌舔了舔她,喉中发出悲怆的呜咽,消失在丛林之中。
终于,只剩下她和人类了。
她的眼警惕地盯着面前的一大群人类,只见那个女人一下子冲出队伍张开双手向她奔来。她也眯了眯眼,露出两侧的獠牙,向她奔去。在女人的手触及她的那一瞬间,她的牙狠狠地咬住了她的腿。女人因为疼痛松开了手,难以置信地看着她,猎户们连忙上前来将准备好的麻醉药注射下去,她神情怔松,昏睡过去。这是她唯一一次展示她的天性,也是最后一次。
时光总能轻易地洗涤旧迹,尽使留下微漠的悲哀。曾经的苦痛给他们留下的痕迹仿佛在她回归之后都沉潜下来。父母总不愿她提及那些曾经的过往,她零碎的记忆里时有儿时丛林里似人非人的欢愉,但当她将要与父母言说时,苍老的面庞上一闪而过的慌乱总让她张了张嘴,却失了言语。太多的岁月成了她一个人的念想。
他们给予她沉默而厚重的包容,仿佛为了弥补那段岁月里寄存在心底无法宣泄的关怀,但她也很难忘记自己选择生物保护专业时他们那隐忍的神色,但却从未有过冲突。
不远万里,她又回到这片曾经的土地,她再也没有遇见过记忆里那最后一抹苍凉的灰色。当年的老猎户已经失去了踪迹,但世代相传的猎人在岁月的更迭中从未改变地生活着。她站在丛林外炽热的土地上,透过竹林,阳光稀稀疏疏地漏下来,画下满地的斑驳,微风拂动时有整齐的摇摆声,再也没有异种屹立其中。
大风呼啸而过,浓密的丛林不动声色地沉寂着,看按捺不住的竹林在风中扭动身姿,“沙沙”作响,吞没她所有的怅惘。她从深沉而又厚重的原始丛林深处挣扎着出走,却最终又湮没于斗兽肆虐,欲望横流的城市丛林之中。走在城郊的旷野上,她张了张嘴,却被迎面的风所带来的寂寥紧紧包围。
(作者单位:杭州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