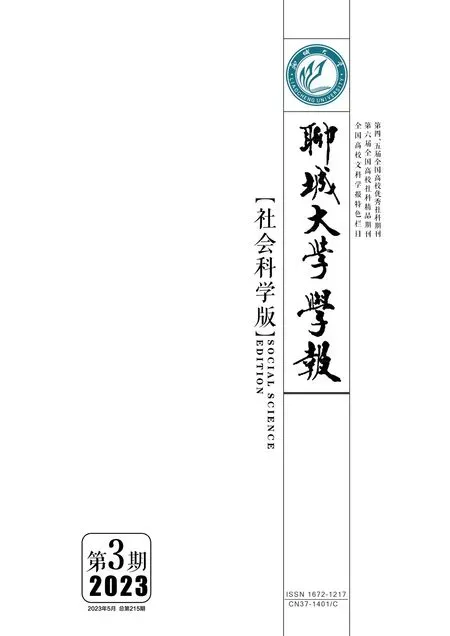汉大赋中动植物书写的特色
踪 凡
(首都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089)
中国文学素有描写草木鸟兽的传统。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已指出《诗经》除了“兴观群怨”之外,还具有“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①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 年,第185 页。的博物功能。当然,《诗经》里的草木鸟兽主要还是用于比兴,例如《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以小洲上关关鸣叫的雎鸠,起兴君子对于采荇菜姑娘的追求;《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以明艳夺目的桃花比喻新嫁娘光彩照人的姿容。《楚辞》继承并发展了《诗经》的比兴传统,采用美人香草之喻,即所谓“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王逸《离骚经序》)②[宋]洪兴祖撰,白化文等点校:《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第2-3 页。。《离骚》的风云、龙凤、草木、鸟兽各有所喻,形成了一组组缤纷陆离的意象群,旨在表达诗人在“美政”理想失败后对社会人生的思考。继《诗经》《楚辞》之后而兴起的“一代之文学”汉赋,对草木鸟兽的铺写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其书写方式却与《诗经》《楚辞》迥然不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独特景观。下文我们就来探讨一下汉赋中动植物书写的主要特点。
一、数量众多,铺列如画
《文心雕龙·诠赋》云:“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③[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年,第134 页。赋体文学区别于其他文体(诗、骚、文)最关键的要素,就是铺陈。汉赋(主要指汉大赋,即汉代散体大赋,或称汉代骋词大赋)中所书写(铺列、描写或涉及)的草木鸟兽,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先秦诗文。试将书写动物较为突出的《诗经·七月》、屈原《离骚》和司马相如《上林赋》加以比较:

《七月》《离骚》《上林赋》书写动物名称一览表①三篇作品的文本,分别以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中华书局,1991),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萧统辑、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为据。
《七月》是一首农事诗,诗中描写鸟兽昆虫15 种,皆与打猎、农耕或岁时密切相关。例如:“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③程俊英、蒋见元:《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1991 年,第412 页。通过三种小昆虫的活动来反映季节变换,贴近生活,令人如临其境。《离骚》中鸟兽虫鱼13 种。作者以鸷鸟自喻,以鸩、雄鸠比喻恶人,驱遣蛟龙、凤凰,营构出缤纷陆离的想象世界。《上林赋》中禽兽虫鱼多达94 种,数量已达《七月》或《离骚》的六七倍之巨,盛况空前。该赋主要写天子上林苑之猎,所有动物皆供猎取之用,包括飞禽、走兽、水族三大类,昆虫没有狩猎价值,故很少涉及。需要说明的是,《上林赋》中既有生活中实有之禽兽,如貔、豹、豺、狼、鸿、鹔、鹄、鸨;亦有神话传说中的动物,如麒麟、獬豸、凤凰、鹓鶵。还有一些语句涉及动物,但仅仅是动物制品或者诗文篇章名,并不直接描写动物本身。例如“树灵鼍之鼓”,鼍指扬子鳄,其皮坚韧,“灵鼍之鼓”是指用扬子鳄皮做成的鼓;《驺虞》为《诗经》篇名,古代诸侯举行射礼时演奏此乐,因驺虞系传说中的仁兽,故亦列入;“曳独茧之褕绁”,形容衣服色彩纯正,仿佛用一只蚕茧中抽出来的纯丝制成,这里取蚕茧本意。
由上表可见,《上林赋》陈列走兽53 种,禽鸟26 种,水族14 种,昆虫1 种。除了这94 种动物外,本赋所书写的植物还有绿(王刍)、蕙(零陵香)、江蓠等草本植物22 种,卢橘、黄柑、楱(橙子)等木本植物18 种。品类之富,数量之多,不仅远远超越前代,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此外,枚乘《七发》、孔臧《谏格虎赋》、司马相如《子虚赋》、扬雄《蜀都赋》《羽猎赋》、班固《西都赋》、张衡《南都赋》《西京赋》都对花草、树木、禽鸟、走兽、水族等有大量铺陈。
汉赋中为何出现大量的铺陈文字?这恐怕与汉代独特的社会背景有关。清人刘熙载《艺概·赋概》云:“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④[清]刘熙载撰,袁津琥校注:《艺概注稿》,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411 页。汉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且长久稳定的中央集权制帝国,国势空前强盛,人民生活相对稳定,中央和边境地区来往频繁,物资流通空前顺畅。居住在都城长安的文人士子,也能看到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异域他乡的动物、植物、器物等等,这些物产林林总总,千态万状,层见迭出,令人不写不快。这在四分五裂的战国和民生涂炭的秦朝,都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汉赋作品的铺陈技法,也是时代使然,它在客观上反映了大汉帝国版图的辽阔、物产的丰富和各地区文化物资交流的畅通,宣扬着帝国的声威气象和大一统的力量,当然也折射出文人士子内心的喜悦和豪迈。前辈赋学家研究汉赋求大、求全、求多的特点①何新文:《赋家之心 苞括宇宙——论汉赋以“大”为美》,《文学遗产》1986 年第1 期。,认为以《上林赋》为代表的汉赋作品“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西京杂记》卷二司马相如语),爬罗剔抉,不厌其烦,堆累材料,多多益善,展示了一个丰富充盈、琳琅满目的世界。
汉大赋中的名物书写,“语象”上一字排列、一气呵成,“意象”上平面铺开、鳞次栉比,具有鲜明的图案化特征。正如易闻晓所言:“赋的名物铺陈就是称名的呈现,汉语一字一物或二字一物,赋家博物,在于识字之多,赋中铺陈,也是名物字或字组的罗列。”②易闻晓:《主物的文学:赋体分别与题材交互》,《中山大学学报》2023 年第1 期。这一点与《诗经》《楚辞》颇为不同。后者叙列的动物、植物大都有所间隔,例如《七月》:“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在“斯螽”(蝈蝈)和“莎鸡”(纺织娘)中间,既有“六月”“七月”两个时令词汇,又有“动股”“振羽”两个具体动作。《离骚》:“吾令鸩为媒兮,鸩告余以不好。雄鸠之鸣逝兮,余犹恶其佻。”鸩与雄鸠各有其言行,时间上也有先后之别。汉大赋中的动植物则以群体方式出现,在一定的空间内铺展陈列,不存在个体描写,亦无时间间隔。这恰好体现了铺陈与叙事、写物与抒情的写法之异,也是赋体与诗体的文体之异。正如朱光潜《诗论》所言:“一般抒情诗较近于音乐,赋则较近于图画。用在时间上绵延的语言表现在空间上并存的物态。诗本是‘时间艺术’,赋则有几分是‘空间艺术’。”③朱光潜:《诗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 年,第203 页。在朱光潜先生眼里,赋(散体大赋)显然属于“空间艺术”,是一种重视空间展列,在性质上近于图画的描绘性文体。
二、分类展列,各具形态
汉大赋对于动物、植物采用分类展列之法,表现出一定的类聚意识。例如司马相如《子虚赋》如此描写楚国云梦泽东、南、西、北各个方位的植物:“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藭菖蒲,茳蓠蘪芜,诸柘巴苴。其南则有平原广泽,……其高燥则生葴菥苞荔,薛莎青薠;其埤湿则生藏莨蒹葭,东蘠彫胡,莲藕觚卢,菴闾轩于。……其西则有涌泉清池,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内隐巨石白沙。……其北则有阴林,其树楩枏豫章。桂椒木兰,檗离朱杨。樝梨梬栗,橘柚芬芳。”④[南朝梁]萧统辑,[唐]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 年,第207-209 页。东部有蕙草(零陵香)、杜衡(马蹄香)、佩兰、白芷、杜若、川穹、菖蒲、茳蓠、蘪芜、甘蔗、芭蕉等等,四言一句,尽情铺列,可见香草园品类之盛。南部平原广泽的植物则分为两大类:高而干燥处生长着葴(马蓝)、菥(燕麦)、苞(蓆草)、荔(马蔺)、薛(艾蒿)、莎(莎莎草)、青薠;低洼处生长着藏(狗尾草)、莨(狼尾草)、蒹(荻苇)、葭(芦苇)、东蘠(泽蓼)、彫胡(菰米)、莲藕、觚卢(葫芦)、菴闾(臭蒿)、轩于(莸草)。这里陈列17 种植物,仅仅是举例言之,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些(所谓“众物居之,不可胜图”)。但大抵为普通的草本植物,甚或有杂草稗莠,并不稀奇。西部涌泉清池只写到芙蓉(荷花)和菱角花两种,用笔极简,当然也是举例言之,备列水生植物一类。北部大树林里的植物有:黃楩木、楠木、香樟、肉桂、花椒、玉兰、黄檗、山梨、赤杨(河柳)、山楂、梨树、黑枣(君迁子)、板栗、橘树、柚子树,此处罗列15 种,大多是乔木,以果树、香木为主,以见北部林木之形形色色,繁茂而芬芳。四个方位各有特色,东部与南部皆为草本植物,但有香花、贱草之别;西部为水生植物,草本;北部则为木本植物。类目分明,有条不紊,各从其类,各呈其态。禹明莲认为:“相如作为文字博物学家,其赋中对动植物不仅仅是以名类聚,鱼贯罗列,而是对动植物的科、属、形状、习性、产地等都有了非常明确的认识”①禹明莲:《司马相如赋中的名物叙写探奥》,《中南大学学报》2013 年第4 期。,颇具眼光。不过,司马相如的属类意识是初步的,尚未达到“非常明确”的程度。
汉大赋对飞禽走兽的书写亦遵循着同类相聚原则。如《上林赋》:“于是乎玄猨素雌,蜼玃飞蠝,蛭蜩蠼猱,獑胡豰蛫,栖息乎其间。”②[南朝梁]萧统辑,[唐]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三),第15-16 页。汉唐学者进行了一系列考证,认为“玄猨素雌”指猿猴(雄性黑毛,雌性灰白色毛),蜼、玃皆如猕猴,飞蠝即鼯鼠,蛭有四翼,蜩不详,蠼猱即猕猴,獑胡即黑腰,豰为黄要,蛫未详。五臣注最为简洁:“翰曰:皆兽名,似猨(猿)而捷,木处也。”③[南朝梁]萧统辑,[唐]五臣注:《文选》卷四,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宋绍兴三十一年(1161)建阳崇化书房陈八郎宅刊本,第15 页a。李周翰的概括十分科学,这9 种动物都是栖息于林木之间、动作敏捷的猿类或猴类,生活习性接近。扬雄《蜀都赋》如此展示蜀地物产:“兽则麙羊野麋,罢㹈貘貒,鹿麝,户豹能黄, 胡蜼玃,猨蠝貜猱,犹豰毕方。……于木则楩栎,豫章树榜, 櫖樿柙,青稚雕梓,枌梧橿枥,㯕楢木㮨。……其浅湿则生苍葭蒋蒲,藿芧青苹,草叶莲藕,茱华菱根;其中则有翡翠鸳鸯,袅鸬鷁鹭, 鶤鹔 ;其深则有猵獭沈鱓,水豹蛟蛇,鼋蟺鳖龟。”④龚克昌等:《全汉赋评注·前汉》,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3 年,第279-281 页。很显然,扬雄满怀热情地列举蜀地的走兽、树木、水草、禽鸟、鱼鳖等,旨在反映蜀郡的物产之丰,表达其对故乡的赞美和热爱。但分类比较粗糙,具体品类亦有可商之处。例如“毕方”,《山海经·西山经》云:“有鸟焉,其状如鹤,一足,赤文青质而白喙,名曰毕方。”⑤袁珂:《山海经校注》,成都:巴蜀书社,1993 年,第62 页。据此,则毕方为西方鸟类,扬雄将其归入兽类,似乎不妥,也许是为了押韵而破例为之。张衡《南都赋》则用“其木”“其水虫”“其鸟”“其园圃”“其香草”等连接语,分类之明确,跃然纸上。
汉大赋具有图案化、类型化倾向,古今学者多有讨论。⑥参见万光治:《论汉赋的图案化倾向》(《四川师范学院学报》1982 年第3 期)、《论汉赋的类型化倾向》(《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3 年第1 期)二文。又,易闻晓《大赋铺陈用字考论》(《复旦学报》2017 年第1 期)探讨联边字的使用,可参。其实,枚乘《七发》即有“比物属事,离辞连类”之语,虽系创作经验之谈,但其“比物”(排列事物)、“连类”(分类铺写,同类相连)之法,实为散体大赋创作的不二法门。《汉书·扬雄传》载:“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必推类而言。”⑦[汉]班固:《汉书》卷八七下,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3575 页。提出汉赋“推类”的技法特色,与枚乘的理论异曲同工。对天地山川万物进行分类展示,源自先秦的“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周易·系辞传上》)观念。《周礼·地官·大司徒》分动物为毛物、鳞物、羽物、介物、臝物五类,分植物为皁物、膏物、覈物、荚物、丛物五类,已甚精密。《尔雅》将语词划分为草、木、虫、鱼、鸟、兽、畜等类别,分别加以罗列、释解。反映到文学作品中,战国时宋玉《高唐赋》已对飞禽、走兽、水族等进行相对集中的铺写。至汉赋则推而广之,物类更繁,琳琅满目,排列密集,应接不暇,于是有“赋如类书”“赋如志书”之说。清人袁枚《历代赋话序》甚至说:“尝谓古无志书,又无类书,是以《三都》《两京》,欲叙风土物产之美,山则某某,水则某某,草木、鸟兽、虫鱼则某某,必加穷搜博访,精心致思之功。是以三年乃成,十年乃成。而一成之后,传播远迩,至于纸贵洛阳。盖不徒震其才藻之华,且藏之巾笥,作志书、类书读故也。”⑧[清]浦铣著,何新文、路成文校证:《历代赋话校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年,第3 页。此说甚精。汉代散体大赋蕴含有朴素的分类思想和类聚意识,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最早的类书——三国魏《皇览》的诞生。而后代类书在分类介绍百科知识时,亦往往参考汉赋,甚至大量征引汉赋文字。如《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无不如此。其中《艺文类聚·鸟部》就曾经收录孔臧《鸮赋》、赵壹《穷鸟赋》、祢衡《鹦鹉赋》、王粲《白鹤赋》《鹖赋》《莺赋》等作品。汉赋对草木鸟兽的林林总总的书写,为类书中花草、树木、禽鸟、走兽、鳞虫等类别的编撰提供了重要素材和分类基础。
三、虚实相间,因夸成奇
汉大赋书写名物,并不全是刻板反映,照实列举,而是有实有虚,并常作超逸之思。司马相如《上林赋》如此铺陈上林苑离宫别馆中的植物:“于是乎卢橘夏熟,黄甘橙楱,枇杷橪柿,楟奈厚朴。梬枣杨梅,樱桃蒲陶,隐夫薁棣,荅沓离支。罗乎后宫,列乎北园。”①[南朝梁]萧统辑,[唐]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三),第13 页,第14 页,第20-21 页。其中有卢橘(给客橙)、黄柑、橙子、皱子(脐橙)、枇杷、酸小枣、柿子、海棠果、红花苹果、厚朴、黑枣、红枣、杨梅、樱桃、葡萄、棠棣、郁李、荅沓、荔枝,一口气罗列了19 种植物,颇有来自异域或产自南方者。比如赋中提到了“樱桃蒲陶”,而《史记·大宛列传》载:“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馀石,久者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汉使取其实来,於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萄、苜蓿极望。”②[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三,北京:中华书局,2014 年,第3852 页。大宛国盛产蒲陶(葡萄),俗嗜葡萄酒,汉使“取其实来”(即带回葡萄籽),尝试种植;若干年后,又在上林苑内进行推广,扩大种植面积。此处“汉使”当指张骞,而司马相如写作《上林赋》(前134)时,张骞出使西域(前138—前126)未归,则赋中所谓“蒲陶”,很可能来自传闻,或出于想象。又,宋蔡襄《荔枝谱》称:“荔枝之于天下,唯闽粤、南粤、巴蜀有之。汉初,南粤王尉佗以之备方物,于是始通中国。司马相如赋《上林》云‘杂沓离支’,盖夸言之,无有是也。”③[宋]蔡襄:《莆阳居士蔡公文集》卷第二五《杂著》,宋刻本,第6 页a。此类来自异域远方的植物,中原士人从未见过,颇感新鲜。至于离宫别馆之外的山坡上,还有众多奇异的物种:“沙棠栎槠,华枫枰栌。留落胥邪,仁频并闾。欃檀木兰,豫章女贞。”④[南朝梁]萧统辑,[唐]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三),第13 页,第14 页,第20-21 页。这里展示的是沙棠、柞栎、槠树、桦树、枫树、银杏、黄栌、石榴、椰子、槟榔、棕榈、檀树、玉兰、樟木、女贞,凡15 种,既有温带植物(桦树、枫树、柞栎等),又有热带、亚热带植物(椰子、槟榔、棕榈),从植物栽培学的角度来看,很难在同一气候环境下培植。相如将它们置于上林苑离宫周围,显然有想象乃至不实成分,后人对此多有诟病。扬雄《法言·吾子》称:“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贾谊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⑤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第49-50 页。对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丽淫”(崇尚丽辞、夸张渲染)之赋深表不满。王充《论衡·对作》《佚文篇》更对当时的“虚妄”之词口诛笔伐,当然也包括赋中的夸大之词。刘勰《文心雕龙·夸饰篇》曾对夸饰现象进行总结:“自宋玉景差,夸饰始盛,相如凭风,诡滥愈甚。”⑥[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608 页。批评赋家描写背离事实,有“事义睽剌”之弊。其实,相如赋中所写,乃是包举天下四方之物而言之,并不拘泥于上林苑所产。换言之,司马相如在铺叙上林苑中草木鸟兽之时,顺便将整个大汉帝国的物产皆加以罗列展示,借以反映帝国土地之广袤、品类之众多、经济之繁荣。正如宋人程大昌《雍录》所言:“极天下之大,并夷狄地而言之,则交广、朔漠气候乃始有此。”⑦[宋]程大昌撰,黄永年点校:《雍录》卷九,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190 页。历代批评家斤斤于上林苑的实际范围和气候、土壤条件,其实并未参透《上林赋》宣扬汉威的主题。
更有甚者,《上林赋》还将传说中的神鸟神兽也纳入上林苑中,甚至以之作为被猎杀的对象:“射游枭,栎蜚遽。……躏玄鹤,乱昆鸡,遒孔鸾,促鵔鸃,拂翳鸟,捎凤凰,捷鹓雏,揜焦明。”李善注引张揖曰:“飞遽,天上神兽也,鹿头而龙身。”又引高诱《淮南子注》曰:“枭羊,山精也。”⑧[南朝梁]萧统辑,[唐]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三),第13 页,第14 页,第20-21 页。玄鹤以下,皆为祥瑞之兽,亦皆为猎手所获。无独有偶,张衡《西京赋》描写猎兽场面云:“鼻赤象,圈巨狿,摣狒猥,㧗窳狻。……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巘,猎昆駼;杪木末,获獑猢;超殊榛,摕飞鼯。”①[南朝梁]萧统辑,[唐]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一),第179-180 页。巨狿是巨大的獌狿,《广韵·二十五愿》:“獌狿,兽长百寻。”百寻长的獌狿(一寻为八尺),显然只存在于传说中。窳即窫窳,《山海经·北山经》:“少咸之山……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赤身、人面、马足,名曰窫窳”②袁珂:《山海经校注》,第91-92 页。,乃是传说中少咸之山的怪兽。对这些神异之兽,猎人采取穿鼻、围捕、戟刺等多种狩猎方式,(李善注引薛综曰:“摣(揸)、㧗,皆谓戟撮之。”)似乎与地上的普通野兽没有区别。研究者认为,这种“动词+兽名”的表述形式乃是“通过动词消解物(兽)之神性,以达到君主掌控万物、手操生杀大权的心理需求”③王振强:《<子虚赋><上林赋>的动物展列和文学新变》,《辽东学院学报》2022 年第2 期。。赋家以此宣扬大汉声威,为汉帝国唱赞歌。
这些出于虚构或者来自神话的动物,皆非作者亲眼所见,反映了作者对奇异物象的高度兴趣,这与司马迁《史记》的好奇心理颇有相通之处。作为文学作品,赋家的夸饰之法成为歌颂帝国实力强大、地域广袤、物产丰富的有效手段,也是汉帝国上升时期囊括万有、征服一切的豪迈心胸的艺术反映。故大汉天子并不以“虚妄”“荒诞”为嫌,反而读之“大说(悦)”,加以奖赏。赋家献赋得官,不仅有君臣相知的美谈,也是汉代文学与政治发生关系的重要途径。
汉大赋的夸张虚构遭受了来自时人、后人的种种责难,前已言之。为此,晋人左思提出了赋须“征实”的创作理论,其《三都赋序》云:“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何则?发言为诗者,咏其所志也;升高能赋者,颂其所见也。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④[南朝梁]萧统辑,[唐]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二),第25-26 页,第207 页。但是一味求真求实,也会限制赋家的想象力和作品的感染力,散体大赋的生命力也因此遭到扼杀。
四、增减自如,组合随意
既然汉大赋中的动物、植物大都是分类展列,每一类别都有鲜明特色,给人以鳞次栉比、密集排列之感,但对于具体的动物或植物,却并无特色与寄托。例如《上林赋》:“其南则隆冬生长,涌水跃波。其兽则㺎旄貘牦,沉牛麈麋,赤首圜题,穷奇象犀。其北则盛夏含冻裂地,涉冰揭河。其兽则麒麟角端,騊駼橐驼,蛩蛩驒騱,駃騠驴驘。”⑤[南朝梁]萧统辑,[唐]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三),第10-11 页。南部的野兽12 种,以牦牛、麋鹿、大象、犀牛为主;北部的野兽9 种,以麒麟、骆驼、驴马为主,皆为体型较大的动物。每一种野兽都是帝王猎杀的对象,并无任何寓意,因而倘若替换其中的个别野兽,或者加以增减,将南部兽减少为“㺎旄貘牦,沉牛麈麋”,北部兽减少为“麒麟角端,騊駼橐驼”,亦不影响整体的文意表达。
汉赋名物具有“可增可减性”与“可替换性”,还可以从异文比对中得到证实。例如宋尤袤刻本《文选》卷七《子虚赋》:“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藭菖蒲,茳蓠蘪芜,诸柘巴苴。”⑥[南朝梁]萧统辑,[唐]李善注:《宋尤袤刻本文选》(二),第25-26 页,第207 页。共计11 种植物,“圃”“蒲”“芜”“苴”同属鱼部,押韵自然,声韵铿锵。《汉书》略同,而《史记》、《文选》宋陈八郎本、日本九条本、朝鲜正德本、韩国奎章阁本“芷若”下多出“射干”二字,其中《史记》作:“其东则有蕙圃衡兰,芷若射干,穹穷昌蒲,江离糜芜,诸蔗猼且。”⑦[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第3642 页。如此,植物增加至12 种,读起来“兰”“干”为韵,“蒲”“芜”“苴”为韵,亦朗朗上口,毫无生硬痕迹。宋王观国《学林》卷四以为:“《史记》于‘芷若’字下有‘射干’,《前汉》于‘芷若’字下无‘射干’。顔师古注以《汉书》为是,而《史记》为非。后世文士,尝于此而疑焉。观国按:《子虚赋》此一段数百言,皆以四字为一句,以《史记》之文读之,则用‘射干’字乃成四字一句,于文则顺,于韵则协。以《汉书》之文读之,则去‘射干’字,遂不成句法。以此知《史记》之文为是,而《汉书》之文阙也。”①[宋]王观国撰,田瑞娟点校:《学林》卷四,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149 页。清人浦铣《历代赋话续集》卷二与之相左,认为《汉书》《文选》(引者按:指李善注本)之文为是,《史记》之“射干”为“俗本妄增,有自来矣”②[清]浦铣著,何新文、路成文校证:《历代赋话校证》,第173 页。。其实,无论有无“射干”,都可以读成四字一句,于文皆顺,于韵皆协,并无高下之分。此外,《文选》尤袤本《子虚赋》“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史记》作:“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兕象野犀,穷奇獌狿。”多出“兕象野犀,窮奇獌狿”8 字,野兽数量也从4 种增加至9 种。从文意和韵脚上看,二者皆通。但是《史记》中“蟃蜒”与“獌狿”,似为同一野兽,有重复之嫌。《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称:“无是公言天子上林广大,山谷水泉万物,及子虚言楚云梦所有甚众,侈靡过其实,且非义理所尚,故删取其要,归正道而论之。”③[汉]司马迁:《史记》卷一一七,第3689 页。对于“删取其要”四字,学术界有不同理解,孙少华认为:“《史记》《汉书》所录《天子游猎赋》,亦非司马相如最初原文,而是司马迁根据时代需要进行了删汰。”④孙少华:《<天子游猎赋>的文本书写、知识来源与思想传播》,《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8 年第2 期。如果司马迁曾经删减过《子虚》《上林》二赋,那一定是此类可增可减的铺陈文字。
总之,汉大赋抛弃了《诗经》轻盈灵动的比兴手法,以及《楚辞》婉转清深的美人香草之喻,使用分类展列的方式书写花草、树木、走兽、飞禽、水族,借以反映新的时代气象,是汉帝国“宣威”的手段之一。但有时候铺陈过甚,名物过多,堆砌辞藻,缺乏性灵,也有“繁类成艳”“腴辞害骨”之弊。汉魏之际抒情小赋兴起,楚骚精神回归赋坛,这种铺陈名物、奇字满篇、笨拙而古朴的散体大赋也渐渐走向了衰落。与散体大赋不同,汉代尚有一些以动物、植物为题的咏物抒情小赋,如贾谊《鵩鸟赋》、孔臧《杨柳赋》、班昭《大雀赋》等,代表了另外一种书写方式,则已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了。
- 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其它文章
- 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省级数字政府建设策略
- 河南省人口结构与经济发展耦合关系研究
- 高校专业类课程思政空间阐释与策略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