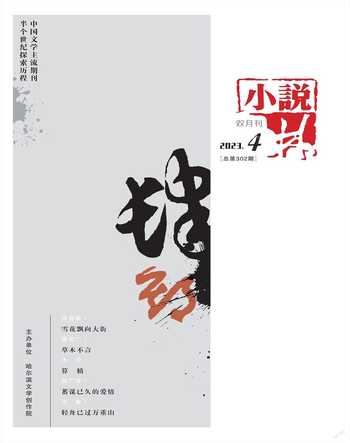案头观米
1964年,一个年轻人背着一卷“破纸”从哈尔滨一路南行。他的目的地是北京。
一路上,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破纸”,这些纸保存下来太珍贵,甚至父亲的命都搭在这上面了。
1945年9月8日,他父亲和骆大昭一同去长春访友,在街头商贩处购得伪满故宫流散的一堆“破纸”。可是,骆大昭知道这些宫中流出的东西必定来历不凡,就动了谋财害命的坏心思,在辽宁营口附近铁路上用匕首将其父亲捅死,带着那一包宫中文物回哈尔滨销赃。但兵荒马乱的年代,想找一个买家也并不容易,还没有来得及出手,就摊了官司。
父亲死后,母亲告发了骆大昭的罪行,骆大昭死于枪下,那卷“破纸”重新回到他家。
上个世纪60年代,挨饿的那几年,母亲就想把这些字画拿出来换钱,她让儿子先到省博打听一下,无奈博物馆工作人员眼拙,拒绝收购。他不得不远赴北京,走进了荣宝斋的大门。
在那卷“破纸”中,最珍贵的要算米芾的《苕溪诗帖》了。该帖虽有残损,但经过故宫文物修复人员据珂罗版影印本修复成“足本”,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一
北宋崇宁五年,五十六岁的米芾成为这个帝国的书学博士。
这个官职不大,从九品,甚至要比他先前的八品官还低一个层级,但却是他人生之中最恰切的工作,他不喜欢繁冗的政务,一生中甚至找不出值得称道的政绩,他痴迷于书画,摹古可以假乱真,创新亦可称一代宗师。历经千载,他仍然是书画舞台上的名角,大浪淘沙过后,他的墨迹至今为人膜拜,年轻人喜欢他的疏狂与张扬,老者欣赏他的笔底波澜,专业人士追求其变化的丰富性,普通爱好者也常以能八面出锋而沾沾自喜。
但越是杰出人物层出不穷,社会竞争也越发激烈,于书法而言,宋代能出类拔萃者,曰苏黄米蔡四家。如果你看到欧阳修、范仲淹等人书法,也会感慨其才气逼人,那么,为何只说四家呢?简单地说,这四个人能代表时代风气,他们在书法艺术方面有创造性,有大突破,而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这些人,在书法上继承传统有余,创新发展不足。
苏黄米蔡四大家,米行三。苏东坡是一个全才,诗词文章艺压群雄,文坛盟主不可撼动;黄山谷为苏学后人,后自立门户,创立江西诗派,书法又是北宋草书的一座高峰;四人中,蔡襄属老同志,开宋人尚意书风的先驱。只有米芾,没参加过科举,没做过大官,冠以“书学博士”,其用功之专,可见一斑。
北宋一朝,仅凭书法博出位而名留青史的,也只有米襄阳一人耳!
二
真正对米芾书法观念有所影响的人是苏东坡。
北宋元丰五年,三十一岁的米芾去拜访苏轼。那一年,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黄州。黄州对苏东坡一生来说,是一个重大节点,文有前后《赤壁赋》,词有《念奴娇》,书法上更有《寒食帖》。而黄州对于米芾来说,也是一种命运的改变。
这是他第一次见到苏东坡,他在《画史》里说:“吾自湖南从事过黄州,初见公,酒酣曰:‘君贴此纸壁上。观音纸也,即起作两竹枝、一枯树、一怪石见与。”
苏东坡在观音纸上画了一幅竹石图,观音纸乃竹纸,不上档次,常用于祭祀,此时偏远的黄州,落魄的苏东坡用一点儿好笔墨也成了奢望。但善书者,不挑肥拣瘦,能在现有条件下活得有滋有味,亦足见东坡先生的生活智慧。
苏轼比米芾年长十五岁,又是名气响彻文坛的人物,米芾见他,如见偶像,这次见面气氛轻松,苏子瞻也是喝酒尽兴,还对米芾讲了“学晋人”的书法之道。这正如高手过招,不需要花拳绣腿,只需会心一击,聪明如米芾者,听后如醍醐灌顶。此后,米芾“承其余论,始专学晋人,其书大进”。
米芾少年学书,是从颜真卿、柳公权入门的,后来也可能受到杨凝式、苏舜钦的影响,和苏轼见面之后,改变了学书路径,由唐至晋,开始有意识的搜罗晋人书法作品,后在丹徒生活期间,甚至把自己的书斋命名为“宝晋斋”。宝晋斋里,至少有王羲之《王略帖》、谢安《八月五日帖》、王献之《十二月帖》,以及顾恺之《维摩天女》几件极珍贵的晋人墨宝。
宝晋斋所藏的《王略帖》,也叫《破羌帖》,是王羲之的一件草书作品,米芾赞其为“天下书法第一”,当然这只是他个人意见,米芾在其著作中有很多类似的武断行为,他就是这般任性而狡黠。
毕竟《王略帖》是他以死要挟才得来的宝物。
王羲之的真迹在唐代已经少之又少了,在宋代能见到数行片纸,简直不要太幸运了。有关《破羌帖》,宋人笔记中记载了一则八卦逸闻。
米芾得知《破羌帖》在蔡京的儿子蔡攸手上,而蔡攸恰好要从米芾所在的真州路过,因走水路,米芾便登船拜见,蔡攸拿出《破羌帖》,米芾見到后,就想用自己收藏的其他书画进行交换,蔡攸哪里肯答应呢!米芾先是一阵哭闹,后来竟然站在船舷之上威胁蔡攸说,你要是不换,我便跳江死给你看。米芾是二王书法鉴赏专家,在米芾面前,蔡攸也要显摆一下,这是人之常情,但没有想到米芾耍起无赖,蔡攸被他搞得头大,就把《破羌帖》给了他,米芾转而为喜。
356年8月,桓温打败羌族首领姚襄,收复洛阳。
东晋偏安东南,北方被前秦大帝苻坚统治,东晋桓温力主北伐,他先平定西蜀,再取中原,两次北伐,最终虽以失败告终,但北伐中一些胜利的消息,还是让南朝知识分子提振士气,毕竟他们多数人还是渴望统一的。《破羌帖》中,王羲之写下“王略始及旧都,使人悲慨深”,写这件作品的时候,王羲之已归隐田园,但他仍进亦忧退亦忧,虽处江湖之远,心系国事不能忘怀,因此深深“悲慨”。这也是其珍贵之处。
南宋时候,陆游也曾临习此帖,并有诗云:“破羌临罢榰颐久,又破铜匜半篆香。”此与羲之悲欢共,心境同。
跳江索帖,有小说家笔法,精彩之处在于人物鲜活,跃然纸上,也印证了米芾不顾体面不拘小节的个性,米芾有“米癫”之称,癫劲儿上来,什么君子,什么小人,人生贵在适意,其他全不在乎。
获得《破羌帖》之后,米芾经常带着收藏的书画,乘一小船泛游江湖,黄庭坚《戏赠米元章》诗云:“沧江尽夜虹贯月,定是米家书画船。”后来,明代的董其昌也效仿米芾,置了一艘自己的书画船。
米芾“赖夺”《破羌帖》这段记载,出自苏州人叶梦得的手笔。而米芾自述说,《破羌帖》是他于崇宁年间在开封以150贯的高价从赵家宗室手中买下的,到米芾手中的《破羌帖》,因为装裱师父手艺不精,已有所破损,但他仍然视若珍宝。因此,也有人说,米芾从蔡家父子手中夺来的不是《破羌帖》,而是谢安的《八月五日帖》,故事情节和这个比较相似。
米芾耍赖,夺人所爱。他连皇帝都不放过,徽宗皇帝喜欢他的书法,命他写一大条屏,徽宗给他准备皇家御用笔墨纸砚,写字的米芾,刷刷点点,激情满满,写完后他向皇帝提了一个要求,说,您的砚台我刚才把它弄脏了,皇上以后恐怕也没法儿用了,不如把这玩意赏赐给我吧。宋徽宗了解米芾的性格,听完会心一笑,便把砚台赏赐给了米芾。米芾也许太激动,毫不顾及砚堂中残留的墨汁洒在衣服上,端起砚台往外就跑,不知道有洁癖的米芾,回家之后,那件衣服还要不要得?
很多人了解米芾见到好物就想“赖夺”的手段,有珍藏的宝物也不敢在他面前显摆,可也有不怕事儿的,薛绍彭便是这样的人。
一次,米芾请客吃饭,并让他再约上几个人凑一饭局,面对米芾摆下的“鸿门宴”,薛绍彭倒是很坦然,他给一个朋友发了一封邀请函,也就是他存世真迹《召饭帖》,他和朋友说,他要带名贵茶叶“密云小龙团”和一件晋人的书法作品以及一幅竹雀图去吃这顿饭,他是不担心米芾来抢的,另外,再把巨济一起叫上,叫他一定要来。宋人的日常生活,也可以从这封信里窥测一二,喝点儿小酒,品品茶,赏读书画,这是风雅的大宋,也是中国文人的一种适意的生活情趣吧。
可是也有人对米芾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
苏东坡从儋州回到中原,准备去常州养老,路过真州,在米芾的西山书院停留数日,给米芾留下不少墨迹,苏轼看米芾那方紫金砚很是不错,苏轼也是爱砚台之人,岂肯放过,便向米芾索要。米芾无奈,他不能驳了师长的面子,再怎么不情愿,也要忍痛割爱了。
可是,那次见面,也不知道苏轼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往后的日子肚子总疼,米芾也给他送过药汤,都没有彻底治愈。一个月后,苏轼到达常州,不久便故去了。
米芾得到这个消息,十分哀痛,写了五首悼念诗。但他对那方砚台也还念念不忘,因为,苏轼说过他死后要用米芾的紫金砚陪葬。送给人家的东西,还往回索要,一般人是干不出这种怪事的。可是米芾能干出来,米芾找到苏轼的儿子索回砚台。然后,他把这件事情记录在一方纵28.2厘米,横39.7厘米的纸上,造就了一件书法史上的珍品《紫金研帖》。其文曰:苏子瞻携吾紫金研去,嘱其子入棺。吾今得之,不以敛。传世之物,岂可与清净圆明本来妙觉真常之性同去住哉。
米芾的理由也有点儿狡辩的意思,他认为苏轼是圣洁之躯,他这方砚台根本不配伴随而去,还不如让它在世上流传下去。米芾的心愿,在近千年后有了回应。上个世纪70年代,考古队清理元大都遗址时,从下水道的淤泥中发现一方风字形的砚台,砚堂有明显的使用痕迹,背后题刻铭文也漫漶不清,但有“此瑯琊紫金石,所不易得……”字样,落款为“元章”。因此有人推测,可能就是米芾当年留下来的紫金砚,但是不是苏东坡曾经要陪葬的紫金砚,就难以断定了。
三
米芾恋物。甚至有点儿病态。
米芾对自己聚集而来的前人书画除了欣赏之外,就是下功夫临摹。其子米友仁跋其临《右军四帖》云:“先臣芾所藏晋唐真迹,无日不展于几上,手不释笔临学之。夜必收于小箧,置枕边乃眠。好之之笃,至于此,实一世好学所共知。”
这段话透漏出米芾对古人作品的病态的痴迷。展于几上,便于品读,手不释笔乃用功之勤,置枕边乃眠,这是个比较鲜活的细节,仿佛一个守财奴,只不过他守护是一种特殊的“财富”。
唐代的书法理论家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察之者尚精,拟之者贵似。”这里的“察”,就是仔细观察,也就是读帖。每一幅书法都有它独特的气息,那或许是字里行间流过的时光沉淀之后的气息。展卷观阅,眼睛盯着一个字,或者一组字,长久不曾离开,人仿佛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但脑海里却在反复揣测古人笔下的速度与激情。这种阅读和如今读小说一目十行是完全不同的,他是通过一个字,一组字,一行字,一整篇字,来感受书写者的生命律动。躺在床上,脑海突然会蹦出曾看过的几个字,没有笔墨,只好用手指在被单上或自己的身体上划来写去,那真是一种不经历过就无法理解的事儿啊。
学书法,除了花功夫之外,还要有科学的学习方法,米芾在前面给后学之人蹚出一条路子,他采用的是“集古字”的训练方法。
米芾启发我们临帖也不必通篇逐字写下来,而是重点锤炼单字笔画,结体,掌握基本规律,而集古字还可以把几个字一组字集合起来,这有点儿临创的意味了,一组字可以写出行气,可以感受到字与字的呼应,以及流动期间的气韵,也就能体会到章法的奥妙,米芾也是这样走来的,自从苏东坡帮米芾指明了学晋人书法的路径之后,不得不说米芾天赋极高,米芾的米,是千家米,最后他用这些各具特点的米,煮了自己的一碗米饭。临摹是书法爱好者成为书法家的必经之路,米芾在王羲之处学会了用笔之道,在王献之那里获得了更大的创作灵感。他善于求变,字的体势大部分是向左侧倾斜,一行下来,偶尔几个右侧倾斜的字,往往起到一行字重心平衡的作用,这也是米芾的特色。
对一件书法作品的临摹,既要造型准确,又要气韵生动,手不释笔的米芾,在对古人书法临摹中完全做到了与原作形神酷似的地步,甚至以假乱真。
沈括和米芾生活在同一时代,他不仅是一位科学家,也是一位收藏家,文人雅聚,大多要把自己的藏品拿出来和朋友分享。一次宴会后,沈括拿出自己收藏的晋代书法家王献之的书法作品,米芾拿过来一看,说,这是我写的。米芾說完笑了,可是沈括却严肃起来,所有人都不相信这是米芾的字。米芾接着说,如果不信,纸缝里应该还有我的印章。众人揭开纸缝,果然有一枚小小的印记。要知道当面揭穿人家藏品是赝品的行为,太不厚道,太不给人面子,自此沈括和米芾就结下梁子了。
米芾交游的人中,有苏东坡、黄庭坚等为人称道的风流人物,也有在历史上被人唾骂的大奸大恶的人,比如蔡京,章淳以及林希,还有一些争议极大的人物,像沈括,这是米芾不辨忠奸吗?还是人在局中,难以自明?
沈括《梦溪笔谈》中品评了当时很多书法家,唯独没有提到米芾。有人就推测和此事有关。事实上,沈括人品确实低劣,不仅气量狭窄甚至阴损,沈括通过打老友感情牌套取苏轼诗稿,他则硬是发扬“科学精神”,在苏轼的诗文中找出很多政治“问题”,成为乌台诗案的始作俑者,差点儿要了苏东坡的小命,但历史和命运也真是难以预测,如果不是苏轼政治上的失意,可能也没有后来的苏东坡。
《梦溪笔谈》没有记载米芾的书法艺术,也没有影响米芾书法在后世的传播和影响,沈括的书法也不错,但又有谁知道呢,又有谁尊为法帖每日临摹呢?
四
正是河豚欲上时,与南京作家顾前、曹寇等游东山启园,在太湖宴饮,席间有河豚一尾,连皮带肉夹起一块吞下,剌嗓子,仿佛鱼鳞没刮干净。他们说河豚皮可养胃,但河豚腹部的皮上有毛刺,翻过来吃会好下咽。
后来看宋人也多有食河豚的记录,但因为河豚有毒性,大多不敢轻易食之,东坡是老饕,不惜为美味而冒死,米芾则没有那么淡定。润州太守杨杰请他吃河豚,他便举棋不定,杨太守不仅笑曰:“你放心吃好了,此乃赝品河豚耳!”
原来杨太守准备的只是与河豚相似的另一种鱼。但此言一出,米芾造了一个大红脸,知道杨太守讽刺他书画作伪的事,好在二人是好朋友,没有伤了和气。
米芾虽曾长时间居于润州,但他对苏州也颇有向往,《书史》云:“姑苏衣冠万家,每岁荒,及迫节,往往使老妇驵携书画出售。余昔居苏,书画遂加多。”米芾一生多次到过苏州,因为苏州人是文人字画收藏颇多,赶上荒年,一些人为了生计,会出来售卖,米芾应该是捡过大漏。为此,他甚至想要请示朝廷,把他调任苏州,但终未成行,这是他一生的遗憾。
但他在苏州也不是没有朋友,葛藻就是其中之一,葛藻常把米芾的临作拿去装裱再进行倒卖,从中牟利。二人同游太湖,多次往返苏州、无锡、湖州等地,而米芾的代表作品《苕溪诗帖》《蜀素帖》以及《吴江舟中诗卷》,都是在这条水路上完成的。
蜀素,是蚕丝之成丝织品,没有染色的,称为素绢,是一种比较名贵的书写材料,它和宣纸有一种共性,存的久一些,会更有利于书画家在上面表现笔墨。刚刚制作出来宣纸,书法家会觉得火气大,绢布也是如此,因为里面含有动物胶成分,需要时间的沉淀之后,胶退化后,才能达到适宜书写的程度。
湖州太守林希邀请米芾访古游山,并拿出家里藏二十余年的一卷蜀素,书法家碰见上好的书写材料往往非常兴奋,米芾兴致一来,在上面一下写了八首自作诗,全篇酣畅淋漓,为其代表作。明代董其昌题跋曰:“米元章此卷如狮子捉象,全力以赴,当为生平合作。”
在这一阶段,米芾还写过《苕溪诗帖》,用笔转折肥美,别有骄色,传至今日,已为行书入门的法帖。《苕溪诗帖》中有“缕会玉鲈堆案”一句,这句多写了一个“会”字,所以在“会”字右下角有个很小的“卜”字,表示这个字是误写,不计入正式的内容中。除此之外,如果仔细读帖,你会发现在《苕溪诗帖》里还有不少字出现补笔现象,也就是说,米芾在写下一笔感觉没有达到效果,就又添补一笔。书法家写字上是有一个大忌讳,一笔下去,果断凌厉,千万不能复笔涂描,否则就给人一种“描”出来的感觉,而不是写的感觉,就成了书法作品的败笔。但米芾为何还要如此?当然是想让字写得更完美了,补上一笔之后,无论在空间、体势上都更舒服一些。但米芾的补笔,不是“描”上一笔,因为他艺高人胆大,处理又极高妙,与全篇秀逸英发气势咄咄的基本格调相吻合,所以并未损害这部名作的魅力。也许米芾就这是这样炫技,他将一直软软的毛笔,在速度和力度的控制之下,跳跃、奔放、迅捷、潇洒、激昂,有音乐的抒情,有舞蹈的旋律,他写出了宋人少有的气势。即如苏轼所言:“风樯阵马,沉着痛快,当与钟王并行,非但不愧而已。”
五
“劳生奔走困粗官。揽镜鬓毛斑。物外平生萧散,微宦兴阑珊。奇胜处,每平阑。定望远。好山如画,水绕云萦,无计成闲。”这首《诉衷情》是米芾填词,其情形好似厌倦宦海,想归隐山林。但当这种机会来了的时候,他似乎還对官场有点儿难以割舍的意思,这一点,他还是没有活出东坡先生的意境。
如有可能,米芾还是希望在朝廷做官的,宰相蔡京是自己的老友,而皇帝也欣赏他的才华,也许米芾根本就不是一块做官的料,他的心也不在这上面,偶发觑觎之心,最终也因为对艺术的狂热迷恋以及外在狂怪表现,而被人视为异端分子。
因此当宋徽宗任命米芾为礼部员外郎的时候,立刻遭到言官对他弹劾,他们认为把一个不拘礼数的人派到礼部任职是对礼部的一种讽刺,米芾虽然为自己辩解,但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米芾为官大小也十几任,但几乎没有可以称颂的政绩。因此他的自我辩白,也未能得到朝廷的理睬。最后他不得不黯然离京,到徐州附近的淮阳军做了军使。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七岁。
也是因为有了礼部员外郎这样一段极短暂的经历,后人才称其为“米南宫”,据说是因为礼部在皇宫的南面,也被称为“南宫”。
米芾在去淮阳军上任的路上,气火郁结,到任之后,便生一场病,头上长了脓疮,继而浑身疼痛,忽烧忽冷。
人在死之前会有预感,尤其是为艺术而生的人,艺术家的直觉超乎常人,对死亡也是如此。
米芾知道自己大限不久,就找人打了一口上等棺材,自己躺在里面,等待死亡的降临。
在等待死神的期间,米芾做了一件令人震惊而又难以理解的事情,他把自己一生费尽心思搜寻的古人书画都付之一炬。
如果说三十年前的那一把火,米芾是悔其少作,觉得年轻时候的作品还不够成熟,这也可以理解,杜牧在晚年也烧掉了自己大部分的作品,这或许也可以视为作家对自己人生负责的一种行为。
尾 声
2021年春节,我沿长江游览金山、焦山、北固山,后专程去丹阳寻访米芾遗迹,可惜只见到了米芾书法公园,有点儿索然。
回到镇江,在北固山甘露寺闲游,揽过长江气吞万里如虎的景象,也品咂刘备和孙尚香相亲的旧地之后,下山途中,突然想起米芾当年初到润州,因为没有房产,只好先寄居甘露寺,后来他去湖州,给人写了一幅书法作品,人家赠他一块石头,他回来后雕刻成一座山形的砚台,米芾非常喜爱,名之曰砚山,后来米芾用这个砚山和苏舜钦的孙侄换了一块地,建造了自己的宅子,取名为“海岳庵”。
米芾有一个名字叫海岳外史,就从此处得来。
如今,海岳庵也无处寻觅了。
归来途中,想起本文前面提到的年轻人,1996年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们都是化名:丁心刚,父亲丁征山,母亲孙曼霞。
这是应该被铭记的一家人啊。
作者简介:梁帅,在《大家》《山花》《大益文学》《延河》《湖南文学》《小说林》《香港文学》《世界文学》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出版长篇小说《补丁》、短篇小说集《马戏团的秘密》等,获萧红青年文学奖,天鹅文艺奖,黑龙江省文艺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