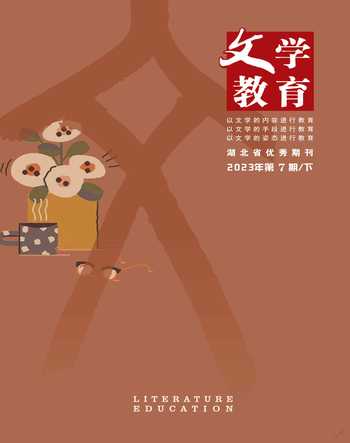王靖《英国文学史》写作中的传记模式研究
张珂
内容摘要:王靖的《英国文学史》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英国文学史,这部文学史的编写不以作品文本为中心,而以传主(即作家)为中心,自觉运用了传统中国人所熟悉的史传模式,力求将外来学术话语与中国本土学术传统相结合。文学史与传记模式相结合,旧识充当了新知的媒介,比较成为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作为中西文化在剧烈碰撞之时中国文人的一种特殊的话语策略,既显示出一种自发的比较意识,也反映了过渡时代传统文类的一种新变。
关键词:文学史 传记模式 王靖 《英国文学史》
20世纪初,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伴随着中国国民教育的起步而肇始。随着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觉醒和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确立,以文学史为主干课程的文学教育模式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开始大量编写中国文学史,而且也开始尝试外国文学史的书写。王靖写作于1917年夏,出版于1920年6月的《英国文学史》是中国人编写的第一部系统的英国文学史,该书分六章叙述了从古代至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发展的主要历程,系文言写成。这本文学史自觉运用了传统中国人所熟悉的史传模式,力求将外来学术话语与中国本土学术传统相结合,对于我们理解20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学术的变迁与发展有着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王靖《英国文学史》传记模式之表现
文学史这种著述形式虽是20世纪现代西方学术的舶来品,但史的书写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19世纪末以来,由于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失败,社会上出现了很多“史”的著作。不单单是文学史,各种亡国史、立宪史、革命史、独立史等层出不穷。中国人崇尚“以史为鉴”,国弱民衰的历史转折时期尤其体现了这种学术风向。梁启超就写过《意大利建国三杰传》等史述,对能在时代风云变换之际担当重任的伟人尽抒仰慕之情。知史以明智,史的书写是时代的迫切需要。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史传传统,最初著中国文学史者,几乎不约而同地转身向中国历史中寻找资源,并从《史记》《文苑传》等历代史书中受益甚多。在他们看来,文学史这种著述模式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目录学、史传、诗文词话、选本等本土学术。在接受和理解异域新知的历程中,处于新旧时代交替的知识分子自然选择了回过身去借鉴他们最熟悉的历史资源。王靖的《英国文学史》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作为中国人追求的异域新知的一部分出现的。
首先,这本文学史的写作语言是文言,对于书写异域文学历史的外国文学史而言,这本身就充满了一种向传统中国学术靠拢的意味。从当时的写作环境上来看,1917年2月,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刚刚发表,自清末开始的文言与白话之争逐渐激化。1920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规定中小学教科书一律采用白话,白话才压倒文言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这个历史背景来看,王靖写作和出版英国文学史之时,先进者已然走向白话,而守旧者依然抱守文言。如编者王靖这般是国内较早接触和研究外国文学的学者,似乎更易接受文言白话之变。但他却如林纾等古文家一般选择了文言写作。他在书中对林纾的文章和译作也多有推崇。因此,以文言书写外国文学史不仅显示出过渡时代学术话语的未定状态,也表明了学者个人的学术选择。以后,随着文学革命的深入展开和白话文的推广,不但文学创作采用白话,学术著作的书写采用白话也成为时代大势。据笔者考证,编者王靖1920年以后亦有关于文学的白话文章出现。而此时,他选择采用文言写作英国文学史,原因作者在书中没有提及,但这种话语策略却天然地使文学史这种舶来品染上了“我邦”色彩,无异于文学史书写的一种归化方式,从客观效果上说有利于其文学史传记模式的运用。
其次,从写作体例上看,这部《英国文学史》分为五卷,每卷均以每一时代文学及文学家作为总卷名,如“英国古代之文学及文学家”、“英国十四世纪之文学及文学家”、“英国伊里沙伯时代之文学及文学家”等。每卷在概述之后便转向具体的文学家,但并不具体分出章节,而是皆以文学家之名划分界限,例如卷三为“英国伊里沙伯时代之文学及文学家”,下列文学家包括“佛兰司培根 Francis Bacon”、“马罗 Christopher Marlowe”、“威廉沙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彭琼生 Ben Jonson”(注:皆按原书样貌,下同)等。以如此密集的文学家分章列目,显示出编者以人为中心的编写理念。此书序二指出,王靖有著述“世界文学史”的伟愿,因而作为“附赠品”,书后附有《美国文学家小史》和《丹麦文学家小史》,分别为美国文学家15人,丹麦文学家1人(安徒生)写史立传。纵观这样的目录安排,给人最深的印象就是突出人的地位,以文学家串联文学史。
在叙述每位文学家时,编者更是采用了中国史书中传统纪传体的模式,姓甚名谁,生卒年月,家族谱系,主要事迹等,不一而足。以其中写罗伯特·彭斯(书中译名为:乌拉勃保司)一节为例,摘录其中章句如下:
“乌拉勃保司十八世纪末叶诗家也。以一千七百五十九年生于亚菲迩Ayrshire。……以言情写景之作独多。悱恻其情。明白其灵。正则其情。玲珑其声。芬芳烈馨。秾华远清。澹白而不厌。亭立而不矜。数语足以尽之矣。如A Fond Kiss,To Mary in Heaven,My Luve is like a Red, Red Rose诸篇。皆言情之作业。长篇如Cotter s Saturday Night, Tam O Shanter二篇。尤为人所赞赏。……一千七百九十六年七月二十一日卒。年三十有一。”[1](P50-51)
中国古代的史传传统崇尚实录,修史遵循质直与简约的原则。不少史家主张“史为本,文为末”,反对“溺于文辞”,显示了对历史真实性品格的追求,但也有学者很早就意识到了“文”的重要性,认为修史者应该把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记述得生动逼真,有感染力,史官也需要发挥文才。中国传统史书的感化力量,也多来源于其中的人物传记,而且史官的文才如何也关系到史书的流传。王靖这部文学史的写作以人物传记为中心,编者在书写时的处理方式也显示出他对文辞、文藻与事实、实录关系的理解。显然,编者以史家之眼和文家之笔对彭斯的生平和著作进行了勾勒。全书重点在于论人而非论文,对人物著作只是在“传”的叙述中提及,专门的著作评价及文本赏析笔墨着实不多。
第三,从写作范围上看,由于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对文学的理解并不仅仅包括纯文学作品,而是指用文字书写的一切典籍文献。在王靖写作的年代,文学观念正处于传统与现代的转换过渡时期,来自西方与literature对应的纯文学观念仍没有完全被学界所接受。因而王靖此书的写作范围,除了有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家,亦有政治家、历史家、哲学家等。如书中收有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等历史学家的小传。这种选择既有利于编者自如运用史传模式,亦可视为对传统学术理念的一种依赖。
二.王靖《英国文学史》对传统传记模式之突破
尽管王靖的《英国文学史》有着诸多传统史书传记模式的痕迹,但作为特殊时代的学术著作,必然反映着时代的变化,带有时代的印记,显示出对传统传记模式的突破。
第一是对文学地位认识的转变。晚清以来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的“小说界革命”,文学救国特别是小说救国的观念大行其道。此书序言云:“余尝言文学左右世运之力,奇伟无伦;起衰振敝,咸文学是赖。尤其善者,且足以变国俗,移人情。……王靖之欲为国人介绍世界文学史,毋亦有忧于是,而欲发扬文学之光辉,使之照耀人世乎!”[1](P2)编者在多处行文中强调了文学与国运的关系:“英国至十四世纪。政治、宗教、始稍稍昌明。民气亦稍开。然非文学左右之。不及此也。故国运盛衰。关系文学靡鲜。”[1](P4)再如,编者在谈狄更斯的小说时慨叹:“迭氏细察社会情形。著为绘声绘影之小说。使读者内省自疚。不敢为非。政治风俗乃于无形中渐渐感化。向善国富兵强。今日称雄于世界。小说与有功焉。呜呼小说岂小言詹詹之类耶。”[1](P87)这段文字正面凸显了小说的救世功用,反映出时人对小说价值的高度认可,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小说界革命的深入人心和研究者文体观念的现代转变。
第二是运用以中释西的比较模式。此书虽靠近中国传统批评,但在具体行文上多采用以中释西的比较模式,使读者获得了对中外文学的崭新认识。例如,传统的《文苑传》常常涉及人物及作品风格的比较,但基本局限在一国文学范围内。王靖创造性地以中国文学典故比附英国文学,从而将比较的视野扩大到了国别文学之间。例如,谈到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家爱狄生“生性嗜酒,奋髯箕踞,雅有刘伶风范”;称柯勒律治与华兹华斯的交往“雅有管鲍分金之谊”;湖边诗人“可与吾邦虎溪三友相颉顽也”。除了人物之间的品评比较,还有文体风格的类比。如认为史诗Beowulf“格调似弹词”;华兹华斯的诗“神韵淡远,用字亦浅现,如白香山之诗,老妪都解”;德·昆西的笔记作品“雄丽隽永,似中国六朝小品文字”。有时还以“歌、行、吟”这种传统的中国古诗样式指称英国的诗歌。不难看出,编者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染,又对英国文学有着较深入的了解,因此旧学新知相互激发,使其看到了中外文学之间的互通性。
“以中释西”实际上是一种自发的比较文学批评视野。在东西文化激烈碰撞的时代,知识分子更强烈和更深刻地感受到了异文化的冲击,但同时又试图以自身的主体意识去消解异文化的陌生感。这种比附尽管有局限性,却是特定时期认识外国作家的便捷手段,未尝不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话语策略。如后来蒋梦麟所说:“对于欧美的东西,我总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这就是从已知到未知的办法。根据过去的经验,利用过去的经验获得新经验也就是获得新知识的正途。”[2]P68在早期的外国文学知识的传播与书写中,由于编者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学底蕴,使得其介入外国文学伊始,就自然获得了比较的眼光。这种自发的比较意识,也成为这一时期外国文学知识编译的普遍特色。
三.文学史中传记模式的普遍性与必然性
王靖《英国文学史》对于传记模式的借重显示了民初文人对外国文学知识摄取与消化,但其写作在内容与体例上并非完全独创。他既非这样做的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1904年至1907年,王国维在《教育世界》上以文言发表一系列关于歌德、席勒、莎士比亚、斯蒂文森、托尔斯泰等人的传记文章。稍早于王靖,孙毓修曾出版《欧美小说丛谈》(商务印书馆,1916年)。《欧美小说丛谈》虽名为小说丛谈,实质也是在为文学家做传,内容侧重人物生平、时代背景和文学风格的叙述。王靖在写作《英国文学史》时对此书多有借鉴,甚至有些评论甚至直接来源于孙毓修。稍晚于王靖,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1918),亦是文人传记、作品批评等材料“杂和做成”。此外,郑振铎、沈雁冰《现代世界文学者略传》(《小说月报》连载,1924年)、孙俍工《世界文学家传略》(中华书局,1926年)、王隐《世界文学家列传》(中华书局,1936年)、钟岳年、曹思彬《世界文学家像传》(上海书店,1949年)等都有类似的编写倾向。可见,相似的时代背景和共同的问题意识决定了他们较为一致的写作策略。这些传记汇编形式的书籍,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外国文学的择取和理解,体现了当时人们的知识趣味。
对于身处中外文化剧烈碰撞,新旧变革时代的学者来说,采用此种话语策略,除了中国强大的史传传统的影响,也许还可以从王靖此书的序言找到线索:“一国文学,多为一国国民性之表征 ……所谓‘沉潜刚克舍英人殆末与归。然其所以至此实其文学士,能发扬其纯良之国民性,而锡其同类也。……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今王靖既著英国文学史,以饷国人,冀收潜移默化之效,余亦祝其有改造国民性之能。”[1]P1
近现代以来,国民性问题乃是时代的焦点。以改造国民性为重心,梁启超引进了“政治小说”,希望借域外文学的冲击,提高国民觉悟,健全民族性格。国民性的问题甚至被提到了国家存亡的高度。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不遗余力地批判民族的劣根性,以国民性改造为己任。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伴随着国民性的焦虑。20世纪初对中国人的文学史书写产生影响的日本人所写的文学史著作,如古城贞吉的《支那文学史》,也都讨论国民性问题。时代对“国民性”问题的关注使得英国文學史的书写被赋予了神圣的救世意义。由是,此书的出版被寄以扭转学风、改造国民性的厚望极其自然。在编者看来,既然文学为国民性的表征,那么关键在于“国民”即“文学家”的书写,刻画文学家的性情身世的纪传体,无疑成为一种最佳书写方式。
作为一部用文言写成的《英国文学史》专书,本书既是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国人介绍了英国文学的历史发展、重要文学家的生平和创作。文学史写作当中传记模式的运用,讽时谏世、臧否人物,纵横比较,无不极力贴近与延续中国的史传传统。文学史也因此甚至被置换成了文学家传记的汇编。即不以作品文本为中心,而以传主(即作家)为中心。虽有不少局限,但可以看出,编者是经过了自身的消化和理解对英国文学做出描述和品评的。它的出现虽也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和局限,但作为民初进一步学习外部世界的一个明证,依然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进步意义。文学史与传记模式相结合,旧识充当了新知的媒介,比较成为与世界对话的途径,作为中西文化在剧烈碰撞之时中国文人的一种特殊的话语策略,既显示出一种自发的比较意识,也反映了过渡时代传统文类的一种新变。
参考文献
[1]王靖.英国文学史[M].上海:泰东书局,1920.
[2]蒋梦麟.西潮[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外国文学与国民教育关系研究”(19YJCZH249);中央民族大学自主科研项目“作为知识生产的外国文学与现代中国国民教育”(2022QNPY20)。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