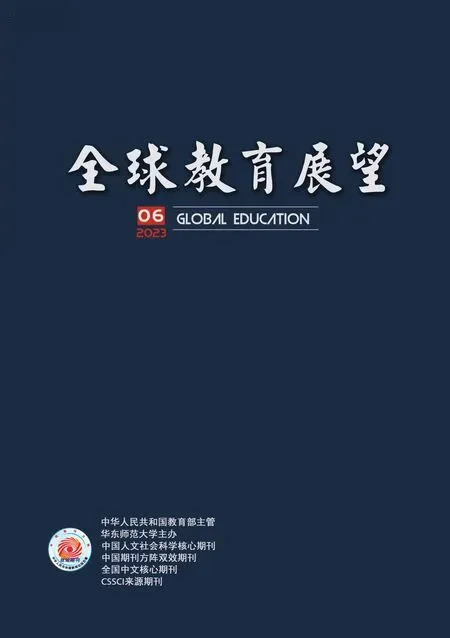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个体生命及其生命课堂建构
刘济良 赵文慧
人的生命首先是作为个体而存在的,生命课堂所追寻的“生命在场”理应是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在场”。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性的审慎和沉思中,赋予个体生命一种独特的诠释视角,同时拓展了生命课堂的多维审思的理论视域。基于此,生命课堂作为以生命为逻辑起点、视生命发展为旨归的特殊实践活动,理应立足个体生命,基于后现代主义视域下个体生命所彰显的精神品性去审思生命课堂的建构,从而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活力。
一、 审思视域:后现代主义的哲学转向
后现代主义在对传统形而上学命题合理性的否定和主体的解构中,对现代哲学进行“重塑启蒙”,以期摆脱思维的预先设定,释放被技术理性裹挟的个体生命,以生成性主体取代传统形而上学的先验主体,以生活世界替代遮蔽“存在”的超验世界,弥合人与他者、与自然的对立。纵使后现代主义存在着否定性、破坏性向度的局限,但其肯定性的、建设性的内涵在对现代性的审慎和沉思中拓宽了人类思维的苍穹。以维特根斯坦式(Wittgensteinian)“家族相似”去追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彼此相似的思想主张,呈现出以下主要特征。
(一) 理性的“陨落”——崇尚非理性
从笛卡尔(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到洛克(Locke)的“理性是最高的法官”、康德(Kant)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以及黑格尔(Hegel)将“绝对理性”作为万物存在之根本,西方普遍理性的张扬在为人类拓展前进道路、为世界“除魅”的同时,日益演变为理性的僭越,在人类前进之途中开掘着“理性的非法运用”之陷阱。理性中心主义以“人是理性的动物”这一不证自明的假定,宣扬理性的权威地位和无穷的绝对力量,无限制的理性成为限制个体生命的工具。
后现代主义者敏锐地察觉到理性正逐渐成为万物的法则,因而转向对“理性至上”话语体系的质疑与批判,直指其理性霸权所孵化的知识暴力和极权主义将理性的效力视作唯一并无限放大,在对非理性的“压迫”与“征服”中遮蔽非理性的存在与价值。在对理性近乎“病态”的“幻影崇拜”中,个体生命沦落为僵化、机械、干瘪的生命样态,异化为“苍白的概念动物”。人是兼具理性与非理性的存在,非理性是理性的孕育之基和内驱之力,自后现代主义推翻理性权威之后,西方哲学家们开始对非理性投入关注,例如海德格尔(Heidegger)的“思”、拉康(Lacan)的“欲望”、德里达(Derrida)的“文本”、福柯(Foucault)的“历史”、巴塔耶(Bataille)和克里斯蒂娃(Kristeva)的“异质性”。后现代主义在对“绝对理性”的“祛魅”与非理性的关注中,消解人类理性中心主义的“自鸣得意”,体现着对个体生命自我认识的深化与自我意识的觉醒。
(二) 主体的解构——转向主体间性
后现代主义对主体的解构是对特定意义上的主体进行批判与解构,他们所主张解构的是传统的片面、抽象、虚妄的主体,所主张消解的是狭隘的、走向极端的主体性,从而建构流动的、生态的、交互的、创造的后现代主体。后现代主义彰显着非中心化的哲学立场,关注非中心化、零散化、具体化的主体,更重视个体及其生命体验,同时强调人的内在关系的实在性。从普罗泰格拉(Protagoras)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到康德的“人的理性为自然立法”,人类将主体置于存在和历史的中心,现代性主客二元论的基本倾向“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1]。后现代主义将这种二元对立的“镜式哲学”视为西方哲学深陷“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狂肆之迷途的症结,否定主客对立的分离状态,强调个体与世界、与他者的互联关系,主张对传统的片面、抽象、虚妄的“异化的主体”进行解构。正如胡塞尔(Husserl)所言:“每一个自我——主体和我们所有的人都相互一起地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上,这个世界是我们的世界,它对我们的意识来说是有效存在着的,并且是通过这种‘共同生活’而明晰地给定的。”[2]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主体中心论”这一人类主宰意识所隐含的“毁灭性的威胁”,在虚化话语权威和去中心化的同时倡导重建个体生命间和谐圆融的关系,由二元对立的主体性转向有机共生的主体间性关系,从分离、孤立、封闭的单子式存在过渡到“共在”的人文学状态,从而客观地认识世界和了解自身。
(三) 本质的消解——走向生成性
后现代主义反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认为知识与文化不证自明、固定不变,具有绝对的“阿基米德点”,本质主义是其合理外推。本质主义者在对事物内在、固有属性的寻觅过程中忽视事物的变化与多样,具有独断论倾向。而后现代主义反对这种消解创造、否定生成的静态思维,拒绝“终极真理”的极权与压迫,认为“不存在绝对的清楚明白,不存在直接的给定,不存在永恒的理性结构”。[3]从福柯的“总体性话语的压迫”,到德里达的“形而上学暴力”、拉康的“主人话语”,后现代主义对“唯一正确的解释”和“独一无二的真理”保持苏格拉底式(Socratic)的警觉,试图走出“根据的根据”之樊篱,以更开放的视野来看待世界,关注“过程的主体”“创造性的主体”,认为“现实世界是一个过程,过程就是各种现实存在的生成”[4]。后现代主义主张消解本质,认为“任何一个追求某种事物的本质的人都是在追逐一个幻影”[5]。在对“本质先定,一切既成”之权威话语的解构中,后现代主义转向对“一切将成”之生成性过程的关注,关注个体生命充满可能性与创造性的生活世界和生命历程,主张克服本质主义以确定性的符号统摄不确定性的生命实践之虚无期望,认为个体生命处于无限的生成、创造过程之中。
(四) 总体性的颠覆——关注差异性
本质主义在对共性本质的强调中试图消融个体生命之间的差异,将其归结为同一的、均质的、封闭的抽象存在。不同于西方现代性对差异的“打压”,后现代主义则对他者的相异性表示肯定。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性的审慎中将矛头指向总体性的宏大叙事,否定这种吞噬个体性和差异性的极权化的理论模式,试图用差异对抗总体性哲学。怀特海(Whitehead)直指“划一的福音”的危险性,视差异为人类精神冒险之旅的“驱动力和原材料”。福柯指出,西方文明危机之重要原因就在于“回避我们现实的差异”,希望人们意识到“我们的理性是话语的差异,我们的历史是时间的差异,我们的自我是面具的差异”。[6]利奥塔(Lyotard)在对总体性宏大叙事的批判中“向统一的整体开战”[7],试图为差异性的合理性正名。后现代主义在对总体性宏大叙事的批判中转向对个体性和差异性的关注,反对普遍化的秩序、总体性话语对个体生命的压制,主张摒弃这种致使“世界的平庸”和“风格的凋零”的“同一逻辑”,强调以“差异逻辑”来把握事物的异质化和多样性,关注个体生命之间的差异性、多样性与开放性。
二、 聚焦个体: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个体生命画像
后现代主义在对现代性的“划界”中试图将传统哲学抽象出来的“异化的主体”复归生活世界之中,同时赋予我们理解生活世界中作为个体而存在的具体的人一种独特的诠释视角,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个体生命彰显着别样的精神品性。
(一) 个体生命的非理性
“就思维过程而言,非理性是理性认识的先导和契机……就认识形式而言,非理性形式是理性形式的辅佐,是进取性、创造性认识活动不可或缺的手段。”[8]理性和非理性的生成、发展也表征着人类精神的变革,其中理性多居于主导地位。当理性被高捧至时代舞台中央,并将“严酷的奴隶状态强加于每个人”时,个体生命在理性的“独唱”中陷入扁平化、抽象化的困境。后现代主义转而崇尚非理性,以期释放被理性霸权所遮蔽的自然生命始源力量,拯救异化为理性附庸的灵动的生命。个体生命的非理性是指抛开知识与理智、逻辑与推理等思维意识,追求或然的、非逻辑的诸如想象、欲望、情感、意志等生命表达方式,是每一个个体生命与生俱来的创造的根基和超越的内驱力。面对后现代主义对非理性的推崇,我们应辩证地看待理性与非理性的内在关系,避免深陷绝对拒斥理性或绝对推崇非理性的极端化思想,应充分意识到个体生命的发展历程并非合逻辑、有秩序的简单线性累积的过程,而是交织着非连续性、无序性、复杂非线性的流变过程,在对非理性之内在力量的关注中,避免理性霸权对个体生命的僭越和人性的异化。
(二) 个体生命的共生性
怀特海以“融摄”解释万物如何彼此互联:“正是因着融摄,万物互即互入,我们影响他人,也被他人所影响。‘我们与其说存在,不如说是共在。’与其说是独生,不如说是合生。”[9]后现代主义将个体生命视作“关系中的自我”,倡导以主体间性消弭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抵牾。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个体生命关系并非外在的、偶然的、派生的,而是内在的、本质的和构成性的。从历时态的角度来看,人的生命是一个文化与历史、精神与意义的共在体,在物种进化和精神升华的交叠中迈向新的文明,个体生命的历程总是牵涉过去、包含现在、指向未来,个体生命的历史演进离不开生命经验与智慧的沉淀与薪传,个体生命的现时经验也深刻地影响着自身和群体生命的未来。从共时态的角度来看,个体生命在与他者、他物的联系中建构着自身的存在,实现着个体与“类”的融合,个体生命向“类生命”的跃迁。可以说,生命是一种共生性的存在,以个体生命为纽带交织缠绕在过去、现在、将来的时间场域之中,联结着主体间的生命关系,生命在共时态与历时态的有机融合中才能走向自由和谐的“类生命”境界。后现代主义主张超越二元对立、自我关涉的狭隘视野,以人与自然和谐的“家园感”和主体间温情的“亲情感”取代掠夺与控制的欲望,消解“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迷途狂想。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强调“对一切存在、尤其是人的存在作一种关系性的、生态性的理解”[10],主张在尊重、融合的基础之上达到和谐共生、持续发展的状态,个体生命通过他者、他物来自我确证,个体生命是置身于关系网络的共生性存在。
(三) 个体生命的生成性
现代本质主义思维的根本性弊端在于试图将人同人的世界割裂,从而便于人们用理性去洞悉与个体生命相对峙的世界及其运行的“本质规律”,并将其视作规约个体生命的金科玉律。“人能够达到的境界,这在本质上是不可计算的。”[11]后现代主义反对本质主义“静观”个体生命的僵化思维,将人从“确定性的存在”的桎梏中解救出来,认为人并不存在“前定本性”,而是未特定化、未完成的、开放性的“可能之在”。个体生命在时间里流变,并不存在永恒章程和精准算法。正如格里芬(Griffin)所说:“未来与现在并不是和过去与现在那样,以一模一样的方式发生着内在联系,因为,这种暗含着把未来按过去的样子安排的观点会拒斥自由。”[12]生命的流变并非时间工厂里复刻标准件的机械流水线,朝向生命“范本”的临摹也难以描绘出生命的旖旎景象。后现代主义推崇创造性的活动,怀特海指出“‘生成过程’是一种走向新颖的创造性的进展”[13],福柯认为人所要做的“不是去发现自己,发现秘密的内在本质,而是去不断地创造自己,将自己造就成一个自主的主体”[14]。格里芬指出:“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至少在这个星球上如此)。”[15]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个体生命不再囿于现实性、确定性的枷锁,而是被赋予更多创造性的生成空间,在“去找另一条路”的创造与生成中从“被动的享乐接受者”走向能动的价值创造者。
(四) 个体生命的不可尽述性
德勒泽(Deleuze)和伽塔里(Guatarri)以“块茎”喻指解辖域化、不规则的非层级化的开放系统。“块茎状思维模式”在“侧生”与“迂回的分支”中破坏既定秩序,呈现出开放性、多元化、差异性及非地域化的指向。后现代主义崇尚这种开放、多元的思维方式,主张文本释义的多重性和解释的无限性,主张摒弃由单一理念阐释文本、观照世界的封闭、僵化的思维模式。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个体生命并非止步驻足于自然“作者”的初始设定,而是基于自身独特的理解与诠释不断生成的。加达默尔(Gadamer)视人为理解的存在,同时这种理解“并不纯粹是重复同一事物的活动”[16],而是隐含着不确定性和不可尽述性。基于镶嵌在特定历史性之中的“先入之见”和不可通观的解释视角,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不尽相同,生命寓于人身之中,但人类对生命的了解始终是有限的,难以用精辟的语言、确切的表达、准确的公式来穷尽生命的奥秘。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个体生命是不可尽述的,现实的目光与言语难以尽述困扰人类已久的“斯芬克斯之谜”,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生命存在,潜藏着无限的发展可能,同时也都是生命文本的演绎者和解读者,在对生命奥秘的探索中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生命故事。
三、 走向“个体生命在场”: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生命课堂建构
教育是直面生命的活动,理想的教育旨在基于生命、循于生命、达于生命,可以说,生命是教育的真正尺度。教育所直面的是一个个独特而灵动的生命个体,对个体生命之意蕴的理解与把握是教育实现对个体生命润泽之必要前提。课堂作为教育润泽生命的重要场域,旨在实现“生命在场”的生命课堂理应智性审思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个体生命特性,在对个体生命特性的合理把握中优化课堂教学,从而使课堂充满生命的气象,焕发生命的活力,实现“个体生命在场”之美好课堂愿景。
(一) 关注个体生命之非理性,构建多层次的课堂目标体系
个体生命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统一体,理性为生命之舟掌舵护航,非理性是生命涌动之源泉。个体生命的发展得益于理性的撑托,但“理性的非法运用”将异化为禁锢个体生命的工具,从而限约着个体生命的整全发展。面向个体生命而展开的生命课堂也应在理性与非理性的钩沉中保持清醒与警惕,避免落入对于理性或非理性的单向度认知偏差,既注重以理性精神促进个体知识技能的增长,还应充分发挥非理性对于理性的补充与调节作用,在课堂教学中将二者适切地结合并统一于发展生命这一根本目标之上。
因此,生命课堂的课堂教学目标设计应兼顾个体生命的理性之维与非理性之维,构建多层次的课堂目标体系。生命课堂应把握理性与非理性间相互渗透、相互促进的整体性关联,促进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精神素质的协同发展,在课堂教学中既注重个体生命理智的积淀与思维的跃迁,同时观照其感性世界,避免遗落对于个体生命的非理性因素的眷注与呵护。在课堂教学中积极探索发挥个体生命诸如直觉、顿悟、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因素的有效路径,在生命力的充分彰显中规避个体生命沉沦于理性编织的“科学世界”之中而异化,充分发挥直觉、灵感、想象、情感、意志等非理性力量,彰显乐学尚思的生命气象和昂扬进取的丰沛意志,进而引导个体生命实现从单维认知积累到多维统协发展的跃升,在“人化”与“化人”的课堂教学实践中,达成课堂所承载的促进个体生命整全发展的愿景期许。
(二) 遵循个体生命之共生性,促成“共生态”的课堂交往
后现代生态论的观点认为,“个人都彼此内在地联系着;因而每个人都内在地由他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他所做出的反映所构成。”[17]无论是加达默尔的“视域融合”观点,还是罗蒂(Rorty)的“主体间协作性”思想,都体现着后现代视域下个体生命存在方式由“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朝向他者“相互嵌入”的根本性转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21年11月发布的《共同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一种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中提出,“要为教育构建一份新的社会契约,通过契约精神维护与践行‘教育是一项共同利益’。”[18]通过这一重新构想实现与他者、与世界的重建,帮助我们共同创造一种共享的、彼此依赖的、可持续发展的未来。面对时代对人、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生命课堂也应重新审思课堂交往,注重引导个体生命超越自我中心主义,在朝向他者开放的多向交往共进中促成主体间的理解与对话,以“和而不同”的学习共同体取代单子式的孤立存在,促成“共生态”的课堂交往。
一方面,课堂交往作为基于课堂这一特定时空的交往活动,应旨在实现生命与生命的相互交融与摄养,而要达成这种交往首先应引导个体生命朝向他者开放。“现代性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它的排他心态,闭锁心态。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转变看作从闭锁心态向开放心态的转变,其核心是对他者的态度问题。”[19]朝向他者开放的态度蕴含着对他者不同于“我”之差异性的尊重和欣赏,从而促成个体生命之间的吸引与交往。正如加达默尔所言:“在同他人说话的时候,我们不断地进入到他人的思想世界;我们吸引他,他也吸引我们。”[20]这种朝向他者敞开的开放态度是促成主体间双向理解、精神融汇的课堂交往的必要前提,是形成主体间“共生共荣”的课堂生态的重要保障。因此,生命课堂的构建应注重培育个体的“觉他意识”和“容他思维”,引导个体生命朝向他者而敞开自我,为实现主体间朝向彼此开放的、“生命在场”的言说与倾听奠定基础。
另一方面,生命课堂应构建“交响式沟通”的学习共同体,达成主体间“共生共荣”的课堂愿景。课堂交往在主体间的对话中展开,后现代主义者的对话是“一种人际发生的过程”[21],是达成主体间“视域融合”的重要途径。因此,生命课堂应秉持着开放性、包容性的对话原则,鼓励并接纳学习者关于同一事物的多重理解,构建“交响式沟通”的学习共同体,在主体间“视域融合”中实现多元声音交响、谱写灵动生命乐章,在充盈活力与温情的课堂交往中构筑出“没有人拥有真理而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的迷人的想象王国”[22],从而实现对话的“无限展开”,帮助个体意识到课堂是“我们”共同成长的精神殿堂,在“共生态”的课堂交往中达成主体间的情意交融、精神共契、智慧共享。
(三) 立足个体生命之生成性,彰显教学设计的开放性与创造性
怀特海视“现实事物的共同体是一个机体,但它又不是一个静止的机体,它乃是生成过程中的一种不甚完善的状态”[23],同时这种过程“在本质上是创造的”。[24]课堂教学作为直面个体生命的活动,是“动态的生命体”,课堂教学应顺应个体生命的生成性,以灵活性和创造性的教学设计,营造出情景化、可再生性的课堂生态,走出教育僵化之壁垒。
一方面,教学设计应坚持适度预设,为个体生命成长“留白”,营造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开放、宽容的课堂氛围。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个体生命并非拘泥于既定的“原初本性”,而是不断生成的、富有创造性和审美旨趣的具体存在。过度的限定与规训阻挡着个体生命通向自由精神之通衢,致使精神生命逐步枯萎。个体生命存在于对美好生活的自由向往之中,以不断超越的“乌托邦精神”朝向“未知之地”前行。教学设计应尊重个体生命的生成性,以灵活的教学实践自如应对课堂情境的变化,追求充满生长气息的“可能课堂”而非一味地固守着预设的“完美课堂”,在个体生命自由生成、创造的涡流中同“控制、预测、操纵”的机械教育观决裂,使生命课堂朝向教育的“美丽风险”开放,释放学习者的无限可能。
另一方面,生命课堂的教学活动应在教师的创造性教学的基础之上,激发学习者自我塑造与创造的内在精神力量。创造性教学是相对于“操作性教学”而言的,其目的不仅在于实现有效教学,更重要的是提升个体生命的创造力。因此,生命课堂的教学设计应创设灵活开放的教学情境以鼓励学习者主动参与课堂,唤醒个体生命发展与创造的内驱力,发展个体生命可持续的认知与创造能力,引导个体生命将课堂所学进行再迁移、再创造,从知识学习者转变为价值创造者,进行生命能量的持续拓展,在潜能释放、自由生成的生命课堂中自主选择、勾勒生命发展的可能图式,以提升个体生命面对变动不居的世界的适应力与回应力,从而回归教育作为“一种拥有最高不确定性的智慧行动”[25]的本质,显现出每一个个体充满活力与创造性的生命灵性。
(四) 理解个体生命之不可尽述性,突显审美导向的课堂评价
面对封闭的总体性思维,后现代主义更强调多元性和差异性,例如利奥塔的“纷争哲学”就是“保存差异而不是压制差异;它追求理性的多元性而不是一种单一的理性”[26]。正是因为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而且这种差异是无法穷尽的,人的生命才呈现出复杂的、不可尽述的特点。后现代主义视域下的个体生命是一种面向可能敞开的非给定性、不可预见的独特的“能在”,面向个体生命而展开的生命课堂也应洞见生命之不可尽述性,尊重个体生命的独特性与差异性,立足生命的多维性与复杂性,以鉴赏式、引导式的评价,充分发挥课堂评价的育人功能。
鉴于此,生命课堂应以审美的眼光去看待个体生命之间的差异及其发展的不确定性,形成因材施评、以评促教的发展性课堂评价观。从课堂教学的视角去理解,差异即“多样化,意味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学习风格:直觉的、感知的,图像的、语言的,归纳的、演绎的,线性的、非线性的,外向的(同他者合作)、内向的(反思型),等等”[27]。个体生命之间的差异正是课堂彰显活力的基石,审美导向的课堂评价即以欣赏的态度去看待个体生命的差异,以关怀的态度去促进个体生命的发展的引导式评价,从而为个体生命的发展预留诗意的想象空间。然而,“在传统的教育思想中,学生的‘学习’被定义为‘进展’,教育就是按照预设的路径朝着固定的教育目标推进。在这里,教师倾向于把‘差异’视为‘偏差’——特定的学生不符合特定的标准,教师借助特定的标准来处置这种差异。”[28]面对人这种发展中的“能在”,课堂评价不应简单地以一种“欠缺”的统一标准去衡量个体与标准之间的偏离程度,而应以发展性评价、多元化评价去“看见”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进步。教师应以审美的态度超越基于标准的评价技术,形成基于美感的评价艺术,自觉涵养以评价促发展的评价智慧,通过课堂评价引导个体生命欣赏自我、激发潜能,在开放的评价系统中引导个体生命拥获发展之无限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