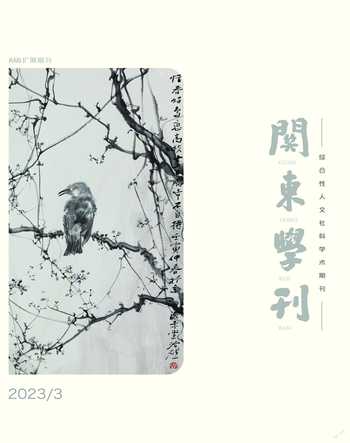茅盾论“鸳蝴”的态度变迁及其关于“通俗文学读者”问题的思考
[摘 要]茅盾在1920年视鸳鸯蝴蝶派为封建丑恶势力,到了1928年却主张要表现通俗文学读者的痛苦和情热,这一奇特转变源于他主持《小说月报》改版时的受挫经历,而更深刻的根源则在于其对中国文学现代抒情传统的自我反思的深化,即如何认识和反映现代文学所朝向的“大众”主题。通过相关书信和文论,可发现茅盾的文学观一步步从“精英”到“大众”的缓慢而深刻的转变。因此,《从牯岭到东京》中他主张文学要重视和表现占读者大多数的“通俗文学读者”群体即“小资产阶级”(主要指小市民、小商人等),其实是从过来人的角度给更新的文学者(革命文学家们)提建议,这也是对于中国文学现代抒情传统强调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本质特征的重新发现。
[关键词]茅盾;鸳鸯蝴蝶派;现代抒情传统;通俗文学读者;小资产阶级
[作者简介]曾道扬(1992-),女,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博士研究生(广州 510275)。
从1920年主持《小说月报》改版,到1928年公开主张重视和表现占读者大多数的“通俗文学读者”即“小资产阶级”的文学,茅盾在短短八年间经历了从文坛新思想代表到文坛落后“反动力量”代表的剧变。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茅盾对通俗文学的态度有着看似180度的大转弯:1920年的茅盾视鸳鸯蝴蝶派(后文简称“鸳蝴”)为封建丑恶势力,1928年的茅盾却声称要表现通俗文学读者的痛苦和情热。这样一个奇特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呢?本文将从中国文学的现代抒情传统的内部变迁来探讨这个问题,认为相对于古典抒情传统的士君子或士大夫的精英化和个体化写作,现代文学抒情传统自新文化运动以后,就全面确立了从写作的主体、读者和语言形式都要求大众化、市民化的现代性诉求。但这个“大众”或“市民”的具体阶层身份或政治身份又当如何定义?这就衍生出了中国文学的现代抒情传统或现代抒情政治的诸种方向或纷争。而在这些不同方向或纷争中,一个极具热点和政治性的文学主题就是“小资产阶级”问题。茅盾从1920年到1928年在论“鸳蝴”中所经历的态度的巨大转变,与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大众”指向的再认识过程密切相关,在这个认识变化中,“小资产阶级”问题构成了其中的重要一环,并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代文学抒情传统的自我反思的深化。本文兹作详论。
一、茅盾论“鸳蝴”:文学观的转变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发生了一个范式上的重大转型。如果说古典文学抒情传统是士君子、士大夫的精英化方向,那么,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开启的白话文写作便是平民的、市民的大众化方向。正如何光顺在谈到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时所指出的:“胡适对于白话文学史写作的提倡和对于文言文学史的贬抑则体现出更强烈的近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文学学科观念,那就是文学的语言必须贴近平民生活,而非那种典雅的、贵族的。”
何光顺:《文学的疆域——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科自觉》,《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贴近平民生活,具有强烈的近代启蒙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和文学学科观念,就是新文化运动的方向;但这个方向,还涉及到作家本人是否能夠成为大众或平民的一员,也就是以精英的视角为平民写作,还是自觉为平民的身份以写作平民或市民的生活?从这个角度看,胡适虽然提出了要写平民生活的文学观念,但其个人却始终是精英化的,这也是胡适在后来延安的革命文学与国统区的资产阶级文学的分化中,终究进入资产阶级文学的阵营,而某种程度上未能实现真正的平民化文学写作的重要原因。
作为左翼革命文学的重要代表,茅盾很自觉地贯彻了新文化运动的方向,即扭转了古典文学过于典雅和贵族化的写作,不断沉入市民大众以及工农大众的写作中。茅盾从文学生涯的起点开始便是一个坚定的“经世致用”派,这样的文学立场充分表现在《现在文学家的责任是什么?》(1920)《文学和人的关系及中国古来对于文学者身份的误认》(1921)《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1921)等一批早期文论中。茅盾主张新文学在内容上要服务社会、“足救时弊”
茅盾:《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茅盾全集》第十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48页。,不是表现个人,而是表现全社会、全民族甚至全人类的痛苦和期望,创造“血与泪”
茅盾:《介绍外国文学作品的目的——兼答郭沫若君》,《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250页。写成的平民文学;在形式上,主张中国文学要转型为新文学,放弃旧文学的体式,重点学习自然主义实地考察的精神和冷静客观的态度。
在这样一个为平民写作的现代性方向的自觉中,“鸳蝴”就成为其中的一个焦点话题。“鸳蝴”的写作原本也是为小市民、小商人的平民群体服务的,但在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平民为大众的写作中,“鸳蝴”又很大程度上被贬斥到平民文学的对立面,而其第一个罪名就是以“游戏”“纵欲”为旨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观就被看作是“罪大恶极”的。如茅盾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中就批判“鸳蝴”或是把文学当成消遣品,以“自快其‘文字上的手淫’”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226页。,罔顾真实人生;或是把文学当成商品,“只要有地方销,是可赶制出来的;只要能迎合社会心理,无论怎样迁就都可以的”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232页。。在驳斥吴宓的《“写实小说之流弊”?》(1922)里,他批判礼拜六派“把人生的任何活动都当作笑谑的资料”,“称赞张天师的符法,拥护孔圣人的礼教,崇拜社会上特权阶级的心理”,因此这些作品都“进不得‘艺术之宫’”。
茅盾:《“写实小说之流弊”?》,《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303页。而到了《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1922),他们变成了“现代的恶趣味”,“污毁一切的玩世与纵欲的人生观”,“对于中国国民的毒害是趣味的恶化”,
茅盾:《真有代表旧文化旧文艺的作品么?》,《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311页。因此他在《反动?》(1922)里定性这些通俗文学“决不是‘反动’,却是潜伏在中国国民性里的病菌得了机会而作最后一次的——也许还不是最后一次——发泄罢了”。
茅盾:《反动?》,《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313页。“这病菌就是‘污毁一切的玩世的纵欲的人生观’。”
茅盾:《反动?》,《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314页。
鸳蝴派的第二个罪名便是其旧式(或华洋杂陈的)小说体式,这是从反对中西方的旧式传统,而务求文学当为现代的大众服务的要求而出发的。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1922)中茅盾认为鸳蝴派小说有三种创作体式。第一种是旧式“章回体”,这种体式不仅呆板、没有美感,而且把“描写”理解成“记账”,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226-228页。人物因此完全立不起来。第二类是“章回体”的初级改良版,停留在对西洋小说拙劣的模仿,华洋杂陈,无法摆脱旧式小说的弊病。第三类在模仿西洋小说上有了更多进步,但仍旧是摆脱不了旧体式的脚镣,而且在思想上虽然也学新文学表现人生,但因为“没有确定的人生观,又没有观察人生的一副深炯眼光和冷静头脑”
茅盾:《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231页。,画虎不成反类犬,人道主义变成了肤浅的慈善主义,描写无产阶级变成讽刺无产阶级。
在这个时期的茅盾看来,鸳蝴派在思想上可谓祸国殃民,在创作上也达不到其所追求的以西洋(主要是自然主义)为标准的新文学理想,因此自然要被打入冷宫。但是在短短八年之后的《从牯岭到东京》,茅盾的文学世界出现了一个有趣的反转,过去他与通俗文学可谓势不两立,批判厌恶之词溢于言表,可在这篇备受争议的主张“描写小资产阶级”的文论里,我们看到茅盾把“小资产阶级”理解为以小市民、小商人为主体的通俗文学读者群,而且还要求新文学为通俗文学读者服务,用他们的语言、写他们的生活、表达他们的痛苦和情热,“新文艺忘记了描写它的天然的读者对象。你所描写的都和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相隔太远,你的用语也不是他们的用语,他们不能懂得你,而你却怪他们为什么专看《施公案》、《双珠凤》等等无聊东西”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第191页。;“如果你能够走进他们的生活里,懂得他们的情感思想,将他们的痛苦愉乐用比较不欧化的白话写出来”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191页。;“我们的新文艺需要一个广大的读者对象,我们不得不从青年学生推广到小资产阶级的市民,我们要声诉他们的痛苦,我们要激动他们的情热”;“为要使新文艺走进小资产阶级市民的队伍,代替了《施公案》、《双珠凤》等,我们的新文艺在技巧方面不能不有一条新路。”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193页。
茅盾的这个转向,代表了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新文学面向大众和平民写作的深度发展,也表明了一种现代抒情传统,它要求懂得以小市民、小商人为主体的情感思想,表现“他们的痛苦愉乐”,而且应当以“比较不欧化的白话写出来”,
茅盾:《從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191页。“要声诉他们的痛苦”,“激动他们的情热”。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193页。这是现代抒情传统或现代抒情政治的平民化维度的展现,新文学不再只是把通俗文学读者等小资产阶级看作是对立物,而将其纳入了文学应当服务的大众层面。这种对小资产阶级的纳入,也是大众群体范围的扩大,是文学为建立一种革命的新的统一战线的自觉。这样,茅盾就借时新的“小资产阶级”的名头,别出心裁地讨论了新文学的“读者”问题。他主张新文学要重视通俗文学的读者,要把通俗文学的受众挖来革命文学的阵营,他并未放弃对“鸳蝴派”文学思想和创作手法的批判,却似乎在过去好文学均以西洋(尤其自然主义)为标准的“五四”旧路上做了调整,指出一条仍有待探索的既能拥有新文艺的思想和手法,又能够取悦通俗文学读者的新文艺(革命文艺)之路。因此,这个看似180度的大转变中茅盾有不变有变、不变的是茅盾改造旧文学、建设新文学的理想;变的是茅盾对旧文学读者的策略,从过去忽视读者的“大多数”、一味“鹜新”
鲁迅:《鲁迅致周作人》1921年8月25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09页。,到现在重视读者的“大多数”。
二、《小说月报》改版受挫:精英主义文学观遭受质疑
茅盾这一意味深长的转变,背后不仅是一代文豪的思想成长史,更重要的是揭示或折射了中国文学现代抒情传统内部关于作者、读者和文学书写形式随着社会和时代变革而不断演绎的历史。这段茅盾个人的思想成长史及其折射的现代抒情传统内部演绎的历史,是与茅盾《小说月报》改版后在出版社的受挫经历和来自通俗文学读者们的反馈密切相关的。董丽敏发表于2002年的研究成果《〈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为我们发掘出了这段历史的一角。
这篇论文立足点是探讨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主编之位的历史真相,我们从中得知几个关键的信息。一是改版《小说月报》让年轻的茅盾陷入了商务印书馆内部的人事纠纷和经营策略纠纷里,成为牺牲品。在茅盾1920年刚入职商务印书馆和接手《小说月报》时,商务印书馆处在张元济主持的时代,在办刊方针上更有文化情怀和理想主义色彩,年轻的茅盾还幸运地获得了“不能干涉我的编辑方针”
茅盾:《革新〈小说月报〉的前后》,茅盾、韦韬:《茅盾回忆录》上,北京:华文出版社,2013年,第142页。的“尚方宝剑”
董丽敏:《〈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茅盾在这时接手《小说月报》及其所获得的独立编辑权,实际上都还是精英主义的文学观念所主导的,即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以茅盾为代表的一些文学作者虽然已经有强烈的以文学启蒙民智的意识,但对于自己的写作面向什么样的大众,却还并未有清醒和具体的认识。
茅盾这种精英主义的文学观,受到了来自商务印书馆内部高层的挑战。在1921年,胡适介入商务的运营,王云五以胡适私人面目的特殊身份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王云五的走马上任让“商务的经营策略正在发生裂变”
董丽敏:《〈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办刊方针从文化和商业兼重而日趋倾向于市场需求,重视营利,重视鸳鸯蝴蝶派的小市民读者群。王云五甚至不惜以“阴谋”骗过沈雁冰的眼睛,创办了通俗刊物《小说世界》,重新取悦对《小说月报》改版怨声载道的小市民读者群,造成《小说月报》和《小说世界》对峙的局面,这自然是西化的、清高的启蒙者沈雁冰所不能容忍的,沈王二人注定不能并存。茅盾与王云五的关系逐渐从微妙不合转变为具体冲突,王云五最终以“内部审查”
董丽敏:《〈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制度的提出和实行确立了商务高层对于商务刊物的控制权,削弱了沈雁冰等人的编辑权,导致主编们纷纷离职。“沈雁冰离开《小说月报》主编位置,其实是商务内部高层为了确立威信与普通编辑争夺编辑权的结果,沈雁冰不幸成了人事纠纷的牺牲品。”
董丽敏:《〈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二是《小说月报》的改版可以说是不成功的。一方面是旧文学读者市场怨声载道,他们看不懂新文艺的论文,更不想看这些论文,“读者全然不知什么人是某文学家,什么是某文派,则无论如何愿意之人不能不弃书长叹”
茅盾:《茅盾致周作人》1921年10月22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7页。。“据实说,《小说月报》读者一千人中至少有九百人不欲看论文。(他们来信骂的亦骂论文,说不能供他们消遣了!)”
茅盾:《茅盾致周作人》1921年8月11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1页。,以至于“联名对商务投了‘哀的美敦书’”
章锡琛:《漫谈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商务印书馆九十年(1897-1987)——我和商务印书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15页。。另一方面是改版得不到新文学主流的认同,鲁迅批评“雁冰他们太鹜新了”
鲁迅:《鲁迅致周作人》1921年8月25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09页。,“专注意于最新之书”
鲁迅:《鲁迅致周作人》1921年8月6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04页。,“维新维得太过”
鲁迅:《鲁迅致周作人》1921年8月6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04页。,陈独秀劝茅盾“放得普通(通俗)一些”
茅盾:《茅盾致周作人》1921年10月12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4页。,胡适则劝茅盾“不可滥唱什么‘新浪漫主义’”
胡适:《胡适日记》1921年7月22日,胡适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19-192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94页。、不要滥收缺乏经验和写实的空泛的创作。因此,尽管茅盾很早就意识到激进的文学追求和读者市场之间的断裂问题,并不断想方设法保住杂志的销量,但显然在这种两头不是岸的局面中无法给商务高层以未来销量稳定的信心,“难以真正实现旧有读者与刊物新格调之间的对接,《小说月报》读者群未来的流失应该是意料中的事。这一缺憾是致命的,也正是商务下决心撤换沈雁冰的根本原因。”
董丽敏:《〈小说月报〉1923:被遮蔽的另一种现代性建构——重识沈雁冰被郑振铎取代事件》,《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6期。
这在沈雁冰的人生中必定是一个重大的受挫经历,因为过于激进的编辑策略,他的职业生涯和文学理想遭受了双重挫折,不光丟了主编的高位,而且也引来新文化先驱的质疑和批评。笔者认为,这一挫折经历必定导致茅盾对新文学如何发展的看法有大调整,经过爬梳相关材料,笔者找到了沈雁冰思想策略调整的轨迹。
三、从“精英”到“大众”:茅盾思想演变的轨迹
《小说月报》从1920年第一期开始半革新,到了1920年底茅盾接过主编职位后,就从1921年第一期起进入了“完全革新”的快车道。可在当年八月给周作人的书信中,新官上任不足一年的茅盾便在向前辈抱怨革新之难:“据实说,《小说月报》读者一千人中至少有九百人不欲看论文。(他们来信骂的亦骂论文,说不能供他们消遣了!)”茅盾:《茅盾致周作人》1921年8月11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1页。
这种消极的情绪恶化到九月份,演变成茅盾要提出辞职的程度:“《小说月报》出了八期,一点好影响没有,却引起了特别的意外的反动,发生许多对于个人的无谓的攻击,最想来好笑的是因为第一号出后有两家报纸来称赞而引起同是一般的工人的嫉妒;我是自私心极重的,本来今年揽了这捞什子,没有充分时间念书,难过得很,又加上这些乌子夹搭的事,对于现在手头的事件觉得很无意味了。我这里已提出辞职,到年底为止,明年不管。”
茅盾:《茅盾致周作人》1921年9月21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2-33页。显然年轻气盛的茅盾一时无法接受这个挫败的局面,“求效心甚急,似乎非一下成功,就完全无望”
茅盾:《茅盾致周作人》1921年10月15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5页。,想扔下这已经“无意味”的“捞什子”
茅盾:《茅盾致周作人》1921年9月21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3页。,做他喜欢的文学工作。
但是茅盾的辞职显然没有得到批准,因为高梦旦和周作人的鼓励,他决定再试一年:“关于《小说月报》编辑一事,自向总编辑部辞职后,梦旦先生和我谈过,他对于改革很有决心,对于新很信,所以我也决意再来试一年。”
茅盾:《茅盾致周作人》1921年10月12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4页。“辞职事现在取消,再试一年看;先生(指周作人——笔者注)教我奋斗”,但茅盾的自尊心看来只够支撑一年:“现在且领教下一年水磨工程,再看如何。如再一年而无效验,无论如何,无颜为之矣。”
茅盾:《茅盾致周作人》1921年10月15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5页。
主编茅盾开始向通俗读者市场做一些让步和妥协。他采取加量不加价的营销手段保住了杂志的销量:“俄国文学号内容很不行,但销场倒还好,大概一般读者被厚重的篇幅迷昏了。上海人所谓‘卖野人头’,似乎中国卖野人头是行得通的”。
茅盾:《茅盾致周作人》1921年10月15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5页。
同时他决心听取前辈和同行的意见,计划在新一年的编辑方针上要勒住一味趋新的快马,适当“通俗”:“前天见仲甫先生,他说可以放得普通(通俗)一些,望道劝我仿《文章俱乐部》办法,多收创作而别以‘读者文艺’一栏收容之。我觉得这两者都是应当的。”
茅盾:《茅盾致周作人》1921年10月12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4页。“仲甫先生谓普通一点,乃指程度不妨放低之意,如论文,史传,创作登载标准,不妨用初步的浅显的,以期初学者可以入门;此意弟以为很是。”
茅盾:《茅盾致周作人》1921年10月22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37页。
陈独秀的建议让茅盾开始煞费苦心地做了很多工作以期引导初学者入门。在1921年10月22日给周作人的信中,他就说到计划在《小说月报》上登一本《西洋小说发达史》,目的是让初学者了解西洋文艺。在次年3月10日给姚天寅的信中,他又提到应读者来信要求,准备编几本研究文學方法的入门书籍,内容包括文学原理、文学流派的历史、文学的国别史和文学家研究几个方面。当年11月10日茅盾又在给马鸿轩的信中反思到,每期杂志顺带讨论一个文学家的做法失败的原因,是国内大部分读者对于西方文学的流派发展过于陌生,因此“忽然提出一个作家”
茅盾:《茅盾致马鸿轩》1922年11月10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94页。,容易因为过于陌生而失去深入了解的兴趣。
但茅盾的“水磨工程”看来还是不够成功的。1922年9月20日他在给周作人的信末尾提到《小说月报》比1921年销量又下降了,言语之间颇为失意:“尚有三期,未必即能有多大影响,挽回些什么。”
茅盾:《茅盾致周作人》1922年9月20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84页。在11月10号给马鸿轩的信里他又说到《小说月报》失意的局面:“哪知上半年试验的结果,不惟不能有益,反减少了大多数读者对于本刊的兴趣”
茅盾:《茅盾致马鸿轩》1922年11月10日,《茅盾全集》第三十六卷,第94页。。
从这批书信可以发现,茅盾前后主要从两个路子来改善《小说月报》的销量:一是“卖野人头”的促销伎俩;二是把大量注意力放在听取读者需求、向初学者引介西方文学、形成杂志和读者教学相长的模式,但显然均未能挽回颓势。
在《小说月报》编辑方针的调整之外,茅盾还不停地开拓新路。这原是周作人提出的,他认为打倒“礼拜六派”最好的办法是再办一个通俗易懂的小刊物,把“礼拜六派”的读者吸引过来,同时教化他们,提高民众的思想。因此,当1922年夏天王云五以吸引和教化“礼拜六派”的读者,以求最终铲除这些通俗刊物为理由,向茅盾提出再办一个通俗刊物时,茅盾选择了跟这位对手合作,这是他一开始同意给《小说世界》供稿的原因,尽管后来事实证明这都是王云五的“诡计”。
茅盾改版《小说月报》的工作最终黯淡收场。但这段经历显然让茅盾对新文艺如何贴近读者、争取读者这些被唯新是求的新文学家们所忽视的问题有了深刻的思考和丰富的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它们清晰地体现在茅盾思想成熟阶段的文论里。
1925年,在无产阶级文学开始在国内萌芽的时候,先知先觉的茅盾发表了《论无产阶级艺术》一文。在这篇旨在厘定“无产阶级艺术”概念的冗长的文章里,我们注意到,茅盾由苏联何以无产阶级艺术独盛的现象,谈到了无产阶级艺术产生的条件,并重点谈到“社会的选择”如何起到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社会的鼓励或抵拒,实有极大的力量,能够左右文艺新潮的发达。有许多文艺上的新潮,早了几十年发生便不能存在与扩大”,“有许多已经走完了自己的行程的文艺思潮,因为不能与当前的社会生活适应,便不得不让贤路,虽有许多人出死力拥护,仍是不中用,也便是这个道理了”。
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505页。因此茅盾认为,在资产阶级仍然支配一切的当今世界,艺术品的发生和传播受制于占社会主体的资产阶级受众的利益,无产阶级艺术因为不合于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发生和传播势必受到资产阶级的抗拒和压迫,“一定要被资产阶级的社会选择力所制裁”
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505页。,这是当今只有苏联最多无产阶级艺术的原因。在这个说法里,作为市民大众的通俗文学读者还没有得到重视。
茅盾对于苏联无产阶级艺术的认识,也可看成是茅盾的夫子自道。在两年前的改版工作里,正是社会的选择(占社会大多数的旧文学读者的阅读偏好)严重阻碍了新文学的普及和传播,无论茅盾如何“出死力拥护”,“仍是不中用”,
茅盾:《论无产阶级艺术》,《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505页。最终商务还是要撤主编,出版新的通俗刊物,向通俗文学市场妥协。
而到了1928年的《从牯岭到东京》,茅盾饱含激情地写下了这些“逆风而行”的句子:“我们应该承认,六七年来的‘新文艺’运动虽然产生了若干作品,然而并未走进群众里去,还只是青年学生的读物;因为‘新文艺’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为地盘,所以六七年来不能长成为推动社会的势力。现在的‘革命文艺’则地盘更小,只成为一部分青年学生的读物,离群众更远。”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190-191页。“你所描写的都和他们(小资产阶级)的实际生活相隔太远,你的用语也不是他们的用语,他们不能懂得你,而你却怪他们为什么专看《施公案》、《双珠凤》等等无聊东西,硬说他们是思想太旧,没有办法;你这主观的错误,不也太厉害了一点儿么?”“如果你能够走进他们的生活里,懂得他们的情感思想,将他们的痛苦愉乐用比较不欧化的白话写出来,那即使你的事实中包孕着绝多的新思想,也许受他们骂,然而他们会喜欢看你”。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191页。“为要使新文艺走进小资产阶级市民的队伍,代替了《施公案》、《双珠凤》等,我们的新文艺在技巧方面不能不有一条新路;新写实主义也好,新什么也好,重要的是使他们能够了解不厌倦。”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193页。
这完全可以看成是茅盾对这段受挫经历的深刻反思,也是茅盾从1920年到1928年思想完全转型和成熟的最大明证,其要义在于从精英到大众,从一开始“加量不加价”的不愿妥协的哄骗手段,到仍有着强烈“启蒙教化”色彩和“精英”姿态的引导初学者入门看西洋书,再到如今让自己成为他们、表达他们、成为他们肚子里的蛔虫,“走进他们的生活里,懂得他们的情感思想,将他们的痛苦愉乐用比较不欧化的白话写出来”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191页。。茅盾“通俗化”的策略可见一步步从西洋“艺术之宫”
茅盾:《“写实小说之流弊”?》,《茅盾全集》第十八卷,第303页。走进庸俗市井,他最终放弃了稍显稚嫩的“启蒙”姿态,走下精英的宣讲台,尝试走进曾经互相怨恨、不共戴天的通俗读者群体的内心。尽管文艺如此迁就社会、精英如此妥協于大众是否可行和值得仍是个待讨论的问题,但茅盾终究完成了自己思想上的一个巨大的跨越,并由此深刻影响了他的政治生命和他与左翼文坛的关系,其对茅盾本人的影响是长远和深刻的。
四、茅盾与“小资产阶级”问题:对通俗文学读者的重新定义
这样一段历史的考证,为我们发掘了一条理解茅盾和“小资产阶级”问题的新路。在这篇有着深刻政治动机和政治意蕴的文论里,茅盾从开篇一直絮絮叨叨谈自己的创作和对“左稚病”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183页。的异议,到了最后的第七节和第八节却笔锋一转,放下政治不说,开始对国内文坛发表意见,并且十分突兀地提出了“读者”这样的政治味道很轻,却更像文学市场、文学销售的问题,这显然出自他从过来人的角度给更“新”的文学者提建议的目的。陈建华在谈到中国现代文学的抒情传统时,曾经强调要以情感和审美形式为重,并弱化政治性。他还援引章培恒在《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中的观点,指出其否定了“把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庸”
章培恒:《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兼及“近代文学”问题》,《不京不海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588页。的以1917年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文学史分期法,而“重申文学的‘感情’和‘美的形式’的重要性”,强调文学应表达“个体”的感情。
陈建华:《抒情传统与古今演变——从冯梦龙“情教”到徐枕亚〈玉梨魂〉》,《文艺争鸣》2018年第10期。但无论是章培恒还是陈建华,他们让中国文学的现代抒情传统疏离于政治性的做法,也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历史的现实。事实上,政治与情感的分立、对峙和纷争及其造成的现代文学复杂矛盾的样貌,才是中国现代文学抒情传统的真实一面。
以茅盾为例,当他最初负责《小说月报》编辑时,他过多地以政治或政治批判为本位,这导致了其对人情或人性及其适当的通俗化的表现形式的忽略或轻视,只有当他认识到这种过于对立的错误时,他才重新审视通俗化的“鸳蝴”派的意义。正是由于这种认识的深化,使他敏锐地感觉到太阳社、创造社搬运苏联和日本的最新马克思主义理论,排挤“同路人”作家,鄙薄“五四”文学,试图在文坛卷起文化批判的做法,与他初出茅庐时在《小说月报》大谈“新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批判鸳鸯蝴蝶派何其相像,都是在走着趋新逐时,同时罔顾大多数读者接受度的老路:“事实上是你对劳苦群众呼吁说‘这是为你们而作’的作品,劳苦群众并不能读,不但不能读,即使你朗诵给他们听,他们还是不了解”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189页。,“结果你的‘为劳苦群众而作’的新文学是只有‘不劳苦’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来阅读了”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189页。。这就揭示出了那种将政治和情感对立的写作,反倒导向了这样的文学不能被普罗大众所广泛接纳,最终导致了文学的政治批判功能也无法实现。而这就需要认识到,文学需要读者,政治运动也要有呼应者,文学领域的“革命”活动更是,总要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方能有社会影响和革命效果。因此成熟阶段的茅盾站在了当年周氏兄弟和陈独秀、胡适的位置,建议革命文学家们不要重蹈他当年改版《小说月报》失败的覆辙,要把占据社会大部的“鸳蝴派”旧文学读者拉拢成为革命文学自己的读者。他认为这样才是在中国大地,尤其上海滩这样的地方卖杂志、谈文学的生存之道,也是实现其文学宏愿的发展之道。
茅盾在同一篇文章里反对“标语口号文学”,更重要的原因也是读者不喜欢、不欣赏也不接受“标语口号文学”:“俄国的未来派制造了大批的‘标语口号文学’,他们向苏俄的无产阶级说是为了他们而创造的,然而无产阶级不领这个情,农民是更不客气的不睬他们;反欢迎那在未来派看来是多少有些腐朽气味的倍特尼和皮尔涅克。不但苏俄的群众,莫斯科的领袖们如布哈林,卢那却尔斯基,托洛茨基,也觉得‘标语口号文学’已经使人讨厌到不能忍耐了。”标语口号文学所导致的结果,是“被许为最有革命性的作品却正是并不反对革命文艺的人们所叹息摇头了。”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茅盾全集》第十九卷,第188页。这与当年鲁迅等“五四”先驱批评茅盾“鹜新”
鲁迅:《鲁迅致周作人》1921年8月25日,《鲁迅全集》第十一卷,第409页。何其相像。因此,茅盾反对“标语口号文学”,与讨论“读者”问题一脉相承,其实都是从过来人的角度给新文学者提建议,希望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放下不受欢迎的“标语口号文学”,学习为大众喜欢的文学表达形式。
由此我们更可以进一步认定,茅盾提出所谓“小资产阶级”文学的逆风之举,决不是政治立场出现了问题;相反他是在做“劝谏”工作,对象既包括年轻的正在犯“左倾盲动”错误的党,也包括时兴的革命文学阵营。而时至今日,当我们重读这样一份忧愤深广的文献,或许可以放下缠绕它多年的政治争议,发现其被掩盖的生命力,那就是茅盾无意中在这样一个革命文学试图吞没“五四”文学的时代风口,提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超时代的问题,即精英思想如何迁就通俗文学市场。在古代中国,经史台阁之文与稗官野史之说原本就是“文学”的两大陌路;到了现代,从“五四”到革命文学,似乎也重复了古老的精英通俗泾渭分明的历史轨迹。文学者和知识阶级的精英主义立场没有实质上的改变,被口诛笔伐的鸳蝴派和十里洋场的海派文学,被长期排斥在现代抒情政治或抒情传统的时代主题之外,却又独自舞蹈、自成一景,现代文学的图景也由此呈现出各自为营的分裂局面。
茅盾恰巧因居于上海滩商务印书馆的高位,碰上“五四”新文学的浪头,同时自己又是处在革命漩涡中心的共产党员,这样一个政商文合一的身份和复杂多元的文化环境让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文学实践经历,并由此提出了一個独树一帜的问题,它的不合时宜引来了数十年的争议,却保留了其在另一个时代的生命力,指出了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可能性:精英思想是否应该迁就社会通俗势力,应该在多大程度上迁就;精英与通俗是否能够合流,通俗文学读者是否真的如1920年代的周作人、茅盾们所愿,能够在接受文学教化的过程中逐步向精英靠拢。这些他们当年尝试失败或未来得及尝试的可能性,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可拓展的广阔空间,笔者认为这是茅盾与“小资产阶级”这个话题在今天仍有待发掘的生命力所在。
五、结语
从1920年到1928年,茅盾从口诛笔伐鸳蝴派的年轻主编,转变成公开主张文学要为通俗文学读者服务的成熟文论家,这样一个奇特而有趣的大转折,源于《小说月报》改版失败的受挫经历所导致的从“精英”到“大众”的跨越性思想转变。这让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再次佐证了茅盾之提倡“描写小资产阶级”并不是政治立场出了问题,相反是一个文坛过来人在给后起的革命文学家们提建议。数十年来,茅盾与“小资产阶级”的话题均缠绕在意识形态争论的漩涡中,但茅盾对“小资产阶级”概念的独特理解(以小市民、小商人等通俗文学读者群为主体)及反思其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抒情传统中的位置,却为我们提供了理解这一问题的另一个重要的面向。从总体看来,茅盾固然在讨论政治,却又不仅仅在讨论政治,他更是在探寻应当如何启蒙,在古老中国大地上如何追求和实现现代性,寻找从中国古典抒情传统的士君子、士大夫式写作向中国现代抒情传统的大众化、平民化写作转向的道路,思考精英思想如何迁就通俗大众。因此说不尽的茅盾和“小资产阶级”问题其实浓缩了一代“五四”先驱的思想历程,有着丰富而深刻的意蕴,仍有待我们后来者继续思索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