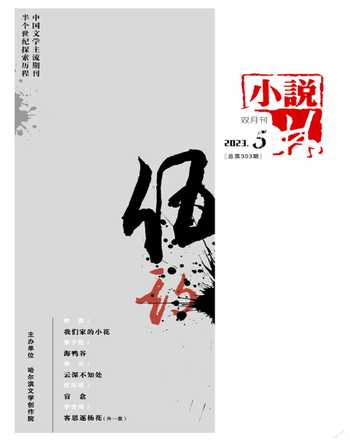苏轼二札
研一条老松烟,写幅扇面,取东坡《赤壁赋》中的佳句:“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我喜欢这段,能消暑。写完之后,再看,与苏处在似与不似之间,最是妥洽。
日常书写的笔墨最有人情味。觀东坡手札和写其他法帖的感觉完全不同,便在于此。我用东坡字法一遍又一遍地抄写他的诗词文章,不觉寒来暑往过了三秋。它既是消磨时光的依赖,也是壮大自己神经的良方,于是,在烦乱中获得一份宁静,于溽热里偶遇凉风,悲愤之余也见一丝希冀,这也是书法的秘密。
《题王晋卿诗》
《题王晋卿诗》写于元祐元年(1086年),苏轼51岁。
这一年,劫后余生的苏东坡重返京师,迁中书舍人,笔墨间已经没有了黄州《寒食帖》那种寒气逼人的压抑与激越,反而典雅平实,行气充沛,自然放松,一派淡然,人生几回伤往事,文字间依旧流淌出对生活的乐观,那颗丰富敏感,豁达通透的心灵在也一笔一画中越发清晰可见。
《题王晋卿诗》全文如下:
晋卿为仆所累,仆既谪产晋卿亦贬武当。饥寒穷安,困,本书生常分,仆处不戚戚固宜。独怪晋卿以贵公子罹此忧患,而不失其正,诗词益工,超然有世外之乐,此孔子所谓“可与久处约长处乐”者。元祐元年九月八日苏轼书。
王诜字晋卿,是书画历史上的重要人物,有《渔村小雪图》《烟江叠嶂图》等传世之作。公元1087年,在王诜组织的西园雅集上聚集了北宋文化界最后一波超级大腕,他们是苏东坡、苏辙、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蔡天启、李之仪、李公麟以及米芾等十六人。雅集之后,米芾写了记文,李公麟绘制《西园雅集图》。这次雅集足可以与东晋王羲之兰亭雅集相媲美,十六人中,唐宋八大家两人,宋代顶级书法家苏轼,米芾,黄庭坚三人,画家有王诜、蔡天启、李公麟三人,另外还有苏门四学士,阵容之豪华,后世恐难有比肩者。
苏轼与王诜交游甚密,在王诜没有做驸马之前就常往来。王诜虽出将门,却热衷诗书,年轻时也想有一番作为,无奈取了长公主,这事就麻烦了。宋朝为了防止宗室干政,给他们的都是虚职,并且限制宗室与朝堂重臣交往。对于王诜来说,这等于再也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舞台了,于是他把志向转移到了琴棋书画之上,遇到苏轼,让他平淡的生活有了滋味也掀起巨大的波澜。
“晋卿为仆所累”,开篇一句即指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案,这是四十四岁的苏轼命运中最悲惨的一年。7月28日,御史台的办案人员突然闯入湖州府衙。长官苏轼虽然也听说朝廷宵小告发他以诗乱政,甚至通过王诜给苏辙的密信也得知朝廷正在派人抓他,但没想到抓人的人来得这么快。苏轼想这次肯定凶多吉少,惶恐之下甚至不知道穿什么衣服出去与来人相见,通判提醒他说,既然现在还不清楚是什么罪行,就还得穿官服。
双方见面,抓人者板着面孔,一言不发,完全是要压垮对方的心理防线。还是那个通判理智一些,他和抓人者要逮捕令,抓人者拿出来的却是“台谍”,也就是普通的传唤书。即便如此,他们还是把苏轼捆绑起来,“顷刻之间,拉一太守,如驱犬鸡”,目击者如无悚然。
在此后的一百多天中,苏轼被关押在御史台深井一样的牢房里,遭受非人的审讯。要不是那么多人勇于为苏轼伸张公道,可能历史中就不会有一个苏东坡了。为苏轼说好话的人里不仅有他的旧日师友,竟然也有他曾经的政敌,比如王安石。
最后,皇帝出面裁决,苏轼被贬黄州。
王诜为搭救苏轼不惜“泄漏密命”,成为乌台诗案牵连最重的一个人,再加上“交结苏轼及携妾出城与轼宴饮”等罪名被勒停所有官职,贬均州。七年后再回京,见到苏轼,老友间执手相看,竟无语凝噎。苏轼感念旧情,引用孔夫子的语言,称赞其“可与久处约长处乐”,意思就是你这个人讲义气,有担当,我要与你做一辈子的朋友。
王诜交往苏轼,更多是仰慕他的才学。他经常请苏轼吃饭,赠送酒食茶果,以及鲨鱼皮、紫茸毡、翠藤簟,乳糖狮子、龙脑面花象板、裙带系头子等奢侈的生活用品。这些朋友之间的馈赠,都成了二人结交的罪证。罪状中还有一条:1073年,苏轼分两次跟王诜借钱三百贯,一次是为了嫁外甥女,一次原因不明,两笔钱,均未归还。也许苏轼想还钱,但王诜没有收,或者拿书画作品抵债了事,但双方没有还款记录,这就不好解释了,也就被别有用心的人拿来当整人的“黑材料”了。
苏轼写字画画,对笔与墨都非常挑剔,因此,王诜也投其所好,其目的还是要在苏轼那里换取一些书画。王诜曾一次赠送苏轼十几种墨,共计二十六丸。宋以前的书法家大多专注于笔法,很少有特别在意用墨之法。到了东坡的时代,物质的发展再次推动艺术的创新。北宋是中国文房用品研发、制作技艺发展的一个高峰期,拿制墨而言先有南唐李廷珪,后有李承晏、潘谷,苏轼都有诗歌赞之,甚至他自己也参与过墨的研发和制造。
宋代的顶级墨大多来自南唐李廷珪的松烟墨。制墨首先要取烟,油烟制墨在宋代还处于初创阶段,不太成熟。北宋大多用松烟,松烟以黄山老松最优,匠人把松树去皮焚烧的烟灰收集起来,再经过淘洗分拣,才能使用。曾抄写过一则制墨配方:烟松一斤,珍珠、龙脑、玉屑各一两,另外还有麝香、樟脑、冰片、藤黄、犀角等材料。如果只看这个配料表,还以为是中药店开出治病的药方呢。是啊,墨也是一种药,小时候看人治病,还真用到墨汁涂抹患处,现在也有一种药墨,只是用墨治病的也少见了。这些原料备齐,再用上半斤皮胶,搅拌后,用木槌反复捶打,曰十万杵,也就是要捶打十万次,当然这只是一个大概的说法,目的是让墨中的各种配料能够更好的融合。这还不算,刚做好的墨还要等待时间的沉淀,阴干之后,存储三五年再投放市场,这样墨里的动物胶也会慢慢退去。壬寅岁末,我在安徽绩溪参访胡适老宅,出来之后偶遇一制墨工匠,带我去他家里。房间里光线幽暗,一位大叔正在熬煮皮胶。皮胶是制墨的关键原料,墨之优劣,在用胶上有很大区别,最优者是鹿角胶,大多使用牛皮胶。苏轼说,北宋时代的制墨名家潘谷用的是鱼胶。但无论用什么胶,都是为了让文人笔下能挥洒出更自由的线条。墨是老的好,新墨燥,涩笔,主要是没有退胶。三五十年的老墨,用起来就有不一样的神采了,墨色透亮,色泽丰富而稳定。苏轼喜欢用浓墨,每次写字都把墨研磨得糊糊的,写出来的字黑又亮,历经千年,仍然光彩夺目。
王诜也善制墨,苏轼说王诜制墨“用黄金、丹砂,墨成,价与金等。”看来,王诜这配料更名贵,墨与黄金等价,这不是虚言,民间本来就有一两徽墨一两金的说法。实际上,墨是一种特别的颜色,它展现的是一个中国文人纯净的精神世界,又岂是黄金可以等价?
除了墨之外,苏轼作书常用诸葛笔和澄心堂纸。苏轼做过一首《黄泥坂词》,那是他被貶黄州时的作品,因原稿保存不善,找出来的时候已残损大半,苏轼凭记忆重写一份,被张耒收藏。这件事情被王诜知道后,就给苏轼写信:吾日夕购子书不厌,近又以三缣博两纸。子有近书,当稍以遗我,毋多费我绢也。
于是苏轼用李承晏墨、澄心堂纸再把《黄泥坂词》誊写一稿,算是还了这位贵公子的文债。
贵公子王诜常常做出一些赖皮的事情。苏轼有一块仇池石,视若珍宝。王晋卿听说后,明里写诗借赏,暗地里要横刀夺爱。苏轼不能不借,也写诗回应,诗名叫《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光看这条长长的标题,就可知道苏东坡那种无奈的心境。
1077年,王诜收藏书画的宝绘堂建成,请苏轼写一篇记文。苏轼写了《宝绘堂记》,其中有言曰: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钟繇至以此呕血发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复壁,皆以儿戏害其国,凶其身。此留意之祸也。……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
可以想见,王晋卿看了这篇文章是何感想?我堂堂驸马都尉,功臣名将之后,我爱好个收藏,咋啦,咋就要招致祸端啦?我本来想请你大学士写一篇美文,装裱后悬于厅堂,本来是一件美事,你可倒好,不会说话不说也行,还“害其国,凶其身”,你看你说的多晦气。于是他写信给苏轼,让他删掉这些不吉利的字眼,可苏轼也犯了犟劲儿,答复曰:你要是不喜欢,可以不裱挂啊,让我写,我就这么写,对不起,一个字也不改。
同样兄弟俩,个性却明显不同,苏辙的做事方式就要沉稳很多。还是在王诜的宝绘堂这件事上,苏辙也写了一首诗,从头到尾唠的都是吉祥嗑,跟人家办喜事他给唱喜歌儿一样。且看一两句:“骐驎飞烟郁芬芳,卷舒终日未用忙。游意淡泊心清凉,属目俊丽神激昂。君不见伯孙孟孙俱猖狂,干时与事神弗臧。”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苏轼在任凤翔签判的一段往事,那时候苏轼二十七岁,年轻气盛,也不怎么把长官陈希亮放在眼里,让他去开会也敢不去,后来被罚铜八斤,并记录在案。不久后,陈长官建造一座高台,请苏轼写记文一篇。苏轼在文章中大加讽刺:“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霜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盖世有足恃者,而不在乎台之存亡也!”这篇文章确实有些刺眼,可是苏轼这位眉州老乡,却显示出了极大的气度,竟然一字未改,刊刻于石。很多年后,苏轼想起这件事,很后悔,在给陈长官写的传记中,他说:“方是时,年少气盛,愚不更事,屡与公争议,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新岁展庆帖》
苏轼的老长官陈希亮有一个儿子叫陈慥。
陈慥不热衷功名,喜欢喝酒弄剑,一身社会气。
苏轼第一次见到陈慥,是在歧山脚下,陈慥带着几个弟兄,正在骑马打猎。苏轼发现他身上有一种诱人的游侠气质,俩人越聊越投缘,没想到和陈希亮不对脾气,却和他儿子成了莫逆之交。
陈慥和东坡共同为中国语言留下了一个词:河东狮吼。这成了某一类女人的代名词。
陈慥虽然在外面吃得开,可是回到家里是龙也得盘着,是虎也得卧着,修道修佛都没有用,全然不敌那一声刺入灵魂深处的狮子吼。“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苏轼如是说。
既能体现苏轼书法美学,读来又清清爽爽的,是苏轼元丰四年(1081年)正月二日写给陈慥的一封信札。
手札的可爱之处,在于它亲切,因为是朋友之间的互通有无,也没有必要端着架子,又逢新岁,下笔轻松愉快,一个新的开始,未来还有无限可能,干吗不去拥抱。
乌台诗案以前的苏轼,少年得志,意气风发,虽有些不如意,朝堂大佬均以国士待之,自己也感觉未来可期。贬谪黄州,虽不至死,但前途茫茫,心境落差必定极大,即使豁达如苏轼者,也不能在短时间内一笑而过。《寒食帖》就是这种情绪低落到了极点的哀鸣。
那个时代很多被贬谪的人都死在了路上,他们面临严酷的生存环境,内心郁结的痛苦与孤独的煎熬,甚至比生存环境还要严酷。万人如海一身藏,说来轻巧,做起来难,要不东坡怎么会半夜睡不着觉!朋友的慰藉让孤独退场,住在承天寺里的张怀民可能不算大人物,但此时却让人颇生好感。中年以后,再读东坡,甚至有点感激张怀民,他恰如其分地出现在东坡最需要慰藉的时候,清冷的夜色之下,你会发现张怀民对于苏东坡来说是多么温暖的存在啊!落难中的苏东坡往往能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张怀民、潘丙、古道耕、郭兴宗,当然也少不了铁杆粉丝马梦得,以及龙丘居士陈季常了。
关于马梦得,《东坡志林》里有一个段子,“马梦得与仆同岁月生,少仆八日。是岁生者,无富贵人,而仆与梦得为穷之冠。即吾二人而观之,当推梦得为首。”初读感觉好笑,再读不免心酸,再三读之,便更觉东坡豁达的妙处。
马梦得原本一任“太学”小吏,后辞职。但这个人一直在苏轼身上押宝,赌他将来定能荣华富贵,好能分他钱财,买山终老。苏轼到黄州,他特跟随而至。也是马梦得与官方争取,苏东坡才能在黄州东门外的一处坡地开荒种田,解决了一家人的温饱。这对苏轼来说是一件大事,从此以后,繁重的体力劳动,以及陶潜隐逸思想的某种暗示,苏轼看到了自己的改变,也体会到了一个农夫的辛苦与收获。某些时候,他觉得自己如同陶渊明转世,还曾写下一首《江城子》:梦中了了醉中醒,只渊明,是前生。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都是斜川当日境,吾老矣,寄余龄。
从寂寞沙洲冷到此心安处是吾乡,心境的转变让生活的眉目更加明朗,苏轼开始渐渐适应目前的生活。有了田地,更想有一所自己的房子,即使不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但能见长江东逝,白浪卷雪也是人间有味的清欢好日子啊。
这时候,我们可以再看一遍这封书札的原文了。
轼启:新岁未获展庆,祝颂无穷,稍晴起居何如?数日起造必有涯,何日果可入城。昨日得公择书,过上元乃行,计月末间到此,公亦以此时来,如何?窃计上元起造,尚未毕工。轼亦自不出,无缘奉陪夜游也。沙枋画笼,旦夕附陈隆船去次,今先附扶劣膏去。此中有一铸铜匠,欲借所收建州木茶臼子并椎,试令依样造看兼适有闽中人便。或令看过,因往彼买一副也。乞蹔付去人,专爱护便纳上。余寒更乞保重,冗中恕不谨,轼再拜。季常先生文阁下。正月二日。
子由亦曾言,方子明者,他亦不甚怪也。得非柳中舍已到家言之乎,未及奉慰疏,且告伸意,伸意。柳丈昨得书,人还即奉谢次。知壁画已坏了,不须怏怅。但顿着润笔新屋下,不愁无好画也。
书信内容安排的很自然,造房子,来朋友,送礼物,另外要借用建州木茶臼,盖房子可能算老苏的一件大事,但因為还没有进入具体操作流程,信中也未详细言说。可是那件借用茶臼的小事,来龙去脉却絮叨得明白真切,且用笔墨最多。足见窘境中苏轼对生活的态度,茶臼是提升生活情调,锦上添花的东西,对于苏轼来说,生活中的这一点儿小情趣也是必要的,否则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死气沉沉地活着罢了!
1079年的那个冬天,苏轼灰突突地从汴梁出发去往黄州,路上偶遇季常。二人已经多年未见,苏轼见季常潇洒如故,但季常竟还不知道苏轼摊了大事,互相寒暄之下,陈季常不提伤心事,只是拉着他回家喝酒。岐亭陈家宅子,环堵萧然,简朴得超出了苏轼的想象。陈慥清心寡欲,醉心修道,“龙丘新洞府,铅鼎养丹砂”,苏轼感觉季常已经不再是以前的那个浪荡子了,时间改变了两个人的境遇,但肝胆相照的内心依然温暖。那天苏轼酒喝得有点多,加上旅途劳累,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
一周之后,苏轼到了黄州。摆在他面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住在哪儿?
好在佛家寺院给他敞开了大门,他和儿子先搬到了定惠院和僧人们一同吃住。半年之后,苏家老小也都来到黄州,这可麻烦了,寺庙里肯定不能住,怎么办,想买房子,又没有财力。太守朱寿昌伸出援手,他们一家人搬进临皋亭。临皋亭虽然局促,但可以安定下来,只是要来了朋友,就没有地方住了。
陈慥来黄州,当地人欲请吃住,陈慥拒之,苏轼想安排他住在寺院或者船上,陈慥亦拒,他更愿意和老友在简陋的房子里抵足而眠。苏轼在黄州四年,陈慥来过七次,每次都盘桓十来天,在此期间,他也建议苏轼置办一处属于自己的房子。
苏轼造房,亲力亲为,被炙热的太阳晒得皮肤黝黑,房屋落成时已是冬天。屋外大雪悠散,屋内他于墙壁绘制雪景,遂给新居取名“雪堂”。“雪堂”容易给人一种浪漫的想象,但实际上雪堂冬天还好,只漏风不漏雨,但到了雨季,可就是屋里屋外一起下雨了,客人来了挪床接漏雨,难免有点尴尬,“他时夜雨困移床,坐厌愁声点客肠。一听南堂新瓦响,似闻东坞小荷香。”诗歌中所言“南堂”,是苏轼同年进士蔡承禧到黄州看望他出资建筑的。雪堂是五间草房,南堂是三间瓦房,住房改善了,雨打瓦片的声响,听起来都那么悦耳。有了这所房子,苏轼可以在这里会客、看书、习字、抄经、画画,当然还有给朋友写信。时间就这样一点点儿的过去,在这些具体细微的活动中,原来那种被贬谪的压抑、痛苦、百无聊赖、空洞洞而没着落的内心,都被时间填满,苏轼也在与劳作、读书、交游之中,不知不觉地代谢掉了垃圾情绪,发现了幸福的密码。
你看他写得轻松愉快,悠然之态跃然纸上。
文字在纸上如同跳动的音符一样,墨色变化也并非一味儿丰腴厚重,而是疏密错落,大小呼应,牵丝连带,轻重缓急,用笔果断而自信,你可以认为这就是苏轼日常写字的样貌。他不夸张,不刻意,笔意欢快,潇洒自如,达到“书出无意于佳,乃佳尔”的艺术效果。
但这种感觉并不是在苏轼所有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的,《寒食帖》字里行间的情绪与线条的沉郁之感相互感染,读来则有哀鸣之音,是情感的极端体现,是即兴表达,有难以复制的是心境和情绪。因此黄庭坚题跋曰: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前赤壁赋》书法与赋文皆美,用笔端稳圆润,结构精当,山峦、水影、树木搭接起来的线条,浸润一种独特的水墨气质,柔软平和,舒展洒脱,又不缺乏生命的韧性与丰盈。但因是赠予给朋友的“誊写”之作,书写中必定用心经营,与人生的旷达相比则稍显拘谨。苏轼多次抄写《前赤壁赋》赠给朋友,但《后赤壁赋》却不见真迹,想来也和文章有关,我更喜欢《后赤壁赋》,感觉后赤壁,更神秘,更私人。
《后赤壁赋》中,苏子不再讲那些大而化之的道理,而变成了一个人的历险记,不仅是冬夜登山望月的历险,更是一次精神历险。此后,苏东坡在梦与命运的启示之下,重又找回生命的巨大意义。
作者简介:梁帅,在《大家》《山花》《大益文学》《延河》《湖南文学》《小说林》《香港文学》《世界文学》等刊物发表文学作品,出版长篇小说《补丁》、短篇小说集《马戏团的秘密》等,获萧红青年文学奖,天鹅文艺奖,黑龙江省文艺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