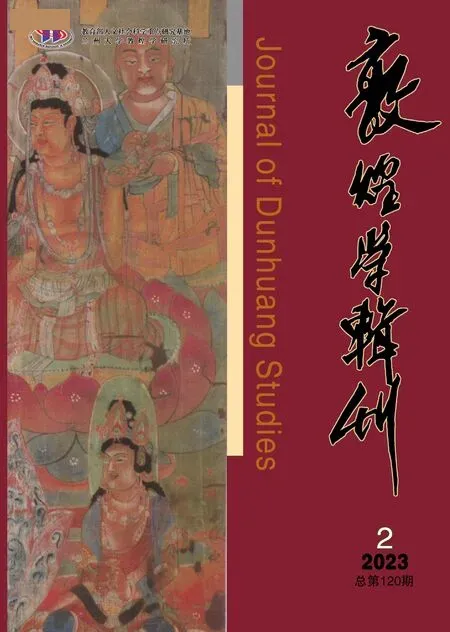比析诸本出新解 纠误释疑呈灼见
—— 《金刚经集注校笺》 评介
米文靖
作为般若经典总纲的《金刚经》 历来备受关注, 其版本之多、 注释之丰不失为众经之首。 在众多注疏校笺当中, 李小荣、 卢翠琬2021 年在巴蜀书社出版的《金刚经集注校笺》 (以下简称校笺本) 将《金刚经》 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此书以朱棣《金刚经集注》 (以下简称集注本) 为底本, 以杨圭所编《金刚经十七家释义》 (以下简称《十七家释义》 ) 和洪莲修补增订重刊的《金刚经五十三家注》 (以下简称《五十三家注》 ) 为参校本进行校记笺注, 其开拓之功有三: 前言部分考辨众说确定《集注本》的版本沿革情况; 笺注部分逐一考辨注家生平, 辨析注文的出处与引用情况; 校记部分通过对比同一注文不同本子的异同, 以不同文献交互佐证, 全面而详尽地纠正了《集注本》 文字和引用问题。 《校笺本》 以跨时空的文献梳理法和跨学科的考据法将《金刚经》 和《集注本》 研究推上了新的研究维度。
一、 考辨众说确定《集注本》 的版本沿革情况
《金刚经》 的译本较多, 其注疏讲义亦达千八百家, 因此众多有关《金刚经》 的“注释集” 应运而生。 影响较大者如唐释道世著《金刚经般若经集注》 收录了姚秦罗什、 东晋谢公、 隋代昙琛、 唐朝慧净等人的注释, 以训诂之法一以贯之, 可惜后世未有传本; 南宋杨圭折衷诸本著《十七家释义》, 富有文学性的语言使其颇受文人居士的青睐; 明初朱棣编《金刚经集注》 博采众长, 以博而返约、 广而专精的书写特征广泛地流传于民间; 明洪莲编《五十三家注解》 海纳百川, 新增《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目录》《金刚经五十三家注解姓号目录》 《金刚经道场前仪》 《金刚经道场后仪》 及洪莲序、杨圭序等, 因此洪莲本又被称为《五十三家注解》 或《金刚经注解》, 多种著称也让此书在后期传播过程中产生书名与版本的混乱与争议; 另有丁小平以无著、 世亲的注释思想为核心, 点校《金刚经注释集》, 共收录了影响甚广的十一家注释。 因此, 作者在众多“注释集” 中选用朱棣《集注本》 为点校底本, 以杨圭《十七家释义》 和洪莲《五十三家注》 为参校本具有特殊意义。
一则《金刚经》 “注释集” 虽多, 但各有所长, 难以并美, 简约者多有遗漏之憾,广博者却失于精要, 详于事相者却失思想精粹, 偏重科分者却失义理大宗。 在众多注本中, 《集注本》 一方面能够集众家之所长, 疏解字词、 详谈名相、 深阐义理、 阐幽唱颂等应有皆有, 可谓折衷诸本、 晓畅精微, 其流传之广、 影响之深远超其他注本; 另一方面《集注本》 所选取的注家生活年代跨及两晋至南宋, 既有高僧大德, 又有禅师居士,亦有文人学者, 所收录的注文具有典型的时代特色和丰富的思想内涵。
二则众多“注释集” 之间相互继承。 学界历来的观点是“ 《金刚经集注》, 原有南绍定杨圭十七家释义四卷, 后演为五十三家注四卷, 明御纂本摒除五十三家本中传为梁昭明太子所作三十二分分目, 略减注者数家, 而益以三十余种经文或注文, 衰成一卷(此观点见《金刚经集注》 出版说明部分第2 页)。” 李小荣等在《校笺本》 比析考辨后则否定了这种说法, 他们认为“朱棣之《集注本》 是在杨圭《十七家释义》 基础上添加李文会一家而成, 后洪莲又以朱棣本为底本进行重刊校订为五十三家” (前言第4页)。 一方面, 作者对朱棣本和杨圭本的注文及出处进行逐条考证, 经过对比发现,《集注本》 实则是在杨圭本的十七家注本之上, 增加李文会一家注文, 其他禅师则源于李文会注文中的引用内容; 另一方面, 作者对洪莲本新增的洪莲序和杨圭序仔细辨析,确定洪连本新增列的三十六家注家是对朱棣本十八家的重刊校订。 同时在李小荣指导下, 李艺敏在硕士论文《朱棣〈金刚经集注〉 之注家研究》 中对比了两个本子之间的细微差异, 佐证了洪连本对朱棣本的相承关系(福建师范大学, 2010 年)。
经李小荣等考辨, 此三本著作书名和版本的沿革情况是: 杨圭本→朱棣本→洪莲本是依次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校笺本》 亦梳理了杨圭本十七注家的姓号, 对比之下, 朱棣本十八家和洪莲本以“某某曰” 的形式增列三十六注家的姓号一目了然。 可见, 朱棣本的《金刚经集注》 具有上承下启之功, 因此《校笺本》 梳理正名集注的版本沿革过程对《金刚经》 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二、 考辨注家注文助益于《集注本》 注文思想的理解
《金刚经》 前后共有六个译本, 其中以语言优美精审、 义旨圆通的罗什译本最为通行。 《集注本》 以罗什译本为底本, 择取从晋到宋诸多文人学者的注文合辑而成, 其语言晓畅精微, 不仅对注文进行字词疏解和义理深阐, 而且在注文后附有小字夹注, 或释佛教知识, 或注典故出处, 故在民间和文人居士中间颇为盛行。 但因注解中多引禅入经、 援儒释佛, 导致出现新的较为晦涩难懂的注文, 且注文中有文字和引用之误, 因此《校笺本》 通过笺注部分对注文重新进行注解和说明, 在校记部分对注文内容进行纠误, 双重校订下极大的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使用。
一则《校笺本》 利用地方方志、 地理总志等各种文献, 对《集注本》 中所引注家的生平事迹逐一进行考辨。 《校笺本》 考证较为详致者有杨圭、 周史卿等43 人(另有对诸佛诸菩萨等佛教中人进行注释说明, 此处皆略), 考辨之人按照思想派系可归纳如下表:

《校笺本》 考辨之人
因居士弃儒入释的特殊经历, 故此单独罗列, 因此《校笺本》 按照人物继承的思想派系可归类为儒士、 道士、 佛僧和居士四大类。 《校笺本》 考辨了此四类人的籍贯、 生平、 作品等, 尤其对佛教人士和居士所属的思想派系梳理极为清晰, 这对研究者进一步研究《金刚经》 及注文思想功不可没。 对考辨之人颇有争议的地方, 《校笺本》 亦做出合理推测, 实不能盖棺定论的地方, 也会呈学界之观点, 从而供读者参考。 如考辨僧了性时, 笺记部分载:
了性: 杨圭《十七家解注金刚金姓号目录》 中题做“云庵僧了性”。 据史料记载, 在杨圭之前或与杨圭同时名为“了性” 的僧人有两位: 一是宋代泉州开元寺僧人, 俗姓黄, 福建安溪人。 宋绍兴中(1131-1162), 曾主持重建开元寺东西两塔。 一位是真州灵严东庵了性禅师, 为南岳下十六世, 径山大慧宗杲禅师法嗣。 这两位僧人与杨圭的活动年代接近, 且一位为福建人, 一位为浙江人。 因杨圭所选取的注家多居闽北江浙一带, 故此处的了性可能是真州(今属江苏仪征) 灵严东庵了性禅师, “云庵” 疑为“东庵” 之误。 (第47-48 页)
《笺注本》 依据杨圭生活的年代及注家生活的地域特征, 合理的推测“了性禅师” 的住寺, 这对读者研究注文集结过程及了解注文的思想有重要意义。 《校笺本》 亦对佛教之诸神、 诸菩萨和诸名物等, 回归梵语本意重新释读, 为读者正确理解经文或注文的思想内容提供了保障, 亦解决了不少争议与困惑。
二则《校笺本》 逐一考辨注文的出处, 对比同一注文不同本子的异同, 呈列尚未定论的观点以供读者参考, 这是《校笺本》 最为浓墨重彩的部分。 《集注本》 的十八家注文涉及范围之广、 作品之丰、 思想之深远非一般作品可比, 因此《校笺本》 深入经论, 从读者角度出发逐一解决阻碍阅读的困难。
首先, 《校笺本》 对生僻用典或名词进行注释说明。 如傅大士注曰“人空法亦空,二相本来同。 遍计虚分别, 依他碍不通。 圆成沉识海, 流转若飘蓬。 欲识无生理, 心外断行踪。” 《校笺本》 笺注“无生” 曰:
无生: 涅槃, 因其超越生死而无生灭, 故云无生。 北宋智圆述《维摩经略疏垂裕记》 卷第二曰: “无生寂灭, 一体异名”。 (第129 页)
涅槃有灭度、 不生、 解脱等意, 但以“无生” 释其意者不多见, 若不能理解无生之意, 就无法理解傅大士对“心无所住而生其心” 的注释“欲识无生理, 心外断行踪”之意。 《校笺本》 释意的同时, 也会标注该生僻词在其他地方的应用, 加强了读者对词句, 尤其对佛义的深入理解。
其次, 《校笺本》 亦对同一用语在儒、 佛不同文化的不同意义分类注释。 如川禅师曰“官不容针, 私通车马”, 《校笺本》 笺注曰:
官不容针, 私通车马: 本意指法律森严, 不容一丝含糊, 却可私下通融。 禅林多用来喻指接引学人时可随机应物, 灵活采用多种方便法门。 (第362 页)
《校笺本》 随后注明此语出于《镇州临济慧照禅师语录》, 是沩山与仰山论“石火莫及, 电光罔通。 从上诸圣将什么为人” 时, 仰山的回复之语。 此笺注对禅林之义的注释有助于读者更好的理解“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 的思想。
《校笺本》 的注文详尽而全面, 对注文的考辨之功和对内容的补充与说明都值得肯定, 不仅解决了阅读时候的很多障碍与困惑, 也为读者更好的理解《集注本》 注文的思想内容提供了便利。
三、 去伪纠误校正《集注本》 的文识讹误
《笺注本》 的校记部分多是经过对比分析之后的纠误, 包括对《集注本》 文字之误和引用之误的校记, 对不能定论的众说观点亦有呈列。
一则纠正《集注本》 原文及注文的文字之误, 这是在传抄过程中出现多种版本及誊写错误造成的。 如《集注本》 载: “须菩提! 于意云何? 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 《校笺本》 校记曰: “足: 底本作‘之’, 误”, 底本即《集注本》, 若按照底本“之” 则无法理解句意。 再如王日休注曰: “此分与第五分、 第十三分之意同, 于此再言者, 为续来听者说也。 (夹注曰: 傅本十三分, 王本十六分) ” 《校笺本》 校记曰:“傅本: 戚本作‘什本’, 误。” 《金刚经》 作为般若部的总纲, 词约义丰的语言特征使得每个字都富含深意, 《校笺本》 通过对比众多本子, 纠正《集注本》 的文字错误, 这是《集注本》 锦上添花的成就, 亦是助益《金刚经》 文学传播的新路径。
二则纠正《集注本》 注文或注家的引用之误, 众多注释集所辑录的注家各不相同,在传播途中必然会出现张冠李戴等问题。 《集注本》 载: “所谓不住色布施, 不住声香味触法布施”, 张文进注曰: “不住声色布施者, 谓智慧性, 照见一切皆空也。 梵语檀那, 此云施……” 《校笺本》 校记为: “查张无尽藏内外著作, 未见有此段文字。 按,据明韩严集解、 程衷懋补注《金刚经般若波罗蜜经补注》 所载, 此段文字出自逍遥翁,但无‘梵语檀那, 此云施’ 一句。 又, 张无尽及此后之所有注文(下段经文之前), 戚本皆无。 从下文之引文风格及行文特色分析, 此处之‘张无尽’ 疑为‘李文会’ 之误。” 此校记有三点重要意义: 查阅张无尽著作确定注家引用错误, 对比不同版本之间该注文的异同及确定此注文的出处, 以现有文献推测最为合适的注家进行纠误。 通过对比同一注文不同本子异同和考辨众注家的作品集, 从而得出正确结论是《校笺本》 校记的重要方法。
除此之外, 《校笺本》 的校记部分也呈列了不能盖棺定论的引用, 以供读者参考,对同一注文注家但不同本子略有差异的部分会给予说明解释, 对《集注本》 引用不合理的地方, 会根据现有文献进行合理的校补等, 具有考辨与研究双重意义, 如:
《集注本》 “须菩提! 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 如人入暗, 即无所见。 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 如人有目, 日光明照, 见种种色”, 其中一注本不显名曰: “有所著,则为无明所障, 不悟真如妙理, 犹昏昏而不能使人昭昭; 无所著, 则洞达无礙, 圆悟如来无上知见, 自觉已圆, 又能觉他”。 (第275 页)
《校笺本》 校记曰: “此条注文, 不知出自何处。 众善堂本无此条注文, 仅将‘自觉已圆, 又能觉他’ 几字换陈雄注之‘如有目者, 处于皎日之中, 黑白自分, 而毫发无隐矣’ 一句。” 《校笺本》 笺注曰: “一注本不显名: 杨圭《十七家解注金刚经姓号目录》 将其作为一单独注家, 列于‘武当山居士刘蚪(虬) ’ 和‘梁朝傅大士颂’ 之间, 可能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本。 底本所辑此注本之注文仅两条”。
《校笺本》 全面收集并整理了《金刚经集注》 的相关注本, 并利用文献考据法对其进行真伪考辨, 可见《校笺本》 校记与笺注的严谨与细致。 一方面, 《校笺本》 详解说明现存的注本, 包括不显名的注本, 并在笺注部分根据已有相关注本的佐证, 对其流行时间进行合理推测, 对进一步研究金刚经的相关注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另一方面,《笺注本》 对现有的各种注本进行详细比较, 并在校记部分列出众注本之不同, 这种横向对比, 大大方便了研究者对金刚经相关注本的版本研究。
诚如李小荣所言: “对《集注本》 这样重要的本子, 学界目前只有点标本而无校对本及注释本”, 这确实是一种遗憾。 《校笺本》 以跨时空的文献法和周密详实的参校法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是《金刚经》 研究新的里程碑, 也是儒、 道、 释三家文化融合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