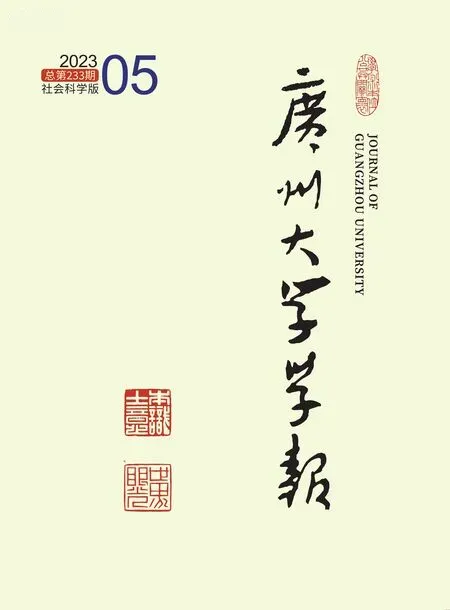数码复制时代的亲密关系:从网络直播到ChatGPT
高寒凝
(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一、虚拟亲密关系的两大类型
亲密关系,指包含了解、关心、信赖、互动、信任和承诺这六种要素中至少一种的人际关系模式。它可能存在于恋人、夫妻、朋友和亲子之间。[1]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构筑人际关系的技术中介,也在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等移动数码设备的深度介入之下,迭代为电子邮件、即时通信软件(如QQ、微信)、社交网络(如脸书、推特、新浪微博)、约会软件(如Tinder、探探)和网络游戏。本论文的研究对象“虚拟亲密关系”,正是某种诞生于互联网虚拟空间,被全新的技术环境、媒介环境所重构的亲密关系形态。
一个较为直观的例子,就是在社交网络、约会软件或网络游戏中,用户/玩家登录自己的账号,以虚拟化身(avatar)的形态与另一个用户/玩家的虚拟化身建立恋爱关系的现象,即俗称的“网恋”。它极大地丰富了人类寻找理想伴侣的途径,让许多原本无缘结识的人们在平等沟通与自由选择的氛围中遇见彼此,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面对面交往的尴尬与焦虑,却也埋下了许多潜在的人身安全隐患。学术界针对这一现象的讨论,更是拓宽了有关人与技术、身体与媒介、自我的在场/缺席、控制与自由以及私人与公共之间的边界等诸多问题的研究视野。①
显然,对于网恋这类现象而言,无论怎么强调“虚拟化”转向带来的影响,数字技术作为一个变量、一个中介,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亲密关系的本质。但在实际的网络民族志观察中,“虚拟化”与“亲密关系”相结合所衍生出的“变体”,却远远不止网恋这一种形态。例如“粉丝与虚拟偶像/虚拟主播”或“游戏玩家与游戏中的虚拟角色”之间的交往,就完全符合本论文对于虚拟亲密关系的定义,却又微妙地偏离了“亲密关系”的固有形态:它的成立并不过分依赖“了解、关心、承诺”等六大要素,而是基于一套特定的商业模式,即虚拟偶像/虚拟主播或游戏制作组利用特定的虚拟形象作为外壳/中介,以自身的“亲密关系劳动”来换取粉丝/玩家的购买力与数字劳动。②
“亲密关系劳动”在本论文的语境中,指的是“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的一个分支。它与情感劳动一样,核心目的都是为了获取报酬,主要表现形式则是对情绪/情感的“整饰”,例如空姐、售货员在工作状态下对面部表情、语气和身体动作的控制等,“微笑,就像你真的想笑一样”[2]。依据上述定义,网络主播/虚拟偶像用温柔的语调对观众说出“宝宝们我好想你们”(换取虚拟礼物、点赞),或乙女游戏③里男主人公对玩家的甜蜜告白(换取充值金额和在线时间)等,无疑是典型的情感劳动。但相比之下,这些隶属于虚拟亲密关系范畴的情感劳动,又明显带有强烈的“制造亲密氛围”(如引发有关浪漫爱情、亲密友谊的幻想等)的倾向。为使后文的论述更加清晰、集中,故将其命名为亲密关系劳动。④
不难看出,以“是否包含亲密关系劳动”作为判断依据,当前最为普遍、也最为大众所熟知的各种虚拟亲密关系形态,也自然地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种类型。其中,包含亲密关系劳动的那一类,正是本论文将要着重关注的研究对象,以下统称为“虚拟亲密关系Ⅱ型”。不包含亲密关系劳动的,则追认为“虚拟亲密关系Ⅰ型”。
二、虚拟亲密关系Ⅱ型的三个发展阶段
以亲密关系劳动这个核心概念为主轴,综合媒介史、技术史中的关键节点,则虚拟亲密关系Ⅱ型的发展历程(包括其“前史”),大致可以被划分为三个阶段。
其中第一个阶段的要点,在于“准社会交往”(para-social interaction)的浮现。“准社会交往”是由美国精神分析学家唐纳德·霍顿(Donald Horton)和理查德·沃尔(Richard Wohl)在其合著论文《大众传媒与准社会交往》中提出的概念。该论文的写作背景,是20世纪50年代前后以电视为代表的大众媒体在美国的广泛流行。论文认为,电视节目的镜头语言制造了一种屏幕中的人正在对观众说话、与观众进行面对面交谈的错觉。基于这种错觉,媒介接受者与他们所消费的媒介人物(明星、公众人物或电视剧中的角色)之间,便会发展出某种单方面的、想象性的人际交往关系,即“准社会交往”或“准社会关系”。[3]
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在《爱,为什么痛?》这本专著中,曾详细论述过“想象”对现代情感生活的形成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在易洛思看来,消费社会的核心维度,就是以一种“受监管的、制度化、商品化”的方式对想象力加以运用。她援引并拓展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观点,认为现代性不仅在于用诸多新方法想象“社会政治纽带”的能力,更包括一种想象“个人幸福乌托邦”的能力——“围绕着他/她的情感和白日梦来组织个人的现代情感主体,并将人们对自由的行使定位在个体性的实现和幻想”。而由大众媒体(印刷出版、商业广告、互联网等)所大量制造的、对于幸福生活叙事的视觉呈现,正是这种“白日梦”的主要参照对象。[4]375-383由此看来,准社会交往并不是孤立的、偶发的现象,恰恰相反,它是以想象的方式构建现代情感生活/情感主体的一系列文化实践的有机组成部分。
如前文所述,准社会交往是一种单方面的、想象性的人际交往关系。其中,大众传媒对媒介人物个人信息(如面容、言谈举止等)的传播,无疑是准社会关系想象最稳定的素材来源;而由媒介技术所制造的“面对面交谈”的幻觉,则是支撑准社会关系想象的基本立足点。这意味着,它并不符合本论文对虚拟亲密关系的定义。事实上,作为准社会交往最初的载体,电视媒介和广播电视节目虽然足以制造出“面对面交谈”的幻觉,却也彻底地排除了“交互性”这一构建人际关系的核心维度:在技术层面上,电视屏幕里的人物影像,根本不可能对媒介接受者单方面表达出的交往意图给予任何形式的实时反馈;而从伦理这个向度来看,即使大部分电视节目的内容设计都在刻意引导、培养观众的准社会关系想象,但当这种想象被宣之于口并试图寻求回应时,它的合法性也会随之烟消云散,并被贴上“狂热粉丝”“心理变态”等等“病理性”的负面标签。
然而时隔不久,这一隐藏在准社会关系概念中的伦理困境,就经由偶像工业的建立和亲密关系劳动的发明而“被发现”,并且“被缓解”了。虚拟亲密关系Ⅱ型的第二个发展阶段,也由此揭开序幕。
偶像工业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历经数十年发展,逐步确立了一套基本的商业模式(主要在中日韩等亚洲国家通行):偶像利用各种形式的“粉丝福利”(fan service),例如在舞台表演的过程中对粉丝示爱、向粉丝比爱心手势等(即“亲密关系劳动”),公开地、大范围地回应粉丝的准社会关系想象,肯定其合理性或至少做到“去病理化”⑤,有意识地制造一种“偶像正在与粉丝恋爱”或“偶像与粉丝亲密无间”的制度化、商品化的想象,以尽可能地吸纳那些原本被污名化、被排斥在外的粉丝群体的购买力。⑥偶像(以亲密关系劳动作为本职工作)因此得以区别于歌手、演员(在做好本职工作之余和粉丝展开友好交流)而成为一个独立的职业体系。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偶像爆出恋爱、结婚或绯闻会被视作重大失职,因为它显然干扰了粉丝的准社会关系想象,也使得偶像的亲密关系劳动大打折扣。[5]
值得注意的是,偶像工业从起步直至发展壮大的20世纪70—90年代,广播电视媒体始终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主流的大众媒介形式。这意味着,即使“回应粉丝的准社会关系想象”已经成为全行业的基本共识,但受限于电视媒介的技术瓶颈,偶像们实施亲密关系劳动的具体方案,大多只能依托于粉丝见面会(握手、交谈、玩小游戏)、演唱会(曲目间隙的自由交谈环节)这样的“面对面”场景。
进入21世纪,互联网尤其是大型社交网站等新兴的媒介形式,逐步取代了电视媒介的垄断地位。虚拟亲密关系Ⅱ型的第三个发展阶段正式开启。
面对从口头语言到书面写作的重大媒介转型,苏格拉底曾经抱怨道:“文字写作有一个坏处在这里,斐德若,在这一点上它很像图画。图画所描写的人物站在你面前,好像是活的,但是等到人们向他们提出问题,他们却板着尊严的面孔,一言不发。写的文章也是如此。……还有一层,一篇文章写出来之后,就一手传一手,传到能懂的人们,也传到不能懂的人们,它自己不知道它的话应该向谁说,和不应该向谁说。”[6]事实上,以“时空一致性”(信息的发布和接收在同一时空中完成)和“交互性”这两个苏格拉底最为关注的维度作为判断标准,过去100年间媒介技术的发展,的确呈现出某种越来越趋近于“面对面交谈”的倾向。如果说,印刷媒介是在时空均不一致的情况下,完成了媒介信息的单向传递,那么,电视媒介就是在时间一致(指现场直播)但空间不一致的情况下完成了媒介信息的单向传递。以此类推,社交网站上的网友交流,则是在地理空间不一致、时间不完全一致,但网址一致(隶属于同一个虚拟空间)的情况下,完成了可持续且可回溯的双向/多向交互。
有赖于“交互性”的复归,利用社交网站开展亲密关系劳动的便利性,显然是电视媒介所无法比拟的。事实上,几乎所有偶像明星都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社交网站账号(常见的有微博、小红书、Instagram等),用于发布工作动态、分享日常生活等,部分偶像明星还很热衷于回复粉丝的评论。⑦偶像明星在社交网站(作为开展亲密关系劳动的主阵地)上制造的流量数据⑧(包括转发、评论、点赞的总数和被搜索的次数等),甚至成为其商业价值的重要表征。擅长以高额流量数据(多由粉丝的数字劳动所创造)作为筹码赢得工作机会的这类偶像明星,通常也被称作“流量明星”。
流量明星与粉丝之间的互动交往,是虚拟亲密关系Ⅱ型最重要的初始形态之一:它主要在大型社交网站所构筑的虚拟空间之中展开,以偶像/流量明星的亲密关系劳动来回应并再次激发粉丝的准社会关系想象,形成一个完整的循环回路。然而,它也并不是虚拟亲密关系Ⅱ型的最终形态或理想形态,因为相较于社交网站,真正在技术特性、核心功能等方面完美适配“亲密关系劳动”这项工作的,正是论文在开篇处便已提及的——网络直播平台。⑨
三、 网络直播平台与亲密关系劳动的制度化
“直播”这个概念最早诞生于广播电视行业,指的是“广播电视节目的后期合成、播出同时进行的播出方式”[7]。它的核心机制,在于“事件的发生与传播同步进行”,至于是否通过电视媒介来完成,则无关紧要。基于互联网媒介的直播,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已出现,例如以文字形式转述体育赛事赛况的“文字直播”,此后又衍生出“图文直播”“直播帖”等变体。大约自2015年以来,得益于网络带宽的逐年提升以及4G技术、智能手机的普及,由个人(而非电视台这样的专业机构)架设信号采集设备(如电脑、手机、摄像头、话筒等),依托网络直播平台进行视频直播的现象一时间蔚然成风。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的总规模已达7.51亿,相比通常被视为“网络直播元年”的2016年(3.25亿),增长了约一倍多。[8]
目前国内较为知名的直播平台,有抖音、快手等短视频网站的直播频道,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的直播卖货专区,以及虎牙直播、斗鱼直播这类深耕特定领域(例如电子竞技)的专业直播网站等。本论文针对网络直播平台的讨论,主要是为了分析亲密关系劳动走向“制度化”的技术条件与商业逻辑。因此,相较于主打推广、销售业务的“带货主播”和提供讲解、演示、咨询等内容服务的主播,那些擅长和直播间(即某个主播的专属直播页面)观众开展亲密互动、帮助他们消磨时光的陪伴型主播,才是本论文重点关注的对象。⑩而这类主播之中最具代表性的,正是论文第一节里曾经提到过的虚拟偶像/虚拟主播。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虚拟偶像和虚拟主播其实是不尽相同的两种职业,但他们所开展的网络直播活动,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来看,都没有任何本质上的区别。国内新近推出的一些虚拟偶像团体,甚至是以网络直播作为常规工作内容的。例如字节跳动和乐华娱乐旗下的虚拟偶像团体A-SOUL,其官方微博上公布的日程里,除声乐、舞蹈训练之外,其余的工作安排几乎都是网络直播活动。
要理解亲密关系劳动在网络直播平台上的运作方式,最有效的切入点,自然是分析“直播间”这个最基本的交互界面。图1所展示的,是弹幕视频网站哔哩哔哩(英文名为bilibili,简称B站)直播频道的主播“雪糕cheese”在2023年4月27日的一场直播活动的截图。

图1 直播活动截图
不难看出,画面正中面积最大的区域,展示的正是当前的直播内容——电子游戏《storyteller》的某个关卡。该画面采集自主播本人的电脑屏幕,借助推流工具上传至直播平台的服务器,即可在用户端进行实时的解码播放。当然,对于陪伴型主播而言,他们在直播时玩了什么游戏、唱了什么歌、或看了什么视频,其实并不重要。边直播边与观众互动、闲聊、分享生活琐事等(即亲密关系劳动),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画面的右下角,则是这位虚拟主播的“皮套”(类似迪士尼游乐园里的人偶服),即一个支持Live2D动态效果的、二次元风格的人物形象。利用摄像头和面部捕捉技术,“皮套”就能实时映射主播当前的面部表情。虽然只有睁眼闭眼、开口闭口、抬头低头、瞳孔位移等简单的变化,却已足够表现喜怒哀乐等多种丰富的情绪。和电视节目利用镜头语言所制造的那种“屏幕中的人正在对观众说话、与观众进行面对面交谈的错觉”,是殊途同归的。
在整个界面的上方,可以看到一条条悬浮着的弹幕,如“甜甜甜”“玩游戏玩游戏”等。这些弹幕均由直播间观众自行发布(无需付费),在直播间没有设置屏蔽词或用户等级屏蔽的情况下,任何人发布的弹幕都会直接显示在直播界面上,面向主播和直播间全体观众公开展示(观众如果不想看到弹幕,也可以选择屏蔽)。类似于一个小型广场,人人都有发言的资格。但这类弹幕并不会长久地停留在屏幕上,而是会以一定的速率从右向左飘移,几乎转瞬即逝。在人气较高、弹幕较多的直播间里,一条弹幕恰好被主播或其他观众注意到,并顺势与之展开互动的概率,其实是很低的。
与前面提到的普通弹幕不同,图1左上方框内的一行字“说好黑幕的扇子签了吗”,则是需要付费才能发出的,它的正式名称为“醒目留言”(英文名为superchat,简称SC)。标注在左上方的“500电池”,意味着发出这条留言消耗了500个名为“电池”的虚拟道具,换算成人民币是50元。它可以在直播界面上留存长达2分钟,价位越高留存时间越长(30元的醒目留言可以停留1分钟,2000元的醒目留言则可以停留长达2小时)。醒目留言的发布,通常伴随着动态特效,主播也会收到提醒,再加上停留时间至少为一分钟,被忽略的可能性是很小的。事实上,除非当前的醒目留言多到看不过来或另有要事,那么,具备基本职业素养的主播,都会认真朗读最新的醒目留言并尽可能得体、亲切地加以回复。仔细观察这条醒目留言,不难发现其发布者的头像下方,有“舰长”两个字。这证明他还付费(“舰长”称号的常规定价是198元/月,“提督”则为1998元/月)购买了当前直播间的VIP权益,包括特殊的身份标识、进入直播间时的特效动画、特殊弹幕效果的使用权等。
画面底端的一排图标,展示的则是当前直播间内允许购买并赠送给主播的虚拟礼物,例如心动盲盒(售价150电池,折合人民币15元)、小电视飞船(售价2.999万电池,折合人民币2999元)等。对于直播间观众送出的礼物,念出赠送者的ID并表示感谢,同样是主播的基本职业素养。以上所有付费业务的收益,均由直播平台和主播本人按合同比例进行分成。
总体而言,以虚拟偶像/虚拟主播为代表的陪伴型网络主播的亲密关系劳动,大致具备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网络直播具有极强的时效性,主播和观众必须在同一时间段内进入指定的直播间,若非如此,那些实时互动的功能性服务也就形同虚设了。从结果而言,这类直播活动的本质,正是某种以时空一致(时间一致、网址一致)为前提的,长时间、高强度、日常化的陪伴。而陪伴这个行为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亲密关系劳动。
其次,内置在直播界面上的各种交互功能,也恰好构成了一套层级分明的即时反馈系统。既有免费的弹幕(随机概率获得主播的回复),也有像醒目留言(极大概率获得主播的针对性回复)、虚拟礼物(一定概率获得主播的感谢)那样,附带特殊提醒和长时间留存等特权,能够帮助观众在一对多架构的直播间内,短暂地与主播达成一对一交流的付费机制。主播和观众之间“用亲密关系劳动回应并再次激发准社会关系想象”的循环回路,也经由这样反复重演的交互行为而逐渐确立起来。
最后,网络直播平台上的亲密关系劳动,还具有绩效量化(主播的工作态度会影响直播间热度,直播间热度则与主播收入直接挂钩)、实时结算、单次计价(醒目留言和虚拟礼物的实质,就是以预付款的形式购买单次的亲密关系劳动)等等制度化的特性。相比之下,偶像工业依靠日积月累的亲密关系劳动,在偶像和粉丝之间建立深厚的情感连接,再以此鼓励(甚至是胁迫)粉丝积极购买唱片和代言商品、为偶像“做数据”(以提升偶像的流量数据为目的所付出的劳动的统称,如转发、点击、评论、搜索等)[9]的盈利模式,就显得过于迂回曲折了。
综上所述,依托于网络直播平台的亲密关系劳动,不仅具有供给稳定、选择面广的特征,更形成了一整套固定的标准作业程序(在本文中具体指主播成熟的话术和对观众发出的SC、礼物的程式化回应)、绩效管理方案和薪酬结算体系。如果说,偶像工业只是用一种松散的交换方式,勉强达成了亲密关系劳动与准社会关系想象之间的循环回路,那么,陪伴型主播的网络直播活动,则借助直播平台的技术特性,将这个循环回路从影视、唱片行业(作为偶像工业的“宿主”)的边缘处、夹缝中提炼出来,形成某种封闭结构,并推动亲密关系劳动向着制度化、工业化方向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四、 亲密关系劳动的虚拟化与自动化
在前面的两个小节中,论文详细描述了“亲密关系劳动”为回应“准社会关系”想象而诞生,并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由“面对面”场景转移至虚拟空间,逐步走向制度化、商品化、工业化的全过程。从偶像明星的粉丝福利,到虚拟偶像/虚拟主播给予直播间观众的陪伴,这些被论文定义为“亲密关系劳动”的行为,它们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是效仿文艺作品对亲密关系的描写,还是作为日常生活之中情侣、朋友、亲子之间交互关系的“摹本”而存在的呢?
易洛思在讨论“想象与现代情感生活的关系”时,着意处理了“爱的情感同大规模制造的幻想的爱情脚本之间的关系”这个衍生问题。她认为,“想象的制度化”在大众文化领域存在一个特别有趣的转型,“其典型特征是技术和文化流派(cultural genres)越来越多地参与想象的塑造,这些技术和文化流派催生了欲望、憧憬、预支情感等,催生了对将至情感的情感(emotions about emotions to come),并决定应如何感受和上演以上情感的认知脚本”。[4]389其中,预支情感(anticipatory emotion)正是易洛思所指认的,使得现代爱情具有独特性的关键所在:它包含着诸般预演纯熟的情感和文化场景,这些场景塑造了对情感的憧憬,也塑造了情感所带来的美好生活的憧憬。她以《叶普盖尼·奥涅金》和《包法利夫人》这两部经典名著为例,引用女主人公达吉雅娜和爱玛的小说阅读经历,认为“达吉雅娜的爱情形式显然是事先制造一个想象,然后等着有个路过的对象来满足”,“这些小说塑造了她(爱玛)对爱情的各种设想以及对奢华生活的梦想”。[4]385-386
像达吉雅娜和爱玛那样,在遭遇爱情之前就已大量接触浪漫爱情题材的文艺作品,正是现代女性情感生活中的常态。这意味着,存在于现实世界里的恋爱经验,早已沦为浪漫爱情小说/诗歌的“拟像”(simulation)——它无需对任何真实存在的爱情故事进行模拟,无需参照某个“原本”,而仅仅通过模型来生产真实。[10]事实上,想要在浪漫爱情题材的文艺作品和日常生活中所见的各种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之间, 分辨出“真本”与“摹本”的序列,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同理,当偶像明星的“宠粉”言行与虚拟主播对观众的长久陪伴、有求必应,已然形成一整套清晰的、类型化的编码,成为生产亲密关系体验、同时再生产虚拟亲密关系的机器,亲密关系与亲密关系劳动之间的等级差异、先后秩序,也就彻底消失殆尽了。
不仅如此,亲密关系劳动最常见的行为主体,如虚拟偶像/虚拟主播,以及论文第一节里提到过的恋爱题材电子游戏的主人公等,都是以某个二次元风格的动画形象作为外壳/中介的。尽管也存在许多真人出镜从事亲密关系劳动的主播或偶像明星,但随着“皮套”制作成本的降低和真人偶像的屡屡“塌房”,只以虚拟形象示人的一系列商业运营模式,反倒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当我们回溯二次元文化的诞生,自不难发现,身为“日本漫画之父”的手塚治虫,就曾因为笔下的女性形象“无血无肉,没有娇媚,像人体模型”而受到严厉的批评。对此,手塚辩解道,他所描绘的女性身体从来都不是对现实世界中的肉体的“写实”,而是在将女性的身体作为符号加以展示。[11]33过去数十年间,日本ACG产业的飞速发展恰恰证明了,这些由简略线条所勾勒出的、不以任何真实存在的女性身体为“原本”的“摹本”,已足够令全世界的漫画、动画爱好者陷入痴狂。而挑起他们情欲的指示物,既可以是兽耳(非人特征)、也可以是女仆装(服饰)或双马尾(发型)等,这最终“切断了现实生活中的身体及由这个身体所引发的冲动之间的关系”[11]34。也就是说,日系漫画,尤其是色情漫画的诞生,正是以现实世界中的女性身体沦为动画、漫画里符号化的女性身体的拟像作为起点的。沿着上述脉络发展起来的二次元文化(无论是男性向还是女性向),包括效仿其美术风格的虚拟偶像/虚拟主播的皮套,自然也继承了这种暗含着“断裂”意味的文化内核。
综上所述,作为虚拟亲密关系Ⅱ型的核心机制,亲密关系劳动的行为主体的外壳及其动作本身,都已经与现实割裂开来,成为拟像。如果说,虚拟亲密关系Ⅰ型只是在亲密关系之中加入了互联网虚拟空间、计算机技术等等变量,最终仍然不免指向(或至少保留这种可能)某种肉身在场的、传统意义上的亲密关系。那么,虚拟亲密关系Ⅱ型则是将无机制的亲密关系劳动从有机制的亲密关系之中剥离出来,自虚拟空间发端,并永远地停留在“以亲密关系劳动满足并再次激发准社会关系想象”的循环回路之中。
2022年末,由美国公司Open AI研发的聊天程序ChatGPT(Chat 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正式发布,成为近年来科技领域最大的新闻事件。作为一个基于大语言模型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ChatGPT的主要功能是与人类进行聊天互动,例如根据对话中接收到的指令为用户撰写文案脚本、演讲稿甚至软件代码等。除去这类辅助办公功能,ChatGPT在应对用户日常闲聊、负面情绪或恶作剧的时候,也表现得足够体贴周到、思维敏捷。这意味着,它很可能足以胜任“亲密关系劳动”这项原本被人类垄断的工作,并且随时待命、全年无休、永不缺席。近年来,完全由大语言模型驱动的语音陪聊AI、虚拟主播和恋爱游戏的相继问世,无疑印证了上述猜想,并进一步提示了某种以“制度化、规范化的亲密关系劳动”为基础衍生出的“自动化(automation)的亲密关系劳动”或“无主体的亲密关系劳动”的可能性。
亲密关系劳动何以“自动化”?一个相对形象、直观的例子,就是科幻电影、科幻小说中,人类与人工智能建立亲密关系的烂俗桥段。尽管这类作品总是以通用人工智能技术已然取得重大突破、仿生人的智力与情感表达无限趋近于人类为前提展开,最终呈现出来的故事情节,也更像是发生在两个人类之间的爱恨纠葛,只不过其中一人被作者强行指认为人工智能而已。但无论如何,“仿生人取悦人类、为人类提供情感支持”这一想象本身,显然完全符合“亲密关系劳动自动化”(不以人作为行为主体)的定义。而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协同演化,也绝非只有“机器变得越来越智能、越来越像人类”这条单向的路径。
在人类社会步入工业化的进程中,各种手工艺技术被机器所逐步取代,并最终迈向自动化生产的历史,总是以这项技艺的制度化、规范化、流程化,即“标准作业程序”的形成作为过渡阶段的。换句话说,手工技艺的制度化与自动化,本就是先后相继的关系,没有制度化这一前置条件,自动化也不可能凭空实现。同理可知,尽管以ChatGPT为代表的聊天程序已经能向用户提供不亚于偶像明星、虚拟主播水准的自动化的亲密关系劳动(例如Snapchat平台的博主Caryn Marjorie就利用自己的视频影像、录音等素材训练出一个聊天AI,并将其租用给粉丝,向粉丝提供自动化的亲密关系劳动),但这一令人惊异的变革,也绝不仅仅仰赖于通用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事实上,过往数十年间亲密关系劳动从偶像见面会、社交网站转移到直播平台,一步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的过程,才是今时今日各种大语言模型能轻而易举地模拟出亲密关系劳动的诸般套路,而消费者亦能欣然接受的原因所在。
这意味着,亲密关系劳动的自动化并不会以一种普遍的、均质的形态降临到每个人身上。而早已被制度化、商品化、工业化的亲密关系劳动所浸染,像惯于食用预制菜和代餐粉那样,以虚拟亲密关系Ⅱ型作为装置,将自身与现实世界中的亲密关系及其对象割裂开来,反复操演着“以亲密关系劳动交换准社会关系想象”这一循环回路的那类人,则注定先行一步,率先坠入“人机亲密关系”的未来图景之中。
【注释】
① 相关讨论可参考南希·K.拜厄姆:《交往在云端:数字时代的人际关系》,董晨宇,唐悦哲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② 数字劳动:指互联网用户在网络平台上进行的、被互联网资本所剥削的各种劳动形态的统称,例如粉丝围绕某部网络电视剧展开的评论、推广以及二次创作等。它是一种典型的无酬劳动(free labour),并且通常呈现为休闲娱乐的形态(playbour)。参见Tiziana Terranova,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SocialText, no.18(2000):33-58.
③ 乙女游戏:“乙女”(おとめ,otome)在日语中的含义为“少女”。乙女游戏,指的则是目标用户为青少年女性的电子游戏,多为恋爱题材。近年来,由国产游戏厂商研发的多款面向女性用户的恋爱题材手机游戏,取得了不俗的商业成绩。这类游戏有时被称作女性向手游、恋爱手游,有时则沿用日本游戏的惯例,称之为乙女游戏,简称“乙游”。乙女游戏主要依靠男性角色们的俊美外形、迷人声线以及暧昧的台词、充满恋爱氛围的剧情、CG画面中与女主人公(通常作为玩家的代入对象)的亲密互动来吸引玩家消费。从表面上看,承担上述一系列“亲密关系劳动”的,当然是游戏中的男主人公们,但事实上,那些美丽的人物立绘、缠绵悱恻的剧情、台词,无疑都是游戏策划、美术、脚本等制作组成员的劳动成果。
④ 亲密关系劳动(intimate labor)这个概念,往往也被运用于看护病人、赡养老人等照料工作(care work)的研究。在本论文中,则只根据上述定义进行阐发。
⑤ 去病理化:指的是将某种原本被认为是病症、病态的状况或行为合理化、常态化、非病化的过程。具体到偶像工业的语境中,指的就是将附加在粉丝这个身份之上的“脑残”“癫狂”、意淫偶像等刻板印象加以清理并合理化的机制。
⑥ 这并不意味着发行唱片、参演影视剧等不是偶像的本职工作,只不过,它们本质上也是亲密关系劳动的一环。例如由偶像出演的影视剧角色,通常都会成为粉丝准社会关系想象的素材(幻想自己与偶像的另一重身份恋爱)。偶像演员在挑选剧本的时候格外重视“人设”并且不太敢于扮演反派,正是出于上述原因。这显然不是身为演员应有的行为逻辑,而是亲密关系劳动的内在需求。
⑦ 新浪微博开始启用“显示用户IP属地”的功能之后,就意外地暴露了许多偶像明星并非亲自回复粉丝评论的事实。例如明星本人在A地点有工作,回复粉丝时的IP却显示为B地点,这恰恰说明亲密关系劳动既是一份“工作”,更是必要的工作。在明星本人无暇顾及的时候,甚至会有相关工作人员随时跟进处理。
⑧ 流量数据:指某个网站地址在一定时期内的用户访问量。是衡量一个网站商业价值的核心标准。而某个偶像的流量数据,则包括他所持有的社交网站账号的数据(评论、转发、点赞、搜索等)及其音乐、影视作品的播放量、点击量等。
⑨ 这并不意味着偶像/流量明星与网络直播无关,事实上,已经有相当比例的流量明星开始通过网络直播与粉丝进行互动。但流量明星毕竟还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不定期地抽空直播,显然无法与长时间、高频次、有规律地从事直播活动的职业主播相比。而一旦某个流量明星的直播时长已远远超过其他工作的时长,那么我们不妨认为他已经转型为职业主播了。
⑩ 陪伴型主播、内容型主播和销售型主播之间,虽然存在明显差异,但也不乏多种功能、定位兼得的现象。极端的例子有董宇辉的“东方甄选”直播间,几乎集陪伴、内容(英语教学)和销售(售卖东方甄选旗下的商品)三种功能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