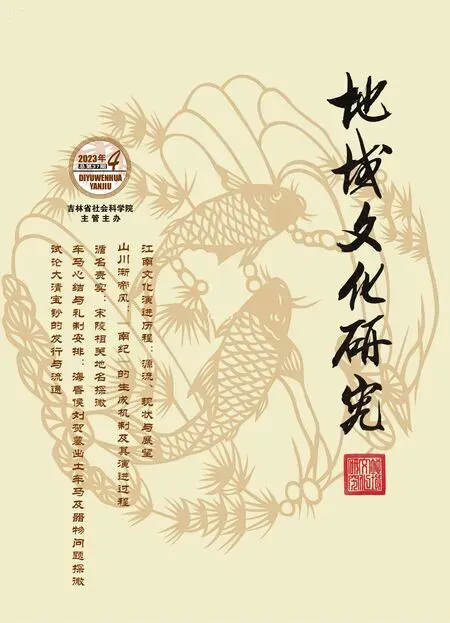山川渐帝风:“南纪”的生成机制及其演进过程
王 星
“南纪”是唐代僧一行“山河两戒”分野学说中的一个重要地理概念,自唐至清,这一地理概念反复出现在各种地理总志、地方志及诗、词、赋等文学性文本和诏、启、制、告、檄、劄等事务性文本中,对古人的空间认知和地理知识表述产生了重要影响。周振鹤即指出,在王士性“三龙说”提出以前,中国古代有关区域地理的认识,长期流行的就是“山河两戒”说①(明)王士性著,周振鹤编校:《王士性地理书三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页。。近年来,学界逐渐注意到了“山河两戒”分野学说②刑庆鹤:《试论〈天下山河两戒考〉中的天文学》,《安徽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85年第1期。唐晓峰:《两幅宋代“一行山河图”及僧一行的地理观念》,《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邱靖嘉:《山川定界:传统天文分野说地理系统之革新》,《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3期。,但遗憾的是,这些探讨多以介绍、评说为主,对“南纪”仍缺乏独立的、长时段的历史地理学分析,且其背后所折射出的政治、文化认同问题亦未得到应有揭示。实际上,“南纪”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经过漫长的知识累积与人为地空间型构以后,“南纪”逐渐超越了分野系统赋予它的地理内涵,而被建构为一则划分“异质”风土的文化符号。因此,“南纪”的生成、凝固与扩张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地理学命题,又是一个典型的政治学和文化史学的命题。
一、南纪的来源——再谈“山川定界”分野理论的相关问题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此处所谓“南纪”的来源有两层意义指向:一指“南纪”的文本来源。二指“南纪”的概念来源。关于“南纪”的文本来源,其文献脉络较为清晰。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二所言,一行“山河两戒”说原载于己著《唐大衍历议》“分野”节,惜此书在北宋时业已亡佚,欧阳修著《新唐书·天文志》时,曾抄录部分内容,“南纪”因此得以保存①(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66页。清人王谟在《汉唐地理书钞》中承其说。。
相较于文本来源的清晰明了,“南纪”的概念来源却十分复杂。对“南纪”概念的梳理是我们深入辨析“南纪”空间的理论基础,为便于讨论,兹引“南纪”内容如下:
一行以为,天下山河之象存乎两戒……南戒,自岷山、嶓冢,负地络之阳,东及太华,连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衡阳,乃东循岭缴,达东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②(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7页。
不难看出,“南纪”实为一条地理界限,这条界限起自岷山,向东到达太华山,与商山、熊耳山、外方山、桐柏山等相连,再折向南边,过江汉抵衡阳南部,又沿岭缴向东,至东瓯、闽中而完结,其目的是为了“限蛮夷”。一行主要从三个方面来对“南纪”进行界定:一是“南纪”的构成要素,即山川的类型与数量。二是这些要素的排列组合方式,也即山川走势。三是“南纪”的作用。“南纪”山川的类型与其所发挥的“限蛮夷”的作用相关,而山川的数量与走势则直接影响到“南纪”空间的大小。
学界对一行“山川定界”分野原则的认识,一直以来都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认为《史记·天官书》中就有“以山河标志分野”的方法,一种则认为隋唐时期才出现关于“山川定界”的分野理论③唐晓峰在《两幅宋代“一行山河图”及僧一行的地理观念》一文中认为,以山河标志分野并非创自一行,这一分野原则在《史记·天官书》中就已出现。邱靖嘉在《山川定界:传统天文分野说地理系统之革新》一文则认为,分野中山川定界原则的确立发生在隋唐时期,一行“山河两戒”说即为其重要代表。。而笔者认为,《史记·天官书》只是“山川定界”分野理论的远源,最早系统运用山河标志来进行分野应当始于西汉的纬书《河图》《洛书》,一行“两戒”说是《河》《洛》分野理论在唐代的发展。
(一)作为“山川定界”远源的《史记·天官书》
唐晓峰认为:“以山河标志分野的说法,在一行之前早已存在。例如《史记·天官书》:‘杓,自华以西南……横,殷中州、河济之间’”④唐晓峰:《两幅宋代“一行山河图”及僧一行的地理观念》,《自然科学史研究》1998年第4期。。《天官书》中的这段话确实是在说北斗七星中的杓、衡、魁与地表山川的对应关系:斗杓对应华山及其西南地区,斗衡对应黄河、济水之间的地区,斗魁对应东海、泰山之间及其东北地区。但此类分野的地理对应十分粗糙。首先,与北斗相对的华山、河、济,海、岱等只是作者为划定地理疆域所随机给定的地标,其内部并无特定的关联性。其次,北斗只对应了部分地理范围,并没有将“中国”疆域完全代表,如古荆扬地区即被排除在外。
其实,除“北斗分野”是用山川定界,《天官书》中“日、月食天干分野”及“气分野”均以山川定界。“日、月食天干分野”即言:“甲、乙,四海之外,日月不占。丙、丁,江、淮、海、岱也。戊、己,中州、河、济也。庚、辛,华山以西。壬、癸,衡山以北”①(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32—1333页。。又“气分野”云:“自华以南,气下黑土赤。嵩高、三河之交,气正赤。衡山之北,气下黑下青。勃、碣、海、岱之间,气皆黑。江淮之间,气皆白”②(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37页。。但与“北斗分野”类似,“日、月食天干分野”和“气分野”中的地理体系同样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在这两种分野中,江汉及其以南地区亦被完全忽略。
《天官书》的材料来源十分复杂,司马迁自述曾参引多种“云气之书”,“推其文,考其应”③(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3306页。而终成此书。据赵继宁考证,除诸子、兵书外,《天官书》还至少征引了包括《甘石星经》在内的22种天文学著作④赵继宁:《〈史记·天官书〉研究》,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57页。。因此,《天官书》是司马迁对春秋战国以来星占学的借鉴和总结,以山川定界只是出于星占学上叙述便利的需要,本意并非要以山川来革新分野中的地理系统。故严格意义上讲,《天官书》中所载“以山河标志”分野的用例,只能算作后世“山川定界”分野理论的滥觞。实际上,《天官书》运用的乃是“十三州”分野系统,其将二十八宿与汉十三州相对应:“角、亢、氐,兖州。房、心,豫州……翼、轸,荆州”⑤(汉)司马迁撰:《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330页。此后在“行星和恒星结合的分野”与“辰星分野”中,地理系统均是以十三州统之。,即已言明。
(二)《河图》《洛书》正式以“山川定界”统筹分野系统
最早系统运用山河标志来进行分野的应该是西汉的纬书《河图》和《洛书》⑥为便于叙述,后文所言《河图》《洛书》,即专指汉唐间流传的《河图》《洛书》的纬书。。“河洛之书”最早见于《周易》,其《系辞上》云:“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⑦(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70页。。但到春秋战国时期,《河图》《洛书》早已散佚,不为孔子、管子等人得见⑧孔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已矣”。(战国)孔子著,杨树达疏:《论语疏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217页。管子曰:“河出图,洛出书,地出乘黄,今三祥未有见者”。(战国)管子著,(唐)房玄龄注:《管子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81页。。至汉代大兴谶纬之学,始又出现了关于《河图》《洛书》的纬书。据汉代纬书《春秋说题辞》载:“河龙图发,洛龟书感。《河图》有九篇,《洛书》有六篇”。此“河九洛六”的文献载体在汉唐间一直存在,且影响很大,不仅被郑玄征引注《易》⑨(汉)郑玄注,(南宋)王应麟辑,丁杰等校订:《周易郑注》,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94页。,还曾被《隋书·经籍志》所著录⑩(唐)魏徵等撰:《隋书》,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940页。。《春秋命历序》在谈及此《河图》时即言:“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11]《春秋命历序》原书已轶,此句收入《水经注》中。(北魏)郦道元原注;陈桥驿注释:《水经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页。。可见,汉唐间的《河图》《洛书》载有大量分野内容[12](唐)瞿昙悉达所著《唐开元占经》也大量征引了此《河图》《洛书》的分野方法。如其卷1“天占”、卷5至卷9“日占”、卷11和卷17“月占”、卷31至卷36“萤惑占”、卷38“填星占”,卷46和卷51“太白占”、卷53、卷55和卷56“辰星占”等均曾征引《河图》《洛书》之说。详参(唐)瞿昙悉达著:《唐开元占经》,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且其分野运用的正是“江河山川”的地理系统。
《河图》《洛书》早已散佚,但其分野所用地理系统却部分保存在了李淳风所著《乙巳占》之中,《乙巳占》卷三“分野”节载:
《洛书》分二十八宿于左:岍:角。岐:亢。荊山,氏。壶口:房。雷首:心。太岳:尾。砥柱,岐。析成:斗。王屋:牛。太行:须女。恒山:墟。碣石:危。西倾:室。朱囫:毕。鸟鼠:奎。太华:娄。熊耳:胃。外方:昂。桐柏:毕。陪尾,觜。冢:参。荆山:东井。内方:舆鬼。大别:柳。岷山:七星。衡山,张。九江,翼。敷浅原,轸。右已上《洛书》,禹贡山川配二十八宿①(唐)李淳风撰:《乙巳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3页。唐晓峰以为将禹贡山川配二十八宿本自李淳风,误矣。此盖出自《洛书》,李淳风《乙巳占》引之。。
又前文引《河图》:
河导昆仑山,名地首,上为权势星。东流千里,至规其山,名地契,上为距楼星。北流千里,至积石山,名地肩,上为别符星。南(流)千里,入陇首山间,抵龙门首,名地根,上为宫室星……洛泾之起,西维南嶓冢山,上为狼星。漾水出端,东流过五关山南,上为天高星。汉水东流至岳首,北至荆山为地雌,上为轩辕星……附耳星,洛水击其间,东北过五湖山,至于陪尾②(唐)李淳风撰:《乙巳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52页。。
据日本学者安居香山和中村璋八的研究,上引《河图》内容应属于“河图绛象篇”③(日)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辑:《纬书集成》,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186页。。但安氏与中氏著《纬书集成》却漏录《洛书》分野部分,盖他们此前并没有注意到《乙巳占》中的《洛书》引文。笔者推断,上引《洛书》分野内容很可能出自“洛书甄曜度篇”④“洛书甄曜度篇”主要涉及星象占卜和天文分野的内容,其中“嶓冢之山,上为狼心”、“五关山为地门,上为天高星”、“荆山为地雌,上为轩辕星”等部分,即与上引禹贡山川配二十八宿的内容十分贴合。详参《纬书集成》所辑“洛书甄曜度”。。《洛书》以二十八宿对应《禹贡》“导山”部分的二十八座(条)山川(其中,山二十七,水一,唯“九江”为湖),对应层次也完全忠于《禹贡》原文叙述顺序⑤《禹贡》“导山”从岍、岐开始,至敷浅原结束,与《洛书》分野同。。《河图》虽不像《洛书》那样忠实《禹贡》原文,但大致还是以《禹贡》“导水”为脉络⑥如《禹贡》河水部分云:“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洛书》则将河分为在昆仑流域对应权势星,在规其流域对应距楼星等九部分。又汉水部分云:“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洛书》将漾水对应天高星,汉水对应轩辕星。汉水入江以后无对应。。《禹贡》开宗明义:“禹别九州,随山浚川”⑦(清)胡渭著,邹逸麟整理:《禹贡锥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6页。,禹所“奠高山大川”是九州内具有代表性的山川,《河图》《洛书》以《禹贡》山川作为分野的地理系统,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该地理系统将“九州”地域范围完全涵盖,使得分野具有完整性。二是山川体系来自《禹贡》,使得分野具有学理上的系统性与经典性。因此,我们可以说《河图》《洛书》最早系统地运用山河标志来进行分野。
(三)“山川定界”在唐代的变奏与定型
作为纬书的《河图》《洛书》虽然最早系统运用《禹贡》山川来统筹分野中的地理系统,但这套分野理论一直没有进入到官方知识体系中。及至唐朝初年,李淳风始借鉴这套分野方法,“但据山川分尔”的分野理论才正式被官方采纳。
李淳风历仕太宗和高宗两朝,在太史局任职近四十年,对唐代的天文历法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①(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717页。。其天文分野理论主要载于己著《法象志》一书,惜此书亦已亡佚,我们今天只能在两唐书和《乙巳占》中大略知其分法。在李淳风看来,刘向编撰《汉书·地理志》时,郡国地名的变化已使得天文系统中“星次度数”“莫审厥由”,加之秦火以后史书残缺,导致后世沿用的分野系统出现“缺疑”,“唯有二十八宿,《山经》载其宿山所在,各于其国分星,宿有变则应乎其山,所处国分有异,其山又上感星象”②(唐)李淳风撰:《乙巳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3页。,故其主张用《山经》中的二十八山来重新规划分野中的地理系统③关于二十八山与二十八星宿的对应关系,吴晓东有《占星古籍:从〈大荒经〉中的二十八座山与天空中的二十八星宿对应来解读〈山海经〉》一文详细论述,兹不赘言。吴文载《文化研究》2007年第3期。。李淳风用《山经》系统来划分地界,表面上与《河图》《洛书》采用禹贡系统相异,但从《乙巳占》中详引《河图》《洛书》的分野方法来看,这显然与《河图》《洛书》以“山川定界”的分野原则一脉相承。不仅如此,“李淳风撰《法象志》,因《汉书》十二次度数,始以唐州县配焉”④(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17页。,他还将唐代州县具体地统筹到了分野体系之中,如“角亢,郑之分野……今之南阳郡,置颍川、定陵、襄城、颍阳、颍阴、长社、阳翟、郏鄏,东接汝南,西接弘农”⑤(唐)李淳风撰:《乙巳占》,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44页。,即此之类。
旋至开元,地理情况又发生了改变,李淳风的分野系统夹杂着唐初州县,实际操作起来极不便利⑥《新唐书》卷31 在论及当时分野学说现状时说:“近代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国。虞、夏、秦、汉,郡国废置不同……而或者犹据《汉书·地理志》推之,是守甘、石遗术,而不知变通之数也”。见(宋)欧阳修、宋祁等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820页。。沿着李淳风“山川定界”的分野方法,一行剔除了地理系统中具体的郡国州县,完全以山川来划分地界。
关于“山河两戒”的山川来源,清人徐文靖曾在己著《山河两戒考》中辨析道:“北戒自三危,南戒自岷山,其即禹贡之导山”⑦(清)徐文靖:《天下山河两戒考》卷1,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雍正刻本,第2页。,并进而认为“南纪”为《禹贡》“导山”中的“南条”⑧(清)徐文靖:《天下山河两戒考》卷1,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雍正刻本,第2页。。徐氏之说大体可信,“南纪”山川确实本自《禹贡》:“南纪”共有十座界山,其中八座来自《禹贡》,即岷山、嶓冢、太华、熊耳、外方、桐柏、荆山、岭缴,只有商山、武当溢出《禹贡》“导山”之外。所以南纪本于《禹贡》基本是可信的。但并非全为“南条”。实际上,岷山、嶓冢、太华、熊耳、外方、桐柏皆为《禹贡》北条南境山脉,只有荆山属南条北境山脉,岭缴属南条南境山脉。所以“南纪”是一行取南条、北条诸山而新创的一条地理界限。关于此,宋人陈藻亦已注意到,其将“南纪”与“三条四列”并论,即承认“南纪”山川本自《禹贡》,但又认为“一行又皆以为(三条四列)不然,而另立两戒之论”⑨(宋)陈藻:《乐轩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95页。。所谓“禹贡之书本载治水本末,而一行之言则将以山河两戒分属周天分野之星”⑩(宋)林之奇撰:《尚书全解》,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2年,第523页。,《禹贡》“导山”被一行有选择地挑选、排列后,成为划分分野的地理系统。
要之,《史记·天官书》可看作是“山川定界”分野理论的滥觞,至《河图》《洛书》方系统地以山河标志来进行分野。此后,这一分野方法经李淳风和一行的吸收、改造后而正式定型,并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二、唐至宋元时期“南纪”的知识累积
杜甫是第一个对南纪进行大量书写的人,其《故司徒李公光弼》一诗中就有:“吾哭思孤冢,南纪阻归楫。”②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82页。《故右仆射相国张公九龄》中有:“相国生南纪,金璞无留矿。”③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14页。《后苦寒二首·其一》:“南纪巫卢瘴不绝,太古已来无尺雪。”④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48页。《暮春江陵送马大卿公恩命追赴阙下》中有:“北辰征事业,南纪赴恩私。”⑤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880页。《江阁对雨有怀行营裴二端公》中有:“南纪风涛壮,阴晴屡不分。”⑥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78页。《题衡山县文宣王庙新学堂呈陆宰》中有:“南纪改波澜,西河共风味。”⑦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2079页。后人普遍认为,杜诗中的南纪指的就是一行“山河两戒”中的南纪,这从宋代的《补注杜诗》《杜工部草堂诗笺》《分门集注杜工部诗》,一直到清代的《杜诗详注》《杜诗镜铨》等较有名的注杜本子上就不难看出⑧如《补注杜诗》卷14即言:盖南纪乃分野名,《广天文志》云:“东循岭徼,达瓯闽中是谓南纪,所以限蛮夷也”,《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卷1与《补注杜诗》同,《杜诗镜铨》卷14:“《唐书》自上洛南逾江汉,携武当荆山至于于衡阳,乃东循岭徼,远东迹至闽中是谓南纪”,等。不止注杜的本子,韩愈《复志赋》中有:“至曲江而乃息兮,逾南纪之连山”句,宋注本《东雅堂昌黎集注》《五百家注昌黎文集》《详注昌黎先生文集》《朱文公校释昌黎先生集》等皆以韩诗之“南纪”即为一行“山河两戒”中的“南纪”。事实上,检点一行以前的文献,诗(文)中鲜少用“南纪”,而一行以后,“南纪”则大量出现在文学作品之中,文学作品中的“南纪”或有受自《诗经·小雅·四月》以来“南纪”意象的影响,然更重要且经常的,诗(文)中的“南纪”应当指的是经一行塑造以后的“南纪”。。此后,在韩愈和杜牧等人的文学创作中,又屡见“南纪”的用例⑨如韩愈《复志赋》:“逾南纪之连山,嗟日月其几何兮”。(唐)韩愈著;钱仲联,马茂元校点:《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18页。杜牧《奉送中丞姊夫俦自大理卿出镇江西叙事书怀因成十二韵》:“惟帝忧南纪,搜贤兴大藩”等。(唐)杜牧著,陈允吉校点:《杜牧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98页。。宋元以来,“南纪”则更为时人所广泛接受。宋代诸如司马光、刘攽、刘敞、洪朋、谢薖、夏倪、曾觌、黄庭坚、李纲、王十朋、陈与义、杨万里、楼钥、李曾伯等人,元代诸如白埏、程端礼、程钜夫、丁复、丁开复等人都曾有过“南纪”书写,且内容涉及赋、诗和词等多种文体①如宋代司马光《梅圣俞挽歌二首》:“南纪光华减,中朝俊秀贫”。刘攽《苦热》:“炎晖共兹世,南纪独何偏”。元代白埏《同陈太博诸公登六和塔》:“绝顶按坤维,始见南纪偏”等诗,不胜枚举。。由于“南纪”在唐宋文学中的广泛运用,故宋人撰《小学绀珠》《玉海》《事类备要》《山堂考索》等诸类书,即悉录“南纪”条②如《小学绀珠》卷1“天道”类即有“两戒”条。《玉海》卷20“地理下”亦有“唐山河两戒”条。章如愚《山堂考索》卷58“地理门”下“分野条”录且仅录《新唐书·地理志》中关于一行两戒之说。。
除了文学性文本,在时人的事务性文本中,亦多见有关南纪的表述。如唐张说在《荆州谢上表》中即云荆州:“山列楚望,水横南纪”③(唐)张说撰:《张燕公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第117页。。又宋人陈藻在策问“地理篇”中借“南纪”来阐明地理形势:“巴蜀虽南纪山河之曲,而其地正西焉”④(宋)陈藻:《乐轩集》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5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94页。。刘克庄《回荆湖制置使启》则云荆湖地区:“南纪宣威,密倚上游之重”⑤(宋)刘克庄著,辛更儒校注:《刘克庄集笺校》,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22页。。再如元人孔浍在《荊山璞赋》中言荆山“钟南纪之地灵”⑥韩格平主编,方稻校注:《全元赋校注》,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16年,第72页。等等。甚至在墓志和祭文中,亦时见有关南纪的用法⑦如宋人洪适《墓祭韩权郡文》中即有:“寄遗骨兮南纪,俟后人兮谋迁”句。。可以说,无论是在上行文书,还是在平行文书和下行文书,乃至唐宋人的日常生活中,南纪这一地理概念已然广入人心,深深地嵌入到了时人的知识体系之中⑧如在宋人魏齐贤、叶棻编《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中,时人有关“南纪”的用例即大量出现在“表”“贺启”“上启”“制诰”“婚书”等条目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唐至宋元时期“南纪”在社会层面被广泛应用的表象正说明,在分野学说内部,作为对“九州说”和“十三州说”分野体系的技术革新,一行的“山河两戒说”实际已经逐渐掌握了分野学说的主流话语。这从时人在编纂地志时对分野系统的选择上即不难看出。如《吴郡志》叙“吴”时,曾用皇帝、费直、蔡邕、陈卓等十一人的分野之说来佐证吴地分野,然无论是从篇幅还是内容来看,范成大主要征引的还是一行“所分星次”⑨(宋)范成大纂修,汪泰亨等增定:《吴郡志》,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700页。。再如《吴兴志》用《汉志》等历代地志而分野殊异,文末还是引一行之语调和:“一行有言曰:古今辰次与节次相系,各具当时,历数与岁差迁徙不同也”⑩(宋)谈钥纂修:《吴兴志》,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4685页。。又如(咸淳)《临安志》“吴越”分野下云“其分野自南河下流,穷南纪之曲”[11](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35页。,并将《汉书·天文志》中的吴越分野与一行“山河两戒”说中的吴越分野对照,云:“唐一行两戒之说分南北河及吴越门,以云汉纪之,则其术详矣”[12](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535页。。它如《齐乘》等志书,情况与之大抵类似[13]《齐乘》卷1“分野”条引一行语云:“邹鲁,皆负海之国”。(元)于钦纂修,于潜释音,(清)周嘉猷考证:《齐乘》,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14页。。其实不光是地方志,此时期的地理总志也在积极采纳“两戒说”。如《太平寰宇记》“四夷总序”即大量征引“两戒说”来论述“华裔之大经”[14](宋)乐史撰,王文楚等点校:《太平寰宇纪》,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293页。。又《舆地纪胜》亦曾多次引用“南纪”说来界定属州分野[15]如卷22“池州”下即云:“分野是谓南纪”。又卷159“合州”下云巴蜀诸川“所谓南纪”。再如卷185“阆州”下云其分野“与一行之说近之”,等等。。而《方舆胜览》虽鲜在分野中用南纪之说,但在“四六”下却择录了大量关于“南纪”的诗文①如卷23“湖南路”下:“惟翼畛牛女之墟,居南纪之上游。”卷27“湖北路”下:“开蕃南纪,遥制边头”,等等。。
自“山河两戒”之说出,后世言星土、叙方志者莫不奉为圭臬,宋人唐仲友在《帝王经世图谱》中就直称其“最得天象之正”②(宋)唐仲友撰:《帝王经世图谱》卷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2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509页。,所谓“得天象之正”,即云其“体现出一种不受朝代更迭和地域变迁因素影响、持久普适的文化地域观念”③邱靖嘉:《山川定界:传统天文分野说地理系统之革新》,《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3期。。这种持久、稳固的文化地域观念,使得“南纪”在唐至宋元之际被广为接受、传播和运用,并逐渐凝固为一个划分内外、区别夷夏的文化符号。
三、“南纪”的边界定型
与南纪在唐至宋元之际知识累积的过程相一致,此时期,南纪山川及其所表达的象征意义正在被形塑为时人心中一条重要的地理分界线。这一地理分界线的定型,一方面是以一行给定的界山界河为基础,而另一方面,区域文化地理的研究实践又在提醒着我们,对任何区域或边界的认识,不能仅仅依靠“给定”和“划分”来进行判定,“当时人的认识是至关重要的”④张伟然:《中古文学中的地理意象》,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4页。。因此,我们对南纪边界的讨论,既要包括一行文本意义上的南纪边界,更要考虑到古人实际运用(感知)中的南纪边界。
围护体系,如墙体、楼盖,其重要的承重材料为木龙骨及其两侧的木基覆面板或防火石膏板,共同构成围护体系的基础。其选材均为国际通用尺寸的规格材及板材。为保证围护体系整体强度,同时确保板材之间均可拼接固定于木龙骨之上,需要专业人员根据施工图纸对围护体系进行拆分编号,然后依据木结构建筑相关设计规范及选材的模数要求进行龙骨布置图设计(图10、11)。 如若龙骨布置过疏,则强度较弱,不利于围护体系的安全性;如若龙骨布置过密,则会造成规格材及板材的浪费。
既然边界是一定空间结构的反映,那么地图则无疑是表现空间结构最直接有效的方式之一。一行以后,宋代曾出现过三幅两戒之图,它们分别为北宋税安礼的“唐一行山河两戒图”、南宋唐仲友的“禹贡九州山川之图”和“唐一行山河分野图”⑤这三幅图后来都收入曹婉如等主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至元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98页、第120页、第121页。。其中,“两戒图”和“分野图”是一行“山河两戒”的专图,“禹贡九州山川之图”则为合图,图中另有禹贡九州和“三条四列”的标绘。两幅专图的绘制要更加详审,不仅有志,还绘有唐代的州县设置,合图仅以禹贡九州为底图,亦无志。就准确性而言,唐仲友的两幅地图更能反映一行“两戒说”原意,税安礼的“两戒图”将荆襄与衡岳之间的广大地区排除在外,颇与一行本意相乖离。
实际上,无论是税图还是唐图,其对“两戒”的绘定均系于分野理论的讨论之下⑥如税安礼的“唐一行山河两戒图”,即和“天象分野图”及“二十八舍辰次分野图”放在一起。而唐仲友的“禹贡九州山川之图”、“唐一行山河分野图”也是和诸如“九州分星之谱图”列为一类。这充分体现出图作者将其系于分野理论之下探讨的写作动机。。也即,宋代出现的三幅“两戒图”,或详或略,或虚或实,其实是关于一行分野理论的学术探讨,而较少关涉到时人心目中真实的南纪边界。欲对南纪边界作一彻底厘清,我们还需回到古人的实际运用(感知)中去。
对边界感知(感觉文化区)的研判,诗文无疑是最适宜的材料①如迈克·克朗(Mike Crang)即认为:“文学作品的主观性并不是一种缺陷,事实上,正是它的主观性言及了地点与空间的社会意义”。迈克·克朗著,杨淑华、宋慧敏译:《文化地理学》,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页。阿兰·贝克(Alan Reginald Harold Baker)也持有类似观点:“小说与其他文学作品的形式可以被用来揭示在特定时期对某一地点进行感知的具有历史烙印的结构”。阿兰·贝克著,阙维民译:《地理学与历史学——跨越楚河汉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124页。实际上,张伟然在探讨唐代感觉文化区时对诗文材料的运用,堪称国内实证研究的典范。。南纪诗文对于确定南纪边界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唐至元的诗文材料较为集中,充足的样本数据能够反映群体的一般情况。二是“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的文学作品,天然的与文化地理感知相契合。
此次统计,共计得南纪诗文54组。其中,唐代9组,宋代37组,元代8组。由唐入宋,时人对南纪的运用不断增多,感知不断增强,这正与上节我们所讨论的南纪在唐至宋元之际的知识累积过程相一致,兹不赘言。值得注意的是,南纪诗文的空间分布呈现出两大显著特征:一是有44组样本数据分布在南纪的东、北侧,占总量的45 强,而分布在南纪西、南侧的数量仅为10组,不到总量的1 5,南纪诗文呈现出明显的界内集群倾向。二是分布在南纪边界两侧附近的诗文共有29组,占总量的一半多,南纪诗文边界聚合的特征也较为显著。
南纪诗文的界内集群,更确切地讲,是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集群。诸如陇右道东部和山南东道北部地区虽然也在南纪之内,但这些地区却丝毫引起不了古人的南纪感知。究其原因,是因为南纪上游在传统分野视域下属雍分,而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则属吴、越和楚分。唐宋以降,虽然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大发展,但不得不承认,在对地域文化的认同上,这些地区还是与中原有所疏离,所以时人一到长江以南,便觉得接近“南纪”。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时人在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的南纪感知十分强烈,但却绝少越过一行对南纪边界的界定,这正说明“南纪”对古人的空间感知有着较强的规范作用。更进一步,在规范作用的反复确认之下,南纪边界的权威性也在此时被逐渐明确。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新唐书》对南纪界山界河的记载颇为详细,宋人包括我们今天均可借此图绘出“南纪”的大致走向,但所谓“纪,纲纪也。谓经带包络之也”②(唐)杜甫撰,(清)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415页。,一行分野系统中的南纪实际是带状展开而非线性分布,后人对南纪的线性图绘只是为了理解上的便利,并非此线性边界即为“南纪”的“金科玉律”。如南纪过武当、荆山后的下一节点是衡阳,从荆山到衡阳几乎南北贯穿山南东道和江南西道。我们将荆、澧、朗、潭等州排除在外,纯属是图绘对文字的“直译”,实际上,自荆山到衡阳几乎无法避免上述四州的实际辖地。基于此,时人在澧州、永州和福州等边界附近的南纪书写庶几也可看作广义上的南纪之内。当然,这也是上文将南纪边界外侧附近的诗文也算作边界聚合的内在原因。关于南纪诗文的边界聚合,我们可以发现,襄州、江陵、鄂州、岳州、衡州、韶州和福州等地又是重点聚合地区,此7地的南纪诗文有22组,占南纪边界附近诗文总量的七成有余。所谓“近乡情更切”,越是南纪边界附近,就越容易激起古人对南纪空间的体认。且在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南纪”段,这种体认就会更加深刻,如上引“南纪之曲”的襄州、江陵、鄂州,“至于衡阳”的衡阳,“东循岭缴”的韶州,以及“闽中”的福州等地,均是南纪诗文的重点聚合地区。南纪诗文的边界聚合现象,反映出时人的地理感知与南纪经典文本之间的强烈契合,古人对南纪的体认大致也是沿着一行给定的南纪走向而展开。
南纪诗文界内集群与边界聚合的分布态势,是时人的地理感知大量叠加于南纪空间的必然结果,这说明唐至宋元时期人们对南纪边界的地理感知趋于稳固,南纪的空间范围即由此得以定型。
四、明清时期“南纪”的边界推移及其政治意涵
按《新唐书》所载南纪走势,云贵、两广和台湾地区均在南纪以外。元以前,时人对南纪的体认谨遵《旧唐书》中的文本规范,这三个地区并不能有效引起古人对南纪的地理感知①实际上宋人也有称桂州和广州为南纪的例子。但考虑到文学书写主体较强的主观性,以及两处例证的相对孤立性,我们仍然认为时人对南纪的主流认知并不及于此地。。但自明代起,人们对南纪的解读和认知发生变化,南纪作为一条虚拟的华夷界限亦开始在以上三个地区寻求突破。具体如下:
(一)南纪边界在云贵地区的推移
中原与边疆地区的人员流动对南纪边界的扩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明初平显在《松雨轩诗集》中就多次称云南地区为南纪,如其《太傅大人回滇》中有:“请公暂挹滇池水,霈作甘霖泽南纪”②(明)平显撰,管正平点校:《松雨轩诗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9页。。《题朱寅仲画呈谢国公大人》有:“滇之海子三百里,天闭灵奇甲南纪”③(明)平显撰,管正平点校:《松雨轩诗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8页。。《奉次素轩大人诗韵五首》有:“南纪民生遂,余波浩莫量”④(明)平显撰,管正平点校:《松雨轩诗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1页。。《贺黔国大人》有:“报国已收南纪捷,春江拭目锦帆回”⑤(明)平显撰,管正平点校:《松雨轩诗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54页。。平显字仲微,原籍杭州钱塘县,洪武年间曾谪戍云南。杨慎《升庵集》卷五十七有“滇中诗人”条,其言:“滇中诗人,永乐间称‘平居陈郭’”⑥(明)杨慎:《升庵全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699页。,这里的“平”即指平显。在平显看来,滇中“天闭灵奇”,民生安乐,俨然已与中原无异。其实,杨慎本人也曾谪戍云南近三十年,现存《滇程记》《滇载记》《云南山川志》等一百八十多种著作(篇章)均为他在云南时期写就,其《昆阳望海》中亦有:“昆明波涛南纪雄,金碧荡漾银河通”⑦(明)杨慎:《升庵全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85页。句,不仅认为昆明雄于南纪,而且还言滇池上通银河,有意识地运用“云汉升降”说来建构云南属于南纪的合法地位⑧“云汉升降”说属于一行分野理论中的内容,它与“山河两戒”说一指天,一指地,相互联系,交相辉映,构成了一行分野思想的基本框架。。明清以降,随着中央对云南地区的纵深经略,特别是越来越多的中原士人涌入边地,观看和感知云南的视角即发生了由“俯视”到“平视”的转变。再如明林俊《送柴季常宪副滇南》:“百年弦颂外,礼则驯陆梁”⑨(明)林俊撰:《见素续集》卷1,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5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456页。。清钱沣《乙未乞假还滇留别京中诸友四首》:“寰中南纪是巫庐,云彩南边路更余”⑩(清)钱沣撰:《钱南园先生遗集》,《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9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0页。等均直称云南为南纪。
除了云南,贵州也在南纪问题上积极寻求突破。如明神宗三大征之一的播州之役后,陶望龄即在《西南平播州记》一文中将此次征伐看作是“永殿我南纪”①(明)陶望龄撰,张昭炜主编,李会富编校:《陶望龄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341页。的重要举措。而(乾隆)《桂平县志》则堪称是指贵州为南纪的有趣案例,其“山川图志”下云:“建都览六合之大势,建邑览一方之形胜,相山川灵秀所聚而辨方正位、度地居民,所必然耳”②(清)吴志绾修,黄国显纂:(乾隆)《桂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第5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53页。,清人称贵州“山川灵秀”的理论来源即是一行的“两戒说”,“桂平山川以僧一行山河南戒之说推之……西粤本岭徼地,而桂平又在省会东南,其山川左右皆自黔滇而来”③(清)吴志绾修,黄国显纂:(乾隆)《桂平县志》,《中国地方志集成》(第54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53页。。事实上,一行所说的南纪山脉走向是“至于衡阳,乃东循岭缴”,其所循的自然是大庾岭,而清人偷换概念,认为西粤的越城岭、都庞岭和萌渚岭也是岭徼之地,就顺理成章地将云贵等“黔滇而来”的山川也纳入到南纪范围之中。当然,曲解“岭缴”概念进而扩展南纪边界并非只发生在《桂平县志》中,晚清时魏源更为夸张,其直接指衡山为五岭,并认为:“五岭始能为中国华蛮之界,非衡岳一峰所能界南纪也”④(清)魏源:《魏源全集》第2册,长沙:岳麓书社,2011年,第87页。。清人对何为南纪自然十分谙熟,但若严格按照一行对南纪的界定,则贵州早已入于蛮夷之地,这无疑会损害主流意识形态对边地文化的建构。故在文本事实与价值认同之间,清人选择了后者。此种缘由,仍与中央对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经略的效果息息相关,《弘治贵州图经新志》载当时贵州地区云:“是邦昔在荒服之外,民皆夷獠,风气习俗不类中州,今则役服供赋,一循法庭,衣冠言编,悉同中华”⑤(明)沈庠修,赵瓒撰:(弘治)《贵州图经新志》,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53页。。所以贵州被纳入南纪的过程亦与其“王化”进程密切相关,明人张天复《贵竹道中》一诗即云:“迷辙周南纪,崎岖入夜郎。山形疑楚蜀,蛮俗即氐羌。远岫浮烟翠,孤城宿草黄。圣朝家四海,声教被遐荒。”⑥(明)张天复:《鸣玉堂稿》卷11,《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34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03页。贵州的自然风光与楚蜀相似,风俗习惯与氐羌相似,然而因为其受到“圣朝”声教浸润,仍被认为在南纪之内。
(二)南纪边界在两广地区的推移
汤显祖在《游罗浮山赋》中写道:“南岭之南,北户之北,固已舆象之所偏,庞独龙之所长寐矣。而庐岳,天子之障,衡山,祝融之标。枢轴虽连于西极,经络未穷于南纪”⑦(明)汤显祖著,徐朔方笺校:《汤显祖集全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341页。。汤氏一方面认识到了岭南是舆象所偏之地,另一方面,他仍认为该地“未穷于南纪”。汤显祖是明末之人,其实在此之前,明人就已经认为岭南属于南纪的一部分。明初魏观在江夏作有《亲友》一诗,其云:“东山偶为苍生出,南纪来分圣主忧”⑧(明)刘仔肩辑:《雅颂正音》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598页。,又刘宗弼《过舒州吊青阳余先生》诗云:“指挥戎马驻江濒,南纪安危寄一身”⑨(明)刘仔肩辑:《雅颂正音》卷2,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7年,第611页。,到了天顺年间,叶盛作《癸未岁广东察院淸明集本朝名人诗十首》时则将它们辑在一起,用以描写广州⑩(明)叶盛撰:《菉竹堂稿》,中华再造善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6年,第32页。。明初人称江夏和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为南纪,叶盛认为这些诗句用来形容广州也毫无违和感,时人对南纪认知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明中期以后,两广属于南纪已为人们所普遍接受,如明“后七子”之一的吴国伦曾知高州府(约辖今广东茂名、高州、电白、信宜、化州、廉江等地),在此期间,他就曾多次在诗中称岭南地区为南纪,其《与吴士二首·其一》有:“将穷南纪胜,一寄北冥踪”①(明)明吴国伦撰:《甔甀洞稿》卷1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2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651页。,《寄怀张肖甫参议时自滇南赴西粤》有:“望望苍梧南纪尽,白云先入故人愁”②(明)明吴国伦撰:《甔甀洞稿》卷1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22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780页。,都是以南纪代岭南。又如明周用在潮州韩愈祠云:“风壤留南纪,乡邦仰后生”③(清)汪森编辑,桂苑书林编辑委员会校注:《粤西诗载校注》,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89页。。清沈大成《题韩山书院》亦云:“讲席开南纪,公来倡古文”④(清)沈大成撰:《学福斋集》卷7,《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4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6页。。再如明林大辂在广西横州伏波庙有:“南纪垂铜柱,荒荒海日红”⑤(明)林大辂撰:《愧瘖集》,《续修四库全书》影印本,第133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73页。。明代申时行《送袁邑博之临桂令》有:“铜标极南纪,墨绶向西粤”⑥(明)申时行:《赐闲堂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3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1页。等均称两广为南纪。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除了诗文,此时期的方志也在积极塑造两广地区属于南纪的书面形象。如(嘉靖)《广东通志初稿》云广东在“云汉下流,南纪之曲,东南负海之国也”⑦(明)戴璟主修:(嘉靖)《广东通志初稿》,广州: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誊印,2003年,第19页。,又(万历)《高州府志》云高州“今则南纪,半附于扬。”⑧(明)曹志遇撰:《高州府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9页。再如(顺治)《潮州府志》谓“潮故南纪也”⑨(清)张世英修,贺宽撰:《潮州府志》,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9年,第38页。。实际上,明清两广地区间或给人“都会罗轩裳,民风杂羠羯”⑩(明)申时行:《赐闲堂集》卷2,《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第134册,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第31页。的文化印象,但总体来看,这些地区已鲜有宋元以前瘴疠、蓄蛊、卑湿、早夭等刻板的地理标签。取而代之的是“霜清八桂瘴,岚结九嶷烟。”[11](明)王慎中著,林虹点校:《遵岩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84页。“被皇风于上世,矜奇迹于南纪”[12](清)陈恭尹著,郭壤忠校:《独漉堂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667页。的“皇风”已逐渐驱散了“蛮夷之风”。
(三)南纪边界在台湾地区的推移
虽然中央政府对台湾地区的实际领辖自古有之,但在清初的分野系统中,由于郑氏集团的割据,台湾地区迟迟未入中央管辖。(康熙)《台湾府志》在论及台湾的分野状况时即云:“岛不入职方,分野之辨未有定指”[13](清)蒋毓英撰,陈碧笙校注:(康熙)《台湾府志校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页。。然而,随着中央政府不断加强对台湾地区的控制,特别是清廷克服郑氏以后,为“以彰一统之盛”[14](清)蒋毓英撰,陈碧笙校注:(康熙)《台湾府志校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4页。,就迫切地需要对台湾分野进行重新整合。一行对分野系统的划分给时人提供了一条有效路径:“唐僧一行有云:星纪当云汉下流,百川归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穷南纪之曲,东南负海为星纪,则台郡宅东南,分野仍属牛女,又与一行之说相符”[15](清)蒋毓英撰,陈碧笙校注:(康熙)《台湾府志校注》,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3页。。实际上,南纪至“闽中”即止,所谓“东南负海”实属清人有意曲解。但不管阐释过程如何,此后,台湾地区已然在分野系统的学理上成为王朝版图的一部分。同时期的《台海使槎录》形胜下亦云:“台湾为土番部族,在南纪之曲,当云汉下流”[16](清)黄叔璥撰:《台海使槎录》,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第2页。,与康熙《台湾府志》之说如出一辙。康熙以后,台湾地区方志的编撰者无不认为台湾就属于南纪,如咸丰《续修台湾府噶玛兰厅志》亦云:“唐僧一行谓:‘星纪当云汉下流,百川归焉’。故其分野自河南,下穷南纪之曲,东南负海为星纪,今台郡宅东南兰处台山之后,对渡五虎,径达泉南,其分野皆属牛女,又与一行之说正相符”①(清)陈淑均撰:《续修台湾府噶玛兰厅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20页。。再如(光绪)《台湾通志》:“唐一行有云:‘星纪当云汉下流,百川归焉’。故其分野自南河,下穷南纪之曲,东南负海为星纪,则台郡宅东南分野,仍属牛女,与一行之说相符”②(清)薛绍元修:(光绪)《台湾通志》,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第3页。,都是通过对南纪边界的新认识来论证台湾地区分野上属于中央王朝的合法性。
方志以外,清人金武祥在《御赐靖海将军侯施琅》一诗中也用“伏波名共美,南纪尽安流”③(清)金武祥撰,谢永芳校点:《粟香随笔》,南京:凤凰出版社,2017年,第986页。来赞扬施琅的安边之功。陈昂的《咏伪郑遗事》亦有“彼苍藉手平南纪,旷古新增一统图”④(清)郑方昆编辑,陈杰、刘大志点校:《全闽诗话》,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489页。句来说明台湾地区的“南纪化”进程。
实际上,“南纪”“北纪”都是人为建构起来的虚拟界限,明清以降,历代统治者大都着意于对边疆地区的经略,这就使得边疆与中原地区的联系日益紧密、差距逐渐缩小,作为划分异质区域的南纪界限自然也就随之失去意义。与之相关,帝国疆域扩大以后,必然需要新的经界来区别内外,“南纪”的扩张自然也是情理之中了。
结 语
通过以上考述可以看到,古人对“南纪”地理观念的认识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变化。宋元以前,时人心目中的南纪范围大致不出《新唐书》中的文本轨范,而明清以降,南纪边界则朝着云贵、两广和台湾地区不断南移。南纪边界的变动趋势正与历史时期中央对边疆地区经略的进程与时效相吻合,所谓“西天日月消兵气,南纪山川渐帝风”⑤语出明人张文耀《游宝峰寺》一诗,(乾隆)《滕越州志》录。,这正反映出“南纪”背后所蕴含的文化意味和象征意义。
近年来,学界在民族(族群)交融、央地关系以及文明互鉴等领域的研究,除了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宏大主题出发外,也越来越注意到从诸如疾病、早夭、卑湿、瘴疠、蛊毒、风俗等微观视角切入的重要性⑥相关研究的代表性成果如,梅莉,晏昌贵,龚胜生:《明清时期中国瘴病分布与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期。左鹏:《“瘴气”之名与实商榷》,《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于赓哲:《蓄蛊之地:一项文化歧视符号的迁移流转》,《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张伟然,夏军:《东晋南朝时人对南方山林的认知》,《云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等等。,这实际已经深入到了地理与人文两方面的研究。但不得不承认,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对中国古代传统地理观念的考察,特别是相关的实证性研究,还稍显不足。实际上,地理观念、地理知识和地理意象,是体现民族(族群)交融与南北碰撞的重要指标,其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黏合和文明互鉴的现实基础,对此我们应当给予充分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