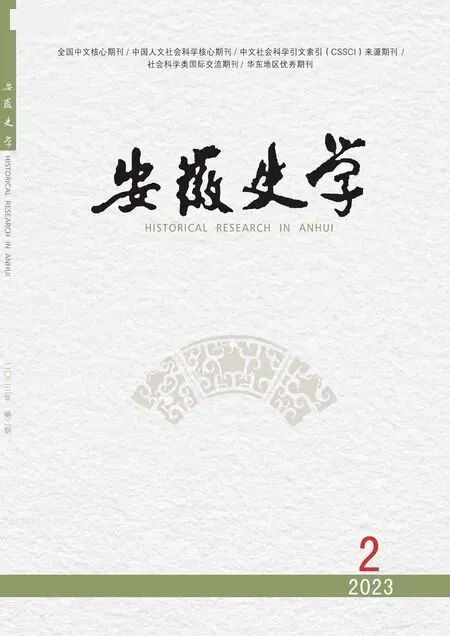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
莫 磊
(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4)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是英国深陷复杂的政治经济形势的历史时期,英国民众在这20多年中经历了战争、经济萧条、社会冲突加剧和法西斯威胁等危机。其间,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将这些危机与资本主义批判相关联,主张在“人民”的主导下推动社会变革,以应对文明危机。在此过程中,左翼知识分子接纳并发展了有着丰富历史意涵的“人民”这一集体概念,并将之纳入对社会历史的认知和解释,继而形成了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历史观。人民史观是英国史学研究社会史转向的重要代表,超越了英国历史研究的精英主义传统和同一时期兴起的诸多社会史流派。考察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对于我们理解两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社会转型与史学研究的转向具有重要价值。
从学术史视角来看,国外学界对英国左翼人民史观的研究侧重于代表性史家的介绍(1)James Klugmann,“The Crisis of the Thirties:A Review from the Left”,in Jon Clark,ed.,Culture and Crisis in Britain in the Thirties,London:Lawrence and Wishart,1979,pp.13-36;James Jupp,The Radical Left in Britain 1931-1941,London:Frank Cass,1982;Stephen Spender,The Thirties and After:Poetry,Politics,People (1933-75),London:Palgrave Macmillan,1978.,而较少着眼于人民史观得以生成的现实维度及其“人民”意涵,对这一史观的理论逻辑和价值向度的总体性考察也相对较少。国内学界倾向于将人民史观置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框架下讨论。梁民愫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产生依赖于两个方面的社会心理与思潮基础:其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传统的保守主义史学已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要。其二,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人民的社会心理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领域里令人震撼的观念冲击。(2)梁民愫:《社会变革与学术流派: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渊源综论》,《史学月刊》2003年第12期。初庆东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渊源入手,分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历史书写以及“人民史学”的形成。(3)初庆东:《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这些关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研究均涉及对人民史观的讨论,丰富了我们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认知。
应该看到,史学研究范式或史观的形成离不开史家对既有理论和学术传统的吸收,但也与历史认识主体的生活实践及其对社会现实的体察密不可分,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中要关注认识主体的研究动机及其时代语境。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人民史观的形成即受到西方文明危机这一社会现实的形塑。作为一种看待社会历史的价值观念和解释模式,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不是“人民”与“历史”的简单叠加,它有着以人民为主体的理论形态和价值向度。本文试图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左翼知识分子人民史观的形成推前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历史时期,梳理这一时期英国的社会危机与左翼知识分子人民史观的形成之间的关联,分析人民史观的逻辑形态和价值取向,进而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总结人民史观的意义。
一、文明危机叙事中的人民史观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面临严峻的经济社会危机。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将现实社会问题与西方文明关联起来,强调通过社会变革以应对文明危机。在探索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过程中,左翼知识分子强调“人民”的价值并对其进行历史地论证,人民史观即产生于左翼知识分子寻找变革力量以应对文明危机的历史语境。
大体来说,一战后的20年是英国刚走出战争却又很快陷入社会失序、大萧条和战争危机逼近的年代。英国在一战中牺牲了近90万人,其中大多是工人阶级。英国的煤炭、纺织和重型工程制造等基础产业遭受重创,主要工业中心格拉斯哥、南威尔士、兰开郡和东北海岸都因战争而陷入长期衰退。(4)James Jupp,The Radical Left in Britain 1931-1941,p.1;p.5.到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的蔓延使英国面临严峻的失业、贫困和社会冲突问题。这一时期,英国失业人数长期维持在百万以上。(5)David Butler and Anne Sloman,British Political Facts,1900-1979,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80,p.343.英国政治家哈里·波利特(Harry Pollitt)在1933年指出:“当前,英国正面临残酷的现实,在饥饿的英国,大多数人缺衣少食、住房简陋。”(6)Allen Hutt,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Britain,London:Martin Lawrence,1933,p.xii.在危机情境下成长起来的左翼知识分子有着新的身份特质和价值观念。20世纪前期,英国传统上以公立学校和大学为中心、以亲属关系为主要联结纽带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上的垄断地位被打破。在不断扩大的教育体系中,中下阶层的教育前景得到改善,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增多,文化生产部门的扩张和新文化部门的出现,共同催生了一个新的、人数众多的知识阶层,他们在出身和职业结构上的差异越来越大,在文化上的同质化程度也低于任何历史时期。(7)Francis Mulhern,The Moment of “Scrutiny”,London:New Left Books,1979,p.9.这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都有着左翼的思想底色。英国“左派主义”(Leftism)是指反对现有政策或制度,在劳工运动内部,它意味着通过改革或革命,实现经济社会主义化的思想主张。(8)James Jupp,The Radical Left in Britain 1931-1941,p.1;p.5.在危机的时局下,左翼的思想和观念也濡染了大多数知识分子。他们“越来越走近工人阶级……马克思主义作为改良主义的替代品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对每一个知识领域都产生了影响。”(9)James Klugmann,“The Crisis of the Thirties:A Review from the Left”,p.35.左翼作家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坦言:“这一代的青年作家群体在政治上几乎都是左翼的。”(10)Stephen Spender,The Thirties and After:Poetry,Politics,People (1933-75),p.13.社会危机的蔓延与左翼思想的濡染,深刻影响了知识分子对西方文明的认知。
作为对文明危机的因应,左翼知识分子认识到变革的必要性。在一战后期,英国思想界就萌生出变革的想法,人们希望英国能够出现新的、取代自由主义的哲学,建立与旧世界不同的全新世界。(11)Janet Roebuck,The Making of Modern English Society from 1850,London:Routledge &Kegan Paul,2005,p.85.在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中,一些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也对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怀疑。后来成为英国首相的保守党议员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在回忆中坦言:“1931年之后,我们很多人都觉得资本主义的痼疾更加根深蒂固了……旧形式的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已经崩溃了,我们必须重估整个体系,也许它根本无法生存。”(12)Harold Macmillan,Winds of Change,1914-39,London:Pan Macmillan,1966,p.285.在人心思变的社会思潮中,左翼知识分子也有着强烈的社会变革意愿。英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汉宁顿(Wal Hannington)感慨:“英国政府机器为了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而运转,却给民众造成无限痛苦,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给人民带来幸福、安全与和平。”(13)W.Hannington,The Problem of the Distressed Areas,London:Victor Gollancz Ltd.,1937,p.282.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40年呼吁:“近年来的历史已经昭示,只有革命才能救英国,这种革命现在已经开始了。”(14)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eds.,The Collected Essays,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An Age Like This,1920-1940,New York:Harcourt,Brace &World,1968,p.539.在对变革的领导力量的分析上,左翼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了作为人民表象的、人数众多的工人阶级,认为工人阶级的使命是用社会主义的英国取代资本主义的英国。(15)James Klugmann,“The Crisis of the Thirties:A Review from the Left”,pp.27-28.这一时期,“人民”在英国政治话语中可以指大众(populace)、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es)、无产阶级(proletariat)、国民(nation)或民族(volk)。(16)Pierre Bourdieu,“The Uses of the ‘People’”,in Pierre Bourdieu,ed., In Other Words:Essays towards a Reflexive Sociology, trans.Matthew Adamson,Californi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p.150.以普利斯特列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认为,“人民”不属于任何根据职业或财富来确定的“阶级”或群体,它由这些阶级或群体之间的所有个体组成的超民族、超阶级的集合。(17)J.B.Priestley,Out of the People,London:Harper &Brothers,1941,p.110.基于对“人民”意涵的共识,左翼知识分子主张用民主而自由的“人民”来构筑新的社会基础。这就赋予“人民”社会变革的主体性,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在探索文明出路的过程中对“人民”价值的肯定。
在对英国文明危机的思考和阐释中,“人民”左右了左翼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的分析和判断,“人民”涵括的社会群体被纳入左翼知识分子对社会历史的解释框架,人民史观就呈现于左翼知识分子的这些历史叙事。这方面的代表如艾伦·赫特(Allen Hutt)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933)、莫尔顿(A.L.Morton)的《人民的英国史》(1938)、R.H.托尼(R.H.Tawney)的《英国劳工运动》(1925)等,都在人民史观的观照下,将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作为叙事主题,动态呈现人民的社会历史地位。(18)Allen Hutt,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Britain;A.L.Morton,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London:Victor Gollancz Ltd.,1938;R.H.Tawney,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25.另一方面,在阐释那些左右英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时,左翼知识分子将人民嵌入社会历史的理论分析框架,强调历时地看待人民的地位及其与社会变革的关系。左翼史家哈米·费根(Hymie Fagan)在《震撼英国的九天》中坦言:“我写这本书时并不是作为一个客观的历史学家,而是作为一个党派成员,一个起义的支持者,就像马克思写《巴黎公社》时那样。”(19)Hymie Fagan,Nine Days that Shook England,London:Victor Gollanz ,1938,p.108.克里斯托弗·希尔在《1640年英国革命》中指出,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以底层民众为代表的掘地派(Digger)最能代表无产者利益,“这是被剥夺的农村无产阶级试图通过直接行动推进某种形式的农业共产主义,他们宣称庄园主和国王都被打败了,人民的胜利解放了属于人民的英格兰。”(20)Christopher Hill,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An Essay,London:Lawrence &Wishart Ltd.,1940,pp.51-52.这些作品都将人民纳入社会历史分析的中心,人民史观也就从这些叙事文本中浮现出来,构成左翼知识分子解释社会历史的思想框架。
二、“人民史观”的理论意涵与价值向度
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产生于英国社会危机加剧的历史语境,作为一种带有价值取向的史学编纂方式和历史解释框架,人民史观并非“人民”观念与社会历史的简单叠加,它有着自身的理论逻辑、叙事风格和价值立场。
首先,人民史观是一种带有历史本体论指向的思想观念,蕴含着左翼知识分子对客观历史的认识以及对史学研究方法的思考。“史学本体论既是关于社会历史过程本身的性质和特点的认识,因而也最容易感应社会历史进程本身的演变的激荡。”(21)庞卓恒:《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产生于资本主义文明衰落和左翼群体探索文明出路的背景中,资本主义的弊病及其对“人民”的危害构成左翼人民史观的立论基础。在其看来,由于广大“人民”被资产阶级剥夺了对生产工具的所有权,从而产生了贫穷、财富分配不公平和个人自由的不平等,这破坏了国家道德、国际和平以及资本主义文明。(22)Beatrice Webb and Sidney Webb,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sation,London:George Allen &Unwin,1923,p.6;p.1;p.171.文明的危机根源于“人民”的利益被忽视和排斥,基于这一认知,左翼知识分子强调“人民”在社会变革中的主体地位。左翼史家哈米·费根对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的历史细节呈现,就表明以农民为主体的“人民”是打破旧式封建经济、推动社会变革的支撑力量。时人认为,“费根的著作比任何一位试图为人民书写历史的前任史家都更成功。”(23)“Review of Nine Days that Shook England by H.Fagan”,The Labour Monthly,1938(20):768-769.在“人民”与文明的关系上,左翼知识分子认为文明属于“人民”的范畴,“人民”应成为挽救文明危机的主体。R.H.托尼强调:“历史已经表明,没有比人民群众是自己所耕种土地和劳动工具的主人这种社会秩序更好的秩序。”(24)R.H.Tawney,The Acquisitive Society,New York:Harcourt,Brace &Company,1920,p.60.左翼的这些论述从历史本体论的角度指出“人民”是文明历史的本体。在这一判断下,左翼知识分子将“人民”视为社会历史变革和进步的主体力量。奥威尔认为,未来社会主义英国的核心,不再是议会上院的贵族,而只能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正在遭受压迫的“人民”。(25)Sonia Orwell and Ian Angus,eds.,The Collected Essays,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My Country Right or Left,1940-1943,p.133.这亦是从本体论层面将“人民”嵌入历史演进的全过程,构成左翼知识分子人民史观的核心。
在文明的历史即为“人民”的历史这一本体论前提下,左翼知识分子将“人民”纳入历史的动态演进逻辑中,主张从“人民”的角度出发认识历史的演进。在其看来,历史的演进不是循环交替,而是复杂社会结构中的“人民”与其他社会要素相互激荡的演进过程。韦伯夫妇在《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中指出,数千年来的历史表明,社会制度一直在兴衰更替,并被更适应人们需求的制度所取代,即使是拥有最先进文明的国家也遵循这一逻辑。(26)Beatrice Webb and Sidney Webb,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sation,London:George Allen &Unwin,1923,p.6;p.1;p.171.在此,“人民”构成社会历史演进的原动力,“人民”的需求决定了社会制度的形态。克里斯托弗·希尔在《1640年英国革命》中指出:“自光荣革命以后,正统历史学家竭力强调英国历史的连续性,试图将革命带来的断裂性做最小化处理……但如果没有革命,就不可能建立起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结构。”(27)Christopher Hill,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An Essay,p.61;pp.37-46.从“人民”的角度出发,左翼知识分子树立了“人民”是社会变革的基础力量,是历史进步的必要条件等历史认识论。左翼《劳工月刊》在评价费根的著作时指出:“英国伟大的社会历史昭示我们:有组织的革命先锋队始终是人民运动发展的自然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最优秀的领导人对群众有着深厚的信任,这是任何群众运动必须建立的基础。”(28)“Review of Nine Days that Shook England by H.Fagan”,The Labour Monthly,1938(20):768-769.这种对“人民”在历史进程中基础性作用的阐述,揭示了人民史观视域下英国历史演进中“人民”与社会历史变革的因果逻辑。
其次,在史学编纂方面,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也有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历史书写逻辑和叙事风格。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叙事大多是在人民史观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逻辑框架下展开,强调社会变革,肯定“人民”的价值也是人民史观主导下左翼知识分子历史书写的基本逻辑。这些宏大的历史叙事涵盖了资本主义的兴衰、社会革命的意义、“人民”的社会历史地位等论题。如韦伯夫妇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衰落》,细致考察了英国社会不平等问题,总结认为:“资本主义的失败对人类来说是一件好事,其不负责任的权力凌驾于人民生活之上,即使这种权力仅限于经济层面,也将带来道德灾难。”(29)Beatrice Webb and Sidney Webb,The Decay of Capitalist Civilisation,London:George Allen &Unwin,1923,p.6;p.1;p.171.克里斯托弗·希尔在《1640年英国革命》一书中,首先分析了托利史学和辉格史学对英国革命的认知,指出资产阶级在革命中对“人民”既拉拢又怀疑的态度。(30)Christopher Hill,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An Essay,p.61;pp.37-46.希尔关于英国革命的历史叙事表现出人民史观的认知逻辑,将此前学界较少关注的人民拉回到历史的中心,关注“人民”在革命各阶段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莫尔顿的《人民的英国史》梳理了英国两千多年的历史,通过阐释影响英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如封建制的确立、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等,肯定了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的进步意义,强调历史的动态性和变革性以及“人民”在此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并在结尾处呼吁“人民”再次投身改变历史进程的伟大事业。(31)A.L.Morton,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pp.526-527.这些代表性著作围绕英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关键时期和重大事件进行宏大的历史书写,呈现出“人民”的主体性与历史演进之间的关联,在多元的历史主题下彰显人民本位的叙事逻辑。
在突出“人民”及其社会变革意义的基础上,左翼知识分子重点讨论了其目睹的经济危机对“人民”的影响,在文明危机的框架下批判资本主义构成了人民史观最基本的叙事风格。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和艾伦·霍奇(Alan Hodge)的《漫长的周末:1918—1939年英国社会史》,以左翼的思想基调,将资本主义文明尤其是大萧条年代的民众苦难归因于英国政府的无能和资本主义体制。(32)Robert Graves and Alan Hodge, The Long Week-End:A Social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1918-1939,London:Faber and Faber Ltd.,1940,p.248.R.H.托尼在《英国劳工运动》中分阶段介绍了一战前英国工人运动的百年历史,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压迫促使工人以各种形式联合起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33)R.H.Tawney,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pp.13-15;p.41.马尔科姆·蒙格瑞奇在叙述大萧条的历史著作中,否定了英国统治阶层存在的合法性。(34)Malcolm Muggeridge,The Thirties:1930-1940 in Great Britain,London:Hamish Hamilton,1940,p.218.左翼知识分子的这种批判也体现在微观的社会历史书写中,如韦伯夫妇在《1931年纪实》中对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和“人民”的选择与历史走向的阐释,科尔和贝文(Ernest Bevin)在《危机》(1931)中将人民的生活日常嵌入资本主义衰落的叙事框架下进行分析,都暗含着左翼知识分子对人民的利益、观念、行动的关注以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这也是人民史观基本的叙事风格。
最后,人民史观是一种看待社会历史的总体性观念,在现实层面代表了“走进人民”和“从人民出发”的实践态度和价值立场。人民史观产生于英国左翼知识分子大规模地与工人阶级联合的潮流中,蕴含着左翼知识分子在看待社会现实方面对真实性的追求。在一战后的20年间,英国民众经历了从国家衰落到社会冲突加剧与经济危机、大萧条及至二战爆发的历史过程。“强烈的民族焦虑感、大规模失业和战争威胁主宰着英国政治,也困扰着英国的政客们,但他们都未能给出答案。”(35)Ben Pimlott,Labour and the Left in the 1930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1.资本主导下的媒体也竭力粉饰太平,回避和掩饰英国的社会矛盾。(36)Andrew Crisell,An Introductory History of British Broadcasting,New York:Routledge,1997,p.45.左翼知识分子将二三十年代视为“低贱虚伪的年代”“饥饿的年代”。(37)John Baxendale and Chris Pawling,Narrating the Thirties:A Decade in the Making:1930 to the Present,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161;pp.17-18.基于人民史观的历史认知逻辑,左翼知识分子认为历史的真实性隐含在“人民”的现实生活中,并在各自的领域走进“人民”。尤其是那些刚毕业又进入大学工作的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更频繁、更密切地接触工人阶级。(38)R.H.Tawney,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pp.13-15;p.41.左翼史家詹姆斯·克鲁格曼指出:“工人阶级、社会中间阶层和知识分子中有如此多的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以个人和集体的方式将自己的职业、行业、社会活动与集体斗争联系在一起,来自中间阶层的知识分子自视为工人阶级的同行者,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寻找自己的未来。”(39)James Klugmann,“The Crisis of the Thirties:A Review from the Left”,p.35.左翼知识分子“到人民中去的”行动路径表征了人民史观的实践向度,展现出人民史观的现实关怀理念。
人民史观最终落脚于解决现实问题时应采取的立场和路径。在社会失序和政治动荡的时代情境下,英国知识界面临如何回应社会现实的难题。克里斯·保林等人认为,随着大萧条的蔓延、饥饿游行、法西斯主义和战争危险的加剧,“历史的客观环境促使个人有立场地在‘真实的世界’中行动。”(40)John Baxendale and Chris Pawling,Narrating the Thirties:A Decade in the Making:1930 to the Present,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6,p.161;pp.17-18.左翼知识分子对危机真实性的揭露、对人民价值的肯定以及到人民中去的社会行动,代表了以人民为本位的价值立场。克里斯托弗·希尔在《1640年英国革命》的结尾揭示了历史对当下的启示:“只有斗争才能赢得改革,正如只有斗争才能保留先辈为我们赢得的自由。如果人民发现法律制度不符合自由的秩序,那么他可以通过联合行动改变这些制度,这就是十七世纪英国革命的历史给我们当下的教训。”(41)Christopher Hill, The English Revolution 1640:An Essay,p.61.莫尔顿在《人民的英国史》的结语中呼吁:“此书完成于英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刻,此时人民的命运和世界的命运,比任何时期都更取决于人民在正确判断的基础上采取正确行动的能力。”(42)A.L.Morton,A People’s History of England,pp.526-527.二战期间,普利斯特列指出:“英国人民有责任保卫自由的文明……当人民鼓起勇气开始迎接挑战时,未来的历史学家不会在人民的意识、勇气和耐力上发现任何不足。”(43)J.B.Priestley,Postscripts,London:William Heinemann Ltd.,1940,pp.22-23.左翼知识分子的这些论说赋予人民的社会行动以历史正义性,也从总体上反映出人民史观的现实旨归,代表了左翼知识分子在历史书写以及应对文明危机方面的基本立场。
三、史学研究的转向与人民价值的彰显
人民史观的兴起突破了英国传统的精英史观在历史阐释方面的主导地位,表现出与同一时期西方史学中诸多社会史流派不同的研究范式。在人民史观的主导下,左翼知识分子将“人民”纳入历史书写的中心,其从“人民”出发来体察社会现实的实践路径,也进一步彰显了“人民”的价值。
从这一时期英国史学研究的总体情形来看,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表现出与英国传统史学不同的理论形态,为自下而上的史学研究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自19世纪历史学科学化和职业化到20世纪初,辉格史学(Whig history)长期是英国史学研究的主流,它将历史演进的逻辑分为推动历史进步和阻碍历史进步的两股力量。与英国精英阶层主导下“人民”遭到排斥的社会观念相映衬,19世纪英国历史学表现出对精英阶层的推崇。一些代表性史家的作品,如麦考莱的《英国史》等都强调伟大历史人物在推动历史进步中的主导作用,赞扬英国制度的延续性。(44)Herbert Butterfield,The Englishman and His Histor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44,p.5.而在历史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层面,辉格史学秉持进步史观,通过对英国重大历史事件的阐释,认为历史的发展呈现不断进步并最终指向自由的终点。(45)P.B.M.Blaas,Continuity and Anachronism:Parliamentary and Constitutional Development in Whig Historiography and in the Anti-Whig Reaction between 1890 and 1930,Hague:Martinus Nijhoff,1978,p.10.这一带有目的论指向的历史观强调辉格党和伟大历史人物在历史进步方面的主导作用,认为“进步与持续”或“持续地进步”,是英国历史的主旨。(46)Krishan Kumar,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04;pp.206-207.在历史书写向上看的价值取向下,“人民”往往缺席于史家对英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尽管19世纪英国史学界如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格林出版了《英国人民简史》等著作,并声称用社会的历史代替国家或文明的历史,但人民只是被纳入历史研究的边界内,却未被置于历史演进的动态过程中进行分析阐释。(47)Krishan Kumar,The Making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204;pp.206-207.在这一时期英国的史学传统中,人民在历史叙事中处于相对边缘化的地位。
与英国史学传统中自上而下的历史观不同,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强调从“人民”的立场出发,自下而上地看待社会历史。人民史观兴起于一战后辉格史学遭到怀疑的史学环境中,尽管在对历史演进趋势的总体认知上,人民史观与辉格史学的精英史观均秉持进步史观,认为历史是通过多阶段、多层次演进,最终走向某种积极的结果。但在对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的认知上,二者存在差异。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强调“自下而上”的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关注底层的普通民众而非辉格史家笔下的伟大历史人物在历史演进中的作用,认为“人民”根据现实需要自下而上地推动社会历史变革。R.H.托尼在《英国劳工运动》中指出,英国工人群体是根植于英国社会中的民主力量,他们不分职业和社会背景,自发地走到一起,这些无差别的大众,即早期改革者所说的“人民”(the people),构成了社会进步的主体力量,他们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为公共政策,继而推动社会变革。(48)R.H.Tawney,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pp.13-15.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不仅将人民纳入历史研究的主题,而且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角度,赋予其在历史演进中的动力意涵。莫尔顿在《人民的英国史》的序言中强调:“无论这本书有什么价值,一定是在于它的解释,而非它所呈现的事实的新颖性……它的目的是让读者对我们历史运动的主线有一个总体的认知。”(49)Raphael Samuel,“People’ s History”,in Raphael Samuel,ed.,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New York:Routledge,2016,p.xvii.克里斯托弗·希尔等人的相关论著,也将“人民”置于历史演进的动态过程中展开叙事,强调“人民”及其意志在推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都表现出人民史观对英国史学传统的突破。
与同一时期西方史学研究中兴起的诸多社会史流派相比,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有着独特的叙事风格和理论视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西方史学研究呈现出社会史日渐兴起的趋势,英国经济史中衍生出的社会史和尚处萌芽阶段的法国年鉴学派均为重要代表。年鉴学派的早期代表性史家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等人,主张从社会结构和社会的角度认识和解释历史,强调历史中人的重要性。费弗尔认为,只有人才拥有历史,而且人的历史是最广义的历史。在英国史学界内部,一战后的英国历史学仍沿着旧的史学传统行进,而经济史则引发了社会史研究,如艾琳·帕沃尔等人从社会史视角写成《中世纪的人民》(1923),再现普通人的生活史。与之相比,左翼知识分子在人民史观的主导下展开的史学研究和叙事,也是新兴社会史研究的重要代表,且其在历史本体论的意义上超越了同一时期以结构化为导向的社会史研究范式。在编纂风格上,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有别于年鉴学派轻事件与人物、重结构和环境的学术取向。在英国社会史内部,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与那些将史学研究边界与人民生活边界相互扩展的做法不同,而是将人民置于历史演进的总过程,在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意义上考察“人民”的历史地位,并带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理念,这为二战后左翼学者自下而上地书写“人民”的历史奠定了基础。
从实践上来看,人民史观彰显了“人民”的社会历史价值,其固有的现实关怀理念和价值立场深刻影响了各阶层的“人民”观念,为处于阶级结构和社会价值变化中的英国社会引入了新力量。在人民史观的主导下,左翼知识分子的历史叙事及其在实践层面与“人民”的结合,凸显出以工人阶层和普通民众为主体的“人民”的价值,这在历史和现实的维度进一步将“人民”带回到社会历史的中心。尤其在20世纪30年代,“知识分子对同盟者、工人阶级及其与同盟者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群体在思想上的合作,都有了丰富经验……学会了用一种易于理解的方式与工人阶级交流,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他们特有的、更专业的、概念化的说话方式。”(50)James Klugmann,“The Crisis of the Thirties:A Review from the Left”,p.35.这在拉近左翼知识分子与“人民”距离的同时,也从思想和观念层面彰显了人民的价值。左翼作家普利斯特列强调“人民”在社会变革中的价值时,就用“人民”代替英国统治阶级主导的民族国家,指在相互支持、合作、共享的群体中组织起来的所有人。(51)Chris Waters,“J.B.Priestley (1894-1984):English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Nostalgia”,in Susan Pedersen and Peter Mandler,eds.,After the Victorians:Private Conscience and Public Duty in Modern Britain,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219.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赋予“人民”以积极、进步和正义的意涵,使“人民”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展,成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公共话语的重要主题,如英国社会将第二次世界大战描述为“人民战争”(the people’s war),从而在情感上贴近民众。(52)Sonya O.Rose,Which People’s War? National Identity and Citizenship in Wartime Britain 1939-1945,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62.在1942年《贝弗里奇报告》发表后,公众舆论将其形容为“人民的贝弗里奇”(the people’s Beveridge)。英国工党在阐释战后改革目标时,将战后英国的社会秩序形容为“人民的和平”(the people’s peace)。(53)F.W.S.Craig,ed.,British General Election Manifestos 1900-1974,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5,pp.123-125.“人民”更加频繁地出现在那些关乎英国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的叙事中。
余 论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面向,它代表了左翼知识分子对待历史的基本价值立场和解释模式。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产生后的较长历史时期内,英国社会环境发生了较大变化,社会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一直存在。但从总体上看,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处于上升期,这使得人们在实践层面很难历史地理解资本主义的弊病,知识界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传播也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而较少将之发展为历史书写范式。学界在介绍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过程中,强调的诸多促成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的历史时期内也一直存在,但要回答在此前相同历史条件下英国没有形成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问题,则需要我们回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之初甚至之前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时代语境下,探究作为知识生产主体的知识分子或史家在知识生产活动中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及其历史阐释。尽管左翼知识分子在范畴上来源广泛,但他们的人民史观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具体体现,通过对这一马克思主义史学面向的截取有利于我们从中窥见这一时期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的基本形态。
“社会历史进程本身的演变越剧烈,史学本体论领域的演变也会相应地剧烈。”(54)庞卓恒:《历史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第一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历史进程,战争带来的创伤也促使人们反思西方文明的诸多核心要素。旧有的社会价值体系和制度规范遭到怀疑,英国文明危机论甚嚣尘上,大萧条的蔓延也在实践层面让更多的人体认到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即产生于文明危机环境下英国人心思变的社会情境中,它的兴起反映了左翼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现实与思想价值面临困境的情形下,对历史主体的探寻,旨在探索出能够真正推动社会历史发展和进步的动力。正是在这一社会情境下,左翼知识分子在思想和实践上接纳了“人民”这一有着深厚历史变革底蕴的集体主义概念,并将之运用于对社会历史的分析,继而形成了以人民为本位的历史认识和解释模式。
“人民”一词在英国的历史语境中有着变革和合法性来源的政治意涵,也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本体论和方法论中的重要主体。左翼知识分子的人民史观不是“人民”与历史观念的简单叠加,亦非在形式上将“人民”纳入史学研究边界内,而是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本体论和认识论中的人民,纳入对社会历史的分析、阐释以及对社会历史演进的动态考察。在人民史观的观照下,无论是左翼知识分子的阶级史叙事或是对“人民”生活的历史呈现,都蕴含了以“人民”为本位的价值立场和解释模式。人民不仅是历史的本体,也是社会历史演进的主体和主导力量。因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人民史观的生成,体现了左翼知识分子在历史书写与叙事方面走进人民的价值取向以及以人民为本位看待社会问题的基本立场,暗含着左翼群体在社会历史变革方面的意识形态要求,呈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在历史解释中的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