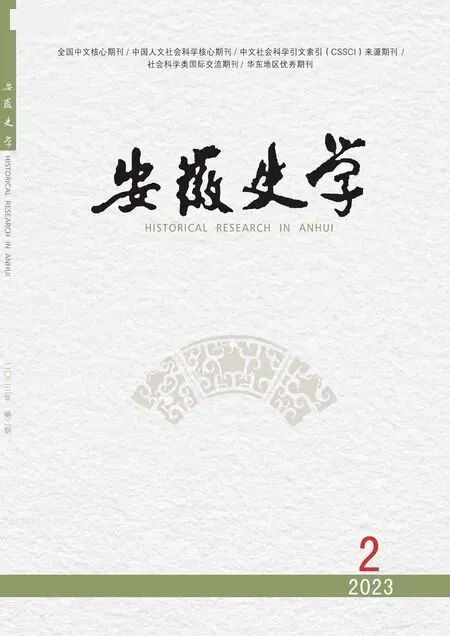“由道变俗”与“道通为一”
——严复的“天演”译述及其世界观转型
段 炼
(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6)
19世纪中叶以来,面对西力东渐,清王朝所遭遇的接连溃败,让这一时期的士人面临普遍的思想危机。对于严复而言,他在19世纪末期的思考,聚焦于因“世变之亟”而让他反复致意的一个主题:“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1)“世变之亟”一语,出自1895年2月4—5日严复发表于天津《直报》的《论世变之亟》一文,王栻主编:《严复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页。“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一语,在严复的论述及信札之中多次出现,已经成为他多年来深思熟虑之后的一种惯常表述。为回应迫切的时代挑战,严复最为卓越的思想贡献,是通过翻译这一“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将西方近代的知识谱系引入晚清思想界,进而为近代中国的制度变革、文化转型与国民形塑,提供了一个建立在进化论和现代科学方法之上的新世界观。
学界关于严复其人及其思想(尤其以译著《天演论》为中心)的研究成果蔚为大观。(2)如李泽厚:《论严复》,《中国近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Benjamin I.Schwartz,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3;汪晖:《严复的三个世界》,《学人》1997年第12辑;吴展良:《严复〈天演论〉作意与内涵新诠》,《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4期;吴展良:《中西最高学理的绾合与冲突:严复“道通为一”说论析》,《台大文史哲学报》2001年第54期;王汎森:《近代中国的线性历史观——以社会进化论为中心的讨论》,《新史学》2008年第19卷第2期;许纪霖:《现代性的歧路:清末民初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史学月刊》2010年第2期;黄克武:《何谓天演?严复“天演之学”的内涵与意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14年第85期,2014年9月,等。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之上,尝试从晚清时期严复所面对的“今之道,无变今之俗”的思想危机出发,描述并分析其如何通过西学阅读、翻译以及古籍批注等跨越中西文明的知识生产方式,反省并探索近代中国世界观的重构,即如何因应近代中国“道”的转化。
一、求道:“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
严复对于世界观转型议题的反省与探索,与其早年的学思历程密切相连。14岁时,严复进入马江学堂学习海军——“所习者为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积微、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3)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严复集》,第1546页。1871年7月,当严复与同学们从马江学堂毕业时,他们在写给英文教习嘉乐尔的信中谈及两点:一是“西方国家教育原理,源自希腊,希腊人的这些原理是从中国输入的”;二是“古时中国对于礼、智的原则会适中运用,但几不注意西方国家所高度推崇的实用原则”。(4)中国史学会编:《洋务运动》(八),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388页。
无论前者对于“西学中源”的表述是否确切,也无论后者对于西学“实用原则”的揄扬是否允当,至少可以断定,时年不到20岁的严复,已经开始密切关注中西文明之中的一系列本源性议题。这使得他较之同时期的诸多读书人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更早也更为系统地了解近代西方的知识谱系与世界观。此后,在长达近30年的军旅生涯——包括国内海军生活(1871—1875)、英国海军大学留学岁月(1876—1879)以及归国后任教北洋水师学堂(1880—1900)之中,严复得以通过一个“内在参与者”的身份,探索泰西诸国实现富强的秘密,体悟全球殖民竞争态势之下清政府屡遭挫败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时期,严复的学术志趣超越了军事战术、炮台建筑、国际法律等海军学堂的实务研究,转而关切人文学者才深感兴趣的政治、道德、人性等形而上的思想议题。通过广泛思索“中西学术政制之异同”,严复业已洞悉“格物致知之学,寻常日用皆寓至理。深求其故,而知其用之无穷,其微妙处不可端倪,而其理实共喻也”。(5)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55页。从此,严复展开对于西方科学公理、公例不懈追求以及对于中国之“道”的执着反省,并由此探寻激烈冲突之下中西文明的辩证关系。
光绪五年(1879),严复归国并就任福州马江船政学堂,翌年调往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教务长)。然而,就在严复“自叹身游宦海,不能与人竞进热场”之时(6)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537页。,初读英国哲学家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即1873年出版的TheStudyofSociology),却让他体会到此中真意。1903年,他以《群学肄言》为题翻译出版此书时写道:“其书实兼《大学》《中庸》精义,而出之以翔实,以格致诚正为治平根本矣。”(7)严复:《〈群学肄言〉译余赘语》,《严复集》,第126页。儒家经典(尤其是重视知识传统的程朱理学)话语与斯宾塞“群学”论述之间的契合与关联,让严复得以反省自身“独往偏至”而不能会通中西的思想局限,从而激发“企图融通中西与一切宇宙人生之理的努力,表现了一种典型的求道性格”。(8)吴展良:《严复早期的求道之旅——兼论传统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的继承与转化》,《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
面对中国在甲午海战之中的溃败,严复对于传统世界观的批判认知与深沉忧虑大大加深。1894年10月,他在给儿子严璩的书信中写道:“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他强调学问之“真”与心术之“正”,才是“治国明民之道”的根基。这一论述贯彻的仍是士大夫通过格物致知与诚意正心,进而实现“治平之道”的儒学主张。另一方面,“今之道,无变今之俗”的判断,表明严复已经意识到,儒家世界观与知识体系不足以应付严峻的局势——即便管仲、诸葛亮这样深合儒家“圣王之道”的经世之才,面对今时今世亦无力回天。在这封信中,他有如下“夫子自道”:“我近来因不与外事,得有时日多看西书,觉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必通之而后有以知天地之所以位、万物之所以化育,而治国明民之道,皆舍之莫由。”(9)严复:《与长子严璩书》,《严复集》,第780页。
至此,严复在中西文明冲突之中竭力“以通求道”的态度已经相当清晰。他认为东西文明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其实彼此相通,可惜中国学术末流“徇高论而远事情,尚气矜而忘实祸”。(10)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3页。与此相反,西学的特征恰恰在于“驯实”且自成周密系统,“及其既通,则八面受敌,无施不可”。这又恰恰暗合传统儒家通过“格物致知”达到“修齐治平”、通过“治学”达到“治政”这一“圣王之道”的路径认知。因此,在严复的思想世界之中,西学已经超越传统知识谱系与价值系统,成为形塑新世界观过程中值得追求的一份“真实事业”。
二、问道:“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
1895年2月至5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相继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原强续篇》《救亡决论》等多篇文章。在这一系列重要论述之中,对于“传统之道”的忧虑以及对于“因应之道”的追问,共同构成了他思考近代中国“由道变俗”的问题以及重构世界观的起点。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此前一年(1894年),赫胥黎所著EvolutionandEthics(《进化与伦理》)刚刚在英国出版。从1896年开始,严复即着手翻译此书,并于1898年推出风行全国的中译本《天演论》。天津《直报》系列论文的运思与几乎同时进行的《天演论》翻译,共同形塑了严复独具个性的思维特质、学理形态与表述方式。
严复注意到,从历史发展的长时段来看,历代中原王朝与周边异族的抗衡,无论前者的“有法”(文教秩序)还是后者的“无法”(游牧骑射),最终均归结为儒家政教秩序的一统天下。然而,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所面对的泰西诸国,却与往日之周边异族不可同日而语——“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11)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1页。
“无法与法皆有以胜我”,意味着中国的对手方不但主宰了这一“世变”,而且通过中西之间的全面对抗,足以确证西洋诸国在国民素质与政治制度方面远超中国。因此,严复指出:“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12)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2页。严复这一系列判断与描述,瓦解了儒家先贤的神圣形象与儒家经典应对“世变”的有效性。同时,这些文字也反向呈现出超越中国人想象之外的西方文明新形象,带给中国朝野各界巨大震撼。
面对中西双方在对照中呈现的巨大落差,严复认为,西方富强的“命脉”,不在于当日中国醉心洋务之人士所声称的“善会计”或是“擅机巧”,也不完全等同于“汽机兵械”与“天算格致”,而在于“业无论兵、农、工、商,治无论家、国、天下,蔑一事焉不资于学。锡彭塞(斯宾塞)《劝学篇》尝言之矣。继今以往,将皆视物理之明昧,为人事之废兴”。(13)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8、53、52页。与此相反,中国“四千年文物,九万里中原,所以至于斯极者,其教化学术非也”。(14)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8、53、52页。在严复看来,西方列强船坚炮利与殖民扩张的背后,贯穿的是精深务实的学术体系与严谨系统的科学公理。因此,学术教化而非技术至上的新世界观,才是西方富强的根基。由此出发,西方列强走向富强之“道”乃是“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15)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2页。
这一理解,直接构成严复对于19世纪60年代以来洋务运动的批判与省思。他不惜笔墨,进一步阐述何谓西人之“学”:
夫西学亦人事耳,非鬼神之事也。既为人事,则无论智愚之民,其日用常行,皆有以暗合道妙;其仰观俯察,亦皆宜略见端倪。第不知即物穷理,则由之而不知其道;不求至乎其极,则知矣而不得其通。语焉不详,择焉不精,散见错出,皆非成体之学而已矣。今夫学之为言,探赜索隐,合异离同,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者,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层累枝叶,确乎可证,涣然大同,无一语游移,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因应厘然,夫而后得谓之为“学”。(16)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8、53、52页。
其中,“第不知即物穷理,则由之而不知其道;不求至乎其极,则知矣而不得其通”一语,最能看出严复对于西方文明的深刻理解。他在另一处的表述则更明确:“一理之明,一法之立,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故悠久;其究极也,必道通为一,左右逢原(源),故高明”。(17)④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5、51页。显然,在严复心目中,西方“理法”的正当性,不再源自超越价值与圣人垂训,而是源自通过归纳与演绎的分析方法,最终形成的可供证伪的科学体系。换言之,通过“即物穷理”(学术行为),才能明白何为西方之“道”。另一方面,将“即物穷理”推向极致,西方“日用常行”的人事(政治)也可以如中国儒家传统一样,实现“暗合道妙”的“极高明”(《中庸》)的境界——此即严复津津乐道的“道通为一,左右逢源”。
三、证道:“天行人治,同归天演”的世界观
随着严复所译赫胥黎的《天演论》在1898年出版并风行全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的中国,逐渐进入由“天演论”所主导的“物竞天择至剧至烈之时”。(18)黄遵宪:《驳革命书》,张枏、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时论选集》第1卷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334页。以“自强保种”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和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观念,开始成为影响近代中国人的核心理念。严复明确指出,当前全球范围的数千年未有之巨变,是包括中国圣人在内也“无所为力”且无法自外的“运会”(19)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页。,故中国只能在“运会”中适应求存而无从逃避。从此,对于“道”的“变”与“不变”的重新理解,开始形塑严复对于“天演”世界观的阐释:
然则,天变地变,所不变者,独道而已。虽然,道固有其不变者,又非俗儒之所谓道也。请言不变之道:有实而无夫处者宇,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三角所区,必齐两矩;五点布位,定一割锥,此自无始来不变者也。两间内质,无有成亏;六合中力,不经增减,此自造物来不变者也。能自存者资长养于外物,能遗种者必爱护其所生。必为我自由,而后有以厚生进化;必兼爱克己,而后有所和群利安,此自有生物生人来不变者也。此所以为不变之道也。若夫君臣之相治,刑礼之为防,政俗之所成,文字之所教,吾儒所号为治道人道,尊天柱而立地维者,皆譬诸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第变者甚渐极微,固习拘虚,末由得觉,遂忘其变,信为恒然;更不能与时推移,进而弥上;甚且生今反古,则古昔而称先王,有若古之治断非后世之治所可及者,而不知其非事实也。④
可见,严复强调的“道”的“不变”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基于“实事实理”之上的自然科学常识与公理,二是基于对诸如“自由”“兼爱”等尊重、解放人性的人之常识。而“可变”的内容,则反而是中国自古以来“信为恒然”,但实际上无法“与时推移”的政治秩序。所以,他在《天演论》的自序中特别指出:“近二百年,欧洲学术之盛,远迈古初。其所得以为名理公例者,在在见极,不可复摇。……夫西学之最为切实而执其例可以御蕃变者,名、数、质、力四者之学是已。”严复以此类比儒家经典《易经》与《春秋》:“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内籀云者,察其曲而知其全者也,执其微以会其通者也。外籀云者,据公理以断众事者也,设定数以逆未然者也。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
严复认为,《春秋》和《易经》固有的重要性,在于司马迁所谓:“《易》本隐而之显。《春秋》推见至隐。”他指出,“始吾以谓本隐之显者,观《象》《系辞》以定吉凶而已;推见至隐者,诛意褒贬而已”。(20)严复:《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1320页。然而,随着严复对于“道”的重新阐发,使得其心目中的“道”,已经逐渐超越传统儒家之道的范畴,承接的是18世纪以来西方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学理之“道”——前者肯定人是最高智慧或终极智慧的概念,后者强调物质世界是基本的实在或者唯一的实在。
这一转变构成了严复眼中关于“执其例可以御蕃变”新的理解。在《天演论》当中,赫胥黎如是说:“小之极于跂行倒生,大之放乎日星天地;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言其要道,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此其说滥觞隆古,而大畅于近五十年。盖格致学精,时时可加实测故也。”(21)严复:《天演论·导言二广义》,《严复集》,第1326页。从此,在严复笔下,《易经》“定吉凶”和《春秋》“意褒贬”的道德评价所蕴含的神圣性、超越性与内在价值的相关性已经瓦解。不仅如此,司马迁对于《易经》与《春秋》的赞颂,反而蜕变为“天演”世界观之下科学话语和知识谱系的注脚:“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其言若诏之矣。二者即物穷理之最要涂术也。”(22)严复:《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1320页。
1898年8月,严复在北京通艺学堂作《西学门径功用》的演讲之时,再度详论作为“格物穷理之涂术”的“内导”(归纳)和“外导”(演绎)的方法,认为“此二者不是学人所独用,乃人人自有生之初所同用者,用之,而后智识日辟者也”。(23)严复:《西学门径功用》,《严复集》,第94页。就在同一年出版的《天演论》按语中,他也谈到:“古者以人类为首出庶物,肖天而生,与万物绝异。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而教宗抟土之说,必不可信。”(24)严复:《天演论·导言一察变》,《严复集》,第1325页。这些表述以更为明确的方式,共同呈现出严复思想当中两个重要议题:第一,“智识日辟”是人类运用天赋理性,改造世界与自身的必然结果。因此,世界观的重构必须建立在以归纳、演绎为方法论和认识论的科学公理的基础之上。因此,必须以超越传统世界观的思路,重建现代政治与道德价值的合法性依据。第二,接受“且演且进”的历史观,从而将未来而非过去视为“理想之世”的目标。在新的历史意识的支配之下,这一思考与严复对于充分发挥人的自由与理性的呼吁相互配合。从此,时间上的差别转变为价值判断的不同和理性选择的不同,19世纪中叶以来愈演愈烈的“中西之争”,由此演化为“新旧之争”与“古今之争”。(25)杨国强:《近代中国的两个观念及其通贯百年的历史因果》,《学术月刊》2012年第9期。
四、载道:“顺乎天演,郅治终成”的道德与政治
19世纪90年代,随着中西之间商战与学战的扩张,在晚清朝野的认知当中,“争的观念因西潮而显,亦由西潮为之正名”(26)罗志田:《西潮与近代中国思想演变再思》,《变动时代的文化履迹》,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更为以竞争成败确认文明优劣的思潮提供了社会语境。正如西方科学史家所言,“物竞天择”之说从达尔文的自然史观肇端,“承认自然的不间断的、不可预言的变化、竞争和进化”。(27)[美]理查德·塔纳斯著,吴象婴等译:《西方思想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页。随后,进化理论即被斯宾塞“宗其理而大阐人伦之理,帜其学曰‘群学’”。(28)严复:《原强》,《严复集》,第6页。柯林武德曾把19世纪的这一思想趋势,评价为“得自进化论的自然主义并被时代倾向强加给历史学”的产物。(29)[英]R.G.柯林武德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的观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64页。因此,作为自然主义“进化史观”反对者的赫胥黎一再强调,“社会的伦理进展并不依靠模仿宇宙过程,更不在于逃避它,而是在于同它作斗争”。(30)[英]赫胥黎著,《进化论与伦理学》翻译组译:《进化论与伦理学》,科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58页。
不过,在19世纪世界历史的图景之中,斯宾塞和赫胥黎关注的是西方社会内部的生存斗争和伦理,而严复面对的则是中国如何在殖民主义的世界氛围当中确定生存权利的方式。(31)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845页。19世纪90年代,当严复在翻译赫胥黎所著《天演论》之时,已经清晰地洞察到赫胥黎与斯宾塞之间的矛盾:“斯宾塞、赫胥黎二家言治之殊,可以见矣。斯宾塞氏之言治也,大旨存于任天,而人事为之辅,犹黄老之明白然,而不忘在宥是已。赫胥黎氏他所著录,亦什九主任天之说者,独于此书,非之加此。盖为持前说而过者设也。”(32)严复:《天演论·导言五互争》,《严复集》,第1334页。
对此,同时代的孙宝瑄在阅读《天演论》之后,同样心有戚戚焉:“《天演论》宗旨,要在以人胜天。世儒多以欲属人,而理属天,彼独以欲属天,以理属人。以为治化日进,格致日明,于是人力可以阻天行之虐,而群学乃益昌大矣。否则,任天而动,不加人力,则世界终。古争强弱,不争是非,为野蛮之天下。”(33)孙宝瑄:《忘山庐日记》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面对“任天而动”的汹汹之势,孙宝瑄的立论点在于以“人力阻天行之虐”,展现的是儒家的道德自觉与人文主张。可见,严复译述赫胥黎的《天演论》之意图重在将伦理原则介入宇宙过程之中,实现对“任天为治”之“末流”的矫正与纠偏。从这一点上看,严复对于斯宾塞保持了“选择性的钦佩”,是一名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所蕴含的伦理原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34)James Reeve Pusey, China and Charles Darwin,pp.155-157.
严复对于“天行”与“人治”之间道德冲突的觉察,既显示出他虽然努力实现中西思想之间的“道通为一”,又呈现出两种世界观在其思想中的角力与纠缠。一方面,19世纪以来的西方进化思想不是一个匀质整体,而是因时、因势、因人而不断变幻的变量。另一方面,严复在接纳新知的过程中,其对标虽是外在的西学,参照系却是内在于传统的中学。对他而言,中西思想之间的折冲与调适必为常态。
从此,在严复的笔下,“任天为治”与“以人持天”就不再是一个关于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二元对立的“现代叙事”,而是因统摄于“天演”世界观之下而获得耐人寻味的平衡。从自然层面看,严复的“天演”世界观接受科学公理并将其作为创造理想政治与社会规范“公例通理”,从而形成科学方法与宇宙法则的密切关联;从道德层面看,严复的“天演”世界观依然延续儒家“天理”世界观的伦理内涵与超越面向,同时也通过人文主义的视野理解“质、力、名、数之学”,从而实现“农商工兵、语言文学之间,皆可以天演明其消息”。(35)严复:《天演论·导言二广义》,《严复集》,第1328页。
“天演”世界观作为一个整体性的观念系统,不仅凝聚了严复对于中西文明之间“道通为一”的深湛之思,而且急切因应19世纪末期中国面临的“物竞天择”的世界变局与时代需求。对于近代中国救亡保种的历史变革而言,这一世界观转型既带来伦理价值上的矛盾与张力,也伴随严复心目中国家与国民(“群”)的政治改造与社会重构。
其实,甲午海战中国兵败之后,严复在前述天津《直报》的系列论文当中,已经展开对于中国政治的激烈批判。严复指出,中国政治之所以呈现“一治一乱,一盛一衰”的循环,因“中国名为用儒术者,三千年于兹矣,乃徒成就此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民,一旦外患忽至,则糜烂废瘘不相保持。其究也,且无以自存,无以遗种,则其道奚贵焉?”(36)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4、11页。
其中,“争自存”与“遗其种”,正是严复再三致意的达尔文《物类宗衍》(今译《物种起源》)的核心内容,也是其心目中检验一国政治社会良窳的新标准(“本”)。既然中国的政道已“不足贵”,那么变法图强之后的良善政治应当呈现何种样貌?严复认为,“道在去其害富害强,而日求其与民共治而已” 。(37)严复:《辟韩》,《严复集》,第35页。显然,严复对于理想政治的期待,不仅有追求富强的国家目标,更有与民共治的民主参与。这是他多年来在中西之道当中“求其会通”的思考结果。严复指出,“从事西学之后,平心察理,然后知中国从来政教之少是而多非。即吾圣人之精意微言,亦必既通西学之后,以归求反观,而后有以窥其精微,而服其为不可易也” 。(38)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第49页。
在严复看来,西方列强之所以能够走出中国式的治乱循环,因其政教秩序“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39)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4、11页。严复认为,“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但是,“恕”与“絜矩之道”专就待人接物的交往尺度而言,而自由的价值却内在于独立的国民个体。所以,“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彼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蚀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而其刑禁章条,要皆为此设耳”。(40)严复:《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2—3页。
因此,当自由与民主分别成为严复心目中理想政治之“体”与“用”,对于传统政治合法性的挑战,势必直接针对戕害自由民主的君权及其衍生的中国政治伦理——君臣之伦。严复在《辟韩》一文中,以唐代韩愈抨击佛道之说、重建儒家道统的《原道》一文作为辩论对象。
在严复看来,韩愈在《原道》之中深情赞颂古往今来的“圣王”,实则“如彼韩子,徒见秦以来之为君。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41)③严复:《辟韩》,《严复集》,第35、34页。究其实际,君主只是万民之一,甚至还可能因人性之恶与制度之恶沦为“窃国大盗”。“是故君也臣也,刑也兵也,皆缘卫民之事而后有也;而民之所以有待于卫者,以其有强梗欺夺患害也。有其强梗欺夺患害也者,化未进而民未尽善也。是故君也者,与天下之不善而同存,不与天下之善而对待也”。③因此,严复的立足点从君主转为民主,他眼中的“君臣之伦,盖出于不得已也!唯其不得已,故不足以为道之原”。
同时,他又以追问“道之原”的方式,展开对于未来中国新道统的思考。这是他从现实政治层面确信“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的努力。严复自觉地在一种新颖却又复杂的知识谱系当中,思考“天演”世界观与国家及国民的关系。他说:“第由是而观之,则及今而图自强,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然则三者又以民智为最急也。是故富强者,不外利民之政也,而必自民之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也。”(42)严复:《原强》,《严复集》,第14页。他通过“标/本”这一传统中国的学术表述方式,传递出在“天演公例”之下,国民为现代国家之根基的思想。只有培养出具有德、智、力之能力的国民,他们才能在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实现国家富强。
在“公例”的基础之上,严复相信“天演”世界观是一个包罗万象并且“一以贯之”的新道统。值得注意的是,严复把国家和国民“开化”的文明使命与道德责任,纳入“进种保群”的政治视野之中,以“公理”“公法”“公论”反对殖民主义的弱肉强食:“必其有权而不以侮人,有力而不以夺人。一事之至,准乎人情,揆乎天理,审量而后出。凡横逆之事,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毋以施于人。此道也,何道也?人与人以此相待,谓之公理;国与国以此相交,谓之公法;其议论人国之事,持此以判曲直、别是非,谓之公论。”(43)严复:《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严复集》,第55页。这些论述再一次表明,作为“天演”世界观的重要形塑者,严复从未放弃对这一科学理念背后的道德意涵的高度关注。“顺乎天演”的“言治”与“治民”,不仅是严复心目中“郅治终成”的政治变革(44)吴汝纶:《吴汝纶致严复书一》,《严复集》,第1560页。,也是极为重要的国家与国民的道德实践。在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历史情境当中,两者共同促成“天演”世界观在读书人心中的内化。
结 语
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严复以其深具洞见的论述以及对一系列西方学术经典的翻译,促成“天演”世界观在近代中国形塑。在“天演”世界观的影响之下,建立在天命、神道与圣人经典之上的“天理”世界观逐渐瓦解。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进入一个由“公理”“公例”“公法”主导的全球竞争时代。(45)晚清以来,传统“大经大法”日渐废堕,在求索新的“大经大法”过程中,西方科学定律或真理观产生了“递补作用”,而在律则式思维的影响之下,兴起了“公理”“公例”式的真理观。关于“公理”“公例”“公法”的概念来源与使用进程,参见王汎森:《中国近代思想中的“未来”》,《思想是生活的一种方式: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版,第251—253页。严复关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的追问,也通过更具普遍性与世俗性的“天演”之道,在古老中国获得了深沉的回响。
晚清时期的严复穿行于英国维多利亚时代(Victorian Era,1837-1901)与中国同治、光绪年间的平行时空,却在两种迥然不同的知识谱系之间,创生出一种复杂而特殊的文化视野。从本文对于严复关于道德与政治议题的描述、分析与评估可见,严复的思想摆荡于中西之间,既接受多种“道”并存的历史现实,却又执著追寻中西学理的“道通为一”。(46)严复心目中的“道”甚至是超越中西以及经验与超验世界的:“吾生最贵之一物亦名逻各斯。(《天演论》下卷十三篇所谓‘有物浑成字曰清净之理’,即此物也。)此如佛氏所举之阿德门,基督教所称之灵魂,老子所谓道,孟子所谓性,皆此物也。”严复:《〈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1028页。然而,严复的这一努力并非简单地认可“道出于二”,进而接纳以“西学为基础”的“外来的道”。(47)参见罗志田:《近代中国“道”的转化》,《近代史研究》2014年第6期;罗志田:《由器变道:补论近代中国的“天变”》,《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8期。借用他在《天演论》自序当中的话,则是“考道之士,以其所得于彼者,反以证诸吾古人之所传,乃澄湛精莹,如寐初觉。其亲切有味,较之觇毕为学者,万万有加焉。此真治异国语言文字者之至乐也”。(48)严复:《天演论·自序》,《严复集》,第1319页。显然,在其乐融融的“考道”过程之中,严复对于中西思想各有批判与取舍,也各有调和与嫁接。他笔下的文字与译述亦因此富含矛盾与张力。在不同的思想语境之下,他对于中国传统的抨击,却往往激活了传统中的因子(如《易经》与《春秋》);而他对于西学(主要是英国的思想学说)的接纳,也每每包含对于西学的修订与扬弃(如达尔文、赫胥黎与斯宾塞的学说)。因此,简单的“道出于二”的判断,无法精确描绘严复在这一时期对于这一系列“英国的课业”(借用James L.Hevia的书名)的复杂反应。显然,严复的翻译与撰述活动所呈现的世界观转型与建构,也是传统儒家思想与西方经典理论在相互交织、密切互动之中实现“典范转移”的过程。
严复认为,他正是在《老子道德经》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当中,发现了“天演开宗语”,认为其尽括“达尔文新理”。(49)严复:《〈老子〉评语》,《严复集》,第1077页。他赞同斯宾塞的看法,以“天演”统摄万物从而实现自然、个人、国家、社会的“止于至善”。但他自身固有的“儒学性格”(50)吴展良:《严复早期的求道之旅——兼论传统学术性格与思维方式的继承与转化》,《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3期。,倡导的却是发展民德、民智、民力的温和渐进的教化力量,而非弱肉强食的无情淘汰与暴力革命。因此,“天演”作为宇宙运行的常理,具有普遍伦理法则、历史哲学和价值源泉的多重含义。“天演”世界观揭示了万物殊异和变迁之中的终极不变性,亦即他在《政治讲义》中所谓的“道”。若借用思想史家史华慈的书名,晚清时期严复的思想探索,其实并非“寻求富强”(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的世俗冲动和科学理性可以简单概括。在寻求“道通为一”的思想张力背后,严复有着对于“超越富强”(beyond wealth and power)的新普遍性的“道”的执著追寻。在清末民初世界观“由道变俗”的进程中,这种贯穿自然、道德与政治的超越价值信念与形而上的追求,通过不同形式保留下来,并左右着国人对于未来中国的种种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