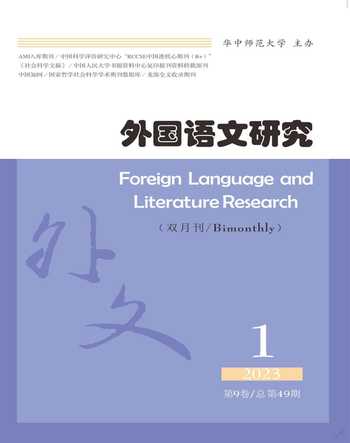孜孜以求的中国译论建构者
王祖友 陈大亮
关键词:陈大亮;翻译理论;翻译境界论;体系
作者简介:王祖友,博士,泰州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外国文学和文学翻译。陈大亮,博士,苏州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翻译理论和政治文献翻译。
王祖友( 以下简称“王”):陈大亮教授,您好!很高兴受编辑部委托,从翻译理论角度对您做个书面访谈。请问您是如何走上翻译理论学习、研究的?
陈大亮( 以下简称“陈”):很高兴接受王教授的采访!说到翻译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我是从读硕士研究生时候开始的,当时的导师是吕俊教授。吕老师理论学养深厚,专攻西方哲学。吕老师在课堂上经常给我们讲结构、解构与建构。受导师的影响,我也开始研究西方哲学,但我没有研究哈贝马斯,而是对伽达默尔的《真理与方法》感兴趣,沿着诠释学这条路线又读了利科、海德格尔、德里达、胡塞尔等人的著作。除了西方哲学,我對西方文论也感兴趣,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到后来的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再到结构主义以及读者接受理论。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哪来这么大的理论学习热情,我在南京师范大学读研的那三年,确实读了很多书,语言学、文学、哲学、美学、文化等不同门类的书籍均有所涉猎。
事实证明,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书没有白读。读过的那些书入脑,又入心,竟产生了写论文的冲动。看到《中国翻译》上正在讨论翻译主体性问题,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而且有自己的想法,于是就写成文章投到《中国翻译》,结果竟然被录用了。当时的惊喜无以言表,接着一鼓作气,又写一篇关于翻译主体间性的文章,后来也发表在《中国翻译》上。学术发表对我的鼓励是最大的,从此我就走向翻译理论研究的道路。
王:看来您是翻译翻译界中的学院派,中国是具有悠久翻译历史的国家,但长期以来有重实践、轻理论的倾向,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传统译论不是理论,是话语,您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陈:我不知您是在什么意义上使用学院派这个概念的,但我在硕士、博士、博士后阶段受过的学术训练、教过我的那些老师对我的影响、读过的书确实让我打下了扎实的理论功底,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真正明白了什么是科研、什么是方法、什么是学术、什么是学问等治学的基本道理。
说到中国传统译论,我在跟王宏印老师读博士期间正式转向这一研究领域,博士论文写的也是中国译论。关于中国传统译论能否称得上理论这个问题,国内翻译界有不少讨论。①我觉得应该用历史的观点,分阶段来分析,得出的结论才能更客观一些。就中国译论的原生态阶段来说,我指的是20 世纪80 年代之前的中国译论,确实称不上是理论,称为“ 译话” 更合适,有点像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的写法,不成体系,但有思想。80年代以后,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学人的眼界大开,中国传统译论开始经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的转型与蜕变,进入现代译论阶段。经过当代学者发展过的中国传统译论就不能说不是理论了。
王:有人说,中国译论落后于西方译论,您是如何看待这些个问题的?中国译论在在哪些方面表现出不同于西方译论的特色?
陈:关于中国译论是否落后于西方,这个问题学界有争议②,这里只谈谈我个人的看法。20世纪50年代之前的中西译论,发展水平基本差不多,很难判断谁落后,谁先进。进入50年代以后,西方译论在语言学的推动下,获得长足发展,势头很猛,成果很多,这种强劲态势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末。从50年代到80年代的这三十年,中国译论确实是落后了,而且差距很大。8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奋起直追,在向西方学习过程中,不断强大自己,差距逐渐缩小。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最近的15年左右,中国翻译研究后来居上,在某些研究领域已经领先世界,走在世界前列。
关于特色问题,这又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学术研究贵在争鸣,我这里也不避讳我自己的观点,姑且说出来与大家商榷。首先,自然科学不存在特色问题,讲特色是针对哲学社会科学而言的。其次,提倡中国特色,是为了纠正中国学术的严重西化、解决中国译论的失语症而提出的话语策略。很多中国学者套用西方理论,脱离中国实际,不了解自己的文化传统,引用的西方译论不解决中国问题。再次,特色是指中西比较视域下的差异性、民族性与传承性,同时也指研究者的主体性与创新性。至于中国译论有哪些特色,这个问题涉及内容太多,这里很难展开论述。我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论述中国译论的特色,刊发在2022年《外语学刊》的第6期上,大家可以展开讨论。
王:如何进行中国传统译论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陈:王老师提的这个问题难度很大,很难回答。之所以说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是因为创新难,尤其是中国传统译论的创新更难。不过,我对这个问题思考了很久,自己也一直往这个方向努力,至少有一些心得体会。我认为,中国传统译论的创新性发展要走中西会通的道路,把不忘本来与吸收外来有机融合起来。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冯友兰、金岳霖、钱锺书等学贯中西的大师在研究方法与治学方法上给我很大的启发。我把他们的治学方法化为己有,形成自己的中西会通思想,用在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上。在不忘本来方面,我提出回归中国传统译论原点的研究思路,具体内容见《上海翻译》2021年第3期上的文章,那里有详细的论述。关于吸收外来,我给硕士研究生开了一门西方翻译理论课,给博士生开了一门中西译论的比较与会通课,这两门课的教学内容就是我对这个问题思考的结果,后续还会有系列论文见刊。会通不是格义,也不是简单地比较,而是在比较基础上的融会贯通以及理论创新。理论创新以及理论体系建构才是会通的最终目的。
王:您对中国传统译论的观点和理想与其他翻译理论研究者有哪些异同?
陈:我导师王宏印走的是现代诠释的路子,即对传统译论的概念、命题与形态进行现代转换,并用现代学理对相应的概念与命题进行现代意义上的诠释。③其他学者选王祖友、陈大亮:孜孜以求的中国译论建构者——陈大亮教授访谈录择某一家译论或某一个人对传统译论进行专题研究与专人研究,如严复的“ 信达雅”、傅雷的“ 神似”、钱锺书的“ 化境”。还有一些学者从历史视角挖掘史料,对某一个问题进行考证,去伪存真,澄清史实,纠正某些不实的说法。张佩瑶总结了阅读传统译论的四种方法,可供参考。④我研究中国传统译论的方法不同于以上几种,既不是现代诠释,也不是针对某个专题与专人,而是通过梳理核心概念的演变,找出中国译论的发展脉络,建构中国传统译论的理论体系,最终目标朝着建构“ 三大体系” 而努力。《文学翻译的境界:译意· 译味· 译境》只是理论体系的一部分,后边还会有《中国传统翻译话语的体系建构与价值考量》、《翻译境界论》两部专著。这是一个宏大的理想,“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我会“ 咬定青山不放松” ⑤,把这一理想变成现实。
王:《文学翻译的境界:译意· 译味· 译境》我拜读了,有系统,有深度,有亮点,很受启发。能具体讲讲您是如何构建“ 三译” 理论体系的吗?
陈:“ 三译” 是指译意、译味、译境,分别对应意义、意味、意境。前者代表文学翻译的三种境界,后者代表文学作品的三个层次。六个范畴同音异义,彼此关联。“ 三译” 的理论体系包括理论依据、核心概念界定、概念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概念交叉的过渡环节、文学作品的三个层次、文学翻译的三种境界、境界的层级性、境界的超越性、超越机制、可译性大小、文学性强弱、境界高低等核心内容。在研究方法上,运用回归原点法、结构界定法、构成要素分析法、逻辑分析法、内容分解法、层层推进法、跨学科融合法、理论与实践结合法,多管齐下才完成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
王:能否介绍一下您的“ 翻译境界三部曲” ?这对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建设有哪些影响或作用?
陈:翻译境界三部曲是指《文学翻译的境界:译意· 译味· 译境》《中国传统翻译话语的体系建构与价值考量》《翻译境界论》三部专著、目前已经出版的是第一部,即将完成书稿的是第二部,正在撰写之中的是第三部。这三部著作围绕我提出的翻译境界范畴,形成一个翻译境界系列,故称为翻译境界三部曲。第一部是在金岳霖的译意与译味说基础上增加译境,建构了“ 三译” 的理论体系。第二部以中国传统译论的“ 信” 和“ 美” 两条主线为线索,把零散的中国翻译话语整合起来,建立核心概念与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梳理其发展脉络,阐释其概念演变,其落脚点是翻译伦理境界与翻译审美境界,因而这部著作是对中国传统译论体系的思考与重建。第三部是在“ 三译”境界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发展其他翻译境界类型与层次,形成译者境界、译作境界、功利境界、伦理境界、审美境界、“ 三似” 境界、“ 三之” 境界等具体内容,并结合具体实例,阐发翻译境界论的理论体系与应用价值。
今年四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国家“ 十四五” 时期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这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层面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规划,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高度重视。目前,我不敢说我的研究对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有何影响,这个问题只能交给时间去检验。但有一点可以说,我对中国传统译论所作的努力,顺应时代发展的趋势,符合国家发展战略的需求,坚持以中国传统、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作为学术话语建构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瞄准“三大体系”建构这个宏伟目标,在学术研究的传承性、自主性、创新性、系统性等方面砥砺前行、不懈追求。
王:您不仅关注理论建设,而且长期从事政治文献翻译工作,真正把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对于年轻学者或学生,您有哪些建议?
陈:这么多年来,我在做理论研究的同时,一直没有中断做翻译实践,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二者在我这里不存在矛盾与冲突。对于年轻学者或学生,我有三条建议:一是理论与实践兼顾,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走得远,走得自信。理论不能高高在上,玄而又玄,要接地气,解决实际问题。实践不能贴在地上躺平,要博览群书,在翻译中研究,在研究中翻译,要有“望尽天涯路”的远见卓识和“蓦然回首”的深刻领悟。概而言之,“学”与“术”并进,“知”与“行”合一。二是要重视学术之道与研究方法。掌握了正确的方法,做事就能事半功倍,不懂治学方法,研究就可能缘木求鱼,事倍功半。年轻学者与学生都要经过严格的科研训练与方法论熏陶,才有可能让学术走上正轨,才能真正明白学问的真谛。建议大家多看些读书、治学与方法方面的书籍,多在研究方法上下功夫。此外,名人传记也很励志,可以激励大家砥砺前行,成就自己的远大梦想。三是独立思考,善于发现。无论是学习,还是做学问,都要有问题意识与独立思考的精神。问題意识是从事科研的前提条件。没有问题意识就相当于无病呻吟,无的放矢。问题意识来自平时的知识积累与独立思考。平时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都会成为发现问题、激发灵感的源泉。独立才能提出有价值的研究问题,思考才能保证研究结果的创新。
王:感谢您分享自己的翻译研究和思考!我想您的体系宏大的中国学派翻译理论和丰富厚重的政治文献翻译实践与研究对中国翻译事业发展和中国话语体系建构必将发挥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陈:谢谢王老师的采访!感谢《外国语文研究》编辑部提供的交流机会!我所表达的观点仅供学界参考,可以讨论,欢迎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