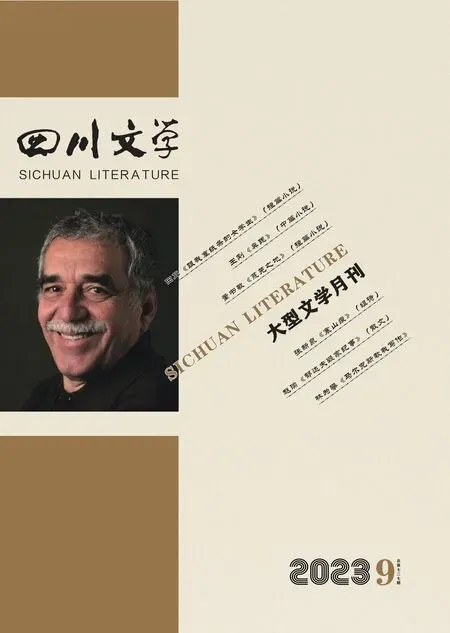父与子(短篇小说)
□文/加主布哈
一
黄昏下的人间像是太阳的巨大血泊,人们在上面颠簸、徘徊,为了躲避闻得到的血腥和看不见的斧头。沿着乌斯河岸回家,我想象要偶遇一条躺在河边的鱼,正在剥自己的鳞片。拉客的马车哒哒地从我身边走过,车夫多是些县城周边村落的彝族老人,他们专跑从火车站到县城老菜市场的线路,约五公里,单线收两块钱车费,我家就住在老菜市场附近。我想着两块钱也够抽几根烟,况且天还早,所以没有搭理他们。
走到半路是一座石桥,叫乌斯桥,阿尔莫苏驾着他的马车让我上去,他的嘴里已经没有一颗牙齿为他把风,说载我一程只要一块钱了。我说想走走路,他把马车停在我跟前说都一年没回来了,还省这一块钱干啥。马车上几个妇人已经怨声载道,我拉不下脸,只好拖着行李上了车,随手掏出两个硬币给阿尔莫苏,大声告诉他真不是为了省钱,并斜看了旁边几个女人的表情。阿尔莫苏坐在前面驾马,马奔跑起来的时候,他头上那顶雷锋帽的两只耳朵就起伏不止,他收过我的硬币,用戏谑的口气说外面回来的人就是不一样,大方得很。我不想理他,这老头嘴里没把风,什么话从他嘴里出来,明天就得传遍这小县城。他一直喋喋不休地跟我搭话,我心中本就苦闷,还得克制心中的怒火,颠簸的马车,让我着实恶心,要是以前,我定会数落他几句,或者说一些阴阳怪气的话,但我这时候真没什么心情,凛冽的风把我的嘴巴缝得很密实,没有一句话想跑出来。
下了马车,我点了一根烟,给阿尔莫苏一根,他说自己只抽旱烟。穿过狭窄的小道,尽头是一座四层楼的老砖房,我摸着漆黑的楼梯来到四楼,左边住着阿尔莫苏和他的孙子。右边原本是空着的,爷孙俩背了一些砖和水泥,搭建了一个小屋子,租给别人,我老婆不知道在哪里得来的门道租了两年,顺便带儿子到县城读书,后来从阿尔莫苏那里买下这小破屋,屋顶还是塑料做的,我从老家背了一些木板隔成两个房间,刚好可以放两张床,在门口放了一张桌子当厨房,外面空出来的地阿尔莫苏种了一些菜,还养了几只鸡,我最受不了那股鸡屎味。一进门,儿子正在床上睡觉,我忍住心中的怒火,掀开被子叫醒他,问他你妈去哪了,他冷淡地说不知道,起身走进另一个屋子,他的个子已经到我耳朵,我本想踹他一脚,却还是忍住了。抽了一根烟,躺在床上,风在屋顶呜咽。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妻子在门口做饭,进进出出的时候,她屁股上那块灰色的补丁很刺眼,一年了,她还穿着这件牛仔裤,只是屁股上的补丁从蓝色变成了灰色。我们没有说一句话。吃饭的时候,不见儿子,我问她儿子去哪了,她阴着脸说我管不了你们父子俩。我说你是不是欠揍,她闷着头咽下一口米饭。
“实在不行,我们回老家吧。”她埋头收拾碗筷,继续说道:“反正儿子也被开除了。”
我的怒火终于忍不住了,把手中的烟蒂扔在脚下踩住,大声呵斥:“你连个孩子都管不好,有个什么用。还回老家,老家现在就剩一块破地,连个挡雨的屋顶都没了,回个屁。”
她抬头看着我,两行眼泪顺着她那平实黝黑的脸颊流下来,手里还端着两个陈旧的瓷碗,我有些不敢与她对视,便点起了一根烟,问她:
“那家人的孩子怎么样了?”
“还在医院,不让探视,我今天去我哥那借了三千块钱,给他们送过去了。他家吃定我们了,狼到羊群做客,哪有饿着肚子回去的。”她把碗放在水龙头下,反复搓洗,几根头发粘在她流过泪的脸颊上,寒风吹着她,吹进那灰色补丁里,吹得她心里结了霜。
我说:“谁是狼,谁是羊,还说不准呢。”她没说话,走进屋子,又准备下楼,我问她去哪,她说去找你那宝贝儿子。
晚上她没找回儿子,说不知道躲哪家网吧去了,让我去找,我说爱死哪死哪去吧,闯了这么大的祸还不知悔改,用被子蒙住头就睡了。很晚的时候她爬上来,贴住我,解开我的腰带,我转向另一边,没有理会。
二
县城在峡谷,又小又窄,只有一条主街,冬天的时候,风吹得街道上的人像散落的稻草,只顾着埋头疾步奔走,没有人跟我打招呼。在幽暗的小道尽头,我找到儿子,他刚从那个叫雄风的网吧出来,身边还有几个同龄人,我本想上去给他一脚,但还是忍住了。我也曾在这里被我自己的父亲踹了一脚,他让我在自己的兄弟面前丢尽了脸,那一脚把我踹出学校,也踹出这个小县城。
我跟在儿子身后,让他带我去找他班主任,他的个子已经快跟我一样高了,心也比我大,前几天把同学打了,据说是用石头砸在别人的头上,这点跟我倒是很像,我也喜欢用石头打人,刀子太短了,石头可以扔过去。班主任是个矮矮的女人,说话很快,我没怎么听明白,最后让我去找校领导,我问找哪个领导,她说校长,然后找了个借口说忙去了。
按照班主任说的,我们找到了校长办公室,但没人。副校长办公室有人,我想着这事副校长也能解决,就敲门准备进去,但是在看到副校长后,我收回了手中要递出去的烟,埋着头走出来了,害怕他认出我。我问儿子这是你们的副校长,他说是,才来没多久。此时,我的心中吹进几缕冰冷的风,风在心里像野马般奔腾,把我的心野践踏得一片狼藉。我让儿子回去,自己走在大街上。
在文化广场遇到几个熟人,其实也没多熟悉,他们准备去喝几杯,叫我一起去,我知道他们只是客气一下,但还是去了,因为我着实不知道去哪里。来到一家茶楼,抱上来两件啤酒就开始喝,县城里有很多这种卖酒的茶楼,大家进来基本上不点茶,直接喝酒,有女人的话会点一点小吃,比如土豆、凉粉。我们几个男人就喝寡酒,桌面上只有一盘瓜子和各自的酒杯,开始的时候是一些客套话,接着会有一些调侃和玩笑的话穿梭在这间只容得七八个人的小包间。老板是个不喝酒的彝族男人,俄牧家族的高个子,穿着一件西装,让他沙马家族的老婆来敬酒,还带上一个衣着鲜丽的闺蜜,几句下来才知道是我家族的女人,听说是同一家族,她叫我哥哥,多敬了我一个酒,又知道我们的老家住得很近,她走出去抬了一件啤酒,说这是请我喝的,我只能再敬她一杯。等两个女人走了,我们的话题也跟着浮躁起来,纷纷嚷着叫几个女人来陪一下。
“把自己老婆丢在家里喝酸菜汤,请别人的婆娘在街上吃香的喝辣的。”我们中间有很多自认为能歌善唱的人,但说出这句话的是唯一正儿八经的歌手崖狄,毕竟他有自己的原创歌曲,而且拥有一把木吉他,他快四十了还没老婆,其实他有过老婆,但是跟另一个歌手跑了。果然,他们真的叫来了别人的老婆,四个女人,她们化着浓烈的妆,说蹩脚的汉语,有一个让我甚至有些恶心,她把自己的脸涂抹得白里透红,但脖颈却很黑,对比鲜明。我在内心里嘀咕:“猴子洗脸,只洗脸不洗脖子。”她们酒量很好,还没坐下就每人打了一圈,我们几个的兴致也上来了,就换了500毫升的大杯子,且把地点也换到了附近的KTV,在暧昧的灯光下,我们把手伸进了她们的乳罩里。一个女人回应了我,隔着裤子抓住我的兄弟,我们在无意中对视时,又同时停止了手上的动作,并且端起酒碰了一下。歌手在唱歌,他唱的都是情歌,但是没有一个女人靠近他,那个化妆只化脸庞不化脖子的女人敬了他一个酒,他没有喝完,后来我们没有听到歌声了,也没看见那个女人。
准备撤的时候,都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路上遇到很多骑着电瓶车揽客的女人,我旁边的男人说:“她们都是老公在外务工,一个人带着孩子在县城读书的妇女,很辛苦。”接着说,“有些也会把揽的客人带到某个角落去的。”他旁边的女人瞪了他一眼,然后依偎在他怀里去了。我旁边的女人问我还要不要去吃点烧烤,我说算了,该回去了。我其实也想去,但我怕遇到自己的婆娘,我知道她也是那些揽客女人中的一员。
到家的时候已经很晚,儿子已经睡了,老婆还没回来,我的心像一座快溢出的堤坝,想找个理由发泄,但是在酒精的麻醉下,还是沉睡了。半夜,她解开了我的皮带,我抽出皮带,抽在她身上,她没有出声,我把她从床上踢了下去,并再次抽在她身上,问她是不是也把野男人载到某个角落了,问她是不是也会被另一个男人叫到KTV喝酒,她哭了,并在漆黑中摸到门外,在院坝上大声叫唤。我追出去,抓住她那稀薄的头发,拉到房间里,正准备挥动皮带时,灯开了,儿子站在那里,面无表情,他把手里的刀丢在我面前,冷冷地说:
“用它吧,把我们两个都杀了。”
我的酒醒了,心中的坝已决堤,变成寂寥的淤泥,只觉得沉重又迟钝。但还是放不下自尊,只得扔掉手中的皮带,钻进被窝里,却怎么也没能入睡。想起儿子学校那个副校长,他都当领导了,而我如今却变成了这模样,白天我在他额头上看到那道伤疤,还很显眼,当年就是我用一颗石头打出来的。我记得那是个冬天,当时我们在一个班,我让他帮我做一道题,其实那题我会,只是单纯看不惯他,因为我们觉得他小肚鸡肠,而且爱装。他不肯,于是在放学的路上,我叫上几个哥们儿把他堵在一条小道上,教训了他一顿,他仍不肯认错,于是我扔过去一颗鹅卵石,刚好砸在他的额头上,看到他的血染红了那条白色的围巾,我才觉得心里解了气。晚上我和几个哥们在网吧玩了一夜,并在后半夜一起看了几部刺激的影片。第二天一早,就被我父亲踹了一脚,从此,我就再没有见过那个小肚鸡肠的人。这些事,既然已经过了那么多年,说实话今天在副校长办公室再次看到他,并不觉得心里有愧,更不怕他朝我的额头扔过来一个石头,我是怕他知道那个犯错的孩子是我的儿子,将他彻底开除,毕竟他是个小肚鸡肠的人。我不想让儿子步我的后尘。
三
妻子假装什么事也没发生,我醒来的时候,她在做饭。我走出门想去上个厕所,又闻到阿尔莫苏那几只鸡的屎臭味,所以抱怨了几句。她没有看我,只是嘀咕着说:“但是人家有一个听话又优秀的孙子,已经考上大学了。”她的右脸有点肿,且横着一条青纹路,那是我昨晚打上去的,所以她说话的声音很抖很轻。她在煮一锅猪蹄,我问他今天是什么节日,她说她哥哥要过来。
我这个大舅子,个头不高,但是口袋鼓得厉害,说话的时候腰板自然也直,他却对我不敢太放肆,因为我假装喝醉把他打过一顿。他一进门就问妻子的脸怎么了,妻子说半夜起来不小心撞到柱子上。我知道她会这么说,因为她不敢,这些年,我感觉我已经把她的胆吞进我肚子里了。大舅子也没问下去,但他心知肚明。吃饭的时候,我问他要不要喝一杯,他拒绝了,说下午还要帮我们家办事,我问他什么事。他吞下嘴里的肉说:“还能什么事,你儿子麻娣打人被开除的事,我认识那家人,下午约了他们家里人,和解了。麻娣才能回学校读书。”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能明显感觉到那种凌人的气势,于是对他说:“我初中同学去麻娣他们学校当副校长了,我昨天已经找过,不用你解决。”说完这句话,我自己其实有些看不起自己,但放不下自尊心。妻子始终没有插一句话。
才吃完饭,我父亲就来了。他一来,大舅子简单问候两句就走了,他俩不对付,是因为当年我结婚的时候,妻子的娘家送了十头绵羊作为陪嫁,但是那群羊识得老路,所以老是跑回去,不管我父亲把它们牧在哪座山上,傍晚都会跑回娘家去。父亲是出了名的急性子,于是在某个他心情本来就不够愉快的傍晚,从妻子的娘家把羊群赶回来,但那只领头羊还是不服气又跑回去,这让他很恼火,于是抓住那只领头羊,宰杀在我大舅子家屋后,并且让我大舅子把羊背回去煮了吃掉。这个行为在彝族地区其实真算得上调戏,甚至可能会引起两个家族的械斗。好在我老丈人是个通情达理的人,当过兵,入了党,不仅没跟父亲一般见识,晚上还让大舅子把羊背到我家,说这羊既然给了妹妹,那羊肉也该你家吃,放下羊就气冲冲走了。我父亲让我把羊肉煮了,叫上村里人吃,他自己一口汤都没喝,只坐在屋檐下抽烟。其实我内心还是很敬佩父亲的这种行为,因为我觉得亲家之间就该这样针锋相对,没必要装得那般彬彬有礼,又不在一口锅里吃饭。我妻子自然不敢对父亲怎样,她是从小就被教会了:“嫁给石头,就跟石头坐一辈子;嫁给树木,便跟树木站一辈子。”但倔强的父亲终究是不肯跟我们到县城来住,所以他至今仍孤身在老家。他抱着两只红色的阉鸡,说可能领导会喜欢这种在山上养的鸡,可以拿去打通一下关系。妻子把鸡接过来,放进了阿尔莫苏的鸡圈里,这两只阉鸡的确跟阿尔莫苏的不一样。父亲问妻子麻娣去哪了,妻子撒谎说去同学家里了。但是他没有跟我说一句话,我也没跟他打一声招呼,在我们这片土地上有一句谚语,大概意思是父与子不对付,就像耕地时,在前面牵牛的人和在后面掌握木犁的人合不来。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很对,从小他就是那个在后面赶着我和耕牛的人,他高兴了会在犁到头的时候喊我的乳名,心情不好了也会挥鞭子在牛身上,也打在我身上,所以父子关系,一直都是鞭策和叛逆,只是这种关系,现在该轮到我和自己的儿子麻娣了。
儿子麻娣回来后,我父亲就要走了,临走时他对麻娣说:“路,一步走拐了,就需要用余生来纠正。”他让我送他到车站,走了一半的路,我们还是没说一句话,看见一家酿酒的店,我进去买了十斤酒给他,他接过酒,让我回去。我点了头,目送他离开,他沿着乌斯河,拄着拐杖,渐渐远去,像一条鱼在河岸上挣扎、蠕动。回去的路上,我经过一家烤鸭店,想起麻娣最喜欢吃,买了两只回去,但是他没在家。
四
天将黑时,我堂弟姆巴来到我家里,他是我们这个家族里唯一在县城上班的人,我只知道他在一个小学当老师,平时来往并不多,说实话我并没有把他当成什么国家干部,毕竟他小时候可是只会哭着让我去为他报仇的爱哭虫。如今他身穿一身黑色西装,人模狗样地出现在我面前,我还是只把他当弟弟。他一进来就指责我出了这么大的事,也不说一声,还让老爷子冒着寒风跑了他家一趟,还带着酒水。我大概能猜到父亲是把我买的那十斤酒带去他家了。我让他坐下说,他说凳子太矮,蹲不下去,于是就坐到床边了,双手放在大腿上,他的圆肚子快把里面那件白衬衫撑破了。他说话的速度很慢,说可以摆平这件事,但是要找一下关系,需要请领导吃饭。我说我明白,你安排一下。他说已经安排好了,就明晚。他走后,我问妻子要那张存折,她不肯,问我出去一年也不挣一点钱吗。我瞪了她一眼,恶狠狠地说:“我在外面还养了一个儿子。”她没有继续争执,翻开床底下的木盒子,在最底层拿出了存折扔在我怀里,就出去了。
第二天下午,姆巴叫来了他所谓的几个领导,在一家彝族餐厅招待他们,我一个都不认识,姆巴挨个给我介绍,每介绍一个就让我喝一个大杯的酒,领导们喝一口。接着,姆巴也敬了一圈,他拿着比我更大的酒杯,走到每个人面前,把腰弯得很低,右手握着大杯子,左手把对方的小杯子抬高。他跟我也这样喝了,让我心里有些不是滋味。几圈酒敬下来,也没提麻娣的事,但我已经喝得有些找不着北。我看姆巴走进厕所,也跟了进去,看到他在呕吐,我也在旁边吐了。我问他为什么不跟领导提那件事,他双手搭在我的肩上,表情狰狞着说还不是时候,等下一场。于是我们又来到KTV,几个领导喝得很高兴,唱得也尽兴,我只能待在边缘,他们会偶尔敬我酒,也会跟我保证没什么大问题,于是我就学着姆巴用左手把他们的杯子抬高过我的杯子,弯着腰说麻烦了,心中就感觉到有一股莫名的挫败感翻涌不止。从KTV出来后,姆巴让他们再去吃点夜宵,有几个称自己喝醉了,就撤了。我忘了自己是怎么到家的,模糊记得儿子麻娣给我脱鞋,把我扶上床。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等姆巴的消息,可他却一直让我等,说这不是什么小事,还得再走动一下,于是我让妻子把那两只阉鸡送到他家,让他看着抱给某个领导。他说还需要再请另一个领导吃饭,还是上次那样,我在路上遇到歌手崖狄,顺便让他去帮我扎场子。我已经熟练了上次那一套,但是姆巴仍然没有把事情说得明白,喝了酒我有些不耐烦,歌手崖狄似乎对姆巴有些意见,蹭到我耳边说了很多姆巴的坏话,大概意思是姆巴是个骗吃骗喝的吝啬鬼,从不掏一分钱,到处混场子,而且看不惯他那低三下四的模样。让我小心点,别被骗吃骗喝了,事儿没办成,甚至他可能都没跟别人说我这个事。我其实也有点怀疑姆巴了,但我内心仍然觉得他不敢坑骗我。散场后,姆巴说送我回家,这时他已经喝得很醉了,但最后一个酒,他还是把酒杯放得最低。在我家楼下他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他说自己真没用啊,这么多年了,一官半职没混到,也不能帮助亲戚朋友。我知道他的难处,毕竟我们也没有帮到他什么,他中职毕业后自己摸爬打滚,从代课老师混到现在的编制已经不容易。但我还是跟他说人不能把自己的腰弯得太低,那样只会让人骑在你身上。我把他扛着回到他家,他在醉意里把我给父亲买的那坛酒开给我喝,我只喝了一口就让他好好收着,便准备离开了。临走时看到三只阉鸡在他家院子里,长得差不多,我大概明白了怎么回事,也不想再多说什么。要是换作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估计会把这三只阉鸡掐死在这里,然后叫醒酒醉的姆巴,让他好好吃完。
走在回家的路上,已是凌晨,突然下起了大雪,雪花飘落在我的肌肤上,融化了我的醉意,我没有加快脚步,事情到这一步,就不能更坏了。如果一件事不能更坏了,那或许就会好起来吧,我并不是个善于安慰自己的人,我已经四十二了,这些年怎么过来的,自己最清楚,对于我们这样的人来说,回头路比继续前行更艰难。到家时,酒已经醒了,妻子睡得很香,我身体里的冷惊醒了她,我把手放在她已经下垂的乳房上,唤醒了她内心的火焰和委屈,于是她抽泣着抱紧我,我分不清她是在享受还是在煎熬。这些年,我很少碰她的身体,实话实说,我在外地打工的时候,都是去找那种风尘女子,所以回到家后,对这事并没有什么欲望。我也很少挣钱回来,一年如果没特别的事,顶多就回来两次,这样想,也的确是委屈她了。不过,就算认识到这些,我也不会对她有什么好脸色的。此时雪在埋屋顶,风是不能成为谁的立场的。
五
雪下到县城,第二天就化得差不多了,只有几家人的屋顶上还有几撮,山上是雪白了,乌斯河并没有因为这场雪有什么变化,只是静静地流淌。太阳出来了一会儿,又不见了。阿尔莫苏来到我家,脱下他的雷锋帽,坐在凳子上抽旱烟。
“我是受人所托,来跟你家商量一下麻娣在学校的那事儿。”他吐出的烟雾很少。
“你认识那家人吗?”
“是的,以前住在我们老家那边,后来也是带着孩子到县城读书。男人死了,就一个寡妇带着四个孩子,生活挺艰难。”
“越是这样的家庭,心眼越坏。他家现在到底想怎么样?”
“那倒也未必,据说那孩子成绩很好,胆子也小,估计就是麻娣欺负人家了。现在他家想要两万。”
“让他直接来把麻娣打成那个孩子一样的伤吧,他们这不就是抢吗?”
阿尔莫苏往烟杆里再放了一点烟叶,引用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谚语,最后说:“大雁按律飞,蜜蜂守规行。我也只是个中间人,你家也开个价,我再去找他们家说。”
我说顶多给他家一万块,多一分我都不干。阿尔莫苏说罢就要走,妻子留他吃饭,他提高了自己的音量说:“我孙子回来了,要带我去街上吃,这孩子,现在真是不懂节俭了。”我讨厌他这样的说话方式。
阿尔莫苏走后,我让妻子把所有积蓄拿出来,大概合计了一下,只有两万三千块。我留了一万给妻子,说这是给那家人的,把另外的钱装进口袋就出了门。在一家超市买了一条中华烟,装在黑色塑料袋里,去往麻娣的学校,在副校长办公室门口,我徘徊了很久,最终还是敲响了那扇门,但没人,只好回去。忘了告诉大家,这个副校长叫沙马古尔。
阿尔莫苏晚上又来到我家,他说那家人肯要一万块了,妻子给了他,但他一直不肯走,旁敲侧击着,我知道他想要一点辛苦费,我是不想给他的,可是又怕他到处传播谣言,到时候他肯定会说我是吝啬鬼,最终还是给了他两百块钱。他嘴里说不好意思要,手却已经把钱揣进那个棕黄色的钱包里,然后就走了。晚饭时,我问儿子为什么打人,他说那小子是个阴阳怪,觉得自己读书厉害,就用一些阴阳怪气的话嘲讽别人:“他说父亲的教诲穿越九座山脉,母亲的箴言跨过五条河流,有些人就算父母安在,看起来也像没人管教,我以为他是在骂我,所以把他打了一顿。”这是麻娣第一次跟我说这么多话,我问他还想不想继续读书,他点了点头,筷子夹住了一条鸭腿。
第二天我来到副校长沙马古尔的办公室,他见到了并没有惊讶,我把手中的塑料袋握得很紧,手心已经出汗,实话说我还是紧张了,仿佛不是儿子麻娣犯错,而是我犯错了在被老师训斥。但我还是假装镇定,沙马古尔说话的语速很慢,我发现当领导的人说话都慢,把每个字都咬得很紧。他说早就知道麻娣是我的儿子,也问了我的近况,似乎想和我套近乎。我问他能不能不开除麻娣,他拒绝我递过去的烟说:“我没抽烟,麻娣其实很聪明,我听他的班主任说他的理科一直很好,只是偶尔会走神,不怎么上心。我跟校长聊过这个事了,决定还是给他一个记过处分,希望他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回来好好读书,毕竟只有读书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我站起身感谢他,然后把黑色塑料袋拿给他,他再次拒绝我,义正词严,我看到他额头上的伤疤,迅速转移了目光。我说晚上一起吃个饭,他也拒绝了,说最近父亲生病,需要照顾。
临走时沙马古尔再次叮嘱我,好好教育孩子,但我感觉他是在教育我,就在背过他的瞬间,我心里想:“脸上笑嘻嘻的,谁知道你喉咙里是不是已经长出了尖利的牙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