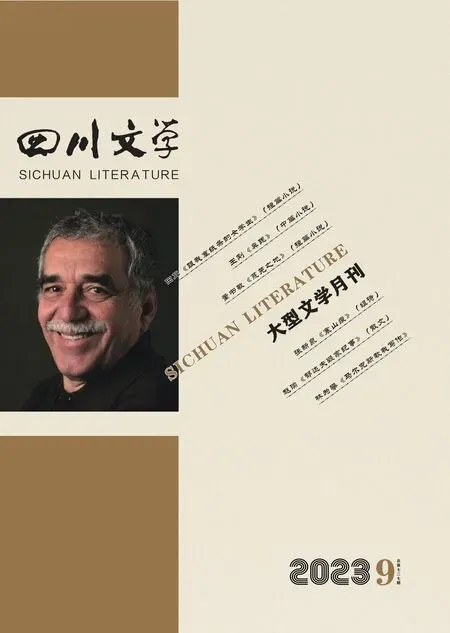倾斜在乡间的修辞
□文/赵会宁
沿着西街口出得城来,只见被楼宇和嘈杂堵急了的大地正以洪流之态,向南、西、北三面急速漫开,又如渐次铺开的毡,向天边铺去;目光扯着身体也平展展地向着平展展的大地生长。绿色在大地上站稳脚跟后,又扯长身子向着灰白迈进。只见绿浪翻滚,从四围涌上来,涌进眼眶,涌进毛孔,涌入骨缝,涌入倾斜的心房,体内便有了一万株玉米的拔节声。这一切变化都在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悄无声息的还有打开肢体的一条路,正被悄无声息的两堵城墙般对视的柳树抬着跑,跑向了悄无声息处。绿色流泻,泻得更是悄无声息:向云巅上泻,向大地的怀里泻,向一个人的心里泻。似乎,泻不出一番别样来便不罢休。
一个午后,一个人的时光慢慢倾斜,倾斜在乡间巨大的词场中,被一种全新的修辞慢慢修饰……
草从不寂寞
总觉得有那么几棵草很笨,笨得专挑着坚硬而逼仄的缝隙生长。一副枯黄猥琐的样子不被人待见。风见了是不是躲着走,我不知晓,但若是有风,脚丫一定会告诉我,迎风的墙会告诉我,崖畔斜了肩的树会告诉我。时光的长风里,谁的脊骨能永远端挺呢?
村子里名字中带“草”字的女人很多。她们人生的第一声哭被一方土炕接住,模糊觉得炕就是母亲;第一声疼种在一方坚硬的土地上,又模糊觉得炕和母亲不一样;第一次扶着墙学走路,又模糊觉得墙像父亲的背。走出窑洞,来到大地上,看到一株草上顶着一髻儿白花,特像母亲看她时的笑,就进一步模糊觉得大地和母亲会开花。花一开人便笑了,人一笑花也就开了。当春风铺展身子漫向大地的时候,大地上都是花,一朵挨着一朵,相互碰一下,大地上到处都是笑。草换茬儿,这些名字中带“草”字的女人长大后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还是一株草。草草的一生里,只知道扎根。一扎根,就扎出一条河来。四爷的女人是捡回来的,没名没姓,更不知道家乡在哪里,四爷就给她起名“草儿”。草儿草儿,四爷叫了一辈子;草儿草儿,风柳村的大人们叫了一辈子;草儿草儿,我们这些孩子也叫了一辈子。村子里不敢生风,一生风,村子里到处都是草儿。初来乍到,草儿确实像一株生在石头缝的草,活得很笨拙。四爷是个火爆子脾气,往往一说二就打,打得草儿在地上打滚儿,压倒了一片草。打完了,四爷走了,草儿起身,身下的草也起了身。草儿死后,她的墓碑上刻着“王府登科糟糠之墓”。我长大会识字时,跟着村里一帮男孩子像风一样在田野里跑,经过坟茔时,会停下来看看墓碑,发现村庄里那些叫草儿的女人的墓碑上别说名字,就连姓氏也没有。那一年,我们修家谱,竟然没人知晓几个奶奶的名字。哎,真是草草的一生啊!
她们寂寞吗?在风里,星子般密布的白色花儿似在点头又似在摇头。
一入伏,雨说来就来,从不打招呼。再厚的云,雨滴都能拣着缝隙落下来。树荫下睡觉的孩子有第三只眼。一滴睡迷糊的雨不小心一翻身,从云头掉下来,恰巧被这只眼捕捉到,一个骨碌起身,抢先于云头往回跑。孩子追着一片阳光跑,云追着孩子的头顶跑,雨追着云的裙角跑。
此刻,草在窃笑,草在期盼。雨一旦落到地上,它就追着雨脚跑。
只管落下来,草从不避让。草见了风就舞蹈,见了雨就清脆,见了阳光就腆起脸。活得真简单啊!大人时时发着感慨。孩子才不管大人的话,躲不过云头时,就任雨水淋下来。雨下着,孩子饮着雨水在长,草饮着雨水在长。缝隙里长的那几棵自是也不例外。把孩子当草养,有人这样想着,有人也这样做着。
在村里,和我年岁不差上下的孩子有二三十个,一个个被叫草儿的母亲藏在心尖上,又一个个被当草养着。七八岁的时候,我们就在田野里跑、沟梁上跑、河道里跑,调皮的几个还向树上跑。树上的鸟巢常常被我们几个弄得底朝天,归来的老鸟看到摔在地上的巢穴,一叫就是一个晚上。本来囫囵的夜都被叫碎了。
有一年冬天,少有下雪,村庄里到处都尘土飞扬。我们这些男孩聚集在大胡同里,把坍塌的矮墙当掩体,把厕所当碉堡,执起鸡蛋大的胡几块(土坷垃)当子弹,发起了一场战争。打着打着,一方弃堡逃向田野,另一方就跟到田野继续厮杀。田野里,风吼土块飞,有几块胡几块不偏不倚落在几个人的前额上,风里就有了一两腔哭声。我后脑勺有一块少了头发,听姐姐说就是打胡几仗落下的。其实我已经记不清了。等到吃晌午饭时,两拨人聚在一起,你看看他,他看看你,都成了一个胡几块,禁不住就是一阵哈哈大笑。笑声被风携着撒在了村庄的各个角落。回到家里,那些被我们叫母亲的草儿们假装生气,抡起扫帚看似要下狠手,但当扫帚落到脊背上时,就变成了唰唰的清扫声,偶尔还能听到一两声掩鼻的嗤嗤笑声。
草一茬,草儿们一茬。在村庄里,草有独生的,但大多数都是扎堆生长。高低错落,左右横陈,偶尔也相互攀附,即是一个长到另一个的脚下,一个爬到另一个的肩上,一个挂到另一个的耳廓,相互之间似无虞。但村里的草儿们却不这样——个别在低处站惯了、站久了的,就极力想着何时能展展腰,只要逮着机会,就格外跋扈。同家二嫂就像一堆冰草中的芦子草。起初,和谁都好,只要话匣子拉开,便手舞足蹈、声情并茂地喋喋不休。不叫叔婶,不开口;不叫姐妹,不开口;不堆满笑脸,不开口,就这样把根默默地扎在了村庄的四处。等到其他的草儿们警觉时,同二嫂已把村庄搅得风声四起,她的嘴就是一片芦子草的草叶,经常割得四邻不安。我十三四岁的一天,刚刚放学回到村里,就听到尖锐的叫骂声裹在北风的锋刃上,把一个村庄割得四处都是口子。细听,仿佛是同二嫂嫌公婆对几个儿子一碗水未端平。最近几年叫骂声少了,但一旦有,村庄的风里就满是“驴锤子”“断子绝孙”的词条。同二嫂的嘴毒啊,村庄里确有断子绝孙的。听人说,同二嫂的儿子结婚近十年了,仍膝下无子。
到了城外,遍地是草。一簇一簇,一堆一堆,一片一片。若是云头上吊下一根线来,草攀着线一定会长到天上。儿时在沟底才能见到的草,现在都长到了塬上。再高的山,草照样能长到山尖。雨后的城外,草木为王。它们喝足了水,漫到墙根,攀住墙上的粗糙处,长到墙头,顺着屋檐就爬上了房顶。不久,就筑起了一座绿院子,顺便也招来禽雀虫蚁。几只鸟儿隐在绿叶里,学着花开的样子,叫一两声,一面墙上都是闪烁的光斑。草木借一场雨实现着自己的心事。不只是向高处长,还爬上土埂,漫过一块荒地,下一个斜坡,向沙地里长。脚长在自己身上,想向哪儿生长就向哪儿生长。最有意思的可能要数沟里的草了。沟底的,抬头仰望山腰的、山顶的,总想着有朝一日坐居高处。山上的,低头俯视低凹处的、褶皱处的,总期望哪一天能睡一个安稳觉。彼此羡慕归羡慕,但从不刻意。雨一来,它们都会抬头迎着雨。
雨一旦落到大地上,就会被草领着跑。云上是生不住根的,所以草长到哪儿,雨就跟到哪儿。特别是未被束缚的草,一见雨就疯了似的长。挤挤挨挨中,各是各的样儿。藤蔓类的,需要攀附,蒿草就会给个肩膀。蕨类的,把地当床,四仰八叉躺下来抱着梦长。
独长抑或群生,谁也未曾见草恣睢过、吵嚷过。草间的事情,有时一场风捋一捋就和谐了。开花与不开花是种子早就决定好了的,只要绿着,就是最大的快乐。
今年一开春,父亲去了姐姐家,老宅被一把大锁一锁就是几个月。人去了,人间的烟火就断了,风都不会光顾。蜘蛛占据高空,四处结网,挡住蝇虫。地上呢,草循着人的足迹长,一个院子就成了草的世界。紧贴地面的是苔藓,把地缝弥合。高过脚踝的是车前草、蒲公英,零星的、扎堆的、地毯似的,锁住泥土,不让风把泥土带走。齐腰的,便是蒿草了,站成人的模样,守望窗口门洞。蜘蛛是不是去年的,我不知道,但这草绝对是去年的,甚至有些还是前年的。我清楚地记得,长在西北角的几株被我砍断了脚踝,爬上台阶的几丛被我揪掉了须发。今年,它们又从原地长出来,一副不记仇的样子,和蜘蛛替我看家护院。草来了,院子不寂寞。
其实,草也从未寂寞过,毕竟大地那么阔大,那么厚实。
露珠这个舞者
一到夏夜,天上的星星就少了。特别是一场雨后,天空被清洗,星星就更少了。当一轮圆月扶着树梢爬上天空时,孩子们惊异地大呼起来:星星落在草叶上了!大人自是不会被孩子们打扰,稳坐在树下、墙根,噙起烟管浸在黑暗中思忖着黑暗,烟雾扯成丝缕后,扭着腰肢曼舞。轻的东西,任何时候都不一定是轻的。此刻,烟雾搅动着大人的心潮。品咂黑色和烟雾,夜里有了一些新的东西。狗伏在大人的身旁,也故作深沉。大人不动,它不动,但黑暗是锁不住孩子的。调皮的几个早已靠近门口的菜地,仔细端详起菜叶上的“星星”了。层层叠叠、遮遮掩掩,叶子为星星们营造着哲学氛围。隐隐约约、星星点点,大地亦学会了辩证。一片菜地上,虚虚实实被隐喻着。闪烁,闪烁着闪烁的意趣。这里没有言语,但透亮却是相通的,亦如这三五个孩子,他们觉着露珠就是星星。看一眼,他们的心也跟着亮起来。想进一步探个究竟的,早已把指尖伸向菜叶,轻轻一拨,密密麻麻的碎银落下来,孩子们又是一呼。
雨后的早晨,草木被洗得透明,全是脆生生、明亮亮、光鲜鲜的。一夜工夫,全都脱了胎、换了骨。被洗的还有人间:牛羊的铃铛声脆了;蝉鸣声里的裂纹弥合了;炊烟一扫疲乏,裙角曼妙;孩子们的脚步稳了、轻了,笑声比叶子还翠。草木的绿绿到大地的骨子里去了,就连一颗颗露珠都是绿的。这样的时刻,风是不敢造次的,也不愿造次,一任露珠在草叶上恣睢。高居叶尖的,明眸远眺;居于中部的,稳坐冥想;栖于叶柄的,朦胧半醒。个个都沉醉在绿色中难以自拔。
蜷缩久了的草可不会顾恋露珠的,一个懒腰,叶子抖了一下。高居叶尖的露珠半个身子就悬在空中,紧接着又是一个鲤鱼打挺,回到了叶尖。惊慌失措中,踉踉跄跄稍稍站稳脚跟后,就屏息束手。时间久了,又是清亮亮的、脆生生的。冥想的,在叶子中部荡起了秋千,稍稍惊慌后就愈加沉醉了。叶柄部的,这会儿彻底醒了过来,目光拐了一个又一个弯儿,想探个究竟。
阳光来了,草木都想着拔节,大人们的目光被青烟扯着拔节,露珠还是各站各的位,在彼此的舞台上舞蹈着。直到谢幕,它们和登场时一样:悄悄地来,悄悄地走,不带走一片月光和云彩。
雨后,草叶里装满了一杯杯清酒,所以牛最贪恋雨后的草。那些年,父亲趁着露珠还未醒过来,就夹了一把镰刀寻嫩草。一片绿色的汪洋里,父亲挥动着右臂缓缓前行。他的身后是一撮一撮摆放整齐的嫩草,如涟漪一样。等我们起床时,铡刀旁一捆嫩草被割回来,割回的还有一坛看不见的清酒。牛闻到升腾的酒味,早已按捺不住,极力地扯着缰绳,嘴角的涎水连成串。被露珠洗了的父亲也便成了雨后一颗最大的露珠,只见他靠着墙壁蹲着,嘴角噙了一杆长烟锅,深深地吸一口后,又若有所思地徐徐吐出来。雨洗后的清晨很干净,烟青得纯粹,一缕一缕慢条斯理地吟哦着只有村庄能懂的言辞。
一锅烟毕,被露珠洗过的父亲用清亮的嗓子吆喝着我们赶紧铡草。铡刀起落间,草断了,草喂养了的人和牛却将一颗一颗的露珠串联成了一条汩汩的河,永远脆生生地流着。
一声蝉鸣起,我从回忆中醒来:蝉鸣竟如此清脆,它一定也被露珠洗过,拣着秋伏这个最后的时节奋力一鸣,是不是想暗示什么?
更深的沉思袭来:
母亲也是一颗小露珠,一生从未走出过她的小院,总想着把她的小院也滋润得青青翠翠。
大个子的母亲走起路来自带风声,只可惜大半生被病痛折磨,她的腰没直过,可我总觉得她的心里一直长着一棵钻天杨,再大的风雪里都没弯过。其实,加上老宅院子里母亲亲手栽的两棵,共有三棵钻天杨,一直把我们成长的目光捋得直直的。
父亲一辈,亲兄弟、堂兄弟算在一起共计六个,起初都生活在一个大地坑院里。分家另起炉灶后,一个院里也住了四家,只要一生火,四家的炊烟都交织在一起,锅碗瓢盆的磕碰声都交织在一起,吆喝鸡狗的声音都交织在一起,一条长洞子里,大人小孩的脚印也叠在了一起,但嫌隙也少不了。特别是妯娌间常常说着家长里短时忘不了夹枪带棒,一个大院里就酿着一场风。每每这个时候,母亲是最沉默的。一个心里种着一颗露珠的人怎能轻易惧怕一场酸雨呢?管好自己的嘴和脚,天地依旧敞亮,没读过书的母亲说出了像草木一样青翠的话。我们这些兄弟姐妹间难免不受大人影响,拌嘴打架的事情常常发生,致使一个院子里火药味很浓。父亲性子耿直,轻则一顿训斥,重则就是一顿鞭打。这时候,母亲眼里噙着泪珠,只是轻轻地说一句该长长记性了。到了暗夜,在朦胧的油灯下,我看到她的肩膀在抽动,被压抑的哽咽声清晰得像一枚钉子钉在夜里。母亲喜欢露珠,常常说,你看露珠不管落在树叶上、庄稼上、花瓣上,还是一根草叶的叶尖上,它一直都是亮晶晶的,它们生活得自在着呢。
我常常想:不识字、活得像一株草的母亲,怎么就成了一个乡村哲学家?
鸟儿吐翠
能否想象一下:
暮色的尾巴还残留在天边,地上一切事物都在沉睡中,寂静覆盖了整个黎明。此刻,在向日葵硕大的花盘上悬了一夜的一滴露珠顺着排列有序的葵花籽的纹理流过,再沿着黄色花瓣的经脉流到尖上,又是一个高悬,然后突然自由落体,撞击在一个玻璃一样的湖面上……
想象即使长了翅膀也无法超越现实!
忙碌惯了的土地从不给自己留下闲暇,雨水充沛的时候,它会想方设法唤醒一些陈年旧种,允许它们顶破自己的肌肤,把一抹一抹绿色擎举起来,然后隐身幕后静听拔节的声音,就如那些劳碌惯了的庄稼汉一样抓住时节,赶紧播种。等绿色漫开来时,他们蹲下身,背贴门墩,装一锅旱烟深深地咂着一口又一口,再慢慢地吐出来,在烟雾的诱惑里听门前菜蔬开花的声音……
供养了绿色、供养了人的土地时时营造出胜境:雨洗了夜晚,绿色向高空、四周逶迤,青翠潜入梦中,村庄长睡不醒。突然,一声绿色的鸟鸣如乍现的皓月,把天地亮了一个浑圆,一块沉睡的绿翡翠就碎了。一个旷野被一只鸟儿叫醒了,如一滴露珠叫醒了一座湖。
燕子冬去春来,它们恋旧又忘旧,只要去年的巢穴在,就修修补补,依然与旧友为邻。若是巢穴没了,它们似乎并不记仇,要么在旧址继续筑新巢,要么重新选址再筑新巢。其实燕子的巢穴都是我们这些孩子因为好奇,想探个究竟而破坏的。特别是看到一窠筑在高高树巅的巢时就非常羡慕,燕子竟然住在离白云最近的地方,它们会不会衔住白云的裙角呢?大人们常说高处不胜寒,难道燕子不知道?每年春天,看着燕子忙碌地衔来草叶、树枝、泥巴这些人类最嗤之以鼻的东西筑巢,就想,巢穴能坚固吗?
那些年,村里的人多数住在窑洞里。这些窑洞基本上都是背靠几十米高的山或崖掘出来的。掘一孔窑不容易,短则一月,长则几个月。要是想掘出一个有三五孔窑洞的院子,那就得三年五载。听父亲说,我们家的那座地坑四合院是两代人花费了六年时间才掘成的。与燕子三五天用一具小小的尖喙筑一窠巢穴相比,人是不是很笨?进入夏季,见云就是雨,有些雨还带着铲子,经常把窑面上的土块铲下来。若逢到这样的天气,大人一晚上都睁大眼睛看水是不是漫到了门槛,支棱起耳朵听雨是不是把窑壁冲塌了,我们则担心的是树杈上的那一窠鸟巢是不是被风刮跑了、吹散了。大清早雨停了,就胡乱地穿上衣服跑上了塬畔,疾步走到树下,仰头望向树梢,结果发现鸟巢像生了根一样依然稳稳地嵌在树杈上,回头时才发现邻家的箍窑被雨水冲塌了。
人还不如一只鸟儿呢,我们这些孩子嘀咕着。这嘀咕声又无意中被风听见了,便传到了村庄的角角落落。上了中学后,在第一堂历史课上老师说人类最早就是住在树上的。后来,人类渐渐强大,再不惧怕周遭的野兽,就从树上下来尝试着在陆地上掘穴而住。哦——原来鸟儿也是人类的师傅。看着坍塌的箍窑,我觉得人类可能是太急了,等不了鸟儿把衔在舌尖上最后秘密吐出来。
哪个孩子还没有一个宏大的愿望呢,看着鸟儿逐着东南风跑,孩子们便逐着鸟跑,嘴里还不时地“咕咕”着。据说,这种鸟是望帝杜宇死后的化身。杜宇贵为皇帝,开明治国,当他看到丞相灵极力治水,使百姓安居乐业,便主动让位给他。不久后,杜宇去世,化作杜鹃,日夜鸣叫,催春将福。做鸟状飞奔的孩子是不管这些的,他们只知道他们乐了,炕头的父母都是乐的,周围的空气都是甜的。风是最妙的推手,把天地间两个尤物的声音以水波的形状向四周推开来。这声音落座绿色的梢头时,旷野愈加舒坦。
“咕咕咕——咕咕咕——”从一个树梢飞到另一个树梢,这信使乐此不疲,把黎明送到每一户人家。很快,一个村庄的大门都开了,把绿色迎进来,又让绿色化为烟,从烟囱口散出去。日子反反复复,青烟不急不躁,循着一条专属的路在沉默中护佑着专属的繁华。
麻雀是个痴者。季节有轮回,草木有荣枯,天气有阴晴,麻雀却从未离开过北方。旷野、村舍、田间,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它们会及时地补进来。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它们和人都居住在村庄里。人在屋檐下唠嗑,麻雀三五一堆,站在枝头慕着人样话见闻。人起身,它们便散开。挡风的事,人经常干,风掉头时,也出卖了人。麻雀的耳朵只有米粒大,但特别会听风。风中有异常,绝对逃不过麻雀的耳朵。这不,一场热烈而专注的讨论才刚刚开始,叽叽喳喳的声音黏满枝头,如一树挤挤挨挨开得正活泼的碎花,突然间集体哑默,头齐刷刷地向着同一个方向,眼睛骨碌骨碌地转动着,翅膀紧裹身体,时刻做着起飞的准备。原来风把一只贴着蒿草潜入的狗的行踪暴露了。
单飞,或者三五结伴而飞,抑或成百只集中群飞,荒凉的天空都是一幅水墨画,空白留得恰到好处,特别是身形与声音飘过的地方总会留下一串遐想。
向崖畔或者山里走,新奇的鸣叫会一腔接着一腔。一个八度不够,就用两个八度;一个节律单调,就用两个节律;休止也用得不合常理。
这撒落旷野、山间的鸟鸣亦如这星星点点、簇簇团团、片片层层的绿色一样存在得自如率性。其实,鸟鸣也在开花,给天空播种思想。这天地本来就是连襟啊。
睡在旷野,被绿色托着,从不用担心天地会塌陷。吃着绿色的人,反过来被绿色所吃,就如土养人,也吃人一样。旷野的宁静被这种平衡永远维持着。
跑累的孩子坐在高高的墙垛上望天上的云,数地上的绿。他们的手指点一处,一处的云便白了十分,一处的绿便深了十分。他们也数鸟鸣,有时更会捡拾鸟鸣。聚起来时,和绿一样,都是脆生生的。
如今,村庄仅仅是老人和鸟儿的天堂。
土地和炊烟终年忙碌着
有炊烟的地方就有人家。人家屋顶上升起一绺儿炊烟,每一个日子都是活的。有炊烟的地方,土地就不会闲着。土地上长草木,长庄稼,长人,更长炊烟。
土地和炊烟是兄弟,打坏了骨头,也连着筋。
母亲在的日子,我家的炊烟从未断过。草儿们在的日子,风柳村的炊烟像草木一样向天上长,长成了炊烟的丛林。
日子潮湿,村庄潮湿,母亲和村里叫草儿的妇女更潮湿。炊烟涌满窑洞,只听得母亲连续的咳嗽从浓浓的烟中挤出来,散漫整个院子。一个院子连着一个院子,都是咳嗽声。一个潮湿的大清早,咳嗽声就在风柳村的土地上冒尖。
麦子一天一天搭了色,布谷鸟不停地在空中扔下“算黄算收、算黄算收”,父亲和村里的壮年男人都去陕西割麦子了,天却漏了底,一场连阴雨铺天盖地而来。
灶膛里没了干燥的柴火,沤出来的尽是烟,外面的湿气又拥堵门窗,炊烟全被锁在窑洞里,母亲就在烟中艰难地做着早饭。只有当一股风旋得树叶啪啪响时,烟才扯一扯身子,从门里、窗户里散出来,再飘到窑脑上。饭做熟了,母亲却涕泗横流,沾满了灰的脸上沟壑交错。
好不容易挨到中午,天亮了些许,雨声由淅淅沥沥变成了滴滴答答。母亲上了窑脑,站在窑脑的高台上看了又看,目光随着搭了色的麦子滑向了无边的田野。风柳村那些叫草儿的妇女和母亲一样都在眺望。眺望后她们祈愿天赶快放晴,她们的男人就能赶几个好场,挣足玉米地里追肥的钱,还有一家人一年的口粮就靠这几亩麦子,千万别让雨淋出了芽。
找出木杈、木锨,掸掸上面的灰尘;取下挂在墙上的牛辔头,把被虫子噬掉的地方修一修;趁雨停了,拿起锄头刮一刮窑脑,等大水退去后,牛套了碌碡赶紧整饬整饬碾麦场。
母亲眼里藏满了忧郁,但却有条不紊地把日子向前推着。父亲有一辆加重飞鸽牌自行车,割麦走时就骑着它,铃子声在胡同里留下了一串串省略号。其实,每年这个时候,铃子声都会从村庄的四处升起来,然后聚集在大路上,像一条河流一样流向关中腹地。风柳村里,母亲和那些叫草儿的妇女既做着女人又做着男人。男人们走得再远,她们都不做撂荒土地的事。土地是家的根,一缕一缕的炊烟是这根上长出的最旺的庄稼,母亲和草儿们怎么会不知道呢?
但撂荒土地的事,都是人干的,风柳村里有好几块地就荒了一年又一年,土地就借风、借雨、借鸟儿、借人的脚步把籽种带过来,然后自己打理,除过秕子、坏死的种子,争取都让每一颗种子发芽。就这样,一步一步向远处长,长出一坨一坨的绿,漫出一片一片的滩,以遮蔽内里的惶恐。这时候,种子是无需挑拣的。庄稼是命,草是命,树是命,苔藓也是命,挑三拣四没理由,所以一片撂荒的土地里什么都有。低、中、高,三个维度三种境界,彼此相依,又互不干扰。草木界从未生过互殴事件。
时间长了,土地能掂量清谁对它好。好了,土地也知道知恩图报。
公路一头向西扎进去,引得车辆也匆忙地扎着,道路两旁的房屋习惯了迎来送往,都淡然地卧着。房前屋后方方正正的土地上末一茬辣子花素朴地开着,呼啸的车流声并没有叨扰它们做梦。茄子硕大的果实在叶子间闪烁。萝卜拨开地皮,四片叶子向四下撑开。柿子树上,肥厚的叶子将青色的果实遮住,不肯示于人。金秋还早,结局尚无定论干啥要那么着急呢。该急的时候,绝不拖延;该缓的时候,绝不毛躁,土地掌握着火候,节气掌握着火候。玉米尺八高,十天半月不见长高一二寸,但一场雨后,就噌噌地向天上蹿。蝉声有多热烈,拔节的声音就有多热烈。
“谁撂荒土地一日,我就撂荒他的肚子一月!”父亲和四叔不止一次声情并茂地翻版着爷爷的原话。父亲今年八秩又四,生活已无法自理,但含糊不清的语言里时常会夹杂着“地……地荒了”。四叔生在土里,长在土里,土把他扛了一辈子,他也把土扛了一辈子。土懂他,他懂土,八秩高龄至今还是打理土地的一把好手。我家门前的两块土地被他打理得生机勃勃。屋后一块被我撂荒了一年,他心疼,向我要走了。经一个月的整理,杂草丛生的荒地长出了疏密有致的紫苏。他还在埂畔点了葫芦,屈曲的藤蔓上如今开满了黄色的圆筒状的花,有几个花蒂上已坐住了拳头般大小的青色葫芦。
土地拣人,像四叔这样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人,土地就和他们亲。邻家大哥墩而胖,说话瓮声瓮气,但手脚与心思绝不毛糙,房子东边的一方土地种满了各种蔬菜。土地挑时,蔬菜更挑时,拿捏好了时分,黄土四季就不会亏人。胖大哥是春菠败了,换秋菠,早萝卜败了,换晚萝卜,白菜一直能吃到立冬。特别是一场冬雪后,白菜才翠得馋人。人不闲,土地也不闲,日子才不会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哲学。
村庄里,高过土地的是庄稼,高过庄稼的是房屋,高过房屋的是烟囱,高过烟囱的除了天空,就是炊烟。一缕一缕炊烟提着房屋的脊梁向高处长。站在云巅向下看,炊烟如绳索,牢牢地系在房子上,一副生怕房子跑掉的样子。小时候,迷路了,就向着炊烟升起的地方跑。边跑边嗅,嗅出熟悉的味道时,母亲已在村口呼唤了。细心点的,常将自家的炊烟和别人家的比,一比就比出了玄妙,自家炊烟的不同之处就在心里生了根。日后,走得再远,也不会迷路。
村庄的高台上有村庄的全貌,有家家户户炊烟的样子,有远方,有天空的云助生的想象。我们这些孩子常去,高台便被磨得明光明光。久而久之,闭了眼,我们都知道谁家在哪儿。风把炊烟捎来时,闭着眼睛一嗅,就知道那是谁家的。一年四季,一有空就回来。来一回,百十个烟囱杵着,百十个烟囱口冒着百十炷炊烟。烟囱一年四季从未停止过呼吸。旷野之上,风从四面八方吹来,但炊烟和屋舍一直不离不弃。
燕子恋旧,秋去春回时,闭了眼都能飞到昔日的檐下。它是循着一种久别的味道来的。这味道就是主人家炊烟的味道。绕着主人家的屋顶不知飞了多少回,主人家炊烟的样子也是烂熟于心。即使身处千里之外,它都能听到熟悉的召唤,但我们总觉得炊烟没心没肺,一年四季就一个样儿。这么专注,是想镂刻什么,还是想播种什么,猜测的时候,一缕缕炊烟就在心里生了根。
母亲在世时,爱做疙瘩面。她好这一口,到了我们,也好上了这一口。一到春季,四处掐一把嫩苜蓿芽,做一锅疙瘩,剥两根鲜葱,炒好葱花炒汤,刚拿起电话时,我们已到了门口。“你们鼻子真尖!”母亲笑着说。“是您做的疙瘩面十里飘香——”我们嘻嘻着回应一句,便端起了碗狼吞虎咽起来。如今,熟悉的味道还在,但劲道的疙瘩面已不再等候我们。
飞快的车轮卷起的风越来越烈,村庄里的烟囱曾寂寞了一段时间。寂寞的那段时间里,旷野上都少了燕子和麻雀,但夏收、秋收季节,布谷鸟依然叫得执着。如今,村里的小路上,孩子的欢笑声渐渐多了起来,禽雀们也逐着笑声飞过来。一到黄昏,雀鸣,孩子跑,大人吆喝,好生热闹。烟囱越来越忙碌,吐出的炊烟也在村庄上空欢快地舞蹈者。
确实,有炊烟的地方才有村庄,炊烟是村庄的碑,也该给母亲的坟头立座碑了,到时我一定要写全母亲的名字。
人气定是绿色的
风闲散,村庄闲散,村庄里的树木、房子、鸟雀也闲散。村庄仄歪在大地的臂弯里,三五处房子仄歪在村庄的一隅,树木扎堆也罢,独生也罢,总黏在房子旁侧。鸟巢骑在树杈上,一骑就把时间骑老了。
小店就在村子的入口处,茅屋变成瓦房,瓦房变成平房。没变的是对面水井的水甘甜了几十年,现在依然甘甜,没变的是刘四叔的笑,嘴角微微一翘,眼角蹙起几道壑。几十年来,水井里的水从壑里流出,绕过小店的墙角,流进了村庄的肌理。
农闲、暖冬,三五人从村庄的肋间走出来,向小店门口的柿子树下移动。树上有柿子没柿子、柿子绿着红着,那是柿子树的事情,那是季节的事情,下棋的人只愿意被树的影子牵着走过黄昏。村口,刘四叔在、小店在、棋盘在,村口就永远亮着一盏灯。
柿子树绿了,枯了,人从未间断过。
青柿子露头,红柿子点亮灯笼,棋盘上的厮杀从未间断过。
啪啪声起,啪啪声落,输赢间哈哈的笑声从未间断过。
公路上,车来车往,车轮裹起的风只在柏油路上来回跑。拇指粗、手腕粗、臂膊粗,柿子树愈站愈稳。阳光透过树叶,跳跃的光斑舞蹈在地上,舞蹈在棋盘上,舞蹈在下棋人的背上,但总有那么几斑斜觑着陷入沉思状。商店门口的黄昏从未褪过色。
过了公路,向南眺望:旷野里,庄稼摆弄画笔,尽管一年四季五彩纷呈,但底色总是绿的。春,绿冒出尖,先把大地绿了。夏,绿从田野涌过来,把村庄染绿。秋,绿被敛进果实。冬,天地昏黄,果实把绿吐出来,染着肚皮,染着村庄。
这么久了,人不绿吗?
“入底炮、入底炮,再动车!”李大夫边说边弯腰伸手把炮由炮位上直接推到了黑方右边的马位上,没等到对方动子,他又拿起河沿8位上的车准备平移到4位。
这时,树把风没囚住,一股跑出来,扰得树叶不安稳了,你推我挤里,一阵笑声四起。
老倔头王根脖子一伸,红着脸训道:“哎呀,你手怎么那么长,别动我的棋子!”说着就从李大夫手中夺回了棋子。这时,脖子上的血管暴起来,似一条蚯蚓在蠕动。
斜觑久了的光斑这时也展了展腰,老倔头王根的额上就有了晃动,夺回棋子的他笑了笑。
刘工刘清不紧不慢地说道:“那有个啥棋嘛,我倒一个相,啥问题都没有了!”说着就缓缓地收相起相。阳光穿过柿子树的叶子,一个光斑正好落在他的右太阳穴上。
坐在刘工右边的张强郑重地提醒道:“小心槽马,两步就可以到位,车应8进4,提上来放到自己河沿上!”边说边用没有手掌的手腕去拨动棋子。
司机白师白军提着一杯茶边左顾右盼边从马路对面向商店门口走过来。人未到,就已经戏谑李大夫了。“你呀,看棋一直看个半步棋,偶尔赢一半次,还卖派自己棋艺高,你让开,我给你教两盘!”
刘总管刘杰一直站在众人身后沉默不语,仔细观看着整个棋局的动向,偶尔瞅向李大夫,嘴角微微一咧,露出不易察觉的微笑。
近八十岁的刘四叔坐在马扎上偶尔看看马路上的行人,偶尔看看棋摊,偶尔和熟人打一声招呼。坐久了,便起身凑向棋摊,指点几语,还不忘折进自家小店给站着的人拿板凳。
柿子树把黄昏拉长,又把黄昏聚成团儿,黄昏的脚步被柿子树寸着,走得很快,也很慢。它的影子由墙壁移到了地上,由远处移到近处,颜色也由浓变淡。每一点变化都精准地镂刻出时光的位移。下棋的人几盘棋下下来,月亮已上了柳梢头。只听得噼里啪啦归拢棋子的声音、收拾板凳的声音、起身的吭哧声夹杂在一起。不久,嘻嘻哈哈里相互拍拍肩膀一哄而散——这里是男人们的世界,他们的身后还有另一片世界,正被母亲和那些叫草儿的妇女守候着、耕耘者。该升火烧炕了,一缕一缕炊烟从一个一个院子里升起来,沿着村庄的道路弥散开来。青烟笼着的村庄里,一棵一棵的草俯身背着大地在走。
旷野暗了下来,柿子树愈加静穆。玉米地里,虫鸣声升起来。短吟轻唱里,墨绿色循着节奏氤氲开来。不久,绿色便稳稳地坐上了村庄这个大棋盘。
此刻,万物归位,一切刚好。
夜拔节了。这拔节的声音只有绿色听得懂,它涌过来,把倾斜的心房慢慢扶起、喂养、矫正。钟摆的铮铮声重新响起。铮铮声里,虫鸣顺着时光生长,一个人顺着时光归位。
一场新的倾斜又悄悄生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