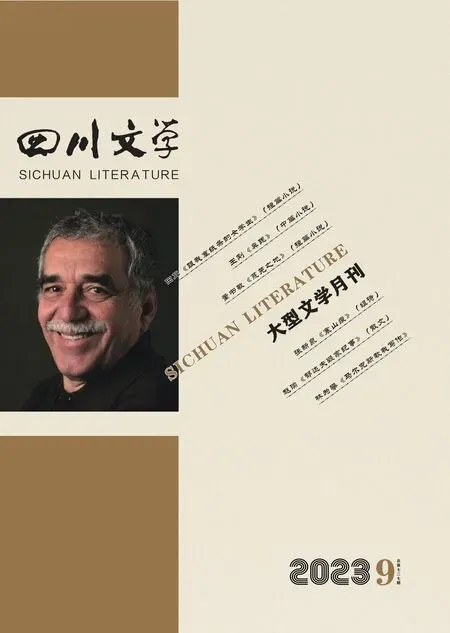悲伤的桥
□文/葛小明
1
周京夫掉下去的时候,酒一直没醒,直到第二天被同村人发现,他竟然还在水边大睡。他没有看到河蟹趁着夜色爬到岸边,为了一口吃食反反复复地疲于奔命。也没有看到那些大如黄豆的沙子在水中努力地划下印记,只为做临行时最后的匆匆一瞥。他只记得那晚头很沉,身体轻飘,左脚与右脚时常交错,可能像一条蛇,也可能只是在深夜里摇摇晃晃的一道黑影,浑浑噩噩漫无目的。酒不足以让其醉意过重,他自信可以穿越那座山和那条河,轻松走回去。可他还是掉了下去,从一条走了52年的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年迈的桥上。
知天命之年,他注定无法迈过那座桥了。这不仅仅是一堆河边的认真堆砌的石头,也不是沙子和水泥的简单混合物,这是他生命中最坚硬又最脆弱的地方。他的长子,也是唯一的儿子,在遥远的宁夏的柏油路上粉身碎骨了。他在县城一直到天黑才回家,随意买了瓶酒,边走边喝,不需要任何下酒菜陪衬,这满腹的悲伤足以果腹。52岁,他知天命、知离别、知生死,却无法知道自己面对巨大的悲伤时,是多么怯懦与无力。
是夜天极黑,乡间小路上并没有一盏灯为伤心人亮起。他穿越熟悉的谷子地,花生地,杨树林,穿越无数个弯弯曲曲的拐角和此起彼伏的虫鸣与风声,总算来到了那座桥。他知道过了这座桥就是周家庄村了,儿子和他出生长大的地方。想到这里,他心里稍得安慰。没想到的是,儿子没有死在周家庄村的某个胡同,没有死在鲁东南大地上的某张软沓沓的床上,而是死在了一条遥远的不知道名字的高速路上。
他放慢了脚步,喝光了最后的一口酒,一阵火辣辣的悲伤涌了上来。不知道该怎么跟家中的妻子解释,他甚至编造不出一个让自己也能够信服的理由。他站在细细的流水之上,拱形的桥把身下的空间无限放大,马蛉和纺织娘在肆意叫嚣,似在宣告领地,又好像在唱这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夜色从他身下四散而去,有一些暗淡的星光通过水面袭来,这是一种凛冽的清醒。这光在告诉他,事实就是,你的儿子死了,永远地死了!打了一个冷战后,酒意退了一些,他用手扶了扶北侧的栏杆,确切地说是一堆风化严重的砂石矮墙,摇晃的身躯勉强立住了。
他再一次认真抚摸了这座桥,他坚信可以从这亲密的接触中获得一些慰藉和温暖。多年来,坚硬的石头和沙子固守在桥面上,始终没被风雨和悲伤冲刷掉,它们与身下的流水保持了友好又相对克制的距离。白天的时候,这座桥上走过最多的不是小汽车和人流,是牛羊,是锄头和四齿耙,是拉满庄稼与肥料的三轮车,是一代又一代乡下人的殷勤与素面朝天的梦想。他们渴望地里的花生个个硕大饱满,吃草的牛羊肚子圆圆滚滚,红薯满满地铺在地里露出紫红色的脸,玉米高粱和谷子都没有遭受病虫害的欺凌。他们渴望的季节是沉甸甸的、满载而归的。他们渴望放学的孩子路过这座桥时脸上洋溢着满分的笑容,也渴望家中的老二已经在锅炉前做好了晚饭,就算跟昨天一样马马虎虎也无妨,毕竟那是一个初次掌勺的人,需要更多的肯定和鼓励。
不同的人走在这座桥上,情绪是各有不同的。出门下地的人,盘算着昨天还有一半的杂草没有锄完,今天得加把劲才能在天黑前赶完进度。傍晚回家的人,总结着玉米地里发生的一切,包括新发现的螟虫和纹枯病,地堑上滚落的几块石头要尽快补全,过几天再来拔一波杂草就等秋天收割了。晨光或者夜色,毫无偏爱,总能在既定的时刻准确降临,它们不会在意你头顶上闪烁的是悲伤还是欢愉。
步行去邻村上学的孩子,要走上9里路、翻两座山、过三座桥。他们不喜欢用时间来计算剩下的路程,不只是因为没有手表,而是这一路有太多有意思的事情。会采一把路边的胡枝子或者泽漆,拿到学校分一分新鲜的野花。也会在回来的途中捉几只蚂蚱,喂养上次捡回的小山雀。甚至不畏惧路边突然露出身子的蛇和牛羊刚刚遗留下来的粪便,这一路总有日新月异的惊喜。上学的人,喜欢桥,每走过一座,就意味着离目的地近了很多。雨水多的时候,他们喜欢站在桥上看水,隔夜烦心事随着水声奔袭而过,那些倒影在此起彼伏的水花里,慢慢长大成人了。
口渴的人,会去寻找那座桥。这座离山最近的石桥,几乎第一时间接纳了山上下来的水。在桥紧邻的南侧,有一处明显的泉眼,水干净略有甜味。下地的人没有带水的习惯,渴了就去附近找水。在山里,往往不只一处泉眼,而桥附近这处,最易取水,并且可以在饮完后到桥下小憩。赶上三伏天,他们也会坐在桥底下乘凉。这时候,人们开始换一个角度审视这座桥,或者说那是一道拱形的门。
有些蜘蛛约定好领地后,在不同的位置筑起了巢穴,一张纤细轻巧的网和一个早已预设的陷阱,就此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它们把丝线有规律地拉扯、组合、粘连、交织,等一切都已织就,便可以惬意地坐享其成了。盛夏的时候,来桥上乘凉的不只是那些身高马大的人类,还有各种各样的蚊虫,它们试图贴近桥壁的时候,就是蜘蛛美餐之时。即使有风吹过,也不能将猎物救走,蜘蛛甚至可以在一场动荡的风中,体验摇摇晃晃的进餐新鲜。蜘蛛有自己的生存哲学,它们的网不大不小,正好够自己吃食,它们绝不侵占同类的领地,也不过分铺张。它们知道,网过大,会有被其他物种破坏的风险,如果碰到乘凉者的头发,甚至会遭受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对于个头较大的群体,它们往往也会放过,除非很久没有捕获到猎物了。比如蜻蜓和螳螂,虽然竭尽全力也有可能吃进肚里,但是这里面有太多不可预测的风险。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打破既有的默契和法则。
桥下的人,偶尔会谈及蜘蛛,说它们会挑地方,冬暖夏凉的。在多数人眼中,蜘蛛是和自己一样的,它们要经常缝补破损的网,要与各种虫子搏杀,为了生活,其实蛮辛苦的。桥下的人,也会讨论一下水中的红蓼,说它有多种吃法,可以焯水后凉拌,也可以放点红辣椒炒,味道鲜嫩爽滑。桥下的人,讨论最多的是地里的庄稼和家里的儿女婆娘。庄稼在土里长得肥壮与儿女在外赚了大钱,获得的成就感几乎是一样的,并且每天重复都乐此不疲。某种意义上,他们仰望那座桥,就像仰望自己的未来,看似很近,其实又那么遥不可及。他们把汗水留在地里,努力地过着一座又一座桥,总想着能够在某个秋天可以获得一场前所未有的收成。水声不停,汩汩而过,水边闲聊的人却在这种流逝中慢慢老掉了。
天空在一次次眺望中被无限拉高,这种人为建立起来的疏离感,只有靠人才能破坏掉。比如心情大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头顶的云格外柔软,像羊群,像山水画,像棉花糖,像少女毛茸茸的心事,无论哪种,都离自己很近。当你深陷焦虑之时,又会觉得天空压抑,白云变成没有晒干的棉花团,湿漉漉的,让人喘不过气来。人们很少仰望一座桥,就像很少跳出固定的圈子,反思一下自己。桥是障碍——要越过去,是凭借物——心存感激,是理想——遥不可及,是自己——难以自知。
周京夫生活中最坚硬的部分,留在了桥上。每次外出或者走进村子,他会用力挺一挺自己的胸膛,两肩的曲线格外流畅,他的目光要比等身高的人高出几许。他并不盛气凌人,但是在这个百十户的村子里,有两个自认为混得不错的孩子,还是很有存在感的。在地头上,抽旱烟袋的时候,两家地块相邻的人会不由自主地凑在一起,闲聊家常。聊到孩子,他的大儿子总能让他两眼生光,仿佛一天的疲惫都能在一个远在他乡的名字里获得宽慰,抽烟的时候也会拉长那段入肺的距离,回味好几秒钟。一袋烟罢,他朝鞋底敲打了几下烟袋锅子,总能在最后离开的瞬间获得满满的成就感。他没注意到,邻地的周京云,投来一段羡慕的目光和一声轻而浅薄的叹息。
2
那些石头与沙子,因为某种机缘巧合组合在一起,或许这种关系也只是临时的,几百年后,它们会重新分离,各奔前程。有一点可以肯定,接下来的若干年要是不遭遇什么大灾大难,它们是一定要风雨同舟、休戚与共的。它们将一起见证发生在桥上的所有事情,生、老、病、死,求不得,怨憎会,爱别离,五阴盛。
空着出去、满着回来的羊群,吃遍了对面山坡上的青草。它们熟知每一块石头的存放位置,能准确地辨认什么是一年蓬,什么是小飞蓬,辨认延胡索与小药八旦子,辨认桔梗与丹参,辨认老鸦瓣与半夏,辨认洋槐与柞树,辨认砂岩和砾岩,辨认花岗石和大理石,辨认西北的风和春天的雨,辨认有毒的红菇和可食用的牛肝菌,也能辨认主人飞来的石头是在引导还是在吓止。哪棵树更加适合挠痒,哪道山梁子风最小,它们清楚得很。晨光掠过,当第一次走在桥上,它们便知道这是充满了自由与冒险的一天,这一路将收获无数美食与风景。当第二次走在桥上,它们开始沮丧,虽然已经果腹甚至有不少意外收获,但是这意味着马上要回到圈中了,那个自己都不愿意闻自己气味的地方。围墙是一根根洋槐树枝插起的栅栏,无论怎么啃食,都无法完成越狱。就算偶尔可以溜出来,仍旧有一道厚实的砖墙,牢牢地锁定了夜里的光阴。
牛走在桥上,步伐坚实而缓慢,像是在走秀,又像是在咀嚼一个时代里最苦涩的部分。只见它四脚有力,一步一个脚印,不慌不忙地通过一座桥。那漫长的一分钟,是完完整整属于它的,谁也无法共享。它有时候会甩一甩蹄子,就像甩尾巴那样流畅自然。不同的是,甩尾巴是用来驱蝇,甩蹄子纯粹是为了感悟时代,它能在每一次抖动中清晰地感受到年月的美好,感受到免遭猪羊一样的贩卖与屠戮,感受到慢是一种哲学,感受到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牛的生存哲学要比羊深刻得多,因为它是在无数孤独中建立起来的,牛的哲学不直面死亡,但是这更能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无一例外,牛羊的哲学都不可回避“桥”这一重要元素。在鲁东南一带的丘陵地区,牛仍旧像几千年前一样,是最重要的耕耘者,人们尊重它、敬畏它,言听计从于它。当它走过一座桥,后面的人一点也不会紧张,他甚至觉得前面是一位先知在引领路径,怎么走都不会有后顾之忧。
三轮车走在桥上,雷厉风行,隆隆而过。它毫不顾及四面地里的人,也不顾及这座古稀之年的桥的感受,轮子只管滚动,马达只管叫嚣,黑烟筒只管对这个世界宣泄着不满。载人,载庄稼,载收成,载生离死别,都没什么两样,无非是走过一条又一条马路,无非是一座又一座桥。
周京夫并不会开三轮车,但他家里闲置了一辆,只开了五天便不再碰。事情的经过很简单,一辈子没碰过车的他,拗不过儿子的央求,半年前从邻村的农机贩子手里买回了一辆。在本村老葛的“指点”下,练了三四天后他就能独自上路了。路过那座桥的时候,他会使劲加大马力,让庄稼地里的左邻右舍看一下,无非是寒暄几句“买上新车了啊”“儿子真孝顺,还给你买车”“没想到你学得这么快,贼溜啊”。不幸的是,第五天的时候,他就把车开到了桥边坡下的玉米地里,胳膊肘都骨折了,车也摔得不成样子。从此以后,他便心有余悸,再不敢碰那三轮,任它锈了、损了、坏了、烂了。
他没想到的是,自己这次会比三轮车摔得还要惨,除了脸上擦去一层大小不一的皮,右小腿也骨折了,两脚扎进去好几块碎石片。更要命的是,就算他痊愈了,能正常走路了,脸上不再有疤痕,他那可怜的儿子也不可能再出现在面前。他再也无法在地头上和周京云炫耀庄稼和子女,不能自信地在鞋底磕一磕烟袋锅子上的灰。回想那个晚上,他完全不记得跌落的惊恐和断骨的疼痛,只记得手触摸到桥身的粗糙与冰冷,是一种人近迟暮的无可奈何。
周京夫不知道,他正在经历的事就是此生最大的事情,过了这座桥、这道坎,这辈子再也没有更大的悲伤了。不幸的是,他没有顺利通过那座桥,醉醺醺地掉在了桥下,即使是第二天也是同村人搀扶着从河沿上回家的。后来的若干年,他要不停地烧纸,告别与铭记,皆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在一堆滚烫的热浪里,反复被唤醒。事实上,这座桥,他只通过了一半,剩下的一半,用了很多年都没有走完。
3
你是否会在某个无人应答的深夜,把自己毫无保留地呈现给一座桥?
你的心中是否有一座桥,始终都没有迈过去?
那晚的事,周京夫不发一言。没人知道他喝了多少酒,怎么掉下桥的。也没人知道他儿子埋在了哪里,对方赔偿了多少损失,没人敢问。几年,几十年后,人们仍旧会走过那座桥,仍旧会说起周京夫,说起那个过桥失败的伤心人。再后来,人们只记得有人因为丧子坠桥,不记得具体是谁了。最后,人们只记得这里有人曾经掉下去过,因为什么,名字是谁,皆不记得了。人们刻骨铭心的记忆,在时间的河流中越冲越淡,越来越远。痛苦终于彻底消失,不见了。桥对一切漠不关心,只管不断风化,过程痛苦而缓慢,但是它会被不同时间段的人铭记,刻在骨头里,深不见底。
一个多月后,出院的周京夫开始反复思量,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家里接二连三地出事。他想来想去,还是怨那座桥,一定是桥上有什么东西跟自己不对付。但是又没有什么办法把它拆掉,他只能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去桥头烧纸。事实上,他家离那座桥有一段距离,晚上走过去得七八分钟,这七八分钟的夜,是漫长的。他需要一个人,用篮子挎上一打纸,兜里揣上一个打火机,心无旁骛地去见那桥。纸有时候多些,有时候少些,多少都随心,他坚信只要能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在那个诸事不顺的桥头,冉冉升起一堆火,就能改变家里的时运。他深知,这并不是件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有一颗虔诚又持之以恒的心,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
纸在桥头上肆意地燃烧,那短暂的熊熊之火,把桥面和桥身一齐点亮。周围的世界隐匿起来,你能看到的是桥、是火、是光,是一个遭受了悲伤但却没有彻底死心的人。群山四伏的村落,天空时常不见月,那些暗淡的星光,不足以把世界点亮。那个人试图用生命最后的几十年,对抗一下这浓黑又死寂的夜色。
纸在燃烧,火在燃烧,知天命之年的人在燃烧。轻碎的纸灰跟着热浪徐徐上升,过程粗暴而毫无章节,它们或大或小,或轻或重,或悲伤或无聊,总能在火彻底凉下来之前逃遁,不知所踪。纸的燃烧过程极其短暂,几十张往往不用三分钟就能成为灰烬。但是烧纸的人,无限地放大了这个过程,在这有限的三分钟里,他想到了自己过去的五十多年,想到了儿子已终结的二十多年,想到了地里的庄稼、家里的婆娘,想到了遗留下来的小孙子和遥远得像夜空一样昏暗的未来。
桥下的水铺上了一层生锈的金光,那三分钟,水流是静止的。你看不到粼粼的波光和为了生活半夜出来打拼的河蟹,你看到的是一道细长的死气沉沉的水,人之所冀向上,人之悲伤向下。汩汩而动的水啊,你也会因为承载的悲伤过多而停滞不前吗?你是不是也能在游泳的星群里,获得某些短暂的欢愉和安慰?
周京夫不知道,纸灰并不能全部飞到天上,总有一些要被反复提起,这部分被印到了桥上,任雨水多次冲刷,仍旧无法磨灭。开始的时候,人们并没有完全接受,毕竟每日走过的桥上多了那么多黄黑色的斑点,很是不雅。直到有人发现烧纸的周京夫是在低声抽泣,年过半百的男人,在一个孤零零的桥上流泪,一定是有了难以迈过的坎儿。
他把一生最脆弱的东西,留在了桥上。这一生,风光过,沮丧过,他所经历的,那座桥都作了足够多的见证。走过桥的牛羊,老了。走过桥的人群,老了。走过桥的河流,一去不回,干脆而决绝。周京夫的悲伤和未了之事,永远地留在了桥上。他不知道,每只路过的牛羊,每个相识的老乡,都曾窃窃私语,咀嚼着这个人后半生的不幸。
2021年5月,周家庄村获得了一个土地增减挂钩项目,许多老房子拆了,重新变为耕地。整个过程粗暴而略显野蛮,曾经华丽的屋顶,瞬间跌落,扬起的尘土风刮了两天都没刮干净。这些地会长出千万斤粮食,也会长出一代又一代的周家庄村人。人们会忘记过去的悲伤,忘掉周京夫这个人和他的一辈子,用一副陌生的面孔出现在桥上,出现在时代的河流之上。同年6月,那座石桥顺势做了修整,光滑的栏杆立起来了,上面有镂空的荷花图纹,颇为好看。小孩子放学后,喜欢趴在栏杆上长时间向下观望,有时候是看鱼,有时候是看水,有时候什么也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