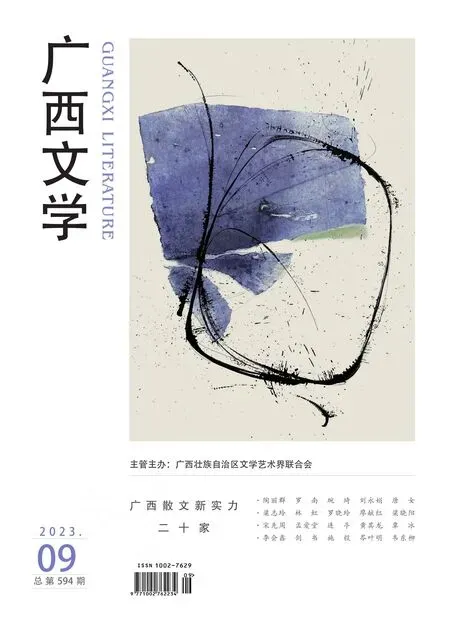越过取景框
施 毅
风景是什么?你觉得美的,能与你内心共鸣的就是风景。起码,我是这么认知的。
每次看风景的感觉不一样,瞬息万变的生活如是,人如是,动物如是。记性不大好,这使得我容易沉浸在变幻的事物中,如同孤身一人驾驶宇宙飞船行驶在无边的黑暗里,试图寻找一颗星球,寻找一个立足的点。这个点,是心的留痕。文字写下,是一张相片,是“一沙一世界”,也可以是阿基米德撬动地球的那个点。
一
由于喜欢用镜头去记录世界,几年前,抱着学习的态度,加入过一个大型纪录片的摄制组。
依旧是脚下熟悉的家乡土地,再次出发,却是从许多部精密、昂贵、高清的摄像机镜头中去“看”这片土地的风土人情、山川河流,“看”这个沉郁、欢乐、激荡的人间。
在广西十万大山余脉,一个叫发明村的地方。第一次来踩点时,大雾弥漫,车子开得很慢,踩刹车的频率甚至多于踩油门。
车子晃悠,前途未明,如同闯进一个又一个生活的谜团。
我坐在后座,紧张之余,打开车窗,探头四望。这才发现我们被无尽的白雾包围。前不见路,后不见山。在这种路上待久了,不免让人沉闷、心慌、迷乱。后来,我在隐约可闻的鸟鸣中安静下来,感知到自己的眼耳鼻舌,觉察到一颗有力的心脏在缓慢有力地跳动。
有时,反而需要在一种看似“困弊”的环境中,才能内观自己,发现生活细微处的美景。
慢慢地,我发现白雾在每段路各有不同,或稀薄,或浓稠,如筛子,像大米团,形态各异。如同山神抽尽漫天白云,躲藏在连绵起伏的山林里吞吐修行。
这些年,喜欢独处荒野,用手机拍下瞬息万变的自然景象。有时看天空、大地久了,诗意的水迹会从坚硬的“石缝”里渗透出来,于是,人心喜悦,雀跃在手机记录的文字中,我与“变幻”的事物发生关联,我融化在万物里。
在山上,久久凝望这些浓稠又稀薄的仙雾,我想抓住某种玄妙的诗意,但车在动,白雾也在飘,所以什么都获取不了。索性,我打开手机,不看参数,不论构图,探上车顶,狠拍了十几张照片,以期通过这些凌乱的相片,寻找彼时那种如云似雾的诗意。
但两月后,看着白雾茫茫的相片,却只蹦出一句:“大山深处,每棵树都有其隐秘的个性。”
因为大雾的缘故,小车开了两个钟才抵达村子。主人公很热情,一见面就用力握紧了我的手,掌心传来的磨砂感,让人感到一种粗粝的温暖。他用白话说,我们这“山角落”(偏僻)的地方,难得有记者来呀。我说我们不是记者,而是摄制组。他憨憨地笑,不说话。
他姓黄,五十多岁的年纪,常年以卖蜂蜜为生。村子附近的山头上,遍布着一百多个他用木头自制的蜂箱。蜂是满天飞舞的野蜂,蜂箱是人工制作的木头房子。这种独特的养蜂技术,颇有点筑巢引凤的感觉。
这里虽叫作发明村,但村落与“发明”二字根本毫无干系。
这里土地贫瘠、稀少,很多房屋难免建在半坡上。我们与黄哥爬上村子去看蜂箱时,有村民不时从后面张望,用奇异的目光盯着我们。在村尾,经过几个造型奇特的木头蜂箱。我们拿出摄像机,做前期记录拍摄。面对镜头时,黄哥却有些蔫了,他回望村巷,说话吞吞吐吐,似有些紧张。
这山村如此偏僻,人们对摄像机是好奇,还是害怕?
想起曾经看过的资料。
1844年,法国摄影师于勒·埃迪尔跟随法国外交贸易使团来到中国澳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后来,埃迪尔又到了广州,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成了中国第一个照相的地方官员。
资料中,没有找到耆英第一次照相时的心理活动描写。那时的古董相机曝光时间很长,拍一张人像,正儿八经坐好,还要等待三五分钟,伴随“咔嚓”一声,有时闪出打光的烟火,就导致有些人惊恐,失魂尖叫。于是,人们四处传说,照相会偷走人的魂魄。
后来,我才知道,村民和黄哥不是怕偷走魂魄,而是魂魄因为人心而慌乱。
以前也有新闻记者来过这“山角落”的村子报道,但发布在网上的图片用了其他村民的蜂箱,内容尽是渲染他的光荣事迹。这让村民很不爽,做人嫁衣,吃力不讨好。
妒忌之心如同烧蜂取蜜的火焰。记者报道后不久,山中似乎出现鬼怪,蜂箱被破坏,蜂蜜不时被盗取。
当他走出泥房时,几个影子就紧紧跟随。一个负责盯梢,只要他爬上这座山,另一座山上的蜂蜜就被盗取。隔壁家的小孩说,是山鬼拿走的,黄哥则说是鬼迷心窍的人偷走的。后来,咽不下这口气,常刷抖音、接触新鲜事物的他,在一些较为集中的蜂箱点装了几个摄像头……后来,偷蜂蜜的人少了,但与他打招呼的村民也变少了……
即使是最“山角落”的村子,人心这东西,还是一样的。
我时而在取景框里看着构图精准的主人公人像,耳边听他讲述辛酸往事。但长久关注取景框的音量值、曝光度、光圈数值,有那么片刻,如同听着另一个世界的故事。
佛说,有三千世界。取景框里的人和景,算是其中一个世界吗?
本着向山讨“吃”的方式,村民或多或少都会放置四五个蜂箱,引野蜂入巢,待一年后,才开箱取蜜。
有的蜂箱就在自家门口屋檐下,有的在大梧桐树底下,有的在悬崖边上,有的蜂箱在树洞里。作为本地最有名的养蜂大户,黄哥有一百多个蜂箱点分布在四周山头。
即便如此,一百多个蜂箱,能有百分之六十的“入住率”已是不错。野蜂也像人一样,对房子很挑剔。蜂箱的质量、舒适度,以及地理方位,还有通风情况,决定了它们是否入巢定居。
野蜂的挑剔有着动物的考究,人有时想挑剔,却无从选择。
黄哥笑说,我造了一百多套“房子”,但还没钱在市里买一套房子。
他统领过几百万只野蜂,但也有被野蜂蜇到休克,躺了一天才醒来的经历。据说,为了寻到好的蜂箱存放点,他也曾爬过一座险峻的山峰,不小心摔下半山,导致腰骨椎移位,瘫痪在床两个多月。在家里,他拿出一堆药盒子,用平静的口吻,讲述治疗各种病痛的经历。
不知是不是一种错觉,爬着陡峭的山坡,黄哥的身形却渐渐鲜活起来。他身手敏捷,在杂草丛生的树林中,如履平地,好似时光逆转,回到三十多岁的年纪。
在山坡的一个开阔地,他挺直身板,左手叉腰,指着周边山林的上百个蜂箱点,如数家珍般介绍起来,像地主老爷得意地介绍自己的大片良田。
人总在自己的长处里找到一个立足点,或者说,必须要找到一个立足点,你站稳了,才能看清前行的路。
时隔半个月,三十多人的摄制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这个偏僻的小山村。上山拍摄时,如同村集体开荒的感觉,大片的野草和藤蔓被踩踏、清理。地上本没有路,人走多了,路也就出来,而且是快速成型的那种,这也符合高速发展的时代特性之一——效率。即使在大山深处,也不例外。
以前,本地的山里有很多路。樵夫砍出的路,牛走的路,山羊踏过的路,猎人蹚过的路,采药人攀爬过的路。但,樵夫、牛、山羊、猎人、采药人都随着时间慢慢消失了。所以对于一群人跟着上山,黄哥表现出兴奋的状态。如同小时候,一帮野孩子跟着他上山玩耍的感觉。
我们的拍摄点位于距离山涧小溪五十多米高的悬崖上,一边是坚硬的石壁,一边是藤蔓野草。随着我们进入,口子在柔软的植被那边,被人为扩大半米,但脚下的泥石路,还是同样面积。我听着蜜蜂的嗡嗡声,慢慢扶着石壁前行,走了十多米才到蜂箱的所在地。
我时而警惕只从镜头中去探寻“美”的摄像工作者的安危,还要防止野蜂的蜇咬,又想多学点拍摄技巧。长久盯着取景框,看着黄哥忙碌取蜜的身影,又从取景框之外的环境里,感受这个危险而又有趣的悬崖峭壁。这种刺激感让我肾上腺素飙升,使人有一种迷幻的感觉。
黄哥戴着面纱,如同一头优雅的熊在细致地掏着蜂巢。摄影师则紧紧盯着取景框,不断变焦,移动镜头,试图用不可言说的艺术来记录这种从古至今还留存的劳动方式。本质上两个都是劳动者,但产品不同,一个是可食的蜜,一个是可视的“蜜”。
中午是野蜂最繁忙的时候。几千只野蜂,有如骤雨急下,密密麻麻地从眼前飞过,无数线影编织了一张令人窒息的网。我忽然想起钢琴曲《野蜂飞舞》,那飞快的旋律在脑海中,嵌入前方的蜂鸣,更加诡异,也更清脆动人。
从悬崖边出来,搬脚架的,扛灯具的,搬运摄影机的,提无人机的,拿剧本的,提蜜糖的,又忙碌起来。像是进行某种庄严神秘的仪式,上山时,摄制组如同扛着一副无形的棺材而来。而今,大家卸下重担,轻松下山。
踩点时,黄哥与爱人以及一个女儿还住在泥房子里。但不出两个月,我们再来补拍镜头时,黄哥却在一片残垣断壁的土堆上种起玉米、南瓜。
我记得,他站的位置,分明就是泥房的客厅。
因为属于易地搬迁户,除了拥有在他乡小镇的安置房,按规定,如果自行拆旧房还得一万多补贴。不出一个月,他毫不犹豫把泥房子给拆了。
我想起野蜂,想起黄哥在大山里的一百多套“房子”。善于造“房子”的人,终于住上了符合现代人居住的房子。
但崭新的楼房,周边没有合适的工作岗位,几番权衡下,他还是返回了大山包围的村子。村委在废弃的小学楼上,给了他两间房子来使用。
一间挂着养蜂合作社的牌子,一间,他用木板隔出两间小房住。
再去补拍,他还是那么乐观。杀了一只土鸡给我们吃,还送了三瓶蜂蜜。或许,他也正如这山中野蜂似的,虽可以飞走,但他离不开大山。
返程时,透过车窗,看到一轮在众山之上的火红落日。在我的坚持下,司机停下车。我掏出手机拍下“停留”在葱茏树木上的殷红落日。隔天,发朋友圈时,文字如下:太阳回家了。
也有人说是朝阳。其实,不细看,是分不出的。
我喜欢这种模糊的感觉。清晨,还是黄昏?时间是一个永恒的谜题,过去还是现在,在大山深处,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心有归所。
二
房屋已经垮塌小半,陈旧的已更陈旧,新长的野草愈加青翠。再次回到这里,她小心绕开村头榕树下聚集的妇女与老人。脸上无悲无喜,如同每一个普通的日子,悄悄走进家门。在导演的引导,或是说沉浸在回忆的游走下,现场变得凝滞。破旧、凌乱的房子如同魔法般,变成了一个奇异的“博物馆”。想进去的人,找不到口子,却被馆内的“舞蹈”所吸引。
她叫李姐,五十出头,个子不高,有些微胖。
这是拍摄的主人公之一。早年,因为帮家公治病,花了很多钱,后来开货车的爱人也病倒了,瘫痪在床两年。有村民说,这就是钝刀割肉呀。在希望与绝望中徘徊。亲人还是相继离世,只留下破旧的空房子,以及一堆债务。
有时候,治重病对村民而言,是一场巨大的挑战。
本地有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体验过病房的冰冷和孤单,以及看过太多“老伙伴”从医院插着管子出院准备后事的场景后,特别畏惧住院。有些遇上难治的大疾病,在确认了即使手术成功后只能是多活半年至两年的治疗方式,老人家(包括一些后辈)就要求开些止疼药,直接回家,等待死亡的来临。仿佛,去趟医院,只是为了知道自己即将死于何种病症罢了。
后来,李姐开始养猪,取得了一定收益。通过村支书推荐,也获得政府的一些扶持。她继续把猪场扩大。但命运还是不公。有一年猪瘟严重,大批的猪相继死去。好不容易,她把这些死后不闭眼的猪,运上村尾的山坡。
当泥土掩埋了最后一只死死盯着她的猪眼睛,人仿佛被抽干了力气,她花了好长时间,才从山上下来。
那一刻,天空阴沉,内心空空,掌心也空空,被风吹一会后,一只微微颤抖的手自然而然攒成拳头。她忽然想起自己的两个孩子。她答应过亡夫,要把孩子养大成人。
苦难如同低沉的弦音,在耳边萦绕,使步履艰难。
不久后,她包下多个鱼塘,种植莲藕,重新开始生活。
时值六月,绿荷起伏,莲花盛开。我们找到一个五十多亩的大藕塘作为拍摄点。在这个被大量桉树包围的山坳处,藕塘用大片的绿和恰到好处的粉红,给我们展示了大自然最美丽的夏景。
阳光清浅,微风徐徐。李姐穿上下水裤,提上撒料桶,缓缓从莲塘一角,滑入水中。
莲叶慢慢与细眉齐平,饱经生活磨砺的脸蛋,此刻,多了些绿和粉红来衬托。她在淤泥中慢慢挪动身躯——亦同这些年来生活的样态,虽身陷泥潭,但慢慢走,累时,身旁也有使人心旷神怡的莲叶与荷花。
身陷泥潭的还有摄影小哥,以及一个摄影助理。他帮护着摄像师的行动与机器的安全。摄像师则专注于李姐的特写表情,一丝不苟,慢慢地,他发现眼前的藕塘,忽然开出一朵不一样的花。
李姐的脸上,慢慢露出笑容,比莲花还美的那种。这是一张饱经苦难的笑脸,像雨后彩虹,自然而然地微笑。大家在岸旁,纷纷拿出手机来记录这难得的画面。我框住的,是李姐轻揽荷花,微笑的神情。
虽身处淤泥,但眼中有山川、莲塘,以及阳光。
这是生命的底色之一。
拍摄采访时,大家一直盯着取景框,沉浸在李姐讲述多年来的苦难生活。但不久后,一个奇异的哭声把我们拉回现实——李姐的眼泪像水珠一样流下来。我挪了一下脚步,看着眼泪哗哗的她,有些不知所措。
导演暗示摄影师稳住,继续拍。收音师以及在场的人,被她的哭声打动,发出了细不可闻的叹息。我第一次感受到,哭也是一种厚重的表达方式,蕴含着言语无法述说的隐秘、沉痛、凄婉、悲凉。李姐的哭声,在曲调高昂时,哀而不伤,不沉溺,内蕴一种温和的力量。
哭泣是生而为人最初的语言。长大后,无论因何事哭泣,都包含着最初始对世界的一种莫名刺痛感。
时隔半个月,为补取一些镜头。导演想邀约李姐到她亡夫家中,拍一些追忆往事的镜头。虽有挖人伤疤的沉重感,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拨通李姐的电话。她听明拍摄意图,沉寂几秒后,只是轻声说,好的,什么时候呢?
导演觉得这份沉重和哭声,应该有更多的故事可挖。他想拿相机这把“尺子”丈量一下苦难的生活。
与亡夫曾经的家,就在现男朋友村子对面。仅隔着一条六米宽的公路,但她已经很久没来过这个荒弃的家。落叶在破旧的院子里叠了厚厚一层。依稀可见的是,破鸡笼、旧水壶、生锈的铁铲、裂口的水缸、一个布满污渍的人偶玩具。
这些物连同一些事和人,死灰的模样,但因为李姐的到来,此刻却散发出某种勾人思绪的魔力。
带我们走进旧宅,她还有些拘谨,不懂如何站位,配合拍摄。我说,忘记我们存在,像回家一样,现在你看到什么,有什么心情,就说出来。
像梦呓般,李姐走进一间低矮的房子,说着与丈夫辛苦搭建厨房的经历,又走出院子,说,这棵芒果树的果很甜,丈夫用竹竿打落果实,剥给她吃的往事,再走往屋后,指着荒芜的土坡,说当初在这里种过辣椒、玉米、青豆、番薯藤……
这里犹如一个以亲情、爱情为主题的博物馆。每一个声音、神态,像被苦难浇灌的奇异花朵,潜隐到今天才绽放开来。她是一个讲解员,也是一个建造者。没有人比她更了解这里的一砖一瓦、一树三房,以及背后隐藏的故事。
这一次,李姐没有哭,很平静。真的,就像回家一样。
三
摄制组在十五天的时间里,要拍摄十一个主人公,行程比较赶。清晨装车,搬运道具,夜晚还要探讨拍摄方案,大家忙得七荤八素。
即便是这样,在有限的摄像取景框里,呈现的东西也是有限的。
摄制组有他们的专注点和记录点。我也在忙碌之余,去寻找属于自己“取景框”的人与风景。
有一次,在一个养牛的主人公村子,我拍了一张老人照片,并附上一段文字来发朋友圈。文字如下:三姐妹加起来有二百六十八岁,问村支书要了两根烟后,畅谈当年……
村支书带我们做前期取景调查,经过一个小巷转角时,在一间两层的水泥楼房门口,遇到了坐在水泥长凳上的三位奶奶。她们看到村支书后,笑脸盈盈,眼睛放光,开口第一句话就是问要烟。村支书愣了一下,但随即讪笑几声,掏出上衣的烟盒,递了过去。她们知道碍于场面和脸面,作为老烟民的村支书,平时不给,这个时候肯定会给的。
她们惬意地抽着烟,用我听得懂一些的方言,说着当年的老故事。坐姿像大男人,笑声敞亮,丝毫不理会我们狐疑的目光,手夹着烟,漫谈人生。这张图片,我反复看着,慢慢品出了闲适、淡泊、从容,甚至还有些“痞”的味道。
岁月老去,她们已经摸到生命的“天花板”,可以更坦然,“放手”活出自己的样子。
同样是老奶奶,我在城市里却看到了另一种人生状态。
她挑着一堆泡沫箱和泡沫板,在道路上缓缓前行,不时挪移大过身躯三倍的大泡沫“行囊”到一旁的林荫步道上休停一会。她给往来的车辆让路,像一只巨型的白壳老乌龟,谦和地给一辆辆铁皮乌龟让道。
如同脱节于这个快节奏时代的舞者,老奶奶徐徐前行。我却急迫地用手机拍了几张相片。
我急,是因为时代惯性,是高强度工作的副作用。但老奶奶不急。
她缓慢,有力气,不急不躁,慢慢前行。
我不由思索,在这个时代,慢与快,哪种生活方式是对的呢?我知道,人的一生,都在平衡这种“慢与快”,我也隐约感知到,现在窘急的“快”是为了以后更为从容的“慢”。
在拍摄纪录片主人公罗哥时,他的老房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
从外墙看,楼房上下层的颜色不一样。一层是清一色的青砖,二层则是颜色更亮的红砖。
他九岁那年,父亲搭窑烧好了足够搭建三间房子的青砖后,就撒手离去。十四年后,母亲用养猪多年积攒下来的钱,终于起了一层砖瓦房。十五年后,三兄弟再用在他乡打工挣的钱,破开砖瓦房顶,又起了第二层。至此,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才有了这西大明山余脉偏远山村里的一栋小楼房。
罗哥用轻描淡写的口吻,对我说着颜色不一的“房子”故事,我却感到眼前的楼房,无意间掉下一块砖块,“压”在心上。
对于有强迫症的人来说,相片里的双色砖头,会给人不适。但若是知道了“双色砖”背后的故事,就会觉得这些砖头十分“耐看”。
相片的意义,正在于此。记录并“讲述”背后的故事。
即使是他父亲梦想中的楼房,也挡不住外出打工的欲望。父亲最大的能力,只能是烧好砖块。建瓦房的木料、水泥、钢筋、人工,还是离不开钱。罗哥很早就出到外省去打工,后来才结识了现在的妻子。也是通过打工挣下的钱,才能养育起两个年幼的孩子。
房子是人生的居所,有时,心的居所却缥缈难定。
我也曾发现过一面特别的围墙。不,准确来说,是两面墙。一边是部分剥落的土墙,一边是砖头砌起的红墙。砌砖墙的师傅是用心的,两面墙完整贴合在一起。屋主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才造就了这面富有艺术气息的墙体。
我一边掏出手机拍照,一边猜想这面“墙”背后所蕴含的故事。一面是父亲搅泥土,拌入剪好的稻草(部分加入米汤)建造的土墙,一面是儿子用砍收甘蔗的工钱砌起的砖墙。他从小就在泥墙里长大,老了,或许也想在泥墙里死去。这是一种关于“泥土”的传承。
从某种角度来说,相机拍出来的是死去的主观形态,但人是活着的,不断更迭的影像。
在拍摄的纪录片中,有给难产小猪做人工呼吸的覃姐爱人,有一边养羊一边种石斛来养病的周叔,有照顾瘫痪老人并积极带领村民改善村貌的陈姐。我从简单的文字资料中初识他们,再从一个个书面化人物,变成鲜活的影像素材。
生活是一个多面体,不只是被拍进去的那部分。摄制组只是艰苦地走到一座“大山”的角落进行记录,但也隐约感受到一座“大山”的沉重与瑰丽不止于此。
在摄影机开机时,大家都处在一种紧张的状态,无论是主人公还是村干,以及摄制组,都是如此。大家披上无形的面具,不由自主,跟随“镜头”的意志,或多或少有所演绎去“摆弄”自己的身躯。
相比之下,我喜欢偷拍主人公脱离摄像机后的生活状态,喜欢拍摄村子里的老牛、龙眼树、竹林、拖拉机、羊群,以及许许多多不知名的植物。这种自然的状态,是我想去记录的。这些所遇所见,都与我有一种莫名的缘分。
相逢是缘,这个不只是对人,也是对景、对物的缘分。缘分如同在命运之河里行舟激荡而起的水花,我信这种缘分,并尽可能记录这些激荡飞溅、在空中晶莹如花的人和事物。
四
常困于泥土的人,无法想象空中的风景。
拍摄纪录片时,除了地上沉重的摄像机,在每个拍摄点的上空,都会有轻盈的无人机影子。
在无人机的遥控器屏幕中,村子周边十公里的山水画像,如同魔法般,浓缩在这个小盒子里。无人机飞手小心拨动着摇杆,慢慢攀升至高处,一个壮阔的山中世界就慢慢展现出来。
后来,我也学会了飞无人机。我时而沉浸在这种“飞翔”的感觉中,进入一种忘却地面事物的微妙感觉中。在无人机的视角里,我慢慢体会到更“高”的境界,用一种上帝视角来审视脚下这片土地,并拍下许多壮丽的风景照片。
但我慢慢发现,即使是一张构图精巧、完美修图的风光大片,如果放大一百倍来看,就会发现很多地方是丑陋的,甚至还能看到方块成像的马赛克。
对生活而言,这些“马赛克”就如同使人癫狂的执念。
把细节放大,是人性的使然。痛苦的根源就是习惯性把自己的“相片”放大,甚至关联他人“相片”一起用放大镜来看。
痛苦时,细节不美。
当长久用“无人机”的视角来看蔗海、山川,以及长河落日后,我才感知,个人是广袤大地上微乎其微的一个点而已,“飞”多了,就知道,山河是固定的,人是易逝的。
叔本华曾说:我们的生活样式就像一幅油画,从近看看不出所以然,要欣赏他的美,就非站远一点不可。
当然,再远一点,上升到浩瀚无垠的星空,从旁无可依的地方(如地球的栖息地)看向地球时,会产生一种巨大的、不可名状的失落感。我们伟大的蓝色地球,在浩瀚宇宙里,也仅仅是微小的一个蓝点而已。
在当代摄影史上,有一张极为令人瞩目的相片——《暗淡蓝点》,这是一张由旅行者1号太空探测器拍摄于1990年2月14日的地球照片,在距离大约六十亿千米的宇宙空间拍向地球,从这个位置看向我们的母星,没有美丑之别,没有仇恨、纷争,各大城市、山川、国家甚至是宗教的界限,都已不重要。在地球母亲怀抱中,各类生物包括七十多亿人类,都浓缩成细微、暗淡的一个蓝色小点。人类的自大和骄傲、钩心斗角、名利追逐,包括大量社会法则和各种荣耀,瞬时变得卑微且可笑。
英国哲学家罗素临终时对人类的忠告里提过一点,关于道德,最重要的是心里充满爱而不是恨,人类追求的是共存,而不是同归于尽。
佛说,一沙一世界。我们仅生于沙漠的一粒沙砾里。
这就是我们已有的一切。
几个月后,纪录片的成片出来时,天空下的村庄,看起来如同油画一般。片头的山还是那座青山,原野上也是大片的甘蔗海,但似乎不是我认知的山和蔗海。这些按照创作者意愿创造的主观镜头,冲淡了我对“乡村”的记忆点。疑惑之余,我又从手机里的“琐碎”相片中,去回忆那些在乡村里劳动、交谈过的可爱的阿哥阿姐们。记忆与相片在慢慢重叠,才缓缓构建了一个相对真实的世界……
几年过去,我也在当地电视台谋了职。工作期间,拍摄了更多的人与风景。这些被眼睛记录的、机器记录的影像万千,它们时常在我脑海里翻滚。我们的一生,会产生多少个T的素材呢?我生发过这样有趣的疑问。
但我知道,硬盘会损坏,人脑也会遗忘很多东西。
似乎,没有什么是永恒不灭的。有人说,人有三次死亡。生物学上的死,下葬入土时的“死”,以及世界上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把他忘了。但科技发展快速的时代,理论上只要一直存留这个人的数字信息的存储服务器没有损坏,或许可以达到某一种程度的“永生”。
偶尔,回想起被荷叶莲花包围的李姐,在山坡上放羊种石斛的周叔,在山后凉亭唱山歌的陈姐。他们的画面,有时嵌入窗外的扁桃树叶上,哗哗作响——似乎想与我继续对话。我无法发出声音回应什么,只在脑海中,隐约听见咔嚓的快门声,如同画出巨人手指缝里一根极细的绒毛——一个时代的细节,就被记录下来。
曾听一个老人家说过,你去看山看水,不要把你的灵识和思绪散发给这片山水,它们不需要你的任何思维,人是最复杂的生物,你的过度关注,反而是一种污渍的沁染。你应该把眼前的山水装入你的精神里,把山川灵气、秀美和壮丽,以及它的神秘悠远,装进你的心里,来丰盈你的精神世界。
出于愚钝,努力把“山水”装进内心的同时,也借助相片来延缓我所看到的山川河流。
我曾无数次从自然风景中,看到天地澄净、连绵起伏的蔗海,每一朵闲云及山峰的轮廓,乃至一大片神秘的蓝天,都使我的灵魂震颤。我用相片记录,如同风尘仆仆而来,妄图延缓伟大神迹的朝圣徒。我摁下拍摄键,贪婪汲取每一缕流经身体的山川灵气。但我又慢慢感知到,只有越过取景框,身体里的血液、肉体、骨骼乃至灵魂,才能与这片天地合为一体。
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宇宙,但又与眼前的世界紧密连为一体。
偶尔,我也会拍下笑哈哈的幼童、缄默的老人、曼妙的美女,也会以山水为背景,自拍一二张。多年累积,脑海中的人,相片中的人,在交织,在重叠,无数张脸,陌生又熟悉。
水与水是相似的。人是流动的水。
卖蜂蜜的黄哥,在拍摄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时不时有联系。当初取景时,我在微信圈发过的一些“甜蜜”相片,吸引了一些友人。他们纷纷委托我跟黄哥买蜂蜜。朋友在微信里会问,是龙眼蜜还是什么蜜?我想起黄哥在山坡上说的话,回应道,百花蜜。朋友发了一个疑问的表情,我回道,就是很多很多花酿出来的蜜。
后又加了一句:我在村里尝过一些,香甜,不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