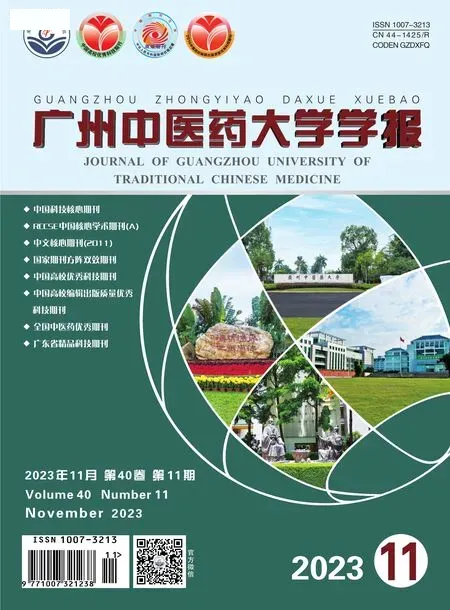劳绍贤诊治便秘经验
董建伶, 段文韬, 杨泽虹, 郭文峰 (指导:劳绍贤)
(1.广州中医药大学青蒿研究中心,广东广州 510405;2.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广东广州 510405;3.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广东广州 510405)
便秘是指因粪便在肠内滞留过久,导致排便周期延长,或出现粪质干结、排便艰难,或便而不畅的病症[1]。我国成人慢性便秘的患病率为4.0%~10.0%,慢性便秘患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升高,且女性患病率高于男性[2]。便秘按病因主要可分为器质性便秘、功能性便秘等。西医治疗便秘,对于器质性便秘主要针对病因治疗,同时可选用泻药以临时缓解便秘的症状;对于功能性便秘,首选基础治疗如合理膳食、多饮水、运动、建立良好的排便习惯等,辅以口服药物如促胃肠动力药、促分泌药、益生菌等,外用药如灌肠药、栓剂等[3],这些药物对功能性便秘治疗虽起效快,但长期应用会影响肠道内环境,干扰肠道正常功能。中医药治疗功能性便秘具有副作用少、药物依赖性小、复发率低等优点,临床可取得较显著疗效[4]。
劳绍贤教授为广东省名中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四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劳绍贤教授出身于长沙“劳九芝堂”医药世家,师从国医大师邓铁涛教授,为著名脾胃病专家,对脾胃病科常见疾病之便秘诊疗颇有心得。现将劳绍贤教授治疗便秘的临床经验介绍如下。
1 五脏功能失调,大肠传导失常而成便秘
中医文献中对便秘的描述有“大便难”“后不利”“大便涩滞”等,《伤寒杂病论》则将便秘称为“阳结”“阴结”“脾约”等。 劳绍贤教授认为,便秘病位虽在肠,其发病与五脏功能失调密切相关。如《素问·五脏别论》记载:“魄门亦为五脏使,水谷不得久藏”;《诸病源候论·大便难候》亦提到:“大便难者,由五脏不调,阴阳偏有虚实,谓三焦不和则冷热并结故也”;《素问·灵兰秘典论》云:“大肠者,传导之官,变化出焉。”肺与大肠相表里,肺燥、肺热移于大肠,导致大肠传导失司而成便秘。脾主运化,胃主和降,胃肠相连,水谷入口,糟粕转输于大肠。若脾虚失运,胃失和降,则可使糟粕内停而致便秘。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肝之主升与大肠之主降结合,共同促进大便的正常排泄。若肝气郁结,则腑气不通,气滞不行,大肠不畅而致便秘。肾司二便,肾气不足则大肠传导无力,肾精亏耗则肠道干涩,肾阳不足则命门火衰、阴胜内结,均致传导失常而形成便秘。因此,劳绍贤教授提出,便秘的基本病机为五脏功能失调,大肠传导失常。
从气血津液辨证而言,便秘发生的机理与气虚、气滞、津伤有关。气虚者,大肠传导无力;气滞者,大肠传导失司;津伤者,肠道失润难行。正如《诸病源候论·大便难候》云:“大便不通者,由三焦五脏不和,冷热之气不调,热气偏入肠胃,津液竭燥,故令糟粕痞结,壅塞不通也。”
2 病证结合治疗便秘
劳绍贤教授临证治疗便秘以证为本、病为枢、症为标,病证结合,随症加减;用药参考现代中药药理研究成果,灵活运用药对,注重一药多用,形成自己独特的用药风格。
历代医家对便秘的治疗均有各自偏重点。张仲景将便秘分为阳明腑实证、阳明兼少阳证、脾约证和阳虚寒凝证;孙思邈将便秘分为虚实两类;严用和《济生方》提出“五秘”之风秘、气秘、湿秘、冷秘和热秘。现代医家认为便秘的发病机制为大肠的传导功能失职,临床多采用通下之法。劳绍贤教授认为,便秘既是一种独立的疾病,也常作为伴随症状在其他疾病中出现,临床应注意鉴别原发病,不可一味通下。其治疗便秘先分急性便秘、慢性便秘和慢性胃病伴便秘三类分别遣方用药,并强调在治疗上需抓住气虚、气滞、津伤3个要点,分清主次,权衡用药,以取得理想疗效。
2.1 急性便秘、慢性便秘的治疗新病、急病的便秘患者,多为阳明腑实证,可采用滋阴增液、通腑泄热之法,常用方为大承气汤或大黄牡丹汤。大承气汤出自《伤寒论》,用于治疗“痞、满、燥、实”之阳明腑实证,条文220 记载:“二阳并病,太阳证罢,但发潮热,手足漐漐汗出,大便难而谵语者,下之则愈,宜大承气汤。”阳明燥热逼迫津液外越,全身津液耗伤,化源不足而致大便秘结,故劳绍贤教授提倡采用滋阴增液、通腑泄热的治法。大黄牡丹汤出自《金匮要略》,主要用于治疗肠痈病脓未成者。大黄牡丹汤集泻下、清利、破瘀于一方,方中大黄与芒硝涤荡实热,宣通壅滞。因肺炎、支气管炎而致的阳明腑实便秘者,可加用葶苈子15 g、瓜蒌仁15 g、牛蒡子15 g。这3 味药物针对肺部症状可祛痰、宣肺、泻肺,同时富含油脂而具有润肠作用。肺与大肠相表里,肺为上焦华盖,大肠属下焦,上焦闭则下焦塞。这也是“提壶揭盖”法在治疗便秘中的体现。
慢病、旧病的便秘多见于临床各种习惯性便秘、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等患者中。劳绍贤教授治疗慢病、旧病的便秘患者,常予自拟润肠通便基础方,重在行气消滞、润肠通便。自拟润肠通便基础方的组成如下:槟榔15~30 g,木香10~16 g(后下),台乌15 g,郁李仁15~30 g,生地黄30 g,玄参20 g,甘草6 g。该方由四磨饮加减化裁而成,木香代替四磨饮中的沉香,取“验廉”之意。木香功擅行滞消积,现代药理研究表明木香对胃肠道有兴奋或抑制的双向作用,同时有明显的利胆功效[5-6]。槟榔主散结破滞行气,张元素在《医学启源》中提到:“木香除肺中滞气,治中下二焦气结滞,及不转运,须用槟榔为使”。槟榔的临床剂量建议控制在15~30 g,因人调量,避免用量过大而出现便前腹痛。郁李仁润肠通便,李东垣认为郁李仁可专攻大肠气滞燥涩不通。生地黄滋养阴血,补肾水不足,治少阴血虚火旺;玄参滋阴降火。玄参与生地黄两药合用有增液汤之意,取其增液润燥之效。
慢病、旧病的便秘患者见脾虚者,于润肠通便基础方基础上加党参30 g、白术30~60 g。白术性味苦温而燥,但无伤阴之虞。如《本草正义》云:“白术最富脂膏,故虽苦温能燥,而亦滋精液……万无伤阴之虞”;《珍珠囊》述白术能“除湿益气,和中补阳,消痰逐水,生津止渴。”白术剂量较小时可止泻,剂量较大时则通便,故具有双向调节作用。慢病、旧病的便秘患者见肾虚者,加肉苁蓉30 g。肉苁蓉可补肾阳,益精血,润肠通便。现代研究提示,肉苁蓉的有效成分肉苁蓉总苷具有拟雌激素活性,可调节女性体内雌激素的平衡[7],尤适用于绝经后妇女大便干结者。此外,若见肝火旺者,加决明子30 g;便血者,加槐花15 g、地榆20 g;失眠者,加柏子仁15 g、何首乌藤30 g;见燥屎者,加火麻仁30 g;见阴虚者,加玉竹30 g、黄精30 g、石斛15 g。
2.2 慢性胃病伴便秘的治疗便秘为慢性胃病患者病程中常见的兼夹症状,治疗时可在胃病辨证用方基础上加用行气润肠药。脾升胃降,乃气机升降枢纽。脾胃升降失常,气机郁滞则出现腹胀便秘症状。此时酌加行气润肠类药物,以通为降,大便得行,气行胀减。
慢性胃病伴便秘辨证属肝脾不调者,可于四逆散基础上加行气之木香、槟榔及凉血止血之地榆治疗。四逆散是疏肝理脾之代表方剂,方中白芍、甘草两味药组成芍药甘草汤,除缓急止痛之效外,药理研究证实芍药与甘草的配伍比例按3∶1最具通便效用[8]。方中白芍与枳实两味药又为枳实芍药散的组成,劳绍贤教授用其治疗肝脾不调便秘腹痛者,止痛效佳。地榆用于治便秘记载于陈士铎的《辨证录·卷九·大便秘结门》中的散火汤,此方主要用于治疗肝郁火盛导致的热结里实证。在注解中,陈士铎认为地榆可“专解大肠之火”,地榆配伍疏肝解郁之品可用治肝火旺导致的便秘。研究[9-10]表明,地榆可抑制炎症反应,对胃炎和溃疡疾病有治疗作用,且其具有凉血止血功效,尤适用于有溃疡出血或便血的便秘患者。
慢性胃病伴便秘辨证属湿热中阻者,治疗可用藿朴夏苓汤去茯苓加木香10 g、枳实15 g、槟榔15~20 g、地榆20 g。湿热型便秘患者多表现为排便次数增多,排便量少,性状黏腻,伴排不尽感。此方去茯苓,乃因泽泻、猪苓等利水效果较茯苓更佳[11],故可使用其他祛湿药物代替。绵茵陈清湿热,煎煮时间不长时具有缓泻通便作用,尤其适合治疗湿热证便秘。劳绍贤教授强调,此时虽为湿热证,但要注意避免使用温燥药物如祛湿之草果、清热之黄芩,以免加重便秘症状。
慢性胃病伴便秘辨证属气阴两虚者,可于消痞方[12]基础上加木香10 g、台乌10~15 g、郁李仁15~20 g、火麻仁30 g、地榆20 g治疗。
3 泻下药在治疗便秘中的应用
治疗便秘通常要运用泻下药。在泻下药的应用上,劳绍贤教授基于多年临床经验,提出大便数日未解者,服用通便药前应先润化燥屎,使排便顺畅,避免大便过硬难下而腹痛加剧。建议芒硝或玄明粉的剂量要大于大黄,加强软坚之力;大黄质佳者用量5 g 后下即能达到通便泻热的效果,也可于口服通便药前选用开塞露润化燥屎。
含蒽醌类成分的通便药如大黄、番泻叶、何首乌、芦荟、决明子等,长服服用可致结肠黑变病。国内外文献对于黑变病与结肠息肉、腺瘤、恶性肿瘤之间的相关性尚无定论。相关研究[13-14]表明,黑变病患者多合并直结肠增生性息肉和低级别腺瘤;程一乘等[15]的研究表明,豚鼠黑变病模型结肠组织中原癌基因的相对表达量较高,提示黑变病具有向结肠癌转变的趋势;但另有研究[16-17]则显示,黑变病与直结肠癌之间无显著相关性。有观点认为,黑变病患者息肉或腺瘤检出率偏高可能是由于表面无色素沉着的结肠息肉在黑变病患者暗视野的肠镜中更容易被发现,也可能与黑变病患者以腹痛、大便性状改变为主要临床症状,故而此类患者主动要求进行肠镜检查的比率较高有关[18-19]。黑变病是否会增加直结肠癌的风险目前尚缺乏直接证据。
劳绍贤教授从医数几十载,未见一例结肠黑变病恶化。另一方面,便秘可显著增加结直肠息肉的发病率且便秘是结直肠癌发病的危险因素。因此,对于便秘患者使用蒽醌类泻剂时要权衡利弊,掌握用药时间。
4 运动食疗对防治便秘的作用
劳绍贤教授认为,保持良好的饮食生活习惯是改善便秘症状、预防便秘复发的根本。便秘患者不可过分依赖于服药。劳绍贤教授常嘱咐患者调整生活方式以巩固疗效、预防复发。
提肛运动和凯格尔训练能够提高排便相关肌肉的兴奋性、协调性,达到促进排便的目的[20]。对于因盆底肌松弛而排便无力的产后便秘女性患者,劳绍贤教授尤其嘱其在服用汤药时需配合锻炼。研究[21]证实,腹部按摩对改善便秘症状有效。便秘患者的腹部按摩方式尚缺乏统一的规范,大多数临床医生采用腹部顺时针按摩或顺时针结合逆时针的按摩方式。劳绍贤教授提出采用逆时针方向按摩腹部,对于便秘患者见硬结粪块聚结于左下腹者,按摩时尤应用力向上推之。
饮食上,便秘患者应多进食富含膳食纤维的水果蔬菜。劳绍贤教授还提倡患者清晨空腹饮水,此时饮水可保证水液在较短时间内到达肠道,以改善大便干结症状。同理,便秘患者中药汤剂建议空腹服用。肠燥便秘患者,可用熟芝麻油一勺、蜂蜜一勺,适量温水冲服;亦可选用番泻叶2~10 g,开水浸泡饮用;可适当补充益生菌制剂,通过调节肠道菌群失衡促进肠道蠕动和胃肠动力恢复,从而改善便秘症状[2]。
5 验案举隅
5.1 气阴两虚型便秘案患者施某,女,24 岁,2021年1月19日初诊。主诉:便秘1年。患者自诉大便每3日1次,便干,难解。舌嫩红有裂纹,脉细。临床诊断:便秘;辨证:气阴两虚型。治法:益气养阴,润肠通便。方用自拟益气养阴润肠通便方加减,用药如下:木香16 g(后下),陈皮10 g,乌药15 g,槟榔15 g,郁李仁15 g,党参片30 g,石斛15 g,玄参15 g,地榆15 g,甘草片6 g。共7剂,每日1剂,水煎,每剂煎煮两次,每次水煎取药汁约250 mL,分两次于早晚饭前空腹服用。嘱患者日常频频饮用温水,每日保持至少1 500 mL的饮水量,多食用蔬菜等富含纤维的食物。
2021年1月26 日二诊。患者自诉大便每日1 次,成形,易解。胃纳可。舌胖,嫩红,有裂纹。守一诊方,地榆、玄参的剂量由15 g 加大到20 g。共7剂,每日1剂,煎服法同前。
2021年2月9 日三诊。患者诉大便每日1 次。另诉疲乏,胃纳少。舌嫩红剥苔,脉细。于二诊方基础上去陈皮,加仙鹤草30 g、五指毛桃30 g、酒山茱萸肉30 g、鸡内金15 g。共7剂,每日1剂,煎服法同前。此后患者又续服14 剂中药,药方同前,随症加减一二味药物,疗效良好,未见便秘复发。
按:此便秘患者为气阴两虚证,舌有裂纹、便干为津伤。结合患者便秘症状,采用自拟益气养阴润肠通便方,以滋阴益气、润肠通便。患者辨证属气阴两虚,故加入党参30 g、石斛15 g补气滋阴,此为劳绍贤教授常用药对之一。二诊时患者便秘症状明显改善,效不更方,增加地榆、玄参剂量至20 g 以提高润肠、养阴之力。三诊时患者大便正常,但具有疲乏、纳少症状,故加入仙鹤草30 g、五指毛桃30 g、酒山茱萸肉30 g以补脾益气缓解疲劳。其中仙鹤草和五指毛桃亦能祛湿,符合岭南多湿邪致病的地理特点;加入鸡内金15 g可消食化积。
5.2 湿热便秘案患者刘某,女,51岁,2021年8月17 日初诊。患者就诊时症见:大便每日1 次,排出困难,呈颗粒状。胃纳少,餐后胃胀,嗳气。舌红,苔腻,脉弦细。患者2021年7月于外院曾行子宫及附件切除术。临床诊断:便秘;辨证:湿热证。治法:清热祛湿,行气润肠。方用自拟行气化湿润肠通便方加减,用药如下:石菖蒲15 g,法半夏15 g,姜厚朴15 g,木香16 g(后下),陈皮10 g,乌药15 g,槟榔15 g,郁李仁15 g,酒肉苁蓉30 g,甘草片6 g。共7 剂,每日1 剂,水煎,每剂煎煮两次,每次水煎取药汁约250 mL,分两次于早晚饭前空腹服用。配合中成药麻仁软胶囊,每次两粒,每日1次。嘱患者平日多做提肛运动及凯格尔训练,并保证每日饮水量和蔬菜膳食纤维摄入量。
2021年12月9 日二诊。患者诉大便每日1 次,条状,排出顺畅。胃纳少,胃胀减轻,嗳气。另述身痒伴潮热。舌红,苔黄腻。诊断为皮炎,以凉血祛风法治之。
按:初诊患者辨为湿热证,湿热胶着,阻滞气机,肠道运化失司导致便秘。选用自拟行气化湿润肠通便方加减以清热燥湿,行气润肠通便。其中木香、乌药、槟榔行气,石菖蒲、半夏、厚朴、陈皮化湿燥湿理气。患者大便呈颗粒状,故用郁李仁、酒肉苁蓉润肠通便。患者已51 岁,处于围绝经期,且子宫及附件切除,此时运用肉苁蓉可补肾阳、益精血,调节体内雌激素平衡。针对患者胃热津亏肠燥之病机,中成药麻仁软胶囊与中药共用可提高其疗效,以备患者无法煎煮中药时服用,防止便秘反复。二诊时患者便秘症状明显改善,自述服药后大便排出顺畅,性状由干结颗粒状转为条状,疗效较明显。此时患者身痒为主,故更方治疗身痒。
5.3 慢性胃炎伴湿热型便秘案患者陈某,男,75岁,2021年8月3日初诊。患者就诊时症见:餐后胃痛、胃胀,伴有嘈杂、反胃。大便每3 ~4 日1 次。舌红,苔根部微黄。西医诊断:慢性胃炎。中医诊断:胃脘痛;辨证:湿热证。治法:清热祛湿,理气止痛。方用藿朴夏苓汤加减,用药如下:法半夏10 g,木香10 g(后下),紫苏梗15 g,槟榔20 g,地榆20 g,合欢皮15 g,蒲公英30 g,醋延胡索20 g,柿蒂15 g,野木瓜30 g,郁李仁15 g,玄参20 g,甘草片6 g。共14 剂,每日1 剂,水煎,每剂煎煮两次,每次水煎取药汁约250 mL,分两次于早晚饭前空腹服用。
2021年8月17 日二诊。患者诉左上腹胀,嗳气,大便每两日1次。舌淡红,苔腻。守前方去合欢皮改用大腹皮15 g。共14剂,每日1剂,煎服法同前。
按:患者初诊时辨证为中焦湿热,故选用藿朴夏苓汤以清热祛湿、理气止痛。证属湿热,故用法半夏以燥湿;木香、紫苏梗、槟榔三药理气、行气,木香配伍紫苏梗取香苏饮之意,亦有和胃功效。劳绍贤教授认为,脾胃重在升降运化,胃以降为和,脾升胃降正常则水谷之气得以下行,故治疗胃肠疾病时使用理气药以调理脾胃,恢复其正常运化功能,避免湿滞中焦化热。患者胃脘疼痛明显,故用醋延胡索、野木瓜止痛;有嗳气症状,加柿蒂以降逆下气;便秘症状用润肠之郁李仁、地榆、玄参。地榆既能抑制炎症,改善胃炎引起的胃脘痛、嗳气等症状,又有助于改善便秘。玄参养阴生津降火。蒲公英清热通便,尤其适用于证属湿热且便质偏干的患者。二诊时患者排便周期由每三四日一行转为每两日一行,便秘症状有所改善。效不更方,但患者舌苔仍腻,故在原方基础上将合欢皮15 g 改为大腹皮15 g,以加强理气利水之功。
劳绍贤教授认为,若患者的症状较多,应注重缓解患者的首要症状。治疗时以证为本,病案1辨为气阴两虚证,治疗以益气养阴为法,用药如玄参、石斛、党参片;病案2 与病案3 辨为湿热证,治疗以清热祛湿为法,用药如蒲公英、法半夏、厚朴。以病为枢,3则病案均见便秘症状,病案1 与病案2 以便秘为主症,中医诊断为便秘病,治疗以润肠通便为法,用药如木香、陈皮、乌药、槟榔、郁李仁;病案3 以胃脘痛为主症伴便秘,中医诊断为胃脘痛病,治疗应以理气止痛为法,用药如木香、紫苏梗、柿蒂、合欢皮、醋延胡索、野木瓜。病证结合,病案2与病案3虽属湿热便秘,均可用清热祛湿之法。病案2 以便秘为主症,用自拟润肠通便方加清湿热之石菖蒲、法半夏以清热祛湿、行气润肠;病案3以胃脘痛为主症,以便秘为兼夹症,用藿朴夏苓汤以清热祛湿、理气止痛。以症为标,随症加减,病案3针对湿热便秘兼症加入地榆、蒲公英、郁李仁、玄参,其中地榆、蒲公英同时可改善患者胃脘痛症状。
6 结语
综上,劳绍贤教授治疗便秘重在辨其新旧缓急。新病急病多为阳明腑实热证,用大承气汤、大黄牡丹汤通下。旧病缓病予自拟润肠通便基础方,根据气虚、气滞、津伤之病机偏颇及伴随症状加减。临床便秘患者多为慢性病程,新病、急病者较少。胃肠道疾病兼见便秘症状的患者,治疗时先辨证确定主方,再加减行气、润肠药物以缓解便秘症状。中药汤药能帮助患者解决当下排便困难症状,恢复正常排便;而良好的饮食习惯、腹部按摩、相关肌肉训练等则能提高中药疗效,有效预防便秘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