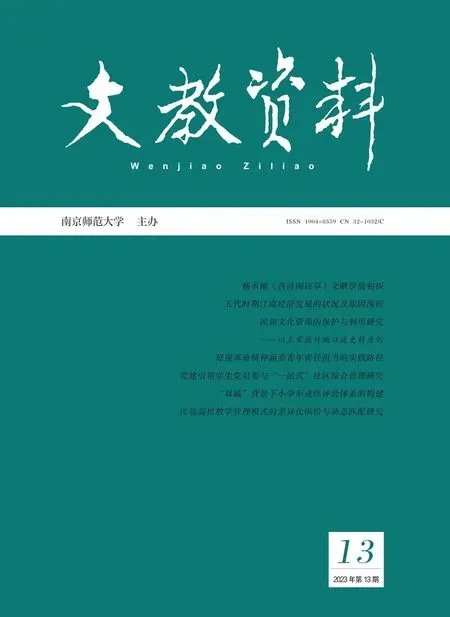杨承鲲《西清阁诗草》文献价值初探
景怡蓉 吕亚蓓
(宁波大学 人文与传媒学院,浙江 宁波 315000)
明代鄞县镜川杨氏家族以诗书传家,至万历十四年(1586 年)前后,杨承鲲以诗文创作崛起于甬上诗坛,成为当时甬上布衣诗人群体的重要成员。杨承鲲(1550—1589 年),字伯翼,号桓溪,少时聪明过人,喜读书,善作诗,以五言为佳;擅长书法,作品飘逸自然,有晋人之风;交游广泛,上至朝廷官员,下至文士隐者,均有诗文往来。杨承鲲病逝于万历十七年(1589 年),著有《西清阁诗草》四卷、《碣石编》二卷传世。杨承鲲虽不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但其诗文却影响甚广,颇受人追捧,屠隆言:“今世灵心伟手,吾伯翼是也。”[1]余寅亦赞:“我国家文如子威,诗如足下有几人哉?”[2]可见对其评价之高。
一、《西清阁诗草》的编撰缘起与成书时间
范钦《天一阁书目》最早载有杨承鲲《西清阁诗草》一卷。现下有《西清阁诗草》四卷万历鄞县杨氏家刊本三册,高19.2×12.5 厘米,半叶9 栏,单行18 字,民国时藏于北平图书馆,现移至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馆馆藏。再有宁波天一阁《西清阁诗草》十二卷,万历鄞县杨氏桓溪山房刻本两册。据王重民《中国古籍善本书提要》记载,此本与北京图书馆藏本相同。另国家图书馆“中文古籍联合目录”载,德国巴伐利亚邦立图书馆藏《西清阁诗草》十二卷,明万历间刻本,如何传入不清。
该卷首序为刘凤撰。刘凤(1527—1610 年),明南直隶长洲(今江苏苏州)人,字文起,更字子威,号罗阳。序云:“伯翼志乃在三代间,而气盖一世,骨力于风雅,而筋节于安世房中,故其诗上自三百篇,下逮开元天宝之盛,及其中叶,无不兼存之。虽存之,亦与之出入,上下鞭箠,使之遇其意所当,值情之感畅,舒写发咏焉……予得受读而惊,谓当世之为诗未有若是擅者。”[3]此序高度称赞杨诗,说明了编纂原因,但未注时间。刘凤《刘子威集》有《重序杨伯翼诗》和《杨伯翼诗序》,后者即杨诗的首序:“杨君伯翼志古者也,往岁来吴始识之,以未得谒元美,今兹复至,示予所为诗……与予所论诗意正同,而犹不自信,质之元美。”[4]再杨承鲲《碣石编》卷二《复刘子威先生书》云:“昨岁辱手教,并示大集,感愧弥至,尊体比当,胜良慰。仆治诗文二十年,今兹见其难耳,盖兢兢守古尺寸,不敢黍米溢也。”[5]此处谈及自己最终未求王世贞作序的原因。
刘序后有诗人友弟钱文荐的序。钱文荐,字仲举,别号石城,慈溪人。序云:“朗初因言伯翼曾有遗嘱,嘱死后求一知己为之序……予犹忆《西清》初刻时,问伯翼何以无序?伯翼曰,‘方今此道弇州擅场,顾弇州交游太滥,得其言不足九鼎。罗阳拙而速,汉城工而迟,姑其俟哉。’……今汉城已逝,而《西清阁序》乃出,罗阳遗稿盖亦声气之同,有莫之求而自至者。然而拙有之,恐非伯翼意也……罗阳序《西清》,虽其言纵横漫衍,终不若自叙简而淡,予忝伯翼知音,序止矣。”[6]钱为完成杨承鲲遗愿,写作此序。由“予犹忆《西清》初刻时,问伯翼何以无序?”推知,杨承鲲于万历十七年(1589 年)早逝,初刻本应早于万历十七年。再“今汉城已逝,而《西清阁序》乃出”一句中,“汉城”为余寅。余寅,字君房,号汉城,鄞县人,逝于万历二十三年(1595 年)十二月后,可知钱序应作于这一时间之后。
此外,卷中还有杨承鲲之子杨德迁的序。综合三篇序跋,均未提及时间,但由钱序推知,当时并无刘凤《杨伯翼诗序》,再据《复刘子威先生书》中“拙集付梓”一句,可知此时初刻本已出。由此推算,《西清阁诗草》在杨承鲲生前已经付刻,时间当不早于万历十四年(1586 年)冬,因无其他信息参考,更准确的成书年月难以判明,但当下刻本包含刘凤、钱文荐、杨德迁三人之序,可推断乃系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后刻本。
二、李白诗式与诗情的摹仿与突破
杨承鲲于甬城外老龙湾建的翛园有一西清阁,《西清阁诗草》以此命名。此卷按诗歌创作时间排序,卷前注明该卷诗歌年份,从乙亥至丙戌,即杨承鲲明万历三年至万历十四年(1575—1586 年)十二年间所作诗歌,多达599 首。其间,诗人已离京返乡,诗歌多为写景抒情的遣兴之作和即事感怀的交游之作。刘凤评“广肆奥微兼总论,浃洞通于情境……五、七言古规苏、李,而驰建安七子,犹未离其质乎”[7]。
(一)承李白风格,创一己格式
杨承鲲喜好山水,有大量写景之作,此类诗多为五言,笔法多变,想象奇特。诗人不受格式束缚,创新出五、七言句等结合的诗作,诗风雄浑深远,清新自然,与诗仙李白创作风格相似。
《西清阁诗草》中写景诗占多数,其中有7 首描述鄞县东山,仅咏东山别墅的就有4 首,如《东山别墅》(以下文中未注诗歌皆出于《西清阁诗草》,不一一标注)“始从东山游,遂为东山客。缘峰溯涧道,望烟诣岩宅。郁纡行莫展,傲倪情自得。岚彩生阴寒,日气相喷射。濯溪拾紫茸,窥洞讨灵液。仙人逝已久,古迹纷浪籍。溜溜阴风生,霭霭素霞积。鼋鼍宿深渊,鸿鹄游大泽。轩冕良傥来,乐全我所适。”《鄞县志》卷六四云:“东山别墅:杨承鲲筑。县东南六十三里横溪之东。”[8]诗人借想象游东山,虚实相生,沿东山曲折前行,岚光四起,在溪边拾取紫茸,于洞内求讨灵液,似刘凤所言“或肆口而歌,灿若霞绮”[9],又引传说“鼋鼍”为意象入诗,写东山的神秘莫测和古老悠久,整首诗有太白洒脱之风。
南宋胡仔有言:“李白虽无深意,大体俊逸,无疏谬处。”[10]杨承鲲亦推崇李白此风格,写景清丽流畅,如《雨晴泛湖·其二》:“水远高于席,山青欲入船。鸬鹚漫自在,出没大湖天”。白描手法,有动有静,浑然天成。诗人游于湖上,恰如水鸟出没湖天之中,逍遥自在。另有清新脱俗、自然灵动之诗,如《山风》“山风吹女萝,细雨石上起。湿尽石边松,还作溪中水。”以拟人手法写微小细节,活灵活现。细雨因风竟从石上弹起,淋湿松树后化为水躲回溪中。
此外,诗人打破常规,创新出多言句结合的诗,如《题画》一诗:“乱峰出云气,孤嶂秋天白。草亭撑拮横翠岩,主人端坐无今昔。下临千仞不断之回溪,上有万丈破碎之石壁。石梁不动白日高,瀑布下激青厓牢。龙湫雁荡若在眼,碧潭霜树风萧萧,侧身南望徒心劳。”长短句交替,得王世贞句法之要,“抑扬顿挫,长短节奏,各极其致”[11]。诗人先用五言点出画中乱峰穿天的壮阔,再七言写草亭翠岩,后九言描绘溪流曲回、石壁险峻的画面。结尾又以七言道出画之萧瑟。第三句与李白《蜀道难》“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12]异曲同工,让人身临其境。
明后期的诗歌创作从复古转向个性,杨承鲲虽承李白之风,但不盲目崇古追古,强调学习古人而超越古人,有个人特色,能突破常规,创新出五、七言等结合的格式,可谓明代后期文学创作自觉发展的体现。
(二)承李白个性,抒自我情志
明嘉靖、隆庆年间文学流派以后七子为主。王世贞晚年放弃复古,主张直抒性灵,认为诗歌本源乃“性情之真”。谢榛亦重情,认为“《三百篇》直写性情,靡不高古”[13],“情乃诗之胚”[14]。
杨承鲲学诗作文,自受流派影响。沈明臣首次见他,就赞为奇才,有《戏赠杨伯翼》:“谁家小儿杨德祖,青天之鹘丹林虎”[15],称他“杨德祖”。后杨承鲲入北京国子监补国子生,北上作《蓟门行》,名声大振,但几次科考不第,便多有感怀之作,表现沉郁叹惋之思,如《郡城瞩眺偶作·其四》:“白水青门落暮霞,孤城遥指月光斜。夫差旧恨空磨灭,无复甬东三百家。”胡应麟云:“凡排律起句,极宜冠裳雄浑,不得作小家语。”[16]海天落幕,孤城独立,月光斜照,首句略有苏轼“两山遥指海门青。回首水云何处、觅孤城”[17]之影,意境开阔又悲凉。
几经波折,杨承鲲选择归乡,平日虽吟咏为乐,但难逃壮志未酬的慨叹,如《烈士篇》:“东山有烈士,慷慨独不常。既惜白日短,复惜玄夜长。岩栖十余载,润泽成文章……蚊蚋各有营,溷浊固难当。不惜肌骨沉,所忧志行伤。翱翔将何集,惋叹沾衣裳。常闻圣人语,固穷有遗方。削竹蒙铦羽,用之何不臧。”诗中“烈士”栖居山野,满怀才能,却难有作为,诗人借此述说自己于现实碰壁,不知何日才能一展抱负的愁闷。谢榛指出“诗以气格为主,繁简勿论……太白深得此法。”[18]读罢杨诗,更令人想到“朝如青丝暮成雪”“千金散尽还复来”等,颇有李白诗之韵味。
杨诗抒写本性,不受拘束。他曾拜谒王世贞,王见其诗文,赞叹不已。事后杨承鲲语:“以吾诗求王先生一序有余。顾王先生博大心慈,客持片楮求誉,辄津津不休,即孺儒贾竖,人人谓王先生知己,其知己多矣,仆尚容厕其间耶?”[19]诗人也细腻重情,与友人赠答送别的诗中可见。此类诗超过180 首,与君同游,记其乐;与君分别,抒其思。在《翛园种梅已着花喜寄友人》中,诗人栽植的梅花已开,忍不住同友人分享:“手种寒梅树,开花已自多。定知江上雪,来和郢中歌。对此情空剧,相看老奈何。百年丘壑客,清影正婆娑。”正如“诗有天机,待时而发,触物而成”[20],诗人随感而作,同好友共赏寒梅或鉴赏美文,均是结友之乐。
杨承鲲归乡后,身边好友多在异乡。万历七年(1579 年),他送友人余寅北上科考,作《送君房北上》:“屡忆临歧语,频伤问字亭。风尘余涕泪,天地正雷霆。惜别防头白,思家及柳青。送君双目力,万里到彤庭。”“送君”“万里”皆为李白送别诗的常用词,如“送君不尽意”“万里送行舟”等。一“送”一“到”,两人依依惜别的画面如在眼前,可见二人情谊之深。
三、《西清阁诗草》表现的文献价值
从《西清阁诗草》中不仅能知晓诗人为人性情和生活经历,还可一探当时文人结交之风和文学发展状况,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另外,不少诗歌涉及社会时事和民风民俗,可作为研究明代宁波的史料参考。
(一)展现甬上诗社发展和文人交游往来
明代很多文人倡雅乡邦,与杨承鲲同乡的张时彻归乡后发起甬上诗社。作为诗社一员,杨承鲲同甬上文人往来,多有诗歌唱和。对照其诗,诗人与社中沈明臣、包大炣、余寅、李生寅、沈九畴、汪礼约、闻大连、闻龙、丰越人、屠隆、屠本畯等十一位成员多诗歌赠答。诗歌内容除学术思想、诗文创作外,还有关喜怒哀乐、日常琐事等,足见其真性情,如《闻大连被酒跌足诗以讯之》《对雪寄丰正元兄弟》《答仲连送酒》《戏赠李之文》《训蔡子行》等。从此类诗歌中可了解他与甬上文人的交游情况,沈明臣《祭大司马张公文》载:“万历丁丑季冬月朔,当大司马东沙先生谢。宾客捐馆,舍之三月。”[21]万历五年(1577年)十二月初一,张大司马逝世。次年,王百谷为吊唁张大司马至宁波,后杨承鲲送其返回江苏,分别之际作《送百谷归姑苏》:“到来堇子国,归去阖闾城。世路有吴越,交情无死生。风高江气紫,霜落海潮清。别后遥相忆,频更月旦评。”
至明中晚期,甬上文坛出现以沈明臣为代表的布衣诗人群体。沈明臣年少成名,同文坛盟主、主流诗人多有来往,后得张时彻赏识,晚年主盟甬上文坛,后辈多随其学诗。与甬上文人的交游中,沈明臣更是杨承鲲文学上的指引者和提携者,结合《叶郑朗先生太叔》所载,“年二十,诗已成,人或以示嘉则先生,嘉则大奇之,谓诸生中何得有此人?……且曰:‘叶生今日李王孙也!吾幸从年少中得一伯翼(杨承鲲),复得一叶生,吾足老矣!’”[22]叶太叔二十岁时,诗作得到沈明臣赞赏,与杨承鲲同为沈的弟子。杨承鲲病后,沈明臣作《柬伯翼》一诗传达关切,“唯有怀卿心独远,更思雪里策红藤”[23],得知其仅四十就病逝时,还作《闻杨三伯翼讣哭之二十韵》叹惋他英年早逝。
(二)呈现明代宁波的内忧外患与饮食特色
明万历年间内忧外患不断,仅水旱内忧多达439次。[24]万历三年(1575 年)夏,浙江多地发生洪水。《海溢篇》为诗人所见所感的记录:“大旱毕,可就饮。大潦高,可就食。惟有海涛溢,倏忽无羽翼。一夕千万里,破山流金石,吁嗟谁令海不波,时无姬公奈海何。”浙江杭州、嘉兴、宁波、绍兴四府,大水海溢,一夜淹没多地,人畜溺亡,房屋倒塌不计其数。
再观外患,影响最大的是沿海倭寇之乱。据《明神宗实录》载,自万历二年(1574 年)起,浙江多次受扰,倭寇先后犯宁绍台温等地。万历五年(1577年)十月,诗人作《北风行》:“甬东十月北风烈,一夜千家尽为雪。天明不见江上烟,日午尚觉行人绝。愁云叆叇冻不开,孩虎野麋空饕餮。东家老翁正僵卧,布被如冰脚如铁。岂无曲突谁置薪,纵有鹑衣亦不热……城南郭北悄无烟,万落千村尽流血……”战火之下,八九十岁的老翁僵卧一处无从取暖,小儿食不果腹成豺狼口中之物。百姓血染村落,存活之人又陷入水旱饥荒的绝境,朝廷出力也无济于事。诗人慨叹倭寇二十多年的侵扰,对此痛心疾首,以凄苦之调倾吐民众的苦难、社会的艰难和自己的痛心无奈,也为后人留下了倭寇之乱下社会现状的珍贵史料。
同时,杨承鲲诗中亦有关于社会风貌的描绘。明代宁波人日常饮食不离海产品,杨诗常提及螃蟹、蛤蜊一类的海产。当地人还利用自然优势,栽培茶树,境内四明山是理想的茶产地,诗人多次提及雀舌茶,表现出对茶饮的喜爱。诗中还提及芋艿、香芋、茭白、茅栗、莼菜、苔菜、山梨之类的常见食物,足见明代宁波人的饮食特色。如《小山归,得长文书及新诗二首兼惠茅栗如数,奉答》中的茅栗、芋艿等。此外,卷中收录了54 首与佛寺有关的诗作,多写寺庙及其周边之景,涉及宁波多地寺庙,对现在寺庙历史文化的考证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翠山寺,原名翠岩乾明院,始建于唐乾宁元年(894 年),南宋初年参知政事张孝伯曾重修,并始建翠山寺桥,现为宁波海曙区横街镇庄家溪自然村庄家溪上的古洞桥。诗人有《翠岩寺废址》:“谁开翠山寺,空有翠山桥。冰雪存丘壑,年华感寂寥。十方传宝额,三殿俨寒椒。得失元如此,无劳万虑饶。”此诗载于丁丑卷,由诗题《翠岩寺废址》和“冰雪存丘壑”可知,明代万历五年(1577 年)冬,翠山寺已毁,而桥尚存。
四、结语
《西清阁诗草》收录杨承鲲个人诗作,初刻本不早于万历十四年冬,现存两本乃万历二十三年十二月后刻成,两种版本相同。虽流传不广,但诗作内容丰富,可待研究。杨承鲲少负才名,为人随性狂放,特立独行。其科考不顺,怀才不遇,归乡后师从沈明臣。他交友广泛,重情重义,为人真挚,这种真性情在其赠答送别诗中可探一二。他受太白诗格和人格双重影响,形成了雄浑、清新、沉郁的诗风,虽承李白之风,但不一味追古,与谢榛不盲目拟古主张相和,能突破常规,创新出五、七言句等结合的格式,是明后期文学创作自觉发展的体现。同时,其诗作涉及的甬上文人,可结合相关文集作为地域文学的佐证。诗中对历史现实、社会时事以及民情风俗的记载,可见万历年间宁波社会现状和民众生活事宜,亦是后人研究明代宁波社会的第一手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