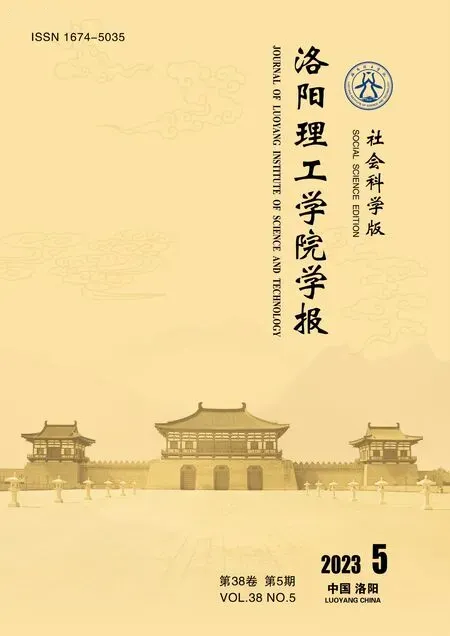史鉴与创新:中华传统法文化价值综论
王 东 阳
(中国政法大学 法学院,北京 100088)
源远流长的中华法文化,是中华法系、中国传统法制、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高度凝练与概括,“凝聚了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和法律智慧,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极其丰富的资源和宝藏”[1]。其“既融入了古圣先贤的政治智慧、法律智慧,又积累了治国理政方面的丰富经验与教训”[2]。中华法文化的丰富价值内涵也蕴藏其中。换言之,古代先贤的治理思想及相关论述、历代的法律制度与实践以及中国传统治理经验教训都可作为中华法文化价值的历史渊源。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从我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中探索适合自己的法治道路,同时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才能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夯实法治基础。”[3]37“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引导全体人民做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4]。中国法律史学的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历史借鉴,着力发掘存在于中华法文化中的跨越时空的民主性因素,为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一、民惟邦本的民本理念
早在先秦时期,古人认识到百姓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地位,在此后的文明演进路径上,民本理念成为历代治国思想的共识,成为传统法律思想与制度之渊源,并成为中华法文化的核心价值。
第一,民本理念贯穿历代治国思想中。《尚书》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周代统治者在反思商亡国的原因后强调“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秦汉时期,贾谊论证了仁义与恤民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正所谓“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汉代儒家董仲舒认识到国家应当体恤民情,满足民众的基本物质保障,不可与民争利,故“圣者则于众人之情,见乱之所从生,故其制人道而差上下也。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5]229。汉代以后,民本理念被历代统治者所奉行。
第二,民本理念构成传统法律的思想基础。民本主义是中国古代法律制度、思想与文化的“哲学基础”[6]118这一基础性观念早期体现为夏商时期的“天道观”,并发展为周代的“保民”“以德配天”观念。春秋战国时期,人道与天道趋于分离,历经先秦时期的重民思想,并经过儒家思想升华,逐步完备,形成了人本主义理论,其成熟标志为儒家的“仁学”:“夫君者舟也,人者水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汉代以后,儒家人本主义理论经过发展,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本主义传统。
第三,民本理念表现在历代法律制度中。首先,历代统治者重视民生。作为传统农业国,历代统治者往往采纳“重农”的政策,并辅之以相关的农业法律保障民生,如土地、畜牧、水利等方面的法律。其次,传统法律也彰显了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以儒家“亲尊”观为例,其在汉代便走向法律化和制度化。西晋时期服制制度开始出现在法律文本中,如“竣礼教之防,准五服以治罪”。隋唐时期,随着中华法系走向成熟,对于弱势群体的保护被写入法律文本,如赋役减免制度规定,“若老及男废疾、笃疾、寡妻妾、部曲、客女、奴婢及视九品以上官,不课”,“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7]882。
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贯穿中华法文化始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指出,良法就是“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贯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8]。我们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中华传统法文化中以民为本的价值理念,进一步推进我国法治建设。
二、德主刑辅的德法共治理念
德法互补是中华法文化和中国法律传统的重要特点与价值之一,二者的交融与互构提升了传统国家与社会治理的效能。在传统国家治理中,通过法律进行治理是一种重要的手段。但德法结合的方式,能够有效填补法律的局限,扩展治理领域。
我国传统的国家治理是“礼乐政刑”综合为治,而“法治”(或是“刑治”)是重要方式之一。先秦时期,管仲提出“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措而已”的观点。韩非子将法、势、术三者结合,使先秦法家理论得以完备,其指出法律对富国强兵的重要作用,“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9]27。汉代之后,通过法律进行国家治理成为历代统治者的共识。德法结合是传统国家治理的重要特点。“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自汉代“法律儒家化”以来,德法共治、儒法结合成为传统国家治理的重要特点,“归纳言之,中国法律之儒家化可以说是始于魏、晋,成于北魏、北齐,隋、唐采用后便成为中国法律的正统”[10]399。作为中华法系的集大成之作,《唐律疏议》开篇明义,明确了“德礼”与“刑罚”各自的功用:“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
德治有效地弥补了传统法律的不足。与法律不同,德治重在教化,其作用方式是潜移默化,相比于道德的预防性与心理干预性,法的作用通常体现为补救性与行为干预性,仅能达到“民免而无耻”的程度。德与法有其自身所擅长的作用领域,正如司马迁所言“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这就需要发挥二者的优势,将德与法有机结合,“国家治理与社会管理既需要行为规制,也需要精神引导”[11]161。在中华法文化发展进程中,德法共治历经多个历史阶段并最终趋于定型[6]2。无论是从历代的治理思想中,或是传统的国家与社会治理中,我们都能发现德法互补发挥的积极作用。“法安天下,德润人心”。在我国法治建设中,必须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要义。
三、实用主义的经世致用理念
中华法文化呈经世致用的特点,即法律应当随着国家与社会发展而不断完善,继而有效回应国家与社会治理面临的新情况与新问题。不同封建朝代法律思想与制度既有内在的联系性,也有不同时期的特殊性和创新性。
第一,在思想层面,中国传统法律的经世致用。先秦时期,商鞅提出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应采用不同的治理手段,“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12]7。作为先秦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认为制定法律应当因时制宜,“古今异俗,新故异备”[9]529,“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9]524,“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9]529;在司法过程中应当“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9]94。南宋时期,《洗冤集录》开篇名义:“狱事莫重于大辟,大辟莫重于初情,初情莫重于检验。”
第二,在制度层面,中国传统法律的经世致用。一方面,传统法制具有因时定制的特点。在法律制定层面,历代王朝在承继前朝法制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法律。唐宋时期,中华法系走向成熟。虽然明清时期国家法制趋于健全,对社会事务实现了全面涵盖,但国家与社会治理仍面临社会变迁所引发的新问题,而法律对于新的社会问题也做出了回应。清代通过制定和修改条例的方式,以加强法的社会适应性,而条例的生成通常基于具体案件或是臣工议奏,这使法律更加实际。另一方面,传统法制具有因地制宜的特点,具体表现为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民族立法间的多元共构。清代中央层面形成了以《会典》为核心的制定法体系,地方结合自身特点制定了以省例为核心的地方性法律体系,如《江苏省例》《福建省例》《治浙成规》等,以则例为核心的民族立法,如《钦定理藩院则例》《钦定回疆则例》等。这些地方立法、民族立法丰富了中华法系,推动“多元一体的中华法文化”[13]的形成。
中华法文化中的经世致用理念贯穿中国法律思想、制度以及学术的发展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需要系统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化,更加需要深刻把握人类发展历史规律,在对历史的深入思考中汲取智慧、走向未来。”[14]
四、公平正义的法律公平理念
法律公平理念是中华法文化的又一重要特点,即通过法的制定与实施,定纷止争,彰显正义。自古以来,法便成为国家与社会公平正义观念的重要制度载体。具体而言,公平正义理念体现于历代的法律思想、法律制度与法律实践。
法律公平贯穿传统法律思想。先秦法家不乏关于法律公平的论述,如慎子所谓“法者,所以齐天下之动,至公大定之制也”;商鞅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应当实行统一而非差等的措施,“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12]138,“上壹而民平”“上壹则信”[12]11;韩非认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9]33。儒家主张的法律公平与法家的主张略有区别,其强调一种实质公平,注重在人际关系差序格局的基础上相对的、实质的法律公平。因此,法是否“公平”在儒家学说相关文献中往往表达为刑罚是否“得中”“允协”。《中庸》有言:“不偏谓之中。”孔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许慎在考释“法”的古体字“灋”的源流演变时,认为“灋,刑也,平之如水”。
法律公平贯穿传统法律制度。“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9]451自成文法公布伊始,法律便成为解决社会纠纷、彰显社会正义的重要标准。汉代儒家主张成为国家官方学说后,法律公平理念逐渐在制度上表现为“内儒外法”的形式。一方面,在法律制定层面,国家通过制定法律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如《唐律疏议》中规定了对老人的赡养制度、对残疾人的收容制度、对儿童的保护制度等。又如清代法典《大清律例》展现对侵犯儿童罪行的严惩和从重处理态势,对于拐卖儿童行为处以死刑:“若以药饼及一切邪术迷拐幼小子女,为首者立绞;为从,发极边足四千里充军。”[15]416另一方面,在具体司法过程中,基层有司衙门也会通过具体立法对显失公平的情形予以纠偏。如汉代伊始便形成“春秋决狱”的传统。明清时期,尽管律例是法官断狱理讼的重要依据,但是仍会结合情理协中裁判。
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牢把握社会公平正义这一法治价值追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16]新时代赓续法律公平理念对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
五、以法治官的权责统一理念
以法治官是中华法文化的另一重要价值理念。传统社会,作为君主行使国家权力的媒介,官吏素质直接或间接影响国家治理效能。正所谓“在良法与善治之间还需要贤吏这一核心环节来进行沟通”[2]。若无良吏,“善法”也无法推行,又如白居易所言,“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因此,如何整顿吏治成为历代国家治理面临的重要问题。在诸多主张中,法律成为历代治吏的重要举措,具体而言,国家通过制定法律约束和规范官员行为,法律又是官员进行社会治理的重要依据。
国家通过制定法律约束官吏。首先,传统法律中关于职官的设置、编制、任免考选、考课奖惩、俸禄休致、官吏的监督与约束、司法裁量等事项通常在法律中有严格规定,这些规定约束了官员的行为,使之可预期、可控制[6]182。官员行为是传统法律的主要规制对象。“中国古代采取‘官法同构’的制度建构基本模式,根据国家事务管理需要,设置官制;根据官吏治理需要,建立法制,进而实现‘治官’与‘治民’的双重目标”[17]。清代的国家通制政书《清会典》结构以清代的中央“六部”体制为标准,形成“六事法体系”,这一体系实现了国家对文武百官的全面调整,通过“治吏”实现“治民”。
官吏依照法律进行社会治理。在传统社会治理中,法律为官员参与社会管理提供依据和参照。一方面,法律是整顿吏治的重要抓手。秦汉以来,吏治成为历代统治者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历史上往往通过建构监察制度规范官员行为。汉初便制定了专门的监察法,如《监御史九条》《刺史察举六条》用于规范地方官的行为,杜绝擅权[18]。唐代的监察法制有了进一步发展,制定了《巡察六条》和《风俗廉察四十八条》等。明清时期,有《宪纲》四十条、《宪纲条例》、《抚按通例》、《钦定台规》等监察法律,其中《钦定台规》达到法典化的水平[19],这些法律对于规范和约束官员行为起到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治狱理讼是官府参与社会治理的主要方式,尤其是对于基层政权而言[20],在此过程中,法律成为官员裁断案件的重要依据。春秋战国时期,成文法公布,司法观念上的类推适用逐渐转为援法定罪,且这一观念经后世得到不断发展。秦汉伊始,援法定罪成为重要的狱讼原则,随着法律的不断完备,隋唐时期的《唐律疏议》,明清时期的《大明律》《大清律例》更是涵盖狱讼审断程序与实体的方方面面,不仅为法官审断提供依据,同时约束法官的任意裁量。治吏是“良法”与“善治”的中间环节,在确立“良法”的基础上,只有通过法律规范执法者的职责,权力才能有序运行,法律才能在具体社会实践中发挥应然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