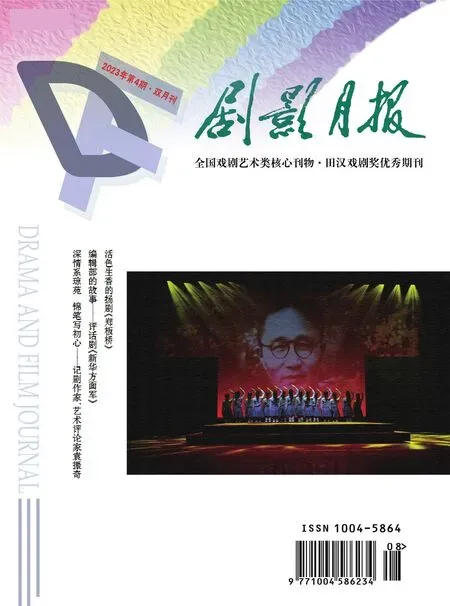优雅的傀儡
——薇拉·齐蒂洛娃电影《雏菊》的木偶美学分析
■段心玫
1966年,捷克女导演薇拉·齐蒂洛娃完成了电影《雏菊》,这部作品不仅作为齐蒂洛娃早期先锋电影的代表而蜚声国际,更奠定了她在“捷克新浪潮”电影运动中不可替代的“旗手”地位。《雏菊》以极具风格化和实验性的视听语言、充满隐喻与讽刺的镜头表现,以及滑稽与严肃并置的哲学表达,成为“捷克新浪潮”乃至世界影史中独树一帜的存在。
《雏菊》影片结尾的字幕显示“这部电影献给那些精神生活完全混乱的人”。齐蒂洛娃曾表示“《雏菊》是一部告诫年轻人的电影,它批判而非赞扬这两位少女”,并将《雏菊》自称为“一部闹剧式哲学的纪录片”[1]。《雏菊》的世界是通过两位少女的形象来建构的,因此国内外学者对薇拉·齐蒂洛娃和《雏菊》的研究视角多集中于女性主义、性别政治及影片的东欧式现代文化批判。
值得注意的是,“木偶”和“木偶戏”作为《雏菊》的贯穿意象和内在美学手段鲜少被研究者关注,尽管两位少女“玩偶”“洋娃娃”般的形象在《雏菊》的评论和女性主义研究中常被探讨,人们认同“齐蒂洛娃希望将两个经典的少女形象刻画成为一种没有感情的、容易被摆布的、温驯的玩偶形象”[2],但不同于在易卜生《玩偶之家》中被认为是“受控于男权社会的玩偶”的娜拉,齐蒂洛娃在《雏菊》中塑造的两个看似易于摆布的“玛丽”,实际上具有比“玩偶”更特殊、更复杂且超越了女性主义批评范畴的身份属性——“木偶”“傀儡”以及“木偶师”或许更能定义她们的存在本质,“木偶”并不是对“玩偶”的简单挪用,而是在齐蒂洛娃独特的镜头语言与木偶戏剧艺术的结合下,开辟出的全新意指空间。
一、被操纵的木偶:《雏菊》的政治隐喻
木偶,即“偶”“傀儡”,美国木偶剧导演比尔·贝尔德在他的《木偶的艺术》中定义“剧场木偶”是“由于人的操作在观众面前活动起来的,不属于动物范畴的人形。”[3]木偶戏剧艺术的研究者通常认为,木偶是人的缩影和变形,它不仅是人类的隐喻,而且通过人与木偶的关系,对人类自身进行了深刻的哲理思考与理性研究。[4]因此,木偶是人的孪生体,是人类灵魂的载体,它向我们传递了更为深刻的信息,影射出文明世界中的人及人与他人、与世界的关系。
木偶戏是捷克最重要的传统艺术之一,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纪,见证了捷克民族的历史变迁,在统治势力更迭、国家遭到入侵和吞并时,木偶戏更成为捷克人民保护文化遗产、保存民族语言的重要工具。[5]在斯大林主义限制真人影片内容的时期,木偶从剧场延伸到荧幕,将其政治功能转移到影像中,产生了大量具有政治讽刺意味的木偶动画,导致捷克动画比电影更容易触碰现实。
木偶本身具有较强的政治意味和后现代隐喻,木偶的面孔似人而非人,专心的神态和僵直的动作让它具有神秘性。一方面,木偶作为被操纵的对象,具有其独有的“偶性”(或“傀儡性”),即在偶师的操纵下造成僵死、机械的效果。捷克动画大师杨·史云梅曾在访谈中强调,木偶根植于他的精神土壤,他认为木偶完美地象征了当代人的性格和生存状态,这种人在现实中被外界操控的状态,正如当时捷克现实中的每个人。[6]
《雏菊》作为一部极具前卫性和实验性的电影,通过一系列的视觉表现手法和叙事技巧,向观众呈现出一个充满反叛和抗议情绪的捷克社会,《雏菊》中的玛丽就是被外界力量操纵的两只木偶。影片开头,固定中景展示两位穿着比基尼泳衣的少女倚靠木板并排而坐,她们四肢无力、面无表情,两腿直直叉开,玛丽一号睁开眼睛,机械地抬起右手伸进鼻孔,接着玛丽二号拿起小号吹出了一个音节,每当她们二人活动肢体的时候都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她们的关节仿佛木制门的铁栓,但身体的其他部位仍然松软无力,就像没有绳子牵引的木偶。除了肢体动作,两位玛丽时常从面无表情瞬间转变为哈哈大笑,如同没有过度表情的木偶。随着两位玛丽接连不断恶作剧的进行,木偶操纵师的面貌也逐渐浮现,有种不可言说的力量支配她们一步步走向更彻底的堕落:醉酒捣乱、捉弄男人、暴饮暴食、欺诈偷窃、焚烧房屋……直到在无人的宴会厅上演最后的狂欢。这种“操控”的主体不仅有她们自身的食欲、情欲等人类欲望,更有堕落、僵化、无聊的现实世界,我们在这种无法挣脱的“操纵”中能看到现实和政治制约中的个体。
木偶本身没有生命,是木偶操纵师为它们赋予了声音和动作,在木偶戏剧舞台上,木偶操纵师作为演员的主体性地位不断被强调,新型的木偶表演者摒弃了遮挡在身前的帷幕,成为演出的主体替木偶说话,这种人偶同台的演出方式冲破了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戏剧模式,转变为布莱希特史诗剧式的“叙述性木偶戏”,其间离效果更加强调了木偶的政治性。
《雏菊》中,导演齐蒂洛娃作为最显而易见的木偶操纵师时常在场,无处不在地施加她的力量和意志,在天马行空的蒙太奇剪辑、滤镜效果以及复杂的拼贴下,两位玛丽木偶本身的表演很难连贯进行,频繁的跳接镜头让影片的时间、空间失序而随意,观众很难全神贯注地卷入传统的故事“幻觉”中,反而在导演的有意呈现中不断被刺激出思考与批判的欲望。影片开头即是军乐号声中,大型机械的铁轮与齿轮在转动,随后接连切换为流弹四射、飞机轰炸等画面,与结尾吊灯坠落后的画面相呼应,再结合开场两位少女经典的“世界在变坏”对话,能够感知到导演有意以此隐喻一个秩序遭到摧毁、意义无限缺失且道德和价值观失范的社会,从而引发两位少女之后不断挑战“堕落底线”的焦虑实践。
因此,齐蒂洛娃和两位玛丽构成了一次叙述性木偶戏的表演,木偶在诸多力量的操纵下完成一次政治隐喻,而导演以独具风格的视听语言完成后现代批判与暗示。在这次表演中,木偶形象成为表现人与政治、都市文明、机械文明冲突以及个体异化的表征。正如洛特曼对木偶文化演进的描述:“我们的文化意识中形成了两种傀儡:一种指向安逸的童年世界,另一种则暗示着虚假的生活、僵化的动作、死亡和矛盾。前者关注民俗、童话和原始,后者使人想起机器文明、异化、二重性。”[7]
作为“被操纵的木偶”,两位玛丽使《雏菊》具有喜剧与闹剧的美学特性,旨在打破观众的惯性思维,引起他们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使木偶美学呈现出一种游戏性和幽默感,使得电影更具吸引力和趣味性。影片中玛丽们的行为轻松而滑稽、敢想敢做,她们的面部表情和躯体动作极不协调,产生了强烈的反差、尖锐的矛盾,造成了可笑性和滑稽感,木偶般的演员、面具式的脸孔,以及与她们形象截然相反的疯狂行为,共同造成了《雏菊》猛烈的视觉冲击力。
二、被异化的木偶:《雏菊》的双重假定
如果说“人偶同台”只是将木偶师请到台前的木偶戏,那么“人偶结合”则是“人戏”与“偶戏”之外的第三种特殊表演形式。不论是中国还是欧洲,都存在人模仿木偶动作、人变成木偶演出的表演形式。中国福建的高甲戏傀儡丑就是人模仿木偶的典型例子。演员在舞台上模仿提线傀儡的动作,且形成了成套的表演程式,并由此出现了一个新的行当——傀儡丑。在欧洲,早在20 世纪,戈登·克雷就提出了将演员作为“超级傀儡”的概念,俄罗斯的布拉吉诺剧院也曾上演过人模仿偶从而暗指人被异化成木偶的表演。
从“人偶”到“偶人”,从“真傀儡”到“仿真傀儡”,这种新型木偶戏强化了表演的假定性与剧场性,甚至实现了“倍增”后的双重假定。洛特曼认为,我们对傀儡戏的认识是在与活人演出的戏剧的相互关系中去理解接受的。因此,如果活的演员扮演人,那么傀儡在舞台上就是扮演演员,傀儡则成为“扮演的扮演”。如果傀儡在舞台上是“扮演的扮演”,这种效果为“倍增诗学”,那么真人演员在舞台上模仿傀儡就成了“扮演的扮演的扮演”,即“再次倍增的诗学”。其舞台效果对假定性的强调,将进一步地将观众与舞台、角色间离开来,破除幻觉并启发他们以批判的态度进入思考。
《雏菊》对木偶戏的极致运用就体现在:剧中的两位玛丽不仅仅是“被操纵的木偶”,更是“被异化的木偶”,或者说是套着木偶外壳的真人演员,她们同时是被操纵的对象和主体,这种双重身份的复杂性混淆了观众的视听,也打碎了她们自身的理性与身份认同,人即是偶,偶即是人,时真时假,矛盾而统一。她们与“木偶外壳”时而和平共处,时而激烈对抗。
影片中,两位少女多次表现出自己的“存在焦虑”——她们究竟是否存在?她们把从杂志上剪下来的纸片人扔进装满牛奶的浴缸,玛丽一号问:“甚至连一个人不再存在也没关系吗?”她们对坐在浴缸中展开对话:
你怎知我们是我们?你存在又从何知晓?
因为有你。
是吧,不然你证明不了。我们完全没有在这里的工作,没有证据证明我们的存在。
她们彼此成了对方存在的证明。而当她们来到郊外,对着田野里干活的农夫呼叫却没有得到注意,在街上行走的时候又与许多骑单车的男人擦肩而过,玛丽一号若有所思道:“我在想为什么农夫没有注意到我们”“你知道什么最让我担心吗?就是我们对他来说是不可见的!我们已经蒸发了,为什么他没有注意到我们?为什么骑单车的人没有注意到我们?”
她们不断逾越着日常生活的边界,试图寻找自己存在的证明,背后隐含的是对自己主体性的怀疑和探索,就像一只木偶试图找寻自己生命气息的存在,而这种哲学式的追问带来的是一次次主客体权力的扭转,她们开始用主体的操纵实践来证明自己作为“活人”的存在。
影片中两位玛丽的乐趣之一是捉弄一个又一个男性,她们纯洁无知的外表看似被男性客体化的对象,但实际上男性只是她们满足进食欲望的手段,在玛丽二号与第一位老男人约会时,玛丽一号表现出了典型的进攻性,她步步紧逼质问男人、放肆吃喝,消费并审视着对方,男人对玛丽的这种“操纵权”十分不适,玛丽反而同时作为木偶师和木偶客体化了对面的男人。而当转向室内,玛丽用剪刀把一大堆香肠、鸡蛋等食物剪碎,同时对电话里追求者的情话无动于衷,无论这里的香肠是否是男性生殖器官的隐喻,玛丽果决而暴力的行为活像一个跳脱于故事之外的木偶师,用平静的目光和“剪”的行为进行自己的木偶表演。
因此,两位玛丽的木偶属性变得愈加复杂,她们同时是木偶和木偶师,包含迎合观看与破坏观看的双重气质,具有“扮演木偶”和“模仿木偶”的双重假定性,在前一节所述“被操纵的木偶”之上实现了更复杂的“异化”,蕴藏着强烈的主体意识和反抗性力量。继承了“人偶结合”的木偶戏,两位玛丽模仿木偶的表演带有鲜明的价值判断色彩,包含更深刻的哲学思考:人异化为偶的原因不仅仅有政治与机械文明的制约,更有归属感被剥蚀的身份危机和精神困境。
作为“被异化的木偶”,两位玛丽使《雏菊》具有悲剧和严肃剧的美学特性。《木偶剧场心理学》中提到观众接受木偶剧的两种方式:一是把木偶当成无生命的物体,二是把木偶看成活生生的人,而当我们以后者的接受模式看待木偶时,会因为木偶“过于像真实的人类”而产生惊奇感和恐惧感。过于真实的木偶尚且可怖,何况具有真人演员属性的玛丽,她们的双重身份使电影在刺激与热闹之外,时常具有迷惘、悲伤的观感以及严肃的批判和思考。
三、优雅的木偶:《雏菊》的道德自由
德国剧作家、小说家、诗人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写过一篇著名的论述散文《论木偶戏》讲述了作者偶遇一位舞蹈家并和他谈话,这位舞蹈家经常在集市看那种下等人才看的木偶戏表演,但舞蹈家却向作者强调“木偶比活人演员更优雅”,“关于优雅,人是比不上木偶的”,他说一个舞蹈家能从木偶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两个人就在这样的对谈中从木偶戏引申到一切艺术的规律和奥秘。
克莱斯特在文章里提问“舞蹈演员没有手上的操纵线,如何像木偶一样操纵肢体动作呢?”舞蹈家回答说,木偶师并非需要一个个去摆弄木偶的肢体,而是“每个动作,都有一个重心;把握住木偶的这个内在的重心就足够了;跟钟摆似的四肢,不用去动它,它自己就会机械地做出动作”。除了木偶师只将心灵落在简单的“重心”之外,文中认为木偶具有人类无法企及的自然和真实,木偶只会以最真实的方式行动,从不存在意志和行动之间的脱节,而人类总会因为克服不了身体和心灵的矛盾而显得矫揉造作,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精神,精神就不会出错”。
克莱斯特强调,恰恰是“理性”和“智慧”的能力使我们被逐出了伊甸园,而只有“再吃一口智慧树上的果子”——对知识和理性否定之否定,才能使我们再次重返天堂。这与《雏菊》中两位玛丽的行为不谋而合,她们作为两只木偶,拥有普通人不具备的纯真和直接,具有《论木偶戏》文中的“优雅性”,她们摒弃了良心和罪恶感,丧失了理性和判断力,她们的“意志”和“行动”之间就像木偶一样没有任何脱节,所有的道德规范和社会期待只是她们的玩物,但她们重返的“天堂”并不是克莱斯特所指艺术上的纯粹与美,而是一种免于被惩罚、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道德空间。
影片场景不断在河边、房间、餐厅、洗手间、站台间跳跃,时间也在不规律的时钟嘀嗒声中呈非线性状态,导演有意塑造了一个非正常世界,而两位玛丽似乎拥有随意掌控这个世界时间、空间的能力。不仅如此,她们的饮食、睡眠、沐浴等生活作息并不规律,她们没有正常生活的能力,却永远以光鲜亮丽的姿态出现,在两人互相用剪刀攻击对方的片段里,她们的身体就像木偶的身体一样,可以在没有痛苦或后果的情况下被拆卸和改造。在这些前提下,一切对她们的道德要求和审判都是空虚的,道德本身也是可戏谑的,更不必提供解决方案,在道德空间里她们只是死去的木偶,只关注一个“重心”的木偶。
利用这种道德自由,导演可以将两位玛丽的“堕落”推向极致,呈现出秩序崩坏的种种后果,她们的能动性可以改变世界但不受任何惩罚,并且将观看电影的观众也拉入其中成为共犯,我们正在看玛丽的“堕落”,而自己也作为旁观者观看着这场奇观,欣赏她们的破坏性行为做出的“贡献”。就像在木偶剧场里,观众需要主动将明显分离的木偶和木偶师的表演统一成一体,《雏菊》也因观众的参与而更加完整。另外,在当时捷克严格的政治审查和官方控制下,这种道德上的自由空间也在一定程度上为齐蒂洛娃提供了保护,尽管《雏菊》仍因“浪费食物”的罪名被禁映,但齐蒂洛娃也在之后的致总统信中为自己辩解:《雏菊》是对两位女孩抱有批评态度的道德剧,它展示了邪恶不一定会在战争造成的破坏狂欢中表现出来,更隐藏在日常生活的恶作剧中。[8]
作为“优雅的木偶”,两位玛丽让《雏菊》的滑稽与严肃得以统一,她们没有任何负担和任务,以木偶的优雅性邀请观众自由地感受和判断,她们可以带来欢乐、幽默和滑稽,也能让人联想起广阔人生的悲剧,感受到现代性焦虑和对既有文化、道德框架的不满意、不信任。这种杂糅的观感就是齐蒂洛娃独具个人风格的电影实验,也是她所描述的“一部闹剧式哲学的纪录片”。
洛特曼在《文化体系中的傀儡》一文中说:“在一种文化体系中,一个给定的概念原有的作用越是具有本质意义,它隐喻的意义也越丰富,这种意义可以非常富于侵略性,有时甚至可以用来形容一切事物。傀儡就是这样一种根本性的概念。”[4]这段话指出,具有丰富的隐喻意义的木偶在文学艺术中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空间。他接着写道:“生与死、复活与僵化、灵活与机械、虚伪的生活与真诚的生活之间的对立在当代艺术中得到如此广泛与多样的反映,以至于越来越明显。”这是木偶哲学的基本内容,也是本文分析《雏菊》木偶美学的根基。
木偶美学是导演齐蒂洛娃独特的诗性智慧,木偶构成了薇拉·齐蒂洛娃电影《雏菊》的核心隐喻,也实现了整部影片的核心美学效果。“被操纵的木偶”体现了玛丽作为被操纵对象的政治意味,使《雏菊》具有喜剧与闹剧的美学特性;“被异化的木偶”描述了玛丽主体与客体身份统一的复杂性,使《雏菊》具有悲剧和严肃剧的美学特性;“优雅的木偶”指涉影片构建的特殊道德空间,让《雏菊》的游戏性与严肃性得以统一,赋予其悲喜交融、平静自由的美学特征。木偶美学的建构不仅让《雏菊》更切中作者的生命体验,更突显了作品的诗性智慧,也更能切近文艺本体,更好地揭示齐蒂洛娃的创作规律,齐蒂洛娃也以此完成了这部生动而多义的影片,启发我们思考个体存在、人类境遇和更深入的现代性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