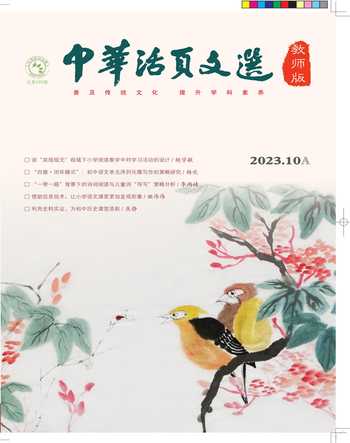刘禹锡的朋友圈
蔡丽霞
摘 要:对刘禹锡《陋室铭》中“白丁”的释义,笔者从教的苏教版教材译为“平民。知识浅薄的人”,部编教材译为“平民。这里指没有功名的人”。这一改动是否恰当,笔者存在疑问和异议。华东师范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教师陈明洁曾撰文从文字释训的角度论述过这个问题,笔者的辨析想从刘禹锡其人和创作《陋室铭》目的的角度,探访刘禹锡的朋友圈到底是怎样的人。
关键词:白丁 刘禹锡 《陋室铭》 DOI:10.12241/j.issn.1009-7252.2023.19.010
一、生平经历论交友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句话写的是刘禹锡在陋室中的交友情况。与什么样的人交友往来,首先我们从他的生平经历来看。刘禹锡从小聪明勤奋,在贞元六年(790)十九岁前后游学洛阳、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的声誉,贞元九年(793),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这一年,他刚好二十一岁。两年后再登吏部取士科,释褐为太子校书。贞元十八年(802),调任京兆府渭南县主簿,不久迁监察御史,当时韩愈、柳宗元均在御史台任职,三人结为好友,过从甚密。从这一段早年生活经历不难看出,刘禹锡可谓是科考之路畅达,仕途开挂,交友俱为博学之士。柳宗元二十岁进士及第,韩愈二十四岁进士及第,比刘、柳二人早一年。古语有云,“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在唐代,有这样一种现象,缙绅虽位极人臣,而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其推重进士,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此三者,在当时都可谓是前程似锦,又有名望。
依据这样的早年生活经历可以看出,与刘禹锡交往的应该都是一些博学之士,而非知识浅薄的人。“白丁”释为知识浅薄之人是可以理解的。页下注释“平民”,也可以理解为知识浅薄的人。但是注释后面特别指出,这里指没有功名的人。这里我们又要从古代的功名制度加以讨论。
在古代,平民百姓没有功名,自然可以理解;反之,没有功名之人,难道都是知识浅薄的平民吗?这个问题值得深思。古人云“学而优则仕”,言外之意,功名的取得一般都是通过科举考试得到。以科举制度已经相对完善的明清时期来看,整个科举考试一共分为五个等级,分别是童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这层层选拔,就算全部顺利,一次通过,也得考上很多年。难怪有孔乙己没有捞到秀才被人耻笑,范进中举之后喜极而疯这样的悲剧。而在刘禹锡生活的唐代,科举制度虽然没有像后代那样严密完善,但想要考取功名也并非易事。唐代科举有很多科目,主要科目则是明经和进士两种。前文提到,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就是说,五十岁考上进士都算年轻的,可见考取功名的难度。而刘禹锡与柳宗元同榜进士及第,同年登博学鸿词科。这时他才二十岁出头,可见他的高才。
柳宗元是大文学家,自不必说,和刘禹锡交情甚好的还有大诗人白居易,柳宗元、白居易这样的饱学之士都是有功名的,而科考落榜之人,虽然没有博得功名,却也藏龙卧虎,能配得上刘禹锡交友的大有人在。就拿唐代來说,李白没有参加过科举考试,他求仕,走的是“终南捷径”;孟浩然四十岁游长安,应进士不第,归隐田园;杜甫屡试不第……这些人虽然都没有功名,但是刘禹锡会和他们做朋友吗?在他的那间陋室里,我想这些人都是饱读诗书,胸有鸿墨的人,他们肯定有资格进入刘禹锡的朋友圈。
二、志趣相投谈交友
接下来,笔者从刘禹锡的性格特点来谈谈他朋友圈的特点。刘禹锡虽然早年得志,但在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唐德宗驾崩之后,原太子侍读的王叔文、王伾素有改革弊政之志,刘禹锡与王叔文相善,其才华志向尤其受到王叔文的器重,于是他就和柳宗元一道成为革新集团的核心人物。
随着改革的失败,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此后的生涯里,刘禹锡是先后被贬各地,从朗州司马到召回长安,又因游玄都观写讽刺诗,迁为连州刺史,后来还当过夔州、和州刺史,直到文宗大和元年(827)才回到长安。刘禹锡在《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用“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记录了这样漫长的贬黜经历,但是在诗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中,他自比“沉舟”“病树”,目光却看到“千帆过”“万木春”这样充满生机活力的场景,彰显了刘禹锡刚健不屈、乐观积极的性格特点。不仅如此,刘禹锡还是个耿直爽快的人,能讥讽当朝官场的不良风气。我们来看一段史料: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王承治《唐诗评注读本》评价说:“此诗借种桃花以讽朝政。栽桃花者道士,栽新贵者执政也。自刘郎去后,而新贵满朝,语涉讥刺,执政者见而恶之,因出为连州刺史。”
再游玄都观
余贞元二十一年为屯田员外郎,时此观未有花木。是岁,出牧连州,寻贬朗州司马。居十年,召至京师,人人皆言有道士手植仙桃,满观如红霞,遂有前篇以志一时之事。旋又出牧,于今十有四年,复为主客郎中。重游玄都,荡然无复一树,唯兔葵燕麦动摇于春风耳。因再题二十八字,以俟后游。时大和二年三月。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近代王文濡评价说:“前因看花诗,连遭贬黜,今得重来,而新进者随旧日之执政以俱去矣,因复借此以讽之。”(引自《历代诗评注读本》)
再来看一段史书记载:
久之,召还。宰相欲任南省郎,而禹锡作《玄都观看花君子》诗,涉讥忿,当路者不喜,出为播州刺史。诏下,御史中丞裴度为言:“播极远,猿狖所宅,禹锡母八十余,不能往,当与其子死诀,恐伤陛下孝治,请稍内迁。”帝曰:“为人子者宜慎事,不贻亲忧。若禹锡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对,帝改容曰:“朕所言责人子事,终不欲伤其亲。”乃易连州,又徙夔州刺史。……由和州刺史入为主客郎,复作《游玄都》诗。
——《新唐书·刘禹锡传》
刘禹锡作诗抨击时弊,涉及讥讽,惹怒当朝者,连皇帝也责罚他,可见他是一个多么耿直的人。一个被贬之人,不懂得谨言慎行,不考虑自己八十岁的老母亲,坚持说真话,刺痛当朝者,实在不算是“明智”的人。《旧唐书》有记载:
禹锡晚年与少傅白居易友善,诗笔文章,时无在其右者。常与禹锡唱和往来,因集其诗而序之曰:“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予不量力,往往犯之。夫合应者声同,交争者力敌,一往一复,欲罢不能。”
——《旧唐书·刘禹锡传》
白居易称刘禹锡为“诗豪”,一“豪”字写出了刘禹锡的性格和诗文特点。在文学创作的理念上,白居易和刘禹锡有很多共鸣。他们都在现实主义的创作道路上前行,二人后期交往颇多,是朋友圈唱和较多的好友。白居易在文学史上和刘禹锡并称白刘,和元稹并称元白,而他们的现实主义诗歌创作,被称为“新乐府”,也就是继承汉魏古乐府诗歌的现实主义精神,以诗歌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笔锋森然。
关于白居易,我们也知道他和刘禹锡一样“同是天涯沦落人”,有着一样的被贬经历。此外,白居易任左拾遗时,频繁上书言事,写出大量的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过失。这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向李绛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唐宪宗广开言路。刘禹锡和白居易都能针砭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所以志趣相投。
刘禹锡的刚健耿直就像是一个小宇宙,能量爆满,这样的经历和性格,假设让刘禹锡遇到清代的蒲松龄,会不会加他为好友呢?我们来看看蒲松龄的经历、性格:
蒲松龄九岁开始读书,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不过,此后蒲松龄在科场奋斗数十年,届届都不中。此后,蒲松龄不再参加科考,专心在家著书立说,晚年留下了一部洋洋洒洒数十万言的《聊斋志异》。郭沫若评价聊斋:“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蒲松龄虽没有功名,但他的才华和孤傲、不同流俗的狷介“士气”,与刘禹锡可谓是志同道合,志趣相投,这样的朋友刘禹锡肯定会喜欢。
古人云“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知己之交必为秉性一致的人,志同道合的人,交友很多时候在于性格合得来,这和是否有功名关系不大。宕开一笔,我们都知道苏东坡的一生也都在仕途宦海中浮沉,但是苏东坡所到之处几乎皆可结交为朋友,林语堂在《苏东坡传》中写道:“吾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是好人。”苏东坡与人交往不拘身份高低,这也是性格使然,否则凭他苏大学士的才学,能有几人进得了他的朋友圈。
三、创作意图看交友
最后,笔者想从刘禹锡创作《陋室铭》的用意来阐述“白丁”的释义问题。该文的由来有个故事:《陋室铭》作于和州任上(824—826)。《历阳典录》云:“陋室,在州治内,唐和州刺史刘禹锡建,有铭,柳公权书碑。”作者曾经参加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藩镇割据势力。革新失败后,陆续被贬,最后至安徽和州当刺史。和州知县见刘禹锡一路被贬,故意刁难他。和州知县先安排他在城南面江而居,作者不但无怨言,反而很高兴,还随意写下两句话,贴在门上:“面对大江观白帆,身在和州思争辩。”和州知县知道后很生气,吩咐衙里差役把作者的住处从县城南门迁到县城北门,面积由原来的三间减少到一间半。新居位于德胜河边,附近垂柳依依,环境也还可心,作者仍不计较,并见景生情,又在门上写了两句话:“垂柳青青江水边,人在历阳心在京。”
那位知县见其仍然悠闲自乐,满不在乎,又再次派人把他调到县城中部,而且只给一间只能容下一床、一桌、一椅的小屋。半年时间,知县强迫作者搬了三次家,面積一次比一次小,最后仅是斗室。作者遂愤然提笔写下这篇《陋室铭》,并请人刻上石碑,立在门前。
由此可见,该文是用来回击知县欺人太甚,表明自己的志趣情操高尚,用自己的“德馨”来光大陋室不陋的形象。所以本文虽只有八十一个字,却处处可见刘禹锡的“狂”与“豪”。开篇用山水比兴,起笔不凡,将自己的陋室和永恒的山水类比,立于天地之间不倒,这其实就暗示陋室主人品德彪炳天地间。陋室环境,在别人看来也许是苔痕满阶,荒草满地的荒芜,而在刘禹锡的眼里确是隐居地的清幽,青绿中不乏生机与明媚,那就是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有人说,想认识一个人,可以看看他交往的朋友。“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与博学之人在这陋室里谈笑,那是一种高雅的交流,是思想的交流,是价值观的交流。就好比是冰心的名篇《太太的客厅》,文中“我们太太的客厅”来访的都是哲学家、画家等“高雅之士”,而且在“我们太太的客厅里”都是要说英文、法文的……排除讽刺不说,这小客厅确实是“谈笑有鸿儒”,是真高雅。
“往来无白丁”就真的排除没有功名的人吗?刘禹锡写此文时,唐王朝正一天天地衰落下去。在宫中,宦官专废立之权,皇帝受制于家奴;在朝廷上,牛李两党互相倾轧不已,妒贤害能,任人唯亲。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士大夫阶层大多只顾寻欢作乐,不以国事为念。刘禹锡对此深感忧虑,却又无力回天,只能采取消极的办法,独善其身,避而不与那些庸俗的官僚来往。纵观历史,不难发现誓不为官的没有功名的知识分子不乏其人,他们的理由多种多样,各不相同,有人见多了官场的尔诈我虞,争权夺利,不屑参与其中;有人洞悉人性丑陋,不愿与世俗同流;有人清高孤傲,不耻与小人为伍;有人为躲避纷乱世事,愿保留心灵一分宁静……但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读书人骨子里那种不同流俗的狷介“士气”,却是大同小异,令人心生敬佩,这样的人自然也是陋室的常客。
再看“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两句,写的是自己在陋室独处时的生活情趣。“调素琴”无异于王维“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高雅绝俗,无异于陶渊明弹素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悦己不愉人,洒脱自在。“金经”沉静人心,与世无争,“丝竹”“案牍”的世俗和官场是刘禹锡鄙弃的生活。这样的心境下,交友的性质不再是高谈阔论,不再是当年的革新壮志,而是淡泊之下的清远,琴棋书画诗酒茶,与有功名的人交友似乎不是很合适,反而那些不为功名所累的人,更潇洒、豁达、自在。
刘禹锡最后又以“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自比陋室。我们都知道诸葛亮在《出师表》中写道:“臣本布衣,躬耕南阳。”以布衣自称的诸葛亮博学多识,淡泊名利,在被刘备请出山之前一直都是平民,隐居在南阳草庐之中。可是按照本文的观点,“布衣”诸葛亮是不能称为“白丁”的,他的朋友同样不能。读过《三国演义》的人都知道,隐居时的诸葛亮有不少朋友,有博陵崔州平、颍川石广元、汝南孟公威,还有后来成为刘备谋士又被逼去曹营的徐庶,更有水镜先生司马徽。这些人在诸葛亮的草庐中做客,的确称得上“往来无白丁”。所以刘禹锡用诸葛庐来比拟自己的陋室,可以说非常恰当,也可见“白丁”的含义。扬子云就是西汉文学家扬雄,他少时好学,博览多识,酷好辞赋。口吃,不善言谈,而好深思。家贫,不慕富贵。他的官职一直很低微,历汉成帝、哀帝、平帝“三世不徙官”。由此可见,诸葛亮和扬雄二人早年都是“布衣”之士中的学识渊博之人,也非有功名之人。刘禹锡自比二人,那是表明自己钦慕二人,与他们为友,以他们为榜样。
综上所述,“白丁”释义为平民,而后面追加补充说明“指没有功名的人”实属多余,且没有足够的证据,笔者解释为“平民,指知识浅薄的人”比较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