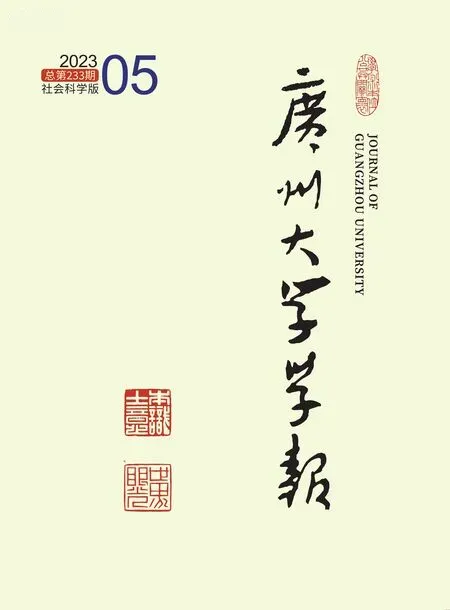概念隐喻理论发凡40年述评:现状与前瞻
孙 毅, 林攀龙
(1.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006;2.延边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延吉 133002)
一、概念隐喻理论源流
随着1980年语言学者莱考夫(Lakoff)和哲学家约翰逊(Johnson)的划时代著作《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WeLiveBy)出版问世,概念隐喻理论(Conceptual Metaphor Theory,简称CMT)由认知语言学领域众多研究人员共同建构完善并广为学界所热议。概念隐喻用源域(source domains)这一具体概念域中的词汇描述抽象的概念域,即靶域(target domains),其核心内容是跨概念域(cross-domain)的系统映射。[1]映射是单向的、抽象的推理过程,是以具体可感知的经验理解抽象不可感知的概念范畴。[2]源域依托字面性实体、属性、过程和关系,建构语义联系并存储于大脑之中;而靶域表征抽象概念,通过隐喻链接或概念隐喻,从源域搭建其结构。靶域在实体、属性和过程之间相互关联并反映源域中的对应关系。
(一)基本隐喻
基本隐喻(primary metaphors)是CMT的物质前提。莱考夫和约翰逊提议以直接身体体验和社会经验为基础建构基本隐喻系统。[3]4维度、方位、大小等直接经验铸造的字面概念体系筑成隐喻概念的底座。基本隐喻概念以共享具身体验为基础,其具身性使之与语言和认知的具体方法相兼容。[4]譬如,蕴含方位概念的“健康为上”(HEALTHY IS UP)和“多为上”(MORE IS UP)等隐喻表达,基于具身的生活物理经验拟构而成,而“时间是金钱”(TIME IS MONEY)、“时间是资源”(TIME IS A RESOURCE)和“时间是有价值的商品”(TIME IS A VALUABLE COMMODITY),则直接源于经济体验,并在时间价值关系的一般类别下形成独立的子类别系统。
建构于特定文化体验基础之上的复杂概念常含多重隐喻。每个隐喻皆强调经验的某些侧面,而隐藏或淡化其他方面。[5]10“论证是战争”(ARGUMENT IS WAR),但“论证”亦可为“建筑”(BUILDING)、“路径”(PATH)、“载体”(VEHICLE)或“游戏”(GAME)。隐喻概念还可延伸至绚丽多彩的奇思妙想之中而超越字面意义。“想法是物体”(IDEAS ARE OBJECTS)等生动形象的规约隐喻使抽象概念具象化,如“把想法用花哨的语言表达出来”(dress thoughts up in fancy words)、“他把想法整齐地排列起来”(he lined his thoughts up in neat rows)及“那条建议石沉大海”(that suggestion sank like a stone)。
与此相仿,“理论是建筑”(THEORIES ARE BUILDINGS)中,“地基”(FOUNDATION)、“支柱”(SUPPORT)和“构件”(CONSTRUCT)等概念表达与日常语言密切联系、融为一体。[5]53Grady视其为简单隐喻“逻辑结构是物理结构”(LOGICAL STRUCTURE IS PHYSICAL STRUCTURE)与“坚持是保持直立”(PERSISTING IS REMAING ERECT)的概念整合。[6]70建筑的若干方面(地板、墙壁、天花板等)与理论既未形成系统映射,亦无直接经验构筑理论概念与建筑结构之间的紧密联系。若将建筑方面映射于理论层面,需假设隐喻内涵和外延由载体推动,而非由说者意图和听者解读牵引。
方位隐喻(orientational metaphors)等基本隐喻建立的连贯隐喻系统,势必影响新颖隐喻(novel metaphor)的演进和发展。“快乐”“更多”“健康”等意蕴“上升”,与之缺乏物理关联(physical correlate)的“社会地位”(social status)等概念常用类似术语拟构隐喻表达。[5]5建构于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隐喻系统往往是连贯而衔接的。譬如,“多为好”(MORE IS BETTER)和“大为好”(BIGGER IS BETTER),与“多为上”和“好为上”(GOOD IS UP)一脉相承,但其对立表达“少为好”(LESS IS BETTER)和“小为好”(SMALLER IS BETTER)则不然。
(二)基本隐喻与复合隐喻的关系
基于“理论是建筑”的讨论,Grady论证了基本隐喻和复合隐喻(compound metaphors)的关系。[6]48-66其分析与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观点不谋而合。即便高度复杂的数学概念,也源于简单概念组合而成的复合隐喻并建构于数量的生物具身性体验之上。譬如,“有目的的生活是一场旅程”(A PURPOSEFUL LIFE IS A JOURNEY),为基本隐喻“目的是目的地”(PURPOSES ARE DESTINATIONS)和“行动是运动”(ACTIONS ARE MOTIONS)的概念组合,因为“在日常经验中,有目的的生活和旅程并无关联”。由此观之,任何特定表达只表征一种潜在概念隐喻,而每种概念隐喻都植根于不甚抽象的特定隐喻组合或独特且唯一的直接感觉运动经验。[3]63
莱考夫和约翰逊提出“思维是运动”(THINKING IS MOVING)、“思维是感知”(THINKING IS PERCEIVING)、“知即见”(KNOWING IS SEEING)和“心智是建设者”(MIND AS A BUILDER)等众多“思维”隐喻。[5]236高度复杂的概念由复杂程度较低的概念榫合而成,复合隐喻亦然,但其并非离散范畴,而是汇成一个连续统(continuum):从以童年早期体验为铺垫,如“情感是热”(EMOTION IS HEAT)和“多为上”,到以童年后期体验为条件,如“争论是身体冲突”(ARGUMENT IS PHYSICAL CONFLICT),再到以自觉文学隐喻(self-consciously literary metaphors)为前提,如备受隐喻理论家推崇的隐喻表达“朱丽叶是太阳”(JULIET IS THE SUN)和“你是我的阳光”(YOU ARE MY SUNSHINE)。
莱考夫和约翰逊还指出,隐喻存在于概念层面,而“论证是战争”等语言标签,是刻意用具体隐喻概念表征整个系统的结果。[3]182他们声称,“论证是国际象棋”(ARGUMENT IS CHESS)、“论证是拳击”(ARGUMENT IS BOXING),甚至“论证是桥梁”(ARGUMENT IS BRIDGE),皆可代替“论证是战争”,且其隐喻分析仍然奏效。说者使用词语和听者解读话语均很少考虑其隐喻蕴涵。[7]不同受众对新颖隐喻解读迥异,同现于论点中的“攻击”“防御”或“战略”等意象,可能构成与国际象棋、拳击或全面战争的概念映射。
“攻击”和“防御”等术语既适用于战争,也契合于争论。[8]“攻击”一词多含进攻、敌意和缺乏克制之意,与“对照证据检验”(test against the evidence)、“试图反驳”(try to disprove)和“试图驳斥”(try to refute)等同义词形成鲜明对比。“攻击论点”(attack an argument)与“反驳观点”(refute an argument)、“给出反例”(give a counter-example)或“构建反论”(construct a counter-argument)蕴涵迥异,且仅在特定语境中可等价替换。这些表达与战争本身并无关联,但其与冲突的隐喻映射致使受众对攻击与批判或反驳的反应大相径庭。
莱考夫和约翰逊用“视觉隐喻”(visual metaphors)对“相似即接近”(SIMILARITY IS PROXIMITY)加以评论,声称倘无该隐喻,相似便无从谈起。[3]59视觉隐喻倚仗相似性和关联性铸就,可分为基于相似性(resemblance-based)的视觉隐喻和基于关联性(correlation-based)的视觉隐喻。[9]相似性涉及方方面面,选择何种视觉隐喻取决于哪个方面最突显,受众理解隐喻蕴涵时往往强化某些相似性层面相对于其他层面的显著性。除此之外,隐喻的不确定性会导致严重误解。譬如,在国际象棋比赛中,“争论”双方无论输赢都期望再度交手;而在战争中,其中一方则希冀以压倒性优势取胜,以致双方无力再战。[10]由是观之,新颖隐喻需阐明个体在何种条件下建立隐喻联系及搭建何种隐喻联系。
(三)隐喻的功能与效用
CMT提供理论框架以阐释藉由构建知识框架和提炼新颖观点融合不同概念的方式。隐喻是思维和语言的普遍方面,是以简单熟悉、触手可及之物来理解复杂陌生、遥不可及之事,其贯穿人类交际过程的始终。[11]隐喻借助理论框架将信息添至语义程序,问题得以甄别并洞悉,同时运用“解决方案”彻底解决问题。“解决方案”隐含于语义结构之中,无需直接表达或明示袒露,保持静默和叠嵌(tacit and embedded)即可。隐喻能够表征相互关联的对应蕴涵,这是CMT的核心要义。隐喻分析还能培养批判性语言意识,从而使人通晓特定表达的蕴涵,以选择影响受众理解的方式。
莱考夫和约翰逊对比分析了相互关联的隐喻表达系统。[5]16譬如,“论证是战争”和“论证是一场旅程”(ARGUMENT IS A JOURNEY)用于建构整体概念,而特异性隐喻表达(idiosyncratic metaphorical expressions)是独立的,如“山脚”(the foot of a mountain)、“桌腿”(a table leg)等,虽也提及山的“肩膀”(shoulder of the mountain)和悬崖的“脸”(face of a cliff),但“山是人”(MOUNTAIN IS A PERSON)的任何意义延伸皆被视为奇思妙想和文学表达,如“山顶云蒸霞蔚”(The mountain’s head was covered with clouds);而山的“胳膊”“肋骨”“股”或“腿”等表达则毫无意义。
Grady重新审视概念隐喻及其语言表达差异的分析,凸显CMT的分歧性或模糊性。[6]212个体是否通过体验建筑构建理论化全程从而自然诉诸建筑来描述和讨论理论化经验?抑或,个体实现理论化的方式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与设计、建造或使用建筑的经验相似?即建筑术语是否适合表达理论化的某些方面?倘若表述成立,则隐喻使用者列述建筑方面映射理论概念的实例足矣,从“逻辑结构是物理结构”和“坚持是保持直立”的角度去解释“理论是建筑”是合理的;从隐喻使用者的直接经验来看,以上实例是从不同层面对特定蕴涵的概念化解释,建筑是组成部分之间结构化关系的范例,寻求更直接的解释亦可接受。
二、 评价概念隐喻理论
40年前,随着CMT登堂入室,隐喻研究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重大革命。CMT认为隐喻不仅折射语言的本质属性,还是构筑人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隐喻语言源于先前存在的隐喻思维,概念隐喻不仅是隐喻语言的表达手段,更是参与人类认知过程的思维方式。[12]莱考夫和约翰逊颠覆了学界对隐喻的认识观,推动了隐喻从传统修辞研究到认知研究的重大转向。[13]身体体验(如温暖、触摸、方位等)和抽象情感体验(如亲近、爱等)加强神经联系,并构成概念理解的基础,继而深化对抽象概念的理解。莱考夫和约翰逊及后继学者提供了系统的语言学理据,以印证概念隐喻切实存在,而不同领域学者也从各自角度对CMT发起了多轮批评。
(一)支持概念隐喻理论的确切理据
传统隐喻观认为,隐喻是不能仅从字面意义加以理解的特殊修辞用语,理解隐喻需付出较多认知努力。[14]莱考夫和约翰逊及其他学者将CMT进一步推广,不仅有力地促成并推进了认知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而且极大地影响了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社会学等研究领域。CMT注重解构暗含靶域的隐喻,而非明示源域和靶域的相似隐喻;但其亦可解释某些相似隐喻,如“我的工作是监狱”(MY JOB IS A JAIL)之于“社会限制是物理限制”(SOCIAL RESTRICTIONS ARE PHYSICAL RESTRICTIONS)。[15]概念隐喻的原始理据源自不同规约表达的系统分析。譬如,以下表达常被用来描述情感关系。
(1)“We’re headed in opposite directions.”
“我们正背道而驰。”
(2)“We’re spinning our wheels.”
“我们在白费力气。”
(3)“Our relationship is at a crossroads.”
“我们的关系正处于紧要关头。”
(4)“Our marriage was on the rocks.”
“我们的婚姻岌岌可危。”
CMT声称,以上实例并非字面意义的直陈表达,而是反映持久概念隐喻“爱是一场旅程”(LOVE IS A JOURNEY)的不同层面,部分要素受其驱动。爱情域实体(如恋人、恋爱关系和共同目标)与旅行域实体(如旅行者、交通工具、目的地)形成紧密映射。隐喻使用者将旅程的具身性体验映射于抽象的爱情关系概念(如爱情关系中的困境被视为物理旅程中的障碍),从而建构源域至靶域的对应联系。此外,爱情关系亦可被视为自然力,即“爱情是自然力”(LOVE IS A NATURAL FORCE),如:
(5)“She swept me off my feet.”
“她使我一见倾心。”
(6)“Waves of passion overcame him.”
“激情的浪潮使他难以自拔。”
(7)“We were engulfed by love.”
“我们被爱吞没了。”
(8)“She was deeply immersed in love.”
“她深深地沉浸在爱情中。”
隐喻概念可解释互不相关的规约表达。CMT框架下,“坚持到底”(stay the course)和“我们在白费力气”(We’re spinning our wheels)等所谓陈词表达并非死隐喻,而是影射隐喻思维的活跃图式。规约表达蕴含概念隐喻之外的意义,如“翘辫子”(kick the bucket)等牵涉转喻修辞格的习语,其系统性为意义受持久隐喻驱动提供理据。除系统性之外,众多新颖表达为规约隐喻的创造性实例,无法详述源域向靶域的映射。譬如,“我的婚姻是从地狱驶来的过山车”(My marriage was a roller-coaster ride from hell),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建成浪漫关系与物理旅程之间的概念化映射。
CMT注意到若干新颖隐喻之间的显著差异。表征规约映射、一次性映射(one-shot mapping)和静态意象映射的新颖隐喻,如“我的婚姻是从地狱驶来的过山车”“我的工作是监狱”“我妻子的腰细得像沙漏”(My wife …whose waist is an hour glass),都并非丰富多产的概念域,而被归结为“意象隐喻”(image metaphors)。[16]多义词意义由规约隐喻激发,如“看”(to see)蕴含的“知道”之义,由“知即见”激活。从历史角度来看,多义词词义源于概念隐喻这一人类概念系统的活跃组成部分,多义词词汇并非源于特异信息库的随机组合,而由概念隐喻等系统递归的认知原则构成。
Kövecses统合分析英语中的规约表达、新词扩展和多义现象,发现其中存在数百个基本概念隐喻。[17]迄今,所有语言均涉及概念隐喻,包括当代口语和手语,以及古埃及象形文字、古汉字和早期希腊罗马文字。概念隐喻以特定方式构建的抽象概念涉及领域宽泛,包括情感、自我、道德、政治、科学概念、疾病、精神分析概念、法律概念、数学和文化意识形态等等,不一而足。“不同语言以系统方式突显隐喻,这一事实足以论证概念隐喻植根于人类共同经验的认知地位。”[18]
(二)诟病概念隐喻理论的驳斥依据
过去40余年间,莱考夫和约翰逊首创的CMT已一跃成为最具影响力的语言学理论之一。不同领域学者的概念隐喻研究成果有力支持了该理论的基本主张。然而,尚不清楚不同学者判断系统性和概念隐喻是否遵循相同标准,他们对语言表达的直觉分析亦无法准确反映其使用隐喻语言的无意识行为。认知语言学者声称“坚持到底”(stay the course)并非隐喻表达却暗涵隐喻意义,而当代英语操用者视其为“死”隐喻、直白言语或多义现象的实例。[19]众多规约表达既无法解释CMT具有系统性的缘由,也难以厘清论及抽象概念时源域与靶域的详细对应关系。国内学者也对该理论的哲学基础、定义、分类、性质、运行机制等进行了批判。[20]出于种种原因,CMT多年来一直饱受猛烈批评,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从各自角度对其发起质疑。
1.方法论
CMT最常遭受的批评之一,是其研究人员往往基于直觉和非系统识别的语言隐喻(linguistic metaphors)凝聚概念隐喻。具体而言,众多研究者以自身心理词汇(mental lexicons)或词典和同义词表(thesauri)为基础,运用发掘的语言实例提炼概念隐喻。譬如,在词典中,动词boil表示“极度愤怒”,explode意为“失控暴怒”,hotdead代指“易发火者”,seething蕴含“强压怒火”。基于此,CMT主张用“愤怒是容器中的热流体”(ANGER IS A HOT FLUID IN A CONTAINER)来对“愤怒”进行概念化表述。[21]一方面,批评者声称研究者想当然地认定哪些是隐喻表达;另一方面,批评者也指出该程序并未关照真实说话者(real speakers)在自然话语(natural discourse)的靶域中使用了哪些实际表达。[22]
隐喻具有三大层次:超个体(superaindividual)、个体(individual)和亚个体(subindividual)。在超个体层面,研究者通过识别并运用非语境化隐喻表达(如词典释义)建构其他概念隐喻;在个体层面,说者在特定交际情境中使用与给定靶域概念相关的隐喻表达;亚个体层面则提供隐喻接受的理据,即隐喻具有具身经验或文化基础。换言之,自然话语中系统识别的语言隐喻与个体层面密切相关。这些异议并未削弱超个体层面“隐喻表达构成概念隐喻的基础”这一目标的效力。语言隐喻和概念隐喻指向不同靶域,二者的靶域互为你我、相辅相成。究其原因,诉诸直观概念而建构的隐喻,将系统识别的语言隐喻组合构成个体层面“更大”的概念隐喻,且真实话语中系统识别的语言隐喻可以发掘迄今尚未识别的概念隐喻。
2.分析方向
CMT批评家还一针见血地点明分析方向的问题,即隐喻分析应遵循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路径。沿袭CMT“传统”实践的研究者遵循自上而下的方法,以去语境化实例为基础构筑隐喻概念系统,并审查其内部结构进而确立映射、蕴含等对应关系。以此为路径,研究者需将概念隐喻本身作为假设前提的更高层次认知结构。相反,遵循自下而上的进路,CMT领域学者审读语料库中大量实例,并依据可靠程序甄别隐喻表达,同时审视其在具体语境中的具体行为(语义、结构、语用、美学等),继而将概念隐喻归结为多阶段综合作用的结果。倘若研究重点关注语言结构和语义过程,则其所用语料库或呈不规则性;若不规则性占主导地位,强调规则性的自上而下的方法(如概念隐喻),便无法解释隐喻表达独特且不规则的语义行为。
究其本质,不规则性源自受特定文化因素影响并由其塑形的不规则隐喻表达(如暗含隐喻的习语),因此更广泛、更普遍的概念隐喻无法解释这一现象。若遵循自上而下的路径,概念隐喻难以统摄隐喻表达的全部意义,即无法描述其不规则的语义行为。传统CMT批评者认为,隐喻语义行为较强的不规则性被强调整体认知结构的路径(如概念隐喻)所掩盖。以CMT为框架阐释隐喻表达的语义行为,须知哪个普遍性隐喻是概念化表达的基础;若无法捕获概念隐喻以解释其表达意义,则该表达便无理据,其意义便不规则;但即便觅得这一隐喻,也无法检索解释特定隐喻表达的语义行为。
Dobrovolskij和Piirainen进一步批评CMT无法解释源于同一概念化实例的隐喻表达的语义行为,认为该理论甚至无力统摄源自同一概念隐喻的两个或以上语言表达的不同蕴涵。[23]109譬如,“他那愚蠢的评论无异于火上浇油”(His stupid comment just added fuel to the fire)和“他们之间的争论爆发了”(The argument flared up between them),均由“争论是火”(ARGUMENT IS FIRE)这一表达激发,但仅凭概念隐喻一己之力则难以充分厘清其意义差异。“增加争论的强度”(add fuel to the fire)和“争论突然爆发”(the argument flare up)意义迥异,但CMT未捕获二者差异。究其本质,CMT并未因建立“争论是火”或“理论是建筑”等普遍性概念隐喻而穷尽其意义。这只是分析过程的第一步,接下来还需审阅靶域对应源域哪些元素,深究源域向靶域的紧密映射是构成概念隐喻的关键。
3.图式化
CMT批评者还鞭辟入里地指出隐喻图式问题,即应在哪个图式层级建构概念隐喻。莱考夫和约翰逊引证的“理论是建筑”这一隐喻实例,并未在适当层级凝练语言事实。[5]53Clausner和Croft提出图式层级较低的隐喻:理论/论点的说服力是建筑物理结构的完整性(THE CONVINCINGNESS OF THEORIES/ARGUMENTS IS THE PHYSICAL INTEGRITY OF THE BUILDING)。[24]这一隐喻的源域和靶域均不及“理性论点是建筑”(RATIONAL ARGUMENTS ARE BUILDINGS)更具图式意义,但他们断定该程式在适当图式层级更能体现隐喻特征,即能精准折射源域哪些元素映射至靶域及哪些元素未映射至靶域。概念隐喻的适当图式层级为何?传统CMT的主张经不起推敲。譬如,“爱情是一场旅程”的映射发生于车辆层面,而非船舶或火车层面;其隐喻映射发生于关系和车辆之间,而非关系和船舶或火车之间。
映射并非形成于上义或下义层次(superordinate or subordinate level),而是发生于基本层次概念(basic-level concepts)之间。若处于上义层次,则隶属同一源域且具类似涵义的基本层次概念是高层次映射的替代表现形式(须可互换)。如想充分阐释这一现象,需借助标准的莱考夫-约翰逊理论之外的概念工具——源域范围(the scope of the source)和主要意义焦点(main meaning focus)。源域范围,即每个隐喻源域都适用于某一组靶域。譬如,建筑隐喻适合政治、经济、人际关系、生活或心智等复杂抽象系统靶域的任何要素。主要意义焦点指源域用于概念化靶域的某个或某些方面。“建筑”源域的意义焦点之一是结构,复杂抽象系统是复杂的物理对象,“建筑”源域可对其结构进行概念化(思考和讨论)。
容器的意义焦点为“压力”,由此生成概念隐喻“抽象张力是物理压力”(ABSTRACT TENSION IS PHYSICAL PRESSURE)。表达这一意义焦点,壶比锅的概念更合适,因壶内蒸汽产生压力,甚至使壶发出哨声。二者虽意义相似,但其意义焦点和隐喻使用却具系统性差异。以“道路”(WAY)和“路线”(COURSE)的概念为例。“手段是路径”(MEANS ARE PATHS),是“道路”的概念化解释,而“路线”是隐喻映射的实例,“规划如何实现目标便是规划如何抵达目的地”(SCHEDULING HOW TO ACHIEVE ONE’S PURPOSE IS TO REACH ONE’S DESTINATION)。综而观之,隐喻映射置身于上义层次,某些表达意义相似,隐喻用法却不尽相同,原因在于这些表达的意义焦点基于不同映射并涉及特定源域。
4.具身性
具身性是CMT的核心要义之一,它将认知语言学与其他认知理论的概念内涵区分开来。具身性以基本身体体验为基础,在理解周遭世界的过程中无法规避。因此,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在具身性概念化层面尤为重要。然而,试图同时阐释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的具身性观点,往往导致理论内部产生矛盾。Rakova断言,建立在意象图式和身体体验之上的理论不能与文化变异观相提并论,而还原论与相对主义不应并存。[25]体验主义常常表现为相对主义,直接表义概念(directly meaningful concepts)和动觉意象图式(kinesthetic image schemas)的普遍性假设,与文化界定的概念化观点并不相符,空间关系概念化中认知层面显著的文化差异,与意象图式理论所遵循的自然主义立场水火不容。
毋庸置疑,“容器图式”等隐喻实例表明,意象图式和具身性是“以自然方式”使事物概念化的普遍经验。譬如,“愤怒”在不同文化中具身性表征大同小异,皆伴随皮肤温度升高、呼吸频率加快、血压升高等不同生理反应,恰如其分地解释了在相互独立的语言和文化中捕获通用概念隐喻的缘由。具身性由若干部分组成,且其中所有要素均由来自不同文化的个人识别并受到关注。要应对上述批评带来的挑战,需转变具身性思考方式,且不宜视其为单一同质因素,进而提炼和改进意义具身性的概念化全程。先前研究将该设想称为“差异体验焦点”(differential experiential focus)[26],为回应这一批评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5.隐喻与文化的关系
与此同时,具身性概念并不刻板,却无法全面统揽文化塑造隐喻概念化的整体方式。建构普遍隐喻的具身性过程与塑造特定语言隐喻的局部文化之间有何精确联系,目前尚不明了。问题在于CMT能否同时解释隐喻概念化的普遍性和文化特异性。自然情境中隐喻概念化源自具身性压力和语境压力,这种双重压力促使身体和文化保持一致,即普遍具身性与局部文化的文化特异性相匹配吻合。语境由局部文化决定,表现为身体、社会、文化、话语等方面,它由背景、话题、受众和媒介等因素组成,进而影响隐喻概念化全程。
特定情境的隐喻使用不仅取决于表达特定意义的给定靶域中的潜在普遍隐喻,还受制于隐喻概念化的背景和主题。隐喻选择受研究者身份的掣肘,其生活经历或关注领域会影响隐喻决断。在确定的自然情境中,职业背景、生活经历、关注领域和兴趣爱好均可为靶域觅得合适源域。隐喻概念化并非简单使用现成的或普遍的隐喻。语境压力是隐喻使用不可规避的因素,与局部语境保持一致是理解自然话语中隐喻蕴涵的重要前提。如今隐喻使用已超出CMT的解释范围,研究者应通过简述新的概念工具,研磨相关隐喻实例,为依托认知语言学理论框架理解语言和文化创造性开辟新路。
三、概念隐喻理论研究沉思:献计与展望
语言学研究并未详细阐述CMT领域的分析方法。概念隐喻的认知语言学分析通常不明示以下具体标准:(1)确定单词或短语层面语言的隐喻构成;(2)定义涉及特定抽象靶域的给定表达之间的系统性;(3)运用某些隐喻表达的系统性推断特定概念隐喻是否存在;(4)依据孤立的、捏造的隐喻实例或从语料库提取的个例断定真实话语分析是否具有代表性。研究人员尝试设计方案构筑可靠程序识别隐喻语言,并开发精确计算程序甄别激发隐喻话语不同语义场的概念隐喻。语料库语言学也编制识别语言隐喻和概念隐喻的程序,判定隐喻映射中哪些是隐喻词汇,哪些是对应源域。语料库研究支持认知语言学领域通过内省提取广泛的概念隐喻,并诉诸量化隐喻模式为不同领域概念隐喻的相对显著性提供重要见解。
语料库研究者对CMT颇有微词,认为概念隐喻须将源域的所有方面映射至靶域,以致形成非连贯映射。然而,CMT并不支持源域所有方面都能经由概念隐喻映射至靶域。该理论中“恒常性假设”(invariance hypothesis)指出,隐喻映射保留源域的认知拓扑结构(cognitive topology,即意象图式结构)。[27]诸多源域均具有意象图式结构,其理据是“感知交互和运动程序反复的动态模式为经验提供连贯性”[28]。源域知识向抽象靶域的不变映射表明,隐喻映射的确立并非以特定属性为基础,而是彼此之间一一对应、密切联系的结果。源域意象图式结构可以预测由不同概念隐喻激发的隐喻词汇及由其提供理据的习语含义。
实验社会心理学表明,概念隐喻还影响非语言理解和社会认知的方式。受身体结构和地心引力等因素所限,人们对空间垂直概念的理解尤为深刻。[29]譬如,运用空间stroop范式对抽象概念上下空间表征进行研究发现,若具积极含义的单词呈现于电脑屏幕顶部,受试会更快做出评价;如具消极含义的词汇出现于屏幕底部,受试会更快加以识别。[30]受试表征词汇褒贬意义与上下方位属性密切相关,若方位信息与褒贬含义一致,则空间垂直维度对抽象概念加工产生促进作用,反之则产生干扰作用。由是观之,好和坏沿垂直空间分布,这一论断与“好为上”(如存活和健康)、“坏为下”(如死亡和疾病)等隐喻表达一脉相承。社会心理学研究直接回应了这一论断,即CMT须论证概念隐喻在非语言经验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任何对该理论的适当评估均须承认并讨论这一非语言理据。
(一)概念隐喻理论与心理语言学交叉研究
认知语言学为概念隐喻理论的哲学基础——经验基础提供了大量理据,但这种“语言—思维—语言”的循环研究模式尚不严谨。[31]认知语言学者普遍通过分析语言表达推论潜在的隐喻映射,再将隐喻映射的可能性归结于语言,继而关注人们在日常使用和理解语言时是否运用概念隐喻。相关实验研究探讨以下问题:(1)概念隐喻在隐性理解隐喻词汇和短语时是否起效?其具体含义为何?(2)概念隐喻在即时生成和理解隐喻语言时奏效与否?回应上述问题至关重要。受试在实验环境下生成和解释隐喻时仅对某些单词和短语概念化,而不做进一步识别。概念隐喻塑造规约表达和新颖隐喻蕴涵意义的默契理解,包括习语和谚语的心理意象研究、习语含义语境的敏感判断、习语源域至靶域的映射判断、基本隐喻隐含的映射判定、文本处理过程中读者对连贯联系的绘制以及概念隐喻的语义和情节记忆。
研究者需冲破藉由语言现象研究概念隐喻的藩篱,结合心理语言学和神经科学实验等手段,开展隐喻语言经验基础的“趋同理据”(convergent evidence)研究,延申和补充非语言领域的概念隐喻现象。对此,心理语言学的实证研究功不可没。心理语言学研究表明,概念隐喻影响语言隐喻的在线处理。譬如,通过组织完成短语阅读测试,研究发现,较之于不同隐喻语境,受试更易理解相似隐喻中的委婉表达。[32]由此,审阅隐喻语境中某些语言隐喻耗时较短,并非完全得益于语境词汇和隐喻词汇之间的词汇启动,而是部分因为语境在隐喻语言理解中发挥着重要影响。譬如,概念隐喻“愤怒是容器中的热液”(ANGER IS HEATED FLUID IN A CONTAINER),在习语“约翰勃然大怒”(John blew his stack)的即时处理中得以通达。比起由不同概念隐喻激发的隐喻,受试更易理解受相似概念隐喻驱动的表达。
近几十年来,心理语言学者提供的大量理据证实了固有隐喻的存在,阐述了具身性体验之于生成和理解隐喻的重要作用。一系列语言心理实验结果表明,具身性体验是使用和理解隐喻语言的基础,弥补了普通语言中概念隐喻的语言学分析。然而,其他研究数据与将概念隐喻解读为语言隐喻的心理学主张相左。分析表明,研究者不应将习语含义的直觉分析作为概念隐喻的理据,因其难免夹杂他们的喜恶偏好而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因此,要确证概念隐喻在隐喻理解中的认知机制,须借助ERPs和fMRI等先进的脑成像技术,利用脑电波变化实时在线观察隐喻使用实况并推断思维过程。[33]
规约隐喻经由概念隐喻得以通达,然而部分学者发布的心理语言学研究结果与该观点相悖。[34]他们发现,以相关规约隐喻为语境审视新颖隐喻,与在非隐喻语境中阅读相比理解速度不算快;而以新颖隐喻为语境审阅相似新颖隐喻时读速更快。研究结果表明,新颖隐喻理解能激活更深层次的概念隐喻基础,而规约表达则不然,这一发现与认知语言学主张相左。相关研究的语料库分析进一步表明,受试审阅的所谓新颖隐喻是规约表达,其他表达则为新颖隐喻,因其反映与语境截然相反的不规则语言模式。[35]当审阅相同概念隐喻驱动的规约表达时,理解新颖隐喻要比审读不同概念隐喻驱动的规约表达更快。由是观之,“规约隐喻仍然奏效”,并且“规约隐喻家族解释新颖隐喻时可以促成相关概念结构的映射”。[36]
(二) 概念隐喻理论与语料库界面研究
CMT坚信,语言隐喻是发现并探索交际中潜在语义结构的有效途径。以莱考夫和约翰逊为代表的传统认知语言学者强调普遍认知结构的重要性,多以自上而下的方法通过内省和语料进行直觉分析,但其研究无法全面观照潜在的隐喻模式,所得结论难免主观片面。Dobrovolskij和Piirainen等研究人员则强调建构特殊概念机制以统摄隐喻表达的全部意义,而单凭普遍认知结构无法达成这一目的。[23]193越来越多研究者以自下而上为进路探究隐喻,强调数据中存有众多不规则之处,无法遵循自上而下的解释路径。语料库研究方法采用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径,系统、量化且全面地分析大量语料,归纳、揭示实际语言使用中的潜在隐喻模式和认知规律,恰如其分地满足了CMT研究领域的数据分析需求,有助于纠正自上而下的传统研究方式产生的理论偏差。
若无隐喻,则无法谈论抽象概念,亦无法直接感知其内涵,惟有倚仗过滤直接经验的具体概念才可理解。通过语料分析发现,大量文献广泛引用“有目的的生活是一场旅程”这一概念隐喻,其他隐喻则用于谈论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有目的的生活是一桩生意”(A PURPOSEFUL LIFE IS A BUSINESS)。如果抽象主题常用隐喻进行概念化表达,并已收集大量语言学理据来支撑这一论点,那么深究所用隐喻成为建构抽象概念的关键。莱考夫和Turner主张,解读概念隐喻需认定概念为具体对象且可用隐喻进行概念化表达。[37]这一观点凸显利用已有知识理解新颖表达的方式,但也暗指隐喻理解过程较慢,需付出相当认知努力,而隐喻理解速度常因人而异。
为充分阐释上述论点,研究者通常识别抽象主题的语言隐喻,并运用潜在概念隐喻予以激发,进而考察靶域的哪些方面得到凸显和隐藏。语言隐喻表征说者或作者的潜意识选择,其语言决断受社区成员共享概念结构的限制。CMT声称,隐喻亦可论及困难、紧张或不寻常体验并展开思考。在其他情况下,说者或作者会刻意选定特定隐喻表达来传达涉及意识形态或说服力的观点。譬如,隐喻分析者试图应用CMT界定文本语料库暗含的意识形态立场。国外学者挖掘了20世纪90年代海湾战争前后《时代》和《新闻周刊》杂志中的隐喻,发现其隐含种族主义倾向——世界被极化为“东方对西方,美国对他们”(the Orient vs. the West, the US vs. Them)。[38]还有学者提取了《洛杉矶时报》反对移民立法相关报道中的隐喻,发现“国家”被喻为“房子”,而移民被斥作“洪水”或“入侵”等威胁意味浓厚的贬义意象。[39]
四、结 语
修辞学界、哲学界一直认同隐喻与语言同属普通思维的组成部分。四十载弹指一挥间,CMT发展迅猛,前景广阔,在学界备受瞩目。莱考夫和约翰逊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一经出版便广为人知,他们旨在提供系统的语言学理据以印证概念隐喻切实存在。毋庸置疑,作为识别潜在意义的工具,极具启发性的概念隐喻也不可避免地存有缺陷。研究人员试图以有限语言理据为基础过度概括观点,并假设建立一致程序穷尽性地识别隐喻现象。20世纪80年代以降,文学、哲学、社会学及经济学等许多学科与CMT融合并取得长足发展,推动这一理论毫无争议地跃升为学界主导性理论框架。同时,学者也对其提出种种批评。“尽管相关研究如火如荼,[概念隐喻]的观点在理论和实证层面皆不足以服众”[40],因此CMT的阐释价值遭到多轮质疑。
本文列举了支持CMT基本原则的各路确切理据,以适当评估持久的概念隐喻在语言、思维和文化中发挥的作用,直接统合批评该理论的重要语言学、非语言学和实验数据。另外,我们还回应了近年来对CMT提出的五路批评,主要涉及方法论、分析方向、隐喻图式化、具身性以及隐喻与文化的关系等。第一,方法论。批评家们提出的概念隐喻研究目标和传统隐喻理论研究目标相悖。认知语言学家基于莱考夫-约翰逊理论框架展开研讨,力图在超个体层面假设概念隐喻,而批评者则力求在个体层面系统识别语言隐喻并生成假设的概念隐喻。第二,分析方向。批评还涉及概念隐喻的定量分析。自下而上的隐喻研究者声称,语言隐喻的不规则性更强,若概念隐喻分析旨在穷尽性地揭示抽象概念的性质和结构,那么定量隐喻分析需辅以直观的定性分析。第三,隐喻的图式层次问题。Zinken等批评者认为,在真实话语中可抓取基础层次隐喻,而无法识别更高层次隐喻,更高层次中隶属同一物理域且具相似含义的表达须具相同隐喻意义,但实则不然,映射发生于基础层次,而非上义层次。第四,CMT具身性的核心思想也饱受批评。具身性可解释隐喻概念化的普遍方面,却无法解释跨文化现象和历史差异。第五,关于隐喻与文化的关系。Rakova等学者质疑CMT能否同时解释隐喻概念化的普遍性和文化特异性。[25]
与此同时,不同领域研究者认为,概念隐喻在以下层面具有相当影响力:(1)抽象概念的文化模式;(2)语言的演变;(3)当代语言(如规约表达、新颖扩展和多义现象);(4)当代语言操用者的非语言思维和交流;(5)当代语言操用者运用根深蒂固的知识建构抽象概念,促使人们理解单词、短语和文本何以传达隐喻意义;(6)当代语言操用者运用根深蒂固的知识重新收集(即通达或激活)在线隐喻语言。学界关于CMT的广泛争议,集中体现在哪些层面,对洞悉概念隐喻之于语言、思维和文化的作用最为关键。譬如,反对CMT的心理语言学者认为,概念隐喻影响1到3,而非4到6。但从动态角度观之,不同层级表征经验中分层组织且相互嵌套的不同时间尺度(从最慢向最快移动),使得某个层级(如层级1或2)的约束以复杂、非线性的方式与其他层级(如层级5或6)的约束耦合。因此,隐喻词汇不仅反映概念隐喻作为吸引域(basins of attraction)(在5和6运作)的影响,还折射出隐喻体验在不同层级以持续互惠方式同时运作的交互作用。譬如,规约表达“我看不透这篇文章的要点”(I don’t see the point of this article),不仅受到基本隐喻“知即见”的简单激活,还因为不同层级之间的相互约束,使读者自发对类似表达产生特定解读。因此,概念隐喻可在思考、说话和理解过程中“软组装”(soft-assembled),而非从长期记忆中“获取”或“检索”。
一言以蔽之,本文在充分回溯四十年中CMT发端和拓展的基础上,梳理了学界支持和诟病这一理论的正反两方面的理据。四十而不惑,莱考夫和约翰逊等学者竭力从语言学角度试图论证概念隐喻存在的合理性及其在不同层面的重要阐释价值,而不同领域学者也从各自角度对其大加指摘。基于此,本文通过概述心理语言学和语料库视域的CMT研究现状,试图探究该理论与心理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等领域实现跨学科交叉研究的可行性,拟构新的研究框架作为“标准的”“传统的”莱考夫-约翰逊理论框架的迭代品,希冀该脉络思路将使CMT在今后的嬗变和演进洪流中更加灵活、开放、包容,力避各种备受诟病之处,扬长避短,趋利避害,使其更具解释力和说服力,进一步拓宽认知隐喻在思维交际领域的研究新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