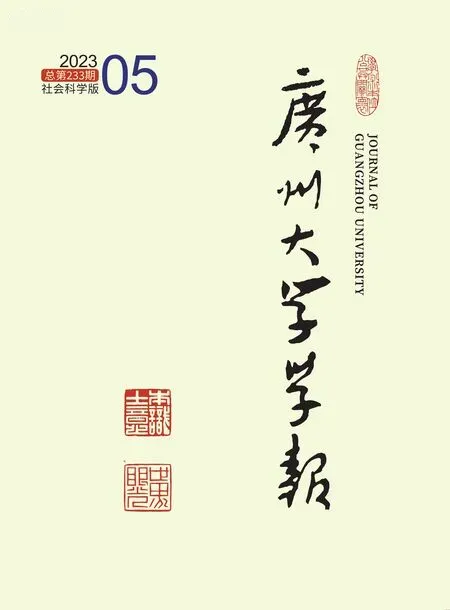景观人文与城市精神:城市交响曲电影美学探析
孙 萌
(中国艺术研究院 电影电视研究所,北京 100012)
一、引 言
电影发明之前,人们通过绘制的地图、拍摄的照片来感知城市。城市作为公共空间成为展现人们生活的一个舞台,节庆的盛大游行队伍,集会、运动比赛、演唱会等大众活动,静态的图片已不能全面展示城市的活力,人们呼唤着摄影机的出现,以便大幅度、大尺度地呈现宏观与局部的人的动势。电影从诞生之初便与城市结下了不解之缘,卢米埃尔兄弟的《火车进站》(TheArrivalofaTrain)、《工厂大门》(ExitingtheFactory)等都是对巴黎景观的呈现,柏林、伦敦、纽约、莫斯科、阿姆斯特丹等现代大都会都有着各自的城市影像,这些城市共同滋养了电影的早期发展。中国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出现在北京,但是它反映的不是城市景观,是一个记录中国传统戏曲的短片,从这一点来看,某种程度上决定了电影两种不同文化的走向。20世纪40年代末,丁力执导的《大团圆》中出现了自行车穿过城门、穿行于胡同的北京场景,交通工具的发展变化为城市现代化提供了动能。中国早期电影的黄金时代出现在上海。上海影像里的花园洋房、小轿车、照相机、电话、酒吧、咖啡馆等作为大都市的时尚符号,体现了摩登时代的特有魅力。从某种意义上说,电影是和现代城市同时出现的。电影院如同城市中心的一个暗室,城市的梦想被投射在暗室的银幕上。电影可以看作是一台旅行的时间机器,它吸收事件和情感,它既是对现实的反映,也包括对过去的记忆和未来的设想。
城市交响曲电影是指以城市为主题与刻画的对象,基于蒙太奇手法的一种电影,这类电影不靠传统的故事叙述来再现现代性的心理和视觉体验,而是以风格化的影像、万花筒式的结构,捕捉城市生活的形式感和节奏感,通过对从早到晚的城市生活的描写来揭示城市生活的独特面,目的是将城市的动态浓缩进诗歌式的电影里。电影人为地突出当代城市的地位与特色,用交响曲的结构来比拟城市生活的结构,城市里的人们各自有着不同的行为动作,在电影剪辑的作用下形成了高低起伏、和谐一致的节奏,如同交响乐队中几十个乐师同台演奏不同的乐器,汇聚成协调统一的旋律。交响曲就是通过种种音乐形象的对比和发展来揭示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冲突和人们的思想心理、感情体验。当今的城市交响曲电影,不管是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对传统城市交响曲电影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延异与变奏,不断改进和提高其表现方式,对城市交响曲电影进行现代性转化,讲求结构上的精巧深刻、内容上的先锋前卫、语言上的富有表现力,以期更加有力、有效地反映人性的复杂以及城市与人的关系,反映当下社会与城市精神。
城市影像中凝聚的人文关怀,是其最为独特的城市精神。景观是大地上所有的空间和构筑物的总和,它既有山水构建的自然风景,也有人类创造的人工环境。景观人文的落脚点是人文,是人类的文化现象,是物理空间所反映出的人文精神,它的核心是精神家园的构建,是寻找让心灵能够安居的地方。就像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所说:“速度,也即当下的节奏,是不能用地铁或摩天大楼来衡量的,而只能用从城市石头下冒出的欢欣小草来衡量。”[1]城市街道上的青草,是原始森林,也是精神家园里的第一批萌芽。
二、早期城市交响曲电影中对现代性的迷恋与反思
在亚历山大·格拉夫看来,“蒙太奇作为都市现代性的表达方式,在界定电影作为‘现代’艺术形式上扮演了重要角色。都市生活的步调与节奏的再现与重构,通过剪接技巧体现出来,成为‘城市交响曲’电影形式的首要特征”[2]。城市交响曲电影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美国导演查尔斯·歇勒与摄影师保罗·斯特兰德在纽约拍摄的《曼哈顿》(Manhatta)成为此类电影的发轫之作。巴西导演卡瓦尔康蒂在巴黎拍摄的《时光流逝》(NothingButTime)、德国导演瓦尔特·鲁特曼的《柏林:城市交响曲》(Berlin:SymphonyofaGreatCity)、苏联导演维尔托夫的《持摄影机的人》(TheManwithaMovieCamera)、荷兰导演尤里斯·伊文思的《雨》(Rain)是这种电影的典范。面对当时的这些先锋电影,海尔莫特·威斯曼惊呼:“一个新的电影类型已经诞生——城市电影。”[3]3法国导演让·维果的《尼斯印象》(proposdeNice)、美国导演温伯格的《城市交响曲》(CitySymphony)、中国导演刘呐鸥的《持摄影机的男人》、瑞典导演阿尔纳·苏克斯多夫的《城市交响曲》(SymphonyofaCity),是此类电影的延续。
早期的城市交响曲电影呼应着时代的律动,表达的不是普通的城市生活,而是城市的现代节奏、新的速度与过度的感官刺激。火车、汽车转动的轮子、旋转的机器、钢筋、街道、桥梁、烟囱、玻璃建筑、摩天大楼等,这些组成城市速度、节奏与运动的交响。节奏感、形式感、运动感建立起城市交响曲电影的突出特征,给人全新的都市体验。本雅明谈到电影时曾说:“大都市里咖啡店、街道、办公室、摆设了家具的房间、车站和工厂,仿佛将我们囚禁起来,没有解脱的希望。可是有了电影,它那几十分之一秒的爆炸瞬间,便炸开了这个集中营似的世界,现在我们被遗弃在散落四处的断垣残壁间,正展开一段冒险之旅。由于特写的关系,景物细节更大更宽广了;由于速度的放慢,运动有了新的向度。”[4]也就是说,摄影机和电影创造了一种新的自由,将人们从单调的漫长街道中解救出来。
第一部城市交响曲电影《曼哈顿》利用在高处对城市的俯拍,展现了一定程度的抽象感与陌生化,这在之前是没有过的,卢米埃尔兄弟的电影基本上是拍摄于地面的纪录片,抽象城市的首次出现,宣告了先锋派的诞生。《柏林:城市交响曲》则给这类影片冠名,用交响曲的结构比喻城市生活的结构,在对现代性迷恋的同时,反映出德国战后对重建社会秩序的渴望。1927年魏玛时期的柏林,让我们看到工业资本主义发展时代下城市人的生活,他们生活在技术和工业蒸蒸日上的时代,行色匆匆,为生活各自奔忙,市场经济和都市理性占据了整个都市人的生活。正如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TheProtestantEthicandtheSpiritofCapitalism)一书中探讨的,冒险资本是现代化之前的文明,而当下的资本是理性,是结构秩序都无从打破的驯化社会,“它的理性特征基本上取决于那些最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靠性”[5]。鲁特曼“通过剪辑的艺术筛选、节奏和放弃传统叙事将现代性体验表现为片段式的和抽象的”[3]23,把记录各事物分散运动的画面复调似的构建到影片整体节奏中,使其在影片中获得一种多声部的、完整的、交响式的视觉节律,在不同场景的互动中开掘出一种富于视觉张力的戏剧性效果,规模宏大,气质磅礴,画面与音乐配合得天衣无缝,充满诗意。他的目标是根据音乐、舞蹈与建筑的法则建构电影,并以一种“视觉交响乐”的形式传达全新的内容与新的现实,用蒙太奇等手法创造城市的总体精神。电影通过四个乐章展现了柏林的一天,对应内容分别是交通、工作、家庭和娱乐。影片的结尾,烟花齐放,象征着大城市繁忙的一天的结束。《柏林:城市交响曲》的时间跨度是一年,尽管镜头中的时间是从清晨到黄昏,但实际上影片拍摄了一整年,从有些镜头中可以看出树叶已经掉光,有些镜头中则枝繁叶茂。1927年的柏林,无论从时空或文化意义而言,如今早已不复存在,因此此片也有了一种影像志的人类学价值。
《持摄影机的人》是“电影眼睛”理论的创始人维尔托夫的代表作。该片主要拍摄于敖德萨,通过对敖德萨从早到晚生活场景的展现,呈现了独特的市景。人们在探索敖德萨、莫斯科等五座城市的同时,也在探索用电影记录城市的方式。在电影的开头,维尔托夫这样强调:“这部电影是对脱离戏剧的电影交流的实验,是一部没有道具、没有演员的电影。换句话说,人们在扮演的就是他们自己。”影片主要分观众入席、城市黎明、人民的工作与休息、体育运动和艺术实践几部分,通过刻画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呈现苏维埃新社会中的理想城市。电影院成为维尔托夫对这个新世纪和新社会发表感言的理想公共空间。维尔托夫在片中创造性地使用了大量蒙太奇的手法,实现了“电影眼睛”理论的视觉化表达。维尔托夫强调用“抓拍”的方式捕捉生活的片段,该片没有字幕、演员,也没有道具、布景,城市自己成为了叙述的引导者和主角。拍摄过程中,摄影师卡夫曼,也就是导演的弟弟,揭去了电影拍摄的神秘面纱,在拍摄的同时也出现在电影画面中,首创了“自我暴露”这一新的电影形式。该片的剪辑是导演的妻子斯维洛娃,她同时也作为剪辑师出现在了电影画面中。在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纪录片中,维尔托夫首次使用了二次曝光、快进、慢动作、画面定格、跳跃剪辑、画面分割等前卫剪辑手法,制作了一段定格动画,并采用了仰角、特写、推拉镜头等新颖的拍摄手法,让摄影机成为电影的某种语言。在所有这些镜头间的相互吸引和排斥中,为观众的眼睛寻找最佳的旅行路线。
《持摄影机的人》在挖掘电影制作各环节自身能量的同时,考察了人民群众共同参与建立一个苏维埃社会时所具有的变幻无穷的力量,反映了俄国共产主义者对大革命、对即将到来的现代工业化的热切心态。那个在银幕上通过繁复的蒙太奇手法变幻成的社会主义工业之城、理想之城,是莫斯科、敖德萨和基辅的结合体,是城市交响曲电影的华彩乐章与激情之作。《柏林:城市交响曲》没有对城市生活进行任何明显的社会或政治分析,影片的重点在于突出城市生活丰富多彩的方面。黑克认为《柏林:城市交响曲》很激进,“以视觉的形式构建了柏林的社会和空间特征”,但它的“最终目标还是视觉享受,而不是讽刺分析”。[3]21克拉考尔也认为鲁特曼“记录日益扩大的机械化,却丝毫不客观表现其可怕的一面”[6]。《雨》用诗意的电影镜头,描绘了一场从坠落到停歇的雨水之旅,我们跟随着摄影机从车水马龙的街市走进人潮涌动的人流,共同谱写着一曲雨的交响乐。伊文思为了制作这部电影,历时两年在城市的不同地点捕捉雨的踪迹。影片大的结构以时间为线索,可分为雨前、下雨、雨后,在这样的结构框架内,导演重点观察了风、云、雨的变化,以及这个变化过程中路人的群像。片中落在洼地积水上的雨珠、马路上的反光、闪闪发光的伞的海洋、反复出现的鸽子,以音乐般流畅的印象派风格,展现了阿姆斯特丹这座城市的独特精神风貌,给予人们一份来自大自然的馈赠,诗意地表现了人类的生存知觉。《时光流逝》运用反叙事的手法客观地呈现事实,注重日常物像的特写。片中汽车与马车的对比、鲜花与垃圾的对比等,展现了上流社会与底层不同人物的悲欢,充满了诗意,“是20年代法国社会贫穷落后、追求玩世现实主义,以及盼望审美自由的缩影”[7]。《尼斯印象》在表现尼斯的大海、土地和天空中融入了更多社会与政治因素,通过对比蒙太奇反映了上流社会的奢华生活以及贫民窟生活的巨大差距。《时光流逝》和《尼斯印象》这两部反映法国城市的电影将城市百态通过社会批判的视角联系起来,对20世纪30年代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电影产生了影响。
与《持摄影机的人》类似,20世纪30年代,中国也有一部名为《持摄影机的男人》的电影问世,导演是上海新感觉派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呐鸥。他在1933年拍摄了这部几近同名的黑白无声记录片,影片分为五卷,共46分钟,包括人间卷、东京卷、风景卷、广州卷和游行卷,分别拍摄了刘呐鸥的家人在摄影机前的状态、在东京游玩时所见的风光与城市风貌,一对青年男女游园的所见,广州市民时尚的行为和装扮,以及军队队列与民间节目演出,在记录人的形象外表时使用固定机位,拍摄生活场景则用推拉、横向摇移的运动镜头。从影片的内容中不难看出,刘呐鸥拍摄影片所表达的“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秉承了维尔托夫的创作理念,呈现了刘呐鸥的都市观察与新感官体验。刘呐鸥通过拍摄这些日常生活的所见所感,使用跳切、特写拼接的蒙太奇剪辑手法来呼应维尔托夫。不同于维尔托夫歌颂新生政权的激越,刘呐鸥的作品映现出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觉和印象,有着布尔乔亚式的浪漫情调。刘呐鸥的先锋电影实践,可看作是“新感觉派”文学书写在电影领域的拓展。
20世纪30、40年代,在“新感觉派”的发祥地上海,还出现了一些反映上海街景与民风民情的城市电影,像袁牧之导演的《都市风光》《马路天使》,沈西苓导演的《十字街头》,桑弧导演的《不了情》《太太万岁》,黄佐临导演的《夜店》,郑君里导演的《乌鸦与麻雀》等。这也让人联想到当下,尤其是近两年,城市微纪录片、短视频海量出现,在万物皆媒的众媒时代,人们可以用数字替代胶片,用手机灵活便捷地拍摄微城市短片,对城市中实时发生的热点事件进行精准捕捉,在抖音、快手、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播出,引起大家的互动与思考,让人们及时看到并关注自己所生活的这座城市,通过传播城市形象,凝聚民众力量,呈现城市文化,塑造城市精神。这些微电影也可视为城市交响曲电影的一种延伸和补充。
三、反映现代性异化与对抗异化的城市交响曲电影
美国电影文化研究学者芭芭拉·门奈尔在《城市和电影》(CitiesandCinema)一书中认为,连结城市和电影的纽带是现代性,城市电影造就了现代性,将城市塑造为现代空间,“一方面是犯罪、互不相识、道德的松弛、失业和阶级斗争,另一方面是进步、速度、娱乐和性解放”[3]4。在通往现代性的道路中,我们在憧憬着工业文明所带给我们巨大便利的同时,各种问题也相继涌现。我们在屈服于资本逻辑的同时,也丧失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异化”是马克思对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深刻概括。异化包括劳动产品和劳动者的异化,生产过程与劳动者的异化,人类的本质与人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城市要求的某种专门化,意味着“个性的死亡”,“自主活动表现为替他人活动和表现为他人的活动,生命的活跃表现为生命的牺牲,对象的生产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即对象转归异己力量、异己的人所有”[8],人被权力、资本、媒体和机器彻底控制,沦为功能性的一个部件,丧失了情感。
1989年上映的美国影片《为所应为》(DotheRightThing),由黑人导演斯派克·李执导,曾获得戛纳金棕榈和奥斯卡最佳原创剧本的提名。《为所应为》的整体结构与传统城市交响曲电影交相呼应。《柏林:城市交响曲》以柏林生活的交响曲为序幕,开始的画面呈现出动态视觉交响效果,描述一列火车在铁轨上奔驰,从乡村进入城市,《为所应为》的开头也与之相似:片头字幕逐一出现,背景音乐是嘻哈乐队“人民公敌”的歌曲“反抗权威”,然后按顺序描述了纽约布鲁克林黑人街区从早到晚一天的生活,用移动的画面构成的心理地图,展示了一天中各个阶段城市里的各种氛围和一系列冲突。鲁特曼的电影以真实的焰火结尾,传统的城市交响曲电影也经常用落日或者夜晚城市里的灯光充当“焰火”,而《为所应为》以社会性的“焰火”结尾,即片中萨尔的披萨店最后毁于大火,这实际上是一种社会反抗方式。导演将现实主义描摹与风格化视听语言融为一炉,运用倾斜构图、主观广角镜头等大量表现主义手法,当人物唱歌时舞台背景不停地变换,舞台幕布就像是城市交响曲电影里的大楼和街景,所不同的是该片更强调社区居民,强调人,反映出《为所应为》对传统城市交响曲电影的继承与新变。
斯派克·李是一位注重现场荷尔蒙和临场体验的导演,电影选择社会变迁中个体的日常生活体验作为表现对象,打破第四堵墙,让黑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和韩国人,分别朝着镜头,暴露心中最强烈的愤怒情绪。在狂躁、不安、热浪滚滚的街区环境里,充满拉丁舞曲、钢琴曲、蓝调、黑人说唱、hip-pop等各类音乐的交织,声音成为影片的升华妙笔。导演在影片最后,引用了20世纪60年代黑人运动的两位领袖马丁·路德·金与马尔科姆·艾克斯的话,前者倡导的是和平争取自己的权利,而后者则主张通过暴力手段取胜。导演在此触及到种族矛盾背后的实质问题,而他无意对此作出回答,持客观中立态度的导演将一切交由观众评判与思考。斯派克·李真正想要探讨的是美国广大黑人群体的茫然,选择马丁,还是马尔科姆?并不是一件能说清楚的事情。“种族歧视”的背后,或许还深藏着更多的社会矛盾,更复杂的人性问题。他只是想说明一个现象,呈现一个事实,而这一现象在三十年后开始波及世界的黑人民权运动中同样上演。《为所应为》影片的主线,就是一名黑人被警察暴力执法致死,从而引发群体性暴动。2020年5月25日的现实生活中,明尼苏达州的一名非裔男子遭白人警察“暴力执法”身亡,警察将膝盖压在黑人男子的后颈长达数分钟,直到气绝。电影与现实的互文本样态,在镜像对照中承载了对现代性异化的社会批判意义,电影成为整个世界的现代寓言。
由罗马尼亚导演拉杜·裘德执导的《倒霉性爱,发狂黄片》(BadLuckBangingorLoonyPorn)也可看作一部城市交响曲电影,曾获得2021年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同时,它还是第一部扎根于新冠疫情时期的国际电影,第一部“口罩电影”,也是一部论文电影、一部数据库电影。导演希望用该片来展现欧洲的现代文明,让电影成为时代的备忘录。影片像一幅布加勒斯特风情画,情色趣味、历史回顾与政治表达完美缝合,把疫情时代的日常自然地融进影片的叙事幽默中,非常具有代入感。影片结构谨严,复杂有序,是引言、三段式正文与多结尾结构,大雅大俗,蕴含着整个社会的样貌与生态,如同一部时代交响乐。第一段一开始就是生猛骇俗的性爱录像,然后是半纪录片式的跟拍,女主角行走于布加勒斯特街头,是本雅明《单行道》(Einbahnstrasse)的影像版,也蕴含居伊·德波《景观社会》(LaSociétéduSpectacle)与克拉考尔“街道电影”的精髓,城市漫游者视角与震惊体验跳出画面。第二部分辛辣刻薄而又冷静地解构了大部分国家后现代生活里的苦乐酸甜,字幕独立于声音,如影像版的《米沃什词典》(Milosz’sabc’s),意象丰富,描绘出罗马尼亚近代史,戈达尔式的科普、解说、讽刺、拼贴、恶搞兼而有之,也契合于追求快节奏短视频与高信息密度的当下生态。第三段即影片结尾,构架了一个舞台空间的审判场景,如同苏格拉底所经历的审判,在当代技术哲学与伦理学主题下产生了古希腊式美学倾向。人物脸上的口罩等同于古代戏剧的面具,也有着希腊神话的喻指,看人要通过映射借看,新冠时代的新命名是:看人要戴口罩看。结尾的未完成性的设计,使得所有的开放结局都不是答案。
导演拉杜·裘德通过交响曲式的多声部的反讽对话来讨论如今罗马尼亚的社会现实:贫富分化加剧、戾气横行、疫情加剧社会危机与信任危机、消费社会、种族歧视、反智、阴谋论、社死、阶级和性别的剥削、民族主义盛行、纳粹势力崛起、独裁、网络暴力、道德审判。疫情的爆发使这些恶意激化,怒火与偏见随处可见,疯狂无处不在。罗马尼亚如此,世界上的各个角落也是如此。互联网成为仇恨的完美载体,我们无法控制,也无处可逃,只能随着这个核武器一同爆炸。在这个疯狂的时代,我们需要这类更加疯狂的影片,以毒攻毒。不同的电影生态导致不同的电影文化,同样的疫情题材电影,由于视角不同,《倒霉性爱,发狂黄片》与《穿过寒冬拥抱你》《你是我的春天》等影片呈现出不同的美学特征,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当下电影,切中时弊,富有问题意识。影片结尾,化身神奇女侠的女教师用大网罩住乌合之众,还击无底线、恶毒、失控的网络社会,又把火把(在电影中是情趣玩具,男人的阴茎)塞进男人的口中,身穿红色衣服的女主人公像是一团火,独自燃烧,一如传统城市交响曲电影结尾的焰火升腾。这部电影也可以说是女主人公社死与新生的故事,戴着口罩的女教师最后成为一个女基督。
《为所应为》与《倒霉性爱,发狂黄片》秉承先锋实验的美学风格,与传统城市交响曲电影相互辉映,丰富了城市交响曲电影的表达形式。像这种反映现代性异化与抵抗异化的城市交响曲电影还有吉姆·贾木许执导的《地球之夜》(NightonEarth),这部在出租车里面拍摄的电影途经洛杉矶、纽约、巴黎、罗马、赫尔辛基五座城市,有着贾木许对个体的疏离、精神的异化、荒诞生话的嘲讽,展现出导演对不同种族、不同地域的人面对城市文化的思考。香特尔·阿克曼十八岁时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短片《我的城市》(BlowUpMyTown),在这部饱含先锋气质的城市交响曲电影中,阿克曼在她布鲁塞尔的厨房里打扫、清洁、点火,肆意破坏、嬉闹和狂欢,充满了少女的癔唱、疯癫与躁郁,用餐、清洁、擦鞋、照镜是挣扎的过程和最后的仪式。阿克曼在滑稽可笑、兴高采烈的气氛中点燃了煤气,引爆了厨房自杀,爆炸声一如传统城市交响曲电影中的焰火。她把房间隐喻为城市,狭小替代了宽广,在炸掉自己生活的这座城市的同时,对异化的自我进行破坏式消除,跳出了自己的生活,在让人震撼之余显示出鲜明的女性主义立场、激进的自我意识与反抗精神。她非常细腻地处理自己影片中的声音,去关照和呼应心底的孤鸣,毁掉的城市是影像中的物质空间,声音指向的抽象之地却留了下来。美国导演高佛雷·雷吉奥在旧金山拍摄的城市交响曲电影《失衡生活》(Koyaanisqatsi)中,展现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影片将现代化大都市看作一架庞大的机器,讲述了工业的影响和城市化进程中的潜在困境,传递出强烈的生态和环境保护意识。维姆·文德斯说:“摄影机是抵挡事物(毁灭)悲剧的武器,并抗拒它们的消逝。”[9]表象世界正被逐渐摧毁,电影是对抗这种消亡悲剧的武器。贾樟柯导演的《二十四城记》,欧宁、曹斐联合执导的《三元里》都深受《失衡生活》的影响。现代性的本质是人向人的复归,关于现代性异化、抵抗与超越异化的理论,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重构人的生存状态不可超越的哲学。正如居伊·德波所倡导的,“情境主义者不能被动而沉默地等待一场遥远的革命,而必须积极投入生活,彻底改造当下的日常生活,改变对世界的看法和变换社会的结构是同一件事情,通过自我解放,可以改变权力关系,并进而改造景观社会”[10]。以居伊·德波为核心主导的情境主义的文化活动,原本就始于总体都市主义或在生活中构建情境的计划,他们力图建构情境以打破常规,并由此使人们摆脱思考和行动的习惯性方式。
四、科幻题材城市交响曲电影中的乌托邦与反乌托邦
城市在科幻电影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科幻电影本身的未来感赋予城市景观特殊的含义。科幻电影是对未来城市的表现和想象的重要媒介,一是可以从空间和视觉的角度出发,去表现现实中未曾实现的未来城市;二是许多充满概念性的未来城市也能通过想象呈现在人们视野中。科幻电影中的城市不仅仅是故事的发生地与背景板,也具备重要的叙事功能,在推动情节发展的过程中,使城市成为文化与价值观念的表征,进而凸显未来世界的城市精神。“城市是上天的应许之地,也是对凡间市民的诅咒。城市既是天堂,也是地狱。有索多姆和娥摩拉那样的罪恶之城,也有耶路撒冷那样的圣城。”[11]如《星球大战》前传系列中银河共和国的首都科洛桑,是一颗被城市覆盖的星球,里面有巨大的穹顶建筑——银河议会,飞过银河议会的穹顶,可以看到矗立在一片开阔地中的绝地圣殿,这里是绝地学徒生活和学习的地方,有着浓郁的乌托邦色彩。《第九区》(District9)里的男主角因感染神秘病毒正逐渐变成外星人,为了不沦为研究的对象遭受非人的实验,他只有逃往惟一安全之地第九区,第九区因此成为城市乌托邦。《第五元素》(TheFifthElement)中的未来纽约城由竖直方向上切入的无数个横切面构成,通过立体化交通的分割与交通空间的多维复合结构,提供了未来城市设计和规划领域中城市交通组织方式的新的可能性。《黑客帝国》(TheMatrix)中的锡安是一个深入地下的城市,是逃出母体回到现实世界中的人们的最后一个栖息地,也是一座泛着希望之光的乌托邦城市。科幻电影中的城市有时是作为被摧毁的意象存在,如《流浪地球》中被冰封的北京、上海,被岩浆倒灌的地下杭州城;《V字仇杀队》(VforVendetta)中的伦敦与《蝙蝠侠黑暗骑士三部曲》(TheDarkKnightTrilogy)中的哥谭市都以暗黑风格示人,犯罪丛生、藏污纳垢。这些无论在具象意义上还是在抽象意义上的废墟城市,都呈现出一种反乌托邦色彩。
20世纪20年代,柏林是个杰出的现代城市。《柏林:城市交响曲》上映的同一年,也就是1927年,还上映了弗里茨·朗(Fritz Lang)执导的《大都会》(Metropolis),影片中蒙太奇手法的运用、人与城市的关系刻画以及城市生活的展现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质,尤其是序曲、幕间剧与终章的结构,也可视为一部城市交响曲电影。这两部影片从现在与未来两个不同的维度丰富了柏林这座城市的内涵。《大都会》是一部一直被效法的无声片时代杰作,也是科幻电影史的第一座丰碑,其影响在后世科幻片中处处可见,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疯狂科学怪人,还是《未来世界》《银翼杀手》《第五元素》《星球大战》等影片中对未来城市景观的想象,全都有《大都会》的影子。影片对20世纪70年代后出现的赛博格电影也产生了巨大影响,被誉为赛博格电影鼻祖。片中的玛丽娅这一人物形象标志着电影史上第一个女性机器人的诞生,通过表现主义反技术观念下的内在叙事逻辑,建构起了一套后工业社会的技术及人类想象,贡献了有关未来叙事、赛博格甚至后人类相关的电影母题,为当代科幻电影中的女性赛博格主义提供了未来想象与范式。《神奇女侠》(WonderWoman)、《超体》(Lucy)、《机械姬》(ExMachina)、《黑寡妇》(BlackWidow)、《钛》(Titane)等影片中的女性都有着玛丽娅的影子。
《大都会》这部现代主义电影向我们展示了都市中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交织的未来,它的时间设定在遥远的2000年,将现代性放在未来城市背景下,同时也强调它的物质毁灭。片中描绘了一个严重分裂的世界,在那里,富有的资本家在美丽的花园和宫殿中享受生活,并在他们昂贵的摩天大楼中从高处管理城市,而工人远离光明和自然,在地下深处为奴,为城市提供动力的伟大机器服务。《大都会》中“上下”垂直分野的等级结构与空间分割地理景观理念,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冲突的具象化,也影响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CityLights)、科幻片《超人》(Superman)、《银翼杀手》、韩国的《寄生虫》(Parasite),以及中国的《马路天使》《我叫刘跃进》等影片。《大都会》中的城市景观以新巴别塔为中心,大体量的高楼大厦如钢筋混凝土组成的高大丛林,呈现出一种压迫和僵硬感,交通系统呈垂直结构,汽车与飞机在楼宇之间穿行,看上去发达无比,和建筑师柯布西耶所描述的“光辉城市”有些相似,通过空间结构象征的二元对立的城市、宏大细密的都市景观与无限复制的流水线等后工业社会的特有形象贯穿了整部影片。《大都会》结合了宗教、劳动和革命的主题,揭露了对底层民众的全面监控:工人被剥夺权力、工人的幼稚病、残酷的剥削、劳资冲突、趋于疯狂的技术革新和自我毁灭,通过电影场景展示了对城市和技术的狂热,表现了乌托邦的未来,在叙事中批判性地表现了对于现代主义未来的反乌托邦思想。
雷德利·斯科特执导的《银翼杀手》是一部后现代主义科幻电影,也是赛博朋克电影的开山之作。它像一首浪漫凄美的未来诗篇,有着传统城市交响曲电影的韵律与节奏。这部向《大都会》致敬的电影引用了《大都会》的布景设计、叙事和主题。斯科特将故事发生地安置在未来的洛杉矶,在戴维·莱昂看来,洛杉矶是“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后现代城市”,肮脏的贫民窟和翻新改造过的社区、机场、酒店和大型购物中心等,都有着后现代性的典型特征,是世界上市中心向郊区分散的、最具象征意义的空间,具有“不断移动的、碎片式的城市流动”,这种“象征性的没有中心”使洛杉矶总体上成为“后现代消费文化的一个隐喻:一切都是零碎的,混杂的,分散的,多元的,而且受制于消费者的选择”。[12]在文化地理学者迈克·克朗的眼里,“这座城市是由黑暗的底层世界补缀起来的,肮脏的城市内部被清楚地描绘出来。城市生活的社会分割被描绘在这些明暗不同的空间里”[13]。《银翼杀手》中的洛杉矶面对现实世界中出现的工业过剩、人口膨胀、生态危机等问题,作为一个异化的都市空间,在电影史上是黑色电影的常设背景。
在赛博朋克电影中,场景构建和视觉空间是其影像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电影用大量的赛博元素来描绘未来世界人类的生存状况,整座城市被设计成由多个巨型建筑组成,这些巨型构筑物可以反复变换着它们的外表。《银翼杀手》营造的可以承载成千上万居民的单片集成城,是未来城市规划的理想蓝图。里面的建筑风格将东西方古典元素和现代元素糅合在一起,泰瑞公司的大楼结合了古埃及、玛雅、阿兹特克人的金字塔建筑风格,建筑物表面的巨幅广告牌、错落有致的霓虹灯,其美学灵感则来自香港九龙城寨和东京涩谷。在穿梭于高楼大厦间的快速飞车下面,是肮脏拥挤的街道;在遮蔽了半个天空的巨幅广告下面,是来自世界各地的芸芸众生。全片色调阴郁、黑暗,不停的下着绵绵的酸雨,热闹的大都市与阴暗潮湿的角落,炫彩霓虹灯和严重的环境污染叠加在一起,营造出一个异常复杂的人文环境。后人类科幻电影中反乌托邦化的未来城市想象,携带着鲜明的当代文化症候,既体现了科技发展引发的文化焦虑,也折射出当下的世界性城市危机。“想象的地理学”在影片中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心灵地图,从而实现了和现实洛杉矶的地理学互文。现在既指向未来,又面对过去,而未来就是现在。《银翼杀手》不仅是对未来世界的幻想,也是对现实世界的担忧。复制人拥有与人类相同的思维和感情,并对人类表现出爱;人类在追杀复制人的过程中失去对生命的敬畏,从而丧失了人性的光辉。斯科特沿用黑色电影的传统表现手法并糅合各种风格表现未来,实际探讨的是一个人应该如何去“认识自我”和“寻找身份”的古老命题,我们看到并经历的是不是人类的主观世界?情感记忆是人之为人的一个标志,相比揭露真相,《银翼杀手》更多的是在唤起想象。对生命的渴望和关乎人性的哲思,使《银翼杀手》成为永不过时的经典。《银翼杀手》颓废的美感、伤感忧郁的情绪、迷幻的音乐、质疑世界本质的虚无主义,以及反乌托邦精神的赛博朋克风格,影响了之后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Intelligence)、《云图》(CloudAtlas)、《攻壳机动队》(GhostintheShell)、《银翼杀手2049》(BladeRunner2049)、《阿丽塔·战斗天使》(Alita:BattleAngel)等很多科幻电影。《银翼杀手》的结尾,复制人罗伊静静坐化,凝重的独白溶解在绵延不绝的霓虹色烟雨中,随着他的死去,一只白鸽划过天际,可视为早期城市交响曲电影结尾的变奏。
20世纪20年代城市交响曲电影建立起了自己的类型特征与美学观念,此后的发展过程中,在延续传统的同时进行不同维度的创新与现代性转化,寻求表现城市生活的路径,用影像独特的节奏与调性反映城市的内在真实。当然,正如其他类型电影从来都不是单一的类型电影,只是在某种类型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一样,本文研究的这些城市交响曲电影,也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城市交响曲电影,有的影片同时还兼具实验电影、诗电影、论文电影、街道电影、数据库电影、纪录片、科幻片、赛博格电影、赛博朋克电影的特性,具有爱情片、动作片、冒险片、灾难片、黑色电影中的某些类型与风格。这些电影创作者以视觉的形式构建了城市的社会和空间特征,以其对景观人文的呈现,让我们感受到他们所创造的城市空间实践与空间想象形式之间的交互共振,并反映出特定的时代与城市精神。在镜头有节奏的切割和重新组合中,城市正在流转,影像记录永恒。在电影人的影像与观众的目光之间,一个新的城市拔地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