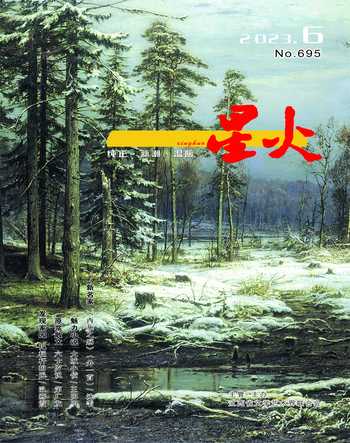古巴的海
夜雨,1998年生于山东临沂。此前未发表过文学作品。
一
医院花园种满了梧桐树。大风吹过,金黄叶子缓缓落下,点缀了碧绿水面。
赵长松吐一口烟,嘴巴里散发着苦涩味道,这是舌尖对自己没吃早饭还抽掉半盒烟的抗议。
赵长松拿不准现在要不要上去见刘玲。刘玲的姐姐这会儿正陪伴她。
妻子刘玲罹患尿毒症已五年,没有痊愈的可能。还能活多久?谁也闹不清楚。意外和明天哪个先到来?对于赵长松来说,这个破问题没有答案。一脚踢飞可乐空瓶,红色瓶盖砸上沥青路面,反弹进绿化带。结婚才七年,将近五年的时间往医院跑。可生活还得继续不是吗?
走进电梯,工作人员问他去几楼,他轻描淡写地吐出两个音节。电梯门关闭,隔绝了流动的空气,封闭的空间锁住呼吸。头顶的散气孔就是装饰,漆黑得像是用马克笔精心涂抹。有没有一种职业,专门涂抹孔洞,使其显得漆黑异常?
走出电梯,来到病房前,房内妻子正与姐姐抱头痛哭。站在门口,他没有勇气进去。
姐姐从背包里掏出一沓鲜红钞票,塞进妻子怀里,妻子想推辞,伸出的手悬到半空,嘴巴半张,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姐姐把妻子的手按下去,擦了擦眼泪,告别,转身与赵长松撞到一起。一场虚假的客套后,才把姐姐放走。
赵长松来到妻子身边。妻子擦干眼泪,把钞票装进口袋,连数也没数。他坐在床沿,把妻子的头按进怀里,轻声问她吃不吃苹果。他知道,只有扭头削苹果皮的时候,她才能安心地哭泣。他从装着水壶卫生纸等杂物的塑料袋里掏出一个苹果,找出削皮刀,刺进苹果的身体。
胸口的衣服被泪水湿透,手中的苹果皮越来越长。
把光秃秃的苹果递给妻子,妻子不吃,只是说,咱们回家吧,我缓过来了。把光秃秃的去皮苹果塞进满满当当的塑料袋,一只手提着,另一只手搀扶妻子。他没有感到吃力。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习惯了轻飘飘的妻子。将她抱到车上,打着火,心血来潮,想问她要不要吃一个冰淇淋时,她已睡着了。赵长松格外注意避免紧急刹车或者鸣笛。就连抱她上楼也小心翼翼。将她放到床上,轻轻盖上被子,倒了一杯热水放在床头柜,关上门,他终于能够松一口气。
二
推开书房的门,各种书籍挤在书架上,琳琅满目,落满灰尘。手指滑过书脊,指纹被灰尘覆盖。点上一根烟,坐在书桌前,思绪比喷薄的烟气更加纷乱。回头看了一眼书架,每本书都像一个招揽嫖客的小姐,冲他搔首弄姿,仿佛在说:来快活呀!他心里痒痒的,想掏出一本黄国俊的短篇小说集子读起来。当然,卡波蒂的也行。欲望来得强烈,点燃整屋的书,燃起熊熊烈火,把他炙烤得难受。眼光落到书架边角的几本杂志上,里面收录了他年轻时写的小说。
他还记得第一篇小说发表的时候,整晚没有睡着,好不容易挨到天明,迫不及待拨通妻子的电话—那時妻子还是他的女朋友,诉说了整整三个小时。事情的发展似乎越来越顺利,第一篇、第二篇……直到,妻子查出来尿毒症,一切戛然而止。灰尘渐渐落满书架。
打开电脑,他审视着自己眼前写下的小说。人物和场景都不堪入目。但这类故事能换到八百块钱,或许更多。联系到专收这类小说的二手贩子,给他发过去。默默坐着,等待回复。
转过椅子,才察觉出指尖的疼痛。原来十指早已皲裂,密密麻麻的伤口。这是他的第一职业留给他的职业病。白天在亲戚开的工厂里打工,刨去每周三次、每次半天的请假,一个月能挣三千四百块钱。再加上下班时写写这种来钱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勉强还能将生活维持下去。还是入不敷出,积蓄慢慢减少直至荡然无存。他盘算着,下个月该怎么开口掠夺父母那份稀少得可怜的养老金。
烦恼掺和着满屋的二手烟,熏得他头脑阵阵疼痛。起身把窗帘拉开,打开窗户,贪婪地呼吸着掺杂了雾霾的空气。夜幕降临,星星点点的灯光装饰着钢筋混凝土的楼。如果他还在写正经小说的话,这个场面他一定要写进去。
手机响了起来,打断赵长松的思绪,是许久未联系的老友陈鹏请他吃饭。电话里,陈鹏哭着说,女朋友把他甩了。
三
做好饭,给妻子端到床上,坐在一边等她吃完,他才敢出门去。
秋风带来一丝冷意,昏暗路灯照不亮的是漆黑灌木丛,叶片铺满灰尘,脏兮兮,正在等待一场秋雨。把脖子缩进外套,挺不直腰杆。妻子的话语在耳边响起:气质你懂不懂?抬头挺胸才有气质,快把你的龟腰挺直喽!
他怎么也挺不直弯曲的腰杆,不清楚是劳累压弯了脊梁,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走到饭店门口的时候,陈鹏已等候多时。进入饭店,找了个僻静角落,陈鹏点了四个菜,两扎银麦牌瓶装啤酒。看架势要不醉不归。
“松哥,嫂子怎么样了?”陈鹏熟练地拆开餐具的塑封袋,装作不经意地询问。
“还那样,隔几天就去医院做透析。”赵长松用手指在啤酒袋上戳了个窟窿,勾出一瓶,用牙齿起开瓶盖,给陈鹏递过去。
无言,只有喉咙吞咽与啤酒泡沫躁动不安。菜还没端上来,俩人各喝掉一瓶。在开第二瓶的时候,油炸花生米、藕盒、春卷三拼盘被服务员端上了桌。花生米酥脆,夹着肉馅的藕盒香脆,春卷外焦里嫩,是韭菜豆腐馅的。单身的时候,兄弟几个总是聚在这家小饭店里,胡吃海喝,畅谈理想。一是这里的饭菜价格实惠,量大;二是口味独特,比较符合胃口。随着年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能聚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赵长松喝着啤酒,想起妻子最爱吃这里的猪蹄,嫩柔软糯,麻辣火爆。医生不让她吃太辣的食物,可她的口味又是那么重,要是她看到点菜区那盆靠在火炉上慢煨的麻辣猪蹄,准会两眼放光。
“松哥!小青把我甩了。”陈鹏酒量不好,两瓶啤酒下肚已是微醺,“她嫌弃我工资少,有房贷。可是我对她那么好。你说,大小节日,礼物一样没有落下。平时就不用说了,什么都是先想着她。我对她一心一意,可是,最终却落得这个下场。”
赵长松把手搭在他的背上,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生活被病情和钞票压得喘不过气,突然聊到情感生活,仿佛是上辈子的体验。“吃菜!”赵长松用筷子指了指刚上桌的炒鸡。被剁得零碎的鸡肉,用油盐酱醋精心烹调,最后撒上一大把干辣椒,翻炒几下,端上餐桌,冒着热气,油光灿烂。夹起一块,放进嘴里,鲜美滋味与舌头纠缠,难舍难分。安静倾听陈鹏诉苦,他知道自己能为他做的事情很少,苦涩笑容不经意间在脸上绽开。陈鹏口中那些事情,在他看来又算得上什么呢?
啤酒在两人口中消失的速度异常快,四个菜刚刚上齐,陈鹏已经在抠第二扎啤酒的塑料袋。酒精在脑袋里肆虐,意识开始和眼睛玩起了捉迷藏。终于,酒桌上的气氛轻松起来,陈鹏开始讲起年轻时候的趣事。
“我现在还记得!有一次咱们和初中那个酒蒙子一起喝,你来晚了,自罚三杯。那个酒蒙子是真能喝!直接倒了两盆啤酒,一盆足足有三四瓶,给你说,不用罚酒,跟他对喝这盆就行。他嘎嘎一口闷掉了,你也是不服输,也给一口气干掉了。然后你说去厕所,扭头打了个出租,逃回家了。”陈鹏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没想到那个楞子这么能喝,这一盆酒,直接给我干蒙了。我当时就想,他妈的,我再喝一圈,非得像喷泉那样喷到桌子上。你还记得吧?咱们高中大门口的那个喷泉,喷得有一米多高。我当时就想,要是跟那喷泉一样就丢人现眼了!我直接,头也不回,去你们的吧!打了个车就回家了。”赵长松也掩面大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现在只想抽烟,然后再喝一口。
陈鹏贴心地点上了烟,啜了几口,塞进他嘴里,又给自己点上一根。烟雾缭绕在桌子上方,形成一团难以消散的迷雾。
四
菜没怎么动,酒已经喝光了。赵长松的尿意涌上来,起身去二楼上厕所。点菜区装着麻辣猪蹄子的大盆快空了,赵长松跟老板娘说,给留上一份打包带走。叼着香烟,步伐摇摆,双腿绵软,就连尿液也溅到便坑外边。再下楼时,陈鹏已经打包好饭菜,递给他。
“松哥,这几个菜都没怎么动,你拿回家热热,跟嫂子对付对付。猪蹄子我给付过钱了,我知道嫂子爱吃,你拿着。”陈鹏搂着赵长松的肩膀,否则在酒精的作用下,站不稳,会重重摔倒在地上。
“兄弟,有个事需要你帮忙,你有个伙计不是二手车贩子吗?你让他帮我打听打听,我那车能卖多少钱。”赵长松猛吸一口烟,等到两扇肺吸收干净,才吐出来。
“怎么,松哥你要换新车了?”陈鹏歪着头问。
“我想换辆几千块钱的破车,马上冬天了,不能叫你嫂子冻着。”
“放心松哥!等我明天醒酒了就给你问,兄弟办事你放心,肯定给你安排得板板正正的。”
“兄弟,谢谢了。”赵长松扶着陈鹏,往外面走去。
大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对街超市的员工,正搬弄摆放在门口的冰柜,马上打烊。送别了老友,赵长松提溜着饭菜,晃晃悠悠回家。头脑很不清醒,马路上的直线变得歪曲。两旁的法国梧桐树,叶子已经泛黄,开始脱落。秋风吹,卷起一波残叶,夹杂着塑料垃圾,旋转不停。困倦涌上头脑,眼皮沉重,多想找块平坦的石板路,躺下,沉睡不醒。
可是手里还提着妻子最爱吃的猪蹄子,再不回家就要凉透了。猜不准,她是否入睡。倒是希望她睡梦香甜,这个想法肯定奢侈,刚做完透析的身体还要疼痛许久。
五
站在家门口,赵长松扇了自己两个嘴巴子,酒醉醒了七八分。掏出钥匙,进家门,打开灯,把菜放到餐桌上,想找一杯水喝。拿起杯子,接水,灌进喉咙。突然意识到哪里不对,扭过头去,桌子上,一沓钞票被水杯死死压住。这沓钞票拿在手里,沉甸甸。一、二、三……足足有五千块钱。赵长松知道,这是刘玲亲姐给她的钱。把钱扔到桌面,顾不上收拾,轻轻打开卧室的门,停顿三秒,确认酒醒,推门进去。妻子闭着眼,不知道睡了没有。蹑手蹑脚钻进被子,倚在床头,眼前漆黑一片。妻子翻了身,钻到他怀里。
“你想吃夜宵吗?”赵长松打起精神问,“我打包了剩菜,还专门买了麻辣猪蹄,是你最喜欢吃的。”
“没有胃口。”她把脸埋进他的肋间,“你真好。”
黑暗中,他感到脸上湿漉漉的,趁着黑暗擦拭干净。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不,别动,让我抱你一会。”
“陈鹏失恋了,哭得稀里哗啦的。”他试图融化氛围,“我的酒量大不如从前,你还记得咱们喝得烂醉那次吗?几乎把家里的酒都喝掉了,那可是半面墙的高度洋酒。”
“当然记得!你钻在马桶里吐个不停,我都不敢冲水,好像按下冲水按钮,你就会被马桶吞进去,最后从太平洋里钻出来。”她笑个不停,下巴戳得他肋骨痒痒。
“你也好不到哪里去!”他说,“我一抬头,你就躺在地上,怎么叫都起不来。”
“真好啊!”她不笑了,“等我病好了,咱们就去太平洋玩。”
“现在也能去!”
“不能去太远的地方。”
“那就去近的!看看海总行。”
“古巴的海是不是很美呀?”
“那是当然了,古巴四面环海。”
“是太平洋吗?”
“不,是加勒比海。”
“你说古巴真的像网上说的那样吗?服务员可以不用看顾客的脸色,不顺眼就可以撂挑子,不理他?”
“也许是吧。”
“我好想去古巴看看海。”
“好!我跟你保證!一定带你去!”
黑暗中,空气停滞了。悲伤像雾气,不知从什么地方升起,淹没卧室,顺着窗户缝,挤到外面去。手机提示音打破了寂静,是他写的那个故事有回音了。二手贩子发来消息,告诉他稿子收了,一字不改,后天就可以把稿费打给他。挂了电话,他告诉她,是陈鹏问他有没有到家。他不想让她知道自己在写那样的东西。
“你真不吃了?”他问她,得到了肯定的答复。“那我把菜放进冰箱。”
把饭菜放进冰箱,收起桌上的五千块钱,终于松了一口气。喝掉一大杯水,去厕所尿尿。他想是不是再写一篇那样的东西。
钻进书房,打开灯,整墙的书籍闯入眼帘,这些书他已看过十之八九。手指轻轻滑过书脊,是鲁尔福是福克纳是布尔加科夫。那年,电商平台打折,几乎一半的书都是二十元以下的价格买来的。是时候让这些书发挥自己的价值了。他找了两个纸箱,却挑不出自己不喜欢的书。打起精神,鼓起勇气,把这本放到这个纸箱里,把那本放到那个纸箱。纸箱还是没有装满。终于,他朝古典文学下手了。大仲马莫泊桑巴尔扎克,全部被他塞进箱子。这些书即将迎来自己最终的命运,贱卖。
六
他的书摊支起来了,就在医院门口。用一个拆开的麻袋垫在地上,把书摆在上面,麻袋上摆不开就摞在后备箱里。妻子做透析的时候,他就在医院大楼底下叫卖。
“你这个书多少钱?”一个光头男人问。
“这边的十块,那边的五块。”他抬头看了一眼,愣住了。
“是正版吗?”光头男人抬头看他,一拍脑门,激动地喊,“赵长松?”
“马老师!”
赵长松一眼就认出来了,这个光头男人是市里文学杂志的主编,赵长松的第一篇小说就发表在马老师编的杂志上。他还记得,接到马老师的电话,约他第二天去杂志社坐坐,他激动得和妻子打了一晚上电话。马老师是他真正意义上的伯乐,给他沏了一杯茶,没有因为他是新人就轻视他。“你是我见过的最有天赋的小说家!”马老师这句鼓励的话,赵长松一直记得。不止如此,他还给赵长松推荐别省的杂志,帮他催问审稿情况。但是从妻子查出尿毒症的第三年起,赵长松不再正儿八经写小说。马老师打电话来,一个劲地说:可惜,可惜。
“马老师!您看上哪些?我送给您。”赵长松说。
“不用,不用!许久没见了,得好些年了吧?”马老师坐在马扎上,“小刘还好吗?”
“是好久没见了。她还是那个样子。”
“是吗,太可惜了。”马老师尴尬地抚摸光头,“里头这么多好书,再版不知道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舍得卖书了?”
赵长松不好意思地说:“把书都卖了,我暂时也看不着。”
“现在还写小说吗?”马老师换了个话题,想让对话的氛围轻松点。
“啊,早就不写了。”赵长松低着头,他不好意思告诉马老师自己目前写的东西,马老师该多失望啊。
一个顾客打断他们的交谈,拿着一本书使劲在赵长松眼前挥舞,大声叫喊:“老板!你这书卖多少钱?”
“这边的五块!那边的十块!随便挑随便选!”赵长松吆喝着。
马老师站起身,和赵长松告了别。看着马老师渐行渐远的背影,赵长松裹紧了外套。秋风吹得凶猛,竟让人感到寒冷。
天气渐渐阴沉起来,快要下雨了。人群散去,赵长松一本一本往车里收书。天色渐晚,黑暗正渐渐入侵曾经绚丽的景色。把最后一本书放进后备箱,是《佩德罗·巴拉莫》,还记得读完这本书的时候,他一下瘫倒在床上,那种美妙的心情久久不能消散。早已忘记的感觉,此刻涌上心头。是兴奋?是激动?是迷醉?是一种身心的洗礼。
后备箱刚砰地关上,雨滴从天空中落下,砸到脸上。赵长松抬起头来,雨滴钻进他的眼睛。他蹲到地上,雨滴砸在后脑勺。雨水拍打自行车遮阳棚,发出怪异的声音。该把车开进医院停车场了,妻子还等着他。想起身,怎么也直不起脊背。钻进眼睛的雨滴让他面部发酸,五官扭在一起。用手擦眼中的雨水,却怎么也擦不干净。
那是秋天的第一场雨,也是最后一场。
七
眼看书架上的书慢慢减少,直至最后一本,赵长松也没等来第二场秋雨。
腊月的时候,赵长松裹得严严实实下楼买烟,还是觉得寒冷无比。买了一包泰山牌的香烟,撕开塑封袋,抽掉锡箔纸,点上一根,在商店门口吸起来。不远处,一对情侣正嬉戏打闹,男的揽住女的肩膀,走到赵长松身边。
“松哥!”
原来是陈鹏,他怀搂一名陌生女子,冲赵长松打招呼。
“松哥!这是我女朋友,小雨!”
“你好,你好。”
“对了松哥,上次你让我问的事,我问过了。”
赵长松给陈鹏递上一根烟,使劲回忆,也想不起拜托过陈鹏什么事情。
“就是卖车那个事!你忘啦?”
“啊!是这个事啊!”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安排,直接开去换车,给算现金。”
赵长松说:“不用了,没那个必要了。”
“嫂子好啦?”他脱口而出。
刚刚说完,陈鹏突然愣住,狠狠扇了自己一个耳光。赵长松脸上挂着的笑容,格外惨淡。他没有再说什么,独自走了。
天空中飄起雪花,慢慢压住赵长松的肩膀、后背。他掏出烟盒,用嘴叼出一根烟,点上,裹紧了羽绒服。石板上,落满了薄薄的积雪,踩在上面,一直打滑。抬起头,望向天空,眼里塞满了砂糖一样的雪花。
刚才忘了和陈鹏客套一下,毕竟人家是为了自己的事情忙活。
顾不上寒冷,转身走回去。
商店门口,陈鹏和他的新女朋友早已走了。去哪里找他呢?赵长松不知道。
妻子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赵长松都提不起劲来。网上的二道贩子联系过他好几次,说他的东西很受欢迎,让他多写点,他拉黑了二道贩子,那样的东西他是不会再写了。
大概几个月后,赵长松开始着手去古巴看海的事,他必须替妻子完成遗愿。真的开始着手,赵长松才知道有多麻烦,不止是走程序的问题,还有经费等各种现实问题。
妻子就这样如愿地用俗务把他羁绊在了这个世上,直到等来今夜的一场雪。
雪,还是很美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