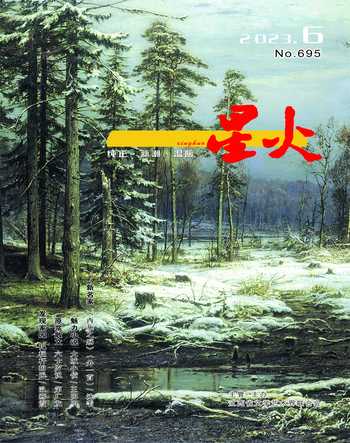一条大河
张声殳,本名张馨怡,1999年生,福建福州人,现复旦大学中文系戏剧专业在读。
有时候,我会想起初三暑假,奶奶去世的那天早上。
太阳热得枯倦,母亲已在巷口等待。去伯父家探望,挪空的客厅,门后病人的呼吸声,爷爷端一碗西红柿鸡蛋面片,声音低垂可怜,好像马上做鳏夫的人是他。的确是他。我的意思是,好像家里要紧的不是死人,而是多一位鳏夫。母亲抱着深切同情,和前一天一样说:
“爸爸,你要顾好身体。番茄蛋花好,有荤有素,你要注意营养,自己煮饭来吃啊。”
爷爷纷乱的发梢摇晃着,拍拍母亲的手。我偎在冰箱边,见他掏出手帕,摘下老花镜,哀叹声随泪水拭净泄出。听力渐衰的副产品是嗓音响亮,我心下怀疑,里屋是否有耳朵被唤醒。
寒暄结束,爷爷转开门,我们的视线刚及枕垫,门便又被关上。我为今天不必入室坐守而庆幸万分。
母亲爱用一个词形容我们:老张家的。她靠语调和嘴角给名词赋予色彩,往后十余年中,我按图索骥。接到奶奶过世消息的那天早上,震惊是早已备好的。父亲先下楼,从柴火间推出电动车,凉鞋磨在地面上,我知道此刻最好跑上前去。跨上座时,我才窥探他的悲容。没有。他面色凝滞,不带隐忍或茫然,一点水渍已干枯,结在眼角边。葬礼三天,父亲未露出任何悲伤的迹象,后来谈起奶奶,也只是脸上多几分尴尬,停一会,再放出老张家的既定说辞:她啊,命苦,那么年轻,没享几天福就走了。
奶奶去世时六十七岁,退休十六年,期间每一天,都在为老张家平静地工作。
近两年,我试图串联某人的一生。八月九日,一九四八或一九四九年,卓姓,福州的闽,兰花的兰。登记员听岔了,写成明南,与衰老后矮胖沉默的样子,倒也相称。年份写早还是写晚一年,闹不清究竟哪个。火化那天,她灵魂飞回了家,带儿媳妇于梦中找见墙上挂包里的三千块钱。她的忌日也是八月九号。小孙女发现了这点,悄声提出,在头七的火盆边,大家啧啧称奇。
小学时,扎两条麻花辫,值得她说道的事件,是午饭吃到一块狗肉;五年级一毕业,她就进了工厂;生怕调皮的孙女让她听写小学二年级生字,每当这时,高压锅总不能正常运转;十六岁那年,镇上举行歌唱比赛,她报了名,没等叫名字就跑走;再后来,因她的父亲去了台湾,她的出身成了问题。
母亲说,别看奶奶总骂你爷爷死老头子,那时候,他们爱得轰轰烈烈。你爷爷三代贫农,前途大好,却死活要娶你奶奶,所以一辈子没能升上车间组长。
我记得,接我回家的坡道上,奶奶几次讲起自己的罗曼史,竟有些轻悄的得意:以前,也有个军官的儿子追我呢,他很高,晒得黑黑的,笑起来一口白牙,天天跑来家门口搭话。
我的奶奶,生性沉默,似乎从无自己的生活主张。想要表示对她的关心极为简单,只需重复几个关键词,譬如,油炸食品。奶奶喜欢吃炸的东西:炸油饼,炸萝卜糕,炸蚵嗲。奶奶对油炸食品的喜爱很广泛。母亲把前一天夜里吃剩的饺子煎热端上桌,说一句,妈,你喜欢吃的炸的。有阵子,父亲得了许多茶点店的折扣券,聚餐總点上一份榴莲酥。次数多了,奶奶说,那地方太高档,不习惯。
奶奶喜欢油炸,也喜欢卤味。奶奶去世那年的六月,我去看她,鸡翅的卤香充盈整间屋子。伯母在灶前忙活,说,奶奶想吃卤鸡翅。奶奶坐在木椅上,一条腿用板凳垫高了,脚下放着痰盂。她嚼,嚼,对我笑笑,把肉全吐进痰盂。奶奶就尝个味道,伯母解释说。
我们也有互相逗乐的回忆。我小学六年的每天正午到晚上,奶奶会到我家打点家务,天黑时回伯父家,顺便拎垃圾下楼。铁门发出荡悠悠的回声,父亲瘫在沙发,问候斜斜飘去:妈,慢走哈。回答的是只有他懂的福州话:慢走走到明天早上啊。很快我也学会了,每次在父亲背后一叠声地抢答,于是大家都笑起来,奶奶也笑,嗤的一声。偶尔我听这声响近似鄙夷。
大部分时间里,奶奶只有一种笑,在别人都笑完了,就差她一人时发出,像是宴席上众人早已开席而她才上桌。我用心窥察着。奶奶这人,不好取悦。你夸她今天的布衫漂亮,她冷笑说老依姆了还漂亮什么;给她夹一块排骨,不久她又放回去;若你想帮她洗洗碗盘,这便惹她大怒,怎样也和她讲不通小孩为何要做家务,只好借口说,能挣零花钱。第二天,奶奶叫住我,腰包里翻出皱卷的五块、十块。给你,不要洗盘子了。我跳开来不肯收。她一把将钱砸到我身上,转头就走。
五年级那年的冬天,上桌早已天黑,炖盅的热气笼着奶奶的窃喜,她预告说,饭后有东西要给我看。我加速把米饭填进嘴里,但奶奶摇头,不行,把菜吃完。晚饭终于结束,奶奶蹲在地垫边轻轻招手,靠近点,再靠近点。我咬着筷子,几近趴下。她将垫子一扬,一只被压扁的蟑螂,触须还微微颤动。我尖叫着飞了出去。
奶奶帮我对蟑螂脱敏的尝试就此告结。不讨好的事,她也不是头一回做。我和奶奶不亲,和同学聊起时,我往往这样讲:我姐姐是奶奶带大的,我是我妈带大的。奶奶只有每天放学来接我。回家的路不长,够高低两双短腿走上三刻钟,奶奶的热情留在前段。要不要吃这个?她指着葡京小站,又张望杂货铺,不经我同意,就要打上一杯路旁的甜豆花。我向来不贪嘴,摆手逐渐加速为不耐烦。通道口立着安德鲁森面包店,邀请与婉拒皆于此处抵达极限。奶奶说,什么都不吃,你要瘦死。我说,那太好了。她又指橱窗里华美的肉松海苔包,我扭过脸。她嗤一声,往通道走去。
时有歇脚的白糕车推过。屉布掀开,热气蒸腾,糕铲已在待令。奶奶与我对视一眼:来一块五的。这种清甜软糯的食物,不夹果仁,仅凭自身米香,凉掉便无滋无味。奶奶催我快吃,这点点,一口气吃完了,回家还有排骨汤。那时,福州遍地的芒果树还未受虫灾摧残,青果把枝压得极低,奶奶站在台阶上,踮脚就能够到。摘两个吧,我怂恿她。她拽下一串。待熟的果子,带着清香,微涩。似乎因满心期待而不得,我们轮番嗅个不停。
十余年里,时间周而复始,并无多少不同:除夕,元宵,清明,端午,中秋,固定的菜肴;开学,期中,期末,放假,学期结束预知下个结束也会如此。生日是一碗太平燕,两颗鱼丸,两个鹌鹑蛋。节日是一人一碗。奶奶照例缺席所有餐桌,她从厨房出来,赶最后一盘炒白果的趟。
奶奶走后第四年,我重返老张家的年夜饭。旧屋拆迁,租房不容大圆桌,但姐姐远嫁,伯母渐消瘦,方桌倒也正好。记忆以加减的形式呈现:减去春卷、虾饼、南瓜酥,减去饭前窝在床上打牌吃小食的时光。儿时除夕的中午,电话便催促不止。早点进来啊,伯父说。不知为何,去老张家始终是“进来”,不是“回来”“过来”,它让人费心,感到几分重。午饭我只应付两口,记着奶奶的叮嘱:早点来,这次的虾饼好吃。我们进门时,奶奶已在油锅前站守。换上拖鞋,打过招呼,炸物分秒不差端上来,烫着手,酥脆作响。奶奶叉腰,看我们将它抢空。
这会儿,五菜一汤,伯父帮衬着一盘盘端上。姐姐呢?我问父亲。他做噤声手势。于是换上笑脸,把菜色逐道夸过去,问食材,问做法,问市场的热闹。我回去躺一会儿,伯母最终说。爷爷端半碗猫饭,在客厅游荡。看看春晚吧,伯父提议。六点十分,还有很久。
十八岁,过去的重点项目烟花,也已失去吸引力。天台整层是爷爷的殖民地,搭爬架,缠丝瓜,其下满当的小盆大缸,春种番茄,夏种薄荷与无花果,秋冬种花菜,此刻统统收入储藏间,为在烟火下得保周全。这是父亲一年一度最慷慨的时候,他抽出两张粉红钞票给我们,姐姐和我手牵手,往三岔路口的烟火摊,挑至零钱用尽。先从柱体、锥体状的小立式烟花放起,火花蹿到半人高,配着尖细嘘声,不大惹人喜爱;接着点满天飞的回旋炮,尖叫,躲避,不知怎么就放完了。放过的烟花壳,用扫帚聚拢起来,燃上一个小火堆。之后是冲天炮。你们谁来放?父亲挥舞长筒挑衅。我主动请缨,油面纸紧攥在双手,滑腻腻的。有个疑惑贯穿我玩冲天炮的年月:或许是我拿反了,它才迟迟不响?每次,火花都顺利飞向围栏外。
烟花燃放殆尽,火堆愈聚愈高。远处,夜晚的重头戏才刚启动,礼花四面飞升凋落,耳际砰砰声此起彼伏。礼花果然得远着看。我挂上栏杆,男人们叉腰于火边,姐姐、伯母和奶奶则挽着胳膊,挨在楼梯口探头。
其实我无法记清那些热闹片段里,是否有奶奶参与;或许仅为主题需要,我才将她塞入背景的缝隙?我同样记不清最后一次春节团圆的场景。二〇一四年六月,奶奶确诊直肠癌,中考结束的傍晚,父亲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听说那是死亡率只有百分之十的幸运癌症。几天后,奶奶进行肠管切除术,十几天便回家了。听说其实前一年已出现症状,依据电视广告,爷爷买来便秘的药物自作主张替奶奶治疗,待去检查,癌细胞已扩散全身。不许告诉奶奶,我听到母亲上楼前叮嘱,你爷爷说了,怕她承受不了。
这些起伏—隐秘、崩溃、无法承受—似乎都与奶奶不相宜,但病情总算瞒下,奶奶随即转为卧床。探望中,奶奶清醒的时候不太多了。她总是在睡,配合爷爷的讲解声,肩颈背部粗重起伏着,如有巨人在其上踏步。不和奶奶对谈,并不失落,只是房间里原来浓浓的药皂和风油精气味几乎消失:奶奶有洁癖,平时一日三次澡,又因为经常筋骨酸痛,所以总擦风油精。
那些短暂但一粒粒经过的时间里,似乎有好多东西我尚不明其意,只感受到无法忍受的凄凉。放置奶奶灵位的小桌,上边的电视机,再想不起它迁居何处。此刻频道的吵闹声从隔壁传来,同每一回节日午后一样。远处长短鞭炮噼啪作响。这是奶奶去世的前夜。屋内关灯,阳台透着昏亮。为了讨论,大人往客厅去,屋内剩下我们两个。
我硌在床沿,这些日子,似乎头一次专注于奶奶的病躯。明天我就会见到她干瘪的皮肤与乳房,闻到她失禁后腐朽或排泄物的味道,她的四肢会渐渐僵硬,要揉开了,借残留的神经反应才能卡进寿衣。眼下透薄的白花点睡衣近乎不蔽体,呼吸像节奏失常的颤动。我看不清奶奶苦痛的神情,实则是选择忘掉。她突然有了大动静,挪着,喘息着,近半分钟,才向我转过头来:那张已被病痛摧残的面孔,眼睛里奇光直射,嘴角翘起来,一个灿烂的微笑。我愣愣盯着它。
后来的故事,都与她无关。第一年清明,全家同去祭拜,爷爷絮叨着姐姐的入职,我考上好高中,还有奶奶想要的收音机,他买回来了。我心下冷笑。第二年,拆迁房归属的那场争执中,母亲与爷爷吵得很凶,最后不欢而散。他的拒绝落在我肩上,一下下,过分地重:依妹,不要担心,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母亲将我拽开,只让我对着奶奶的遗像磕头。如果你奶奶还在,她一定站你这边。不知为何,我却对她的不在感到庆幸。
高三寒假,陪母亲回乡,归属台溪镇的村落有一道长流穿过,屋外,水声汩汩,昼夜不停。那是母亲的母亲溪。躲避责打时,她便跳进溪水顺流而下。二十年,母亲经过奇异的原谅重新将自己带回家乡,她也为我溯到了容貌的根源,我,外婆,圆眼,圆脸,鹰鼻,矮瘦的骨架,那些在长脸长身的张家认不出的遗传。他们讪笑说,就个头随奶奶了。外婆勉强点点头,避开我贴近的身体,借口忙着为我炖鸡汤。汤端上来时,她又夹起鸡腿,另装小碗留待表弟。
凌晨,入睡无望,索性出屋,面对那溪水琤琮。月亮在头顶圆着,投进水就碎了,碎片被水流掳走。我想起福州随处可见的闽江。去奶奶家要经过晋安河,奶奶每日来回的桥坡下,十余年,河道始终青黄发臭。
在我的想象中,奶奶的家乡是一条大河。穿过狭长的客厅,沙发角沾染阳光,厨房,地面,桌椅,置物架,锅灶上嗞嗞作响。两个水盆,交替在池中洗泡,奶奶的双手不停,哼唱逐渐清晰:“风吹稻花儿香两岸。”我自然将歌名记作《一条大河》,就如我把歌中的豺狼当真,奶奶的青春时代,一切都热盼新生。我见过奶奶某次参赛的演出。收尾,观众不依,让她再唱第二节,她便笑了,羞怯地,稳稳嗓子,高声往下唱。太可惜了,我兴冲冲对她讲,如果十六岁那年你上台,一定能拿第一,进国家歌舞团。她又笑起来。
耳机中放过四版《我的祖国》,合唱,协奏。公路与爷爷的絮叨将其颠断。爷爷将写着楼层、塔位号的卡片检查一遍,放回衬衣口袋。这里太远,你自己去肯定找不到路。我不忍告诉他,我换乘过整天的高铁巴士,寻找作家墓园,在荷兰野狗般游荡,任不识的语言与列车将我卷携。我意识到,老张家以半径千米外的区域为冒险,爷爷的六十年,父亲的三十年,他们窝进单元楼和单位大楼,连点成线,成方块,不愿突破。看望市区边缘寺庙中的奶奶,兹事体大。入园门前,爷爷高举右臂摆剪刀势,我蹲身拍照。
日头渐正,在桥沿留一线阴影,爷爷安静、缓慢地远离我,将自己塞进荫凉中前行。
我终于跪于佛龛前。圆坛,炖罐大,奶奶的小照躲在脏玻璃里边,爷爷的脸则映在玻璃上。他敲敲柜子,叫她的名字,我和依妹来看你了,过几年,我的骨灰也放这儿。他指指双人塔位空出的一半,当时买得好,两个人才三千八,现在,都涨到十万了。母亲再度出聲:奶奶最后那段时间,只让老张擦身体,排泄物都是老张收拾。我听见,并听见回应的一道轻笑。爷爷奶奶拥有相守至终的爱情,这感情达到尊严以外的依赖与信任,它可以发生,它很可能发生了。但我无法辨明,母亲说的是事实,还是她个人的希望。
我屏息,欲将心思凝于阴阳寄托,塔位溢价的高低却穿耳而过。念完,爷爷垂手直立,我闭眼十几秒,起身。我们同去拜了底楼的无名观音。出门时,我截下管理员,低声问烧香火的去处。管理员告诉我已关闭。我再三保证只烧一张,是信。我扬扬手上的东西,薄薄的。那是前晚,我一气用斗大的字写下的。五年级,我的小说头次发表,八百字,密密的半页递至她眼前,我想起那时教她写字,一个“喝”字,“匈”要跑去西域。我是多么聒噪的小孩。那封信里我什么也没有写,我也什么都没说。我想过告诉她战胜蟑螂的秘方:我的爱人害怕它,我便不怕了。我想我与母亲的差别是她总有话可说,而我没有。
当然,有百千件事情可翻出来讲,只是此刻,面对眼前的他们,我选择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