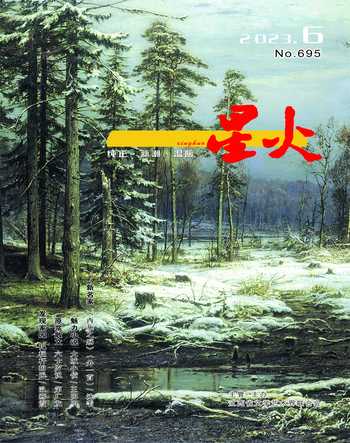去寻乌
田宁,江西上犹人,作品见于《星火》《滇池》《湖南文学》等刊。获江西省第六届谷雨文学奖短篇小说奖。
一
这些年的《星火》读者驿站活动,像一场接一场即兴的召唤与奔赴,起念之后,在驿长村、朗读群、火炬村、锐评团等微信群一声招呼,于是一群人背起星火包说走就走。往往在起念那一刻,各方力量就已开始生长,并向一个方向汇集,而到最后,事情真就成了。去赣州古城墙把《星火》读给你听,去鄱阳湖上点一盏渔火,去资溪的稻田写一首诗,去草山云海迎接日出,都是这样。
这次去寻乌,一群人同样说走就走。当然不可能全无规划,简单的攻略还是得有。几天前已经建了活动微信群,确定外地驿友的出行方案、到达赣州的时间,安排赣州周边的驿友接站,拼车前往寻乌。寻乌在江西最南端,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目前没通高铁,从赣州前往只能开车上高速,其间约二百五十公里路程,哪怕中途不停,也需要近三个小时,外地驿友前往寻乌,是个不小的难题。好在参加本次活动的外地驿友不多,在继亮、天岩的安排调度下,小锋从余干、张玉情从上高、金琳然从奉新、王艳金从更远的杭州到赣州后,以《星火》为号,各有接头人。
动身那天是周五,临时活动群一早就活跃起来。群友互致问候,寻乌驿驿长卢美娟、火炬手尹婷在群里迎候各路驿友,提醒驿友虽然时间已是初夏,但活动地点项山甑上依旧可能气温寒冷,需带好防寒衣物;外地驿友通报高铁行程,《星火》团队提醒远道的驿友注意途中安全事项;客家驿驿友蒲公英已提前为即将到赣州但还需结伴才能前往寻乌的驿友准备好临时休息的地方,酒店位置链接和美食图片都发在群里,贴心与热情跃然屏上。微信群的消息提示不断,热烈且美好。某个此前从未谋面的遥远的陌生人,仿佛近在咫尺且相识久远。这大概是驿友间最可理解的共情。驿友早已达成的共识:驿站的每场活动都像一场烟花,绚丽短暂如梦幻,让深陷在各自生活之境的人们暂时褪去多余的身外之物,还原成一颗简单赤诚的星星之火。
捎上前一天才决定去寻乌的驿友远兰,开车前往赣州西站接小锋。同车前往寻乌的还有韵如。在车站等了一会,韵如到了,背着星火包,我们一起在站前广场等候小锋。站前广场在五月的阳光下辽阔空旷,花坛里不知名的花红艳夺目。我们都有好心情。陆续有旅客从出站口出来,我们一一确认,都不是小锋。当一个背着星火包的身影悠然出现在出站口,小锋到了。韵如举手招呼,远处的小锋举手回应。
车上了高速,一次以《星火》为名的聚会算正式开始。参加过多次驿站活动或其他场合的聚会,车上四人早已是旧相识,相互之间有宽泛自由的交谈,因此接下来的二百五十多公里路程并不显得特别遥远。一般情形下,我们习惯在各自的日常里做一名潜伏者,因为胆怯或羞于表达,隐藏思想或想法的一部分,保持沉默或只保留必要的口头交往,或者哪怕在人群里高声谈笑,也避免涉及某些话题,以保护易碎的尊严,而当合适的交谈者出现,藏在暗处的东西才敢于袒露出来。当然了,袒露与遮蔽,只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们对此有足够的清醒。而所谓文艺高出现实一英尺,并非脱离现实,我们对此更明白。一路停停走走,等车到寻乌,天色已经暗下来。大团的绿色凝聚在路边和远近的山上,浓烈,简洁,干净,和三年前一样。三年前初到寻乌,我已经对寻乌遍地的绿印象深刻。到了酒店,参加活动的驿友基本到齐。晚餐的餐桌上,寻乌驿驿长卢美娟介绍第二日活动行程。一切都有安排。
二
认识卢美娟是在2019年,前一年《星火》读者驿站在南昌成立,次年卢美娟和她的寻乌驿加入进来。我们开始的交流仅限于驿站群,几个月后在共青城见到她本人,后来又一起参加了几次驿站活动,对她有了更直观的认识:常戴一顶精巧的圆边帽;喜欢摄影,活动中相机不离身;谨慎,寡言,该自己表达时才说话,说话时斟酌词语,语句间时有停顿;时常有爽朗的大笑;教着一班学写作的孩子。后来还知道,她丈夫经营了一片果园,她偶尔去帮忙打理,种花种树,种菜也饲养家禽,闲时与寻乌的驿友寻山问水,拍摄精美的图片,这样在我们看来,她的诗和远方,从来就是她脚下那片坚实丰饶,有饱满绿色的土地。
三年前的夏天,各地驿友齐聚寻乌,参加卢美娟组织的纪念《星火》创刊七十周年驿旗与火种包传递至寻乌的交接仪式,见证了一场梦幻的星火之旅,也近距离观察了一群性格鲜明的驿友。交接仪式与之后的采风都有条不紊,从大夫第到项山甑,到高山草甸放飞的彩色氣球,寻乌的人文与山水,与《星火》有近乎完美的呼应。活动中的卢美娟出现在每一个需要她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与几乎每个人每件事对接:深夜的酒店门口,门巷回环如迷宫的大夫第,林木茂密的古驿道,草甸山脊上一群人的尾端。有个场景令所有人印象深刻。在住宿的酒庄里,在一群人刚刚抵达的忙乱中,卢美娟安排住宿时,因为不被理解或被质疑,与她的寻乌驿驿友发生激烈的争吵。在那一刻,我们看见一个与平时截然不同的卢美娟。但仅仅片刻之后,她与她的驿友就又各司其职,该干什么继续干什么,相互间甚至言笑晏晏,好像刚才的激烈争吵并不存在,而是所有人一时的错觉。这里是否有客家人最原初质朴的较真,有边地深山久远的强悍血性,但同时又有守望相助的先民遗风?还是因为驿友本就是朋友,有话直说,不藏不掖本来就是相处之道?
之后的某一天,我和继亮从龙南去往会昌,途经寻乌澄江,卢美娟从县城赶过来,与我们一起去往周田,寻访当地的老房子。她还是老样子,向我们介绍寻乌当地风物,谨慎地选择词语。当晚卢美娟将我们送至寻乌与会昌交界的筠门岭,然后搭车返回寻乌。当她搭乘的车向南驶进夜色,我们开车往北,我恍惚想起那些流传千古的殷勤的送别,此时耳边该有临别的风笛。当然没有风笛,只有灌进车窗的呼呼夜风。在普遍功利且凉薄的文学圈,解释《星火》驿友间因一份文学刊物建立的情谊,并不容易。想来同为《星火》驿友,就已经同是某个共同体中的一分子,共享了一分隐秘的情怀。而那些之前散落各处的无限的少数人,经由这份情怀,将一个个原本陌生的他者视为同路人。
是不是这样?
在卢美娟为本次活动预定的行程里,有一站是攀登赣南第二高峰项山甑。上一次卢美娟组织各地驿友去了高山草甸,这一次她希望能登顶项山甑。连日来寻乌多暴雨,卢美娟为防万一,多次上山确定路线。她说那天她上到山上,一场暴雨果然下起来,上下左右全笼罩在雨雾中,山路之上全是乱石,山上的水流混着泥石冲刷下来,人寸步难行。一个女人就这样困在一场漫无边际的山中暴雨里。她决定活动当日如果下雨,就改在室内,因为雨中的项山甑的确不安全。
三
第二天早餐后,我们离开酒店,和本地驿友一起,一行二十多人前往项山乡。项山乡地处寻乌东部,东邻福建武平,南接广东平远,武夷山与九连山在境内结合。我们在项山乡政府稍微停留,然后去往此行的第一站卢屋村。卢姓曾是赣南望族,赣南有多处卢屋村,对中国近现代美术史深有了解的人,对寻乌项山卢屋当不陌生,赣南卢氏三杰,就是从卢屋这条山沟走出的杰出美术家。村庄在项山甑对面的山脚。车到村部时,村部前面的水田里几位妇人正在插秧,见我们一行人身背星火包,在路边饶有兴致地观望,很快又对我们视如无物,低下头继续插秧。正是夏种的时候,到处是新耕的水田和新插的秧苗,水田之间时有白色的鸟飞起和降落。对面的山则一片葱绿,群山汇聚突起的地方,应该就是主峰项山甑。
卢氏宗祠离村部不远,几步路就到了。祠堂夹在几座平房中间,前面是一片空地,空地往前是水塘,水塘被栏杆圈起,塘里种有荷花,荷叶已经出水。塘上有曲折的游廊,一座亭子和宗祠隔着水塘相望:这应该是卢屋人闲步的地方。宗祠看上去颇老旧,砖木构造,正门方向两根立柱,立柱之间没有封闭的门,两根立柱和墙体之间,也只是各自安置一块半人高的板壁,于是整座宗祠正门上半部分全无遮挡,简古而坦荡,风和燕子、日光和月光都能自由进出。站在门口,一眼能看见宗祠正中的红色匾额上“衍盈堂”三个金漆大字。我们进了宗祠,细读墙上对卢氏先祖的介绍,触摸一座村庄的历史。寻乌驿驿友向众人介绍卢氏三杰中成就最高的卢是,介绍卢是的生平与艺术成就。墙上的卢是脸部略显清瘦,目光清冷,看着眼前这群背着星火包的人。他们当中有没有谁,像当年负笈远游的自己,怀着对美和艺术的深爱,将生命烧成灰烬?出了宗祠,驿友们散布到水塘周围拍照打卡。驿旗被王艳金举在手里,飘在我们中间。
离开卢氏宗祠,下一站是蕉头坝。我们开车上了一段从主路岔开的陡坡。路很窄,斜着往上,路面渐渐高出下面的平地有数米,路边没有护栏,当然也没有危险指示牌,稍有不慎坠落下去,不堪设想。在寻乌驿驿友的前车带领下,车队谨慎往前,路边有茂密的芦苇,一路刮拂车身,刷刷作响。到了一条溪边,一群人纷纷下车溯溪而上,卢美娟在前面带路,众人跟在后面。我停好车准备跟上时,发现转过一片芦苇丛,人都不见了,只听见溪水激石发出的泠泠声响。眼前是密不透风的绿色,人被绿色包围,能听见自己清晰的心跳和喘息。好在几天来都下雨,路上有凌乱的脚印和踩倒的杂草可以追踪。转过几处田墈,终于跟上了前面的驿友,众人踩着水中的石头穿过溪流,进入一片林子。
林子里都是树,看来少有人至,石上布满苔藓,地上有厚厚的植被,脚踩上去,感觉要陷入其中。大家在林子里寻路前行。一棵树横卧在我们面前,树应该是被风吹倒,根部连着泥土裸露在外,顶部却枝叶葱绿。横着的树干上,有枝叶往上生长。树倒了,但没死。我们弯腰低头从树干下鱼贯穿过,保持对一棵倔强的树应有的尊重。卢美娟告诉我们,这里本来是梯田,栽种水稻,多年前退耕还林,之后成了一片山林。山林往上本来有个小村落,住着数户人家,退耕还林后,村里人逐漸迁往山下,村子也就废弃了。最近几年,据说有个人独自返回山上的村子,养了一群羊。我们往山上看过去,果然看见一层层阶梯状的山体,但没看见我们之外的别人。林子深处有不知名的鸟鸣。天岩提议去村庄看看,但无人附议。能看什么呢?一座卷土重来的山林,将整座山包裹得严严实实,它甚至安排一条溪流,一段横卧的树,希望阻挡那些危险的脚步,也许因为它明白,一个念头或一把火,都能让整座山林再一次消失。
四
终于到了项山甑下。山石壁立,果然如一只饭甑倒扣在山顶。
短暂的午休后,下午两点多,驿友们各自上了车,向项山甑进发。同车的还是原先的四人。我和小锋三年前来过这里,看见过高山顶上排开的巨大风车,也看见过草甸七十只彩色气球腾空飞起那一刻,听见过气球腾空时人们的欢呼和群山的回响。路和上次不同,车上了一条水泥路,看来好走。我刚暗自庆幸,水泥路就断了,一条乱石突起遍地滚石的山路向前延伸。车轮打滑,车开始在路上摇晃。山路下面是深谷。到了一处斜坡路面,车轮在石头堆里空转,没法继续往上。小锋三人下车步行,我加足马力爬坡,能听见石头硌着轮胎发出绵密的爆响。车终于奋力爬过坡面,回头看后面的人也都下了车。才稍微喘息,等他们三人上了车,车往前开了一段,路上又出现相同的斜坡。巨大的山体呈现在我们面前,山路像根带子悬在山腰。路边偶有山羊,瞪着惊讶的眼睛。一路停停走走,我担心轮胎承受不住,好在项山甑终于到了。
前车在路边停下来。驿友纷纷下车站到路边,看脚下低伏的群山和头顶的项山甑。风从远处吹过来,满山林木发出巨大的声响。隔着山上的林木,项山甑如在半空。路边上有一条登山者踩出的小道,我们拉着一条下垂的粗藤爬上小道。小道陡峭湿滑,不拉紧身边或头顶那些伸手可及的树枝竹条藤蔓,根本无法前行。登山的人喘着气,手脚并用才勉强爬上某个高坎,却难掩兴奋。一些人如我已经太久没去攀爬一座山。我们住进各自的城市,看层叠的楼房,眼目枯涩太久,偶尔去城市近郊体验一回农家乐,误以为重返了祖辈的家园,直到眼下真正贴近一座山,才感觉自己是真实的自己。
大约半小时后,我们气喘吁吁到达山顶,找地方坐下来,有人捶打自己的腰腿,抬头发现项山甑还在半空,才知道眼前这块平地还只是项山甑的山脚,不觉吸了口凉气。一片雾气飘过来,遮住项山甑,我看着缥缈的山顶,问自己,还能继续攀爬?驿友们却已一声招呼纷纷起身,继续往上,驿旗在前面招展,后面是逶迤的队伍。我坐在一块石头上没动,太久没爬山,刚才的攀爬已经耗费了大部分体力,我不确定自己能上到山顶。正在犹豫,寻乌驿驿友中那位年过六十的长者已经起身,手上搭着衣服,缓慢上了登山的路。我觉得羞愧。
一路攀爬,终于登顶。当驿旗在项山甑的最高处高高举起,成为半空中一抹灿烂明丽的红色,当二十多名驿友背着星火包在项山甑最高处向群山与不可见的星辰挥手,身后是阔大的云天,脚下是渺远的人世。与从弋阳湖塘村到横峰葛源镇的十六公里高温徒步向先辈致敬一样,这回我们以攀爬一座高峰致敬天地山川,致敬我们栖息的家园。我们是否也实现了一次征服?人当然不能征服一座山,但可以征服自己,软弱与卑怯,狭隘与傲慢,人世的虚名与浮利,在俯身攀爬的汗水里,想必能得到部分稀释?返回到休息的山脚,寻乌驿驿友围坐在一起,用当地的客家方言,把《星火》读给项山甑听。
五
篝火再一次燃烧起来。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看着一盆火在眼前跳跃。火光映红了围坐的人们的脸,一阵浓烟被夜风吹过来,有人闪避,有人静坐如故。篝火是《星火》驿站活动的灵魂,一团火在铜鼓,在资溪收割后的稻田里,在大余丫山的山谷,在奉新潦河边的济美牌坊,在安福和浮梁,在婺源和余干,在更多的地方点燃,不同的夜空,同样的星辰,不尽相同的围火而坐的人,同样的《星火》和篝火燃尽时的歌声。篝火串联起一条明亮热烈的《星火》之路。大概《星火》人认为,一个人面对头顶浩瀚的夜空和璀璨的星光,以及眼前跳动的火焰,更愿意袒露灵魂,哪怕最不善言谈的人,当他围火而坐,一颗心也容易被滚烫的言辞激励,被一盆火照亮。
所以来吧,说说你自己,你是谁,来自哪里,从事什么职业,什么时候成为《星火》读者驿站的驿友,一本文学杂志或一群与你气息相同的人,给你的生活带来了什么。或者随便说点什么,说你此刻的心情,说你对文学或文艺生活的热爱,在一团火面前,我们都可以畅所欲言,你的听众是我们,也可以是你自己,是天上的流云,是这山上的夏虫与夜风。
围着一盆篝火,有多少人曾经袒露心声?想一想,真是一个数量庞大的群体。那些被压抑的、疲倦的、坦荡的、欢喜的、微小的、静默无声的、坚强的、被误解的、天真的、失去自我的、无限热爱的灵魂,都曾在这团火光中呈现,讲述一段心灵史。生活或生存,真实而具体,也许微小得仅自己可见,却在这一刻有了光芒。就像在这一刻,有人感激,诉说生活种种,而《星火》成为生活中的一束光;有人以自己的方式理解驿站的文学文艺生活于自己的价值。一位年轻的图书馆馆长讲述自己如何与《星火》结缘,她的孩子,一名五年级学生则表达了对《星火》作文范文式的期许。继亮、小锋、天岩各自分享驿站建设的经验,年轻的火炬手们分享发现那些无限的少数人的经验。卢美娟终于放下一天的紧张,将自己经营驿站的想法和将來的打算和盘托出:一种文艺生活如何延续,新旧如何交替,等等。
不知不觉已是深夜,一盆篝火燃烧将尽,夜风寒冷,山下遥远的灯火零星闪烁。当最后一名驿友的话说完,篝火夜谈也就结束了。驿友们清理现场,纷纷离去。如一场长谈,有人倾诉,有人倾听;有人建言,有人听取;有人质疑,有人包容。一个场域张开双手,拥抱每一个人,接纳每一颗心灵。而我们都知道,心有所归,就是家园。
当所有围火而坐的人散尽,我们几人在酒庄屋檐下的一张方桌前坐了下来。酒庄主人为我们送来几袋零食,为我们的继续聊天添加一点佐料。
六
绿色。还是绿色。大团大团的绿色像喷薄的绿云从树丛中涌出来,山上山下,村口路边都笼罩在这些绿色的云团里。绿色中偶尔突然冒出一团白色,这白色就显得极其亮眼。那是满树大朵的桐花,白得像少年人的情书,纯洁且热烈。好几次,正在开着的车突然停下,有人举着相机从车里出来,在一树桐花下流连不去。
这是项山乡福中村,我们前往江西广东福建三省交界,一脚踏三省之地。界碑立在福中村、广东平远差干镇新岭村和福建武平民主乡坪畲村的接合处。我们到了地方,看见一块群山之间的谷地,用卵石铺设成圆形,中间竖着一根三角棱状水泥柱。这就是界碑了。棱柱三面分别刻着各省名称,朝向各省的方向。周围是茂密的林木,围成绿色的屏障。驿友们绕着界碑转圈,在三省之间往来穿梭。
离开三省界碑,下一站是罗福嶂会议旧址。旧址还是在福中村,是一座客家民居,土墙黑瓦。屋前广场的前方是八个大字:一根火柴点亮中国。1929年,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击赣南,在项山罗福嶂村召开了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史称罗福嶂会议。会议扭转了不利局面,是创立中央苏区的起点。他们“在项山找到了一根洋火,找到了一个落脚点”。
一份文学刊物的落脚点在哪里?从会议旧址出来,每一个《星火》人也许会自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