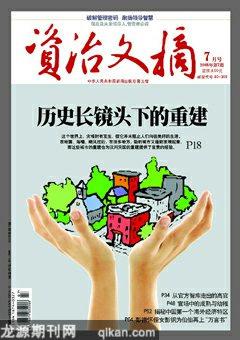中国城市化发展四大认识误区
陈 钊 陆 铭 许 政

一些大城市政府没有看到,城市的治理能力完全可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也会随着城市治理能力的提高而提高。
不管是理论,还是实证的研究,都表明了规模经济的集聚效应有助于提高城市的劳动生产率。但是,中国的城市发展中却存在着规模偏低、规模差距过小的问题。这与人们对城市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认识误区有关。事实上,也正是这些误区,使得地方政府相应地采取了不利于城市化发展的政策措施。
误区一:
通过限制人口流入保护城市居民利益
因为担心外来人口争夺有限的城市公共品资源和就业岗位,很多城市政府会通过各种手段限制外来劳动力流入。
但限制外来人口流入的政策会损害包括城市在内的各方的利益。首先,外来人口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外来劳动力的利益受到损害,因为他们更难以在城市立足,有很多农民不得不仍然滞留在土地上。其次,限制人口流入的政策使企业不能雇用到更为合适的劳动力,或者必须为现有的劳动力支付更高的工资,这使企业因成本上升而失去一定的竞争优势。最后,由于劳动力要素不能充分地流动,城市的规模效应赖以存在的要素匹配与分享等机制将受到限制。事实上,外来人口不仅增加了城市的劳动力供给,也通过集聚提高了城市劳动力的生产率。从长远看,所有这些因素都会损害城市的效率和当地居民的福利。
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但目前以户籍制度为手段的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仍然存在于中国各地的城市,特别是大城市之中。不拥有本地城市户口的外来农民在工资水平、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不能享有与城市人口同等的待遇。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根本的改变,那么随着未来持续的城市化过程中更多的外来人口进入城市就业,在城市内部就会形成“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二元社会”分割的现象。
城市内部的“二元社会”的形成又会导致低收入人群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社区公共品资源的恶化,并可能由此进一步扩大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将影响低收入阶层的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积累,加剧未来城市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社会矛盾,给未来的城市治理以及城市内部的社会和谐发展和城市经济的持续增长带来巨大的挑战。
误区二:
小城市(镇)发展才是未来方向
由于担心出现拉美国家的“城市病”现象,认为小城市(镇)才是未来城市发展的合理方向的观点始终存在。
这样的认识误区只会造成中国目前这种大城市规模偏小,小城镇过度发展,城市规模差异过小,从而损失经济效率的局面。事实上,从大城市到小城镇的发展,是集聚效应不断加强的结果。随着交通成本的下降,大城市经济活动的辐射范围不断扩大,中心城区的集聚效应进一步加强,但同时也导致地租、工资等商务成本的上升,这种拥挤效应的增加就促使一部分产业向周边地区转移,带动了周边小城市(镇)的发展,从而形成了经济功能互为补充的“城市圈”或“城市带”,使大城市的规模效应充分得到发挥。更多样化的产品需求与供给、更好的公共品提供以及更高的城市治理水平都将在大城市的发展中得到体现。相比之下,如果仅仅只有小城镇,无论是社会公共品提供,还是多样化需求都无法得到充分的满足。
在当前中国的城市发展中,一些大城市往往出于对城市人口承载能力的担忧而有意识地控制城市规模的扩大,这些城市的政府并没有看到,城市的治理能力完全可以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也会随着城市治理能力的提高而提高。
比如,东京因为保持了便捷的交通、清洁的环境和较低的犯罪而使其容纳了3500万人口,成为世界最大的城市,并使整个日本的经济发展受益于由此产生的集聚效应。相比之下,目前在政府看来已经人口规模庞大的上海只要能够进一步提高城市的治理能力,就可以发挥其在人口吸纳与规模扩大上的巨大潜力。即使从已有地铁的运能来看,东京每公里地铁的运客量是7472.88万人/年,而上海为每公里387.07万人/年。可见,即使是上海这样的国际性大都市,在交通基础设施的硬件和管理方面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因而城市未来的规模扩张也有极大的潜力。
误区三:
“民工荒”表明劳动力短缺时代到来
始于2004年春天的“民工荒”似乎预示着中国劳动力短缺时代的到来,资本似乎应主动向劳动力较充裕的内地转移。如果不考虑城市化进程中城市集聚效应的进一步发挥,不考虑可能发生的制度上的变化,只是静态地看一些地区出现的民工短缺现象,上述结论是有可能的。

但事实却是,除了一些导致民工局部性短缺的短期因素外,城市劳动力市场对民工的政策歧视才是导致民工荒的更为重要的根本性原因。表面上来看,似乎没有户籍并不影响在城市工作,但是,没有户籍却意味着那些在城市打工的劳动力不能拥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他们的劳动权益也往往在城市有关部门的关注范围之外,他们的子女在城市上学常常还需要交纳额外的费用,甚至在学校里也会受到歧视。由于这些制度上的城乡分割,中国的农村劳动力流动以短期为主,大部分外来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在婚后以及有孩子的期间将回到农村。
也正是由于人为原因造成的劳动力市场分割和流动成本,大量农村劳动力不能在城市化进程中转变为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换句话来说,事实上在中国农村仍然有大量“潜在”的剩余劳动力,随着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持续提高,这些劳动力还有必要大规模地转移到现代二、三产业中去,继续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从劳动力供给角度来看,由于历史上的“三年自然灾害”和“独生子女”政策,中国农村人口结构存在一些低谷,而在2002~2007年间,作为劳动力流动主力军的20~25岁人口恰恰处在人口数量的低谷,这是造成近年来“劳动力短缺”的重要原因之一。
同时,2004年之后,中央实施的惠农政策也相对降低了进城打工的收益,成为造成“劳动力短缺”的另一个客观原因。当然,农村土地长期以来难以流动也是阻碍农村劳动力长期离开土地,定居城市的重要原因。
误区四:
应当限制东部城市的发展
不少人认为,城市发展中的集聚效应会扩大中国的城乡与区域发展差距,为此应当采取限制东部城市发展的政策措施。对这个认识误区的剖析,需要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客观地看,城市的集聚效应短期内的确可能扩大城乡间的发展差距,但只要劳动力是充分流动的,劳动力市场是充分竞争的,这种差距的扩大就更多只是体现在GDP的统计上,而并非实际收入上。一个很好的例子便是,1.5亿农民工进城打工的收入绝大部分都被用于反哺农村家庭。
第二,农村劳动力在返乡后,会带回在城市先进部门所积累的资金、技术、管理等,这些农村稀缺资源能够有力促进农村的发展,一定程度上缩小城乡差距。城市化是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
第三,从长期来看,城市集聚效应发挥到一定阶段,部分产业或产业链的某些环节就会向内地或农村地区转移。而此时,随着劳动力的流出,内地的人均资源(尤其是土地等自然资源)的拥有量将增加,这必然会带来内地劳动生产率以及收入的增长。因而在长期中城市集聚效应的充分发挥并不会扩大区域间的收入差距。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在美国、智利和巴基斯坦,地区间的收入收敛都是因为更充分的要素流动性,而不是地区发展的特殊政策。在美国和法国这些发达国家的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地区间差距扩大的现象,但是后来,地区间的差距出现了持续的缩小趋势。事实上,只有要素流动和持续发展才能最终缩小地区间的差距。
即使在短期内地区间的发展差距有所扩大,中央政府也可以通过适当的地区间财政转移来避免过大的地区差距。例如,政府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来缩小城乡和区域间在公共品提供和社会保障方面的差距,提高落后地区的教育水平,为地区间最终的协调发展做好基础设施、社会保障和人力资本的准备,也为劳动力最终的自由流动做好准备。
(摘自《望东方周刊》2008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