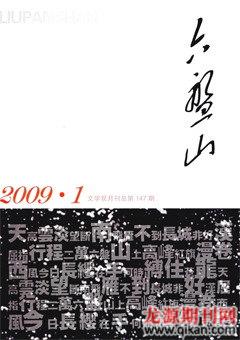记忆残片
张虎强
探望父亲
今天趁工作闲暇之际,偷偷跑回了老家。
父亲就坐在靠近门前的椅子上,脸上布满了沧桑。
父亲看到我时,问我怎么没上班,我说办事顺路回家转转。父亲欣慰地看了我一眼,目光是那样的清澈。母亲是躺在床上休息的,她知道我为什么要回来。
我问父亲大便怎么样,父亲说不太好。怎么会好,父亲患的是直肠癌,我知道那是很痛苦的。等星期一全面化验报告出来,我和几位兄长再商量是否给父亲手术。不管怎样,我们还是要尽最大的努力。
父亲是坚强的,他说要减一减肥,肠子的负担也会轻一点,这样会有利于病情。说完,还挥了一下胳膊,表示自己身体状况还可以。我的眼睛有些潮润。
父亲明显已经瘦下去了。
流泪的端午
今天父亲终于住进了医院。
在端午节这一天,这对我来说多了一份记忆。只是这记忆中多了一份苦涩。以前,我们家的端午节一向过得很隆重。包粽子、挂香囊、折柳枝、喝黄酒一样都不会少。今年的环节减了不少。在我的感觉里,北方的端午节与纪念屈原倒没有多大联系,但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气。过了这个节,就该到了农忙季节了。一方面在这段时间人们比较清闲,另一方面是对收获前的一种庆祝吧。大家对这个节日还是比较看重的。尽管那时的日子过得很贫苦,但家家还都尽可能地去买一二斤肉,包一些粽子,蒸一笼白面花馍。嫁出去的女儿们都要带点礼品回娘家看看父母,老人也要给孙子孙女送一些各种各样小动物图案的香包。那些日子,整个家里总是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这一切,留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有关粽子和香包的记忆。
记忆中的端午节就这样一年一年地过去了。
但是今年的端午节,是一个流泪的端午节。
魂兮归来
今天是父亲66岁的生日。
这个生日是在我心里过的,因为父亲是不能进食的。我不知道面对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父亲在想些什么?从婴儿到老年,岁月在他脸上刻出痕迹,他的脸颊已经干瘪下去,眼睛深陷着,眼神却是那么地安闲。
托尔斯泰说:“人要真正地生活,就要独自生活,不要为赞扬而生活,不要为别人而生活,因为别人无权安排你的生活,而你也无权安排别人的生活”。
是的,生命是什么?没有人能说清。我们不必常常拷问生命的原委。我是谁?我来自何方?我又将向何处去?我们存在便是最好的说明。最终的目的并不十分重要。
生命的过程就是一切。生命的歌谣就是一曲生命自己韵律谱就的曲子。生命的啸声便是生命自我存在的证言。生命的每一圈年轮就是生命永留的痕迹。
自然界的万事万物,道理都是相通的。对于父亲的病情,也许是冥冥之中注定的,我的心里有最坏的打算。
生命是一张空白的画布,你可以将痛苦画上去,也可以将幸福画上去。
现在的生活,是父亲的涂鸦之作。
生命的终极还是死亡。从出生那天起,就开始了生命的倒计时。生命开始了淘汰,有人在幼年、青年、中年就倒下去了。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耄耋之年的老人临终的想法是什么?当他回首这苍凉坎坷的一生时,会有怎样的感慨?大地、河流、万物,这些生命之源的轮回,难道只是为了生命的延续?还是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支配?
天堂在哪里?心中自有日月。我们之所以看不到希望,看不到天堂,是因为很多理想还未实现。
父亲坚强的生活态度,常常令我感动不已。其实父亲还有他未了的心愿,这个心愿可能珍藏了一生。他选择了这个生命的麦田,他想经营好自己的家园。
感恩的心
今天是第23个教师节。当然这也是父亲的节日。
父亲是我授业启蒙的严父与恩师,也是我一辈子最大的财富与骄傲。在我看来,父亲值得自豪的地方很多,尽管他貌不惊人,工作普通,然而父亲的坚韧品质却令我钦佩。几十载的贫寒岁月和旁人的冷眼嘲讽并没有把他击垮,反而激发出了他生活的勇气与信心,他默默把心血都倾注在了孩子身上……
父亲是一名小学教员,1963年参加工作,2002年正式退休,整整为人民教育事业奋斗了四十年,用青春的画笔描绘出了最具色彩的风雨人生。青春的韶光转瞬即逝,父亲似乎一夜之间变老了。我还清晰地记得父亲送我上大学的那个秋天,风摇曳着我的思绪像秋叶般飘飞,他执意要为我扛行李,我没拒绝,我知道那是父亲对我的爱护与鞭策,父亲与我一路踩着枯黄的落叶,去车站的路仿佛走了一个世纪般的漫长。那场送别,成为我终生难忘的回忆。工作后,我和父亲之间亲近了许多,每次看到父亲染白的鬓发和佝偻的身体,那种触动会是怎样的一种心酸呢?这种突然的转变,是我成熟了,懂事了?还是因为父亲老了,病了?这个问题多少又让我有些感伤。我借口工作忙、压力大,在忙忙碌碌中,在喧嚣和浮躁中,常常不经意间忽视了与父亲的沟通和交流。其实亲情不需要太多的礼节,它只需要内心真的有一份真情保留。保留着这份真情,它自然就会流淌,它的流淌有时只需要一个电话,一个问候,一个微笑……
寂静与芬芳
沿着荒草湮没的小道,我终于走到了那片林子的尽头。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封土不高的坟堆,在苍白的阳光下格外醒目,就在这座冰凉的墓冢下面,长眠着我的祖父。林子周围到处弥漫着祭祀过的烟火味,残留的食物被一群群蚂蚁蚕食着。我的记忆一片空白,跟随父亲蹒跚的脚步前行着,我清晰地听到了脚下生命成长的声音,就像这无情的生命轮回。
逝者如斯,三十年不过惊鸿一瞥。祖父出事那年,我才一岁,根本无法回忆起他的音容笑貌,我只知道他被车撞了,死时已八十八岁高龄。据父亲回忆,祖父是在步行去集市的途中出事的,他被车挂倒了,身上外伤并不明显,就像平时睡着了一样。那一刻,我不知道祖父在想些什么?是对生命的缱绻之情?还是对儿孙有难舍的牵挂?但他就以那样的方式走了,悄然寂静,甚至没留下在这艰难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当沉重的棺木落入阴冷潮湿的地穴时,残留的只有呼啸耳畔的千年风声和亲人悲怆的哀鸣,一切随着生命的消失成为一种结局:尘埃落定。但坟堆上长出的花朵还是依然年年在夏天散发出清香。
山城的四月,山桃花开得灼灼灿烂,这个春天注定不同寻常。当父亲、兄长和我怀着满心虔诚,齐刷刷跪在祖父的坟前点燃纸钱时,潜藏在内心深处的情感喷薄而出。尽管祭拜的过程很短暂,但我们对祖父的怀念却留在心里,那是比生命更长久的记忆……祖父是旧社会从河南逃荒到西海固的,起初给有钱人家打工混口饭吃,后来攒了点本钱,就挑起担子当货郎了。那个年代,兵荒马乱,交通闭塞,更别提经济发展。因此,货郎成了流动“超市”,走街穿巷,上山下乡,生意一度相当红火。祖父是个很有眼光与抱负的人,并没有满足现状,而是瞅准了固原的羊毛市场,办起了私人织毯厂。他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对羊毛毯子的制作工艺与质量要求十分严格,收羊毛、弹羊毛、擀羊毛、染羊毛,直至成品出炉,每一个流程都亲自把关。生意兴隆时,祖父招有十几个徒工干活,每天卖出三条毯子,一条毯子在当时要卖三块大洋,而一个长工一年的工钱才挣六块大洋,可见利润丰厚。发家后的祖父并没有忘记自己的贫苦出身,在城郊购置了田产,过上了安逸殷实的生活。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祖父就将厂子与田产充了公,自己赶上驴车参加大队里的集体劳动了。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北风卷着雪粒针扎似的刮在脸上,祖父穿起羊皮袄,戴上大棉帽,一手拿着鞭子,一手拿着旱烟锅子,天蒙蒙亮就出发了。那时的固原城漂亮极了,四道城门,砖包墙体,固若金汤,祖父架起驴车穿瓮城出东门,吆喝声清脆悠扬地回响在城门之间。回眸的瞬间,那弥漫在雄关上的雾气如烟叠嶂,煞为壮观。也许人生的匆匆正如这时间的匆忙一样,在经历了无数次的磨难之后,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农民包产到户了,分到了属于自己的土地。祖父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有了咱自己的地,只要肯吃苦,娃娃们就不怕再挨饿了。”说这话时,祖父已八十六岁高龄了。一年多后,祖父离开了我们,葬在城郊古雁岭上。
岁月的河水无声地流淌着,祖父离开我们已快三十年了。都说叶落归根,但祖父最终还是安息在他辛劳了一辈子、为之流了一辈子汗水的异域他乡的土地上。又逢清明时节,纸灰飞扬,泪眼矇眬,山桃烂漫,祖父在天之灵若是有知,儿孙遥寄情思,您在九泉之下安息。
寂静过后便是芬芳……
[责任编辑:杨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