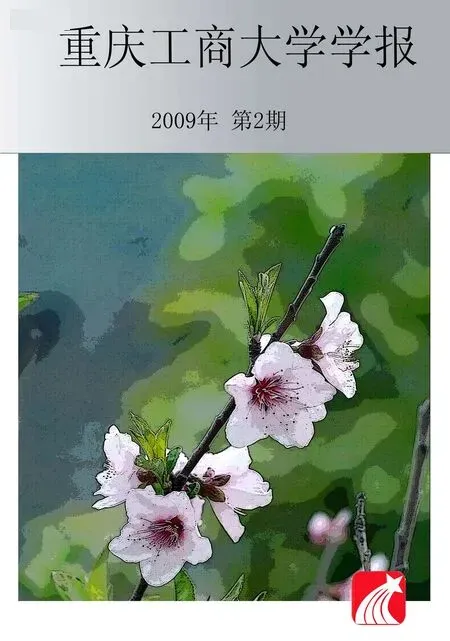“陌生化”手法在文学翻译中的再现*
——以标记性主位句为例
程瑾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系,陕西杨凌712100)
“陌生化”手法在文学翻译中的再现*
——以标记性主位句为例
程瑾涛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系,陕西杨凌712100)
陌生化是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的核心概念,是文学性的代名词。陌生化手法对于文学作品的价值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对于译者而言,如何看待和处理原作中的陌生化手法也决定了译作的成败与否。以文学文本中的标记性主位结构为例探讨文学语言的陌生化效果及其翻译。
文学翻译;陌生化;标记性主位;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文学性;艺术手法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是俄国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流派的核心概念,其理论实质是以一种与常规相对立的表现方法,或以反常的形式摆脱审美的“自动化”(automatization)状态,从而去贴近和呈现真实。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的观点,陌生化是文学性(literariness)的代名词,文学作品没有了陌生化,便不能被称为文学。文学家在创作时,往往采用“陌生化”手法,即“偏离”(deviation),对习惯性、自动性、平淡性的生命常态加以违背,以新奇、陌生的面貌来唤起读者的兴趣,但是,当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时,我们发现译者往往以“常规”来处理原文中的“陌生化”现象,而多数情况下并非是由于目的语的限制不得已而为之,而是译者想当然的选择。这样做虽然迎合了部分目的语读者阅读的畅快感,然而带来的隐患也不可小视,譬如,原作中的诗学特征(poeticalness)有可能因此被取消。本文试以文学文本中的标记性主位句为例指出在文学翻译中,译者应对于特定的反映原作者陌生化手法的语言特征加以保留。
一、“陌生化”手法及其在文学中的作用
俄国形式主义大师什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指出:“艺术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使石头现出石头的质感。艺术的目的是要人感觉到事物,而不是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就是使对象陌生,使形式变得困难,增加感受的难度和时间长度。”他还指出:“感受过程本身就是艺术的目的,而对象本身并不重要。”[1](45)换句话说,文学创作的目的不是要达到某种审美认识,而是要达到审美感受,即通过阅读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在这一感觉的过程中产生审美快感,这种审美感受是靠“陌生化”在审美过程中加以实现的。[1](46)陌生化手法对于增强作品的文学性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在英语文学作品中,作家大量运用各种陌生化手法,对形式与内容加以“陌生化”的变形处理,目的就在于要使其尽可能地被读者所感受。同样,为了对抗阅读中的审美疲劳,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也会寻求新奇感。读者在被文学作品中的陌生化形式吸引的同时,也会去探究作家的深层用意。
什克洛夫斯基在谈到陌生化理论时指出,诗学语言是实现陌生化过程的重要条件。从而引出了一个新问题: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的联系与区别。什克洛夫斯基认为,“在日常生活中,说话的意义(内容)是最重要的成分,而文学语言内容却没有它的外壳(形式)重要。在文学语言中,表达本身,即形式,就是目的,意义只成为手段,成为语言游戏无关紧要的材料。”[1](47)也就是说,日常语言或科技文本关心的是信息传递,而文学语言关心的是审美。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的论点,如果说,日常语言具有能指功能(声音、排列组合的意义)和所指功能(符号意义)并以所指功能为主导,那么文学语言是以能指功能为主导的。
俄国形式主义的另一核心人物,布拉格学派和美国语言学小组的发起人 罗曼·雅各布森指出,“文学性”存在于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之中。在《结束语:语言学与诗学》一文中,他提出了语言六要素和六功能说。六要素体现在任何语言交际都包含说话者(addressor)、受话者(addresee)、语境(context)、信息(message)、接触(contact)、语符(code),相应的,言语体现出六种功能:当交际侧重于语境时,就突出了指称功能(referencial);侧重于说话者,就强调情感功能(emotive);侧重于受话者,就突出意动功能(conative);侧重于接触,交际功能(phatic)就突出了;侧重于语符,元语言功能(metalinguistic)就占主导地位;最后,只有当交流侧重于话语本身,诗学或审美功能(poetic)才居于支配地位,当言语以本身为依归,突出指向自身时,其诗学功能才突现出来,其他实用功能降到最低。[1](50-51)[2](88)也就是说,诗学语言虽然也具备如提供信息等功能,但以“自指”(self-reflexivity)的审美功能为主。文学语言的诗学功能越强,语言就少指向外在现实环境,而指向自身,指向语言本身的形式因素,如音韵、词语和句法等。
实际上,在中国古典诗学著述中,强调艺术作品“可感性”的人也不在少数。韩愈《答刘正天书》说:“夫百物朝夕所见者,人皆不注视也,及睹其异者,则共观而言之。”日常生活中朝夕所见之物往往不能引起我们的注意,然而突然一天,惯有程序发生变化,习见的事物以迥然不同以往的方式呈现于面前,必然会使我们钝化的自动化感觉活跃起来,使得我们重新以一种不同的新眼光去认识感知事物。这与俄国形式主义所说的“陌生化”的意指是相同的。这种“变形”在我国古典诗学中表现为“违背常理”、违背惯用的“标准语言”,力求破陈示新,比如诗人们常常有意颠倒、打乱语言的正常顺序,藉以求得“陌生化”效果。如王安石诗句:“溶溶院落梨花月,淡淡池塘柳絮风”,如改为常规表达“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便成了毫无生气的诗句。[3]
二、标记性主位结构与陌生化手法
主位结构是布拉格学者马泰斯(Mathesius)在分析句法功能时首先提出的。它包括“主位”和“述位”两个语义成分。韩礼德(Halliday)给主位下了这样一个定义:“主位是信息的起始点,是小句的出发点。”主位有标记性(markedness)和无标记性(unmarkedness)之分。一般说来,英语中陈述句的正常顺序是SVO(主谓宾),这样的安排可以减少人们的认知难度。看到主语,人们会期待谓语的出现,而谓语后面则应紧跟着宾语。当主语充当主位时,这个主位是无标记的,其他的句子成分如宾语、补语、状语等充当主位时则是有标记的。[4]如例句(1)Mr. Micawber has talent,but not capital.是带无标记的主位,而例句(2)Talent Mr.Micawber has,capital Mr. Micawber has not.的主位是有标记的,因为它的语序是违反常规的。但是,在文学创作中,作家有时候会有意使用标记性主位结构,使得句子产生特殊的审美效果,如用来揭示人物性格,推动情节发展等等,这样的表达往往能够打破读者的心理预期,因此也应列入陌生化手法。
然而在我国,由于重内容轻形式一直是文论界和翻译界的主流,很多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看重的是原文的信息内容,至于形式则不是看得很重。严复提出的翻译原则“信、达、雅”,在我国翻译界更是影响深远,而“信、达、雅”也被解释为“忠实、通顺、美”为现代译者奉为真理。问题是,英语行文中作家为达到陌生化效果,以新奇、陌生的面貌来唤起读者的兴趣而有意使用的标记性主位结构往往是反常规的,其结果往往是语言表层体现出来的不通顺。而一旦译者受到这种重内容轻形式的翻译观的影响,不可避免会轻易地将原文的陌生化手法简单地归结为语言差异,进而依据目的语的表达习惯和行文规范来对原文进行调整,其结果是译作抹杀了原作者苦心经营的美学效果,最终不可能忠实于原文。
三、未能再现“陌生化”手法的英汉翻译例证
文学作品中很多标记性主位往往体现了原作者陌生化的艺术手法,蕴含了更深层次的美学关怀。但是很可惜,由于译者的主观局限性,这些“陌生化”手法在译作中没能得到再现,可以说,这既是原作者的遗憾,也是译语读者的遗憾。
例一:That eye of hers,that voice,stirred every antipathy I had.Shaking from head to foot, thrilled with ungovernable excitement,I continued …(Jane Eyre,Chap.4)
这是摘自《Jane Eyre》(《简·爱》)第四章的一段文字:小简·爱的舅妈决定打发她去Lowwood学校,并对校长撒谎诬陷简。校长走后,简·爱与舅妈发生了冲突,长期以来受到的蔑视侮辱,加上舅妈一番冷漠无情的恶语中伤使得愤怒像即将喷发的火山,简·爱再也按捺不住了。这段文字之妙在于作者用了一个标记性主位来强调人物心理过程,生动再现了一个孩子在遭遇多次欺侮后自然爆发的单纯而直接的反应。且看下例译文作何应对:
原译:她那种目光、那种语调激起了我无限的反感。我在无法控制的激动下,从头到脚打着哆嗦,接着说:“......”[6](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简·爱》,1990;粗黑为笔者所加)
原文中标记性主位Shaking from head to foot, thrilled with ungovernable excitement,I continued…被改写成了无标记性主位句“我在无法控制的激动下,从头到脚打着哆嗦,接着说:‘......’”,原文因主位突出而彰显的人物的无意识心理因此受到压制。
不仔细推敲联系语境,这段译文可说是“语言流畅通达,逻辑清晰。”通常,译者对原文所作的改写最常见的原因是:其一,译者认为原文的句法结构为其语言特有的表达方式,不便直接转换为目标语;其二,为满足读者一目了然,畅快淋漓的阅读感受。殊知,这两点理由在此均不能成为正当的理由,因为一是相比于讲究形合的英语,汉语是重意不重形,最不拘泥于句法形式约束,因而行文灵活多变,形散神聚。二是为满足读者的阅读需求应该以不损害著者的原意为底线。原文中“从头到脚打着哆嗦,”按常理应该是因于“无法控制的激动下”,然而,原文出乎意料的颠倒了这种普遍接受的逻辑。显然,原文是在颠覆这一认知定势,而正是这看似不经意的逻辑的颠倒生动自然地再现了小主人公此时此刻即将爆发的愤怒:没有刻意地去计划,情绪的自然流露。译者将原文的“反常规”改成了常规,译文“流畅”的表达使得原文陌生化手法所要传递的人物情绪变得分外冷静,使一个十岁小女孩具备了与其年龄不相符的沉稳,扭曲了人物的心理和性格,违背了原作者对人物的刻画。因此,为保留原文标记性主位结构所蕴涵的深层美学效果,我们不妨改译如下:
她那种目光、那种语调激起了我无限的反感。从头到脚颤动着,约束不住的激昂使我抖索,我继续说道:“......”。
从认知角度讲,语言表达方式是基于人们对事物或事件的感知,外界对大脑的刺激是杂乱多样的,大脑要对它们进行整理,根据最突显的物体来组织语言表达,对语言的运用与我们怎样感知周围的事物和情景有密切关系[5](195)。许多标记性主位结构所引发的陌生化效果,实质上肯定了认知心理学关于人们观察某一情景时,往往以不同的视角、选择不同的注意点、突显不同的方面因而形成不同的意象的事实。在文学翻译中,还原这种标记性主位结构将会引领目的语读者理解和把握文本所创造的真实情景,给读者置身其中的感受,达到文学文本的审美体验。
例二:This parlour looked gloomy:a neglected handful of fire burnt low in the grate;and,leaning over it,with his head supported against,the high, old-fashioned mantelpiece,appeared the blind tenant of the room.(Jane Eyre,chap.37)
这段文字摘自《简·爱》最后一章,可以说是该部小说的高潮部分。简在冥冥中听到罗切斯特先生的呼唤,毅然回到了桑恩费尔德庄园。在得知她走后庄园失火被毁及罗切斯特先生因救疯妻双目失明致残的真相后,又赶往罗切斯特先生隐居的一处住所。此时的罗切斯特痛苦绝望,大部分时间只是蜗居在房子里。天色变暗于他来说毫无区别,因此在简傍晚赶到时,客厅里并没有灯光,幽暗沉寂。这段文字生动再现了简从室外向昏暗的客厅张望时,目光所触及的情景。标记性主位结构的使用,仿佛一个远景镜头给读者以舞台剧的视觉效果。由于客厅昏暗,从常理来讲,壁炉里的火首先引起简的注意,随后,但仍以壁炉里的火为背景,简的目光向周围推移,注意力从一个焦点移向另一个焦点,最后获得了整体形象认出了罗切斯特。我们试看译者是如何处理的。
原译:客厅看来是幽暗的:一团没有人过问的火在炉栏里燃着,烧得一点不旺。这屋里的盲目的居住者,倚在炉上,头靠着旧式的高炉架。[7](陕西人民出版社《简·爱》,1982;粗黑为笔者所加)
显然,译者对原文中有标记性的主位所带来的陌生化效果未引起重视,采取了目的语读者喜闻乐见的常规表达,即用非标记性主位来代替,从而遮蔽了原作者苦心营造的氛围。我们不妨改译如下:
客厅看来是幽暗的:一团没有人过问的火在炉栏里燃着,烧得一点不旺。俯向着它,头靠在高高的老式炉架上的,就是这间屋子里的双目失明的主人。
修改后的译文保留了原文中的标记性主位结构,从而再现了作者采用陌生化手法所要追求的美学效果。
以上两例均取自小说体裁,在标记性主位结构中,本应位于句首的主语被放逐到句子的末端,将焦点留给了状语等其他成分,从而产生了陌生化效果。其实,作为文学性语言的代表,诗歌语言的诗性功能最强。英语句子常规表达要求主语在前,系动词和表语紧随其后。但在文学文本中,尤其是诗歌的创作中,为达到诗律的节奏和谐及取得特定的陌生化效果,诗人往往打破定律,将表语置于主语前,这在汉语的古诗中不乏其例,如前文提到的王安石诗句:“溶溶院落梨花月,淡淡池塘柳絮风”。在英语诗歌中,也是屡见不鲜。
例三:Heavy is my heart,
Dark are thine eyes.
Thou and I must part,
Ere the sun rise.(Mary Coleridge,Slowly)
张传彪曾就诗歌“Slowly”的汉译,即李建红的翻译,发表了观点并提供了自己的翻译。
我的心情悲戚,你的眼神忧郁。
你我必须别离,早于日出之时。(李建红译)
吾心悲愁结,君目忧郁现。
终须两相别,东方破晓前。(张传彪译)[8]
当然,张译旨在探讨诗歌标题Slowly的汉译,本文选取此例,只为说明英语诗歌中的标记性主位的翻译,视角不同,并无他意。
原文例一、例二采用标记性主位,将主语heart,eyes置于句末,将表语heavy,dark放在句首,笔者认为原因有二。其一,主语heart,eyes置于句末和例三句末词part,rise呼应,形成谐音,取得修辞效果;其二,heavy,dark作为表语置于主语之前,有加强意义,突出强调的效果。遗憾的是,以上两译例均未保留原诗作中的标记性主位结构,而是代之以常规化表达,从而影响了原诗作的美学效果。实际上,汉译完全可以保留标记性主位结构,甚至保留四字结构。试译如下:
戚戚吾心,幽幽子睛。
与子之别,东方未明。
四、结束语
在翻译有效文本时,译者的基本职责就是忠实地传达原文的意义。要想做到这一点,译者必须准确、透彻地解读原文。文学文本作为区别于科技文本的主要特征在于其“文学性”,体现在文学语言的自指性及产生的陌生化效果。简单地说,就是文学文本作为符号,其本身的结构配置,即形式,产生了附加的意义并具有特殊的美学效果,而这种形式往往是偏离常规的。作为译者,不能为迎合读者的情趣无视原作中一些反常规的表达,而是有必要尊重原作,对原作者有意采取的陌生化艺术手法加以保留,从而影响读者,让读者更充分地领略原作的美学价值。
[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2]郭建中.当代美国翻译理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
[3]杨向荣,曾莹.诗学话语中的“陌生化”[J].天中学刊,2003(3):81-85.
[4]Halliday,M.A.K.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M].London:Edward Arnold,1985.
[5]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
[6]夏洛特·勃朗蔕.简·爱[M].吴均燮,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
[7]夏洛蒂·勃朗特.简·爱[M].李霁野,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
[8]张传彪.从诗歌Slowly的汉译谈起[J].中国翻译,2005(5): 60-63.
(责任编校:朱德东、段文娟)
The representation of defamiliarization devices in literary translation——Taking marked theme as an example
CHENG Jin-tao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Northwest Agriculture and Forestry University,Shaanxi Yangling 712100,China)
Defamiliarization,a key concept in Russian Formalism,embodies literariness and is thus vital to literary works.For translators,how to handle defamiliarization devices in the original determines the quality of a translation.In analytic marked theme construction in literary works,this paper attempts to invite attention on defaniliarization devices in literary works and their translation.
literary translation;defamiliarization devices;marked theme;formism;literary critic;literature;art method
H059
A
1672-0598(2009)02-0135-04
10.3969/j.issn.1672-0598.2009.02.027
2009-01-09
本文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专项项目“符号学在文学翻译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08080303)阶段性成果。
程瑾涛(1978-),女,陕西西乡人,讲师,硕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外语系教师,主要从事英汉对比与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