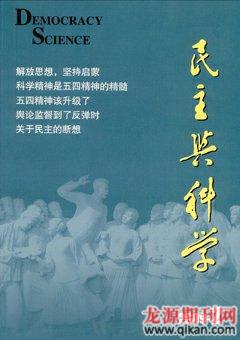思想创意的优先权
孙慕天
在自然科学中,长期存在优先权(priority)之争。科学社会学家齐曼(J.M.Ziman)说:“关于什么人、在什么时候作出什么发现的问题,经常产生激烈的争论。按照惯例,做出某项特殊发现的优先权的权利,属于首次发表论文报告该项发现的作者们。”
早在17世纪,伽利略在《试金者》一文中就痛斥了四个试图想要与他争夺优先权的人:一个是关于望远镜的发明,第二个是关于太阳黑子的发现,第三个是关于木星卫星美第奇的发现。后者是一个叫马里于斯(Simon Marius)的人,宣称是他而不是伽利略首先发现了美第奇卫星,而使用的手段却极不光彩:他在公布这一发现的刊物上注明的日期是根据儒略历,而不是格里戈里历,这就使他的发现赶在了伽利略的前面。伽利略愤怒地斥责说:“他使用了一种狡诈的方法企图确立他的优先权。”而牛顿则更深地卷入了优先权之争。首先是关于一些光学和天文仪器的发明,其次关于平方反比定律的发现,胡克和牛顿发生优先权的争执,胡克甚至声称牛顿的一系列发现全都是由他发起的,以致后来牛顿不得不在自己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插入一段声明,指出胡克也是平方反比定律的发现者之一。
关于牛顿和莱布尼兹谁最先创立微积分的争论,是优先权之争最典型的案例。牛顿创立微积分是在1665年,他在解决加速运动的瞬时速度问题时,发明了流数法,这有他1665年11月13日的笔记为证。1669年他在致巴罗的信中阐述了这一方法。而1672年2月10日,他曾在致科林斯的信中明确提到他发现的这一新方法及其在方程论中的应用,这封信后来成为牛顿对微积分学原创性贡献的有力佐证。1671年他写了《流数方法》的手稿,详尽论述了关于流数的思想。莱布尼兹在1674年在研究用无穷级数求曲边形面积时,考察了求构成曲边形的元素之和的方法,进而创立了微积分学。他的笔记和手稿表明,在1675到1676年间,他开始尝试使用独特的微分和积分的记法。莱布尼兹曾于1673年访问伦敦,结识了皇家学会秘书奥尔登贝格(Henry Oldenburg),1677年他写信给奥尔登贝格,说明了求曲线的切线的方法及相当于求积分的逆问题的解法。1684年他在一篇文章中系统地阐述了他所制定的微分学原理,提出微分学的关键是一个算式所依赖的变量的无穷小增量,称之为“差分”(difference),并用字母d来表示,写作dx、dy。后来他又论述了作为逆运算的积分学原理,并用其本质是求一个量的相继元素之和(summa),因此用一个拉长的字母s- 来表示。牛顿与奥尔登贝格稔熟,很可能通过后者了解到莱布尼兹的工作。1676年,牛顿写信给奥尔登贝格询问莱布尼兹的情况并提到自己的流数法,翌年莱布尼兹致信奥尔登贝格回答了牛顿的询问,介绍了自己的方法。但问题是,牛顿《流数方法》的概略尽管于1703年以《求曲边形面积》为题作为《光学》一书的附录予以披露,但全书迟至死后9年(1736年)才发表。这就造成了一种印象,即牛顿似乎是在莱布尼兹之后提出流数法的,况且微积分的正式记法是由莱布尼兹给出的。1705年,莱布尼兹在一篇对牛顿《光学》的匿名评论中,说牛顿的流数是对莱布尼兹差分的改头换面。而1708年牛津物理学讲师萨维尼则反唇相讥指斥莱布尼兹剽窃了牛顿,莱布尼兹遂就此提出上诉。1712年英国皇家学会为此任命了一个委员会进行审理,发表了支持牛顿优先权的报告,但没有对莱布尼兹的贡献作出评价,却认为莱布尼兹在1676年已看到了关于牛顿流数法的文件,并受到了启发。莱布尼兹对此向皇家学会提出抗诉,该会在一次有外国大使参加的会上就此进行审议,根据与会者的建议,牛顿与莱布尼兹进行私下磋商,但并未得出结论。
今天看来,一方面,牛顿在其开始于17世纪60年代的力学研究中,已经开始创立并使用了微积分学的方法。他在1687年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明确提出:“量消失时的最后比实际上不是最后量的比,而是无限减少的这些量的比所趋近的极限。”这是关于导数的最早的科学定义,并制定了流数(fluxiones)这一专门词汇,给出了x、y上加一点的记法。同时,正是牛顿把这以数学方法应用于实证科学研究,开启了使用数学物理方程的先河。这确实略早于莱布尼兹。不过,莱布尼兹虽然迟至十多年后才提出自己的微积分理论,但看来确实是独立提出的。19世纪中叶英国数学家莫干对这桩公案做了详尽的考辨,证明莱布尼兹没有看到过牛顿关于流数法的原始文献。牛顿1676年的信在谈到流数法时有意使用了字谜式的隐语,所以莱布尼兹不可能从中取巧。更重要的是,莱布尼兹创立了微积分记法,由于该记法被克雷格用于1685年出版的一本书中,而这一记法因其简洁、方便和完善而被广泛采用,对微积分学的发展和传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一直使用到现在。其实,牛顿早在原理第一版中,已经肯定了莱布尼兹的工作,说:“十年前在我和最杰出的几何学家莱布尼兹的通信中,我表明我已知道确定极大值和极小值的方法、作切线的方法以及类似的方法,但我在交换的信件中隐瞒了这方法……这位最卓越的人在回信中写到,他也发现了一种同样的方法。他并诉述了他的方法,它与我的方法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他的措词和符号而外。”从这段曲折复杂的历史中,可以看出,公正地评价一个科学家的真正贡献,正确地确定发现的优先权,有时常常是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决不应草率行事。
科学上关于优先权争吵绝不是无谓之争。黑格尔认为,真理是个过程,自然科学知识正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过程。从本质上说,这一认识是对客观自然对象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尽管科学理论的更迭存在着范式的转换,但却总会构成一个逐步提升的认识阶梯,所以牛顿才说他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最先做出发现的科学家理所当然地占据前面的一级阶梯,成为那一特定阶段科学所达到的高度的界标,肯定这一点是对历史的尊重,也体现了学术公平原则,从而保护了学者的创造积极性和科学生产力。优先权体现了科学的求真和向善两种本质要求的统一,谁最先作出了发现和发明,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尊重这一事实就是捍卫真理。同时,为了认识前所未知的自然规律,科学家必须致力于原创性的探索,不能容忍任何投机取巧的违规伎俩,遵守这一原则就是维护科学道德。甚至可以说,是否尊重科学发现和发明的优先权是衡量一个科学家学术品格的试金石。既然知道了别人在同一课题上已经得出了正确结论,如果秉持求真的意愿,所应做的就只是对该成果的改善和推进,再重复同样的结论就完全是多余的了。问题是,由于优先权问题与科学的社会建制有关,涉及到与知识产权相联系的财富、权力、荣誉的获取,结果如科学社会学家默顿所说,优先权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的科学价值观和规范的结果”,于是在个人利益的驱动下,就出现了妄图窃取优先权的卑劣行径。在评论默顿关于优先权的研究时,斯廷奇科布(Arthur Stinchcombe)历数了科学界为争夺优先权而发生的丑闻:“喜爱争论、坚持己见的要求、怕别人占先而保密、只报告支持某一假说的数据、毫无根据地指控别人剽窃、甚至偶尔偷窃别人的思想以及在极少数情况下编造数据——所有这些行为,在科学史上都出现过。”
优先权问题的权威研究者默顿明确指出,围绕优先权的争论“社会科学中的情况几乎一模一样”。斯科特在《亚当·斯密:学者和教授》中,列举了亚当·斯密的朋友弗格森和罗伯逊都剽窃过他的见解,而前者为了“确定优先权”,被迫公开发表演讲,“把他的新思想列了一个相当长的清单”。另一个典型案例是,圣西门指责历史学家基佐盗用他在《组织者》一书中的观点,嘲讽说:“公众和我本人都极希望他像以往对待我首创的思想那样,尽可能充分盗用它的内容。”就连马克思也不例外,他曾经义愤填膺地斥责海德曼是自己思想的明目张胆的盗贼,而且对马尔萨斯和巴斯夏剽窃前人思想的行为嗤之以鼻。
优先权的核心恰恰是新思想、新观念的最初创意,而且正因这种创意是无形的,其最本质东西只是一种思想闪光或精神火花,它虽是一切创造的源头,是特别宝贵的,但一旦原创者发表了这些想法,它们就特别容易被有心人借用,而当这些创意被当作借用者的原创时,实际上已经是对真正创造者优先权的侵犯。然而,这种初始创意却尚未体系化、赋形化,也未纳入社会学术体制,因之对它们的优先权保护是不可能规范化的,基本上只能凭借道德约束,诉求于应用这些创意的人自己的学术良心。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麦克斯韦电磁场方程的发现。麦克斯韦关于位移电流和交变电磁场的思想,追本溯源来自对超距作用的怀疑,这来自坚持电磁作用要通过“中间物质的中介而发生”的信念,并且认为这种作用的传递是沿着法拉第的力线逐点连续发生的。麦克斯韦明确指出,他的这一信念是受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波斯科维奇(Roger Boscovich)的启发:“波斯科维奇提出的理论是,物质是数学点的集合,每一个点都按照一定规律而对另一个点施以引力或者斥力。”须知,波斯科维奇1758年发表《存在于自然中的力还原为单一法则的自然哲学理论》一书,提出力点论;而麦克斯韦在《论物理学的力线》一文中首次提出交变电磁场的惰轮模型,时间是1861年。两者相隔103年,而波斯科维奇并不是声名显赫之辈,他一生颠沛流离,最后客死他乡,麦克斯韦祖述这样一个尘封于历史记忆中的过气人物,绝对没有攀附之嫌,而是对前贤的由衷敬佩和对优先权的自觉尊重。
哲学思想是一种领悟,其核心观念的产生是灵光一闪,形态虽极简约,义理却是宇宙和人生的真谛,其启发价值是无可估量的。哲学观念的作用犹如传说中的哲人之石,所谓点石成金,它是撬动思想巉岩的智慧杠杆。但唯其蕴藉不彰,漫汗无迹,也极易被人忽略。尽人皆知计算机改变了人类历史,但是计算机的发明与哲学思想的关系却几乎淹没无闻。图灵被计算机的现代电脑的主要设计者冯·诺伊曼誉为“计算机之父”,他指出“计算机的基本概念属于图灵”。就在1939年,图灵与哲学家维特根施坦讨论数理逻辑中的矛盾。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施坦认为矛盾是毫无意义的,并相信有一种完美的理想语言,可以避免任何歧义;图灵不同意这一观点,二人发生了争执。事实上,维特根施坦当时也正在修正他早期的观点,认为公众采用和发展的是包含内部矛盾的语言,亦即日常语言。这场讨论启发了图灵,使他深入把握了计算机语言的性质。图灵机是一种不考虑硬件形态的计算机逻辑结构,图灵甚至提出一种“万能图灵机”,用来模拟任何一台图灵机的工作,从而首创了通用计算机的原始模型。这里明显地有维特根施坦理想语言论的影子。英国学者爱德蒙兹和艾迪诺在谈到这件轶事时说:“在图灵思考原始计算机波姆贝(Bombe)的逻辑设计时,他们争执的这个记忆也许起了作用”。雪泥鸿爪,雁过无痕,哲学思想的作用一向如此,正是由于哲学思想的这一特殊性质,与科学成就不同,哲学发现的优先权问题甚至未见有人提出过,哲学思想首创者的权利往往轻易被轻忽,被侵凌,被践踏。
时代久远,典籍佚失,一些重要哲学观点的原创者隐没在历史的深处,后人不加深究,常以自己的见解充作前人未发之覆;等而下之者,则专以“盗墓”为业,以为无法起古人于地下,与之争夺优先权,从而可以遮尽天下人耳目。其实,哲学上的原创者和科学大师们一样,他们的开创性功绩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我们既然不能掠美于时贤,也同样不能掠美于古人。在这一点上,哲学和科学一样,也有累积效应,哲学家同样也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现代西方分析哲学、哲学逻辑和语言哲学真正的创始人是弗雷格。他于1879年发表《概念文字》一书,1884年出版《算术基础》,并在19世纪90年代发表《论概念和对象》、《论意义和意谓》等开创性的论文。弗雷格第一个提出了意义和指称的区别,奠定了构建形式语言逻辑演算系统的基础,是罗素、卡尔纳普等人当之无愧的先驱。他长期在耶拿大学执教,但他所使用的符号和形式演算方法过于艰深,很少有人理解。他的课堂常常只有三个学生,其中一个就是卡尔纳普,校方对他的课评价一直不高。弗雷格的思想太超前了,而他又极度低调,从来不会炒作自己,相反,作为一个严谨的思想家,最高追求是所构建的理论体系的完美。1902年,在他的著作《算数的基本法则》第2卷即将付印时,他收到了罗素的一封来信,罗素在高度评价他的工作的同时,也指出他的逻辑体系导致矛盾的可能性,这就是著名的“罗素悖论”。这封信强烈地震撼了弗雷格,他说:“在工作之后发现那大厦的基础已经动摇,对于一个科学工作者来说,没有比这更为不幸的了。”他随即放弃了原来准备出版的《算数的基本法则》第3卷的计划。弗雷格始终没有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在郁郁寡欢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二十余年。这以后的弗雷格差不多已经被世人遗忘了。直到1973年,在弗雷格去世四十八年后,才由达米特在其巨著《弗雷格:语言哲学》中,全面肯定了他在现代哲学中的开创作用和现代语言哲学奠基者的地位。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主流话语霸权的遮蔽和掌控。经济、科技、军事霸权往往带来文化霸权,当今世界的西方中心主义和英语文化的主流化,把其他民族国家的文化统统边缘化了。于是在哲学领域就出现了一种风气,似乎只有西方特别是英语国家的哲学才可以登上哲学庙堂,其他国家的哲学文献都不屑一顾。即使非西方国家的学者作出了独创性的发现,也完全可以视若无睹。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对待苏联哲学研究的态度。虽然在长达七十年间苏联学者在哲学上走了许多弯路,但在许多领域和一些重大的哲学主题上,苏联学者也做出了超越西方学者的原创性成果。奇怪的是,就连我国的许多哲学研究者也对这些成果视若无睹。其实,被国人当作新发现公诸于世的一些观点,人家早就做了深入的讨论,并且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学术水平。在这些人的眼里,对英美学者的成就必须尊重,而苏联学者的成果似乎不属于“地球人”,可以弃之如敝屣,即使那些成果摆在那里,仍然可以继续大搞重复劳动,并面无愧色地宣布自己拥有发现的优先权。
哲学研究的另一个特殊性是与政治关系密切。在威权主义时代,由于统治的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于是哲学上的思想创造就被看成是政治领袖的专利,一般学者只配充当领袖思想的注释者、解读者和宣传者,觊觎哲学创造则被视为狂妄之徒,乃至反革命野心家。事实上纵观哲学史,对哲学作出伟大贡献的人却并非政治领袖,而是纯粹的学者。两千多年的哲学史上,在有独创性哲学思想的哲学家中,只有古罗马的奥勒留是一位帝王。拿康德说,他的一生真是平凡得很,不过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学究而已,甚至可以说有一点“冬烘”。康德研究者奥特弗里德·赫费说:“关于康德很难写出一部扣人心弦的传记;他的外在生活过得平稳单调。我们找不到一个他让同时代人十分激动的事件,也没有一次能够抓住后人好奇心的冒险行动。康德不像卢梭过着一种不稳定的漫游生活;也不像莱布尼兹与他同时代的所有大人物都有通讯往来;不同于柏拉图和霍布斯,他从未参与政治活动;不同于谢林,他从未卷入‘女人故事。他的生活作风中也没有任何越轨的行为;从不着引人注目的服装和发型,也从未有过狂飙突进时期人们所喜爱的慷慨激昂的姿态。”虽然如此,康德却“属于西方最伟大的思想家,他对近代哲学的影响无人可比”。
在我们的时代,难道不会再出现康德式的思想家吗?信息时代的符码效应,使人们的眼球纷纷转向名人和明星;学者不甘寂寞,也全身心的浮躁起来,潜心治学的人越来越少了,动辄鸿篇巨制,著作等身,自封“大师”“泰斗”。近年来,国内标榜学术评价科学化的做法大行其时,并俨然成为政府行为,于是在定量化的指标体系规范下,以多为胜成为不成文法,在一阵高过一阵的量化喧嚣中,有谁还会关心什么人最初提出了什么创意呢?上世纪前半叶英国牛津大学奥斯汀被评价为“伟大而又富有独创性的哲学天才”。正是奥斯汀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言语行为的概念,斯台格缪勒说:“对于那些2500年来以任何形式从事语言研究的来说,这真是一件丑事,而且是一件带有耻辱性的丑事,即他们在奥斯汀之前这么长的时间内,没有作出奥斯汀的发现——就是借助语言表达我们可以履行不同种类的行为。特别是在我们时代哲学转向语言研究已经过去了数十年,直到一位哲学家作出了有语言行为的发现。”但是,用时下流行的标准看,奥斯汀实在不能算“大师”和“泰斗”,因为他生前仅仅发表了区区七篇论文,没有任何专著,他的大量创造性的思想是来自讲演和交谈,所谓“述而不作”。人们重视的是他的原创性的思想,尽管这些思想甚至并没有用文字固定下来,但是奥斯汀拥有发现它们的优先权,却是无可置疑的。
看来,问题仅仅在于,从老子和泰利士诸位老先生以来,你究竟说了几句从来没有人说过的话?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