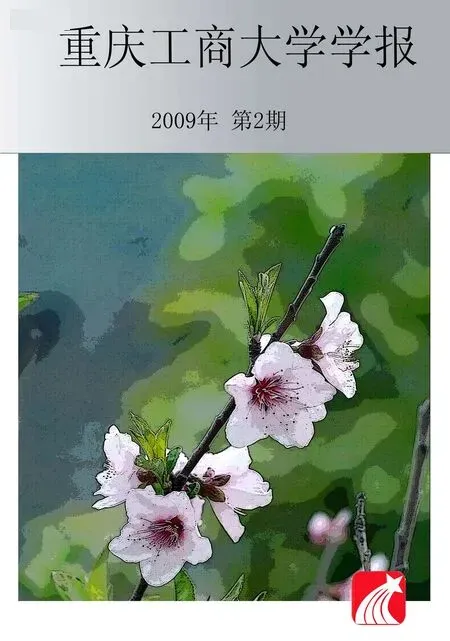西方关于中世纪晚期英国自由农发展地区不平衡的几种解释*
李彦雄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西方关于中世纪晚期英国自由农发展地区不平衡的几种解释*
李彦雄
(安阳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河南安阳455000)
中世纪晚期(1300-1500)英国农民在从农奴到自由农的转变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地区不平衡,西方学者对其原因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代表性观点主要有人口说、生态说、商业刺激说、阶级关系说、田制说等。主要针对这几种代表性的观点进行简要述评。
中世纪晚期;英国;自由农民;地区不平衡
中世纪晚期(1300-1500)英国的农业变迁和自由农民的发展中存在的地区差别,长期以来是西方学术界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学者们早已注意到,中世纪晚期的农业革新最初是从农作物种植革新开始的,而不是从节省劳动力开始的。也就是说,这个时期的农产品的增加最初是由于增加土地的生产率而不是劳动生产率实现的。所有革新都比传统农业耕作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可是,为什么英格兰东部和西南部地区在需要更多劳动力投入的情况下,不仅没有强化保障劳动力的农奴制,劳动者反倒率先摆脱了农奴制、较早出现了大量自由农民、发生了诸如工资劳动等变化,而且很少遭到抵制,而其他地区却发展滞后呢?对这个问题西方学者进行了不懈的研究,主要形成了以下有代表性的几种观点。
一、人口说
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是埃斯特·博萨伯(Ester Boserup)。他在《农业发展的条件》[1]中指出,英格兰东部和西南部地区人口稠密,这些地区的高人口密度为农业发展提供了动力。人口压力促使农民追求更高效的耕作方法以满足更多人的生存需要,从而刺激了土地持有结构的改变,而土地持有制的改变也就意味着农民法律身份的变化,即从农奴义务下的解放,因此这些地区的农民较早从农奴制中解放了出来。
这种观点在英格兰东部最具说服力。这个地区在中世纪晚期人口稠密,并且在整个中世纪晚期都是英格兰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人口压力早在13世纪就促进了东部地区精耕农业方法的发展。人口说还可以解释为什么13世纪晚期在这些地区采用的许多改良的农业方法在14世纪中期的大瘟疫后会在该地区停止使用。
然而,人口密度说不足以解释在14世纪的人口危机后持续存在的地区差别。东部地区继续是英格兰乡村经济最繁荣的地区,即使在14世纪晚期和15世纪早期人口压力大大减轻之后仍是如此。乡村社会土地所有制和社会结构的大多数变化发生在14世纪的人口减少之后,例如向契约性所有制发展的趋势和大规模联合农场和圈地农场的出现。事实上,正是人口减少使得这些变化成为可能,因为人口减少提高了工人的讨价还价能力并使富于进取心的农场主有更多的可以利用的土地。
人口说也不能解释西南部的情况。西南各郡在中世纪晚期都保持较低的人口密度,然而和英格兰其他人口密度较大的地区(如米德兰平原)相比仍是非常富裕的经济区,农民从农奴义务下解放发生得要早、程度要高。和东部地区一样,这种繁荣在14世纪中期人口减少以后仍然持续。同样和东部地区一样,人口的下降促进了土地持有在本质上的转变和大农场的产生。然而人口下降对各地的影响是不同的。在其他地区,比如米德兰平原和英格兰中部多数地区,低人口密度对农场规模和土地持有制结构的这些影响并没有显现,尽管那些地区人口减少更严重。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人口密度与中世纪晚期农业变迁和自由农发展的地区差异方面之间的关系,与人口水平决定论的假设不符,将人口密度与自由农发展简单地联系起来是没有说服力的。
二、生态说
生态说是部分人解释中世纪晚期英国自由农发展和农业变迁地区不平衡的一种观点,代表人物是杰克·戈德斯通,他在其《1500-1700年英格兰和法兰西的地区生态与农业变迁》[2]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戈德斯通研究的虽然是近代早期的情况,但同样的地区差别早在中世纪晚期就已经存在,因此,学者们普遍认为他的观点同样适用于中世纪晚期。戈德斯通认为农业变迁的地区差别是生产模式(modes of production)的一个产物,反过来也可以用地方生态(local ecology)来解释。他认为农业发展和自由农发展的不平衡是地区生态差异造成的,尤其是土壤和气候条件的差异。这种观点认为土壤和气候条件优越的地区,适宜农业发展,农民经济比较发达,农民相对富裕,农民经济实力的壮大又进一步促进了农民权利的发展,使得这些地区自由农的发展领先于其他地区。
然而,这种解释不适用于中世纪晚期的英格兰。首先,许多自由农发展较快的地区明显不具有有利的生态条件。诺福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虽然诺福克是英格兰一个主要的粮食产区,自由农的发展也领先于英格兰中部地区,然而该郡很多地区土地贫瘠而且夏季干旱,冬季来自北海的东风席卷该地。另一方面,米德兰平原虽然土壤、气候及灌溉条件都很好,对畜牧和农耕都很适宜。然而这个地区农业生产率明显落后,自由农的发展显著滞后于东部和西南部地区,该地自由持有农数量明显少于东部和西南部地区,而且农奴成为自由农的时间也晚于东部和西南部地区。有人提出了土壤排水性能低和排水技术的缺乏是阻碍米德兰平原早期农业和自由农发展的主要原因。[3]然而,如果考虑到同时代的荷兰人的排水技术,这种观点似乎有些肤浅。荷兰的农业发展状况恰恰与生态决定论相反,荷兰北部的农业环境比米德兰平原更加恶劣,该地区不仅是沼泽区而且始终面临大海的威胁(随时有被海水淹没的危险)。当地人凭借巨大的努力才改造出田地。然而从1500年到1700年间该地区的农业增长很快,成为全欧洲最繁荣的农业区。[4]也许诺福克农民的聪明才智使得他们能够克服面临的许多自然问题。问题是为什么米德兰的农民不能较早地解决他们面临的排水问题而富裕起来并走上“自由之路”呢?
其次,生态说有自相矛盾之处。戈德斯通认为生态说还可以逆转(turn around),在强调有利的生态利于农业和自由农发展的同时,他又指出相对恶劣的生态也是促进农业进步和农民发展的间接原因。他认为生态恶劣的地区趋向于形成人烟稀少的畜牧业地区,而生态较好的地区倾向于成为人口稠密的农耕地区。畜牧区有更多的公田和荒地,充足的牧场,很少管理畜牧业和农业的公共规则。公共规则的缺乏,使得这些地区对农民经济的制约和限制因素相对较少,更有利于圈地和农业新技术的采用,从而会间接促进农民和农业的发展。这些地区低人口密度和空闲土地的充足有利于农民经济的扩大。畜牧为主的另一个好处是有大量的牲畜,大量的牲畜意味着有大量的肥料可以用来提高地力。因此,戈德斯通指出,靠近城市市场的畜牧区在近代早期农业和自由农的发展相对较快。
戈德斯通对生态说的逆转思考看起来似乎有一定道理,然而却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农业和自由农发展的地区差异不符。首先,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很少有以畜牧业为主的地区,几乎所有地区都是农耕和畜牧的混合经济,与生存型乡村经济相适合。最符合戈德斯通论述的地区 即人烟稀少、拥有大面积公田和荒地的以畜牧为主的地区 主要在英格兰偏远的北部和西部山区。[5]这些地区远离城市市场并且相对落后,农民变化缓慢。英格兰东部地区尽管比较富裕,自由农发展较快,但除诺福克的布雷克兰(Breckland)从来不是以粮食生产为主的地区外,其他地区都是以农耕为主。[5]在东部地区,高产的耕作地区单位谷类土地上也没有太高的牲畜比率[5][6](153,163)。其次,一些人口稠密并缺乏荒地和公田的地区农业和自由农发展都比较快。中世纪晚期东部英格兰的高产地区(肯特、艾塞克斯、东盎格鲁)中有些在当时是人口最稠密并且几乎没有荒地和公田的地区。[7]例如,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很发达的地区之一的东诺福克的很多地方不能归为畜牧农业种类。这个地区人口非常稠密并且到13世纪成为主要的粮食输出地。东诺福克为国际市场生产大麦和麦芽。即使在14世纪的大瘟疫造成人口减少促使英格兰很多地区向畜牧农业转变的情况下,东诺福克仍以粮食生产为主。[8](59,65)然而这里的农民获得自由却要明显领先于中部地区。最后,即使靠近市场的畜牧业为主的地区自由农的发展也未必领先。例如,温彻斯特大教堂的各个庄园在1350年后牲畜数量增加超过了两倍。这些庄园位于英格兰中心地区(主要在汉普郡),至少靠近一个主要港口(南安普敦)。然而1350年后牲畜的增加(畜牧业的发展)并没有带来农业生产率的显著提高和自由农的显著发展,这个地区仍属于英格兰的落后地区。[6](164)
生态说虽然不能正确解释中世纪晚期英格兰自由农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的原因,然而戈德斯通的论述对我们研究自由农发展不平衡问题还是有一些启发意义的。如他指出了自由农的发展和农业变化更易于在农业制度更加灵活和对农业的公共控制较少的地区发生,这启发了我们从社会因素入手考虑自由农的发展问题。
三、商业刺激说
主张生态说的戈德斯通在论述中世纪晚期英格兰自由农发展地区不平衡时就强调了市场的作用,他指出靠近城市市场的畜牧区发展较快。费歇尔(F.J.Fisher)和里格利(E.A.Wrigley)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商业刺激说(commercial incentives)。商业刺激说认为城市商业的发展是促使城市周边乡村农业发展和旧的生产方式变革的主要原因,因此靠近商业发达的城市的乡村自由农的发展相对较快。费歇尔和里格利注意到发展较快的东部和西南部各郡都靠近面向国内和国际市场的几个输出港口,就指出东部伦敦市场的发展和西南部布利斯托尔(Bristol)市场的发展极大地刺激了那些地区农业生产和农民自身的发展;并把靠近港口或便利的水运路线作为各地自由农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9]
我们不否认市场和运输因素对农业和农民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影响,靠近主要的城市市场或水路运输线也许有助于经济发展和旧的社会结构的解体,然而却不是农业发展和农村阶级结构变化的充分原因。例如,同样非常靠近伦敦市场的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却存在明显的差异 比如,剑桥郡和诺福克郡或者肯特郡和苏塞克斯之间。肯特和诺福克在15世纪分别比它们的近邻苏塞克斯和剑桥要富裕得多,自由农的发展也比较快。[6](76,135)中世纪晚期诺福克的变化要早于剑桥郡,[8]肯特要早于苏塞克斯。[10](119-36,268-85)
地理位置因素不能够解释这些反常的例子。牛津郡(在中部英格兰)经泰晤士河可以进入伦敦市场,然而发展却不如诺福克。南部英格兰可以通向主要港口南安普敦(自中世纪以来就是一个重要港口),然而附近地区(汉普郡)经济或农业及自由农的发展却不像英格兰东部和西南部一样。以上事实表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农业发展和变迁的地区差别不是农产品是否易于进入市场的必然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真正决定各地旧的生产方式和农业阶级结构变化(包括自由农的发展)的商业因素不是外部市场的商业刺激,而是农民经济的商业化程度。农民经济的商业化程度是由各地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差别决定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地区差别决定了各地农产品商品率的差别,或者说决定了农民经济市场化程度的地区差别。农民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依附农民摆脱庄园制束缚,向着自由发展的步伐就快些,反之,农民经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依附农民走向自由的道路就更长些。对已经和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农民来说,靠近商业发达的城市市场和运输线,尤其是靠近城市农产品市场,当然会促进其发展。然而,对于没有和市场联系起来的农民以及市场化程度不同的农民来说,商业刺激究竟起多大作用就另当别论了。
四、阶级关系说
阶级关系说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伯伦纳,他在1985年发表的《欧洲前工业化时期的农村阶级结构和经济发展》[11]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农业基础》[12]两篇文章中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伯伦纳对中世纪晚期英国乡村社会发生的变化给出了一种社会解释。他认为不同地区农业和自由农发展的不平衡可以追溯到财产所有者领主和“无财产的”农民之间的乡村阶级关系的本质上的地区差别。
伯伦纳的阶级关系说最初主要是用来解释英格兰和法国之间农业发展的差异的。但也涉及了英国内部农业发展的地区不平衡。他认为法国的小农民所有者(small peasant proprietor)(自耕农)与英国的小农民所有者相比,他们的财产权利得到了王室更多的支持。这些不同可以追溯到12世纪英格兰的法律改革。这些改革意味着在英国国王不能干涉领主和他的惯例佃农之间的关系。因此,与法国农民相比,英国农民在和领主的对抗中处于更加软弱的(powerless)地位。这种状况导致英国庄园领主易于剥夺其佃农,而在法国却是不可能的。在英国对农民的剥夺为大型商业化农场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这种阶级关系说用于解释英国国内的地区差异时,就是在和庄园领主的对抗中农民所有者的财产权利较弱的地区,会最先出现采用工资劳动的大农场和商业化农业。后来在《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一文中,伦伯纳又指出,这些地区应该是农民在土地上拥有个人财产权利的地区。伯伦纳的理由是农民个体土地权利比共同体整体掌握的土地权利更加脆弱,这种脆弱会促进对农民的剥夺、面向市场的生产以及大农场的发展,从而引起农民身份的变化。[13]
从表面上看,伯伦纳的观点似乎有些道理。因为至少在中世纪晚期,伯伦纳所说的农民个体土地权利的地区和大型商业化农场发展的地区是一致的。尽管英格兰大多数地区大农场的发展是在14世纪中期的人口下降之后,前文中已经提及东部和西南部地区大农场的发展比中部地区更加广泛。这些正是公田很少和农民拥有个体土地财产权利的地区。(见图1)由此看来,伯伦纳关于自由农民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的结论是正确的,然而历史事实表明他的论述方法是错误的。
首先,在东部和西南部在1350年后首先建立大农场的是农民,而不是领主。事实上,这个时期领主的大型家庭农场的规模减小了,领主直接控制的大型庄园地产时代过去了,很多领主把家庭农场(领地自营地)出租给了若干个佃农农场主或整体出租给了一个农场主。
其次,这些地区庄园领主相对于农民的力量并不是最强大的,而且农民的财产权利也并不弱。东盎格鲁、艾塞克斯和肯特东部各郡在中世纪晚期拥有大量自由持有农,自由持有农有牢固的合法权利并且能够向王室法庭上诉。这些合法权利使得他们的土地财产权利比构成米德兰平原和中部郡主体的惯例佃农的财产权利更加牢固。而且在东部和西南部地区,即使惯例佃农的情况也要比米德兰平原和英格兰中部地区好得多。在这些地区,一个村庄分属于几个庄园,通常是几个庄园领主竞争领土和其他领主权利,庄园义务和劳役相对较轻,农民可以利用这种有利的环境。比如,惯例佃农能够很快把他们的法律案件送到几个庄园法庭中的一个。大概正因为如此,这些地区的农奴制很早就消失了,惯例土地也比较早地成为公簿持有地。相反,落后的米德兰平原和中部地区反倒是典型的一个庄园领主完全控制整个村庄的地区,农民的力量相对比较软弱。[14](1572)

图1 16世纪末无公田土地所占比例图。右上方数字自上而下依次表示70%及以上、50-69%、30-49%、15-29%、5-14%、不足5%和数字不详的地区。
最后,这些地区也没有强制剥夺农民的证据。14世纪中期的人口下降以后,这些地区农民佃农联合起来组成了许多大农场。这些人无论在自由和其他方面确实是处境比较好的农民,然而并没有证据表明较穷的农民曾经被强制剥夺土地。以后的几百年间许多小农场和大农场的并存充分证明了东部和西南部地区小农所有者的权利保障。尤其在东部地区非常小的农场保持了很大的比例。[10](617,702)直到19世纪中期东部和西南部都还有很大比例的小农(5-100英亩土地的农场主)(见图2)。

图2 5-100英亩农场在所有5英亩以上(包括5英亩)农场中所占比例图。右上方自上而下依次为67.7%及其以上、60.2-67.6%、54.5-60.1%、49.7-54.4%、42.1-49.6%、42.0%及其以下。[14](1573)
这些小农场远非伯伦纳所说的是阻碍农业发展的因素,它们在中世纪晚期和后来东部和西南部农业发展和变迁中可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该地区的大农场借鉴了许多小农场率先采用的改良方法。例如,后来广为农学家称道的芜菁、豆类等新作物,在东英格兰小农中有很长的种植史。[15]
富裕的小农场主的存在还为以后的几百年中不断扩大规模的大地产上的大农场培养了一批精明能干的佃农农场主。未来经营大农场的佃农不仅要有经营大农场的能力和愿望,自身还必须拥有一定的财力。境况较好的英格兰东部和西南部小农场主充分具备了这些品质。历史研究发现一些小佃农起源的家庭后来成为大土地所有者和地方显赫家族。如诺福克的汤森德家族(Townshends)和肯特的克奈齐布尔家族(Knatchbulls)等。这些家族在14和15世纪的历史档案中最初都是佃农农场主身份,几百年后他们成为当地的贵族。[16]这样一个富有进取心的小农阶层在中世纪晚期的存在是大农场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条件。
中世纪晚期英格兰东部和西南部地区尤其是东部地区确实有大量的无地人员在大农场或当地的工业部门充当雇佣工人。东部地区普遍存在的分割土地遗产的继承惯例(诸子继承制)对无地的贫苦人口的增加起到了一定作用。经过数代人在多个孩子中间的连续分割土地,造成了很多不能维持生存的小块土地。[17]这些人被迫寻找别的工作。另外,这些地区无疑有很多小农由于伯伦纳指出的原因而失去土地,比如不能应对歉收、疾病、市场波动等。然而,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地区有人曾经被强制剥夺土地。
对伯伦纳观点的最有力的反驳可能是,在明显剥夺农民的米德兰平原和中部地区,农业发展和变化以及自由农的发展非常缓慢。米德兰平原和中部地区对农民的剥夺主要发生在15世纪。这个时期的经济不景气对当地造成了极其沉重的打击。粮食价格下降并维持在很低的水平,许多农民和领主转向经营利润较高的羊毛、肉类和牛奶等商品。这些行为还发挥了使用劳动力较少的优势,而这一时期这些地区劳动力正好短缺。[10](80,87)由于这些原因,米德兰平原和中部地区的粮食种植面积急剧缩小。
向畜牧业的转变刺激了农场主和领主在这些地区进行圈地。和东部和西南部地区的圈地不同,米德兰平原和中部的圈地导致了巨大的社会灾难。许多小农依靠公共放牧权为生,而圈地常常意味着在公田上放牧权利的终结。因此,这些地区的圈地遭到了大规模的抵制。领主经常用武力镇压反抗,只是简单驱逐反对圈地的农民并把他们的土地并入大型牧羊农场。1517年的调查委员会揭示了前些年许多蓄意驱赶佃农的案例 都发生在米德兰平原和中部地区。[10](88)由于这些地区的佃农主要是惯例佃农,就使得领主合法(和非法)驱赶佃农成为可能。这些驱赶促成了一系列的反圈地暴乱,并最终形成了1607年的米德兰平原严重的反叛。这被称为英格兰最后一次农民起义。[18]
然而,这个时期剥夺农民并没有自然导致这些地区高产耕种农场的产生。大养羊农场主要是面向市场生产羊毛,主要富了羊毛生产者。到16世纪,新型轮种农业开始遍布整个中部地区,这提高了谷物产量。然而,这些地区农业产量的增加直到17世纪才体现出来。[14](1577)整个15世纪(以及很久以后)英格兰的产粮区仍是东部和西南部地区,尤其是萨福克东部、肯特一些地区和西南部沿海地区。[10](135)
综合以上分析,伯伦纳的阶级关系说不足以解释英格兰农业变迁中自由农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然而伯伦纳关于生产中的社会关系是农业变迁和自由农发展的重要的决定性因素的认识却不应该被忽视。
五、田制说
1994年5月罗斯玛丽·L·霍普克罗夫特在《美国社会学杂志》发表《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农业变迁的社会起因》[14]一文,提出了“田制说”。作者以大量的历史事实为依据,采用多元分析的方法,反驳了人口说、生态说、市场说和阶级关系说,指出造成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农业变化地区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包括自由农发展的不平衡)的决定性的因素是各地生产的社会组织(the local social organization of production)或田制(field system)的不同。
罗斯玛丽·L·霍普克罗夫特选择1334年和1515年之间英国44个郡的社会财富增长率(GROWTHRATE)作为从属变量,把市场、工业、人口、地方农业社会组织(田制)和农业的技术革新作为独立变量,进行多元分析。分析的局限性在于没有直接测量农业发展或变化。由于中世纪晚期英格兰各郡的农业生产要素 土地、劳动力、资金 的生产率全面详细的数据资料难以估算,不能对农业发展进行直接衡量。霍普克罗夫特假设来自工业生产的任何财富都是农业发展的间接证据,这样经济增长就包括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的生产率报酬。因此他采用经济增长来代替农业增长。在各个独立变量中,多数采用的是14世纪晚期的数据,例如,市场因素指标采用港口数量和1334年的市场数量;工业衡量指标采用到14世纪晚期为止每年的布匹生产数量和毛纺织工业中心的数量;人口因素采用每平方英里人口用来衡量人口密度的影响,数据来源于1377年的人头税数量。农业技术革新的指标,采用领地畜力中马匹的百分比,马虽然要贵些,却是比牛更加高效的牵引牲畜,马的使用是农业革新的一个标志。只有田制是一个虚拟变量,他把英国敞田制分为典型的敞田制(Regular Open Field System)地区与非典型的敞田区(Irregular Open Fields)和圈地区(Enclosures),以是否典型的敞田区作为衡量农业的社会组织在农业变革和自由农发展中的作用的一个独立变量,因为典型的敞田区与圈地区或非典型的敞田区相比庄园化程度更高而且自由农民数量较少。
霍普克罗夫特通过分析论证得出的结论是,造成1600年以前英国经济发展的地区不平衡的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是工业发展的程度、人口密度和地方农业社会组织,造成农业发展不平衡的最重要的因素是地方农业生产的社会组织即田制的不同,农业新技术的利用,农场规模的发展、农场的联合和圈地以及契约型和非“封建”土地持有协议(contractual and nonfeudal landholding arrangements)最先出现在非典型的敞田制地区 英格兰东部和西南部地区,农业发展相对落后,农民向自由劳动力发展相对缓慢的地区都是典型的敞田制地区。
“田制说”假设工业财富的增长是农业增长的间接证据,用经济增长代替农业增长,以及各个变量的设定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无疑是值得商榷的。然而,霍普克罗夫特把自由农发展的地区不平衡归咎于田制却是不应被忽视的,因为他把这一问题的解决视角转移到了“田间地头”和在其中劳作的农民身上。
[1]Ester Boserup,The Conditions of Agricultural Growth. [M].London:Allen&Unwin,1965.
[2]J.Goldstone,Regional Ecology and Agrarian Change in England and France:1500-1700,[J].Politics and Society, 1988,16(2-3):265-286.
[3]J.D.Chambers and G.E.Mingay,The Agricultural Rev olution:1750-1880,[M].London:B.T.Batsford,1966:65.
[4]Jan de Vries,The Dutch Rural Economy in the Golden Age:1500-1700,[M].Yale University Press,1974.转引自Rose L.Hopcroft,The Social Origins of Agrarian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9,No.6.(May,1994):1567.
[5]B.M.S.Campbell and John P.Power,Mapping the A-gricultural Geography of Medieval England,[J].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1985,15(1):24-39.
[6]B.M.S.Campbell and Mark Overton,English Seignorial Agriculture Pp.144-182 in Land,Labour and Livestock, [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1.
[7]J.C.Russell,British Medieval Population,[M].Albu querque: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1948.
[8]R.H.Britnell,“Eastern England”in the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3,1348-1500,edited by Edward Miller.[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59,65.
[9]F.J.Fisher,The Development of the London Food Market:1540-1640,135-52.in Essays in Economic History,vol. 1.Edited by E.M.Carus-Wilson,[C].London:Edward Arnold,1954.E.A.Wrigley,Urban Growth and Agricultural Change:England and the Continent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J].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1985,15(4): 683-728.
[10]E.Miller,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3,1348-1500,[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1991.
[11]Robert Brenner,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pp.10-63 in The Brenner Debate: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edited by T.H. Aston and C.H.E.Philpin.[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12]Robert Brenner,The Agrarian Roots of European Capi talism,213-327 in The Brenner Debate: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 dustrialEurope,editedbyT.H.AstonandC.H.E.Philpin. [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13]Robert Brenner,The Social Basis of Economic Develop ment,pp.23-53 in Analytical Marxism,edited by John
[14]Rose L.Hopcroft,The Social Origins of Agrarian Change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J].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9,No.6.May,1994.1559-1595.
[15]B.M.S.Campbell,Arable Productivity in Medieval Eng land:Some Evidence from Norfolk,[J].Journal of Eco nomic History,1983,43:379-404;Edward Miller,The A 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Vol.3,1348-1500,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p.210.
[16]F.R.H.du Doulay,Who Were Farming the English Demesnes at the End of the Middle Ages?[J].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65,2d ser.17(3):443-55.
[17]B.M.S.Campbell,Population Change and the Genesis of Commonfields on a Norfolk Manor,[J].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80,2d ser.,33:174-92.
[18]E.Miller,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Vol.3,1348-1500,[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 sity Press,1991.637;John E.Martin,Feudalism to Cap italism:Peasant and Landlord in English Agrarian Devel opment,[M].London: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83.
(责任编辑:杨睿)
Review of researches of west academe on the regional differences of free peasants’growth in later mediaeval England
LI Yan-xi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Social Development,Anyang Normal College,Henan Anyang 455000,China)
Historical evidence showed that it had had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course of villein translating into free peasant during the late of medieval England(1300-1500).West scholars have worked hard for a long time to research the reasons for leading to the results and they have studied many ways.The main views include standpoints of Population Density,Ecology, Commercial Incentives,Class Relation and Field System.This article is a paper of review on above mentioned views.
later medieval;the United Kingdom;free peasant;regional difference
K10
A
1672-0598(2009)02-0083-07
10.3969/j.issn.1672-0598.2009.02.017
2008-11-09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经费资助研究项目(项目名称:中世纪晚期英国自由农民发展中的地区差别研究;项目类别:规划项目;批准号:2008—GH—006)的阶段性成果。
李彦雄(1971-),男,河南安阳人,历史学博士,讲师,安阳师范学院,从事中世纪史和英国农民问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