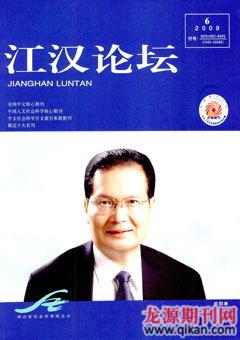王阳明经学思想新探
蔡方鹿 付 春
摘要:王阳明提出化繁就简,去好文之风;提倡和重视心学,强调“四书”、“五经”不过是说这心体;认为看经书就是要致吾心之良知,由此主张复《大学》古本,以阐发自己的致良知说。形成与程朱理学不同的经学观,从心学的角度发展了中国经学。
关键词:王阳明;经学思想;心学
中图分类号:B24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6-0010-05
在学术发展史上,明代的学风继南宋朱陆之争逐渐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朱熹将义理与训诂相结合,以“四书”为主,遍注群经的尚博学风逐步转向舍繁求简、崇尚心悟的简易学风。明中叶。心学蔚然形成一代学术思潮。王阳明从心学立场出发,把经学纳入心学的范畴,认为经典不过是吾心的记籍,治经学的目的是为了发明本心、致良知。在阐发其心学思想时,也借用了经学的形式,并对以往的经典和经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这是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不可或缺的心学发展阶段和环节。针对程朱学在明初被定为官学,学者争相趋之,而出现祖述朱熹,把程朱对经典的注解当作新的章句,盲目推崇、繁琐释之,而不求创新,流于空谈程朱性理之学的弊病,王阳明起而纠弊,而提出化繁就简,去好文之风;提倡和重视心学,强调“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并提出“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的思想,由此主张复《大学》古本,以阐发自己的致良知说,发展了陆九渊“六经”皆我心注脚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阳明心学经学观的特色。
一、返朴还淳,化繁就简,去好文之
南宋时期,朱熹提倡泛观博览,博而后约,其后学流于繁琐;陆九渊提倡简约,内求于心,为王阳明所继承和发展,由此他提出化繁就简,以去好文之风,对历代学风加以评说。学风的差异,体现了学术思想不同的特质。他说:
以明道者使其返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饶饶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巳也。……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
王阳明提出“返朴还淳”的思想,以追求淳朴学风,而反对美其言辞以夸世。强调明道重于删述“六经”,在道与“六经”之间,道更为重要,这反映了王阳明经学思想的要旨。他把天下大乱归结为虚文盛而实行衰,认为孔子删述“六经”,是为了废当时的好文之风:就《易》而言,废《连山》、《归藏》等纷纷之说,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易》,使天下言《易》者归于一;于《书》废《典》、《谟》以后之文;于《诗》去《九丘》、《八索》等一切淫哇逸荡之词:于《礼》、《乐》废名物度数;于《春秋》削其繁。总之,孔子述“六经”,担心繁文之乱天下,惟简是求,化繁就简,归于淳朴,去好文之风以求其实,并非以文来教之。这体现了阳明经学的简朴学风,与朱熹遍注群经,通经求理的学风形成对照。
王阳明化繁就简,提倡返朴还淳,去好文之风,这不仅是对所谓的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思想的继承,而且其理论针对性更是对汉学及朱学流弊所表现出来的记诵词章、广探博览、辨别名物度数、空谈仁义以为行等治经方法的修正。李明友先生认为,王阳明“除了批评汉唐时期的注重文字训诂的学术方法之外,主要是批评朱子后学的拘泥于朱子文字蹈旧的风气”。对此。王阳明批评说:
工文词,多论说,广探极览,以为博也,可以为学乎?……辩名物,考度数,释经正史,以为密也,可以为学乎?……整容色,修辞气,言必信,动必果,谈说仁义,以为行也,可以为学乎?……去是三者而恬淡其心,专一其气,廓然而虚,湛然而定,以为静也,可以为学乎?
通过与学者对话,王阳明对三种学界流弊提出批评。他认为,工于文词,多方论说,广泛探索,大量阅览,以此为博;考辩名物度数,释经正史,以此为详密;整容色,修辞气,注重言行礼仪,以此为实行,这些都是需要克服的学界流弊。王阳明从经学的角度对朱学提出了批评。这具有时代的必然性。指出程朱之后,其后学弟子未能将师友之道继承下来,使经学重新陷于训诂支离之中,追求辞章之学,以习举业,如此使圣人之学几至衰息。其原因在于未求其心,未致良知。并对宋儒周敦颐、二程以来“言益详”、“析理益精”造成的弊端提出批评。他说:
颜子没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唯一贯之旨传之孟轲,终又二千余年而周、程续。自是而后,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以难。盖孟氏患杨、墨;周、程之际,释、老大行。今世学者,皆知宗孔、孟,贱杨、墨,摈释、老,圣人之道若大明于世。然吾从而求之,圣人不得而见之矣。其能有若墨氏之兼爱者乎?其能有若杨氏之为我者乎?其能有若老氏之清净自守、释氏之究心性命者乎?吾何以杨、墨、老、释之思哉?彼于圣人之道异,然犹有自得也。而世之学者,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谓圣人之道劳苦无功,非复人之所可为,而徒取辩于言词之间;古之人有终身不能究者,今吾皆能言其略,自以为若是亦足矣,而圣人之学遂废。则今之所大患者,岂非记诵词章之习!而弊之所从来,无亦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欤!……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
指出颜子没后而圣人之学亡,曾子将一贯之旨传给孟轲,后又经二千余年(实则一千三、四百年)而周敦颐、二程加以继承。从此而后,由于言益详,导致道益晦;而析理益精,造成学益支离无本,而求学于外,使得更为繁琐和艰难。从表面上看,今世学者,都知道宗孔、孟,而贱杨、墨,摈佛、老,圣人之道好像是大明于世。然而在王阳明看来,却求之而不得见圣人。其原因就在于未能有自得。王阳明甚至指出,即使被视为异端的杨、墨、老、释,虽其学说与圣人之道相异,但它们“犹有自得也”,即不论其学说的性质如何,都需要“自得”,而不得徒假外饰。由于世之学者,陷于章句之末,人为地雕琢描绘以夸俗;认为圣人之道难以求得,而把注意力放到取辩于言词之间,使得圣人之学遂废。并指出,如今的大患就在于记诵词章之习,而流弊的产生,正在于“言之太详、析之太精者之过”。为纠正学界流弊,王阳明提出学仁义、求性命,应离开记诵辞章而不为,把功夫放在“求以自得”上。并坦承自己曾究心于佛老,后来交友于湛甘泉,而共同倡道,即把向内探求、自得其心放在首位,而不得流于训诂、辞章之末。他说:“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业举之习,圣学几于息矣。”指出程朱之后,“六经”分裂于训诂,学者陷于辞章、举业之陋习,形成新的章句训诂之学,使得圣学几息。而王阳明起而振之,以“自得”为宗旨,目的在于化繁就简,抨击“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的繁琐好文之风,以明心见道。王阳明“化繁就简”的学风有对佛教心学吸取的因素,他承认佛老等也
“犹有自得”,强调“自得”于心,教人于身心上做功夫,这反映了经学理学化过程中儒家学者对佛老之学的借鉴,以此开创了儒学的心性哲学的学术思想体系。
二、“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
王阳明治经、读经书的目的是为了明心。其心即道,明心也就是明道,而不是仅停留在读经书,弄懂经书字面的文义上。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得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在回答学者问题时王阳明强调,看经书不能只从文义上讲求,而是要明心体,明道,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就是说这心体的。在王阳明看来,经典的权威在心的权威之下,他明确提出心体明即是道明,认为儒家经典只是为了说明心体的,这是对陆九渊以六经为我心之注脚思想的继承。并认为心即是道,心体明即是道明,心、道没有什么区别,这是做学问的首要之处。进而王阳明强调:“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正人心也就是为了明道,这是圣人之所以删述“六经”的目的。认为如果道明于天下,孔子就不会删述“六经”。可见“正人心”、“明道”,在王阳明看来,是治经学的宗旨。这也体现了宋学中陆王心学一派的经学特色。
从“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心体明即是道明”出发,王阳明进而提出“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的思想,把“六经”与吾心、道联系起来,而以心为主。他说:
“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君子之于“六经”也,求之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纪纲政事而时施焉,所以尊《书》也;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时发焉,所以尊《诗》也;求之吾心之条理节文而时著焉,所以尊《礼》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时生焉,所以尊《乐》也;求之吾心之诚伪邪正而时辨焉,所以尊《春秋》也。盖昔者圣人之扶人极,忧后世,而述“六经”也。……故“六经”者,吾心之记籍也,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而世之学者,不知求“六经”之实于吾心,而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然以为是“六经”矣。……呜呼!“六经”之学,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功利,崇邪说,是谓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没溺于浅闻小见以涂天下之耳目,是谓侮经;侈淫辞,竞诡辩,饰奸心,盗行逐世,垄断而自以为通经,是谓贼经。若是者,是并其所谓记籍者而割裂弃毁之矣,宁复知所以为尊经也乎!
所谓“六经”为吾心之常道,是指吾心在自然、社会、天地万物、宇宙时空等各个方面的表现而由《易》、《书》、《诗》、《礼》、《乐》、《春秋》等“六经”记录下来,“六经”作为载道之书,记录了心体之常道,而“六经”之道各有侧重,其中《易》是记载吾心之阴阳消息之道的经书,《书》是记载吾心之纪纲政事之道的经书,《诗》是记载吾心之歌咏性情之道的经书,《礼》是记载吾心之条理节文之道的经书,《乐》是记载吾心之欣喜和平之道的经书,《春秋》是记载吾心之诚伪邪正之道的经书。与之相应,君子对于记载吾心之常道的“六经”而言,求吾心之阴阳消息而时行之,这就是尊《易》;求吾心之纪纲政事而加以实施,这就是尊《书》;求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抒发情感,这就是尊《诗》;求吾心之条理节文而谨守礼仪,这就是尊《礼》;求吾心之欣喜和平而生喜,这就是尊《乐》;求吾心之诚伪邪正而分辨是非,这就是尊《春秋》。强调圣人述“六经”是为了扶人极,忧后世,而“六经”之道存于吾心,所以“六经”乃吾心之记籍、而“六经”之实,则具于吾心。所谓记籍,指把心的状态数目记录下来而已。“六经”作为吾心之记籍,它是为明心、明道服务的,所以王阳明批评“徒考索于影响之间,牵制于文义之末,硁硁陉然以为是‘六经”的治经方法,认为尚功利,崇邪说是乱经;习训诂,传记诵是侮经;侈淫辞,竞诡辩是贼经。这些自以为通经的人,不过是对经典的割裂毁弃,更谈不上什么尊经。王阳明“心体明即是道明”,“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的思想,在抬高心的地位的同时,对经典也给以一定的重视,认为经典是吾心的记籍,治经学的目的是为了明心、明道。在阐发其心学思想时,也借用了经学的形式,但强调心对于经典的主导,这体现了阳明经学的心学特征,也就是说,从心学的角度发展了经学。
三、“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
王阳明的经学观主要体现在把治经学与其心学思想的核心致良知说结合起来,提出“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的思想,由此发展了陆九渊“六经”皆我心注脚的思想,充分体现了陆王心学经学观的特色。从而从心学的角度发展了中国经学与宋明理学。与此相关,王阳明为了论证其经学观和致良知说,提出复《大学》古本的主张和知行合一说,丰富了《大学》的理论和中国哲学的认识论。
王阳明对陆氏心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他提出致良知说。在经典与良知的关系上,王阳明突出良知的重要性,认为经典为良知服务,看经书的目的是为了致良知。他说:“圣贤垂训,固有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取其有益于学而已,则千经万典,颠倒纵横,皆为我之所用。一涉拘执比拟。则反为所缚。”指出经典虽为圣人所作,但在经书之中有言不尽意之处,所以致吾心之良知要摆在治经的首要位置,使儒家经典为我所用。并反对拘泥于经书文字,反为经典束缚了致良知。王阳明的这一思想是对汉学考据训诂之习的否定。同时也是对二程“经所以载道”思想的发展,把“经所以载道”的道发展为良知,使二程经典作为载道的典籍的思想一变而为“六经”为吾心之常道的观点。他说:“六经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以典型的“六经”注我与程朱的我注“六经”区别开来,认为经典不过是吾心的记籍,它记述心内的种种事物,把儒家经典的权威性附属于吾心,也就是从属于良知。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盲从旧权威的创新精神。王阳明还指出: “只致良知,虽千经万典,异端曲学,如执权衡,天下轻重莫逃焉,更不必支分句析,以知解接人也。”以只致良知来权衡经典、异端曲学之是非,而不必去“支分句析”地诠释经典。在经典与心之良知的相互关系上,以心之良知为本,以正人心为目的,以经典服从于心之良知,为致良知、“正人心”服务,强调以致良知为宗旨来读经书。这体现了王阳明心学的经典观和经学观。
四、复《大学》古本
王阳明对《大学》一书很重视,撰有《大学问》一篇。章权才先生认为:“在经学方面,王阳明主要围绕《大学》著书立说。”阳明弟子钱德洪云:“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之全功,使知从人之路。
师征思、田将发,先授《大学问》,德洪受而录之。”并云:“《大学问》者,师门之教典也。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使人闻言之下,即得此心之知,无出于民彝物则之中,致知之功,不外乎修齐治平之内。学者果能实地用功,一番听受,一番亲切。师常曰:‘吾此意思有能直下承当,只此修为,直造圣域。参之经典,无不吻合,不必求之多闻多识之中也。”将《大学问》称为“师门之教典”,可见其重要性。并可知王阳明重视《大学》的针对性是批评“多闻多识”的学风,而提倡“直下承当”,“直造圣域”的简易工夫,即以求之于吾心之良知为宗旨。
虽然总的来说,王阳明认为经典只是吾心的记籍,但王阳明亦重视通过《大学》来阐发其心学思想的核心致良知说。尽管阳明与朱熹均推重《大学》一书,然而王阳明所依傍的《大学》文本却与朱熹不同,他对朱熹把《大学》一书分为经之一章、传之十章的经传两个部分,以及为了解释经之一章的格物致知之义,人为地增补了《格物致知补传》134个字持不同意见。以为朱熹改本非圣门本旨,而主张复《大学》古本,去掉朱熹增补的文字,不再分章,以复《大学》之旧。他说:“《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失在于过信孔子则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传也。”认为《大学》古本为孔门相传旧本,以朱熹补本服从于《大学》旧本。并指出:“且旧本之传数千载矣,今读其文词,既明白而可通;论其工夫,又易简而可入。”对《大学》古本推崇有加,在此基础上,王阳明阐发其致良知说。
王阳明对《大学》的“致知”之义十分重视,认为“致知”二字,真是个千古圣传之秘。能认识到它,百世以待圣人而不惑。在程朱那里,千古圣人相传以道,而在王阳明看来,致良知则成为千古圣人相传之密旨,从而以致良知说取代了圣人传道说。王阳明重视《大学》的“致知”之义,但其致良知说与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存在着区别。王阳明为《大学》古本作序,表现出与朱学的不同的思想倾向。他说:
致知者,诚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实也。物格则知致意诚,而有以复其本体,是之谓止至善。圣人惧人之求于外也,而反复其辞。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务于诚意而徒以格物者,谓之支;不事于格物而徒以诚意者,谓之虚;不本于致知而徒以格物诚意者,谓之妄。支与虚与妄。其于至善也远矣。合之以敬而益缀,补之以传而益离。吾惧学之曰远于至善也,去分章而复旧本,傍为之什,以引其义。庶几复见圣人之心,而求之者有其要。国
王阳明以己意解《大学》,认为“《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而致知为诚意之本,格物为致知之实。如果不以诚意为要,而就去格物,那是支离;不从事于格物而只去诚意,就是虚;不本于致知而就去格物诚意,这就是妄。表现出致知对于诚意的重要性。其思想倾向是惧怕人们求知于外,而强调诚心中之意,致心之良知,把人们的注意力转向心内之世界,而不是向客观物质世界探求。由此批评朱熹使《大学》“旧本析而圣人之意亡”,而主张“去分章而复旧本”,以恢复《大学》古本的本来面貌。对此,王阳明指出:“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认为致知并不是向外追求,扩充知识,而是为了致吾心之良知。在知行关系上,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说,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他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与行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并指出,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把知行合为一体。通过对《大学》的重解,来论述自己的“知行合一”思想。并指出:“后之学者,附会于《补传》而不深考于经旨,牵制于文义而不体认于身心。是以往往失之支离,而卒无所得,恐非执经而不考传之过也。”批评朱子后学附会于朱熹的《格物致知补传》,而未深究于《大学》的经旨,是牵于文义而不体认于身心,失之支离,并非是执经而不考传之过。从王阳明治经的学术倾向看,他并不重视执经考传的训诂考释之事,从他批评“牵制于文义而不体认于身心”来看,他的主要倾向还是要体认于自家身心的。以上可见,虽然阳明、朱熹都重视《大学》,以之作为阐发自己理论的经典文本依据,但对《大学》的格物致知之旨却有不同的理解。
王阳明的经学观在总的属于重义理轻考释的宋学阵营和理学思潮的前提下。他更偏向于陆氏心学一派,陆学不受经典束缚,内求于心,忽视知识,不立文字,以己意说经的学风得到王阳明的赞同;而对朱熹一派重视对经典的学习和阐发,强调义理从经典出的治学倾向则不大认同。反映了学风的转向和学术发展的趋势。王阳明提出“凡看经书,要在致吾之良知”的思想,以致吾心之良知作为其思想体系的最高原则。在良知与经典、良知与圣人关系问题上,王阳明认为看经书是为了致良知,良知超越圣愚,在圣人的权威之上,从而强调“致良知之外无学矣”,突破程朱天理论、道统论一统天下的局面。以致良知说取而代之。在新的高度重新确立起心的权威,这对于批判旧传统,充分肯定主体的价值和人的主观能动性,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在程朱理学末流弊端日益显露的时代,王阳明提出致良知说,强调经典为良知服务,看经书的目的是为了致良知,以更具主体思维能动性的“良知”范畴和致良知说扬弃并发展了程朱理学,使良知说成为左右当时思想界逾百年的学术思潮,表现出他的心学经学观和不盲从旧权威的思想解放精神,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责任编辑陈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