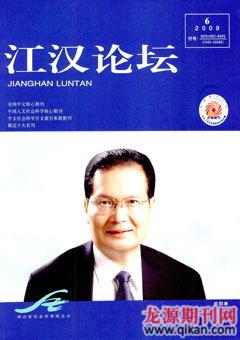富于东方意蕴的权利探求
赵秋棉 梁晓辉
摘要:川端康成塑造了一系列独具东方意蕴的青年女性形象。作家以独到的视角去感觉她们无闻于世间的“绝美”的存在;凄美的营造着她们在困境中生存的迷茫与无奈;最终,在优美的悲剧性结局中发出了对女性权利的最悲戚的呼唤。敲击并震撼着男权社会里人们麻木的心灵。
关键词:川端康成:东方意蕴;青年女性权利
中图分类号:1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6-0106-03
川端康成是值得同情的,生活的孤独和遭遇的不幸几乎影响着这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全部感觉。所以,他不是现实的积极参加者和干预者。这种“局外”性恰恰促成了作家向自我的回归,用文学来书写心灵。如椽巨笔之下,他“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自己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川端康成宣称自己从未放弃过根底上的东方传统,同时,作为新感觉派运动的发起者,他的创作艺术又贯通中西。正是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塑造了川端康成作品中独具风格的青年女性形象,作家赋予这些青年女性独特的东方意蕴。进而在绝美的营造中发出了对于女性权利的呼唤。她们的存在是默默无闻的。面对其困境下的遭遇。我们感受到凄美的感伤与无奈,最终,在优雅的“撕碎”面前,我们追随作家体验着更深层次的震撼。
一、绝美的存在:无闻于世的卑微呈现
每一位大艺术家都有自己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川端康成是用感觉去体验的,他的作品始终在竭力地表达一种美的存在,这种美体现在他对女性的观照上,从而造就出一系列绝美的青年女性形象。这些女性的美是外表与心灵的结合,美得令人感動,富于东方意蕴。
美感总是率先通过外表的纯美展示出来。在川端的早期作品《伊豆的舞女》中,最让二十岁的“我”心动不已的熏子就带来一种纯洁的清爽。那是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的俊俏舞女。尤其舞女唇上的一点胭脂红,和眼圈上的淡青阴影。宛若暗夜中舞曳的萤火虫,点燃了初懂情事的青年人若有若无的纯真之爱。作家将这种纯美全面的演绎在《雪国》中。驹子是川端康成《雪国》中极力赞美的第一位女性,女人给人的印象是洁净得出奇。甚至令人想到她的脚趾弯里大概也是干净的。小巧的朱唇却宛如美极了的水蛭环节,光滑而伸缩自如,在默默无言的时候也有一种动的感觉。这种美驱动着男主人公岛村的欲望,而叶子则引起了他内心的震颤。叶子的洁净是完美的、纯粹的、未搀杂任何瑕疵的,宛如一尊矜持脱俗的雕塑,进而延伸为纯美的象征。同样的纯美还演绎在《睡美人》里,《睡美人》调动了主人公江口老人的视觉、嗅觉、触觉、听觉,从多个角度呈现睡美人之美,纯洁之美极致到姑娘身体的“冰凉”,意想不到的美,竟然令江口老人觉得自己“另一颗心脏”在振翅欲飞。
一旦外在美与心灵之美结合起来,就构成了女性的绝美。无拘无束、无邪无欲的熏子荡涤着青年学生“我”的邪念,这言谈纯真而坦率,“好人”两个字是天真地倾吐情感的声音,舒畅了“我”的心情,清除着孤独和抑郁,而舞女的美也将永久占据“我”的心灵。纯真状态下的美丽真实且令人感动,绝美的造就也成为作品最打动人心之处。为了知恩图报做了艺妓的驹子是善良的,对生活充满了热情,外在的洁净象征着的是她内在的纯洁,展示着完全不同于都市人的精神面貌。正是这一点吸引着岛村从东京来到雪国求取心灵上的慰藉。驹子拒绝一切功利目的的献身精神,使她平添了许多女性美的魅力,深深震撼着一向虚无的岛村的心灵。川端康成借驹子之口指出:能够真心去爱一个人的,惟有女人才做得到!从而对女性美的尊崇推向灵魂净化的高度。叶子的美更是在于心灵,某种程度上,她是作为岛村和驹子心灵的开启者而存在的,日本川端文学研究会会长长谷川泉说:“以雪国为背景,在岛村与驹子身心倾斜的遥远处,安插了拥有纤细心灵的美少女叶子这一异常的生命,这是《雪国》的关键。”叶子是凛然不可侵犯的,她身上充分体现了作家美在心灵的理想。涅槃式的结束,谱就了一曲心灵的赞歌。当心灵之美用纯洁来形容,到任何地步也不会过分。川端康成极力将绝美演绎到极致,终至于无可书写,或许不复存在就意味着存在的极限。在《睡美人》那里,只是一个白姑娘,无名无姓的纯美呈现,附带的是无可捕述的心灵,在作家那里,或许当内在之美终于不再可描述的时候,绝美就将深深印刻在人的心灵深处。
川端康成的高明之处在于能够将这些青年女性的绝美在默默无闻的卑微中呈现。生活于男权文化传统之下,女性本来就处于从属者、被动者的地位,她们本就毫无身份可言,只能是默默忍受人生的卑微。在带有日式特色的东方传统之下她们的这种卑微似乎已经注定了她们终将黯然消逝的命运。如果不去刻意的观照,她们的美也许永远得不到丝毫的关注,而这正好和川端康成的“孤儿情结”是契合的。川端在悲哀孤独的眼泪中成长,母亲、祖母和姐姐先后死去,人生的孤独推动着他从普通人群中去寻找爱,母爱的过早缺失又促使他将这种追寻投放到了青年女性的身上,于是卑微中的绝美成为他的关注点。于是我们看到,熏子小小年纪,却是伊豆的舞女,过着漂泊不定的羁旅生涯;驹子的身份是一名艺妓,处于社会的最底层;苗子不过是在村子里当雇工,自幼生活在贫苦之家,饱尝了人世间的苦难(《古都》)。同样还有《舞姬》里的品子、《花的圆舞曲》里的星枝、《母亲的初恋》里的雪子等等,她们都是川端康成极力赞美的女性,这些不为人重视的人物身上,是精神与肉体结合的纯粹之美。正是因此,她们愈发显得熠熠生辉,魅力无限。也就是由于这些闪光点的呈现,使得川端康成的文学意蕴无穷。
二、困境中的迷茫:凄美的徒劳与无奈
在青年女性形象的绝美呈现过程中,川端康成对人物的境遇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绘。他是把日本传统文化中“物哀”的美学观念运用到极致的一位。通常认为,“物哀”就是审美主客体之间情感达到一致、和谐之时产生的美感。这里的“哀”包含了同情、哀伤、悲叹、赞颂、怜悯等多重内涵。川端康成抓住了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女性人物特有的内心情感,成功地塑造出一系列感人至深的美的艺术形象。她们的形体动作、心理活动乃至语言都是在优美的环境中展开的,这种展开总是带给我们一种温柔的感伤,吸引我们去体味那种淡淡的无奈与哀愁,进而深刻的认识到她们的生存困境。困境中的迷茫带给她们如许的无奈,种种冲破困境的努力都是徒劳的,但是,在以青年女性为中心的作品中,已经能够看到作家含蓄的女权探寻。
困境仿佛无处不在,给无奈身处其间的青年女性带来无限的迷茫和感伤。做舞女的熏子纯粹是出于无奈,她们一群被当时社会公开蔑视的流浪艺人。即使她们极端的自重自爱,却依然难以被茶馆老太太代表的社会所接纳——她们是只要有人留,哪儿都能住的那种人。一路上,“我”看到一些村口,都竖着“乞丐、江湖艺人不得入内”的牌子,在这些牌子的映衬下,舞女仿佛已
经无路可去,空余一片感伤和迷茫。执意报恩的驹子在决定做艺妓的那一刻就把自己投身于困境之中了。她是社会的被损害者,不知道自己的出路在何方。她在陪客时狂饮,实际上是在精神上进行自我麻醉。她总盼着做一个正经女人,却不知道如何才能改变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她盲目地为岛利付出了全部,好像是为了爱情,但只不过是把自己投入了另一个精神的困境,一切依然是迷茫的。相比之下,叶子的迷茫还在于,她把全部的爱都凝聚在了身患重病的行男身上,随着行男的病逝,她的一切希望都落了空,只能是伤感而迷茫的逡巡在行男的墓前;《古都》中的千重子是幸运的,她得到了父母之爱,但想到自己的弃儿身份,就陷入悲哀的無法摆脱的精神困境。对于自己的爱情婚姻,千重子有着自己的憧憬,但她又不断的怀疑幸福本身,甚至幸福就在身边,她也从不觉得自己真正拥有幸福。川端康成给予这位少女以无限的哀怜和同情,也预示着千重子的哀伤永远无法排解。
这些绝美的青年女性在困境中也有挣扎,甚至发出女性权利的呼唤,但这些反抗同样是东方式的,最终是追求徒劳的感伤与无奈。在《雪国》中的驹子是这种徒劳的典型。她为生活做出的全部努力与追求都是徒劳的。为了给行男治病她不惜卖身为妓,但行男之死证明了她奉献的徒劳;她有自己的生活信念,几年如一日地写日记,“不论什么都不加隐瞒地如实记载下来”。她认真学歌谣,练书法,读书,更练出一手铿锵有力的拔弦,不看谱子弹奏自如。她认为这才是“正正经经的生活”。但这一切在岛村眼中,不过是“一种虚无的徒劳”,不过是供酗酒者作乐之用罢了。更为悲哀的是,她把对爱情的执着追求寄托在虚无者岛村身上,对岛村一心一意,以心相托、以身相许,却终究是所爱非人。所以当她从岛村的话中体会到他“就是为了这常来的”时候,必然感受到深刻的刺痛和侮辱,终于发出了反抗的声音,但仅仅限于哭泣而已。挣扎似乎总是那么的无力,对于千重子这样的富家小姐亦如此。她喜欢真一,每次当她的父母提起她的婚事时,她的头脑中马上浮现出童年时期真一天真的笑容。但嘴上却是一再强调。自己的婚姻一切听从父母的安排,在事实上放弃了自己的主动追求。于是,在创作的后期川端康成甚至极端化的放弃掉了这种挣扎,让一个个的睡美人带给我们更大的哀伤。
川端康成利用困境与哀伤感觉的营造,叙述着女性受制于男性话语的生存事实。在川端的作品中可以看到,身处困境的青年女性是毫无话语权可言的,她们的世界观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更多的把希望寄托在男人身上。哪怕在身体和心灵上受到男人的侮辱和损害。也只能是忍气吞声的无奈。在川端看来,男人是如此的需要拯救却难以拯救,这也正是造成那些青年女性由绝美演变为凄美的重要方面。青年学生“我”或许还是可救赎的,伊豆的舞女们用她们的自重自爱、天真清纯打动着“我”,改变了“我”的看法,甚至生发出清纯之爱:然而,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很快被随后以岛村为代表的社会代言者湮没了,颓唐的他们在川端康成笔下的凄美与哀伤面前显得渺小而丑陋,作家用感觉带领我们去揭露、鄙视这种丑陋,进而正视女性的权利和地位。同时,也告诫那些以贤妻良母为自己生活和精神上最高理想的女人们,甘于做封建心理历史积淀的完全承载者,终将使她们陷入无力自拔的苦难深渊。
三、敲击与震撼:撕碎的优美与哀伤
川端康成内心应当是充满矛盾的,当他以一颗美好的心对待生命、对待生活、展示生活生命的美的时候,忽然发现并不是一切都像他所期待的那样美好。他用自己的方式感觉生活,怀着深深的爱将这些纯美的女性放置于叙述中心,然而美的极致却本就意味着毁灭,随着情节的一步步发展,悲剧性的结局竟至于无可挽回。倾尽全力,不过是优美的撕碎。她们的毁灭甚至没有任何声响,“无言的死,就是无限的话”。发生在青年女性身上的无言的悲剧,构成了人生最大的悲哀。借着优美的悲剧性结局,川端康成发出了对女性权利的最悲戚的呼唤。敲击并震撼着我们麻木的心灵。
川端康成无奈的看着自己塑造的美丽伴随着追求的徒劳逝去。《温泉旅馆》中的阿雪为了自己理想中的爱情,宁愿抛弃一切追随仓吉而去,结局是“山村里风传她被那个男子拉着四处流浪,最后被卖掉”,阿清虽然拼命挣扎,却终究逃脱不了沦落风尘、客死他乡,而她最后的希望也注定了无法实现——她所爱的孩子们没有排着队伍出现在给她送葬的队列里,送葬是名义上的,其实只有两个男人抬着一口用漂白布覆盖的棺材。《招魂节一景》中,樱子认真地表演着马术,直至精疲力竭,从马背上掉落下来;而“我”却是心情晴朗,怡然自得,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悲痛。死亡是悲剧性的,川端康成尽最大努力为我们营造一种美丽的感觉,以期冲淡死之惨烈,然而美丽并未曾将惨烈消解,反倒是带来了更强烈的敲击与震撼。死者在毁灭的凄惨中升华,而生者面临的仍将是无尽的悲伤与无奈。叶子凤凰涅槃式的结束,是作家对叶子的最美好的赞歌,生命的本真由此至于永恒和无限:驹子最终也没有寻求到生活的真实意义,因而陷入无尽的悲哀;《千只鹤》中,文予以她“纯洁的痛楚”拯救了菊治,但终于忍受不了“乱伦”的道德压力,默默地选择了孤独。
在川端康成的小说中,青年女性作为行动者统摄了整个小说叙事的方向。并成为叙事的中心。她们陨落的悲惨事实和叙事者的平静、欣赏甚至赞美之间形成强大的反差。我们看到的是东方的隐忍和无奈。这种无奈最大程度上使文体形成强烈的反讽效果,作家也由此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深层意义指向,这样的绝美是不为人世所容的,我们欣赏乃至赞美的不过是她们的苦难。某种程度上,正是对这种深层意指,引导着他的创作走向悲剧,当作家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甚至会为《古都》的停笔感到幸运。《写完<古都>之后》一文,道出了他的这种心情:“《古都》写了一百余回就结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幸运,也许是幸运的吧。但倘使再写下去,说不定《古都》会变样,一定会酿变成两位姑娘的悲属,造成悲剧的结局。作者有这样的预感:千重子既不会同龙助也不会同真一恋爱、结婚,北山的苗子也不会同秀男--恋爱也不会结婚吧。恐怕会越写越麻烦,会越写越苦恼吧。这些,只是隐藏在作者的内心底里,没有表现出来。”
如千叶宣一评价川端康成时所说的:“人只是一种走向这种死亡的存在,这种根本性的空虚与绝对孤独,使他将生的拯救寄托于美。”川端康成的局限性就在于,他从来没有像后期的女权主义者那样认识到,个人的不幸不只是个人的问题,而可能是社会问题,因而也是政治问题。当他一再站在叙事者的立场之上,用美来表达他对现实的感觉。并妄图以此冲淡对现实的失望的时候,只能是一步步步人绝望的深渊。《睡美人》中熟睡不醒的姑娘似乎向我们预示着美的失落,“熟睡”本身就意味着另一种意义上的死亡,“美”的拯救手段于事无补,当死亡终于降临——“睡美人”逝去,江口老人便觉察到“美”已逝去,自己的死期即将来临。川端康成把自身投入到美的虚幻之中。寻求以美的方式达到超越和永恒,却又陷入苦苦的挣扎与无奈,一旦醒悟,精心构筑的美的神殿便轰然坍塌。他的晚年陷入了极度的精神危机之中,绝美的营造者最终以自我毁灭收场,展现出了现代灵魂的深度痛苦和悲哀。
美最终结局是死亡,悲剧的结局,绝不仅仅是作为人的悲哀,这就是川端康成笔下的青年女性形象向我们呈现的。这些绝美的承载者。用她们的困境中无奈的挣扎演绎着人生的迷茫,并最终以优美的陨落与凄美的悲哀完成了人生的倾诉。生存的价值归于徒劳。悲哀便成为一个阶层的悲哀,一个社会的悲哀,一个历史的悲哀。而后来的女权主义者们要做的,就是要摆脱这种悲哀。波伏娃指出,在社会历史中,男性居于主导和决定地位,女性则处于被主导和被决定的地位,因而成为“第二性”。从川端康成这里我们也应该能够进一步寻求到,根本上是男性的需要和利益决定形成了女性的历史和现状,女人要摆脱这种“第二性”的地位,就应当站在这样一个基点上去努力争取权利的实现。
责任编辑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