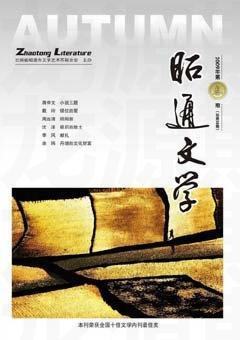经营人生
金 鹏
从记事起,也就是1960年,我只知道,自己降生在洞庭湖边沅江县,我家的门对着滔滔湖水,特别是涨水时节,浪打在河堤上,轰轰隆隆,水溢上堤,直奔我家那高高的门槛,吓得我大门都不敢出,躲在我五娘金白云的怀里直哆嗦。家的斜对面是一个高高的立在堤上的塔,塔里供奉着面目狰狞的龙王。当时,有三个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第一个是在广州当兵的父亲,当时,他是某炮师钢铁连的连长。五娘带着我玩的时候,总爱拿出父亲身着黄色军装,系着武装带的威武的照片对我说,长大了像你父亲一样,到广州当炮兵军官,打国民党。父亲年轻时有1.75米高,高鼻大眼配在端端正正的瓜子脸上,十分的清秀,父亲当兵时留下的身着黄呢子,系着宽宽的武装带的老照片上的样子,按现在时髦的话来说,长得十分的帅。以至于,我们几兄弟常常讨论父亲是如何看上不起眼的母亲的。所以,父亲形象在我朦胧的意识里就是天底下第一条汉子。第二个是在益阳农村生活的小脚外婆。外婆从小就裹脚,10多岁就在当地的一个大户人家当丫环,这家人很懂得教化丫环,每天晚上织麻布时,一边织布,一边教读书,外婆记性好,一个字不识,却能背得许多文章,如:女儿经、三字经、柳毅传书等。外婆每隔一段时间,总是要带一点红薯干来看望我,在那个生活十分困难的年代,有红薯干吃,对我来说是十分高兴的,特别是秋收时节,她每天都要到田里拾稻穗,把十天半月拾到的谷子,晒干后,用臼舂成米粉,从益阳到沅江,背着米粉和红薯干赶60多里的路送给我吃。外婆的脚小,只有大人的拳头大小,走60多里路是十分不容易的。第三个是我那长得天仙般的17岁的五娘,她的秀色和灵气在补了又补的补疤衣服内发光,我出生才两个月时,母亲为了国家的大跃进,就毅然决然地把我的奶断掉,到长沙纺织厂去工作了,父亲又在广州工作,所以,我一直是奶奶和五娘带着的,可能是奶奶太过于严格的缘故,对奶奶的印象不深,但是对五娘的印象特别深,因为,她一放学,就背着我到处去玩,我从小进食,都是五娘喂的,大一点的时候,自己会吃饭了,都要耍娇,赖着五娘喂饭,也只有五娘惯着我,背我,喂我,带我玩。但是,我不听五娘的话时,她就拽着我到塔下的龙王庙内吓唬我。后来五娘成了常德市的文工团名角。
我四岁的那一年,由于1.75米的父亲工作过分劳累,得了肺结核,组织上为了照顾父亲,安排他到炮兵教导团训练加农炮炮兵,并把母亲也调到广州工作,我们一家就在广州的一个兵营里安营扎寨了。茫茫荔枝园中藏着一个没有围墙的军营,母亲安排在军营的一个幼儿园里工作,我也在该幼儿园的小班里开始了启蒙教育。我们住的地方全是身着黄色呢子的军官,天天和那些威武、俊秀的叔叔阿姨们在一起生活,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建立起了军人高、大、全的形象。以至于现在,我在梦中都常常回到那片荔枝园,那个让我性格变得坚毅的军营里。
没有想到,1963年我父亲由于结核病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加上教导团的工作十分的繁重,父亲那80公斤的身体一下子就垮到55公斤左右,父亲实在耐不住了,于是,提出了退伍的申请,当时团里的优秀教练很少,领导一直都在做工作,希望他留下。可是,父亲坚持要退伍,领导看见他瘦得不成人形,只得答应他退伍,并以方便治疗为理由,把他和母亲安排在广州邮电局工作,可是父亲却坚持要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工作,领导的一片好心被他当成了驴心肺。大家都知道他固执,也就随着他。这一将就不要紧,可是苦了我们这一家,外婆和我们一家都跟着父亲来到云南的巧家养护段安家了。
巧家,银色(金沙江)的背带系着,大山背大的一个金沙江边上小县城,是彝族堂琅文化的发源地,和四川的金阳县隔江相望。夏天,站在养护段后面的小山上远远地看巧家城,一间间青瓦板壁房子组成的城市,被郁郁葱葱的甘蔗林构成的青纱帐层层包围,远远望去,绿绿的林海中间露出几个青瓦顶,县城在季节的怀抱中多了几分神秘和几分诗意。
巧家养护段是一个背靠红卫山的四合大院,大门对着环城路。院内种着石榴、青竹、蚕桑、梧桐、黄角兰。父亲到巧家养护段当副段长,工作依然很忙,当然,比起部队里还是轻松多了。我当时在巧家新华小学读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在家的时候,我们一早起来,水缸内挑满了水,父亲在屋子外的树下,抽着烟,白衬衣都被汗水打湿得巴在父亲那见骨的背上。父亲出差时,外婆一大早就把我叫醒,要我和她到一里外的龙潭抬水,巧家天气热,加上外婆是小脚,走路颠来颠去的,抬回水来,我和外婆的一身都湿了。
放学后,我和弟弟们喜欢在门前树下办家家。晚上,我们一家都在门前的树下吃饭歇凉,父亲肚子里总是装着道不完的龙门阵,摆起来一套一套的,每天晚上都吸引着一大群孩子。父亲的象棋下得好,在巧家也算一个远近闻名的高手,每逢周末,都有几个象棋爱好者到我家下棋,我就是那个时候学会了下棋。
我们这种安逸日子没有过几年,就开始文化大革命了。当时,父亲刚升为段长没几天。就被打成“走资本主义的走资派”了。段里的几个由于工作失误被父亲处理过的职工打着文革的旗号,把我父亲揪去批斗。一开始大家都文明批斗,讲道理摆事实,要父亲老实交待。父亲说,自己根子正,不是走资派,特别有两个因强奸罪被公安机关关过几年的工人,说父亲不老实,就动手打起人来,接着,父亲每天晚上都要被打得遍体鳞伤才回来,外婆和母亲害怕父亲想不通,总是一边搽着药酒,一边安慰他说:“你要挺住,这个家全靠你撑着,我们在这里没有亲戚,你一垮,我们就可怜了”。父亲总是答道:“为了这个我从湖南带来的家,我不会做傻事的,我在部队里,训练抱着死人睡时,就理解到了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再艰难的困境,我也会生存下去的,你们放心,有一线希望,我都会坚持下去的”。回家后,父亲还要写“检讨书”,父亲有个习惯,一写起文章来,就烟不离手,父亲的烟瘾也愈来愈大了。文革期间,造反派停发了父母亲的工资,外婆看着父亲没有烟抽而痛苦的样子,对我说,我们在巧家没有亲戚,父亲是我们的主心骨,不能倒,你去想办法弄烟给你父亲抽。晚上,我就领着弟弟到茶室里捡烟锅巴。白天,就把烟锅巴抖散,试着用自制的卷烟机卷成纸烟。当我制出第一支烟递给父亲时,父亲流下了被造反派打都没有流的眼泪。不知怎的,我们一家都流泪了,父亲抚着我的头说:“好孩子,男儿有泪不轻弹,你看,我每天被打,天天跪在瓷瓦渣上给毛主席请罪,都不叫不哼”。我懂事的点了点头。
巧家的武斗开始了,而且,战场就在巧家养路段后面的红卫山上,我父母也不知道被造反派带到什么地方去了。“红旗漫卷”和“6•2•9”两派为了争夺红卫山,打了三天三夜,手榴弹的爆炸声、枪声就像在我家的房顶上一样,外婆只得带着我们躲在床底下睡觉。三天后,几个“6•2•9”的守山学生和转业军人被“红旗漫卷”的抓到了,在养路段的操场上被挑了脚筋,头上钉三颗10公分长的钉子送到“6•2•9”去了。又过了几天,母亲被放出来了,为了避免武斗对我们的伤害,带着外婆和我们三兄弟到“6715”地质队家属区居住(“6715”是省属单位,在巧家是中立的)。
三个月后的一天早上,一个头发长长的白头老人突然敲开我家的门,外婆问:“老人家,你找谁”?“妈——,您认不出我来了”。“哇——我的伢子。”外婆突然大哭起来。我们全家外衣都没有穿就同时站在了堂屋中间,这时,母亲和白头人拥抱在一起哭啼,我们这才弄清楚白头人就是父亲。于是,我们一家人抱在一起,哭成一团。过了一会儿,父亲坚毅的说:“我没死!能回到这里,就是一个了不起的生命创举,我又挺过来了”。
是的,武斗开始,两个造反派都给父亲做工作,要父亲教他们使用六零炮,父亲坚决不答应,他说:“我教你们使用炮,打的都是革命群众,我都是罪人,所以,我是死也不会教任何一派的”。于是,“红旗漫卷”派人先下手,将父亲软禁在巧家乔麦地道班。为了逼他教他们使用六零炮,两个多月不准烧火,不给盐吃,不给理发,没有衣服换洗,天天给一撮箕猪洋芋生吃,他们看见父亲临死不屈,就是不教,准备把父亲砍掉喂狼。一个好心的道班工人当夜值班,在他的帮助带领下,一夜跑了120多公里路,过了四五个检查站,才到了家。我们一家到今天都感谢那位不知名的好心人,要不然,我们的主心骨——父亲可能30多岁就夭折了。
武斗后期,造反派打仗,把一座大桥炸了,50多人和车掉进了百多米的深渊。父亲闻讯,冒着生命危险带着我赶到现场,看到人和车摔成一片浆糊的惨景,父亲放声哭道:“天啊,都在做些什么啊”!接着,马上组织当地农民清理现场。
1969年,文革后期,父母亲带着我们全家来到巧家大海梁子道班,接受劳动改造。在道班工人和供销社职员普大爹一家的帮助下,我们把行李和家具都搬到了一间黝黑的土胚青瓦房子里,进了堂屋中间。在一片漆黑中,片刻,才看见是一间客厅套两间住房的房子,进门的右边有一个四四方方的火塘,几坨树疙瘩支在一起,火苗儿直往上蹿,一条油亮的铁丝从花楼上吊下,勾着一个黑漆漆的水壶,水开得好欢,火塘边摆着几个坐得发亮的草墩。尽管天气寒冷,这里仍然是春意融融的,我们一家就在这一厅两室的房内住下了,而且一住就是三年。
巧家大海梁子,是因为这里有一个秀丽的大海水库而得名,距离铅(yan)场街子10多里路。来到这个简陋恶劣的新环境里居住,我们反而十分高兴,父亲从供销社打了一壶苞谷酒和道班工人及普大爹一家一起喝得烂醉才回家,喝酒时那快乐的笑声在山野里回荡。因为父亲有病,母亲从来都不准父亲沾酒,今天,父亲、母亲都十分高兴,母亲就没有阻止父亲喝酒。当母亲把喝醉的父亲扶到床上睡下时,在火塘边坐下后就哭了起来。外婆也跟着哭起来,我不知所措地安慰母亲说:“妈妈不要哭了,今天应该高兴呀”,母亲点点头,哭得更伤心了。外婆说:“你父亲能活到现在,不容易呀!我们这个家,能有今天也不容易呀,就让你母亲哭吧”。从文革开始,被打成走资派的父亲就没有笑过。今天,他开心地笑了。是的,这里正是我们苦苦寻找了很久的避风港和与世隔绝的桃花源。这里没有武斗,没有派系;这里没有人揪斗父亲,强迫他戴高帽子,挂20多斤牌子,并且跪在瓷瓦上,面向毛主席像编排自己如何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行;这里更没有人要挟我的父亲游街批斗。
几天后,县革委会领导担心父亲的言行会同化道班工人。于是,把所有的工人都调走了,道班上只剩下我们一家人和供销社的普大爹一家了。
开始,父母亲白天带着我一起到公路上补路,晚上父亲就指导我学习,母亲用缝纫机给附近的乡亲做衣服,外婆在火塘边教弟弟们背三字经、柳毅传书等。你看,这个家庭,是不是一点也不像饱受文革洗涤过的家,父母对这样的日子十分的满足。
1971年秋天,父亲平反了,并调到昭通养护段当段长。我们又举家迁到了昭通。到了昭通养护段不久,公路八团就用手柄把段里五张翻斗拖拉机和翻斗车摇得发起电来,嘣嘣直叫,工人们就叫它“嘣嘣车”。当时,谁都不会弄它。开嘣嘣车嘛,难不倒当过加农炮炮连连长的父亲,父亲一跳上车就开着走了,在场的工人们都傻了眼。于是父亲就办起培训班来,一下子就教出了十多个徒弟。其他养路段的“嘣嘣车”驾驶员都要上“路八团”学习一个多月才上路,昭通段自己就培训出了一批驾驶员,一时成了佳话,各段都派人前来取经。
文革后,为了整顿文革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父亲作为清理整顿工作队成员先后被派到了“汽八团”、“昭通地区运输公司”工作,他每到一个地方,由于正直,无私,敢于面对事实,政策把握得当而得到大家的尊重和爱戴。父亲参加整顿完昭通地区运输公司后,就留在公司里工作。
1977年恢复高考后,父亲十分重视我们的学习,无论我们在学习上有多大的困难,他都尽力帮助我们,鼓励我们,并且请好老师给我们辅导,所以,我们几兄弟都考上了大学,得到了相对稳定的工作。
父亲病逝时只有67岁。这时,我们四兄弟都找到工作了,成了家。父亲临终时,笑着对我们四兄弟说:“我的一生虽然短暂,也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我对得起培养了我的党和人民,对得起曾经培养过我的部队。唯一对不起的是你们和你们的母亲,我把你们带到这艰苦的地方来,又没有给你们留下什么……”。
67岁的父亲就这样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完成经营家庭,经营人生,经营事业的使命。父亲的一生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一是“对人真”,“真”得没有一点掩饰,特别是对待那些伤害过他的人都能一分为二对待。二是“对党忠”,“忠”得有点迂腐,无论文革如何无端的迫害他,以至于差点丢掉了性命,他都认为是党对他的考验。三是热爱家,“家”是他生存的希望,无论有多大的困难,为了家,都坚强地活下来了,对家庭的每一位成员都能宽容和呵护,特别突出的是我那长不大的四弟,无论如何的淘气,他都没有放弃对他的教育,当四弟找到工作后,成了家,父亲才松了口气。
弥留之际,地区运输公司的领导到医院看望他时,问他有什么愿望,父亲说:“希望你们向上级党委反应,我死后,能把党旗盖在我身上,就是我最后的愿望”。
父亲,完成了支撑我们这个家庭的任务,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应尽的义务,父亲的伟大之处就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为同事,为顾客办好事,办实事。他思想上最闪光的地方是:终身都相信党,热爱党。
【责任编辑 吴明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