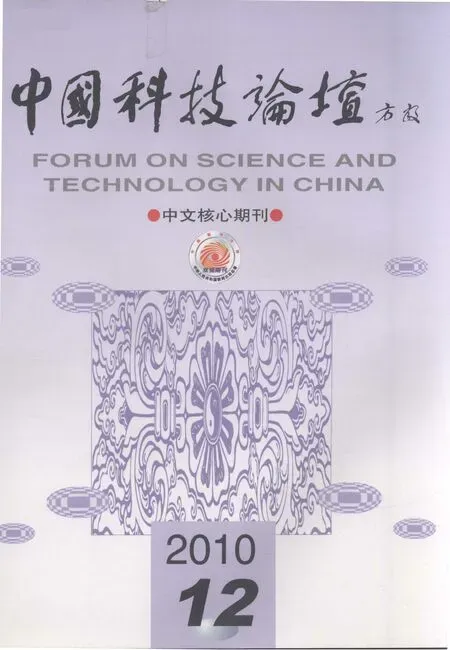知识视角的技术联盟的形成动因研究
徐小三,赵顺龙
(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知识视角的技术联盟的形成动因研究
徐小三,赵顺龙
(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1816)
以回顾战略联盟形成动因相关文献的形式,指出在使用知识视角来分析战略联盟形成动因时,理论界存在着分歧,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技术联盟形成动因问题,并在分析理论界对于技术联盟形成动因三种倾向性解释的基础上,指出技术联盟形成动因是一个三维统一的整体,它包括了知识整合维度、知识获取维度、知识创造维度。
知识视角;技术联盟;动因
Abstract:By reviewing related literatures on formation motivation of strategic alliance,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the use of knowledge perspective to analyze the formation motivation of strategic alliance in theory horizon.Based on this,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formation motivation of technology alliance,and based on three tendentiousness explanations analysis of formation motivation of technology alliance,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formation motivation of technology alliance is a three-dimensional unified whole,which includes the knowledge integration dimension,knowledge acquisition dimension,knowledge creation dimension.
Key words:knowledge perspective;technology alliance;motivation
引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工业组织领域最明显的趋势之一就是独立公司之间合作的增加[1]。与此同时,很多巨型公司都逐渐收缩边界,将一些“非核心”业务外包出去给一些更加专业的公司去做,开始了所谓的“归核化(refocusing)”进程。这也导致公司间需要开展更多的合作,以便参与到更多的业务当中和利用企业自身边界之外的资源。这一进程的开展同时反映在战略联盟飞速发展这一经济现象中。战略联盟的形式有很多种,包括:供需伙伴关系、业务外包协议、技术合作、联合研究项目、新产品开发、联合分销协议、交叉销售协议等等。随着战略联盟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普遍也越来越重要,理论界对于这一实践的研究也越来越热。然而,战略联盟形式的多样性也反映出其目的和动机多样性,有的联盟是出于市场力量或规模经济的考虑而建立的,有的则是为了利用外部企业一些有形资源,如销售渠道等,当然,还有一些战略联盟的建立则是出于知识获取或利用的考虑,如技术转让、技术引进等。总之,由于战略联盟的形式和目的的多样性,对于其形成动因,理论界始终未能找到一种比较全面、合理的解释。
目前,国内外关于技术联盟形成机理的研究总结起来主要集中于资源基础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动态能力理论等视角,主要观点就是技术联盟产生的目的在于获得外部资源、减少交易费用等。虽然这些先前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技术联盟提供了帮助,但是这些观点对于技术联盟形成的一些关键问题显得解释力不够。技术联盟作为战略联盟的一种特殊类型,是组织之间共同致力于技术合作和技术创新的战略联盟。作为战略联盟的一种重要形式,技术联盟具有区别于其他类型战略联盟的一些特征,因为它的目的是致力于技术开发、创新或转移,而技术本身被视为一种特殊形态或类别的知识而存在,所以技术联盟的建立又被视作一种超越组织边界的知识管理活动而存在。从而,关于技术联盟的形成动因采用知识的视角进行分析将更具有针对性、会比传统的一些理论和视角对这一问题的分析更加深刻和透彻。另外,针对于技术联盟形成动因及其维度的分析可以让联盟实践者们认识到技术联盟实践在现实中的不同特征,从而针对不同类型的技术联盟实践采取不同的联盟行为模式,并将其延伸到与企业技术创新密切相关的企业知识管理活动和实践中。在此基础上建议技术联盟实践者在考虑建立技术联盟时,不仅要考虑不同类型技术联盟预期的报酬,而且还要考虑其它一些重要的因素,例如:产品开发和市场占领时效性、长远发展战略和长期竞争能力以及资源投入、研发效率和研发成功率等。
1 理论追溯与文献回顾
公司间组成战略联盟有多种原因,包括规避风险、规模经济、进入新市场和寻求生存的合法性等[2]。很多学者曾用不同理论或从不同视角来阐明或解释公司间组建战略联盟的现象及其原因。然而,因为战略联盟形式和类型的多样性,很难找到一种全面的理论来解释,虽然前人已经开发了很多理论来解释该问题,比如:创造市场力量以产生垄断租金(Katz,1986;Schwartz,1987),资源依附理论(Barley et al.,1992;Van de Ven,1976), 战 略 选 择 理 论 (Hurry,1993;Kogut,1991;Sanchez,1993), 产品的互补性和网络外部性(Rotemberg 和 Saloner,1991)以及交易成本理论 (Oxley,1997;Ring 和 Van De Ven,1992;Williamson,1991),其中以交易成本理论占据主导地位[3]。这些理论,尤其是占据主导地位的交易费用理论已经被证明在理解战略联盟现象时是有用的,但是,资源基础理论认为这些研究都未能在分析中给予伙伴企业的资源足够的关注。资源基础理论认为战略联盟基本上都是企业间资源整合的结果,因此资源基础理论可能帮助我们对于战略联盟现象有更加深入的理解。与交易费用理论只关注于费用的最小化不同,资源基础理论更加强调企业通过整合利用资源达到价值最大化。资源基础理论认为企业有价值的资源通常是稀有的、不易模仿的和缺少直接替代物的(Barney,1991;Peteraf,1993)。因此,资源的积累和交易成了战略性的需要。如果资源交换市场是有效率的,那么企业将继续各自为战,不会想要去结成联盟,因为只要依靠市场就可以得到想要的资源。然而现实是很多资源的市场并不是有效率的市场,如知识和技术交易和转让市场,因为技术一般都嵌入在一些组织惯例和有形的设备中,并且是很难进行定价的。这样看来战略联盟的动因就很明显了,就是为了集中、共享和交换有价值的资源,当这些资源不能够有效地通过市场交换或并购获得时。Kogut(1988)[4]的组织学习模型,也属于广义资源基础理论的范畴,该模型为那些基于企业技术或知识资源而形成的联盟提供了精炼的看法和观点。根据他的观点,建立联盟有两个可能的原因:其一,获取其他企业的知识和诀窍,其二,在保持自身知识和诀窍的前提下从其他组织的资源中获益。将这样的方法延伸一下用于企业所有种类的资源,即企业建立战略联盟或进行兼并收购的目的无外乎两个,一是获取其他企业的资源,二是在保留自身资源的前提下和整合其他企业相关资源的基础上开发自身的资源。公司可能利用联盟或并购来获取其他公司的能够形成竞争优势的有价值和关键的资源。最常见的莫过于跨国公司在试图进入海外市场时大多寻求与当地公司建立联盟或对其进行收购,真正目的在于利用当地公司的资源,如当地的设施、知识和关系等。另外,企业也可能在保留自身资源的前提下与外部企业建立战略联盟,将自身资源与外部企业的互补性资源整合利用,以使自身的资源配置得以优化。较为典型的案例就是20世纪8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将全球范围内多个闲置汽车制造工厂与丰田汽车进行合作的NUMMI项目,这比将这些闲置的资源直接出售带来的经济和战略利益要大得多。
资源基础理论将企业视作具有独特的难以模仿的稀有资源的集合,那些独特的、有价值的资源占有被认为是给企业带来差别的回报或租金,因此,企业资源一般被视作异质的。但这种传统的资源基础视角将企业视作静态的、几乎不随时间变化的资源簇,在外界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核心能力会形成核心刚性。动态能力理论关注于动态因素(创新、组织学习),而不是关注于现有资源的分布。动态能力理论关注企业资源的变化,这种资源的变化对于企业快速应对外界环境条件的变化是必要的,其中一种动态能力理论的观点主要关注于通过组织学习获取新的能力,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形成了一致的观点——组织学习可被视为竞争能力发展最为重要的渠道和媒介。
虽然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都帮助我们解释战略联盟中的组织学习,但是两者对于战略联盟中的一些关键问题的解释都无能为力,因此研究者们转而寻求第三种理论——知识基础的企业理论[5]。来源于资源基础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并在新近发展起来的企业知识理论则认为企业拥有的独特的知识是企业异质性的根本原因,也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该理论将知识看作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源,将组织学习能力视作企业最重要的能力。依据这种观点,企业技术知识和组织学习能力的差异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企业竞争优势和绩效差异的根本原因。因为在传统的经济组织理论中战略联盟是介于市场与等级制度之间的一种资源配置方式,所以很多基于资源基础理论的研究都将战略联盟的形成归因于对一些关键性资源的需求。在知识基础理论中知识被视为是企业最关键的资源(与资源基础理论相一致),知识除了可以以专利和版权等显性的形式存在,也可以融入公司日常运行的惯例,隐性地存在于每个工作人员身上。与资源基础理论不一样(与动态能力理论相一致),这种理论关注企业资源的动态变化,而不仅限于资源的静态差异,这种新的理论对于企业间可以观察到的联盟合作的趋势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因此,理论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寻求通过资源基础理论以及由其延伸出来的知识基础理论为公司间的战略联盟提供更为全面的理论基础。很多学者们都在其研究中提及对战略联盟发展趋势的一个重要的解释因素是其为获取新知识提供了一个平台(Doz 和 Hamel 1991; Inkpen 1995;Ireland et al.2002;Kogut 1988; Khanna et al.1998)[2]。先前已经有很多关于战略联盟的研究识别出知识(包括技术、诀窍和组织能力)的共享是这些联盟建立的主要目的 (Ciborra,1991;Dyer 和 Nobeoka,2000;Inkpen 和Crossan,1995;Kale et al.,2000;Khanna et al.,1998;Larsson et al.,1998; Mody,1993;Mowery et al.,1996,1997;Simonin,1997,1999)[1]。而其中大多数都是采用组织学习和知识获取的观点,即假设建立战略联盟的根本目的在于获取、学习合作伙伴的知识,这个假设的结果导致联盟机制成为 “学习的竞争(competition for learning)”,联盟各方都希望比合作伙伴学习的更快以便于在知识的交易中取得积极的平衡[6],这样也会导致战略联盟的不稳定性。针对这一趋势,Grant和 Fuller(2004)[1]两位学者从知识基础理论的视角提出了关于战略联盟形成动因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企业建立战略联盟的根本动因到底是为了学习和获取外部知识,还是为了整合利用外部知识?他们认为现今广泛流行的强调学习和知识获取的观点并没有认识到联盟作为一种灵活的整合利用专有性知识的组织模式的好处。他们承认任何联盟内部都存在学习过程 (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组织层面)而且有的联盟建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学习和获取知识,比如技术转让协议等,但知识的整合利用才是建立战略联盟的最主要的动因 (即使是在高科技行业:生物制药、半导体、航空、通信和消费电子行业)。过去近30年间部分企业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Quinn(1992)[1]发现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公司战略的新趋势是“归核化”,更加专注于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部分核心的知识和服务技巧,成为真正的聚焦的(focused)公司,而将自己不擅长的部分交给其他更加专业的公司去做,或与他们建立战略联盟。这成了现今知识视角对于战略联盟分析的分歧和问题。被视作一种超越组织边界的知识管理活动,而存在的技术联盟领域是否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呢?
2 技术联盟形成动因的知识视角解释
有关知识基础的文献识别了知识管理两个概念不同的维度,那些增加组织知识储备的活动——March(1991)所谓的 exploration,spender(1992)称为“knowledge generation”,那些整合现有知识来创造价值的活动——March(1991)所谓的exploitation,spender(1992)称为“knowledge application”,在战略联盟中,这种知识管理活动的区别直接影响到联盟内伙伴企业间的知识共享的方式和程度[1]。在前一种情况下,合作伙伴间会发生大量的知识转移和吸收以便创造新的知识,各方的知识基础都会因此而发生一定的变化,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各方只是接触到对方的知识并进行互补性的利用,并没有太多的学习发生,都试图保持自身专有性的知识基础。先前的几项研究都注意到联盟中这两类知识共享方式的区别。 Hamel(1991)[6]指出只是接触到合作伙伴的技能和实际内化合作伙伴的技能之间的关键区别很少被明确划定。Inkpen(1998)[7]也曾指出:“在一些联盟中,合作伙伴积极寻求获取联盟内的知识,而在另一些联盟中合作伙伴对于知识获取则采取更加消极的态度和做法。知识获取与知识整合两者之间的区别对于合作伙伴的知识基础的演化有着重要的影响。
本文认为虽然战略联盟实践的多样性使单一理论无法对其作出全面的解释,但是技术联盟作为一种特殊的战略联盟,被视作一种超越组织边界的知识管理活动而存在,使其在使用知识视角进行解释时可以获得较为全面的解释。针对上文中Grant和Fuller(2004)两位学者从知识基础理论的视角提出了关于战略联盟形成动因的问题,总结前人研究的内容和结论,结合知识管理文献中对知识产生、开发(knowledge generationexploration)和整合、利用(knowledge applicationexploitation)两种知识管理活动的分类,本文认为技术联盟形成的动因分析,从知识的视角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倾向:知识的整合倾向、知识的获取倾向、知识的创造倾向。知识整合倾向认为技术联盟的建立的主要动因在于提高不同知识整合到复杂的产品和服务中的效率,同时提高不同知识的利用效率,但却不改变各自的专业技术知识基础或影响微弱;知识获取倾向认为技术联盟的建立主要动因在于获取对方的知识、学习对方的技术,从企业外部获取有价值的技术知识以充实和丰富企业自身的技术知识基础,从而建立自身的竞争优势;知识创造倾向则认为技术联盟形成的动因在于通过双方的合作创造出单方面无法或很难创造的新的技术知识,使双方都能够从合作中获益,充实各自的技术知识基础。
2.1 技术联盟形成的知识整合倾向解释
技术联盟形成的知识整合倾向解释强调技术联盟的建立使不同企业间技术知识的整合变得更加有效率,同时使各企业专业化的技术知识的利用也更加有效率。这种倾向解释认同并发展了知识分工理论的观点。知识分工理论认为不同企业在专业化分工过程中处于不同的生产环节,不同生产环节的知识积累导致企业间知识的差异。知识分工导致每个企业的知识结构愈加专业化,但是相对于整个生产过程或整个行业来讲,各自的知识就显得愈加贫乏,所以对其它企业的依赖性就愈加增强,各自专业化知识的价值只有参与到社会合作网络的知识整合的过程中才能实现。知识的整合过程既可以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技术联盟的形式来实现,然而就目前而言,技术交易的市场远非完善,很多技术知识很难甚至无法通过市场交易来获得。而技术联盟的建立则使得企业间技术知识的整合变得更加有效率,对于企业个体而言,也使得各自的技术知识利用率得到很大提高,各自专业领域技术知识的价值得以充分实现。这种观点和解释为企业战略 “归核化”趋势的发展和技术外包业务的快速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这种观点并不否认在技术联盟建立和运行的过程中会发生个体层面的学习和技术知识的转移,只是强调知识的整合、利用的效率性才是技术联盟建立的最为主要的动因。
2.2 技术联盟形成的知识获取倾向解释
技术联盟形成的知识获取倾向解释认为技术联盟的建立主要是为了获取对方的知识、学习对方的技术,以建立自身的竞争优势。通过建立技术联盟学习别人的长处,从企业的外部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技术知识。该理论强调技术联盟的建立是双方在技术知识存在差异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对方的知识,或者联盟双方各自将某些领域的专业技术知识进行交换。外部有价值的技术知识通过个体和团队层面组织学习的方式进入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系统,从而增加企业自身的技术知识基础。这种倾向的解释是目前技术联盟文献的主流[1],也是理论界关注、研究最多的。理论研究来源于经济生活中的联盟实践,跨国技术联盟的蓬勃发展为此种解释提供了土壤。东道国企业与跨国企业建立的技术联盟中,东道国企业基本上提供的是一些基础设施,而技术方面则主要依赖于跨国企业的输入,这种情况下东道国企业的主要目的就是学习、获取国际企业的先进技术。虽然在通过技术联盟的方式学习、获取外部知识的过程中也会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学习竞赛和联盟稳定性等问题,但是这种基于获取知识、学习技术目的的解释强调的是:建立技术联盟会对企业技术知识基础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观点可以看作是对知识整合论的发展,联盟企业在技术知识的整合的基础上进一步交流和共享,以组织学习的形式促使各自的技术知识基础得以增长和丰富。
2.3 技术联盟形成的知识创造倾向解释
技术联盟形成的知识创造倾向解释的主要思想来自于日本学者野中郁次郎先生的知识创造理论,只是野中的理论最早关注于企业内部的知识创造,并提出了称为知识创造的螺旋模型。这是一个将知识的存在维度从“个人”上升至“组织”,并在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的螺旋式相互转换过程中不断扩充和增长的模型。组织之间的知识创造过程和组织内部的过程有很多共同点,只是其存在维度跨越了组织的边界,发生于企业与外部组织之间联盟层次中,具体表现为联盟机构内(研发中心、研发团队等)的知识创造过程。技术联盟中的新技术知识的创造宏观上表现为联盟企业合力开发新技术,但是在微观上仍然是通过联盟机构中双方技术人员技术知识的交流、共享,经过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四步骤的相互转换,在知识创造的螺旋中产生的。不过先前关于技术联盟的主流文献一般都只关注于联盟企业间的知识转移和共享,大多忽略了联盟层次和范围内的知识创造的动态过程[8],很少有文献对联盟层次的知识创造活动和过程进行描述和研究,而现实是越来越多的联合研发中心不断建立起来。知识获取倾向解释是从外部学习技术、获取知识并使之参与到企业自身技术知识创造过程中,而知识创造倾向解释比知识获取倾向解释又更进一步,通过整合各自擅长的技术,并在交流学习的基础上在联盟层次和范围内进行技术知识创造活动,从而增加整个联盟和盟内各企业的技术知识基础。
2.4 技术联盟形成动因是三种倾向解释的统一
知识获取的结果是将外部知识与企业内部知识整合,整合之后内化到企业自身的知识基础之中参与知识内的知识创造过程中;知识创造的整个过程本身就始于共同化过程,即个人知识共享、整合的过程。所以说,知识整合是知识获取和知识创造的必要过程,知识获取和知识创造的过程中必然包含着知识整合的过程。技术联盟形成的动因应该是以上三种倾向解释的统一,或者说技术联盟形成的动因存在三个维度:知识整合维度、知识获取维度、知识创造维度,理论界之所以存在三种倾向的解释主要原因在于不同的研究者所观察到的技术联盟实践的特征不同,可能某一技术联盟实践的其中一个或两个维度比较突出而已。而且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技术联盟形成动因知识视角的三种倾向解释反映出联盟内知识管理实践的三个递进的发展阶段。我们还可以借鉴经济学上对于企业行为模式分析方法,将三种解释所描述的不同类型的技术联盟实践对应于三种不同的联盟行为模式即惯例性整合模式、模仿性学习模式、创造性创新模式。虽然经济学分析认为这三种不同的行为模式所对应的报酬是不同的 (选择惯例性整合模式的结果应该是报酬递减的,而模仿性学习模式则导致利润的平均化,只有创造性创新的模式才能获得超过平均的报酬,这部分超额利润就是熊皮特意义上的创新的报酬),但是在现实经济生活中,技术联盟的实践者们却出于各种因素的考虑,选择不同的联盟行为模式和联盟实践形式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有的联盟可能出于产品开发和市场占领时效性的考虑选择惯例性整合模式;有的联盟可能出于长远发展战略和长期竞争能力的考虑选择模仿学习模式;还有一些联盟则可能出于对资源投入、研发效率和研发成功率的综合考虑而选择创造性创新模式。
3 结论
综上所述,前人基于诸多视角的研究对于我们认识技术联盟提供了帮助,但是技术联盟始终是致力于技术的合作和创新的战略联盟,关注的重点始终是技术知识,因此从知识视角来对技术联盟进行研究将更具针对性。虽然理论界对于技术联盟形成的动因存在分歧,存在不同倾向性的解释,但这并不影响我们联系现实的技术联盟实践来从整体上研究探讨这个问题。理论来源于实践,理论上的分歧来自于对于现实观察的角度不同。技术联盟形成动因的三种倾向性解释本来就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同阶段而已。在产品开发或技术创新领域,战略联盟被用来集中、整合各企业不同技术性诀窍和专业性知识,这就是所谓的战略技术联盟。可以看出两位学者所谓的战略技术联盟就已经谈及了整合和创新两个方面,而在给出定义的时候省略了对获取和学习过程的描述而已。
[1] Robert M.Grant,Charles Baden-Fuller.A knowledge accessing theory of strategic alliances [J].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2004,8(3):17-30.
[2] Inkpen A.Knowledge Acquisition and Transfer in Strategic Alliances,in Davis J.,Subrahmanian E.&Westerberg A. (editors),Knowledge Man-agement:Organizational and Technological Dimensions.Physica-Verlag Heidelberg,2005:97-113.
[3] T.K.Das,Bing-Sheng Teng.A resource-based theory of strategic alliances[J].Journal of Management,2000,26(1):31-61.
[4] Kogut B.Joint ventures: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88,(9):319-332.
[5] Wilfred Schoenmakers,Geert Duysters.Learning in strategic technology alliances [J].Technology Analysis& Strategic Management,2006,18(2):245-264.
[6] Hamel G.Competition for competence and inter-partner learning within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alliance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1991,12 (Summer Special Issue):83-103.
[7] Andrew Inkpen.Learning,knowledge acquisition,and strategic alliances [J].European Management Journal.1998,16 (2):223-229.
[8] Xu Jiang,Yuan Li.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the case of alliances[J].Research Policy.2009,38(2):358-368.
(责任编辑 刘传忠)
The Motivation of the Formation of Technology Alliance based on Knowledge Perspective
Xu Xiaosan,Zhao Shunlong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Na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Nanjing 211816,China)
F062.4
A
2010-06-10
赵顺龙(1965-),男,安徽铜陵人,博士,南京工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企业组织理论、战略管理、技术联盟与区域创新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