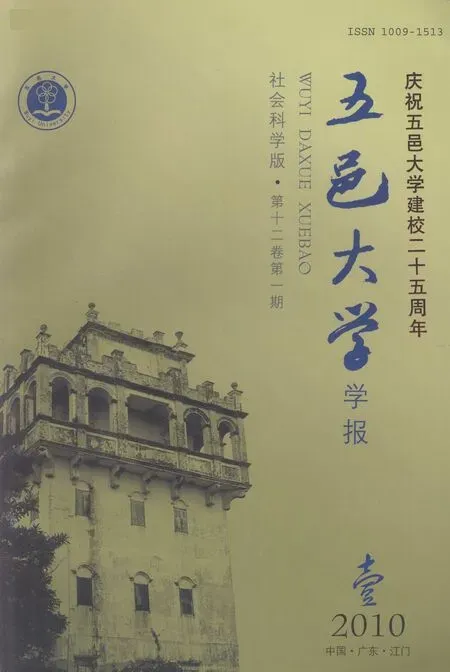疑与不疑之间
——兼谈对待传统文化之立场
郭继民
(海军兵种指挥学院 政工系,广东 广州 510430)
疑与不疑之间
——兼谈对待传统文化之立场
郭继民
(海军兵种指挥学院 政工系,广东 广州 510430)
相比较而言,中国传统文化缺乏怀疑精神,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亦蕴含着怀疑精神,只不过这种怀疑是以更隐蔽和适度的方式出现的。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应采取适中的继承原则,同时,怀疑本身亦值得追问,在信仰、价值等领域要审慎地使用怀疑。
怀疑;传统文化;适度
一
谈及中西教育之差别,世人公认的看法是我国的教育传统历来缺乏怀疑精神,这从《论语》与《理想国》的叙事风格便可看出:《论语》乃圣人对弟子“不容置疑”的教诲;《理想国》则为师徒间平等的探讨、辩论甚至争执,而亚里士多德在追求理性知识时所谓“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之“宣言”更加固此观念。此看法固然有一定道理,然而笔者以为,在评判此观念前更需澄清一种态度,即对“怀疑”所持的立场——是否一定把“怀疑”视为一种价值判断,换言之,是否只有“怀疑”才是有价值的,才是好的。其次,还要追问中国式的“怀疑”之特质,因为缺乏怀疑并非没有怀疑——而解决好中国式怀疑精神将涉及到如何应对经典文化之大问题,故不可不慎。因此,对上述问题需慎重对待之,更需置入具体语境内进行参照和评判。先举两个支持中国缺少“怀疑”精神的例子——
其一是载于《五灯会元·卷四》的一个典故:陆亘大夫问南泉:“古人瓶中养一鹅,鹅渐长大,出瓶不得。如今不得毁瓶,不得损鹅,和尚作么生出得?”泉召大夫,陆应诺,泉曰:“出也。”[1]陆从此开解。
其二是宋代守端禅师的一个偈子:“分明皮上骨团团,封面重重更客观;拈起草鞋都盖了,这僧却被大随瞒。”[2]说的是有学僧看到一乌龟,感到好奇,于是就向大随禅师请教:“众生都是皮裹骨,为何乌龟却是骨裹皮?”大随禅师听后,并不作答,而将自己的草鞋脱下,覆盖在乌龟背上。守端禅师得知大随这一举动,于是有了上面的诗。
陆大夫救鹅,鹅在瓶中仍然没有出来,但当南泉大师猛喝一声,陆大夫幡然醒悟:原来自己被鹅束缚住了,当他从有关“鹅”之“牛角尖”问题中跳出时,难题于是被消解,“鹅”也就出来了。大随禅师则用“遮盖”的方式解决问题,有了问题不是及时解决,而是将其“悬置”、“覆盖”起来,进而避开,使得问题“不复存在”而“解决”。
上述两个例子可归纳为一个问题,就是对“质疑”精神的“遮蔽”和不作为,用当下哲学流行的话语说,就是通过人为的对“质疑”精神的“遮蔽”,进而使质疑精神“退场”。对“问题”意识的遮盖,折射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用冯友兰先生的话来讲,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不去积极地解决问题,而是通过对问题前提的“化解”,使得问题不再能构成“问题”,从而使问题得以“解决”。事实上,西方亦有类似的解决方式,譬如古罗马哲学家马克·奥勒留在《沉思录》中曾说:“丢开你的意见,那么你就丢开了这种抱怨;‘我收到了伤害’,而丢开‘我受到了伤害’的抱怨,这个伤害也就消失了。”[3]此论与中国的“化解论”可谓不谋而合。不过,“化解”问题的前提或取消问题的合法性,需要很高的智慧,儒家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佛家“去执”后的圆融无碍,道家少私寡欲式的“自然心”,即谓如此。
当然,表面看来,上述两例所传递的信息似乎是“作为宗教信仰的佛教是排斥怀疑精神”的。其实不然,相反,佛经大多是“释迦牟尼佛答弟子问”。譬如《圆觉经》乃佛对12弟子的答疑,《楞伽经》则是佛对大慧108个问题的解答。佛学之所以被后人称为圆融之学,很大程度上乃是其能较圆满地解决各种“疑问”。若无诸种疑问,经书亦无存在之必要了。同样,基督教也容忍“怀疑”精神,中世纪哲学之所以沦为神学的婢女,相当程度上与其对大众所允诺的“质疑度”有关。有质疑,才需要哲学去解释;有合理的解释,人们的信仰亦将更踏实。若宗教完全采取“唯信仰”方式,恐怕基督教很难维持,此言“教理”(解释)之重要。自然,宗教中的怀疑与西方知识论立场中的怀疑是截然不同的:宗教中的“答疑”或曰“怀疑允诺”,最终是为了对“信仰”不疑;而知识论之怀疑则是为了“知识的增生”,是伴随人们对宇宙认识的“自然生发”。这里要追问的是,既非宗教亦非惟“知识论”立场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否存在质疑之精神?如果存在,这种质疑精神又当如何表现?
二
欲回答上述问题,首先须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之特质。本质上,中国传统文化乃一种内省的、崇尚践行的伦理(德性)文化,即借助身体去“做”的文化,而非“说”的文化。外在知识非其所好,历来圣贤皆以追求贯通天地永恒之大道为鹄的,而非热衷表层知识之“知”;而且古人对纯粹知识甚至还报有排斥心理,因为外在追求有可能导致人之自性迷失。即便现代大儒亦作如是观,譬如熊十力先生曾言:“知识之败,慕虚名而不务潜修也;品节之败,慕虚荣而不甘枯淡也。”(《十力语要》)其态度很明显:缺乏修养(身体力行)的知识是不足为道的。孔子述而不作,乃由于“天(道)”蕴涵于现实的生活之中,靠个人体悟而达成。是故当其弟子子贡问起“天”时,孔子以“天何言哉!天何言哉!四时运行,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回答之。禅宗有“挑水砍柴,无非妙道”之论,看重的亦是“实干”的“修行”。道家对知识论的立场更加鲜明,老子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知识不但无助于人对道的认识,反而诱惑了“道”,使人远离“大道”,“智慧出,有大伪”(《老子·十八章》)。庄子则提倡“坐忘”,通过忘却外在的“知识”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即谓得道。既然得“道”意味着天人合一的融会状态,它依靠个人行动后的体悟,而非逻辑的论证和反驳,所以古代的大哲是不屑于辩论的。此亦造就中国哲学的格言形式,几乎是清一色的感悟、语录之语,而没有形成西方逻辑架构下的宏大体系。宇宙在斯,万物在斯,“道”亦在斯,靠直观和感悟即可领会大道,而“语言上”的怀疑和辩论不过是庄子所谓的“小知间间”、“小言詹詹”的意气之争。因乎此,古人没有提出“吾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口号。更何况,在以“孝”、“礼”治天下,以“天地君亲师”伦理格局贯而通之的农耕社会里,后生小子对老师更多是尊重、景仰和服从而非辩驳。由是,反叛精神和怀疑精神似乎要“逊色”不少。
如此看来,国人似乎真的缺少怀疑“反叛”意识,但根底上,国人并不缺乏质疑精神(譬如在治学上,孟子、朱子均提倡“疑”的精神,即使孔子亦有“当仁不让于师”之说),只不过这种质疑精神表现得更为隐蔽、含蓄、温和。因为无论怀疑还是反叛,首先要建立在彻底理解“他者”的基础之上,否则别人说一你非得说二,别人说东你偏说西,那是抬杠而不是真正的怀疑。古人对他者的意见,尤其对经典著作首先充满敬畏之心,更抱着践行态度以圣贤书开启心智、完善人格(为求个人私利而读圣贤书者不在此列),那么即使“经典有错”,也只有在长期的践行中“觉知”,而非即刻通过简单的想象推理以求知晓。譬如王阳明对朱熹“格物”的怀疑,就是在“格竹”到七日后仍无所获才开始进行的,并非“看到”格物一语就怀疑之。并且个人的体悟亦不能代替“他人”(经典)的体悟,岂能轻易否定他人?尤其经典,所以历经数百年甚至逾千年流传下来,自有其价值所在。更饶有兴味的是,不少最初对经典持批判怀疑态度者,最终却又回归经典,譬如“五四”中不少“打倒孔家店”的激进精英便是如此。盖真学问乃蕴藏于亲身践行之中,不到一定火候是难得其中三昧的,故笔者将此称为“务实的质疑”;其二,古人对经典的置疑乃采用温和之态度来表现。譬如对经典的注释,仅《易经》而言,就不下于三千家,这事实上表明了古人的质疑态度,若无“质疑”之勇气,一律沿袭古人之义,何有三千家之言?古人注解有“书不破注”的传统,你注你的,我注我的,纵然与他人意见相左,但依然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将之和盘托出,此为“大度”之质疑。其三则是“适度”的质疑。传统的质疑带有不温不火的中庸色彩,并非以极端的方式“一棍子打死”、“推倒重来”,而是以“克服中有保留”、破立结合的适度原则进行,这使得五千年的文化能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避免了其他文明古国古文化烟消云散之命运,也规避了虚无主义的浸染,不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让人们无所适从。
三
古圣哲对经典的怀疑精神可归结为“适度的质疑”。“适度的质疑”意味着“质疑”的限度,自然也意味着一种理性的质疑精神。正如佛教虽允许质疑甚至提倡怀疑(如禅宗),但不能对其“真如”、“自性”产生怀疑;基督教允许对细节质疑,但不可对上帝的存在“质疑”。同样,西人哲学虽极力倡导追问精神,但其“追问”仍有限度,仍应止于“不能追问处”。譬如,康德之“物自体”、黑格尔之绝对精神、柏格森之本质直观、叔本华之生存意志等皆不容“他者”质疑(至少对其哲学体系而言),否则根基动摇,其“理论大厦”也将崩溃。当然,从另一个角度看,对他者哲学之核心无疑又是需要“怀疑精神”的:在黑格尔怀疑精神下,康德的“物自体”消失了;在叔本华的怀疑精神下,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被“埋葬”;在柏格森的怀疑精神下,西方的主、客对立被“解决”。但是,无论哲学怎样转换形式,始终有一个“形上之本体”存在,无论物自体、绝对精神、本质直观还是上帝、生存意志、权力意志(尼采),甚至马克思的实践观都可以近似归结为一个“宇宙的基础”,不同的只是称谓和解释而已。一句话,西方哲学怀疑精神的背后仍然有一个坚固的基础存在,此乃人之生存的理由和根基;否则,怀疑将走向自己的反面,哲学连同其怀疑精神亦将不复存在(后人对他者的质疑大多亦从他者出发,体现了“扬弃”的辨证精神)。退一万步说,即使具有质疑个性的西方文化怀疑历史、怀疑知识、怀疑信仰乃至怀疑一切,然而绝对不怀疑其充满批判力的“怀疑精神”——理性。即使有非理性崛起,而它对理性的批判仍然根基于“理性”。就是说,怀疑是有限度的。
人类作为理性的动物,固然需要怀疑,需要批判。然而,在人们享受由“怀疑”带来的所谓“进步”时,更需要反思:哪些是需要怀疑的?哪些又是必须固守的?这里笔者要探讨的是,在当今科技一统天下的时代,在西方文化铺天盖地抢占全球领域之时,中华民族的经典文化是否还有固守的必要?是否也要用一种强制性的怀疑将之搁置于历史的博物馆中?亦或以“西化”取而代之?
窃以为,民族文化之精华仍需固守。在马克思预言的共产主义未到来之前,民族文化、民族精神乃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根基。尽管当下盛言“经济全球化”、“地球村”、“文化村”,然而在“全球一体化”的背后隐藏着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消解、控制和“覆盖”,因此愈是“全球化”,愈需树立民族文化之自信,愈需固守民族之根基而不能盲目抛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近代以来一向以含蓄著称的国人在西方强势文化进攻下,却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全面“质疑”,其中五四尤甚。
众所周知,一个民族存在之标志乃是其文化,而文化之核心则为其语言文字。然而,在100年到80年前,当西方势力强烈质疑中国文化并将其列入应淘汰之列时,当中华民族面临亡国亡种亡文的紧要关头时,部分国人却先于西人进行中华文化的“自我彻底质疑”和清算:“他们没等外国人来亡我们的文化,便自己开始阉割;没等外国人来灭我们的史,就自己开始谩骂;没等外国人来除我们的圣人,就自己动手来推翻。”[4]当时文化界、知识界竟然对母语进行彻底否定:瞿秋白认为“汉字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茅坑,中国的汉字已经是十恶不赦的混蛋的野蛮的文字了”;鲁迅认为“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倘不首先除去它,结果只有自己死”;钱玄同则认为“欲废孔学,不可不先废汉文”。诸多言论,今日读来,简直不可思议。孟子云:“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5]信夫此言!
难怪佛学会长王志远发出如是感叹:“我们站在今天来看,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危亡的时候,救国,在文化方面怎么竟有这番高见?……我看到这些文字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4]尽管当时部分“五四激先锋”的出发点是为国家民族利益,在当时背景下亦不得已而采取此矫枉过正之手段。然而这种对民族“本根的质疑”乃属“质疑过度”,其消极作用显而易见——因为在一个极端的时代,它极有可能将民族文化置于死地。当孕育民族精神的“文化”被抛弃,即使有国、有种,但处处以他族文化为“模本”,这样的“存在”又有何意义?五四之后,国人尤其大陆对传统文化又进行过若干次“清算”,几乎将传统文化置于死地。
反观西方,尽管其骨髓里流淌着怀疑主义,然而对待经典的态度,却是旗帜鲜明的“传承”。譬如美国大学本科阶段,不分文理,古希腊、文艺复兴之经典著作均为必修内容。哈佛大学尤其重视传统,其校训即为明证:“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与真理为友。”[6]哈佛重视传统,相信传统中有深远的智慧,所以哈佛不可能出现全盘反传统、全盘反历史的疯狂现象。而我国的高等院校除了政治思想品德课外,传统文化教育几乎丧失殆尽。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客观地讲,即使对于古代经典文化可以质疑,亦可以批判甚至“彻底放弃”,但问题是在放弃之前,得先拿出一套比经典(如《论语》《老子》《中庸》)更好的东西。如果拿不出来,那么最老实的态度还是回到经典,倾听并体悟智者的声音,并藉此为根基去传承、感悟、发展、创造。
四
再回到“怀疑”的立场,这种怀疑的立场是对“怀疑本身”的反思和追问。人们为什么要质疑?怀疑的目的何在?——为进步而怀疑?为凸显自我而怀疑?亦或为民众利益而怀疑?如果将怀疑、质疑仅仅当作一种时尚,一种流行话语,甚至将“怀疑”蜕变为一种文字游戏、一种口号,那么,“真正的怀疑精神”——适度的、客观的精神——距离寿终正寝之日便不会太远了。如果将怀疑理解为一种适度、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和负责态度,那么“怀疑”才是真正应当追求和拥有的品质。
在当今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凸显的时代,在“创新压倒一切”的消费时代,一切(无论信仰还是知识)似乎都建基于怀疑之上:只有怀疑才能创新,才能解放自我,才能获得自由,一句话,怀疑似乎成了社会进步的“动力源”。然而这种“不假思索”、“不分领域”的武断怀疑亦将导致严重的后果,譬如在信仰领域的怀疑将导致“虚无主义”的产生。上世纪末崛起于西方的激进“后现代主义”破釜沉舟,用解构手术刀怀疑、反叛一切,价值、意义、德性、本体……乃至人们生存的理由,一切的一切都不存在了。由怀疑导致的“虚无”已对人们的生存构成威胁,造成信仰真空和精神危机。实际上,生活在17世纪的西方人,已遭受过由“上帝退场”所造成的人们精神上无家可归的焦虑与孤独,帕斯卡针对失去上帝监护的、所谓“理性人”的精神状态做过如次描述:“我们是驾驶在辽阔无垠的区域里,永远在不定地漂流着,从一头推向另一头。……我们燃烧着想要寻求一块坚固的基地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的愿望,以期在这上面建立起一座升到无穷的高塔;但是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7]33谁能保证盛行于当下的技术理性、实用主义、全球化不会把人们从一个“深渊”引向另一个“深渊”?
其实,这种充满质疑精神的现代性“背谬”亦在我国上演。“现代性”在中国的兴起解决了人们基本生存的问题,但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质疑和摈弃,却击碎了人们共同的精神家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譬如良知、诚信,譬如淳朴、节俭,譬如宽容、大度,譬如同情、谦虚……三鹿奶粉、黑砖窑、红心鸡蛋等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日益促逼着人们的道德底线。人固然需要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问题,但人绝不能仅仅满足于肉体的物质性存在,更需要有道德、价值、信仰等精神诉求。“仓廪实而知礼节”,但人并非只有到仓廪实之时才需要礼节。遗憾的是,尽管我们一再强调“精神文明、物质文明两手抓”,但“精神文明”却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我们已为“经济人”的获得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更吊诡的是,持续不断的“怀疑”往往让人类又回到“原点”。以文艺复兴后为例,西人似乎在“之”字形道路上往复:先用怀疑精神对世界进行了“祛魅”,如今又着手“复魅”;文艺复兴时期反抗专制、追求自由,工业化时代又“逃避自由”;工业时代鼓吹“征服自然”,后工业时代又倡导“回归自然”……这种“推倒,重建;再推倒,再重建”的游戏似乎构成了人类走不出的怪圈。两千多年前老子曾有“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之感叹,难道人类社会的进展真的是一个闭合的圆?
亦因乎此,对于怀疑,应该保持一种警醒的认识:谁能保证当下质疑、反对的东西不会复苏?人类历史时常会上演“惊人相似的一幕”。也许,对于怀疑,须借鉴康德的划界思路:在知识(科技)领域,要高扬怀疑之精神,发扬“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之务实作风;在(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触及生存意义、价值之领域,则应始终保持一种敬畏、审慎之态度,万不可轻易否定。因为人们须臾难离其精神依托和价值坐标:“一定要有一个定点,才好做出判断。港岸可以判断坐在船里的人;可是我们在道德方面以哪里为岸呢?”[7]170-171这也许是“适度的怀疑”的另一含义。
如何在疑与不疑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保持一种“适度”,确实需要一种智慧。而这种智慧的习得,既需要不断追溯历史、回归经典并汲取古老的智慧,更需要从现实出发,时刻保持实事求是的真诚态度。惟其如此,怀疑才不至于被误用,怀疑精神才可能真正为人类进步提供强大的动力。
[1]陈启福.儒、释、道名言经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412.
[2]明空.禅的故事[M].北京:新世纪出版社,2004: 364-365.
[3]马克·奥勒留.沉思录[M].何怀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23.
[4]王志远.呼唤东方文化鱼肚白的前夜[EB/OL]. (2008-09-15)[2009-08-25].http://www-china2551-o rg.htm.
[5]朱熹四书·孟子[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4:255.
[6]杨立军.从十大名校看美国式精英教育[M].北京:学林出版社,2007:92.
[7]帕斯卡.思想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6.
Between Dubiety and Belief——On the Treatment of Classic Culture
Guo Ji-m in
(Political Work Department,The PLA Navy A rms Command Academy,Guangzhou 510430,China)
Comparatively speaking,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lacks the spirit of doubting.In fact,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s not in short of the spiritof doubting w hich exists in amo re hidden and moderate way.Moderation should be the p rincip le in treating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Meanw hile,doubting also needs questioning and should be cautiously app lied in the field of beliefs and values.
doubt;traditional culture;moderation
G122
A
1009-1513(2010)01-0038-05
[责任编辑朱 涛]
2009-09-02
郭继民(1972-),男,山东郓城人,博士,讲师,主要从事中西哲学文化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