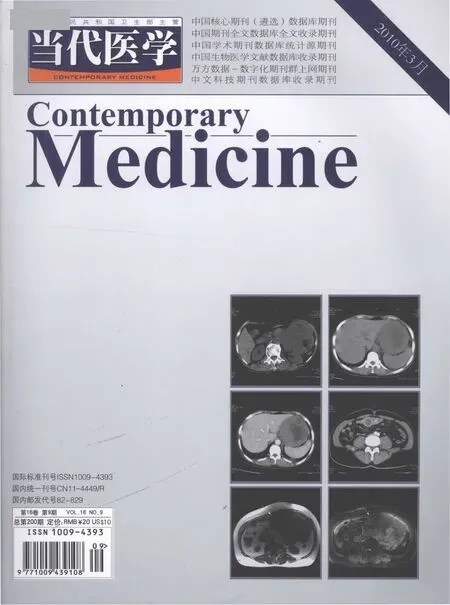脑微出血的MRI检查和临床应用进展
陈峰 陆建明
对于脑血管疾病患者产生临床症状之前,只能从相关的检查中获取信息,目前常用的检查方法有眼底检查、脑阻抗血流图、经颅骨超声彩色多普勒断层法、数字减影血管造影术、CT和CT血管成像、磁共振成像和磁共振动脉造影。这些检查方法共同的不足之处在于,它们都只能发现较大血管的病变,而不能检出微小血管病变。随着影像学技术的发展,到上世纪90年磁共振T*2加权梯度回波成像(gradient-echo m agnetic resonance im aging,GRE-MRI)技术的应用,使作为脑内微血管病变标志的脑内微出血(intracerebralm icrobleeds,CMBs)才逐渐被人们重视。CMBs一般定义为在GE序列上的表现为均匀一致直径2~5mm的卵圆形信号减低区,周围无水肿。CMBs是由于基底节区或皮层下微血管的破裂,大多数无临床症状,在GRE序列上信号丢失考虑是由于含铁血黄素沉积造成的,血细胞的分解产物导致局部磁场不均匀导致信号丢失。当排除了血管间隙、软脑膜的含铁血黄素沉积或者不伴有出血的皮层下的钙化灶,即可确认为CMBs病灶。CMBs的好发部位主要为皮层、皮层下白质、丘脑、基底节、脑干和小脑等部位。
1 危险因素和发病机制
高血压、脑淀粉样变性(cerebral am y loid angiopathy,CAA)、CADASIL(伴有皮质下梗死和白质脑病的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脑动脉病cerebral autosomal dom inant arteriopathy with subcortical infarcts and leukoencephalopathy)、既往缺血性卒中等造成的脑微血管病变是CMBs形成的主要原因。
1.1 高血压
ICH(intracerebral hem orrhage,脑出血)和腔隙性脑梗死是脑小动脉病变的结果,而CMBs最常见于ICH和腔隙性脑梗死患者,其数量与ICH的数量或腔隙性脑梗死的数量以及白质缺血性改变的数量呈正比,CMBs病理学检查具有中度-重度纤维玻璃样变性[1],提示CMBs与脑小动脉病密切相关。引起ICH的小动脉脂质玻璃样变和微动脉瘤的最重要的原因是高血压。高血压病患者脑小血管的管壁薄弱,尤其是平滑肌被纤维组织取代或被坏死组织取代,则可发生血管破裂,此前可以有或没有动脉瘤的形成[2]。左心室肥大通常作为高血压靶器官损伤的标志[3]。超声心动图提示,左心室肥大的患者(含缺血性卒中72例和出血性卒中30例)中,基底核、丘脑或幕下CMB伴随更严重的左心室肥大。多因素分析表明,CMB的数量与左心室肥厚和既往卒中史有关。左心室质量指数程度(mass index grade)是中枢灰质核团和幕下非皮质下白质CMB严重程度的独立危险因素[4]。近期我国研究也提示脑微出血与高血压病史相关[5]。
1.2 脑淀粉样变性
CAA是70岁以上老年人原发性脑叶出血的主要原因。脑淀粉样血管病(CAA)是淀粉样物在血管壁的沉积,随着CAA的进展,淀粉沉积的血管壁发生结构性改变,如各层之间裂缝,微动脉瘤形成和纤维素样坏死[6]。CMBs常见于散发性(16%~38%)或遗传性(69%)CAA[7]。Lee等[2]报道了晚期高血压和CAA可导致CMBs在不同区域分布,前者CMBs好发于颞枕叶,后者则为顶叶,而且CAA相关的CMBs几乎无例外地发生在皮质和皮质下白质,罕见累及深部灰质核团、胼胝体、小脑或脑干,而高血压CMBs的最常见定位是基底神经节、丘脑、小脑或脑桥。这些发现有可能对早期伴有孤立性皮质-皮质下CMBs的CAA患者提供鉴别诊断的依据。具有脑叶出血病史的患者,多次脑叶出血则提示这种出血可能为CAA,但其中一些仍可能属于高血压性微血管病变。皮质-皮质下的低密度灶可能代表高血压性微血管病CMBs,也可能是CAA的CMBs,或两种血管病同时存在。所以依据CMBs的分布部位来判断血管病变的类型并不可取。CAA可能是CMB的独立危险因素。CAA患者中CMBs的高发率与疾病进展、复发ICH和CAA相关损害有关。组织病理学证实,在高血压微血管病变合并淀粉样脑血管病变的患者中,CMB分布得更加广泛CAA与ApoE4和ApoE 2等位基因有关,但CMB与ApoE的关系尚未得到证实。
1.3 CADASIL
CADASIL是一种由19号染色体Notch3基因突变导致的显性遗传性的小血管病变,以小动脉病变为主,典型的临床表现为反复的脑缺血发作或脑梗死、认知障碍、有先兆的偏头痛以及精神异常,偶有ICH个案报道,提示受累的动脉并非具有出血倾向。但是Oberstein等[7]用GE-T 2W-MR研究了63例CADACIL病及其家庭成员,发现31%症状性CADASIL Notch受体携带者具有CM Bs,相对于其他类型的脑小血管疾病,CADASIL发病较早(多在40~60岁)。研究发现,25%的Notch受体携带者存在CM B,有症状的Notch受体携带者CM B,达31%。有些研究中,CADASIL者CMB发生率可高达69%,且多呈多病灶。Choi等[4]研究发现,有症状的CADASIL患者25%有ICH,其发生与CMBs的数量密切相关。
1.4 抗血小板聚集或抗凝治疗
有研究认为,抗血栓药主要是抗血小板凝集药物的应用组CMB发生率高,抗血小板凝集药物的使用与CMB的出现显著相关。Fan等[8]研究了121例年龄为(67.96±10.97)岁的急性脑梗死患者,发现CMB与缺血性卒中的进展无显著关联,但在继发出血的脑梗死患者中,绝大多数曾使用过阿司匹林和抗凝药,早期应用抗凝药与CMB的发生显著相关。服用阿司匹林的ICH患者比服用阿司匹林无ICH者更常见到CMB,提示服用阿司匹林若合并微出血则是患者发生ICH的危险因素。但是抗血小板聚集治疗的出血风险可能很低,故对合并CMBs的血栓性疾病患者二级预防时应评估治疗风险。
1.5 其他
CMBs与其他脑微血管病形态学改变显著相关,例如腔隙和广泛脑室周围及深部白质缺血性高密度损害。研究发现,无论是出血性还是缺血性卒中,初发还是复发性卒中,CMBs的发生率都与白质缺血程度密切相关[8]。
2 影像学表现
ICH后,血肿信号的强度随血红蛋白演变的时间而改变。出血急性期(含氧或去氧血红蛋白)T 1W像上呈低信号或等信号,而亚急性血肿呈高信号;慢性期血肿由于含铁血黄素的沉积,在所有序列上均呈低信号;陈旧性出血,含铁血黄素存留在巨噬细胞内,它的磁性导致T2W像质子旋转发生快速相移,造成MR局部信号丢失,从而使得陈旧出血灶在T 2W像上呈现为周边无水肿带的局灶性低密度影。
CT及自旋回波T 2W对少量含铁血黄素不敏感,而GRET 2W-MR序列对磁化率的差别高度敏感,很容易发现这种病变。单摄梯度回波T 2W可以在2s内获得全脑资料[9],只要存在CMBs,就能够查出。但需要注意将CMBs与导致GRE信号缺失的其他原因相鉴别,如局部钙化、小血管畸形、海绵状血管瘤、剪切性损伤也可引起GRE-T2W-MR局灶性低信号改变。基底节区的钙或铁沉积也可有与CM Bs类似的影像学表现,但往往呈对称性分布,CT上可见高密度影。海绵状血管瘤与CMBs难以区分,但其常出现癫痫和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症状且发病年龄较轻,大多可在常规T1W、T2W上发现病灶。如横断面上的小血管流空影常与CMBs难以鉴别,但可通过多层扫描显示血管走行来加以区分。此外,MBs还应与继发于脑挫裂伤、外伤性弥漫性轴索损伤的斑点状病变、毛细血管扩张症相鉴别。由此可见,对于GRE-T2W-MR信号缺失的原因,应根据病史、病变的位置、数目、分布以及相应的影像学表现做出综合判断。
在不同病因的患者中,CMBs的分布可能有所不同。在脑出血患者中,CMBs多位于丘脑,其次为基底节区、皮层一皮层下区域和幕下区域。在缺血性卒中CMBs分布依次为皮质下白质丘脑、基底节、脑干、小脑。而在CAA患者中,可能多数位于皮层-皮层下区域。CADASIL患者中,CMBs的平均直径小于5mm,但最大直径达10mm,多数在丘脑、皮层及皮层下白质也有分布[10-11]。
平面回波成像(echo p lanar im aging,EPI)也是一种较常用的序列,是在梯度回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以读出方向连续施加梯度场的方法来产生多个梯度回波,可以在一次激发后得到所有的空间信息,是目前最快的MRI成像方法,特别适用于不合作、烦躁、小儿以及幽闭恐惧症患者。此外,由于EPI技术采用一组梯度回波,故对磁敏感效应具有较高的敏感性。研究显示,CMBs在GRE-T 2W-MR序列上显示良好,而SE T 1W I、FSE T2W I、DW I序列均未能显示,与N ighoghossian等[12]的研究结果基本相符。虽然EPI对显示出血敏感,但在研究中采用EPI检出的MBs数目较GRE-T2W-MR无明显差异且图像信噪比欠佳,说明GRE-T2W-MR仍是检测CMBs的首选方法,EPI可作为GRE-T2W-MR的补充手段,将MRI的GRE序列和SW I序列相结合,将会使CMBs的诊断更准确[13]。
3 脑内微出血的临床意义
CMBs的发现具有重要的诊断意义。
3.1 CMBs是血管壁疾病的标志
CMBs是血管壁疾病的标志,发生ICH的危险性较高,卒中治疗时应加以考虑。MRI对脱氧血红蛋白感,可评估ICH的不同分期,而CT仅能检出急性亚急性出血。溶栓治疗前,MRI检查有无CMBs很重要的价值。研究发现,有CMBs的急性脑梗死患者在采用溶栓治疗或抗凝治疗时发生出血转化的概率明显高于无CMBs的患者。治疗前GRE-T 2W-MR序列上发现少量CMBs的缺血性脑卒中患者仍可安全地接受溶栓治疗,而多发的CMBs则可能是弥漫性出血倾向的表现。因此有学者提出,对准备实施溶栓、抗凝治疗的患者应预先进行GRE-T2W-MR检测。既往CT确诊有脑出血病史者,是溶栓禁忌证,但对于GRE-T 2W-MR发现CMBs的患者是否可行溶栓治疗尚无相应指南,提前发现有可能导致溶栓后出血转化的因素,将有助于溶栓病例的筛选,从而最大程度减少合并症的发生。
3.2 CMBs是一种易于出血的脑微血管病
CMBs是一种易于出血的脑微血管病,预示将来可发生出血性卒中。ICH患者常有脑白质缺血和底节区腔隙灶,说明微血管病变既可造成出血性脑损害,也可造成缺血性脑损害。脑微血管病变使血管壁变得脆弱,从而导致出血,如果血管没有破裂,则可能发生节段性血管闭塞,从而导致腔隙性梗死。因此,有人提出,CMBs与ICH或脑梗死有着共同的病理学基础,CMBs也可预测再发性ICH、抗凝后ICH或抗血小板治疗预防缺血性卒中出现的ICH等并发症。
3.3 脑淀粉样变性
随着CAA的进展,淀粉沉积的血管壁发生结构性改变,如各层之间裂缝、微动脉瘤形成和纤维素样坏死。微动脉瘤周围的脑组织中可见小出血,含有含铁血黄素的巨噬细胞和胶质细胞,梯度回波-快速平面成像(GRE-EPI)所见的低信号能够发现通过动脉壁漏出的血液残留物,多发CMBs的存在提示微血管病已很严重,受累血管易于出血。因此,CAA患者的CMBs可作为判断疾病进展的一个指征,CM Bs的检出有助于评价CAA病程进展情况。
3.4 CADASIL患者年龄依赖性的CMB增多
CADASIL患者可见年龄依赖性的CMB增多,提示出血危险性很高,如果对这些患者进行抗凝或抗血小板治疗则需高度警惕脑出血的发生。
3.5 与脑血管疾病患者的认知功能损害有关
CMBs数目的增多,证明新的受累小血管增多。研究证明,CMBs并不是完全无症状的,CMBs数目和患者认知缺陷和功能障碍存在一定相关性,随着CMBs数目的增加,患者认知缺陷和机能障碍逐渐加重。W erring等[14]研究认为,患者认知缺陷和机能障碍可能与额叶和基底节区组织损害有关,CMBs破坏了额叶皮层下的联络纤维。这个发现对于诊断伴有认知缺陷和功能障碍卒中患者有提示作用。对脑卒中患者应常规行GER-T2W I检查以检测CMBs,从而为临床评价有无进行性出血倾向的微血管病变及其严重程度提供信息,对于减少出血性脑卒中、血管性痴呆的发生,对于适当应用抗高血压治疗和抗血小板治疗改进卒中患者治方案以及判断预后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4 总结
CMBs是随着新的影像学技术的广泛使用而逐渐被人们认识的一种微小血管病变。现有的临床研究已证实,脑微出血与卒中,特别是与出血性卒中有密切关系,对缺血性卒中患者出血性转化具有预测意义[15]。CMBs更常见于再发血管事件,可能因为它们反映了更严重的小血管病。大量皮质下CMBs可预测再发ICH和腔隙性梗死。CMBs也可能是导致认知障碍的潜在血管病变(如CAA或高血压性小血管病)的生物学标志[16]。特别对高血压、脑小血管病、CAA和需要抗凝血治疗的患者而言,CMBs影像学证据比其他临床或形态学改变更有助于对出血并发症高危患者的鉴别,成为ICH危险分层潜在的重要依据。因此CMBs对脑卒中患者治疗方法的选择和预后的判断有着重要意义。
[1]Wardlaw JM,Lewis SC,Keir SL,et al.Cerebralmicrobleeds are associated with lacunar stroke defined clinically and radiologically,independently of white matter lesions[J].Stroke,2006,37(10):2633-2636.
[2]Lee SH,Kmi BJ,Roh JK.Silentmicrobleeds are associated with volume of primary intracerebral hemorrhage[J].Neurology,2006,66(3):430-432.
[3]Dufouil C,Chalmers J,Coskun O,et al.Effectsof blood pressure lowering on cerebralwhitematterhyperintensities in patients with stroke:the PROGRESS(perindopril protection against recurrent stroke study)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substudy[J].Circulation,2005,112(11):1644-1650.
[4]Choi JC,Kang SY,Kang JH,et al.Intracerebralhemorrhages in CADASIL[J].Neurology,2006,67(11):2042-2044.
[5]杜雅星,黄鉴政.脑微出血与脑卒中[J].中华神经医学杂志,2005,4(12):1245-1248。
[6]Werring DJ,FrazerDW,CowardLJ,et al.Cognitive dysfunction patientswith cerebral microbleeds on T2*-weighted gradient-echo MRI[J].Brain,2004,127(10):2265-2275.
[7]Lesnik Oberstein SA,van den Boom R,van Buchem MA,et al.Cerebral microbleeds in CADASIL[J].Neurology,2001,57(6):1066-1070.
[8]Fan YH,Mok VC,Lam WW,et al.Cerebralmicrobleeds and white matter changes in patients hospitalized with lacunar infarcts[J].Neuro,2004,251(5):537-541.
[9]Roob G,Fazekas F.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of cerebral microbleeds[J].Curr Opin Neurol,2000,13:69-73.
[10]Blitstein MK,Tung GA..MRI of Cerebral Microhemorrhages[J].AJR,2007,189(3):720-725
[11]Alemany M,Stenborg A,Terent A,et al.Coex istence of microhemorrhages and acute spontaneous brain hemorrhage:correlation with signs of microangiopathy and clinical data[J].Radiology,2006,238(1):240-247.
[12]Nighoghossian N,Hermier M,Adeleine P,et al.Old microbleed are a potential risk factor for cerebral bleeding after ischemic stroke:a gradientecho T2*-weighted brain MRI study[J].Stroke,2002,33(3):735-742.
[13]张金彪,王晶,张勇.脑微出血的临床及影像学特征分析[J].中国脑血管病杂志,2008,5(4):163-164.
[14]Werring DJ,Frazer DW,Coward LJ,et al.Cognitive dysfunction inpatientswith cerebral microbleeds on T2*-weighted gradient-echo MRI[J].Brain,2004,127(10):2265-2275.
[15]Dichgans M,Holtmannsp tter M,Herzog J,et al.Cerebral microbleeds in CADASIL:a gradient-echo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 and autopsy study[J].Stroke,2002,33(1):67-71.
[16]Viswanathan A,Chabriat H.Cerebral microhemorrhage[J].Stroke,2006,37(2):550-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