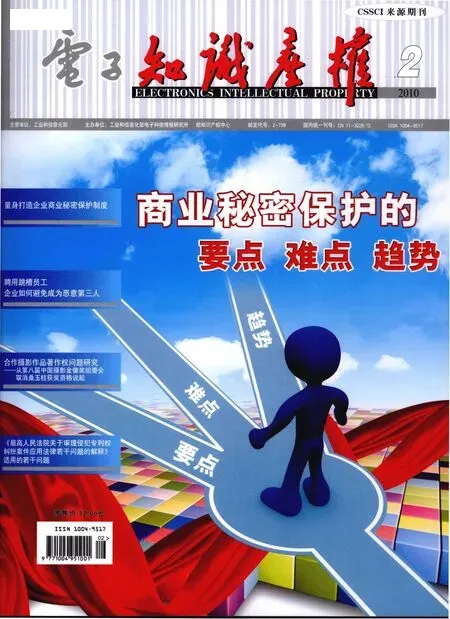我国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定位与规制探讨
崔立红/文
我国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定位与规制探讨
崔立红/文
我国学术界对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法定化存在两种完全相反的意见,但司法活动在遵循现有共同侵权立法的规定前提下,偶有突破。从平衡知识产权人、技术提供者、社会公众利益出发,应将民事《侵权责任法》作为上位法,在知识产权法中对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作补充和例外规定。在坚持间接侵权的共同侵权性质、承担连带责任的前提下,对其认定应把握更严格的条件。
知识产权 间接侵权 共同侵权 连带责任
一、我国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理论与实践现状
从当前我国学术界的研究情况看,尽管赞成建立间接侵权制度的观点居多,但仍有反对的声音出现,并且一直得到立法和司法实践的支持。而我国立法和司法在知识产权间接侵权上的实践呈现基本一致的态势。
目前我国 《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没有间接侵权的明确规定,民事基本法在侵权规范中也未启用“间接侵权”这一专门术语,实践中一直是通过一般民事法律中的共同侵权理论来处理此类侵权行为。司法方面则从1993年至今审理了多起间接侵犯知识产权纠纷的案件,判定应当承担共同侵权的责任。但也有少量案例在缺乏直接侵权构成要件的情况下,法院仍旧认定构成间接侵权。1.如广东省高级法院(2006)粤高法民三终字第355号北京慈文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诉数联公司案。
二、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定性——视为共同侵权
(一)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行为类型
什么是间接侵权?在此定义上一直存有争议。比较多的学者援用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01年通过的 《专利侵权判定若干问题的意见 (试行)》中“间接侵权”的定义:行为人实施的行为并不构成直接侵犯他人专利,但却故意诱导、怂恿、教唆别人实施他人专利,发生直接的侵权行为。另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定义所涵盖的间接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范围更为广泛:没有实施受知识产权“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即没有实施知识产权的“直接侵权”),但故意引诱他人实施“直接侵权”,或在明知或应知他人即将或正在实施“直接侵权”时为其提供实质性帮助,以及在特定情况下为“直接侵权”准备和扩大其侵权后果的行为[1]。
国际社会上对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定义中,有代表性的、也有我国学者及实践者援引作为“间接侵权”渊源的是美国1952年 《专利法》第271条(b):任何积极引诱和教唆他人侵害专利权的人负有专利侵权的法律责任。同样,在版权领域,在SONY案和NAPSTER案之后,在GROKSTER案中不论是否有实质性帮助,只要有怂恿、劝说第三人利用其提供的工具或装置从事侵权行为,都要承担侵权责任。韩国在判例中也明确了版权帮助侵权的判断标准:侵权行为人不仅要知道或有理由知道侵权行为的存在,而且实质上对他人侵权行为提供了帮助。
综上所述,间接侵犯知识产权并承担责任的行为,集中在教唆、诱导、怂恿、帮助以及其他提供实质性帮助的行为上,主观上多为故意。因此,将“间接侵权”称为“帮助侵权”更为合适,而国外及我国司法实践中也多使用该术语。
(二)知识产权间接侵权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从间接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表征上看,帮助侵权行为与直接侵权行为之间对造成权利人的损害后果有关联,但在传统共同侵权理论框架下,这种有关联的共同行为会因为缺乏主观意思上的关联,即没有共同故意或共同过失,而不能被认定为共同侵权。原因在于知识产权直接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的是严格责任,即使帮助侵权人具备侵权故意,与直接侵权人之间达成意思联络也很难实现。哈耶克曾经担心现有知识的控制容易扼杀促使新知识出现的机会[2]。但共同侵权理论的发展证明了哈耶克的担心是多余的,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已经发展到 “客观说”——共同侵权人之间只要有共同的侵权行为或者侵权行为之间存在有关联性,即从行为本身考察,就可以承担连带责任[3-4]。当前,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广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包括:狭义的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加害行为)、“视为”共同侵权行为(教唆和帮助者)、“准”共同侵权行为(共同危险行为)[5]。大陆学者梁慧星先生、王利明先生、杨立新先生在《侵权责任法》建议稿中对教唆和帮助侵权者的地位界定与王泽鉴先生的观点几乎一致。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专利侵权(infringement)本质上是一种侵权行为(tort),所以其专利法体系有一套关于共同侵权责任的补充性原则。美国在早期的判例Thomson-Houston Elec.Co.v Ohio Brass.Co.中清楚地阐述:专利侵权是类似侵权行为的侵害或间接侵害诉讼。从早期开始,所有参与侵害的人,或者是实际上直接参与,或者是教唆侵害,都被认定为是对造成的损害负有连带责任。这项健全的规则如果不适用于对专利权的损害,那么,美国宪法和法律所包含的对发明者的保护就成了一个蹩脚的谎言[6]。与英美法系国家不同的是,大陆法系国家因为在《民法典》中有对侵权责任的一般性规定,相当成熟和完备的民事侵权行为法中有关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则,所以认为间接侵权只是这些规则在知识产权法领域的具体适用。
可见,目前国内外的立法、司法和学术实践中,知识产权间接侵权都是在共同侵权(帮助侵权)的框架下解决,它是民事侵权行为的一种,因此民事侵权行为的一般规定可以适用于其上。
三、建立我国利益平衡的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立法体系
间接侵权,本质上仍旧是侵权行为。我们应该将该问题纳入到一般侵权立法,尤其是共同侵权立法的框架中,针对专利、版权、商标等知识产权的特点,在相关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中对共同侵权原则的适用做补充,即以《侵权责任法》为上位法,同时《专利法》、《著作权法》、《商标法》对间接侵犯知识产权的共同侵权行为进行一些限制和例外规定。
(一)对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的认定应该从立法和司法上把握更严格的“度”
这是正确把握知识产权人、科学技术发展、社会公众(消费者)三者之间平衡的必然结果。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的发展历程来看,新技术的出现和突破都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权利人遭受侵权损害的风险,但发达国家已有的实践证明,新技术的出现不是知识产权人的“末日”。最好的例子是美国1984年SONY案,虽然版权人在法院败诉,但是从该案发生至今,美国的电影市场非但没有出现版权人悲观以及收入滑坡的现象,年均票房收入反而从1984年的40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96亿美元,增长160%。因此,当域名出现导致与商标、商号等发生冲突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并没有急于将域名纳入知识产权范围,也没有将域名与商标等的冲突统统划归到侵权之列,这种态度值得赞赏。对于立法者和司法者来说,面对新技术的时候,也不必一味认定侵权或视为合法,正确的态度是在尽力不打破知识产权法长期以来在保障权利人利益、推动技术创新、推广和传播信息之间形成的平衡前提下,做出审慎、科学的研究和选择。我国2009年12月26日发布、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侵权责任法》规定:二人以上共同实施侵权行为,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8条);教唆、帮助他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应当承担连带责任(第9条);共同侵权中连带责任首先按照责任大小承担,不能区分责任大小的,平均承担(第10~14条)。作为上位法,《侵权责任法》中的上述规定可以适用于知识产权间接侵权。
(二)知识产权法律中对间接侵权的补充规定——间接侵权共同责任的构成要件
1.主观过错。间接侵权行为的确定要在构成要件上严格把控,主观上必须是故意,即明知或应知。“明知”是指当事人在主观的实际意识到直接侵权行为必然发生或已经存在。“应知”是指只要当事人已经获得了足以促使合理谨慎者调查潜在侵权行为的信息,那么对经合理调查能够发现的侵权行为,在法律上都视为“知道”。
我国2006年5月颁布的 《信息网络传播权条例》第23条中适用的是“明知或应知”,到《侵权责任法》第36条,网络服务提供商的主观过错要求是“知道”。2.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条例》第23条中同时规定了判断过错的“通知删除制度”(notice and take-down regime):“网络服务提供者为服务对象提供搜索或链接服务,在接到权利人通知书后,根据本条例规定断开与侵权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的链接的,不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明知或应知所链接的作品、表演或录音录像制品侵权的,应当承担共同侵权责任。”从通知删除制度上看,即使权利人没有向网络服务提供商提交该条例规定的通知,行为人对提供搜索链接侵权服务有过错的,仍然要承担侵权责任。
但在司法实践中,“侵权警告”的发出曾经成为法院认定过错的必要条件,判决结果大相径庭的是七大唱片公司诉百度案3.参见(2005)一中民初字第8474号民事判决书。和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案4.参见(2007)二中民初字第2627号民事判决书。。前者因为权利人未发出正式的“侵权警告”而使百度摆脱了过错的认定,成为胜诉方,后者有过错的依据在于权利人数次向雅虎发出“侵权警告”而雅虎未履行删除义务,成为败诉方。百度案的结果明显与《条例》相悖,所以后来北京高院对此问题表明态度:“侵权警告”不是认定过错的唯一条件,即使没有通知,但网络服务提供商明知或应知所链接的作品是侵权的,仍应承担侵权责任。
不可否认,被控侵权人在权利人已经发出真实、明确的侵权通知的情况下,仍旧不删除侵权的内容,应属主观上有过错。但作为判断不够权威和专业的知识产权人来说,难免在对侵权通知的判断上缺乏确定性,尤其是侵权通知如果是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干扰经营者的正常活动,该通知的发出就已经偏离了维护知识产权的正常轨道,有可能给权利人滥用侵权通知、损害当事人或第三人的正常经营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实践中应该有更多判断主观过错的标准。目前,在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国家都在靠拢依因果关系判断的“可预见性规则”,即是否有过错是以一个理性人所具有的普通或通常经验为标准来判断的,可预见的范围以该损害后果是在特定过失行为可以预见的自然后果的范围即可,不要求预见某一损害后果发生的精确形式。使用“注意义务”标准在侵权判断上更具客观性,也符合当代侵权法加强对受害人保护的趋势[7]。我国司法实务中已经开始这种尝试,如在上述雅虎案中,虽然北京高院适用的是“明知、应知”标准,但在判断过错的时候,增加对行为人“预见能力”和“预见范围”的考察,如“榜单的设置表明搜索引擎服务商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应当知道、也能够知道其搜索、链接的录音制品的合法性。”比较遗憾的是北京高院对MP3搜索引擎服务商注意义务的程度及明知、应知的标准没有具体阐述。主要原因也是因为搜索引擎服务商的行业利益与权利人维权成本与收益比之间的平衡,是一个需要好好把握和拿捏的重大问题。
2.有直接侵权行为的发生。缺乏该要件的责任承担,将直接导致利益天平的失衡。例如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审理的(2003)沪一中民五(知)字第212号吕学忠等诉航空所等擅自制造销售专利产品关键部件间接侵权案,以及太原重型机器厂诉太原电子系统工程公司等擅自制造销售专利产品关键部件间接侵权案。上述两个案例采用“独立说”,即无直接侵权行为存在而追究专利间接侵权责任的典型案件。“独立说”带来的最明显弊端是动摇了专利侵权判定的标准——推翻了全面覆盖原则,即使实施权利要求书中的部分技术特征也要被追究专利侵权责任;弊端之二是缺乏全部技术特征的等同判定只能是整体等同的判定,后者早已经在专业范围内被抛弃已久;弊端之三,“独立说”的适用,实际上是多余指定原则的翻版,因为它们都由法官来改写专利权利要求书,改写的过程取决于法官的自由裁量。前述弊端必然导致原本公众可以依据来判断专利权范围的重要文件——权利要求书在法官的理解下出现了不确定性,不仅公众难以准确判断自己的行为是否落入专利权范围,而且专利权人同样对自己权利的保护程度不能预期,司法活动的不统一也就是必然的结果[8]。
3.存在以教唆、帮助、诱导、怂恿等方式参与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该要件必须要与主观过错、直接侵权存在要件一并考察,否则容易导致客观归责。例如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第(6)款对未经权利人许可破坏、删除作品上所加的技术措施的行为,定性为侵犯著作权。在不确定是否发生了直接侵犯著作权的情形下,直接追究该行为的侵权责任,违背“无损害则无救济”的传统法理原则,实际上是在扩张著作权人的权利范围。再者,即使实施他人的知识产权,但主观上并不明知,从保障交易安全和维护善意受让人的原则出发,受让人的行为也不存在定性为直接侵权的法律依据,自然不符合间接侵权或共同侵权的构成要件。EIP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法学院)
[1]王迁,王凌红.知识产权间接侵权研究[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
[2]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册)[M].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39.
[3]王利明.民法典侵权责任法研究[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336.
[4]史尚宽.债法总论[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166.
[5]王泽鉴.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三册)[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2.
[6]联邦判例汇编[M].第80卷.1897:721.
[7].刘信平.侵权法因果关系理论之研究[M].法律出版社,2008:58-59.
[8]魏征.我国不应该有专利间接侵权理论的应用空间[J].中国专利与商标,2008(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