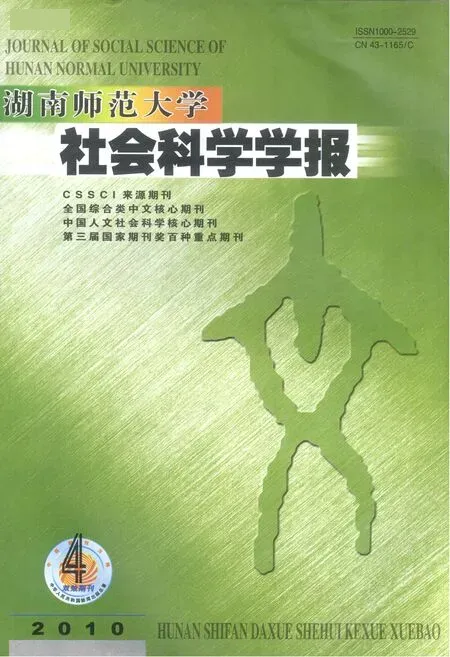论适度的法律程序
黄 捷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论适度的法律程序
黄 捷
(湖南师范大学 法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法律程序除应当具有“正当性”之外,还必须具有“程序性”。“正当性”是法律程序的实体价值的取值所在;“程序性”是法律程序的程序价值的存在基础。法律程序在正当性意义上必须满足最低正义的标准;而法律程序在“程序性”意义上则必须满足适度的要求;必须如此,才能够是真正的正当法律程序。判断法律程序是否具有程序性,取决于对应某特定社会活动的立法是否具有两个以上的、以义务为内容的、具有内在联系的程序规则。
适度;程序性;法律程序
适度也可称之为适当,属于程序法理论中“程序性”的问题。提出法律程序的“程序性”问题,是深化程序法理论研究的一个新问题,它有别于被学界普遍关注的“正当”法律程序问题。逐渐深入人心的、渊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被推崇为正当法律程序的原则“任何人都不得充当自己的法官”和“任何人的陈述皆应当被公平听取”等核心内容[1],实质上仅仅属于最低限度的正当问题。而该原则指向的“正当”或“正当性”从本质上属于法律程序的价值判断与选择问题,是法律程序的“实体”问题,也可称“正当性”问题,并不属于法律程序的“程序”问题。法律程序的“程序”问题应当归结为“程序性”,它是指一个法律程序应当在多大程度上表现为程序,或表现为程序的特征有多少和多强。这种特征或强度,我们都可以称之为“程序性”以及“程序度”。
对法律程序的“程序性”展开讨论,用以丰富程序法理论,帮助判断法律程序是否正当并促其完善,显然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本文针对该问题讨论,试图引发争鸣和促进学术深化,抛砖引玉,推动法治。
一、法律程序“程序性”问题的提出
程序的“程序性”通常没有被学界充分认识和讨论。笔者以为程序性是以程序本身特征的强弱来体现的。其中狭义的程序性含义可以单纯地指组成程序规则的数量的多与少,比如我国民事诉讼法有268个条文,刑事诉讼法有225个条文,仲裁法有80个条文,行政诉讼法只有75个条文(其中的义务性条款对程序性起着决定性作用)。广义的含义则也应当包含组成程序规则之间的关系等。凡具体的法律程序均须具有“程序性”。狭义的“‘程序性’专指法律程序作为法律规则集合体所体现出的程序化程度。这是一个由法律程序对应的社会活动内在复杂性程度和法律程序为其设置的程序规则数目,经过彼此比例分析和测量后,提出的一个用来衡量法律程序的程序化程度的指标体系的概念”[2](P13)。“程序度”属于广义的程序性所包涵的内容。“程序度则讨论程序规则的关联状态和程序柔韧程度,以及程序自身的纯洁程度。换言之,程序度事关程序自身的‘保健’状况和整体的对外关系。程序度问题同时也影响着我们判断法律程序的各个规则之间是否可能存在有所疏漏的‘黑洞’或‘后门’”[2](P15-16)。
在讨论法律程序的问题上,渊源于“实体为重”价值思维的传统,人们热衷于讨论正当法律程序。但相对一个自然物品或社会活动,人们都可以提出“度”的问题,比如:强度、韧度、长度、宽度、深度、速度等。正当法律程序必须是具体的法律程序,它必须指向某一个具体的社会活动。因而,没有具体指向的法律程序是抽象的,抽象的法律程序也是中性的,无所谓正当。有意义的法律程序只能是具体的,具体的法律程序总是或高或低、或左或右、或疏或密、或长或短、或韧或脆地存在着。在实体价值判断中,它们必然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或介于正当和不正当之间,同时混合着正当和不正当的因素的法律程序。这里的“正当”显然是自然正义的价值判断,无关乎法律程序的“程序”性。那么判断一个法律程序正当与否,除了实体上应当符合“自然正义”的两项基本原则之外,其程序性意义上难道不需要标准吗?笔者以为答案是肯定的,自然正义的原则没有给出法律程序的程序性标尺,当然也无法满足我们在法律程序的程序意义上做出价值选择。
相对于传统的法律程序正当性问题,程序性问题不太着眼于程序的实体价值判断,而是将组成法律程序的程序规则之间的关系作为考察的视角,进而分析归纳,试图探究相对于一个特定的社会活动,设置或组成一个法律程序所需要的程序规则究竟在数量上、质量上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状态上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才能是科学的和合理的法律程序。研究这一问题的意义在于我们不仅可以在立法上重新审视多年来我国程序法治中的程序设计的缺憾,而且也可以在司法实务中提高程序主体恪守程序正义规则的自觉,以适当行为避开程序后门和填补程序疏漏,降低程序运行成本。这正是笔者拟就本文的宗旨。
二、法律程序适度是程序正当不可缺无的要素
人们所普遍接受的正当法律程序内涵中,首先总是在其价值选择上需要符合人类的理性目标,比如:要求“任何人不能做自己的法官”所追求的目标是“中立”与“公正”;要求“公平听取所有人的陈述”所追求的目标是“公平”。这两个原则要求的共同点是意味着其程序关系架构应当吻合人类的善意追求,从而成为所有程序活动的最低正义标准(因为即使那些不以争议处理为内容的法律程序活动,亦可用该两项原则作为衡量自身活动正当性存在与否的尺度)。
现实中也经常发现许多具体的法律程序似乎已经属于符合“自然正义”两个原则的正当法律程序①,但实施中却也常被诟病,被指斥为不正当,有漏洞,以至于责难纷至。比如民事审判程序的审理期限问题、审级制度问题、地域管辖问题等。该现象的出现,促使我们深入考察,发现法律程序仅仅满足现有的“正当”性,是远远不够的;其同时还必须获得程序上适当的“程序度”或“程序性”,才能够满足人们对于“正当”性的全部需求。
据此,我们似乎可以有了一个判断:不吻合自然正义两项原则的法律程序肯定是不正当程序;而吻合该两项原则的法律程序也并不一定属于真正的正当程序。
相对于一个特定的社会活动,比如:司法审判、行政处罚、物品拍卖,法律为其设置的程序应当达到什么样的程序性程度,才是适当的和科学合理的?这是在程序立法对程序进行设置时候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我国长期以来奉行摸石头过河,体现在立法中宜粗不宜细的立法理念,导致大量法律、法规,其中的法律原则性强而操作性弱,即缺乏“程序性”、缺乏适度的法律程序调整和规范相关社会活动的实施。其实质就是在程序操作上留下模糊空间,而便于在实施过程中随机调控。后果就是大量的法律、法规沦落为“看”法②。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也就是在法律程序的程序性上判断什么才是适度的法律程序。
一列奔向城市目标的列车,其目标性、方向性、动机目的、动力等要素已经确定的情况下,其车轮必须奔驰在设定的轨道上,其速度和安全可靠程度除了受动力源能量大小的影响,同样也受其车轮与轨道之间的关系影响。车轮和车轨过于紧密的关系会增大摩擦导致列车无法奔驰,但过于疏散的关系又将导致车轮脱轨出现事故。结论是车轨和车轮之间必须相适应。因而,在各类关节和关键的问题中要求适度性相对于一个物体的运动同样是成立的。
强调适度的法律程序是用来满足法律程序正当性以外的“程序性”意义上的合理性、科学性,更是实用性。在传统意义上判断为不正当的法律程序,即使具有适度的程序性,它也是应当在价值选择上被否决的程序;但传统正当的法律程序,倘若不具有适度性,那么它纵然在价值选择上是可以肯定的,但在达成价值目标的中途(程序过程)也是会被否决的,或者至少是会被迟滞的。因此,笔者以为:仅仅满足正当性意义的“法律程序”其本质可能会依然不属于正当法律程序。只有在程序性意义上同时也满足法律程序适度性的法律程序,才能够成为真正的“正当法律程序”。
三、法律程序“程序性”和“程序性适度”的衡量
1.程序性的判断依据
笔者在此提出正当法律程序除了具有“正当性”要素以外,还必须具有“程序性”。其中程序“正当性”的理论,通过学界不懈的努力和讨论的逐渐普及而为人们所认同,并开始渐渐融入我们的生活。但即使“正当性”的理论空间也并没有因此而获得体系性的整理,人们所接受的“正当性”理念,还仅是实体价值意义的,并且依然存在着学术探索的极大空间③。
“程序性”问题显然还是一个全新的、具有现实意义的问题。提出法律程序必须具有“程序性”,否则,不成其为程序。法律程序是否具有“程序性”的判断,取决于一个被视为法律程序的规则系统是否已经针对一个特定的社会活动设置了对应的、特定的活动规则,从而使得该社会活动具有了活动的特殊表现形式,即有序性。
判断被视为法律程序的程序具有“程序性”需要与之对应的程序活动吻合大多数研究程序法问题的学者们所称的“步骤、次序、过程、方式,它反映人类行为的有序性,并与无序、混乱相区别。换言之,程序是人们对某种行为经过多次重复,对其规律的认识和确定”[3]或者“从法律学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为按照一定的顺序、方式和手续来作出决定的相互关系。其普遍形态是:按照某种标准和条件整理争论点,公平地听取各方意见,在使当事人可以理解或认可的情况下作出决定。”[4](P18)“从事法律行为、做出某种决定的过程、方式和关系。过程是时间概念,方式和关系是空间概念。程序就是有这样的时空三要素所构成的一个统一体”[5](P15)。
事实上,上述所引的这些关于揭示程序特点的表述有些颠倒和失真,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法律程序和法律程序活动属于两个不同层面的理论问题。程序的特征最主要的表现应当是,人们的活动或关系在限定的时空范围内因为程序的制约而有序,而并不是人们有序的活动或社会关系本身等于程序。所以程序和程序行为过程应被视为两个层面的问题。法律程序必然是以“行为义务”作为基本规范内容的规则体系[2](P18-21),那些没有或脱离程序予以规范和引导的人类行为或社会关系将是自由的和无序的,因而也必将是非程序性的、或权利性的。所以,将法律程序和法律程序活动区分开来将有利于我们完成对法律程序及其“程序性”的后继分析。换言之,具有“程序性”的法律程序也就意味着该程序具有了约束某特定活动中人们行为的效能,并能够使得这些行为在活动形式中表现出步骤、次序和方式上的有序性。
综上所述,判定一个称为法律程序的程序具有“程序性”的基本标准应当包括:(1)该程序是否对应某特定的社会活动(此处强调特定社会活动,而非社会关系)而设置了行为规则,或者说其所设置的行为规则是否具有特殊的对应性;(2)具有对应性的行为规则是否对活动主体设置了相关行为方式、时间、地点等义务性的要求(即该规则应当为义务性规则);(3)该义务性行为规则是否为彼此有关联的两个以上。
2.程序性适度的衡量基础
“程序性适度”是在判断法律程序已经具有“程序性”的基础上提出的何种程序性强弱状态才能最大效益实现程序目标的问题。
程序性适度是一个历史性指标体系,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人们对法治的认识加深和适应能力提高,法律程序总的发展趋势必将是程序性逐步增强,而且程序设计会愈来愈精密,程序度愈来愈高(如程序法文件每次修改,其条文总数一般都会有所增加)。但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程序性受到法治理论水平、制度建设效率、人们的适应能力等因素的限制。
根据法律程序是由法律程序规则(并且主要是义务性程序规则)所组成的特征④,程序规则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到程序性的状态。所以,程序性的强弱又可以区分为两个方面的指标:密度和韧度状态。
1.密度状态问题实质也即上文所提到的狭义“程序性”问题,是指开展特定社会活动获得公正与效益目标所实际需要的程序规则数目与实际存在的程序规则数目之间的比值。这里所称“实际需要的程序规则数目”应当是一个依据开展特定社会活动的实体价值目标而确立的内在隐形需求,笔者将其假定为1或100,视为百分比之分母。“实际存在的程序规则数目”则是已经或准备体现在立法文献中的规则数目。二者之间比值越高,则表现出的密度越大、程序性越强;但并不等于比值越高、密度越大,程序性就适度。不同的社会活动需要不同的适度要求;因而相对不同性质的程序,也需要不同的密度。
直观的感受是:密度是程序规则的数量多少问题。
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无论开展任何社会活动,过于冗杂繁密的(程序)规则,会增加人们行为的紧张频率,可以令人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动辄触规,以至于在一些特殊的社会活动领域可以导致让人不敢涉足。有经验或有特殊动机的立法者或规则制定者常常会以此阻止或隔断那些不愿让其发生或过多人涉足的社会活动。过于简单空乏的(程序)规则或授权意义的规则,会增加人们行为的自由,可以让人具有更多的选择和从容,但也更容易让人滋生懒惰和恣意,以及更容易使人一心二用,同时兼顾不同的活动和事务。
另一方面,是否能够适应并参与特定的社会活动,并让自己游刃其间获得相应的权益,达成自身的目标,也取决于人们对应性地学习和训练。因而,经过训练的大量的专业人员诞生,他们相对于其他人,参与特定的社会活动,在其中经历和适应程序,更能够在程序活动中取得优势和达成目标、获得成功。
因而考察特定的社会活动的法律程序在密度方面是否适度,需要考虑下列要素:
(1)特定社会活动的性质。不同性质的社会活动,满足人类不同层次的需要。根据其中人们对利益需求的大小和重视程度,为其设置不同密度的程序。比如实践经验中,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军事活动的重要性,因而在各个国家事关军事活动的程序规则一直是密度极高的一类。其次,司法活动。其三,政府活动。其四,公益事业活动。最可以享受自由的是纯粹民事性质的各类社会活动,意思自治。如订立契约,连规则本身的内容和数量也交与公民、法人自己设定,仅要求公民、法人须受自己意志的约束。
(2)特定社会活动的专业属性。社会分工导致的社会活动分门别类。不同专业属性的社会活动具有不同的价值目标,也需要不同的程序。当然,其密度也需要与此相适应。
(3)活动参与主体的社会性。普通的社会主体参与一般的社会活动,其基准是平等的。但普通社会主体参与专业性社会活动则基准应当是不同的。
(4)特定社会活动的长期实践获得的经验与教训总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判断法律程序密度的适当与否,最重要的是能够及时地在已经发生的实践中获得经验,修正现有法律程序的不足,完善制度建设。
2.韧度状态问题实质也即上文所提到的狭义“程序度”问题。是“讨论程序规则的关联状态和程序柔韧程度,以及程序自身的纯洁程度。换言之,程序度事关程序自身的‘保健’状况和整体的对外关系。程序度问题同时也影响着我们判断法律程序的各个规则之间是否可能存在有所疏漏的‘黑洞’或‘后门’。”[2](P15-16)
直观的感受是:韧度是程序规则的质量问题。
紫云独立在秋风中,眼光落在水仙芝身上。曾经,她们一起读书,都爱过班上的蒋海峰,如今双双失落在河边。一阵风吹来,紫云迟疑片刻,悄悄地从她身后的大堤上走过。抄小路回到家里,和衣而卧,陷入不可自拔的痛苦中。
韧度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即我们已经认识到,法律程序的成立至少应当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以义务为内容的程序规则,是程序规则所组成的规则体系。既然法律程序至少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程序规则,也就必然意味着这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程序规则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某种联系。而该程序规则的内容和其彼此之间联系的状态如何,将决定着该法律程序的“颜色”、“类型”、“对外关系”等等属性。
这里的“颜色”是象征意义的,是指法律程序与其所对应的社会活动共同表现出的外在形式在视觉方面的象征性;“类型”是人们将法律程序归纳分类后的归属问题,因为程序规则之间内在联系不同而将具有共性特征的法律程序视为同一类型;“对外关系”是指法律程序因为颜色、类型的不同而导致的法律程序及其所对应的活动本身与法律程序活动以外的事务之间的联系状态。
韧度较强的法律程序,对外具有较高的防御性。其程序编排和运行往往缜密而高效,不受外部因素滋扰和干涉,程序自我调控能力强;程序主体在该类程序运行过程中,会感受到不自由、高度紧张和容易疲劳,但纪律强、效率高。韧度较弱的法律程序,对外一般具有开放性,其程序规则之间编排松散,程序外的主体容易切入或侵入程序活动⑤。程序主体也容易将自身行为溢出程序活动,同时兼为其他行为等。优点是程序主体在该类程序运行中自由空间和时间充裕,不足是容易滋生懒惰和怠慢。
韧度过强的法律程序,程序主体会失去自由。韧度过弱的法律程序,程序主体会自由无度。因此,法律程序必须具有合适的韧度,才能确保程序运行的价值目标获得实现。
法律程序韧度的强弱取决于这样一些要素:
(1)设定该法律程序的立法目的。(2)法律程序规则的规范内容。规范内容是法律语言表达出的对程序主体行为方式、时间、地点的指引和规范。其表达的具体含义不同会决定该法律程序的整体开放状态。(3)法律程序规则之间的关联性和对应性。法律程序规则之间具有关联性而且关联性很强,会促使程序的规范内容获得较好的保障;法律程序规则之间具有关联性而且关联性很弱,则程序的规范内容会散乱和失去制约。
四、当前我国法律程序适度状态的考察与评析
我国主要的法律程序包括:立法程序、司法程序、行政程序和拍卖等社会活动程序。其中目前最为们所关注的是司法程序、行政程序。司法程序和行政程序通过法律文件的形式确立,表现为三大诉讼法的法典文件和行政处罚、行政许可等有关的行政立法文件。我们把法律程序规则中包含有“可以”或“有权”或“享有”词义要素的条文,看作是标志意义的“权利性”法律程序规则;把法律程序规则中包含有“应当”或“必须”或“不得”词义要素的条文,看作是标志意义的义务性法律程序规则。经过对该不同法律文件条文规则的比较,笔者试图找出其中法律程序适度问题的差异。
我国《刑事诉讼法》全部225个条文中包含有“应当”一词236个,包含有“必须”一词29个,包含有“不得”一词32个,共计297个义务性表述;同时包含有“可以”一词132个,包含有“有权”一词31个,包含有“享有”一词4个,共计有167个权利性表述。
我国《民事诉讼法》全部268个条文中包含有“应当”一词205个,包含有“必须”一词44个,包含有“不得”一词23个,共计272个义务性表述;同时包含有“可以”一词148个,包含有“有权”一词25个,包含有“享有”一词1个,共计有174个权利性表述。
我国《行政诉讼法》全部75个条文中包含有“应当”一词27个,包含有“必须”一词1个,包含有“不得”一词3个,共计30个义务性表述;同时包含有“可以”一词38个,包含有“有权”一词14个,包含有“享有”一词0个,共计有52个权利性表述。
我国《行政处罚法》全部64个条文中包含有“应当”一词55个,包含有“必须”一词14个,包含有“不得”一词15个,共计84个义务性表述;同时包含有“可以”一词25个,包含有“有权”一词8个,包含有“享有”一词2个,共计有35个权利性表述。
我国《行政许可法》全部83个条文中包含有“应当”一词109个,包含有“必须”一词2个,包含有“不得”一词31个,共计142个义务性表述;同时包含有“可以”一词32个,包含有“有权”一词7个,包含有“享有”一词4个,共计有43个权利性表述[2]。
综合而言,上述五部法律文件分别为不同的法律活动设置有相应的法律程序。但我们可以注意到其间的密度差异是显著的。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显然受到了更为密切的注意和重视,其立法予以约束的规则自然在密度上高于其他法律程序。其中我们更可以注意到刑事诉讼法义务性表述高达297个,是上述法律程序中密度最高的。民事诉讼法有272个义务性表述,密度次之。行政许可法有142个义务性表述,密度第三。行政处罚法有84个义务性表述,密度第四。行政诉讼法则有30个义务性表述,密度最低。这其中民事诉讼法268个条文立法长度最高,刑诉中225个条文长度其次,行政许可法83个条文长度第三,行政诉讼法75个条文长度第四,行政处罚法64个条文中长度第五。
另外,我们也可以注意到按照上述顺序,刑事诉讼法有权利性表述167个,民事诉讼法有174个,行政许可法有43个,行政处罚法有35个,行政诉讼法则有52个权利性表述。这其中民事诉讼法174个最高,刑诉中167个其次,行政诉讼法52个第三,行政许可法43个第四,行政处罚法35个第五。权利性表述意味着权利的存在,无论是在法律关系中还是在法律程序中权利都意味着自由。因而,权利在法律程序中也意味着法律程序的弹性和韧性,权利丰富的法律程序其韧度会低,权利受到制约的法律程序则韧度会强。
在上述统计和比较中,我们已经能够发现其中的行政诉讼法是密度和韧度都比较匮乏的法律程序,其总条文长度不高,但授权较多,义务约束较低。这些问题表现在司法实务中,即是出现大量行政诉讼司法不端和不满的情绪与申诉,说明其是“程序性”较差的法律程序。刑事诉讼法在当前比较中是程序性较强的法律程序,但事实上其和自身所担当的程序价值目标相对应的关系而言,依然存在着大量不适。其程序性在满足法制进步发展的需求上尚值得更进一步提高。限于篇幅,另文再论。
注 释:
① 学界所论述的满足自然正义原则的法律程序一般并不涵盖那些指向正常社会活动的法律程序,如互动性的合同的交易活动程序、行政决策的执法程序。
② 这里所称的“看”法,是比喻许多法律、法规只能看,不能真正发挥其对社会关系的规范、调控作用。
③ 事实上,“自然正义”中的两项基本原则只是判断程序正当性有无的原则。就“正当性”而言,依然存在着强度大小变化的理论空间和现实空间。
④ 本文以下所提到的“程序规则”皆主要指程序义务性规则。
⑤ 笔者将那些程序外的主体通过合法途径正常进入程序活动的行为称为“切入”,那些未经过合法途径非法进入程序活动的行为称为“侵入”(类似于网络中的黑客行为)。
[1]孙祥生.论自然正义原则在当代的发展趋势[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06,(2):3-9.
[2]黄 捷,刘晓广,杨立云.法律程序关系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3]司春燕.程序法的现代理念[N].学习时报(思想理论版),2002-06-03.
[4]季卫东.法律程序的意义——对中国法制建设的另一种思考[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
[5]孙笑侠.程序的法理[M].商务印书馆,2005.
(责任编校:文 泉)
On Appropriate Legal Procedures
HUANG Jie
(College of Law,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legal procedures should not only be“legitimate”,but also“procedural”. “Legitimacy”is the entity value of legal procedures;“procedure”is the legal basis for the existence of procedural value.Proceedings in the sense of legitimacy must meet the minimum standards of justice,while the proceedings in the sense of“procedure”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 of appropriation.Only in this way,can it be the real due process.Judging whether legal procedures are procedural process depends on whether the legislation corresponding to a particular social activity has two more obligative rules of procedure which are inherently linked.The vague opinon,which makes procedures equivalent to“step,sequence,process,method,”or“relationship”,is the consequence of lacking deep study for procedures and confusing the procedures and program activities.
appropriation;procedural;legal procedures
F222
A
1000-2529(2010)04-0063-04
2010-03-15
黄 捷(1962-),男,河南信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