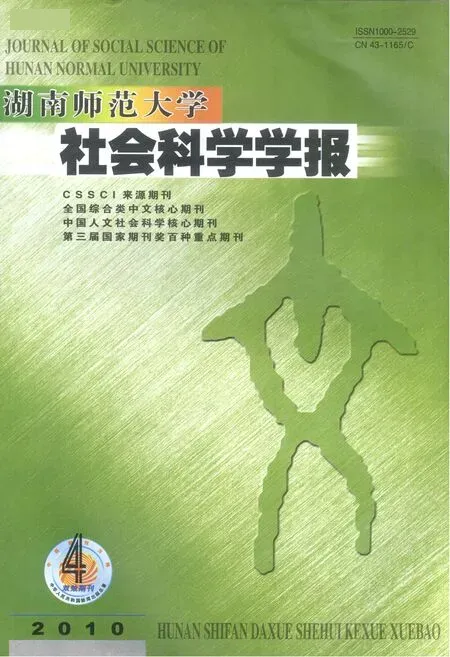金圣叹文学创作思想研究
赵炎秋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金圣叹文学创作思想研究
赵炎秋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金圣叹文学创作论中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思想。他在虚构的基础上提出“无实写论”;从“怨毒著书”、“锦心绣口”和“成奇文以自娱”三个方面探讨文学创作的心理动因;通过“格物致知”和“亲动心”说探讨作家如何把握世界、塑造艺术形象。这些思想至今仍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金圣叹;文学创作;作家
金圣叹是明末清初著名文学批评家、评点家。金圣叹的文学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对《水浒传》与《西厢记》的评点中。在评点《水浒》与《西厢》时候,金圣叹对于文学创作有较多的涉及,有些观点至今仍有一定的价值。本文试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是任何批评家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在有关《水浒传》的评点中,最早透彻说明这一关系的是叶昼。叶昼一方面认为,“世上先有《水浒传》一部书,然后施耐庵、罗贯中借笔墨拈出;若夫姓某名某,不过劈空捏造,以实其事耳。”一方面又指出,“《水浒传》事节都是假的,说来却似逼真,所以为妙。”“《水浒传》文字原是假的,是为他描写得真情出,所以便可与天地相终始。”[1](P194,196)金圣叹继承了叶昼的观点,一方面认为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础与源泉,一方面强调创作的虚构性。
金圣叹从文学作品中所写的古人古事的真实性入手,进行探讨,得出结论,“古人实未曾有其事也。乃至古亦实未曾有其人也。即使古或曾有其人,古人或曾有其事,而彼古人既未尝知十百千年之后,乃当有我将与写之,而因以告我。我又无从排神御气,上追至于十百千年之前,问诸古人。然则今日提笔而曲曲所写,盖皆我自欲写,而于古人无与。”[2](P49)这段话设想了两种情况:一是文学作品所描写的古人古事在古时根本就不存在,一是这些古人古事虽然存在,但时过境迁,古人既不可能告诉我,我也不可能溯时间而上去问古人,因此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进行创作。无论哪种情况,作者的想象与虚构都是不可避免的。他以《史记》和《水浒》对比,进一步说明文学创作虚构的性质:“《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3](P1)以文运事,也就是组织文字将既有的事件表现出来,因文生事,则是根据作文的需要,虚构出一定的事件来。一个强调真实,一个要求虚构;一个文字可以千变万化,但已有的事实不能改变,一个不仅文字可以千变万化,事件也可以根据写作的需要进行变化。金圣叹的这段论述不仅指出了历史与文学各自的特性,而且指出了它们在运用语言上的区别。
从肯定文学的虚构性出发,金圣叹又提出了“无实写”论。他认为,“从来妙文,决无实写一法”,“自古至今无限妙文,必无一字是实写”。[2](P90,93)而“著书之家”也从来不计其所写的“其事其人之为有为无”。[3](P598)不过,金圣叹这里所说的“实写”主要不是从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的角度,而是从文学与生活的描写关系的角度来说的。换句话说,所谓“从来妙文,决无实写一法”的意思主要不是说文学的内容完全来自虚构,与生活无关,而是说文学不可能完全如实地描写生活。《西厢记》第一卷第四折写张生第三次见到莺莺,称赞她“檀口点樱桃,粉鼻倚琼瑶,淡白梨花面,轻盈杨柳腰”。金圣叹评道:“世之不知文者,谓此是实写,不知此非实写也,乃是写张生。直至第三遍见莺莺,方得仔细,以反衬前之两遍全不分明也。……从来文章家决无实写之法。吾见文之最实者,无如左传《周郑交恶》,传中‘涧溪沼之毛,苹蘩藻之菜,筐釜之器,潢行潦之水’,板板四句,凡下四四一十六字,可称大厌。而实则止为要反挑王子狐、公子忽两家俱用所爱子弟为质,乃是不必,故言不过只采那涧溪沼中间之毛,唤作苹蘩藻寻常之菜,盛于筐釜野人之器,注以潢行潦不清之水,只要明信无欺,便可荐鬼神而羞王公。四句不意乃是一句,四四一十六字,不意乃是一字,正是异样空灵之笔,然后谛信自古至今无限妙文,必无一字是实写,此言更为不诬也。”[2](P89,92-93)《周郑交恶》描写“毛、菜、器、水”可谓非常之实了。但它的意思却不是要实写这四样东西,而是为了说明只要有了诚信,随便什么东西都可以为质,不一定非要自己宠爱的子弟。这里看似实写,实际仍是虚写。由此可见,文学作品并不一定要实写,只要逼真,虽是虚构,仍是妙文。那么,为什么文学作品不要“实写”呢?原因之一,有些事物因条件限制,无法亲见,只能想象,如金圣叹好友王山笔下的庐山。他没有到过庐山,却写得栩栩如生。原因之二,有些事物实写不出,只能虚写,如莺莺之美。原因之三,有些事物过于复杂多面,只能选择性地描写,如白马解围。原因之四,即使是实写的,也往往含有其他的含义,如《周郑交恶》。原因之五,描写总要渗进作者自己的感情,无法完全客观。如张生讲述的莺莺长相。也正因为真正的“实写”难以达到,所以“文到入妙处,纯是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联绾激射,正复不定”。如“张青述鲁达被毒,下忽然又撰出一个头陀来,此文章家虚实相间之法也。然却不可便谓鲁达一段是实,头陀一段是虚,何则?盖为鲁达虽实有其人,然传中却不见其事,头陀虽实无其人,然戒刀又实有其物也。”[3](P232)就虚实而言,这段话至少有两层意思:一,鲁达是实,头陀是虚,因为前者是《水浒》中的一个人物,而后者只是人物口中提到而已。二,鲁达不一定是实,因为相关的历史记载中没有这个人,而头陀也不一定是虚,因为他的两把戒刀的的确确在张青的店里。就这样有虚有实,虚实相间,打造出世上无数妙文。
如果稍作引申,金圣叹的“无实写”论实际上涉及到了语言表达的问题,他似乎隐约意识到了语言与现实之间的距离,意识到了语言无法完全如实地表现现实的问题。而这正是20世纪西方语言论文论的核心思想。金圣叹文学思想的超前性在这里显露出来。
不过,在前面那段论述中,史书上没有鲁达相关的记载,这是历史事实,而头陀的两把戒刀则是小说中的描写。金圣叹将两者都作为论据来说明自己的虚实论,有将现实与文学混为一团的嫌疑。金圣叹在这一点上似乎没有想清楚。但由此引出另一个问题:文学创作的假定性。所谓假定性是指文学作品将自己建构的虚拟世界设定为真实存在的一种性质。接受文学作品,就必须接受它的假定性,否则文学创作与文学接受都不可能进行。中国文艺实践一直具有很强假定性。比如戏曲舞台上人物做一个运作,就表示开门、关门。几个人在舞台上厮杀一阵,就表示千军万马在鏖战。都是对于假定性的运用。但到金圣叹为止,理论上的讨论并不多。金圣叹涉及到了这一点。在《水浒传》第5回的回评中,他写道:“耐庵忽然而写瓦官,千载之人读之,莫不尽见瓦官也。耐庵忽然而写瓦官被烧,千载之人读之,又莫不尽见瓦官被烧也。然而一卷之书,不盈十纸,瓦官因何而起,瓦官因何而倒,起倒只在须臾,三世不成戏事耶?又摊书于几上,人凭几而读,其间面与书之相去,盖未能以一尺也。此不能一尺之间,又荡然其虚空,何据而忽然谓有瓦官,何据而忽然又谓烧尽,颠倒毕竟虚空,山河不又如梦耶?”[3](P52)一卷书就十来页,作者写有一个瓦官寺,然后又写瓦官寺被烧了,读者也就相信有那么一个瓦官寺,有那么一个瓦官寺被烧了。金圣叹在这里提出了疑问:“何据”,读者凭什么相信呢?金圣叹的回答虽然有点虚无的色彩,但他毕竟肯定了读者这样理解是正确的,也是必须的。他虽然没有正面阐述文学创作的假定性原则,但却天才地“猜到”了这一原则。
与虚构相联,金圣叹还探讨了灵感问题,认为灵感既有天赋的成分,又有后天的成分。灵感具有不可重复性。从灵感的不可重复,金圣叹又探讨了创作的不可重复性问题:“今后任凭是绝代才子,切不可云,此本《西厢记》我亦做得出也。便教当时作者而在,要他烧了此本,重做一本,已是不可复得。纵使当时作者,他却是天人,偏又会做得一本出来,然既是别一刻所觑见,便用别样捉住,便就是另样文心,别样手机,便别是一本,不复是此本也。”[1](P13-14)赫拉克利特认为,人无法两次进入同一条河流。不仅灵感是转瞬即逝,逝不再来的。作家的思想、经历、观点、情感、技巧等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因此,文学作品是无法重复的,即使是同一作家重新创作自己的同一作品,新的作品也不可能与原来的作品一模一样。金圣叹的这一观点不仅深刻,而且具有较强的现代性。
二
文学创作的动力,是批评家们一直关心的问题。我国批评家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提出了“诗言志”(《尚书》)、“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不平则鸣”(韩愈)等观点。金圣叹继承这一传统,从创作心理的角度,提出了三个重要的命题:“怨毒著书”、“锦心绣口”、和“成奇文以自娱”。
所谓“怨毒”,也即怨恨、不满,因为怨恨、不满,所发言词便不免激愤,有伤中庸之道,因而为“毒”。在《水浒》第18回回评中,金圣叹写道:“此回前半幅借阮氏口痛骂官吏,后半幅借林冲口骂秀才。其言愤激,殊伤雅道。然怨毒著书,史迁不免,于稗官又奚责焉。”作家居于社会之中,亲历、感受着社会种种不平,而又无力匡正,只好发为议论,形诸文章。因此,“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3](P107,152)只要天下还处于无道的状态,作家就无法不议论。金圣叹肯定了作家怨毒著书的权利与合理性,并把这种“怨毒”的产生归诸于社会和统治阶级。金圣叹继承孔子的“兴观群怨”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并将作家“怨毒”与否同社会状况联系起来。这种思想是值得肯定的。
如果说“怨毒著书”主要是从作家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立论,那么,“锦心绣口”则主要是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着眼。金圣叹指出:“大凡读书,先要晓得作书之人是何心胸。如《史记》须是太史公一肚皮宿怨发挥出来……《水浒传》却不然。施耐奄本无一肚皮宿怨要发挥出来,只是饱暖无事,又值心闲,不免伸纸弄笔,寻个题目,写出自家许多锦心绣口,故其是非皆不谬于圣人。后来人不知,却于《水浒》上加‘忠义’字,遂并比于史公发愤著书一例,正是使不得。”[3](P1)这段论述从另一个方面指出,作家创作是源于表达与展示的需要。作家秉赋才华、富于想象,在现实生活中,不免常常生出无限暇思,涌现许多念头、场面、人物、形象。当这些暇思、形象在心中充塞、活跃的时候,作家便必然会试图将其发为作品。因此,作家创作并不一定是出于“怨毒”,也可能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绣口),或内心的想象与思绪(锦心)。
“锦心绣口”与“怨毒著书”表面看似矛盾,实际并不矛盾。创作本身是多面的。一方面,作家有社会责任,有义务也有权利批评社会,另一方面,他又有自己的艺术追求,需要通过作品将自己层出不穷的思绪、上天入地的想象、操纵语言的能力表现出来,写出自己的“锦心绣口”。从这个角度看,“锦心绣口”与“怨毒著书”其实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侧面,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古代文论往往强调“不平则鸣”,“穷愁出诗人”,诗“穷而后工”。这主要是从文学的社会作用而言的。诗人感受到社会的黑暗与不平,自己也处于不利的处境,因而产生“怨毒”,发而为文学作品。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作家创作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原因,他也可能因为娱乐、消遣、表达,甚至仅仅只是为了表现自己的才华、引人注目而进行创作。唐代诗人韩愈在“传道”的同时就有游戏之作,白居易在写作“新乐府”的同时也写作了大量的“闲适诗”。有学者认为“‘戏’与‘道’,‘闲适’与‘讽谏’,无不显现出当时文人的‘一体两面’。这种分化和裂变在宋代文人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从中唐开始,‘合理’的存在和‘适意’的存在之间展开了拉锯,从而导致了新的文学品格和文学格局的形成。”[4](P17)金圣叹的“锦心绣口”说概括了这种现象。自然,作家要为娱乐而创作,必须无后顾之忧。因此金圣叹强调作家要处于“饱暖无事,又值心闲”的状态,才可能写出“绵心绣口”。宋代之后,市民阶层兴起,对文艺的休闲、消遣、娱乐功能的要求大大增加,文学创作成为文人谋生的手段之一。金圣叹的“锦心绣口”说实际上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反映,相对于“怨毒著书”说,更是一个纯文学性的命题。
但更有创新意义的还是“成奇文而自娱”说。金圣叹认为“君相能为其事,而不能使其所为之事必寿于世。能使君相所为之事必寿于世,乃至百世千年以及万世,而犹歌咏不衰,起敬起爱者,是则绝世奇文之力”。因此,史书一方面要为“一代纪事”,一方面仍要“出其珠玉锦绣之心”。而“稗官之家,无事可纪,不过欲成绝世奇文以自娱乐”,就更需惨淡经营,写出锦绣文章。[3](P246)这段话从两个方面说出了文史的区别。一方面,史书的任务是记载真实的历史事件,而文学则无此任务;另一方面,史者著书是为了将历史事件传诸千古,而作家创作则是为了自娱,自我欣赏。这就像某些女性在年轻时将自己的玉体拍下来,其目的并不是要示之于众,而是想时时自己欣赏,以记得自己曾经多么美丽。“成绝世奇文以自娱”说从作者自我欣赏的角度探讨文学创作的动机,虽然有一定的偏颇,但也不是没有一定的道理。它肯定了作家个人的精神愉悦对于文学创作的推动作用,肯定了文学创作的动力不一定都是功利、实用的考虑。马克思认为,人在自己的活动中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到自己所接触的对象上面,“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肯定自己”[5](P125)。人在这种对象化中不仅肯定自己的力量,而且感到精神的愉悦。作家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因此他在创作中能够感到愉悦,是当然的。因此,金圣叹的“自娱说”在理论上也是站得住脚的。“自娱”说作为创作动力说的一种,有较强的超前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康德的“无功利的功利性”,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以及语言论文论的“文学作品是不及物的”等观点的影子。
自然,我们不应将金圣叹的三种观点对立起来,三者实际上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它们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文学创作的动力问题。
三
在创作主体方面,金圣叹主要从创作的角度,提出了“格物致知”和“亲动心”说。这是他在作家论中最重要的理论贡献。
“格物致知”这一术语最早见于先秦典籍《礼记·大学》:“古人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礼记·大学》)这里的“格”是推究的意思,“致”是求得的意思。从字面上讲,“格物致知”的意思是穷究事物原理,从而获得知识。但是,在《大学》中,“格物致知”并不是一个纯认识论的概念,它实际上是儒家学派为实现自己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思想而提出的阶段性行为目标。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最高理想,而格物与致知则是达到这一理想的最初两个阶段,具有浓厚的政治伦理色彩。“格物致知”说在宋代得到多方探讨,其中朱熹的观点最为重要。朱熹认为“致知”先要“格物”,格物的目的是致知,致知是在格物的过程中实现的。朱熹理解的“物”,是指一切事物,既包括客观的物质实体,也包括主观的思想精神,“知”则是他所说的“理”。他认为,“格物”就是要广泛地学习、研究事物(包括书本),格物达到一定程度,就会贯通而得到一普遍原理,用这个得到的原理进行推类,就可以知道那些未知的事物之理。朱熹将“格物致知”从先秦儒家的以修身齐家为根本的政治伦理哲学范畴转到了认识论的范畴,对“格物致知”论是一个大的推进。但朱熹所说的“理”并非客观事物的规律,而是一种先于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的形而上的东西,它也存在于人心之中,这样,朱熹便把格物致知引向了人的主观的一面,又有一定的局限性。明末清初,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传进,中国人研究自然科学的热情高涨,“格物致知”转向客观方面,偏重于探究自然,把握客观规律。这是金圣叹提出“格物致知”说的主要背景。
金圣叹是从认识论的角度提出“格物致知”说的。他的格物致知说既继承了前人的思想又增添了新的内容。在金评《水浒·序三》里,他写道:“施耐庵以一心所运,而一百八人各自入妙者,无他,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斯以一笔而写百千万人,固不以为难也。格物亦有法,汝应知之。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忠恕,量万物之斗斛也。因缘生法,裁世界之刀尺也。施耐庵右手握如是斗斛,左手持如是刀尺,而仅乃叙一百八人之性情、气质、形状、声口者,是犹小试其端也。”[6](P10)施耐庵十年格物而一朝物格,通过长期地观察、探究事物,而终于达到了对于事物的深入认识和透彻把握,在这种认识与把握的基础上再来创作小说,描写人物,反映生活,自然得心应手。在评点中,碰到描写发挥得精彩的,金圣叹常用“诚乃格物君子”加以肯定。如《水浒》第42回,写李逵沂岭遇虎。“那母大虫到洞口,先把尾巴去窝里一剪,便把后半截身躯坐将入去。”金圣叹批道:“耐庵从何知之?诚乃格物君子,奇绝妙绝。”[3](P213,375)这种事情是施耐庵不应知道的,但却写得合情合理。正是因为他通过长期格物,而达到了对于自然、社会、人性的透彻了解,因此能够充分合理地发挥想象,写得真实可信。
金圣叹认为,格物之法,以忠恕为门。何为“忠恕”?金圣叹在《水浒》第42回回评中做了比较详细的解释:“夫中心之谓忠也,如心之谓恕也。见其父而知爱之谓孝,见其君而知爱之谓敬。夫孝敬由于中心,油油然不自知其达于外也。……善亦诚于中形于外,不善亦诚于中形于外,不思善,不思恶,若恶恶臭、好好色之微,亦无不诚于中形于外。盖天下无有一人,无有一事,无有一刻不诚于中形于外者也。”“盖忠之为言中心之谓也。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为喜怒哀乐之中节,谓之心。率我之喜怒哀乐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忠。知家国、天下之人率其喜怒哀乐无不自然诚于中而形于外,谓之恕。知喜怒哀乐无我无人无不自然诚于中形于外,谓之格物。能无我无人无不任其自然喜怒哀乐,而天地以位,万物以育,谓之天下平。”“能忠未有不恕者,不恕未有能忠者。看宋江不许李逵取娘,便断其必不孝顺太公,此不恕未能有忠之验。看李逵一心念母,便断其不杀养娘之人,此能忠未有不恕之验也。”[3](P367,368)心中情感自然生成自然表现出来便是“忠”,能按心中情感行事并且知道我这样别人也必定这样就是“恕”,能从自身推及他人乃至万事万物便是格物。因此,格物必经忠恕,忠恕是格物之门。
另一方面,既然无论善恶,都是诚于中而形于外,天下无一人一事一刻不诚于中而形于外者,忠恕自然可以成为“量万物之斗斛”。而因缘生法,则是“裁世界之刀尺”。这里“斗斛”“刀尺”都是标准、尺度的意思。“因缘生法”本是佛教用语。“法”指包括精神与物质在内的大千世界中的一切事物和现象,“因缘”指产生这些现象的内外原因。“因缘生法”指一切事物都是由一定的原因产生、发展的,存在于一定的因果链中。既然一切事物都处于因果关系之中,“因缘生法”自然可以作为格物的“刀尺”。另一方面,格物的目的又必须通晓万物之间的因果、规律。在这个意义上,“因缘生法”又是格物的目的之一。
由此可见,金圣叹的“格物致知”说一方面强调要研究事物,把握其内在的规律,另一方面又把这种规律归诸于人的内心,强调推己及人。前者值得肯定,后者有待商榷。不过,即使归诸内心,它的目的还是要把握人的思想、心理与性格的特点与规律,而这正是叙事作品创作所需把握的重点之一。而且,在具体的评点中,“格物致知”在金圣叹那里也往往用来指对客观事物的考察。因此,宽泛地说,金圣叹的“格物致知”是作者把握包括人的主观精神在内的外部世界的重要方法,主要是相对于作者之外的客观世界说的。
与“格物致知”相对,金圣叹的“亲动心”说则主要是针对作者的主观世界而言。《水浒》第55回,金圣叹称赞施耐庵写豪杰像豪杰,写奸雄像奸雄,写淫妇像淫妇,写偷儿像偷儿。人们说,“非圣人不知圣人。然则非豪杰不知豪杰,非奸雄不知奸雄。”施耐庵能够写好豪杰与奸雄,还可以说他身上兼有豪杰与奸雄之气,然而,他肯定不是淫妇,也不是偷儿,他又怎么能够“写淫妇居然淫妇,写偷儿居然偷儿”呢?金圣叹经过思考,得出结论:“谓耐庵非淫妇非偷儿者,此自是未临文之耐庵耳。夫当其未也,则岂惟耐庵非淫妇,即彼淫妇亦实非淫妇;岂惟耐庵非偷儿,即彼偷儿亦实非偷儿。经曰:‘不见可欲,其心不乱。’群天下之族,莫非王者之民也。若夫既动心而为淫妇,既动心而为偷儿,则岂惟淫妇偷儿而已。惟耐庵于三寸之笔,一幅之纸之间,实亲动心而为淫妇,亲动心而为偷儿。既已动心,则均矣,又安辩笔点墨之非入马通奸,笔点墨之非飞檐走壁耶?经曰:‘因缘和合,无法不有。’自古淫妇无印板偷汉法,偷儿无印板做贼法,才子亦无印板做文字法也。因缘生法,一切具足。是故龙树著书,以破因缘而弁其篇,盖深恶因缘;而耐庵做《水浒》一传,直以因缘生法为其文字总持,是深达因缘也。夫深达因缘之人,则岂惟非淫妇也,非偷儿也,亦复非奸雄也,非豪杰也。何也?写豪杰、奸雄之时,其文亦随因缘而起,则是耐庵固无与也。或问曰:然则耐庵何如人也?曰:才子也。何以谓之才子也?曰:彼固宿讲于龙树之学者也。讲于龙树之学,则菩萨也。菩萨也者,真能格物致知者也。”[6]现实生活中的施耐庵当然既非淫妇也非偷儿,但在创作的时候,他却可以设想自己是淫妇、是偷儿,从而体会到淫妇、偷儿的心理,了解他们的性情、特点,把握他们的习惯、言行,从而写出栩栩如生的淫妇、偷儿来。那么,为什么施耐庵将自己设想为淫妇、偷儿,就能知晓淫妇、偷儿?金圣叹仍是用“因缘生法”来解释。世上的道理都是一样的,深达因缘的人,自然能够通过“亲动心”把握到淫妇、偷儿、奸雄、豪杰等一切类型的人。那么,为什么施耐庵“亲动心”就能把握,而其他的人“亲动心”则不一定能够把握呢?联系到金圣叹其他的论述,这是因为施耐庵“十年格物一朝物格”,通过“格物致知”达到了因缘的深处,而一般的人没有下他那样的功夫,也没他那样的才华,自然也就难于像他那样格物致知,难于达到他那样的境界。这样,金圣叹就根据自己理论体系,阐明了他的“亲动心”说。
用今天的话说,“亲动心”就是创作时的设身处地,化身为自己要描写的人物,体察他们可能具有的思想、性格、习惯、言行,并加以适当的想象,从而写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而“因缘生法”是作者体察、想象的依据,“格物致知”则是作者能够把握“因缘”也即事物的本质与规律的基础与保证。
“格物致知”与“亲动心”是金圣叹关于作家创作的两个重要理论。前者主要从客观方面说明了作者认识、把握大千世界的方法与途径,强调观察、研究、了解事物的重要性。后者主要从主观方面说明作家创作时的一种重要心理现象,指出作家把握世界、塑造众多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因缘生法”则将两者联系起来,由此形成金圣叹作家创作论的主体框架。
此外,金圣叹还探讨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问题,提出写好当前的主张,等等。金圣叹在创作方面的思想是比较完整的,有一定的系统性。对这一方面,我们以前注意不够。本文抛砖引玉,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探讨,以期获得更多学者的注意。
[1]黄 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2]金圣叹点评,周锡山编校.贯华堂第六才子书《西厢记》[M].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09.
[3]金圣叹,李卓吾点评.水浒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9.
[4]杨合林,张 红.追踪飘忽的“文学性”——读川合康三教授《终南山的变容》[J].中国文学研究,2010,(1):17.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曹方人,周锡山标点.金圣叹全集:第一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5.
(责任编校:谭容培)
Study on Jin Shengtan’s Literary Creation Thought
ZHAO Yan-qiu
(College of Liberal Arts,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There are a lot of thoughts to which we ought to pay attention in Jin Shengtan’s theory of literary creation.On the basis of fiction,he put forward“no writing which is the same with reality”.He discussed the psychology agents of literary cre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writing work for hate”,“delicate thoughts and beautiful writing”,“amusing oneself by creating wonderful masterpieces”.He discussed how writers realized world and created images by discussing“studying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in order to acquire knowledge”and“placing oneself in other position”.These thoughts still have certain significance of inspiration.
Jin Shengtan;literary creation;writer
I206.1
A
1000-2529(2010)04-0106-05
2010-01-0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古代叙事思想研究”[03BZW004]
赵炎秋(1953-),男,湖南邵阳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