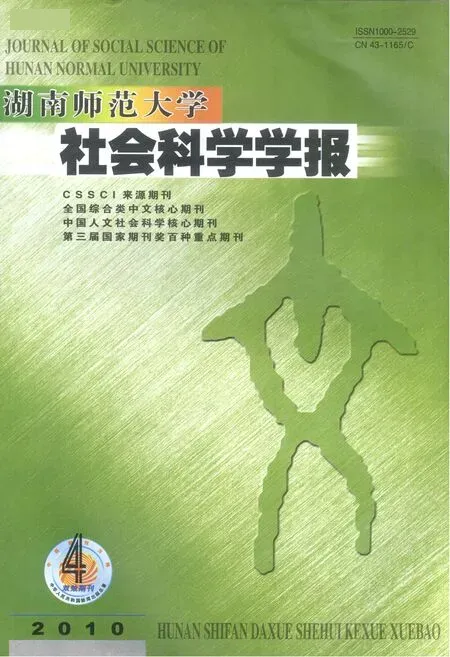论庾信入北儒士情愫的复归
周 悦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论庾信入北儒士情愫的复归
周 悦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庾信萧梁时期纯文人气质彰显,入北以后儒士情愫复归,由纯文人气质向儒文兼备的气质转化。其表现为:家国败亡的沧桑巨变激发他对历史和现实作出深刻的反思,唤起他作为儒士的强烈的功业意识,也促使其对儒家伦理的回归。入北以后庾信固有的文人气质又影响北方本土士人价值取向由重儒向慕文转变。庾信和北方本土士人气质呈反向改变而共同趋向于儒文兼备,成为南北融合的表现与成果。
庾信;入北;文人气质;儒士情愫;南北融合
考察南北文学融合之轨迹,南北朝后期由南入北的庾信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考察对象。作为“穷南北之胜”“集六朝大成”者,庾信一生以入北为界,前后期江南关中异处,仕梁荣恩华贵与仕周羁旅困顿境遇迥然有别。①其个人行径与文学作品的复杂矛盾和丰富意蕴引起后人众说纷纭的评判。如唐代人孙元晏叹息:“苦心辞赋向谁谈,沦落周朝志岂甘。可惜多才庾开府,一生惆怅忆江南。”②晚唐崔途《读庾信集》则云:“四朝十帝尽风流,建邺长安两醉游。惟有一篇杨柳曲,江南江北为君愁。”上述两诗一唏嘘慨叹一讥刺嘲讽,正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好其文乃及其人者,论心而略迹;恶其人以及其文者,据事而废言。”③庾信于梁元帝承圣三年(公元554年)四十二岁时以梁使者身份聘于西魏,这一年西魏攻梁。据《太平御览》卷三百零六引《三国典略》载:“周遣常山郡公于谨率中山公宇文护,大将军杨忠等,步骑五万南伐。太祖饯于青泥谷。时庾信来,未返。太祖问之曰:我遣此兵马,缚取湘东,关西作博士,卿以为得不?信曰:必得之,后王勿以为不忠。太祖笑而颔之。”江陵陷落后,庾信被留长安仕西魏北周,从此入北不遣。从上述记载来看,庾信的回答见风使舵,纯然迎合宇文泰心意,毫无聘使作为儒家士大夫之忠君士节可言,因而招来后人诟病。但也是特定情境中的无奈选择。表面上看,庾信淡薄的忠君士节意识和迎合北方统治者的政治态度,使得他能够被西魏北周君臣士子普遍接纳,而实际上内心深处的“夷夏”正统观念使他基于失身异族的屈辱感而生亡国之痛,故国之思,这成为他后期创作中的情感主要基调。然而,在真实的现实处境中他又不得不维护宇文氏政权,取悦王室成员如滕赵诸王,建立新的人际关系,谋求仕途上的发展以安身立命。入北庾信创作中显性的改变,最为突出的是由萧梁时期的纯然绮丽而变为融入沉雄苍凉的风格。这一点被后人广泛关注,已有学者深入论及。在庾信因入北不遣的诸多变化中,还有人所未及而尤可注意者是庾信个人气质的改变。具体而言即是由纯文人气质向儒文兼具的气质转化。这种变化可从后期一些诗赋的题材选择情感表现中获知,亦可从其他的文体类别中感悟。本文试图立足于儒文之渗透转化视角来观照庾信入北致个人气质的改变,就庾信入北之“儒化”作一点探讨。
立足于学术文化儒文对举的基础上,学术文化的拥有者文士个体气质亦可儒文对举。④文士群体分化为儒生和文人。以此观之,则萧梁时期庾信的纯文人气质彰显。
一、庾信早期的儒学修养与文人角色
庾信曾自叙其家世:“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禀嵩、华之玉石,润河、洛之波澜。居负洛而重世,邑临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艰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墙壁,路交横于豺虎。值五马之南奔,逢三星之东聚。彼凌江而建国,此播迁于吾祖。分南阳而赐田,裂东岳而胙土。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水木交运,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文词高于甲观,模楷盛于漳滨。”⑤可见他出生于一个儒学底蕴非常深厚而又儒文并重的家庭之中。《北史·庾信传》云:“信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说明他早年就深受儒家经典的熏陶。虽然生活在堪称儒学复兴的萧梁时期,本人对儒家经典也有研习,但是庾信不属于经学家,不以经学著称。⑥事实上,与两汉魏晋和北朝相比较而存在的南朝儒学更多的是立足于学术层面和影响个体人格修养,因而萧梁时期儒学对于庾信而言,更多的只是作为一种文化价值传统成为个人必备学养的一部分。同时,与齐梁时期的士大夫一样,庾信留心典籍也不过是为创作中的隶事用典之所需,并不曾接受儒家的经世致用和道德准则方面的内容。而且,庾信的声望也不因政治上的作为与军事上的才干,可以说他毫无政治上的经邦治世才干和军事上的谋略才能⑦。庾信仕途上的平流进取主要依赖世袭的家族声望和个人的文学才华,《周书·庾信传》说:“既有盛才,文并绮艳,故世号为徐庾体焉。当时后进,竞相模范。每有一文,京都莫不传诵。……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于东魏。文章辞令,盛为邺下所称。”因而萧梁时期的庾信尽管精通儒学,长于史学,具有广博而精深的文化素养,也有仕宦统兵经历,但是,他所显示出来的仍然主要是纯文人的个人气质。就他个人身份而言,既非沉潜学术的经生,也非经纶世务的儒者,而是舞文弄墨驰骋文辞的文人。作为文人,又生当承平之际,因而他的日常生活就是侍宴侍游,奉和应制。正所谓:“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廊庙之下,不知有战阵之急。”⑧其萧梁时期的创作正是这种优游逸乐生活的反映,如有名的《奉和山池》一诗:“东宫多暇豫,望苑暂回舆。鸣笳陵绝浪,飞盖历通渠。桂亭花未落,桐门叶半疏。荷风惊浴鸟,桥影聚行鱼。日落含山气,云归带雨馀。”作为奉和之作,无所谓个人真情实感流露,纯然是描摹细致精美清新的篇章。又如与萧纲唱和的《七夕》诗:“牵牛遥映水,织女正登车。星桥通汉使,机石逐仙槎。隔河相望近,经秋离别赊。愁将今夕恨,复著明年花。”吟咏牛郎织女长年隔河相望只能一夕相会的爱情传说,这不过是晋宋以后文人经常歌咏的题材。“隔河”两句由空间阻隔联想到时间绵长,情韵悠然,显然是从古诗十九首中“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化出。⑨即以赋而言,《春赋》《七夕赋》《灯赋》《对烛赋》《镜赋》《鸳鸯赋》《荡子赋》也都是奉和酬唱之作,驰骋文辞,流光溢彩,但题材选择皆无涉于社稷政治,情感表现亦无儒家士大夫家国情怀,偏于哀怨轻艳,更多的是在一种审美理想指导下的普泛的情感再现。
二、庾信入北以后儒士情愫的复归
然而,入北以后,国破家亡羁旅异域的悲惨经历促使其儒家士大夫情怀被激发,南朝时期深隐于心的儒家文化价值取向开始深深地影响到他的立身处世和人生追求,导致他的个人气质有着明显的“儒化”倾向。他开始注目于社稷江山、现实政治,反思梁朝败亡历史,谋求在现实的仕途际遇中有所作为。相对而言,唯务吟咏的文士特质有所淡化。这种转化可以从其《拟咏怀》《哀江南赋》《枯树赋》《伤心赋》等诗赋及一些碑表类文体中获知。可以说,就庾信个人身份而言,入北后的庾信儒士与文人双重角色兼备。虽则文仍是庾信赖以受尊敬的根基,但随着他对社会历史人生认识与体验的加深和士人、儒士意识的强化,在他身上便自觉地形成了儒与文的融合。具体而言,入北庾信儒士角色意识强化之表现可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1.家国败亡的沧桑巨变激起他对历史和现实作出深切的反思
从其入北以后的诸多创作,尤其是入北之初近十年的创作中,我们可以明确地感受到他那种忧时伤国的深重情怀。透过那些血泪浸染的文字,我们可以看到庾信对于他前半生优游期间的那个繁盛承平的萧梁王朝的深情眷念,对于梁王朝五十年江表无事而竟至于一朝倾覆的沧桑巨变的沉痛反思。如《拟咏怀》其十一:
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啼枯湘水竹,哭坏杞梁城。天亡遭愤战,日蹙值愁兵。直虹朝映垒,长星夜落营。楚歌饶恨曲,南风多死声。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
从其沉哀悲怨的情调中可以看到对于江陵陷落君臣被戮的凄惨情状的无比痛惜。《拟连珠》其九:
盖闻彼黍离离,大夫有丧乱之感;麦秀渐渐,君子有去国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犹瞻灞岸;德阳沦没,非复能临偃师。
其十四:
盖闻死别长城,生离函谷,辽东寡妇之悲,代郡霜妻之哭。是以流恸所感,还崩杞梁之城;洒泪所沾,终变湘陵之竹。
这其中倾泻出来的是对于国破家亡百姓流离的深重慨叹。而尤其富有惊世骇俗的震撼力量的则是《哀江南赋》。
作为以赋述史的鸿篇巨制,《哀江南赋》以哀江南命题,取意于宋玉《招魂》:“目极千里兮伤心悲,魂兮归来哀江南。”和屈原《招魂》:“目极千里兮伤春心,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庾信对于他早年生活的江南萧梁王朝,盛极而衰一朝败亡那一段风云变幻的历史所作的全面观照与深刻反思。是庾信儒家士大夫情怀被激发,进而在神圣的历史使命感和强烈的现实责任感驱使之下构造出来的饮声泣血之作。如描写江陵陷落时百姓流离失所的凄苦情状:
水毒秦泾,山高赵陉。十里五里,长亭短亭。饥随蛰燕,暗逐流萤。秦中水黑,关上泥青。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况复君在交河,妾在青波。石望夫而逾远,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忆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阳亭有离别之赋,临江王有愁思之歌。别有飘摇武威,羁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温序死而思归。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
这段文字借助于萧条昏暗荒芜苍凉之景,又罗列出众多的典故,渲染出一股浓重的去故离乡之悲。而对于这一场突如其来的悲剧原由,赋中作出了深刻的反思:
天子方删诗书,定礼乐,设重云之讲,开士林之学。谈劫烬之灰飞,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鱼齿,城危兽角。卧刁斗于荥阳,绊龙媒于平乐。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
从这一派文恬武嬉的景象描写中,隐然透出对梁武帝“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履霜弗戒”(《南史》)的尖锐批评,也表露出对那些临难苟免不负责任的百官大臣的无情指责。毫无疑问,《哀江南赋》特别集中而典型地显示出庾信作为儒家士大夫注目于国运兴衰的入世情结,可以看作是其由纯文士气质向儒文兼备气质转化的鲜明标志。
2.儒家的功业意识被激发
入北后庾信不仅注目于国运兴衰,反思现实,而且始终自觉将自我融入现实之中,尤为看重自我价值,体现了强烈的儒家功业意识。“若夫立德立言,谟明寅亮。声超于系表,道高于河上。”可见儒家的“三不朽”理念在他心目中的影响。在《哀江南赋》中说:“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为族;经邦佐汉,用论道而当官。”“家有直道,人多全节,训子见于纯深,事君彰于义烈。”在追述其家世时,尤为称道家族世功。“王子滨洛之岁,兰成射策之年。始含香于建礼,仍矫翼于崇贤。”“侍戎韬于武帐,听雅曲于文弦。乃解悬而通籍,遂崇文而会武。”在回顾自己的仕宦经历时,一方面炫耀自己的笔墨谈吐,尤为标榜的则是自己任兼文武立功立言的光荣历史。“护军慷慨,忠能死节。三世为将,终于此灭。济阳忠壮,身参末将;兄弟三人,义声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丧。”叙述抗击侯景战争中的将领韦粲、羊侃、江子一兄弟三人,对他们的“慷慨”“忠壮”表示由衷的敬佩,字里行间流露出庾信对建功立业的尤为推崇。“信生世等于龙门,辞亲同于河洛,奉立身之遗训,受成书之顾托。昔三世而无惭,今七叶而始落。”叹息先世之德降及己身而至于衰落,其实是对自己出使西魏不达使命反而屈仕敌国的痛悔与愧疚。儒家要求“使于四方,不辱君命”,以这种儒家准则来检讨自己,则不仅无功可言,反而铸成遗恨终身的过错。因而感慨“其面虽可热,其心长自寒。”继而叹息:“惟忠且为孝,为子复为臣。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深感人事既尽,身存名灭。因此,“壮情已消歇,雄图不复申。”而事实上,入北以后,庾信既不曾闭门匿智,也没能归隐园田,在二十八年的仕北生涯中,在其强烈的功业意识支撑下,始终谋求在现实的境遇中有所作为。从其入北之初的一些作品来看,人们普遍关注到的亡国之痛、乡关之思、羁旅之苦并没有消解庾信的功业意识。554年冬作《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555年或556年作《小园赋》,557年作《哀江南赋》、《伤心赋》,555年到557年之间作《和张侍中述怀》,558年作《思旧铭》,560年作《枯树赋》、《拟连珠四十四首》,563年作《竹杖赋》、《拟咏怀二十七首》中若干。它们是庾信尤其情感激荡的作品,突出地反映出庾信的真实心声,其中流露出来的儒家功业意识非常明显。如《奉和永丰殿下言志十首》,是与梁故永丰侯萧的唱和,诗中反复表白的是建功立业显身扬名的强烈愿望。如“立德齐今古,资仁一毁誉”(其一),“帐幕参三顾,风流盛七舆”(其二),“大夫伤鲁道,君子念殷墟”(其三)。尤其是其八:“弱龄参顾问,畴昔滥吹嘘。绿槐垂学市,长杨映直庐。连盟翻灭郑,仁义反亡徐。还思建邺水,终忆武昌鱼。”诗中追忆早年出入禁闼,享誉承恩,虽然身经离乱,仍旧系念江南。结尾两句,透过乡关之思,可以体会到在梁元帝父子生死未卜之际,作为一介使臣,他依然渴盼有所作为。在六十句的言志抒怀长诗《和张侍中述怀》中,我们固然看到梁朝太清、承圣之乱后,屈仕敌国的庾信悲凉与自责的心态意绪:“操乐楚琴悲,忘忧鲁酒薄。”“惟有丘明耻,无复荣期乐。”然而诗的结尾几句却流露出对未来的热切期望:“生涯实有始,天道终虚橐。且悦善人交,无疑朋友数。何时得云雨,复见翔寥廓。”对有朝一日重振旗鼓,翱翔于寥廓蓝天充满了真切的向往,诗中用世之志坦然表露无遗。
其实作为一介文士,现实生活中的庾信既谈不上有何为政的才干,也缺乏统军的方略,但是在他入北之初的作品中,却一再突出自己的军事才能,如《哀江南赋》中说:“乃解悬而通籍,遂崇文而会武。居笠毂而掌兵,出兰池而典午。论兵于江汉之君,拭玉于西河之主。”“谬掌卫于中军,滥尸丞于御史。”而且在诗文中总是自称为将军,如“岂知灞陵夜猎,犹是故时将军;咸阳布衣,非独思归王子。”《拟咏怀》中:“空营卫青冢,徒听田横歌。”叹息自己不能如卫青征战,起冢庐山;又不能学田横五百壮士俱死海岛。从这些情感抒发中皆可透视到庾信强烈的功业意识。“眼前一杯酒,谁论身后名”,这表面上是在于消解功业意识,实际上恰恰说明自己没能建功立业的恨憾萦系于心,无法解脱。
就庾信入北以后的仕历来看,滕王宇文過的《庾信集序》中叙及的庾信仕历,特别突出弘农郡守、司宪中大夫、洛州刺史、司宗中大夫四个职位,这是他入北二十八年所担任的较为重要的官职。据鲁同群《庾信入北仕历及其主要作品的写作年代》一文考证,庾信任弘农郡守是564年,已是他入北十年以后,公元564年到575年间,他是断断续续奔走在各个军幕之中。任司宪中大夫是575年底,入北二十一年后。任洛州刺史是在576年,入北二十二年以后。任司宗中大夫是578年,已是入北二十四年以后。大象初,公元579年以疾去职。可以说,他真正通显要从575年任司宪中大夫时开始,他在《正旦上司宪府》一诗中说:“孟门久失路,扶摇忽上抟。栖乌还得府,弃马复归栏。”颇有仕途久失意而终于达到追求目标的欣慰之意。可见功业追求贯穿庾信入北始终。
与其他入北文士相比,庾信也有着超乎他人的功业追求。如和他同样文名享誉的王褒,美丰仪,览史传,工属文,而儒士情怀和功业追求则相对淡薄。王褒入北后的作品,诗歌情感悲哀,风格质朴,缺乏庾信诗中的沉痛激愤和遒劲风骨。他的骈文中也更多的是学力和技巧的展示而不是个人真情实感的倾泻。因而有“荷恩眄忘羁旅”之评。这其中当然有个性差异和处境差别的原因。
3.儒家伦理观念的回归
在庾信的后期作品中,我们首先能透视到的是儒家忠节观念导致其强烈的耻感意识。江陵陷落以后,转瞬之间庾信由萧梁使臣沦为北周羁臣,屈仕敌国。昔日的风流倜傥志得意满荡然无存,这种处境身份地位的顿然改变是庾信不得已的痛苦选择。在“事主则忧亲,求生则虑祸”忠孝难全的两难困境面前,效忠于梁室的节义观念最终让位基于孝道的保家护亲情结。而这一无奈的选择带给庾信的是萦系于心挥之不去的恨憾。他长时间为自身不达使命,蒙羞失节,且屈仕敌国的行为痛悔愧疚,毫不留情地将自己的灵魂送进传统的儒家道德法庭拷问。在《哀江南赋》中他念念不忘自己“畏南山之雨,忽践秦庭;让东海之滨,遂餐周粟。”《拟咏怀》中反复叹息:“惟忠且惟孝,为子复为臣。一朝人事尽,身名不足亲。”(其五)“在死犹可忍,为辱岂不宽。古人持此性,遂有不能安。其面虽可热,其心长自寒。”(其二十)《拟连珠》中通过假喻沉痛地表述:“盖闻卷施不死,谁必有心;甘蔗自长,故知无节。”(其三十八)“盖闻执圭事楚,博士留秦;晋阳思归之客,临淄羁旅之臣。是以亲友会同,不妨怀抚凄怆;山河离异,不妨风月关人。”(其二十六)在《枯树赋》中慨叹:“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拔本垂泪,伤根沥血。火入空心,膏流断节。横洞口而欹卧,顿山腰而半折。文斜者百围冰碎,理正者千寻瓦裂。载瘿衔瘤,藏穿抱穴。木魅,山精妖孽。况复风云不惑,羁旅无归,未能采葛,还成食薇。沉沦穷巷,芜没荆扉。既伤摇落,弥嗟变衰。”透过这段声泪俱下的倾诉,一方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作为羁臣失国丧家流落异域的离愁别恨,另一方面从“采葛”“食薇”中可知其引伯夷叔齐之事自喻,表达既屈节魏周又不能畏讥避谗的内心矛盾。正如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三十三所说:“北朝羁迹,实有难堪;襄汉沦亡,殊深悲恸。子山惊才盖代,身堕殊方,恨恨如忘,忽忽自失。生平歌咏,要皆激楚之音,悲凉之调。”其悲凉痛苦的情感流露,根源之一乃是儒家的忠节观念。
庾信对儒家伦理思想的推崇,还表现在以仁义礼智信的儒家伦理观念作为评价人物的标准。尤可注意的是《拟连珠》四十四首,历历贯珠,假喻达旨,评论人事物理,特别标榜的是儒家之忠信仁义。如“盖闻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内,芬芳可录。”(其三十一)“盖闻虚舟不忤,令德无虞,忠信为琴瑟,仁义为庖厨。”(其四十三)同时也表达了对许多历史人物的评价,如称颂孔子和伯夷叔齐的安贫有节,守死善道:“盖闻悬鹑百结,知命不忧;十日一炊,无时何耻。是以素王之业,乃东门之贫民;孤竹之君,实西山之饿士。”(其二十九)又如“盖闻君子无其道,则不能有其财;忘其贫,则不能耻其食。是以颜回瓢饮,贤庆丰之玉杯;子思银佩,美虞公之垂棘。”(其四十)以颜回之乐道而贫对比庆封虞公之不义而富,明确赞扬君子好道。对当代人物的评价中,亦可见庾信持有同样的评判标准。如《周使持节大将军广化郡开国公丘乃敦崇传》中称颂:“崇清净为政,廉明为法,人不忍背,吏不忍欺。”“仁义礼节,是所用心,缇帙缃素,爱玩无已。”特别是墓志碑铭一类文体,更集中体现了庾信评价人物莫不取法儒家伦理标准。
如《周上柱国齐王宪神道碑》中评价宇文宪:“用之作宰,则万方协和;用之抚军,则四表慑伏。岂直皋繇为士,国无不仁;随会为卿,民无群盗。爱玩书籍,敦崇礼乐。”
《周太子太保步陆呈神道碑》评陆季明:“公仪表外明,风神内照,器量深沉,阶基不测。事君惟忠,事亲惟孝,言为世范,行为士则。”
《周大将军司马裔神道碑》称颂“公资忠履孝,蕴义怀仁,直干千寻,澄波万顷。”标榜“孝家忠国,扬名显亲。”
《周柱国大将军长孙俭神道碑》中说:“公以五常蕴智,六气资德,……直心于物,水火恬然;无负于天,雷霆不惧。”
庾信的墓志碑铭均作于入北后期。自周武帝保定三年(563年)出为弘农郡守以后,自保定五年(565年)始,文名日盛的庾信创作了大量的墓志碑铭。其中虽不乏谀墓之辞,但我们仍可看出儒家伦理在他心目中已然根深蒂固。这从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本人儒士意识之强化。
三、入北庾信气质转化的意义
身经变故由南入北的经历,使庾信成为南北文化环境综合影响下融合的标本:由纯粹文人进而成为儒文兼备的士人。而这正是士人普遍推崇的类型。即颜之推尤其推崇的“上品”。《颜氏家训·勉学》中论及南北儒士兼通文史的情形说:“学之兴废,随世轻重。汉时贤俊,皆以一经弘圣人之道,上明天时,下该人事,用此致卿相者多矣。末俗已来不复尔,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施之世务,殆无一可。故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梁朝皇孙以下,总卯之年,必先入学,观其志尚,出身已后,便从文史,略无卒业者。冠冕为此者,则有何胤,刘献,明山宾,周舍,朱异,周弘正,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绦等,兼通文史,不徒讲说也。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野闲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在颜氏看来,那些好经术擅文章儒文兼备者方为“上品。”庾信以一介文士不仅研习儒家经典,并且入北后儒家士大夫情怀被激发,以此衡量,庾信入北以后无疑晋升为“上品。”与此同时,他固有的文人气质又影响北方本土士人气质由偏重于儒士而逐渐强化文人气质。庾信带着萧梁时期所形成的绮丽文风入北,即刻风靡朝野,引发“效庾”现象,并且绵延长久,导致北方本土士人价值取向改变,争相向慕南方华美绮丽文风。如北方本土文人李昶一方面认为:“文章之事,不足流于后世,经邦致治,庶及古人。”⑩看重经邦致世似乎不以文章为意,而实际上他的诗却有意追求文采与南朝文人之作无异。如《奉和重适阳关》:“衔悲向玉关,垂泪上瑶台。舞阁悬新网,歌梁积故埃。紫庭生绿草,丹樨染碧苔。金扉昼常掩,珠帘夜暗开。方池含水思,芳树结风哀。行雨归将绝,朝云去不回。独有西陵上,松声薄暮来。”这首诗没有明示奉和的对象,似是奉和赵王宇文招或滕王宇文过之作。而他们都与庾信过从甚密,接受庾信影响理所当然。《周书·赵僭王招传》则明确的说:“学庾信体,词多轻艳。”滕王宇文过《庾信集序》更是模仿庾信的骈文,雕章琢句文辞华美。《隋书·柳巧传》中也说:“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可见隋炀帝亦曾倾心于庾信的文风。事实上,从庾信到柳巧到隋炀帝有着一以贯之的承传。在庾信与庾季才等享有盛誉的入北文士集会游赏时,柳巧是作为后进而随同申游者,⑪这些群体活动中的人员声气相投,柳巧耳濡目染,文风自然承袭王庾。又柳巧对隋炀帝影响很大,是隋炀帝师法和看重的文学宠臣,《隋书·柳巧传》:“王好文雅,招引才学之士诸葛颖,虞世南,王胄,朱等百余人以充学士。而巧为之冠,王以师友处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润色,然后示人。尝朝京师还,作《归藩赋》,命巧为序,词甚典丽。初,王属文为庾信体,及见巧以后,文体遂变。仁寿初,引巧为东宫学士,加通直散骑常侍,检校洗马。甚见亲待,每招入卧内,与之宴谑。……由是弥为太子之所亲狎。炀帝嗣位,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与同榻共席,恩若友朋。”由此可见北方本土士人气质由好儒向慕文转化,儒士气质弱化,文人气质强化,这中间贯穿了庾信施与的巨大影响。他和北方本土士人之气质呈反向改变而又目标一致,共同趋向于儒文兼备,这从士人个体气质塑造一个方面显示出南北融合的一些信息,同时也是南北融合的表现与成果。
注 释:
① 其实庾信入北以后仕途坎坷,并非一直“位望通显”。可参见牛贵琥《庾信入北的实际情况及与作品的关系》
② 《全唐诗·卷767.咏史诗75首之62》
③ 《管锥篇》第四册1519-1520页论及全祖望批评庾信,顾炎武批评谢灵运时说:“盖“韩亡”,“天醉”等句,既可视为谢庾衷心之流露,因而原宥其迹;亦可视为二人行事之文饰,遂并抹杀其言。”
④ 参见李生龙师《儒家文化与中国古代文学》一书第三编《历代儒文之互渗与冲突》)
⑤ 《哀江南赋》
⑥ 据夏增民《南朝经学家分布与文化变迁》一文认定为经学家须依据三个标准:一是有经学著作;二是曾聚徒教授;三是曾在国子学和东宫任教职。满足此三个标准其中之一者,即认定其为经学家。他收录南朝99人作为研究对象,而庾信并不在此列。
⑦ 《周书·庾信传》:“侯景作乱,梁简文帝命信率宫中文武千余人,营于朱雀航。及景至,信以众先退。”这一事件在《通鉴》卷一百六十一的记载更为详细:“辛亥,景至朱雀杵南,太子以临贺王正德守宣阳门,东宫学士新野庾信守朱雀门,帅宫中文武三千余人营杵北。太子命信开大杵以挫其锋,正德曰:“百姓见开杵,必大惊骇。可且安物情。”太子从之。俄而景至,信率众开杵,始除一舶,见景军皆著铁面,退隐于门,信方食甘蔗,有飞箭中门柱,信手甘蔗,应弦而落,遂弃军走。”其胆怯惊慌之状溢于言表。
⑧ 《颜氏家训。涉务》
⑨ 此诗本集失收,见于《玉台新咏》卷八
⑩ 《周书·李昶传》
⑪《北史·庾季才传》云:“季才局量宽弘,术业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常吉日良辰,与琅邪王褒,彭城刘,河东裴政及宗人信等为文酒之会。次有刘臻,明克让,柳巧之徒,虽后进,亦申游矣。”
On Return of Yu Xin’s Confucian Emotions in His Northern Travel
ZHOU Yu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Changsha,Hunan 410081,China)
Yu Xin’s pure scholar temperament was manifested during the Xiao and Liang dynasties.While after return to the North,he regained Confucian emotion,and transformed from pure scholar temperament into the temperament of both the literary and Confucian culture:the vicissitudes of his conquered country inspired him to make a profound reflection on history and reality,to arouse his strong sense of contribution,and also to promote his return to Confucian ethics.Along with his return to the North,Yu’s inherent scholar temperament affecte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he local northern scholars,from highlighting Confucianism into admiring literary.The contrary transformation of Yu and the local northern scholars’temperament,tending to make them have both literary and Confucianism,was the embodiment and outcome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Yu Xin;return to the North;scholar temperament;Confucian emotion;the integration of the North and the South
I106.2
A
1000-2529(2010)04-0111-05
2010-01-05
湖南省教育厅课题“梁至唐初南北文学融合过程研究”[07C601]
周 悦(1965-),女,湖南长沙人,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校:谭容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