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拓片之一:黑的城
禾 日
即便是冬季的雨夜,我也依然选择不留宿上海,而连夜返回杭州。
远非说明我不爱这所亲切的城市,这里有我年迈的母亲,适才为她送去了足以吃半年的保健品,选料应该是精良的。也留下了不少她并不那么有实际效用的人民币。母亲有退休工资,姐姐一家住得很近,哥哥一家尽管不在同一个区,但也因为自驾车的便利隔三差五会来看她,因而,母亲的日常生活必需品永远处于供过于求状态,母亲且永远有早睡早起的习惯,自然,陪她早早地吃过晚饭,陪她唠叨过一遍一切她热爱的新老文艺明星和文艺节目,我便告辞了,独自行走于雨中的归途。
雨夜的上海彷佛是映在水中的倒影,亦真亦幻。源头不明,忽明忽暗,或远或近的光束照着透湿的马路上,可以领略到断断续续的灯红酒绿,也可以领略到几乎成涟漪状的高楼大厦。阵阵凉风吹来,密密的雨丝斜斜地打在我身上,使着装永远不会超过两件的我才意识到这分明是在冬季的户外。我只能扣上棉衬衣的风纪扣,拉好棉风衣的拉链,戴上帽子加快了脚步。
越过一个建筑工地,便是八号线地铁站了,连忙赶上刚到站的地铁。这里无风无雨,也不再寒冷。有的只是极其拥挤的乘客。我不禁困惑,这是怎样的场景?地铁何以成为如此高密度的容器?人群怎么可以如此零距离地叠加在一起呢?你的吸气里有着他的呼气。这难道就是为我的亲朋好友们始终津津乐道的邪气好白相勿要太灵光美丽不可方物的大上海吗?
高密度容器风驰电掣地一路奔跑,人民广场站到了。我要在这里换乘1号线地铁去上海铁路南站。我随人流蜂拥而出。这是一个连接多条地铁线的中转站,人流在这里实实在在地幻为浩浩荡荡的蚁族,而我又随其中的一队蚁族急切地朝1号线的方向涌流。
想必我已经深深陷于斯德哥尔摩情结之中了,我的步履节奏丝毫无异于常蚁。上了1号地铁,随着南站方向的越来越近,蚁族的密度也越来越小了。我总算可以坐下了。
无论何种情结,坐地铁是我自己的选择。因为行装轻便,我执意不让对方公家用公车送我;因为没有孩子同行,我同样执意不让侄子用家里的车送我。选择地铁或许意味着选择环保、省钱、快捷乃至不给他人添麻烦,但付出的机会成本便是舒适度,以及可以做一个特立独行的蚂蚁,以及可以做一个坐在小车后排继续想入非非的蚂蚁。
座位对面的电视版面正在播放着香艳妩媚的美女广告,似乎是关于某医院推广韩式整形的,可以彩光嫩肤,可以植入金丝,可以打毒瘤杆菌,可以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动刀,你想崛起哪一区域?你想凹陷哪一区域?“我们”无所不能,所向披靡。我不寒而栗,下意识用双手捂住头颅。就算“我们”倒贴我人民币,我还是不干,让“我们”鄙视我好了:我可真OUT!
又似乎播了几个商场年终打折的广告,邪气名贵邪气漂亮的女性服饰现在邪气便宜!买三百,送三百。这应该就是传说中的“血拼”机会吧?我的几位美女同事获悉此等信息总是两眼放光,从不打算放弃。我也时常恍惚,而今挣钱已经需要拼命了,花钱为什么还要拼命呢?但随即遭到“麾下”美女们的阶级性攻击:“我们不像你家这么多金!你当然可以去奢侈品专卖店去买当季服饰,没有人和你挤来挤去的。我们就是要血拼!”其实美女们明知道我远没有这样迷恋奢侈品,她们不过为了高擎起“漂亮一下又何妨”的旗帜而已。我和我家另一成年公民的生活志趣几乎异曲同工,简约恒定,奢华偶尔。我们端稳了的饭碗,靠的也绝不是尊容。
跟随蚁族浩浩荡荡从1号线地铁终点站走出,直接穿行于硕大的铁路南站,晕眩于这里的现代化设施,纵横交叉的钢架、整面整面的电子屏、四通八达的电梯、无处不在的标识图……
须臾,我坐的动车组启动了。再见了,上海。
此番出差其实任务及其简单,是参加一个刊物的笔会评比,由几位80后年轻人组成的编辑部以及他们的刊物显得青春肆意,才情飞扬,当然也有欠厚重,略显脂粉。以至于我情不自禁地引以为志同道合者,以为可以就此一起嬉笑怒骂,继而推杯换盏。然而,他们却用得体的礼仪和真诚的敬仰使我意识到我早已没有资格与青春和朝气为伍了,那样一个美丽新世界已经分明与我相去甚远了。
其实这么多年来,尽管我爱好也广泛,也看了一些书,并且也有些许心得,写成了些许文章。但实际上与任何一门学问来说,我都属于“野狐谈禅”,修不成正道的。也远不足以对他人有所教益。但是否我的旁门左道与奇谈怪论也或多或少对这些年轻人产生了丁点的启发呢?我完全没有自信。我也真诚地谢绝了他们今晚的招待,原本此时该去一个叫金茂凯悦酒店的地方吃日本料理的,那应该在浦东金茂大厦的56层,临窗就座,可以看见对面名叫汤臣一品的顶级楼盘。其实于消费水准而言,无论是在高耸入云处享受日本料理,亦或是对面一样充斥着城市噪音和汽车尾气的汤臣一品享受居家生活,葡萄绝对是真葡萄,只是对一个“野狐”而言,让我说一说个中滋味……唉,算了。我彻底没有底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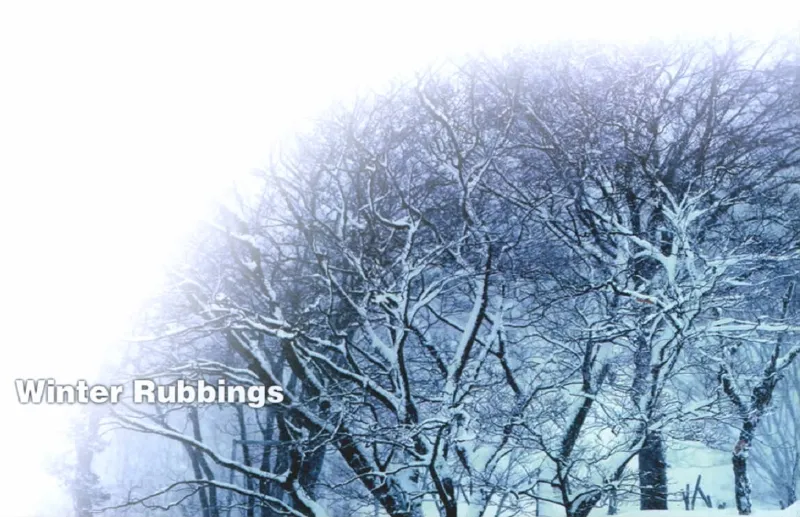
其实这里也还有许多亲切的面孔,他们有的爽直可爱,即便本次不见,下次照例可以乘兴来我们邪气偏僻的杭州乡下观赏风景,顺带视察乃至下榻啊拉邪气“下只角”的民居,顺带倾倒一车皮的知心话。风卷残云,呼啸而归。自然,即便窗外便是空山静湖,让他们久居,可就邪气勿好白相了,要闷死的。他们不能没有大上海的万种风情,他们不能放弃身为上海人的至尊地位。他们不能失去这份“腔调”。
他们有的忙碌有加,此刻要求他们接见我?不遭白眼就算邪气客气了。一定有什么有益社会的大建设构思正在他们的心海里汹涌澎湃着。我的分量显然重不过这些构思的。
当然还有他——我的挚友。同时也裹挟着我的爱,亦或是我的困惑?我渐渐相信爱是我灵魂的一部分,它比之我身上那些先升腾旋即幻灭的,一相情愿地希望挽留些什么情节的私欲更加经久不衰。它一定是我历经沧桑的情感废墟之上的常青藤,它会沿着我余留生命的残垣断壁悄然攀升的,当然也一定会跟随我的灵魂听凭尘土的召唤一同回归的。
确实没有理由留宿上海了,即便是这冬季的雨夜。那样的灯火阑珊,那样的应酬,那样的奢华,那样的拥挤,都与我无关。俗谓缘分,禅谓因缘,都一样,我的八字与此城的风水不和。
走吧。洋溢着灯红酒绿的一幢幢高楼大厦何尝不是城市为蚁民设置的一道道高墙?高墙之内是种种邪气“腔调”的迷津。自囿于此,我也会焦躁至死的,我必须突围。
普鲁斯特说:“生活在什么地方筑起围墙,智慧便在那里凿开一个出口。”同样适之于我的生活。如今,当我用感官去品鉴自己的生活,去怀疑种种“腔调”、种种高贵,种种关于幸福的诠释之时,我依旧会庆幸自己的选择,仿佛我捡拾起一颗被他人遗弃的珍珠。
杭州。雨还在下,灯红酒绿还在延展,无怪乎此地已经被称之为上海后花园了,消费文化的接轨是重要的。
杭州不算大,我的家在城乡结合地带,小区宁静如常,树木在寒风中婆娑起舞,冷雨迎面,呼出的热气随即飘散,穿过小片竹林,家便到了。当然,此种境界还远非“小隐隐于林”可攀,而我,也实在不是自由入化,智慧入化的野狐,我只是以勤奋工作换取温饱的蚁民。
哦,到家了。且让我享受一下家的洁净与温暖吧。
我的家几乎和我的衣着一样简约,我选择远离奢华,远离累赘,有些许木质的家具、些许棉布的家纺、些许同我一样生存意志坚强的植物,足矣。工作已经那么激进那么纠结那么繁杂了,余下来的生活还用得着用多余的物品层层叠加吗?做点减法不好吗?
此时尽管另一位忙碌的家庭成员和一位寄宿学校的家庭成员没有在家,但我可以为自己沏一壶好茶,正山小种,品性温和,可以暖胃。看一本好书,《季羡林散文》,一个童心未泯的老者毕生的生命感悟,一个学贯文史哲的泰斗在开垦了千亩学问良田的溪边陌上,再精心栽种的一行秀于常林的诗意棠棣。此等夜宵,实在可以算得上精良了。
如我之辈的蚁民,做减法可以,减到极致,一切皆空,还欠修炼。但至少,在冬季的雨夜,可以减去那个城市的一切,也减去这个城市的种种,因为还有来日,此时城可以是黑的,不必用那么多的能源让它亮如白昼。
只要有一盏灯,一壶茶,一本书,心便是明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