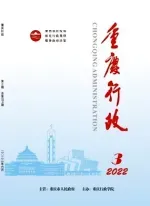高等学校与学生间法律关系的界定
□ 李晓钰
高等学校与学生间法律关系的界定
□ 李晓钰
不同的法律关系中,法律主体的权利和义务不尽相同[1]。明确界定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对保护高等学校和学生的权利、平衡高等学校和学生之间的义务、维护高校秩序以及社会稳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美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理论的演变
(一)代理父母地位说
直至20世纪60年代,“代理父母地位说”一直在美国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领域占主导地位。根据该学说在美国产生的特殊背景可知,[2]“代理父母地位”实质上就是高校代理了父母的监护职责,一方面,高校拥有像父母一样对学生的排除他人干涉的管教权,另一方面,高校也因代理的监护职责而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
(二)宪法关系说
20世纪60年代,随着“代理父母地位说”的衰落,“宪法关系说”逐渐盛行。随着19世纪后半期德国大学办学模式的深远影响,美国学生观开始发生改变,逐步符合美国宪法的基本精神,形成自由、自治、平等的核心特质,进而从法律中获得支持。[3]学生作为国家公民,享有来自宪法的基本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学校的管理行为必须保证学生的基本权利。
(三)契约关系说
“契约关系说”是“代理父母地位说”衰落后的又一主流学说,与“宪法关系说”相对,主要适用于美国私立学校,保护的是私立高校学生因私法上的契约关系享有的权利。
(四)演变轨迹评析
任何事物总是存在两面性。“代理父母地位说”被彻底取代后,走向了“纯宪法关系化”、“纯契约关系化”的反向极端,学生权利的过度扩张与高校对学生权力失控的双重作用,致使高校完全失去了监管学生的权利,从而使高校对学生受到的人身伤害不再承担责任,法院直接或间接地要求学生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在一些学生伤害案件中,法院裁决说:“现代美国大学不是学生安全的保险者。不管早期大学负有什么样的责任,当今大学管理的制度角色在最近几十年已经有了很大地削弱……以前学校管理所具有的权力已经转交给了学生。现在的大学生不再是未成年人,在社区生活几乎所有阶段,他们都被看作是成年人。”[4]
这样的结果完全偏离了高等教育的根本宗旨,完全失去社会和公众的信任和支持。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关于代理父母地位说有了新的争论。校园暴力的受害者主张,
高校有义务保障在校学生的安全。但高校则辩解说,代理父母地位说已经不再适用;高校之所以拒绝这个学说,是因为避免增加其责任。但同时,一些院校出台了有争议的诸如限制恶意言论等学生言行的规章。[5]
由此可见,不管是 “代理父母地位说”还是“宪法关系说”、“契约关系说”,对于任意一方的过分倚重,也即对任意一方的彻底否定,都不符合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根本实质。
二、德国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理论的发展
(一)特别权利关系说
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产生于19世纪君主立宪制的德国,由于它有利于实现行政管理目的、维持行政秩序,诸如日本等许多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纷纷植入。但由于它有悖于法治和人权理念,二战后,原来那些提出和植入特别权力关系理论的国家都对其进行了调整、修正和突破,主要表现为两种趋向,一种是彻底摈弃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另一种是修正特别权力关系理论,典型代表是重要性理论的提出。
在第一种趋向下又出现了另一极端倾向即法律无所不能。但实际上,存在许多领域法律并不能介入,如涉及伦理道德及日常不涉及权利义务的些微小事等等,都处于法律领域之外。因此,纵观宪法理论较为发达的国家,最终也未将特别权力关系彻底清除。
在教育领域里,特别权力理论也随着民众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和学生权利保护的日渐强势而受到置疑和批判,逐渐弱化或部分消亡。
(二)重要性理论
传统的特别权利关系遭到摈弃,修正后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依然具有浓厚的特别权力本位化色彩,因而招致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同时也遭到了司法实践领域的抛弃。因此,通过缩小传统特别权利关系的适用范围而发展出了“重要性理论”。 1972年,德国联邦宪法法院通过司法判例首次提出的“重要性理论”,其涵义是只要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必须由立法者以立法的方式而不能让行政权自行决定。因此,即使在管理关系中,如果涉及人权的重要事项,必须有法律规定。一方面,它承认了行政机关及公务法人与其成员或利用者之间的关系仍有别于普通的行政法律关系,不能完全适用法律保留原则。仍有必要赋予特别权力人(公务法人、机关)一定的管理与命令权力,这是维持公务法人正常运作的基础。另一方面,它摒弃了特别权力关系排除司法救济的传统观念,承认在特别权力关系中,只要涉及人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均应由立法规定,也均可寻求法律救济。[6]
就教育而言,“重要性”意味着只要涉及学生的基本权利,立法机关应以立法方式进行调整,并需司法介入,其它非基本权利的重要事项归入特别权力关系调整范围。
(三)发展轨迹评析
从“特别权力关系说”到“重要性理论”,不是完全的拿来主义,也不是一味的否定主义,“重要性理论”并不是对“特别权力关系说”的全盘否定,而是对“特别权力关系说”的一次发展。发展的本意是既能贯彻法治原则和人权精神,在基本权利事项上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和司法介入,同时又能照顾到高等学校此类公务法人中确实存在的特别权利关系。部分研究者也认为,重要性理论在考虑教育理念的更新和学校教育管理的实际需要上都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7]但是,由于其“重要性标准”缺乏确定性,重要事项的范围相应的也缺乏稳定性和统一性,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受到了诸多限制。
三、日本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理论的嬗变
(一)部分社会说
“部分社会说”其实质也是对“特别权力关系说”的修正,与“重要性理论”的内容无特别差异,日本最高法院避开“特别权力关系”这一用词,是为了避免直接适用已广受批判的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该学说认为,高校因其教育学生和研究学术理论的特殊目的,就法律法规未作出规定的事项自主制定规章制度,执行这些自律性规章制度与学生产生了特殊的部分社会关系,排除司法审查。
(二)私法契约说
在批判和否定“特别权力说”的背景下,由日本学者室井力提出了“在学契约说”,这一理论的提出在保护学生的权利和地位方面都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在学契约说”的第一个发展阶段表现为“私法契约说”。私法契约关系即民法上的契约关系,是高校基于教育目的为学生提供教育服务,学生支付学费,遵守学校规定而接受学校教育服务的契约关系,高校和学生双方地位平等。这种关系中根本不存在公权力的作用,是一种脱离了行政法范畴的私法关系。
(三)公法契约说
由于“私法契约说”将教育看做一种商品,认为教育活动是一种买卖交易,这种观点对于解释私立高校与学生间的关系或许可行,但对于公立高校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则有欠妥当。而且,高校的教育管理活动不可能完全地避免公权力的介入。因此,随着对“私法契约说”的修正,又出现了一种比较盛行的“公法契约说”。“公法契约说”是“在学契约说”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行政契约”理论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它认为,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公法上的契约关系,这种公法上的契约关系的属性又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法是行政法上的一部分,因此,是行政法上的契约关系,在这种关系中,虽然学校与学生地位平等,但产生的纠纷由行政诉讼或其他行政程序解决。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法是独立于行政法的一种特殊的公法,教育法上的契约关系,这种关系既非一般行政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也非单纯私法(民法)上的契约关系,而是主要契约内容采用作为特殊法的现代公教育法的结构,属于特殊契约关系的教育法独特的契约关系。[8]笔者赞成第一种观点,因为第二种观点始终没有说清楚教育法这种特殊的公法到底是什么性质,在实际操作中会造成困难。
(四)发展轨迹评析
从“特别权力关系说”到“部分社会说”,其实就是从“特别权力关系说”到“重要性理论”的发展,同德国。从“私法契约说”到“公法契约说”,体现出私法契约关系的局限性,虽然这种关系能够保障大学自治和抵御公权力的入侵,但其很难用于概括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因此,又产生了“公法契约说”。
四、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比较考察的启示
(一)“代理父母地位说”类似于我国学校对未成年学生的“监护关系说”,只是其对象为已成年的大学生
这种学说已失去了主导地位,但对它的彻底否定会致使高校完全失去了监管学生的权利,从而背离了高等教育的初衷。因此,在确立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时,不管最终定位为何种关系,高校对学生的管理关系是必须内化于其中并得到充分体现的。也就是说,应当承认高校与学生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这一点,我国的“准行政关系说”(又称为内部行政关系说)做到了,但却只偏倚了行政管理关系,漏缺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关系,仍需改进。
(二)对于公立高校与学生间的关系,美国适用“宪法关系说”,德国适用“重要性理论”,日本适用“部分社会说”和“公法契约说”
1.以美国为代表的英美法系强调的是宪法赋予学生的基本权利,非经法定程序不得剥夺,“宪法关系说”充分保护了学生合法权利,是社会民主、法治和人权保护的进步的体现。其实,这一理论对我国高校与学生间的关系理论已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部分研究者在著述中已提到了由宪法授权(以受教育权为主)而在高校与学生间产生的宪法关系,但由于我国没有专门的宪法法院或法庭,因此目前适用这一关系理论在司法实际操作中还较难。
2.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大陆法系强调的是除涉及人民基本权利事项外的其它事项纳入行政法特别权力关系范畴,排斥法律保留原则的适用和司法介入。我国的高等学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而事业单位法人与德国公法上的“公务法人”及其相似。而且,特别权力关系客观存在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领域,但在理论上却没有得到承认。特别是随着特别权力关系理论运用范围萎缩,在基本权利事项上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和司法介入,再加之该理论在某些特殊的管理关系中发挥了及时解决争议、保障正常管理秩序的积极作用,因此,这一理论在我国仍有一定的存在空间。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对于“重要性标准”的确定缺乏客观性标准,造成重要性事项的范围模糊、主观性大,仍然是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难以承认这一理论的主要原因。
3.日本还发展出了“公法契约说”,但公法契约关系仍然有其缺陷,主要是对于公法契约中高校的公权力性质未能清晰定位,而且,公法契约关系忽视了高校与学生之间的主体地位并非完全对等,如高校对学生的处分、学位证和毕业证的授予等权力具有明显的行政权力的性质,这些都是与契约原理相违背的。因此,这样的规定不但没有全面、系统地概括高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反而使得关系更加混乱。我国理论上的“教育契约关系说”与其类似,也存在同样缺陷,因而不可取。
(三)对于私立高校与学生间的关系,美、德、日三国等采用了“私法契约说”,也可以称为“契约说”
但就我国立法及实践而言,将法律教育机构定义为事业单位法人,不但规定“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而且对教育机构的适用也没有区分公立与私立,私立和公立教育机构都是公益性法人。因此,将我国的私立高校完全等同于国外的私立高校,将我国私立高校与学生间的关系完全归结为“私法契约说”,有欠妥当。但以上分析并不是完全否定私法契约关系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存在,在某些情况下,学校与学生或其家长之间确实存在着市场的自由交易行为,诸如提供膳食、寄宿、后勤,以及业余时间开展的特长培养、学习辅导活动等国家教育标准之外的项目,就可看成是一种服务,所构成的关系应视为一种基于自由交易的私法上的契约关系。但是这种观点不宜推而广之,把学校与学生或其家长之间在特定条件下形成的契约关系推广为学校领域的一种普遍关系。
五、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间法律关系的界定
根据我国理论界和实践界的经验,借鉴国外比较法上的启示,笔者认为我国高等学校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应采用“双重关系说”。
“双重关系说”认为,一方面,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表现为行政法律关系,高校在国家法律法规的授权下对学生学籍、学历、学位等方面进行管理,此时校方是以行政主体的身份出现的。就我国立法及实践而言,将法律教育机构定义为事业单位法人,具有公务性,不但规定了“不得以营利为目的举办学校及其它教育机构”,而且对教育机构的适用也没有区分公立与私立,私立和公立教育机构都是公益性法人。因此,我国的公立和私立高等学校依相关法律、法规授权行使行政管理权力的活动,应视为行政主体的活动,高等学校与学生间的法律关系为行政管理关系。另一方面,校方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又表现为民事法律关系,这种民事法律关系主要表现为侵权损害赔偿和教育合同两种债权关系。[9]
部分研究者认为,“双重法律关系说”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即对高等学校和学生这两类特殊主体之间的教育、管理、保护的法律关系的特殊性没有体现,因此提出了“教育管理法律关系说”。该说认为,依据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校方与学生之间是法定的复合型的教育管理法律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一定的隶属性,但并不同于行政机关与被管理者之间的行政管理关系;这种关系具有一定的平等性,但也不是一般的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关系。[10]
但“教育管理法律关系说”也受到了质疑。首先,这种概括根本未对高等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作出明确的判断,没有明确这种教育管理法律关系是属于行政法律关系,还是民事法律关系。显然校方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不是独立于行政法律关系和民事法律关系之外另一种独立的法律关系,而只能归结于二者之一,或者二者兼而有之。[11]其次,比较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关于校方与学生法律关系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各国法律均认为校方对学生负有教育、管理和保护义务,区别之处仅在于其范围的大小和保护程度的高低有所不同。[12]因此,这种学说无法准确解释高校与学生间关系的实质。
在我国,由于司法审判明确分为民事审判、刑事审判和行政审判,对于哪些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纳入民事法律关系、哪些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纳入行政法律关系的界定十分重要,因为这一问题未明确,法院在是否受理此类案件、以何种方式受理此类案件以及如何判决等方面都会面临着诸多问题。哪些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可纳入司法审查的范围、哪些将被司法审查排斥,只能通过归纳入不同法律关系的方法予以分类,要想通过罗列等具体方法予以界定,不具有实际意义与操作上的可行性。因此,双重法律关系说的表述比较符合我国现行教育体制、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与诉讼法律体制下的校方与学生关系的表象,这也是双重法律关系观点的产生基础。[13]
[1]孙国华.法理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5(1):375-378.
[2]李奇,洪成文.代理父母地位说:美国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主导理论[J].比较教育研究.2004(4).
[3]李明忠.美国大学生事务管理的学生观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4:43-44.
[4]李奇,洪成文.代理父母地位说:美国高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主导理论[J] .比较教育研究·2004(4).
[5]InLocoParentis, [EB].http://www.answers.com/topic/inloco-parentis.转引自方恩升.论法律视野中高校与大学生的纠纷[J].求索·2007(1).
[6]马怀德.公务法人问题研究[J] .中国法学.2000(4).
[7]于亨利、周方.高校管理中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认定研究[J].西北师大学报,2003(3):24.
[8]申素平.高等学校与学生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J]·中国高教研究·2007(2).
[9]梁馨予.论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2).
[10]孙平.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研究[J].教育与职业.2007(9).
[11]梁馨予.论学校与学生之间法律关系的性质[J].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05(2).
[12]董新良、姜志峰.对未成年学生伤害事件处理问题的再认识[J] .教育科学研究.2007(5).
[13]王晓东.谈学校与学生之间的法律关系[J].辽宁警专学报.2007(1).
重庆工商大学2008年度青年科研基金项目“构建和谐校园与高校学生意外伤害事故法律责任研究”
重庆工商大学环生学院
责任编辑:宋英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