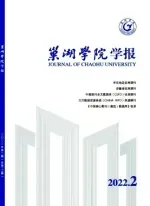新时期史家主体的学术实践与历史话语体系转型
朱玉票
(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安徽 巢湖 238000)
新时期史家主体的学术实践与历史话语体系转型
朱玉票
(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安徽 巢湖 238000)
在新时期,随着“改革开放”不断走向深入,解脱了政治束缚的史学家们获得了较为自由的学术空间,在对新的研究范式、内容体系等方面展开探索的同时,也积极对旧有的政治色彩浓厚、封闭性较强的意识形态话语进行反思与解构,一种新的多元化开放的学术性话语体系正在逐步形成。
新时期;史学主体;历史话语
新时期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变革的时代。作为学术大家庭的一员,历史学在反思与解构前期流行史学范式与方法论体系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步入了话语体系转型的进程。尽管历史话语体系转型是由新时期社会结构全面变革的整体因素推动的,但作为社会变革和学术研究主体的史学家们以其群体或个人的学术实践直接推动了历史话语的转型与重构的事实,是我们不能不加以关注和研究的。从历史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史学家主体从建国以来的学术研究经历和生活体验共同构成了史学家主体意识结构的知识基础和情感体验因素,从而使这一因素具有了独特的开放性和动态性,并随着时代演进和社会变革不断地自我更新、发展。这不断更新、发展的认知因素正是引起史家个人和群体历史认识不但变化和演进的内在结构性动因。无疑,它在新时期的诸多嬗变也必然对史学家的学术研究范式、方法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变革与转型产生结构性影响。
1 历史话语的内涵与特征
“话语”一词源于西方,大致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我国学术界流行。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其基本内涵是指一个比语句更大的语言单位(即:discourse),主要用于指称对某一内容进行形式的描述。我国学术界对这个概念的使用主要在三个领域:即语言学领域、文艺叙述学领域和多学科领域。[1]“话语”一词用于语言学领域时主要指句子、语句、言语和篇章,而用于其他两个领域时,则需要与特定的论域相结合才能够明确它的指称范围。“话语”概念引入历史学领域,通常是指史家书写与讨论历史时所用的语句、言语以及由此衍生的书写语境和表达形式,有时特指书写历史的文本和文体。
由于使用的时空与论域具有不确定性,不同时代、国家、领域乃至不同的史家往往会创造和使用不同的话语体系,因此,历史话语具有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从建国以来的历史话语演进轨迹来看,新中国的历史话语体系先后表现出“传统蕴含丰富的民族性、与政治关联紧密的意识形态性、改革开放时代的世界性和多维综合性”等特征。
2 建国以来知识分子的精神履历与话语轨迹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在建国以来的社会建设、变革与发展的大舞台上扮演了多重的角色,时而因为需要进入国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中心,时而又因为另一种需要被不断边缘化。新中国的知识分子正是在这样一个一波三折的生活与精神历程中行使着他们的学术职责,参与建构和使用着各个时代不同的历史话语。
2.1 建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与“革命”话语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因此,建国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对于建国初期的马克思主义运动,从知识分子的角度来看,恐怕就会有两重意义了。一方面,当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学人们欢天喜地地投身于马克思主义的学习、运用和建设中去的时候;另一方面,那些非马克思主义的文人们则不得不面临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要么坚持原有的主义而被淘汰或抛弃,要么委曲求全地接受改造。这是那个特殊时代的社会政治给本来可以是一个群体的知识分子们造成的强制性分裂。
在这样一个“拔白旗,插红旗”的思想论辩与改造的时代,不仅在学术界,乃至全社会都被诸如共产主义、修正主义、意识形态、辩证法、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反动派、贫下中农、合作社、大跃进、自力更生,超英赶美、以钢为纲等等“革命”味十足的话语所包裹。由于得到国家意识形态的支持,这个话语体系明显具有强势的导向性和教育意义。
2.2 “文革”十年的人格困厄与“阶级斗争”话语
文革时期,知识分子遭到了空前的命运挫折与灾难。在极端一元化的政治利益框架下,知识分子除了接受改造或批判,就只能投身到文化革命的阵营,否则,他们只能被作为反动文人遭到“肉体的消灭”。在这样一个万马齐喑的黑暗时代,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遭到 “人人洗澡”式的清查。经过这样的“文化革命”,知识分子们除了在一片改造的漩涡中陷于困厄,就只有丧失生命或蜕变为“文化革命战士”,这后两个方面的事例,可由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师、“新史学五老”之一的翦伯赞的含恨自杀与现代新儒家主将之一的冯友兰被“彻底改造”[2]为典型代表。
这是一个“斗争用语”一统天下的时代。包括历史话语在内的一切用语都以 “斗争性”作为最基本的特征,从极端到极致,体现出强烈的不宽容意味,如打倒、横扫、炮轰、火烧、砸烂等等,中华民族的汉语——这一古老优美的语言工具——在这一时期变得无比简单粗暴。除了这些暴力意味浓厚的词汇,直接能够体现斗争内容的还有红卫兵、红五类、红宝书、文攻武卫、最高指示、牛鬼蛇神、封资修、黑五类、上山下乡、斗私批修、苏修美帝、批林批孔等等。面对这样的生活环境与话语体系,负责任的知识分子只能缄默不言,忍受着人格与良心的双重困厄。
2.3 八十年代的反思、学习与“西化”话语
改革开放时代,随着西方20世纪新的思想学术不断涌入,学术界在反思、审视旧的流行史学范式及其基本命题的同时,积极学习、吸纳国外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理论方法论,掀起以新、老“三论”为代表的理论方法论探索与建构热潮,西方的学术理论与话语不断被各个领域引进和尝试运用。这些理论与话语的纯学术特性,为新时期史学界消解旧有的与政治关联紧密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起到了极其重要的导向性和实践性作用。在这样的话语体系引导和促进下,八十年代的历史话语终于突破了原来的意识形态话语框架,向着带有西方色彩的学术性话语方向转型,流行于西方世界的文化形态、社会心理、生活心态、长时段、主体性等话语也成为这一时期知识分子们口边的常用言语和书写用语。但是,由于这种理论方法论热潮没有能够带来人们期盼的丰硕成果,加之它的显著的“西化”色彩,最终还是随着八十年代末那场政治风波的平息渐渐冷却下来,代之而起的是一种更为理性的多维度学术性话语体系。
2.4 九十年代以来的理性“自省”与“多维度学术性”话语
如果说80年代的学术界因为没有新型的话语体系,在对旧的史学范式和话语进行反思与清理时,使用的话语多少保留了一些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特点,那么,到了 90年代,这种状况随着史家主体意识的增强逐步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变。
90年代的知识分子在经历了前几个年代的风雨之后,尤其是在穿过80年代的思想与理论热潮的喧嚣之后,逐渐的冷静下来,开始了理性的思维和自省。对传统文化的自觉与对西方学术的尊重及跨学科的多维度立体视野共同构成了90年代历史学的基本走向。一种不同于以往的学术意识开始觉醒,即把总结规律的任务还给哲学,而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对历史过程的具体考察上,逐步实现历史学向自身特征的复归,将活生生的历史还给历史。以往的较为单一、封闭、并具有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逐步为多维度的、传统与国际接轨的、开放性的学术话语体系所取代。
3 新时期史家主体的学术实践与历史话语体系的转型
新时期的史家在经历了建国后那段特殊时期的磨难和消沉之后,重新获得了清新自由的生活环境和学术氛围,逐步从前期学术个性的困厄走向群体的自主与独立,没有顾虑、没有束缚地思考和研究生活和学术。这一时期,史学家们跟随其他知识分子一道,经历了反思、危机、变革、学习、探索、自省与建构的全部过程,极大地丰富了自身意识结构的情感体验和知识基础因素的时代内涵,增进了自身对史学范式、方法论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探索和创新意识,增强了对传统文化和外来学术的判断力和认识能力,从而有力地推动了新的历史话语体系的建构。
3.1 解脱政治束缚:历史话语从意识形态走向学术
自建国伊始,陷于政治束缚的学术研究乃至史学家人身,不得不依附于国家政治,沦为替意识形态理论进行注疏和维护的工具,因而,也就必然地陷入了“革命话语”和“斗争话语”的漩涡。“我们的史学界与政治社会共用一套话语,而这套话语则是‘充斥着二十世纪政治与文化方面的诉求’的意识形态话语。像‘封建’、‘封建社会’、‘阶级’、‘阶级社会’、‘地主’、‘地主阶级’ 等等,以及与这些术语相关连的许多社会历史理念、若干带有全局性的重要假设,都只有在特定的意识形态语境中才有意义,远非学术语言。”[3]进入新时期以后,一方面,脱身于政治束缚的史学家们,在“自我认知”基础上不断地增强自觉、自主的探索与创新意识,积极清理和解构旧的史学范式和话语体系。同时,旧有的流行史学范式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环境和学术土壤已经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已经不复存在,存在的合法性被消解注定它只能被取代。另一方面,原来被“革命话语”和“斗争话语”所边缘化的传统历史话语与西方纯学术性的历史话语在新时期汇流,共同促进了学术色彩与特性更鲜明的历史话语体系应运而生。
3.2 吸纳西方学术:历史话语从封闭走向国际化
改革开放以前,“旧有的话语系统还成为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进行对话的一个主要障碍。我们原来使用的话语系统是外人无法弄懂的……这造成了与世界史学的隔膜,难以与别人对话。”[3]
新时期不断引进的西方学术思想与理论打破了我国学术界封闭、平静的局面,引起了理论方法论学习与探索的热潮,诸如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结构主义方法以及计量史学、心理史学、比较史学、口述史学等新的研究理论、方法和手段不仅被引进,还得到了实际运用。伴随这些理论方法论一起过来的不仅仅有思想家和著作本身,还有学术话语,譬如,当下世界流行的解构主义思潮从90年代传入中国以来,其代表思想家福科、拉康、德里达、罗兰?巴特等已经成为我们学术讲坛的常识性人物,他们的消解、颠覆、反抗、亵渎、边缘等话语,对我们的学术研究和书写策略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从而成为我国学界乃至当今世界的流行话语。
3.3 多元价值取向:历史话语从单一走向多维重组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新时期多元化的价值取向,主要表现为研究方向和选题的多维化;研究方法和手段的复合化、立体化;研究态度的理性化;研究视野的全球化等。改革开放改变了以往国家意志高于一切的以消解个体利益为前提的强制性一元化整体价值取向,一切 “以人为本”,强调对个体意志和利益的尊重,因此,所有社会成员个体和局部的利益都进入了选择的视野,价值观念呈现出动态的多元化取向。这就要求学术研究能够而且必须尊重、关注和理解多元化价值群体的利益。
新时期的史学研究从新的方法体系探索开始,逐渐将学术目光投射到社会进程、生活实践、文化传统、民众心理等各个领域,打破旧的政治、经济、阶级斗争史为主体的单调的内容和话语体系,走向综合运用方法手段、理性尊重不同学术、多维立体研究内容和具有世界眼光的跨学科开放性的史学范式,并由此重组和建构相应的话语体系。
“把历史还给历史”是我们这个时代响亮的口号和座右铭。
[1]文贵良.何谓话语? [J].文艺理论研究,2008,(1).
[2]王永江,陈启伟.评梁效某顾问[J].历史研究,1977,(4).
[3]王学典.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J].山东社会科学,2009,(1).
TRANSFORMATION OF THE ACADEMIC PRACTICE OF THE HISTORIANS AND THE SYSTEM OF THE HISTORICAL DISCOURSE IN THE NEW ERA
ZHU Yu-piao
(History Department, Chaohu College, Chaohu Anhui 238000)
With the profound development of the reform and the wide opening of the door to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new era,the historians,free of political constraints,have obtained a more academic freedom of space in the new research paradigms and content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they have also started actively the reflection and deconstruction on the old, closed and outdated ideological discourse of strong political flavor,which has inspired the formation of a new pluralistic and open system of academic discourse.
new era; historical subject; historical discourse
K061
A
1672-2868(2010)02-0108-04
2009-10-19
朱玉票(1968-),男,安徽巢湖人。巢湖学院历史旅游文化系讲师。
责任编辑:陈 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