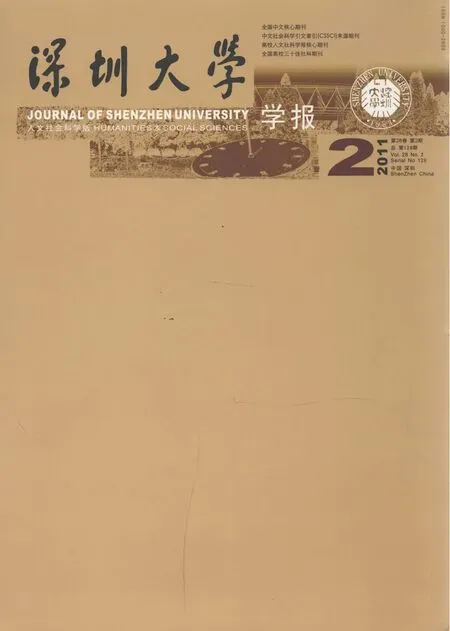生涯辅导理论本土化辨析
陈德明
(深圳大学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教研室,广东深圳518060)
生涯辅导理论本土化辨析
陈德明
(深圳大学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教研室,广东深圳518060)
生涯辅导理论本土化需要解决价值取向、目标定位、技术运用与模式选择等问题。我国在借鉴西方生涯辅导理论时应结合国情,充分考量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经济发展阶段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中西差异,着力探求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以提高“生涯适应力”为目标,灵活运用“指导”与“非指导”的辅导技术,践行“规划定向实践定位”模式。
生涯辅导;理论;本土化;辨析
发轫于西方的生涯辅导理论历经百年发展形成了诸多理论流派,如何将这些理论适用于我国并有效指导实践,本土化乃必经之路。生涯辅导理论在我国的本土化需要解决价值取向、目标定位、技术运用与模式选择等问题,而这些离不开对历史文化、价值观念、经济发展阶段与劳动力市场状况的中西差异比较,以及结合时代特点与具体国情的综合考量。
一、价值取向:“个人”与“社会”
生涯辅导理论本土化,首先是价值取向与价值观念的本土化。西方不少生涯辅导理论侧重在从个体的角度来探讨职业行为,重视个性等内在因素对职业选择与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这些理论又分为三类:以强调个人特性与职业特性相匹配的特性论模式,如特质因素论、人格类型论;以强调个人内在动机为核心的动力论模式,如需要论、心理动力论;从发展的观点来研究个体职业行为的发展论模式。尽管也有研究个人职业选择和职业发展的社会环境因素,如社会学理论、经济论等,以及综合研究个人因素和社会因素对个人职业行为的影响,如行为论和决策论等,但从总体而言,西方生涯辅导理论属于个人本位取向,这与西方价值体系的取向也是吻合的。
那么,问题就此出现了。有人认为,我国是一个长期讲求社会本位的国度,生涯辅导在我国不能再坚持个人本位不变,应该改成社会本位;也有人认为,西方生涯辅导关注个人生涯发展,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坚持个人本位更有利于个人的发展。其实,不管是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社会本位论偏重人的社会属性,个人本位论偏重人的自然属性,都有其相对真理性,但各自又都有偏颇。人是社会实践的主体,既受社会制约,是社会的生成物,同时也是社会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发展的受益者。人既需要并必然社会化,又需要并必然个性化。人是作为社会的人与作为个体的人的统一,是作为受社会制约、规范的人与作为受个体需要和追求驱动的人的统一[1]。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当一个人选择了符合社会发展大势的道路时,其个人发展就与社会发展联系起来。这正如马克思在《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所指出的:“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守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不应认为,这两种利益会彼此敌对、互相冲突,一种利益必定消灭另一种利益;相反,人的本性是这样的:人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自己才能达到完美。”[2]即使在崇尚个人本位取向的西方国家,也没有完全否定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美国著名生涯辅导学者舒伯(Super)1951年指出,“职业辅导”要可以“满足个人的需要,同时造福社会。”[3](P27)在我国,的确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非常强调社会本位的价值取向,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我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也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个体发展与社会发展并不矛盾。“以人为本”并不是对社会性的否定,而是在更扎实的基础上,通过对人本身的关注,更有效地实现其教育的社会目标。“以人为本”是教育的入口,以“社会为本”是教育的出口。二者的关系是,“以人为本”是微观性、操作性理念,是显性过程;以“社会为本”是宏观性、目标性理念,是隐性追求,它们互为前提和条件[4]。因此,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是辩证统一的,两者互为补充、缺一不可。至于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孰轻孰重,要看具体的历史条件而定。当前我国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阶段,与计划经济伴随的社会本位以及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个人本位都会同时并存。
因此,生涯辅导理论在本土化过程中,应该协调处理个人本位与社会本位的关系。首先,在设计个人发展方向时,以时代趋势、社会需要作为大的方向,从大处(社会利益)着眼,从小处(个体)着手。这是个人生涯规划得以实现的重要基础。其次,个人生涯规划要结合组织需求。组织是社会的细胞,每个人都需要在一定的组织内学习和工作,完全脱离组织需求来搞个人生涯规划或者将个人生涯规划凌驾于组织之上的做法都是不合适的。再次,在个人规划与社会利益、组织利益发生冲突时,应重视社会与组织的长远、整体利益,同时保留属于个人的合理、正当、必需的利益。
二、目标定位:“适合”与“适应”
从生涯辅导诞生之日起,“人职匹配”的理念就颇得人心。1909年,美国波士顿大学教授帕森斯(Parsons)首先提出了职业指导的三大要素:一是了解自己,包括了解个人的能力、能力倾向、兴趣、资源、限制及其他特质;二是了解各种职业成功必备的条件、优缺点、酬劳、机会及发展前途;三是合理推论上述两类资料的关系。后来,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威廉姆逊(Willialnson)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特质因素理论。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学者霍兰德(Holland)在特质因素理论的基础上创立了人格类型理论,用人格类型与职业类型之间的匹配取代了人的特性与职业因素之间的匹配,从而可以扩大人的职业选择的范围。直到今天,“适合的就是最好的”观念在人们心中扎根,乃受“人职匹配”理论的影响所致。然而,追求“人职匹配”目标的人们逐渐发现,理想与现实之间仍存在巨大的差距,特别是随着“易变性”生涯时代的来临,人们即使能找到“人职匹配”的工作也是短暂的,于是舒伯(Super)等人在1981年开始提出“生涯适应力”的概念,并逐渐成为生涯心理学理论研究的新的增长点。
那么,在我国实施生涯辅导是应该沿用“适合”(“人职匹配”)目标呢,还是选择“适应”(“生涯适应力”)作为目标?比较两者的差异,会有助于我们做出合理的选择。首先,“适合”更多体现的是一个静止的理想状态,而“适应”则体现了一种变化发展的运动状态。“人职匹配”理念的提出对个人生涯规划、组织人才选拔和配置具有重要意义,而由于时代变迁加快以及科技进步的日新月异,职业对工作者的要求也处于不断变化之中,“人职匹配”这种理想状态作为一个短期的目标尚可,要保持长期的“适合”,需要人们不断去“适应”职业发展带来的新变化。可以说,“适应”的过程,就是“去适合”的过程。其次,“适合”重视职业测评开发与结果解读,而“适应”则强调个体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为了追求“人职匹配”,人们依赖职业测评来取得较为精确的“配对”结果,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客观”的考察,但是却忽视了个体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而这恰恰是“适应”所重视并加强的方面。再次,“适合”更多的是从个体角度出发来做选择,而“适应”则考虑了个体与职业环境的互动关系。追求“适合”最常见的问题就是兴趣在生涯发展中的作用被夸大。不少大学生在学习了霍兰德的人格类型理论后一味追逐个人兴趣而置自身能力、就业形势等其它因素于不顾,过分强调了“爱一行,干一行”,导致专业思想不牢固和敬业精神更加欠缺。此外,有些大学生在选择工作时考虑的只是自己的需要,却忽视了自己是否也能满足用人单位的需要。过分追求“人之匹配”还导致出现了“频繁跳槽”和“有业不就”现象。根据国家劳动部的“第一次就业调查”报告显示,三分之一以上的大学生把第一份工作当成职业的跳板,大学生就业后一年内流失率高达50%,两年内的流失率接近四分之三。有的毕业生以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为由,宁可在家“啃老”也不愿去参加工作。比较“适合”目标与“适应”目标的现实性,还需要考察中西劳动力市场与就业制度等方面的差异性。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水平不均衡。西方国家是人少职位多,处于“人选职业”状态;我国是人多职位少,处于“职业选人”状态。西方国家就业地域间差异较小,一般是就近就业,相对选择的就业机会也多;我国就业地域间差异大,为寻求“最优”就业机会,人们往往会挤到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就业,造成就业竞争激烈。此外,我国就业制度与法制不够完善。在西方国家人们有较充分的就业选择自由,而在我国,由于各种就业歧视、招聘“潜规则”、就业信息不对称、地区就业保护壁垒等的存在,使得完全意义上的“人职匹配”较难实现。
鉴于此,我国生涯辅导不应一味强调“人职匹配”的理想化追求,而应以提高个体“生涯适应力”为现实目标。Super、Savickas以及诸多生涯决策理论的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主张“适应”是过去与现在观点差异之间最佳的整合。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适应”并非全然舍弃过去的主张,只是企图更完美地诠释我们正在经历的各种生涯现象与问题[5]。“适应”在此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既考虑职业对个体需求的满足,也关注个体对职业要求的符合。美国学者奥西普(Osipow)等指出:“当生涯有多种选择时,个体强调的是对满意度和兴趣的期待,当生涯几乎没有选择余地时,个人的能力和技能及其应用,都是个体在其生涯决策中所重视的。”[6]简言之,就是就业机会多时讲“适合”,就业机会少时讲“适应”。二是要坚持终身学习,积极行动,始终保持自己与职业发展要求的同步。
三、技术运用:“指导”与“非指导”
西方生涯辅导技术经历了从“指导”到“非指导”的发展历程。1939年,明尼苏达大学教授威廉姆逊在帕森斯(Parsons)理论的基础上形成一套独特的辅导方法,他将职业指导分为分析、整理、诊断、预测、咨询和追踪6个步骤,提出了咨询的直接建议、说服和解释3种方法。由于这套方法教导意味很重,因而被称为“指导学派”。1942,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Rogers)提出了以当事人为中心的方法,认为传统的“指导学派”过于重视咨询者的地位,提倡采取“非指导性”的技术路线,即采取不主动、不判断、不指导的“三不原则”,这使得帮助方式由“指导”向“非指导”发展,并成为生涯辅导的主流技术方法。总括而言,“指导”重视专家和权威的地位、职业素质测试的技术开发与运用,忽视来询者的作用;而“辅导”则是以来询者为中心,强调职业咨询方法与技术的运用,辅导人员的作用是协助、促进和转化。
生涯辅导应该是采用“指导”方式还是“非指导”方式,这个在国外似乎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但在我国本土化过程中却发现“非指导”式技术在应用时“水土不服”,这是由于教育文化、辅导者角色与辅导对象的中西差异造成的。首先是教育文化的差异。我国自古以来对“师者”的要求是“传道、授业、解惑”,“传”、“授”、“解”3个动词皆由“师者”而出,与“直接建议、说服和解释”的“指导”方式极为相似,这种“指导”文化源远流长,根深蒂固。其次是辅导者的角色差异。与西方国家从事生涯辅导工作者的专业人员不同,我国绝大多数的从业人员是从行政口、政工口转岗而来,除了“咨询师”的角色外,他们还是“德育教师”,“育人”是其根本职责与任务,不能采用“不主动、不判断、不指导”,否则就是放任自流。最后是辅导对象的差异。我国的学生依赖性较强,在应试教育的长期“熏陶”下对索取“标准答案”已形成思维定势,让他们自己去探索反而容易导致茫然失措。
那么,是否意味着我们还要坚持“指导”式的方法?“非指导”式方法究竟有没有可以借鉴之处?应该如何正确处理“指导”与“非指导”的关系?笔者以为,“以当事人为中心”的“非指导”方式体现了对来询者的人格尊重;不代来询者决策,而是以增强其自我负责意识和能力,提高其自我效能感和行动自主性,这符合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本质要求,更加人性化,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非指导”式的辅导方式也有其缺陷,不主动、不判断、不指导的“三不原则”这种所谓“价值中立”路线与我国的德育价值主导有冲突。学生并非成熟的个体,其价值观尚处于形成过程,如果坚持“不干预”而任其自由发展并不符合德育的发展规律;更何况,价值选择从来都不是抽象的,任何阶级社会都有其主流价值观,只有在主流价值观允许的范围内才有所谓的“自由选择”。此外,我们要考虑到我国的国情、文化特点,在充分尊重人格的前提下,也需要适当、适时使用“指导”的方式,以提高辅导的效率。舒伯(Super)也没有完全否定“指导”方式的运用。舒伯认为,生涯咨询必须同时涉及个人的理性与情绪,从而进行自我探索、作决定及现实的考验。在“谈话”的过程中,辅导人员可以通过重述、反应、澄清、摘要、解释、面质等技巧,依据个体的问题性质给予指导及非指导式的咨询。指导的方式主要用于咨询过程中汇集资料和进一步探索主题,并进行现实考验;非指导的方式强调与个体共同探讨行动方向与计划,主要用于协助个体探索问题、描述自我观念、澄清个体对自我接纳的感受、突破因现实考验而引起的态度和情绪感受[3](P63)。由此可见,“指导”与“非指导”方式并非截然对立,它们在生涯辅导中的作用是互补的。
四、模式选择:“确定性”与“非确定性”
传统生涯辅导理论强调生涯规划的技术性与可预测性,通过对各种职业测评工具的不断开发与完善来保证生涯选择的准确以及生涯规划的有效实施。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的飞速发展,人们的工作环境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人们的工作变动性也越来越大,生涯发展路径更加难以界定和预测,有人将这种新的生涯型态称之为“多变性生涯”。21世纪初,Pryo与Bright正式提出了生涯混沌理论,对经典的生涯心理学理论,如帕森斯、霍兰德以及舒伯等人的理论展开了批判。他们认为,经典的生涯心理学理论倾向于将人类生涯心理看作是确定的、理性的和合乎逻辑的,而忽略了人类生涯心理的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长期变化的难以预测性;经典的生涯心理学理论采用的所谓科学的还原论方法将人类生涯心理当作静态的,并将其还原为几个有限的关键因素,而忽略了人类生涯心理的整体性和动态性,以及人们对生涯意义的追求;人类生涯心理的发展也并非按照经典生涯心理学理论所设定的几个阶段线性的发展,而是非线性的、跳跃性的,混合着意外事件和经验。斯坦福大学教授克朗博兹(Krumboltz)等人也提出生涯的偶然性理论,指出我们要承认偶然性因素在生涯发展中的作用,但同时又不能只是守株待兔地等待好运的到来,而是要学会制造、认可,并在职业发展中利用偶然事件来为自己服务,而保持好奇、坚持、灵活、乐观、冒险等有助于我们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对许多大学生而言,实际从事一个职业要比做一个职业选择更具挑战性,因此不仅要帮助学生择业,还要培养实际工作能力。要重视实践,不仅要学会选择,而且要注重技能的养成和培训。因此,环境的“变”与个人的“应变”,成了个人生涯发展过程中应有的警觉与认识。无怪乎有的学者(Maanen&Schiein,1977)认为,“生涯之学,即应变之学。”[7]
那么,应如何看待生涯发展的“确定性”与“非确定性”呢?笔者以为,我国个人的生涯发展还是有其一定的“确定性”,表现为个人的特质与人格特征一般不会在一段时间内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每个人经历的主要生涯发展阶段与阶段性任务也大致相同,就业环境在一定时间内持续严峻与就业岗位不足也是事实,这是我们进行生涯规划的基础;同时,我们的生涯发展也面临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譬如,个人生涯发展会遇到不同的偶然事件,家庭、工作单位和社会也会发生一些变化,这些“不确定性”有些是我们可以预测或者能大致预测到的,也有些是我们意想不到的,需要我们做出应变。如果无视飞速变化的当代职业环境,过分追求所谓完美无暇的“匹配”和“和谐”,会导致陷入不切实际的“生涯规划妄想症”;而如果以职业世界的飞速变化为理由,而漠视生涯规划在生涯发展中的导向作用、凝聚作用和激励作用,游戏人生、随波逐流,那会导致“生涯规划无用论”,也是不可取的。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以为,合理处理“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关系可以采用“规划定向、实践定位”的理念与方法。所谓规划定向,就是指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确定个人的学业、专业和职业发展大方向,这时候,选择方向比盲目努力更重要;所谓实践定位,就是指在大方向确定的前提下有目的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包括实习、兼职、做项目和参加实际工作,这时候,把握机遇比固守规划更重要,要学会根据环境变化和社会期望适时修订原规划[8]。“规划定向”,解决的是“确定性”的问题,是对经典生涯辅导理论模式的继承;“实践定位”,解决的是“非确定性”的问题,是对当代生涯辅导理论模式的发展。“规划定向”中的“定向”并非一次可以完成,体现的是一定“确定性”条件下的发展方向,起到引导实践指向和激发实践动力的作用;而“实践定位”中的“定位”也同样并非一次完成,体现的是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逐步调适与动态平衡,起到夯实规划成果与把握新的发展机会的作用。“规划定向”和“实践定位”相辅相成,将生涯辅导理论的传承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当是妥善解决生涯发展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矛盾的可行模式选择。
[1]李建芹.构建德育创新理念:社会本位与个人本位的融合[J].教育导刊,2005,(4).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7.
[3]沈之菲.生涯心理辅导[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4]李艳.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整合向度[J].现代教育科学,2008,(7).
[5]赵小云,郭成.国外生涯适应力研究述评[J].心理科学进展,2010,(9).
[6]塞缪尔.H.奥西普,路易斯.F.菲茨杰拉德.生涯发展理论[M].顾雪英,姜飞月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0.229.
[8]金树人.生涯咨询与辅导[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17.
[9]陈德明.青年生涯辅导的价值取向及其局限性[J].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0,(5).
【责任编辑:湜得】
An Analysis of the Localization of Career Coaching Theory
CHEN De-m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for Occupational Development and Employment Guidance,Shenzhen University, Shenzhen,Guangdong 518060,China)
The localization of career coaching theory needs the solving of value orientation,target positioning,application of technology and pattern choices,etc.In China while we want to draw on the theory of career coaching,we should fully consider China’s historical culture,concepts on values,particular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differences in the market of human resources by combining the country’s actual conditions.Stress should be placed on the joining point of individual and societal development so as to heighten the coaching technique featured with a flexible employment of“guiding”and“non-guiding”,with“adaptability to one’s career”as its target and put into action the pattern of“oriented by a plan and positioned in practice”.
career coaching;theory;localization;differentiation and analysis
G 641
A
1000-260X(2011)02-0153-05
2010-10-22
陈德明(1969—),男,广东湛江人,深圳大学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从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生涯辅导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