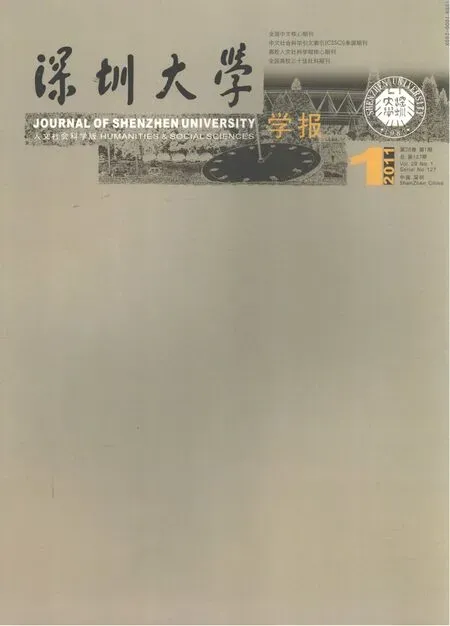学术与人生的贯通
——王国维“忧生诗学”与诗学话语的创构
伍世昭,王正刚
(1.惠州学院中文系,广东惠州516007;2.揭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广东揭阳522000)
学术与人生的贯通
——王国维“忧生诗学”与诗学话语的创构
伍世昭1,王正刚2
(1.惠州学院中文系,广东惠州516007;2.揭阳职业技术学院中文系,广东揭阳522000)
所谓“忧生诗学”,乃是基于王国维将人生问题的探问与学术活动相贯通的诗学追求而言的。其内在动力为“忧生情怀”;“形上之思”使王国维发现人生苦痛之因及解脱的审美途径;文学的审美解脱功能得之于“境界”的创造,“境界”的创造则来自于“有境界”的创作主体;通过提升创作主体之境界,创造出“有境界”的文艺作品,从而提升读者之境界,最终实现人生痛苦之解脱,寄托了王国维遥深的审美理想。
王国维;忧生诗学;话语创构
王国维诗学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某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理论命题或概念范畴,更在于由这些理论命题、概念范畴所构成的以忧生为动力、以审美解脱为目标、以“境界”论为核心的“忧生诗学”之总体建构。所谓“忧生诗学”,乃是基于王国维将人生问题的探问与学术活动相贯通的诗学追求而言的,“忧生情怀”是其诗学创构的内在动力。正是这种对个体生命乃至整个现实人生的人本忧思情怀,驱使他去思考人生苦痛之因与解脱途径,并最终建构起以“境界”论为核心的“忧生诗学”体系。
一、“忧生情怀”
1.诗性呈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第十八则论及李后主词时说过这样一段话:“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以血书者。’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亦略似之。然道君皇帝不过自道身世之戚,后主则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之意,其大小固不同矣。”[1]书之以“血”,表明情感之真,在王国维那里,这是“有境界”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俨有释迦、基督担荷人类罪恶”的说法,则实际上表明了王国维借文学以解脱人生苦痛的一贯思想,因为在他看来,只有那些超越了个体“身世之戚”而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感才能真正打动读者,从而实现人生苦痛之解脱。其实王国维自己也是具有这种情怀的,那就是由个体生命之忧上升至整个现实人生之忧的“忧生情怀”,这正是其“忧生诗学”建构的内在动因。
王国维的“忧生情怀”多体现在其诗词创作中。据《王国维遗书》所载,其《人间词》凡115阕,其中《苕华词》92阕,《观堂长短句》23阕;《人间诗集》所收古今体诗亦有49首之多。在这些诗词作品中,王国维于人生问题的探寻中所表现出来的“忧生情怀”是相当明显的。据统计,《人间词》115首中,直接用到“人间”二字者达38处之多,“人间”问题一直在其心头萦绕。而与“人间”如影相随的还有一个“梦”字,在《人间词》中亦出现28次之多。把“人间”与“梦”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是一个暗喻,喻指出王国维人生如梦的喟叹。这些词中有生命短暂的感慨:“最是人间留不生,朱颜辞镜花辞树”(《蝶恋花》);有人世无常的迷茫:“人生只似风前絮,欢也飘零,悲也飘零,都作连江点点萍”(《采桑子》);有人生虚无的悲歌:“算是人生赢得处,千秋诗料,一抔黄土,十里寒螀梦”(《青玉案》);有人生宿命的的凝思:“陌上楼头,都向尘中老”(《蝶恋花》);有存在的疑惑:“人间总是堪疑处,唯有兹疑不可疑”(《鹧鸪天》);有离别之苦:“为谁收拾离颜,一腔红泪,待留向、孤衾偷注”(《祝英台近》);有悼亡之恨:“往事悠悠容细数:见说他生,又恐他生误”(《蝶恋花》)等等,都可以归结到人生如梦的暗喻中,喻指出王国维对个体生命和整个现实人生的深广忧患。
王国维的诗歌创作同样如此。《人间诗集》共49首,直接用到“人间”或与“人间”相类的词就有19处之多。如《红豆词(二)》:“门外青骢郭外舟,人生无奈是离愁。”《书古书中故纸》:“书成付与炉中火,了却人间是与非。”《嘲杜鹃二首》:“干卿何事苦依依,尘世由来爱别离。”《游通州湖心亭》:“人生苦局促,俯仰多悲悸。”《六月二十七日宿硖石》:“人生过处唯存悔,知识增时祗益疑。”《来日二首》:“人生一大梦,未审觉何时。”《拚飞》:“欢场祗自增萧瑟,人海何由慰寂廖。”《平生》:“人间地狱真无间,死后泥洹枉自豪。”从其诗中可以看到,与人生相伴的多是“离愁”、“是非”、“别离”、“局促”、“悲悸”、“疑悔”、“梦”、“寂廖”、“地狱”等等,其深广的人生忧患由此可见一斑。
王国维这一时期的诗词创作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人生苦痛的宣泄上,而是由此去揭示造成人生苦痛的根源,并探寻着人生苦痛的解脱路径的。关于人生苦痛的根源,他在多篇诗作中提及。《偶成二首》以“我身即我故,外物非所虞”、“大患固在我,他求宁非谩”的诗句告诉我们,造成人生苦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我”、“身”即“欲”,与老子的“有大患者,为吾有身”的说法相近。《蚕》以蚕为隐喻,揭示了人生的辛苦劳碌却终归幻灭且代代循环的悲苦命运,而造成这一命运的原因也在于口腹之欲和生育的本能,这又与叔本华的“欲望论”相类。《端居》则表达了摆脱生活之欲的束缚而求得解脱的心迹:“安得吾丧我,表里洞澄莹。纤云归大壑,皓月行太清。”关于解脱的途径,他在《拼飞》中写到:“拼飞懒逐九秋雕,孤耿真成八月蜩。偶做山游难尽兴,独寻僧话亦无聊。欢场祗自增萧瑟,人海何由慰寂寥。不有言愁诗句在,闲愁那得暂时消?”视诗为消愁之物,代表了王国维这一时期诗词创作关于解脱的总体意向。这在他稍后创作的多阕词作中亦可以看到。所谓“觅句心肝终复在,掩卷涕泪苦无端”(《浣溪沙》、“更堪此夜西楼梦,摘得星辰满袖行”(《鹧鸪天》)、“西风林下,夕阳水际,独自寻诗去”(《青玉案》等等,都是如此。“尔从何处来,行将徂何处”(《来日二首》),尽管人生的终极目的王国维还无法洞悉,但心灵的安宁(王国维所谓“心安”)却是不变的诉求,而求“心安”的确切途径,就是审美的游戏。从人生苦痛真相的呈示,到人生苦痛根源的揭示,再到审美的解脱,隐含着王国维这一时期诗学建构的某些信息密码。
2.影响因素
王国维“忧生情怀”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社会环境因素,也有家庭生活因素,还有个人身心因素。就社会环境因素而言,他生活的前期(1898-1911)正逢中国千载未有之劫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强邻环绕,虎视眈眈”,已到了最危急的关头。青年王国维对时局极为关切,渴望国家能变法图强;然而戊戌变法转瞬落败、六君子喋血街头的结局,却让王国维深感意外和震惊。他曾在致友人的信中说道:“危亡在旦,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得不死乎?”[2]可是面对黑暗的现实,王国维只能借诗歌抒发满腔愁绪。《八月十五夜月》是王国维对戊戌政变一周年的感言:“一餐灵药便长生,眼见山河几变更。留得当年好颜色,嫦娥底事太无情。”《杂感》则诉说心绪:“侧身天地苦拘挛,姑射神人未可攀。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驰怀敷水条山里,托意开元武德间。终古诗人太无赖,苦求乐土向尘寰。”从中可以读出诗人眼见山河破碎却无力回天,因而一片忧生情怀驰骋于山水之中,理想却寄托于盛世的心灵告白。
就家庭因素而言,首先是幼时丧母、中年丧妻之痛。王国维三岁时母凌氏病卒,由祖姑母范氏和叔祖母抚养,而父亲又常年在外,直到王国维十岁那年才结束幕僚的生涯回家教子。王国维从小性格忧郁,郁郁寡欢,不善言辞,当与这一遭际有关。尤其不幸的是,王国维三十岁时又经历了丧妻之痛。从王国维事后发表的多篇词作中可以看到,他与妻子莫氏的感情非同一般,爱妻的早逝更增添了王国维人生如梦之感。其次是父亲对王国维学术志向的不理解。从父亲王乃誉的日记里可以看到,他对儿子的成长作了自以为很好的设计,希望王国维能在科举功名上有所成就。王国维迫于父亲的压力多次参加科举考试,终日为举业而劳苦。然而不喜“寻章摘句”、不屑“时文绳墨”的王国维在考取生员后,却屡应科考而不中。关于科考失利的心情,王国维本人并未提及,因而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王国维科举失败后的心理活动,但从父亲在日记中对王国维的多次严厉指责中可以间接地推想到他的忧郁苦闷[3]。再次是家庭经济问题的影响。王国维出生于没落的商人家庭,他曾自称:“余家在海宁,故中人产也。一岁所入,略足以给衣食。”[4]从中可看出,其家境不过略足衣食,解决温饱罢了。1894年甲午战争后,国内掀起了变革图强的热潮,有条件的热血青年均意欲出国留学,王国维也有此意,但以王国维仅足以给衣食的家境,是没有这个条件的。王国维当时蜗居于家中,郁郁不可终日,“家贫不能以资供游学,居恒怏怏”[4](P470),就是对当时心境的追述。
就个人身心因素而言,王国维曾在《自序·一》中说:“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4](P471)王国维从小体弱多病,成年后也屡有疾患。“体素羸弱”,说明体质差,易患病。最典型的例子是他常患一种严重的脚气病,曾让他几度辍学。1900年王国维在罗振玉的资助下东渡日本,入东京物理学校留学,才几个月时间,就因脚气病复发返回了上海。这对以学术为生命理想的王国维打击很大,一度形销骨立。如前所述,忧郁之情也从小就深深根植根于王国维心中了。“体素羸弱,性复忧郁”这两个因素驱使他追索“人生之问题”,而此类问题之难以解答更增其忧郁。忧郁而又往复思索人生问题的结果,反映在其文学创作中,便是常常在其诗词中感叹生命存在的苦痛,咏叹人生的无常变化。
二、形上之思
所谓形上之思,乃指对问题所作的不同于文学创作的哲学上的理性思考。王国维对人生苦痛根源和解脱途径的探问在这里得到了更澄明的呈示。
1.苦痛与欲望
王国维从理论上系统探讨“意志”——“欲望”作为人生苦痛根源的文章当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该文援引老、庄开篇:“老子曰:人之大患,在我有身。庄子曰: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在老庄看来,身体的存在是个体忧患的根源,有形则有欲,有欲则痛苦继之以生。王国维认为,“生”与“忧患”、“劳苦”是相“对待”的,“生”是人人想要的,“劳苦”与“忧患”是人人想要避免的;但人们之所以“欲其所恶”即宁愿选择“劳苦”与“忧患”,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生”,无论是“个人”之生存,还是“种性”之“保存”。他指出,人们为了“生”,欲望不可谓不切,用力不可谓不勤,设计不可谓不周;但“吾人之忧患劳苦,固亦有所以偿之者欤?”,这就“不得不就生活之本质”“熟思而审考之”[1](P1-2)了。王国维从“生活之性质”和“吾人之知识”两方面探讨了这一问题。
关于“生活之性质”,他说:“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究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1](P2)很明显,生活的本质就是苦痛,而造成苦痛的根本原因就是下文所说的“生活之欲”。而关于“吾人之知识”,他说:“吾人生活之性质,既如斯矣,故吾人之知识,遂无往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吾人之利害相关系。就其实而言之,则知识者,固生于此欲,而示此欲以我与外界之关系,使之趋利而避害者也。”[1](P2)他认为常人之知识,只知我与物之关系;科学之知识则不仅知一物全体之关系,更知此物与彼物之全体之关系,从而使人的生活之欲“增进于无穷”。在他看来,科学与政治一样,均建基于生活之欲之上,都是“生活之欲的结果”[1](P2-3)。他的结论是:“由是观之,吾人之知识与实践之二方面,无往而不与生活之欲相关系,即与苦痛相关系。”[1](P13)
在王国维那里,“生活之欲”先于人而存在,人生只不过是欲的外在表现。这从《红楼梦评论》第二章“红楼梦之精神”的论述中可以见出。他引用《红楼梦》第一回和一百一十七回中的有关情节得出了两个相关的结论。第一回的情节涉及女娲补天剩下的最后一块通灵顽石因不得补天而“自怨自艾,日夜悲哀”,最终落入红尘的内容。在王国维看来,通灵顽石在附身宝玉而入“忧患劳苦之世界”之前,就已经是欲望的化身了,而因它的“幻化”所造成的十九年之历史与一百二十回之事实,实由它的“一念之误”,“此可知生活之欲之先人生而存在,而人生不过此欲之发现也。此可知吾人之堕落,由吾人之所欲,而意志自由之罪恶也。”[1](P7)第一百一十七回的情节涉及宝玉与和尚的一段有关“还玉”的对话。宝玉衔玉而来还玉而去,在王国维看来,实际上就是怀着欲望入世(痛苦)去除欲望出世(解脱),因为“所谓玉者,不过生活之欲之代表而已矣”!
王国维对人生苦痛根源的探讨,是有着中国传统道家哲学的思想储备的。所谓“有大患者,为吾有身”[5]、“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6],就是老庄哲学给予的馈赠。但在这个问题上影响更大的则是叔本华的“欲望论”。可以这样说,性情忧郁的王国维正是带着老庄哲学的思想储备走向叔本华并对后者产生共鸣的。王国维关于“人生如钟表之摆”的比喻就直接来自叔本华。叔氏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说:“……一切欲求的基地却是需要,缺陷,也就是痛苦;所以,人从来就是痛苦的,由于他的本质就是落在痛苦的手心里的。如果相反,人因为他易于获得的满足随即消除了他的可欲之物而缺少了欲求的对象,那么可怕的空虚和无聊就会袭击他,即是说人的存在和生存本身就会成为他不可忍受的重负。所以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的来回摆动着……。”[7]王国维关于知识弥广所欲弥多而所感痛苦弥多的观点,则来自叔本华关于人比动植物更痛苦而天才最痛苦的言论:“原来随着意志的现象愈臻于完美,痛苦也就日益显著。在植物身上还没有感性,因此也无痛[感]。最低等动物如滴虫和辐射体动物就能有一种程度微弱的痛[感]了。……直到脊椎动物有了完备的神经系统,这些能力才以较高的程度出现……到了人,这种痛苦也达到了最高的程度;并且是一个人的智力愈高,认识愈明确就愈痛苦。具有天才的人则最痛苦。”[7](P424-425)王国维所谓欲望的先在性乃来自叔本华的“生命意志本体论”。在叔本华那里,生命意志作为本体——自在之物,本质上是一个“没有一切目的,一切止境的”“无尽的追求”[7](P235),一切现象包括人的生命只不过是意志的“客体化”的产物,生命是伴随着意志一起出生的,而意志必定带有求生本能,它的本质也就是“欲”。
2.“解脱”与审美
“人总得有条出路啊!”陀思妥耶夫斯基所提的问题也正是王国维所要解决的,那就是王国维对人生苦痛之解脱所作的形上之思。他首先探讨了“解脱”的可能性问题。这一探讨是从解构叔本华“拒绝意志”说开始的。尽管叔本华看到了审美静观所具有的解脱功能,但在他那里真正的解脱却并不在此,而在于否定生活意志,消除一切欲望,最后达到生命的寂灭,即所谓“拒绝意志”。王国维相信意志的先在性,但对本体世界实际上并不太感兴趣,他关注的是从“欲”的自我“解脱”中所到达的可体验的伦理境界。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他对叔氏“拒绝意志”的置疑,以及由此引发的对释迦、基督式的所谓“解脱”的怀疑。他说:“夫由叔氏之哲学说,则一切人类及万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绝意志之说,非一切人类及万物,各拒绝其生活之意志,则一人之意志,亦不得而拒绝。”[1](P16)因为,意志之存于“一人”,与存于人类及万物同,拒绝了“一人”的意志,就“姝姝自悦曰解脱”,显然不能令人信服。在王国维看来,即便是释迦、基督自身之解脱与否,也在不可知之数。因为他们的解脱是无法证实的,不然释迦示寂以后、基督受祭以来,人类及万物“欲生”之念、苦痛之累,就应该得到了摆脱[1](P16-17)!
那么,在王国维那里,解脱的可能途径是否存在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那就是艺术——审美。他说:“以人生忧患之如彼,而劳苦之如此,苟有血气者,未有不渴慕救济者也,不求之于实行,犹将求之于美术。”[1](P19)艺术——审美之所以具有解脱之功能,是因为它有着“可爱玩而不可利用”[4](P31)即超越功利的独特性质:“兹有一物焉,使吾人超然于利害关系之外,而忘物我之关系。……然物之能使吾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者,必其物之于吾人无利害之关系而后可;易言以明之,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然则非美术何足以当之乎?”[1](P3)
但为什么艺术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之关系呢?上引“必其物非实物而后可”一句话是理解的关键之一。所谓“实物”,乃指对象的实体;“物非实物”,则指艺术作为美不与对象的实体相联系。在王国维看来,艺术一旦与实物联系起来,就会被物我之关系所纠缠而趋向功利的考虑;艺术作为美之所以能使人超越于利害关系之外,乃在于它是诉诸形式本身的。“美在形式”就是王国维对艺术作为美的一个基本判断。王国维还进一步把“美之为物”分为优美、宏壮与古雅三个类别,论证了美在形式从而使人忘物我之关系的观点。他认为此三者作为形式之美,各有其审美价值。具体地说,优美所涉及的形式之变化调和由于不关乎人的利害关系,因而使人能忘掉利害之念,获致一种“和平”的心境[4](P34);宏壮以其“无形式之形式”唤起人的崇高感,使人的生活意志遁去,“唯由知识冥想其理念”[4](P321)而“忘物我之关系”;古雅作为艺术表达方式即所谓“第二形式”,同样具有一种“使人心休息”的独立的审美价值[4](P34)。
王国维关于艺术——审美与实体无关和“美在形式”的观念乃来自康德“美的分析”。在康德看来,鉴赏判断的愉悦之所以不带任何利害,是因为它不关乎“对象的实存”。他说:“被称之为利害的那种愉悦,我们是把它与一个对象的实存的表象结合着的。……但现在既然问题在于某物是否美,那么我们并不想知道这件事的实存对我们或对任何人是否有什么重要性,哪怕只是可能有什么重要性;而只想知道我们在单纯的观赏中(在直观或反思中)如何评判它。”[8]王国维所谓“美在形式”也与康德的看法联系着。在康德那里,美不关乎利害、不涉及概念,还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美的形式规定性。他认为“美真正说来却只应当涉及形式”[8](P58),而“只是通过其形式而使人喜欢的东西,才构成了鉴赏的一切素质的基础”[8](P61)。康德所说的形式尽管是“单纯形式”,但却是“合目的性”的形式,因为这种“单纯形式”是趋向“美的理想”的。与康德一致的是,王国维所说的形式不管是指唤起人之“美情”的“材质”,还是指“纯形式”,都不仅仅指向形式本身,它最终是要通向“实念”——“理念”的。王国维把艺术——视为“实念的知识”,就说明了这一点。
王国维把美——艺术视为“实念的知识”,出自其《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一文:“美之对象,非特别之物,而此物之种类之形式,又观之之我,非特别之我,而纯粹无欲之我也。夫空间时间既为吾人直观之形式;物之现于空间皆并立,现于时间皆相续,故现于空间时间者,皆特别之物也。既视为特别之物矣,则此物与我利害之关系,欲其不生于心,不可得也。若不视此物为与我有利害之关系,而但观其物,则此物已非特别之物,而代表其物之全种。叔氏谓之曰‘实念’。故美之知识,实念之知识也。”[4](P321)这段话大致解释了“美”作为“实念的知识”何以能使人超然于利害之外而忘物我之关系的问题。就客体说,“美”所表现的对象不是个别(特别)事物,而是由“个象”所代表的“种类之形式”即“实念”;就主体来说,他必须作为“纯粹无欲之我”,即“不视此物为与我有利害之关系”以“观物”,对象客体才跳脱“根据律”而显现为“实念”,即“永恒的形式”[7](P250)。个别事物由于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必然会与其他事物“并立”或“相续”,而发生利害之关系;“实念”作为意志的直接客体性,则超越了时空因果等“根据律”而指向“普遍”、“永恒”和“自由”。因而当“美”——“艺术”超越了个别事物而表现出“实念”时,那么在审美观赏中观赏这客体的人,就有可能超离物我之利害关系而成为“纯粹而无意志的认识的主体”[7](P292)。
三、诗学建构
如果说在王国维那里文艺的解脱功能是肯定的,那么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并不是所有文艺作品都有这种功能,也不是每一个创作主体都能创作出具有如此功能的文艺作品的。在他看来,只有那些有“境界”的文艺作品才能使读者超离“生活之欲”的束缚,也只有那些“天才”式的“大家”才能创作出有“境界”的文艺作品。
1.文学作品的“境界”
“有境界”是王国维评价文学作品的一杆重要标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1](P141)那么怎样才算“有境界”?他在《人间词话》中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1](P142)“能写真景物、真感情”是王国维对“有境界的总体要求,具体可以展开为“真”、“自然”、“不隔”三个主要方面。
“真”乃“境界”之内核,包括主体感情之真和艺术表现对象客观之真,即情真和景真两个方面。情真是要求抒发纯真、率真之情。王国维主张作家“对一草一木,亦须有忠实之意”,而反对所谓“游词”即虚假之情。他认为“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一诗,“可谓淫鄙之尤”,但人们之所以不视为“淫词”、“鄙词”,乃在于它的真挚[1](P156)。在王国维那里,感情的真挚还不仅是这个意义上的,创作主体必须把一己主观之感情提升为人类普遍之感情,或者反过来说,“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4](P30),才是感情之真的本意。他之所以扬李后主而抑宋徽宗,原因也在于前者有“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这样的“担荷人类罪恶之意”,而后者则“不过自道身世之戚”而已[1](P144-145)。景真指写景“豁人耳目”、“如在目前”即“真切”。它包含两方面要求。一方面是所写之景能给人以鲜明突出的直观印象。王国维认为诗歌虽借助概念以唤起直观,但其价值却不是概念的,而全在于其能直观与否,而这正是诗歌多用“比兴”的原因所在。“红杏枝头春意闹”、“云破月来花弄影”分别用“通感”(“闹”)和拟人(“弄”)的手法,生动地写出了盎然的春意和幽谧的夜景,从而给人以意境上的美感。所以王国维说“着一‘闹’字而境界全出”、“着一‘弄’字而境界全出”。另一方面是所写之景能超越“个物化之原理”,而呈现出“种类之形式”,即通过鲜明可感的个象而呈现出“理念”。王国维之所以盛赞“细雨湿流光”“能摄春草之魂”[1](P146),“水面清圆,一一风荷举”“真能得荷之神理”[1](P149),也就在于它们分别描画出了作为“春草”与“荷”的“种类”的顽强生命力这一“永恒的形式”即“理念”。
“自然”是指在艺术境界营造中的合乎造化而无人为雕琢痕迹所达到的高度。“自然”是王国维文学批评中经常提到的字眼,其《人间词话》亦多次提出了自然的要求,最有名的是下面一段话:“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1](P154)这段话中直接与“自然”有关的句子无疑是“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妆束之态”。但在王国维那里,真正的自然,并不仅仅体现在语言表达层次上,换句话说语言表达的自然是建立在“真”的基础上的。所以他特地将“其词脱口而出”与“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写景也必豁人耳目”放在一起说。在他看来,如果抒情写景能做到“真切”,那么语言表达上“脱口而出”就可以了;而没有必要绞尽脑汁去“雕琢”、“作态”。当然要做到“自然”,还与创作主体的修养有关。所谓“大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才创作出毫无矫揉妆束之态的浑然天成的艺术作品,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人间词话》第五十二则还从这个角度肯定了纳兰容若:“纳兰容若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此由初入中原,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1](P153)这充分说明主体的人格修养之于“真切”、“自然”的重要性。
“不隔”是指文艺作品所创造的艺术形象,生动可感、“如在目前”;所表现的情感,素朴真切,引人共鸣。“不隔”乃建立在直观之真的基础上。从王国维把周邦彦的“一一风荷举”的诗句“能得荷之神理”与姜白石《念奴娇》、《惜红衣》“犹有隔雾看花之恨”对着说可以看出,后者的“隔雾看花”与缺乏直观之真紧密相关。他举例说,“‘池塘生春草’、‘空梁落燕泥’等二句,妙处唯在不隔”[1](P150),而“‘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1](P150);姜白石之“‘叹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气。’则隔矣。”[1](P150)在他看来,造成“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念化、使用“隶事”(典故)“代字”就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上举的被认为“隔”的诗句,就是缺乏直观可感的概念化造成的。关于隶事,他说:“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于此见。”[1](P155)在他看来,像《长恨歌》此类“不隔”之作,较之非隶事不办的梅村歌行,优劣立见。关于“代字”,他说:“词忌用代字。美成《解语花》之‘桂华流瓦’,境界极妙。惜以‘桂华’二字代‘月’耳。梦窗以下,则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则语不妙也。盖意足则不暇代,语妙则不必代。此少游之‘小楼连苑’、‘绣毂雕鞍’所以为东坡所讥也。”[1](P149)他认为只有在“意不足”、“语不妙”,不能直接写出“真感情”、“真景物”的情况下,才使用“隶事”、“代字”之法,而这正导致了情的隐晦曲折和景的模糊朦胧。
王国维从不同角度对境界作了多种分类,与创作主体人格修养密切相关的一组则是“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创作“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都有一个心理动因问题:“无我之境,人唯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1](P142)在“有我之境”中,“物”“我”之间一开始是对立的,创作主体需经过一番挣扎,才能使其心境摆脱功利欲望的束缚;而在“无我之境”中,则“我”即“物”,“物”即“我”,“物”“我”浑融为一。两境之间,“有我之境”乃一般诗人之境,“无我之境”则为“大诗人”——“豪杰之士”所造之境,所以比较而言,“无我之境”为高。对“无我之境”的推崇,隐含了王国维对创作主体人格“境界”的某种期许。
2.创作主体的“境界”
在王国维那里,文学作品的境界始终是与创作主体的“境界”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创作主体需具备怎样的“境界”,才能创构出“真”、“自然”、“不隔”而“意与境浑”的“境界”呢?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若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文章者,殆未之有也。”[1](P126)。在他看来,“高尚伟大”的文学乃源于“高尚伟大之人格”;同样的,文学境界的创造,也只有那些人格高尚、具有“赤子之心”和“天眼”的“天才”才有可能的。他说:“原乎文学之所以有境界者,以其能观也。”[1](P176)“能观”即涉及到创作主体的人格境界问题;而所谓“能观”,用叔本华的话来说,就是一种卓越的“观审的能力”。叔本华认为,“艺术的唯一源泉就是对理念的认识,它唯一的目标就是传达这一认识。”[7](P258)而对理念的“掌握”只有当主体处于“纯粹观审”状态时才有可能:“完全浸沉于对象的纯粹观审才能掌握理念,而天才的本质就在于进行这种观审的能力。……天才的性能就是立于纯粹直观地位的本领,在直观中遗忘自己,……从而一时完全撤消了自己的人格,以便[在撤消人格后]剩了为认识着的纯粹主体,明亮的世界眼。”[7](P259-260)王国维“能观”的见解主要来自叔本华的上述“观审”说。在他看来,创作主体只有具备这种“观审”能力,才能做到“观物也深,而其体物也切”[1](P25),从而创作出“有境界”的文学作品。然而要获得这种能力,“必吾人之胸中洞然无物”,即唯有摆脱意志的束缚而“忘物我之关系”,而这只有具备伟大“知力”的天才方能做到:“独天才者,由其知力之伟大,而全离意志之关系,故其观物也,视他人为深,而其创作之也,与自然为一。故美者,实可谓天才之特殊物也。”[4](P322)
王国维曾在谈及“大诗人”之于境界创造的作用时说道:“山谷云:‘天下清景,不择贤愚而与之,然吾特疑为我辈设。’诚哉是言!抑岂独清景而已,一切境界,无不为诗人设。世无诗人,即无此种境界。夫境界之呈于吾心而见于外物者,皆须臾之物。唯诗人能以此须臾之物,镌诸不朽之文字,使读者自得之。遂觉诗人之言,字字为我心中所欲言,而又非我之所能自言,此大诗人之秘妙也。”[1](P173)“大诗人”王国维有时说成“大家”,也就是他笔下常提到的“天才”。“天才”在叔本华那里,是仅就审美创造而言的,他曾断言,天才仅属于艺术创造,科学理性的发现均无关乎天才[7](P258)。王国维也多在这一意义上使用这个词,但他更多的是从创作主体的人格角度着眼的,所谓“德性”、“内美”,都是与人格有关的字眼。从这一角度看,王国维那里的“天才”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素养。一是功利欲望的消除。“词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1](P145)所谓赤子之心,即为纯真的超物我利害关系之心。只有具有赤子之心的天才人物才能以审美的眼光来观物。二是“知力远胜意志”。由于消除了功利欲望,摆脱了意志的束缚,因而具有非凡的“观审”“理念”的能力,能于平凡人生中发掘常人体会不到的真美。这就是所谓“诗人之眼”。三是能超越个体趋向普遍。由于同样的原因,“大诗人”往往能透过个体之“我”的苦痛而思考整体人生忧患,因而在创作上常常不以抒发个人一己的感情为限,“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其著作也就成了“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就能得到感情的共鸣[4](P30)。在王国维看来,正是因为“大诗人”具有上述非同寻常的人格素养,所以才能创造人人“心中所欲言”而又非人人“之所能自言”的审美境界,从而给读者以深切的审美感悟而超然于利害关系之外,这就是“大诗人”的“秘妙”之所在。这里实际上已给出了审美解脱如何可能的答案。他在《〈红楼梦〉评论》说:“夫自然界之物,无不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纵非直接,亦必间接相关系者也。苟吾人而能忘物与我之关系而观物,则夫自然界之山明水媚,鸟飞花落,固无往而非华胥之国、极乐之土也。……然此物既与吾人有利害之关系,而吾人欲强离其关系而观之,自非天才,岂易及此?于是天才者出,以其所观于自然人生中者复现之于美术中,而使中智以下之人,亦因其物之与已无关系,而超然于利害之外。”[1](P3)文学作品的解脱功能得之于境界的创造,境界的创造则来自于“有境界”的创作主体,这应该就是隐含在王国维“忧生诗学”建构中的内在逻辑。
四、结语
王国维是带着人生的困惑走向哲学、美学和诗学的。人生之问题,无时不在王国维心头萦绕,其人生历程中的哲学探讨、诗词创作、理论建构无一不打上了“忧生”的烙印。
其由时代、社会、家庭和个人气质塑造的“忧生情怀”,使他超越自身个体之忧患而探寻一般人生问题,当其“期待视界”与老子、庄子等中国哲人和叔本华、康德等西方哲人的思想世界取得融合时,他便为他们的思想所深深倾倒。老庄和叔本华给予王国维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但相同而又最重要的有两点:一是人生痛苦根源的揭示,二是人生痛苦之解脱的审美途径的发现。康德的“美的分析”则充实了王国维对美——艺术解脱功能的理解。王国维的“忧生诗学”就建构在中西思想文化诗学的双向影响与化合当中。
王国维由哲学到文学的“转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并不意味着哲学所给予他的影响遭到了摒除,而是更深层次地融入到了其诗学建构当中去了。既然人生是痛苦的,它才需要解脱;既然审美能实现人生痛苦之解脱,王国维才不遗余力地强调文学的审美价值;既然文学的根本任务在于“示人以解脱之道”,他才由衷赞赏《红楼梦》为“绝大著作”。这正得益于其深沉的哲学思索。
在王国维那里,人生痛苦之解脱主要是借助文艺的审美特性实现的,所以他十分强调文艺作品的“境界”,因为只有当创作主体能“写”“真感情”“真景物”,即创作出的作品“有境界”,才能真正打动读者,并提升读者的精神境界。而“有境界”的前提则是“有境界”的创作主体,因为以“真”、“自然”、“不隔”等为规定的“境界”,都是那些具有“赤子之心”和“忧生”、“忧世”情怀,兼具“内美”和“修能”的“大家”方能创造的。可以说通过提升主体之境界从而创造“有境界”的文艺作品,以提升读者之境界,最终实现人生痛苦之解脱,寄托了王国维遥深的审美理想。而把人生问题的探问与学术活动相贯通,这正是王国维不同于一般文论家之处,所以其诗学建构才给我们以更深刻的启迪。
[1]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一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145.
[2]王国维.致许家惺[A].王国维全集:书信[C].北京:中华书局,1984.17.
[3]袁英光,刘寅生.王国维年谱长编[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6-9.
[4]王国维.王国维文集:第三卷[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470.
[5]老子[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
[6]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7]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M].石冲白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82.427.
[8][德]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38-39.
【责任编辑:向博】
The linking-up of Learning and life——WANG Guowei’s Poetics of Worrying about Common People and the Setting-up of the Discourse in His Poetics
WU Shi-zhao1,WEANG Zheng-gang2
(1.Department of Chinese,Huizhou Institute,Huizhou,Guangdong 516007,China;2.Department of Chinese, Jieyang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Institute,Jieyang,Guangdong 522000,China)
The so-called“poetics of worrying about common people”is based on the pursuance for a type of poetics featured by the linking-up of WANG Guo-wei’s inquiry into the issues of human life and his academic activities,the internal motive power of which is his“feelings of concerning himself with the common people”; WANG’s metaphysical thinking made him discover the reasons for human agony and the aesthetical channels for the freedom from the agony.The aesthetical function of freeing oneself from agony results from the creation of“the plane intended”,which comes from the subject of creation,who has obtained such a plane.By way of enhancing the“plane intended”of the related subject of creation,literary and artistic works boasting a high plane can be created so as to elevate the readers'plane and finally realize the freedom from human agony,which embodies the far-reaching and deep-going aesthetic ideal of WANG Guo-wei’s.
WANG Guo-wei;poetics of worrying about common people;setting-up of discourse
I 2
A
1000-260X(2011)01-0118-08
2010-12-10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王国维‘忧生诗学’与诗学话语创构的普适意义”(08J-04)
伍世昭(1962—),男,湖南东安人,惠州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从事20世纪中国文论研究;王正刚(1978—),男,湖南邵阳人,揭阳职业技术学院讲师,从事美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