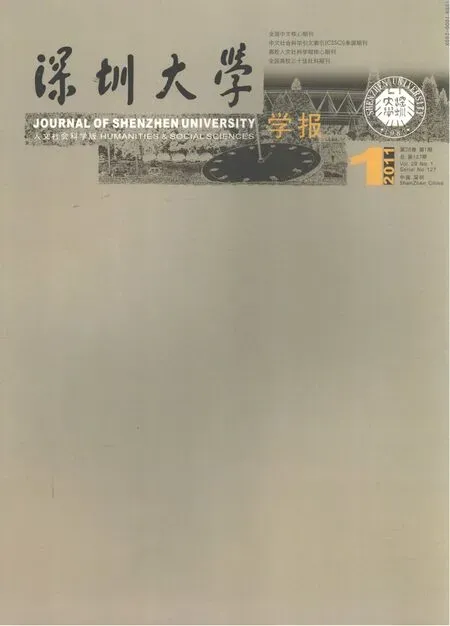“重陆轻海”与“通洋裕国”之海洋观刍议
黄顺力
(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
“重陆轻海”与“通洋裕国”之海洋观刍议
黄顺力
(厦门大学历史系,福建厦门361005)
明清两朝正处于世界性海洋历史发展的“千古变局”时代,但统治者沿袭传统模式,在立国思想上“重农抑商”、“重陆轻海”,在国防战略上以“禁海”代替海防,禁海迁界、“守土防御”,反映其海洋观念的淡薄;而东南沿海地方官员,尤其郑成功“通洋裕国”思想的提出和实践,显露出“以商立国”,向海洋空间发展的意涵;传统时代“重陆轻海”与“通洋裕国”所反映的海洋观念,对国家民族发展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忽略不计,但大航海时代,海洋作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影响到世界历史走向和发展格局时,“重陆轻海”观念所带来的深层影响会因此而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
明清时代;大航海时代;“重陆轻海”;“通洋裕国”;海洋观
明清是世界大航海历史巨变的时代。1644年,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将关注点主要放在完善王朝统治赖以生存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其观念意识也沿袭历代中原统治者“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思维模式。而以闽台海域为主要基地的郑成功海商武装集团为了与清王朝进行长期的抗衡,提出了与传统“以农立国”思想完全不同的“通洋裕国”主张,其“大开海道,兴贩各港”,致力发展海洋经济贸易,曾一度执东西洋海上贸易之牛耳,与递航东来的西方海上殖民者亦成分庭抗礼之势。后来郑氏集团在与清王朝的武力抗争中败北,这股新兴的地方海上势力也随之湮灭不彰。坐稳江山的清朝统治者处此世界性海洋历史发展的“千古变局”时代,却恰恰在海洋问题上产生许多困惑与迷思,结果导致了此后晚清时期“落后挨打”的历史性悲剧。
一
自汉唐以降,中国西北的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不断冲突与融合,历代王朝统治者要从根本上稳定政权的统治,其国家安全防卫方向的重点基本都在西北,形成“历代备边多在西北”的传统治边意识,此为“重陆轻海”海洋观的思想基础。
以明代为例,明太祖朱元璋所定“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1]的国防方针,实际上是在东南沿海采取防御的保守姿态,希望同海外诸国和平共处,造就一个比较安定的国际环境,以保证国内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而对于占据漠北的元蒙残余势力则采取积极的进攻姿态,频频主动出击。这其中的原因就在于残元势力虽然远遁沙漠,但其“引弓之士,不下百万众也,归附之部落,不下数千里也,资装铠仗,尚赖而用也,驼马牛羊,尚全而有也”[2],随时可能卷土重来,危及明朝政权的安全。因此,明洪武初年,朱元璋命大将徐达、常遇春等多次西征,集中兵力,以图肃清西北扩廓帖木儿和李思齐等残元割据势力。明成祖朱棣即位后,更是“五征漠北,皆亲历行阵”[3],最后还病殁于北征归途之中。到明代后期,社会动荡,狼烟四起,“中原之寇”、“西北之虏”和“东南之氛”三大患接踵并至,明王朝也是集中精力首先对付“西北之虏”和“中原之寇”,而对“东南之氛”的郑芝龙海商武装集团则实行招抚政策,以期借郑氏集团之力去平定东南沿海海盗的骚扰,解除后顾之忧。因此,尽管明初因禁海、开海,明中叶嘉靖朝因“倭患”等海疆问题曾一度闹得沸沸扬扬,但就总体形势而言,明朝统治者的国防战略重点始终放在北方陆疆,不敢须臾懈怠。这种情况的存在不仅是因历朝历代频仍不断的“西北边患”所致,而且与中原农耕民族把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寄托于土地和农桑的农业文明传统也分不开。
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后,清承明制,很快就承袭了中原农业文明的传统,其倾力关注的也是广袤的陆地疆土,而非波涛汹涌的东南海疆,同样表现出“重陆轻海”的传统观念意识倾向。
早在清兵入关之前,满族统治者即制定出联合漠北蒙古作为战胜明王朝,入主中原的战略决策,即所谓“草昧之初,以一城一旅敌中原,必先树羽翼于同部,故得朝鲜人十,不若得蒙古人一。”[4]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对漠北蒙古地区的稳定极为重视,并逐步形成一整套极具特色的治蒙政策。对新疆、西藏地区则采取各种强有力的措施,以强化清朝中央政权对新疆、西藏地区的管辖,这其中的原因在于:“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匪特陕甘西各边时虞侵轶,防不胜防,即直北关山亦将无晏眠之日。”[5]对于东北地区满族统治者自身的“龙兴”之地,其重视程度就更不必赘言。
然而,对于东南海疆,虽有郑成功海上政权顽强的抗清活动,但清王朝基本承袭明王朝的传统思路,以海洋防御为其基本的政策取向。在屡次招抚不成的情况下,遂采取大规模禁海迁界的防海政策,试图以此断绝以海上贸易为依托的郑成功海商武装集团的经济来源。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曾任福建漳州知府的房星烨向清廷建议说:“(郑氏集团)海舶所用钉、铁、麻、油,神器所用焰硝,以及粟、帛之属,岛上所少,皆我濒海之民阑出贸易,交通接济。今若尽迁其民入内地,斥为空壤,画地为界,仍厉其禁,犯者坐死;彼岛上穷寇内援既断,来无所掠,如婴儿绝乳,立可饿毙矣。”[6]主张以禁海的方式阻断郑氏集团海上贸易的经济活动。
顺治十二年,浙闽总督屯泰又奏请:“沿海省份,应立严禁,无许片帆入海,违者立置重典”[7],并得到清廷允准。次年,清廷即公开颁布《申严海禁敕谕》,敕谕沿海各省督抚及文武各官“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货物等项与逆贼(指郑氏集团)贸易者……即将贸易之人,不论官民俱行奏闻处斩,货物入官。”[8]并对负责执行“禁海令”的失职文武官员从重治罪。很显然,清王朝“禁海”的目的是想通过断绝海上贸易往来,阻塞大陆货物的出海通道,使郑氏海商集团失却经济来源的“通洋之利”,迫使其就范。郑成功的叛将黄梧也向清廷提出“剿寇五策”,强调“将所有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寸板不许下水。凡溪河监桩栅,货物不许越界,时刻了望,违者死无赦。”[9]黄梧为福建漳州平和人,原为郑成功部将,了解郑氏海商集团海上贸易经济的特点,故其建议受到清廷的高度重视。
顺治十八年(1661年),郑成功占据台湾后,清廷正式颁布“迁界”令,“迁沿海居民,以垣为界,三十里以外,悉墟其地”[10]。此后,又于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十八年(1679年)连续进行三次大规模的迁界移民,范围遍及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五省沿海,而以福建、广东推行迁界令最为严厉。根据清朝统治者的设想,厉行“禁海”、“迁界”措施,是要在沿海与内陆之间形成一个无人区,以此杜绝陆海之间的往来,彻底隔断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与大陆的经济联系。
但清王朝这种严厉的“禁海”、“迁界”政策却收效甚微。史称:“福省奸(民)林行可等凭(颇)不畏法,包藏祸心,自去年(指1655年)八月间,潜运麻、油、钉、铁等项,以助郑孽。令渔船贼首刘长、卞天、郑举仔等,陆续搬运,竟用逆贼(洪)旭运印记,购买造船巨木……公然放木下海,直至琅琦贼所,打造战船……铤险罔利,已非一日……(违禁下海者)结党联宗,更番出没,或装载番货,如胡椒、苏木、铜、锡、象牙、鱼皮、海味、药材等项,有数百担,神偷鬼运,贸迁有无,甘为寇盗之资。”[11]又称:“沿海一带每有倚冒势焰,故立墟场,有如鳞次。但知抽税肥家,不顾通海犯逆。或遇一六、二七、三八等墟期,则米、谷、麻、篾、柴、油等物无不毕集,有发无发,浑迹贸易,扬帆而去。此接济(郑氏)之尤者,而有司不敢问,官兵不敢动也。”[12]海上违禁走私活动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难以遏止。
造成沿海地区这种“通海犯逆”现象的主要原因在于:(1)当时郑氏海商集团的海上势力实已掌握中国、日本及东南亚之间海洋贸易的控制权,“凡海舶不得郑氏令旗者,不能来往。”[13]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后,拥有了一块较为稳固的抗清基地,其原本活跃的海洋贸易活动也更加发展。史载:康熙五年,郑氏“遣商船前往各港,多价购船料,载到台湾,兴造洋艘鸟船,装白糖、鹿皮等物,上通日本,制造铜熕、倭刀、盔甲,并铸永历钱;下贩暹逻、交趾、东京各处以富国。从此台湾日盛,田畴市肆不让内地”[14]。清廷虽然在沿海一带设界防守,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却不但没能遏阻郑氏的海外贸易,反而使其独得海外贸易之利,财力也因此更加雄厚[15]。(2)尽管清朝实行禁海和迁界,但不能真正切断郑氏海上政权与大陆间的经济联系,无法有效地阻绝民间商贾通过走私的途径与郑氏政权进行海洋贸易,“郑成功盘踞海徼有年……向因滨海各处奸民商贩,暗与交通,互相贸易,将内地各项物料,供送逆贼……”[16]在郑氏海上政权治理台湾期间,沿海内地的货物仍然通过郑氏海外贸易渠道源源输出,史称“当是时闽粤逐利之氓,辐辏而至,岁率数万人……彼往此来,以搏贸易之利,而台湾物价大平。”[13]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清王朝实行禁海迁界措施虽然对郑氏海上政权没有达到预期的“不攻自灭”的目的,但这种消极防御的经济封锁,却给清朝统治者的海洋观念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害的思维定式,即禁海迁界、毁船内缩,不仅忽视在海上掌握积极主动姿态的制海权,而且还自动放弃对岛屿及沿海地区的掌控,把海疆防御和控制的重点放在内陆,消极退守,以防为主,呈现其传统“重陆轻海”的固有思想倾向。这一思维定式所造成的深层影响对有清一代海洋事业的发展可以说相当深远。因此,当施琅奉命率兵渡海征台,将郑氏海上政权剿灭后,虽然清廷下令停止海禁,并在康熙后期及雍正、乾隆年间有过几次时间长短不一的禁海和开海,但此后清朝统治者对付海疆不靖的主要法宝就是退守内陆,固守以消极防御为主的“禁海”和“防海”政策。一直到晚清时期,清王朝对海洋的认知就是在“禁海”、“防海”的困惑中被动地接受来自西方海上强敌的有力挑战,而失败的祸根实则早已种下。
清朝的“重陆轻海”传统观念意识也表现在对台湾海洋战略地位的认识上。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七月,施琅率兵克复台湾后,清廷内部出现关于台湾弃留问题的争论就是其中典型的例子之一。有人认为:“方郑氏初平,廷议以其海外孤悬,易薮贼,欲弃之。”[17]理由是“此一块荒壤,无用之地耳,去之可也”,且“得其地不足以耕,得其人不足以臣。”[18]
结果这场有关台湾的弃留之争竟拖延了8个月之久,最后在姚启圣、施琅等人的力争之下,台湾才得以保留在清王朝的版图内。康熙皇帝虽最终支持保留台湾的建议,内心深处仍然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19]保留台湾也只不过是为了消弭后患,免得“为外国所据,奸宄之徒窜匿其中”,给大清王朝再带来新的麻烦。事实上,康熙皇帝对台湾的海洋战略地位并不如以往有些论者所说的那样,有着高瞻远瞩的认识。
由上所述,有清一代王朝统治者“重陆轻海”的海洋观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立国思想上以农为本,重视农桑,轻视海洋。台湾归入大清版图后,清王朝部分开放海禁,但又严格限制民间制造海船,规定沿海各省渔船只许用单桅,梁头不能超过一丈,舵工水手不得超过20人[20],甚至连出海船只每船所带船员的粮食也有严格的限量规定,只许近海作业,不准开海远航。清王朝对海洋造船事业的种种限制,从表面上看,只是对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一种控制手段,而实际上其思想根源仍然在于传统“重农抑商”、“重陆轻海”的观念意识。在清统治者看来,开放海禁,虽能增加一些财源,缓和因禁海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但“商船一出外洋,任其所之……恐至海外诱结党类,蓄毒酿祸”[21],很可能会形成新的海上反清势力。因此,最稳妥的办法还是立足于农本,极力宣扬“四民之业,士之外农最贵……故农为天下之本,而工商皆其末也”。可见,清统治者的立国思想始终难以摆脱重农抑商、重陆轻海之传统观念的深层影响。
第二,是国防战略上以“禁海”代替海防,且倾向“防内重于防外”。作为以弓马骑射得天下的清王朝,素以游牧民族的剽悍驰骋疆场,而对波涛无常的海洋水战则不谙习。因此,对于占踞海岛、海战能力较强的郑氏海上武装力量,首先是采取“防海”、“禁海”、“迁界”、“限制夷船”、“杜绝接济”等陆上防御措施,将兵力收缩于内陆防守,而不注重掌握在海上的主动权,结果在以“禁海”代替海防的同时也就等于自动放弃了制胜海上的长远策略。这种禁海迁界、毁船内缩,把陆上防御套用到海上防御的“禁海”、“防海”思想也鲜明地体现在国防战略上倾向“防内重于防外”的特点。
第三,是国家海防战略指导思想上的“守土防御”。清初为了对付郑氏集团的海上抗清活动,清军水师成立伊始即强调“沿海各省水师,仅为防守海口、缉捕海盗之用,辖境虽在海疆,官制同于内地。”[22](卷135)实际上是缺乏放洋出海、制胜于海上的战略思考。后来虽然重用郑氏降将施琅等人,操练水师越海攻台而一统版图,但随着郑氏海上势力的消失,清朝的水军建设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国初海防,仅备海盗而已。”[22](卷138)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国家海防战略一直是立足于海岸、海口的防御,鲜明地体现了“守土防御”的基本特色。
由于清朝海防思想的不成熟,加之“重陆轻海”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平定郑氏海上势力之后,清朝水军的衰弱是必然的发展趋势。清嘉庆年间,“浙江战船俱仿民船改造,山东战船亦仿浙省行之,其余沿海战船,于应行拆造之年,一律改小,仿民船改造,以利操防。”[22](卷135)海上战船越改越小,火炮也又小又旧,加之水师训练荒疏,军纪废弛,“弁兵于操练事宜,全不练习。遇放洋之时,雇佣柁工,名为舟师,不谙水务,”已是徒“有水师之名,无水师之实,积弊相沿,废弛已极。”[23]而反观此一时期的西方世界,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近代海军建设开始进入武器装备发展的转折阶段,“就技术发展而言,海军必须从木壳船体、风帆动力和火药弹丸向铁甲、蒸汽动力和炮弹过渡。这一过渡过程中的每一步骤都是一场革命。”[24]1807年美国人富尔敦首先制成第一艘蒸汽动力轮船之后,英国、法国等相继把蒸汽动力用于作战船舰,提高海军的作战能力,同时在铁甲、火炮技术方面也取得长足的进步。当清王朝的水师走向衰落之际,西方世界的海军却在迅速发展,并借助海洋的力量进行海外殖民扩张。古老的中国成为西方殖民列强觊觎的对象,自然将出现前所未有的严重的海防危机。
二
耐人寻味的是,与明清中央王朝“重陆轻海”的观念意识有所不同,东南沿海地区地方官员的海洋观念则相对比较开放。这既与他们在滨海为官,了解地方民情有关,更与明清以降民间私人海上贸易的迅速发展,尤其是郑成功武装海商集团“通洋裕国”的海外贸易实践活动有相当的关系。
早在明万历年间,时任福建巡抚的陈子贞就指出:“闽省土窄人稠,五谷稀少。故边海之民,皆以船为家,以海为田,以贩番为命……一旦禁之,则利源阻塞,生计萧条,情困计穷,势必啸聚……万一乘风揭竿,扬帆海外,无从追捕,死党一成,勾连入寇,孔子所谓‘谋动干戈,不在颛臾’也。”[25]表达了对明中央王朝所定“禁海”政策的不同意见。他还认为,不仅不必禁海,而且对沿海居民实行开海通商还有利于统治者了解海外情况,掌握外情,对国家的海疆防御和财源收入也极有裨益,即“洋船往来,习闻动静,可为吾侦探之助。舳舻柁梢,风涛惯熟,可供我调遣之役。额饷二万,计岁取盈,又可充吾军实之需。是其利不独在民,而且在官也。”[25]
曾任两广总督的张瀚、给事中傅元初等人也主张开海贸易,既利民生,又弭寇患,而且有利于国家的财政税收。应当说,沿海一带地方官员反对“禁海”政策,主张开海贸易,绝不是一种偶然的现象。明代后期商品经济发展、私人海上贸易活跃,对传统“重陆轻海”观念意识所带来的巨大冲击,也对清代沿海地区的地方官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廷的禁海迁界令正式颁布不久,即受到一些沿海官员的非议。湖广道御史李之芳认为,东南沿海一带鱼盐之利,土产之饶,可为国家“富强之资”,“今五省之民,沿海已居其中,当道者不思制插安民,只欲尽以迁移,能使贼自毙乎?是贼未必能歼灭,未必能尽降,而国家先弃五省之土地人民。”“今兵不守沿海,尽迁其民移居内地,则贼长驱内地,直抵其城邑,其谁御之?!”[26](卷5)
时任广东巡抚的王来任也指出:“臣思设兵原以捍卫封疆而资战守,今避寇侵掠,虑百姓而资盗粮,不见安壤之策,乃缩地迁民,弃门户而守堂奥,臣未之前闻也。臣抚粤二年有余,亦未闻海寇侵掠之事。所有者仍是内地被迁之民,相聚为盗。今若展其疆界,即他盗亦卖刀买犊耳。”[26](卷6)明确反对禁海迁界,以安抚沿海居民。此外,施琅、姚启圣、范承谟、史伟琦等人也有类似的意见,反对禁海迁界,划地为牢,自我束缚。
如果我们将活跃于闽台两地的郑氏海上政权也视为另一种地方官府之象征的话,那么,整个地方层面的海洋观与中央王朝海洋观的区别,更集中体现在郑氏海上政权提出的“通洋裕国”的立国思想上。
明代后期,在东南沿海一带相继出现众多的私人武装海商集团中,以郑芝龙、郑成功父子的海商武装集团最为著名,其累积的资本之厚,号称“岁入以千万计,以此敌国”。郑氏集团为了发展海上贸易,曾一度借助明朝廷的名号和力量,铲除与之竞争的其他对手,垄断了东南沿海的海上贸易。
清入主中原后,郑氏海商集团的头号人物郑芝龙为了保住自己海上贸易的特权,未作坚决抵抗即投降清廷。而其子郑成功则继承家业,起兵海上,反清复明,并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建立起雄踞一方的郑氏海上政权。清人郁永河评论说,郑氏政权之所以能够以海岛为根据地,坚持抗清斗争十余年,主要原因就在于其控制了东南海上贸易,拥有巨大的“通洋之利”。事实也的确如此,郑成功凭借“通洋之利”与清王朝对峙,成就一番事业,其“通洋裕国”的立国思想集中反映了明清时期地方层面海洋观念的显著特点。
与中原王朝统治者以“农桑为本”的立国思想有所不同,郑成功认为“通洋”,即发展海外贸易,能够使国家臻于富强,不必非得固守“以农为本”的传统。他根据郑氏海商集团自身的发展,以及东南沿海地区的具体条件,曾向南明隆武帝奏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26](卷2)之策,主张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以通洋之利充实军饷,凭借沿海险要之地,抵抗清军的进攻。
清军入闽后,郑芝龙决意降清,郑成功规劝其父说:“吾父总握重权,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26](卷2)从这里可以看出,郑成功主张“大开海道,兴贩各港”,通过发展海外贸易,“以足其饷”,巩固国本,并将此作为反清复明的基本国策。郑成功这一主张实际上已显露出“以商立国”,向海洋空间发展的意涵,如果我们联系大航海时代以来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这种“大开海道,兴贩各港”,追求“通洋裕国”的立国思想的确有其“与时俱进”的时代价值和历史意义。
1650年,郑成功占领金门、厦门后,委派富有经商经验的郑泰、洪旭专管海外贸易,一方面积极建造航海大船,通贩日本、吕宋、暹罗、交趾等国,“行财射利,党羽多至五六十人”[27],另一方面分“山海两路,各设五大商”,向内地秘密收购商品,转贩外洋,获取高额利润。在郑成功的大力经营下,郑氏海商武装集团的资本更为雄厚,海洋贸易成为军需粮饷和其他费用支出的主要财源。
值得重视的是,在“通洋之利,惟郑氏独操之”的情况下,郑氏海商集团控制了东西二洋海上通商权,对侵犯其经济利益的荷兰海上殖民者也敢于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荷兰殖民者窃踞台湾时,因多方刁难郑氏海船到台湾贸易,郑成功“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物货涌贵,夷多病疫,至是令廷斌求通。”[28]迫使荷兰殖民者向其屈服。1661年,郑成功为了拓展新的抗清基地,消弭“通洋裕国”的潜在威胁,率军东征台湾,并于1662年初,把窃据台湾达38年之久的荷兰殖民者驱逐出去,完成收复台湾的壮举。
由上可见,郑成功“通洋裕国”思想的提出和实践,顺应了明后期以来东南沿海商品经济蓬勃发展的要求,也契合了大航海时代世界历史发展转型的大趋势。其大力发展海外经济贸易,并以此作为致国家于富强的主要途径,显然与历代中原王朝统治者“重陆轻海”,固守农桑为本的传统观念有所不同,这种对海洋经济资源的认识和利用的观念变化,已开始“透出一股活泼、开朗、新鲜的时代气息,显露出新旧冲突变动的征兆。”遗憾的是,由于郑成功复台后不久即不幸病逝,郑氏海商武装集团的海上政权在与清朝政权的抗争中失败而最终被剿灭,使这个一度曾执中国、日本、东南亚之间海洋贸易之牛耳的地方海上力量也就此销声匿迹。从当时的时势来看,一方面是西方海上强国不断地向东方海洋的殖民扩张,另一方面则是明清王朝统治者陆续地从海上“主动”退却,古老中国在万里海疆上影响力的衰落实际上已埋下了此后鸦片战争等连续失败的潜因。而令人扼腕的是,此一时期郑成功海商武装集团“通洋裕国”思想所带来的新旧观念交替的冲动,终究还是“为一场改朝换代的活剧所取代了”。
综上所述,“重陆轻海”与“通洋裕国”所反映的海洋观念,只是明清之际国人对海洋的社会属性和经济属性的不同认知,是国人海洋意识的淡薄和强化的不同而已。这在传统时代,“重陆轻海”观念对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当世界开始进入大航海时代,海洋作为人类的第二生存空间而影响到世界历史走向和历史发展格局时,传统“重陆轻海”观念所带来的深层影响却会因此而改变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在世界性海洋时代来临之际,缺乏海洋意识的传统国度注定要在未来的竞争中落伍,晚清鸦片战争及其之后的历史发展反复证明了这一点。这应该也是本文讨论“重陆轻海”与“通洋裕国”所反映的海洋观的意义所在。
[1]明太祖实录:卷68,明洪武四年九月辛末[O].
[2]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10,故元遗兵[O].
[3]孟森.明清史讲义:第二编,第二章.靖难[O].
[4]魏源.圣武记:卷1,开国龙兴记一[O].
[5]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卷50,奏稿[O].
[6]王胜时.漫游纪略:卷1,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九帙[O].
[7]清世祖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六月壬申[O].
[8]明清史料:丁编,第2本,申严海禁敕谕[O].(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刊本.
[9]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1[M].校注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
[10]陈寿祺.重纂福建通志:海防,正谊书院[O].同治七年重刊本.
[11]韩振华.一六五0——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时代的海外贸易和海外贸易商的性质[J].厦门大学学报,1962,(1).
[12]皇清名臣奏议汇编:初集,卷12,敬陈管见三事[O].
[13]连横.台湾通史:卷29,颜郑列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14]江日升.台湾外纪:卷13[O].
[15]黄叔敬.台海使槎录:卷4,伪郑逸事[O].
[16]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严禁通海敕谕[O].
[17]魏源.圣武记:卷8[O].
[18]施琅.靖海纪事:卷下[A].恭陈台湾弃留疏:附录八闽绅士公刊原评[O].
[19]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十月初十条;十月十一日条[A].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科选辑[C].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326-327.
[20]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57,兵部·绿营处分例·海禁[O].
[21]皇朝经世文编:卷83,施琅,论开海禁疏[O].
[22]赵尔巽等.清史稿.兵志六:卷135[M].北京:中华书局,1997.
[23]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24,兵23.9706[O].
[24](德)H·帕姆塞尔.世界海战简史[M].屠苏等译.北京:海洋出版社,1987.10.
[25]明神宗实录:卷262,万历二十一年七月乙亥[O].
[26]江日升.台湾外纪:卷5[O].
[27]明清史料:已编,第6本[O].福建巡抚许世昌残题本.
[28]杨英.先王实录[M].校注本.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87.
【责任编辑:陈红】
My Reflections upon the Different Views on Oceans of“Laying Stress on the Land but Underestimating the Sea”and of“Enriching the Country by Opening up Sea Routes”
HUANG Shun-li
(Department of History,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ere just in an important period once in a thousand years of international sea development history,but the rulers thereof,due to their copying the traditional patterns of thought,“stressed agriculture while restraining commerce”and“laid stress on the land but underestimated the sea”in terms of ideology of building its nation while in the strategy of national defense,they practiced“sea blockading”in stead of coastal defense and“safeguarded the land for its defense”,which reflected the lack of their concept of maritime development.Nevertheless,the local officials of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areas,ZHENG Cheng-gong in particular,raised and practiced the idea of“enriching the country by opening up sea routes”, which indicated the implication of building up the nation to develop to the maritime space.In the traditional age, the influences exerted by the different concepts on the sea expressed respectively by“laying stress on the land but underestimating the sea”and of“enriching the country by opening up sea routes”,to a certain degree,were of so minor importance that they could be neglected,yet,when the times of great navigation came,the impact of the concept of“laying stress on the land but underestimating the sea”could change the destiny of the state and the nation accordingly.
Ming and Qing Dynasties;times of great navigation;“laying stress on the land but underestimating the sea”;“enriching the country by opening up sea routes”;concept of the sea
K 928.44
A
1000-260X(2011)01-0126-06
2010-10-10
教育部博士点社科基金项目“近600年来中国海洋经略思想的衍变及其影响”(03JB770024)
黄顺力(1953-),男,福建永安人,厦门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从事历史学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