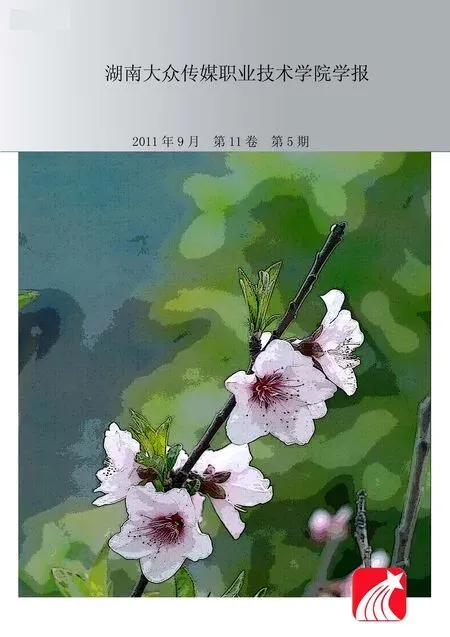“湖南电视现象”研究
冯一粟
(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100)
一、“领异标新”的湖南电视
当我们审视中国电视发展的轨迹,将清楚地看到自20世纪末出现的一个亮点——湖南电视现象。在经济不甚发达、电视基础也曾相对薄弱的湖南,“电视湘军”如一匹黑马脱颖而出,短短的时间里超越了自己,也超越了几乎所有的省级电视台,直逼中央电视台诸频道的收视率。其标新立异的风范使它迅速成为广大受众津津乐道的一个话题,其节目从形式到内容也被同行争相仿效,并形成品牌效应。那么,湖南电视的核心竞争力究竟是什么呢?
(一)娱人耳目的电视理念
80年代,湖南电视办得十分平淡、平庸,乏善可陈;90年代中期,湖南经济电视台的创建和湖南电视台的上星引发了三湘大地电视业的有序竞争;90年代末,随着生活频道、文体频道等相继推出,电视湘军已经逐步形成了比较完备的系统,群雄并峙,各领风骚。人们在惊羡之余,突然发现湖南电视的制胜之道竟然简单到只有两个字:娱乐!
1. 娱乐节目的滥觞——经视风暴
外省受众所了解的湖南电视很可能只是湖南卫视,而实际上湖南电视打娱乐牌的始作俑者是湖南经济电视台。1995年12月28日,按商业化运作的湖南经济电视台开播,其全新的栏目和节目编排风格使广大受众耳目一新。该台主打娱乐类栏目《幸运3721》,收视率最高时达60%以上,经济电视台因此一炮而红。受此鼓舞,“幸运”系列、《真情对对碰》、《故事酒吧》等娱乐节目不断涌现,一时间“经视风暴”席卷湖南,引发了湖南电视媒体的激烈竞争。不仅如此,经视台还率先推出电视新闻直播,率先实行从员工到台长的全员聘任制和末位淘汰制;在电视剧制作上,一改琼瑶电影、电视的悲剧范式,率先以喜剧化、娱乐化的风格推出琼瑶作品,其制作的《还珠格格》在全国各地播出时收视状况可谓万人空巷。湖南经济电视台是一个按公司模式运作的电视台,这比传统上作为行政事业单位运作的电视台具备了更多的市场因素。经济电视台是在银行贷款的困难条件下开播的,而在开播一年后便归还了本息,第二年创收增长一倍,第三年达9900万元,这些数据说明了新的电视理念和新的机制能给媒体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在经视一浪高过一浪的冲击下,湖南电视台感到了巨大的挑战。
2. 娱乐节目蔚成风气——卫视星空
就在打造“经视品牌”之际,湖南电视台的内部改革已经在悄悄进行。推行节目制片人制,让节目制片人享有一定的人、财、物支配使用权;通过内部机构调整,将台里的中层干部换上一大批年轻有为的骨干;将当时一套节目剥离为三套节目,新闻时政类综合频道、文体频道和图文信息频道平行播出,并于1997年1月将第一套节目送上卫星直播。此外,还实行了节目淘汰制,即对所有节目通过收视率调查进行评估,最后两名自动淘汰出局,被淘汰的节目制作人员另谋出路。机制活,栏目兴。由模仿经济电视台同类娱乐节目起步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栏目不断涌现,并借助更为先进的传输覆盖手段迅速走出湖南,走向全国,湖南电视台的收视率因此直线上升。从《快乐大本营》到《玫瑰之约》,从《有话好说》到《晚间新闻》,湖南电视的许多栏目都深受广大受众喜爱,为许多外省市媒体竞相仿效。从主持人的新异台风到话题涉及的范围角度,从播报方式的特殊选择到新闻资讯的加工方式,都使湖南广播电视业蜚声海内。 此后,湖南卫视的收视率直线上升,直逼中央台诸频道。
3. 娱乐节目的转型——从娱乐大众到大众娱乐
深谙媒介与受众的供求关系的湖南电视人灿烂了一把娱乐星空之后,迅速开始了娱乐节目的转型,从娱乐大众到大众娱乐被提上议事日程。因为信息时代的电视节目不应设立更多的门槛和权威,要让大众掌握话语权,所以这一转变带有必然性。善打娱乐牌的湖南电视人先是以《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等节目开路,迅速抢滩成功,做成最大;然后以“大众”为名,行“大众”之事,各频道从2002年开始陆续主办《星姐选举》、《超级男声》、《超级女声》,《完美假期》、《绝对男人》、《明星学院》等选秀节目。2004年,《超级女声》通过湖南卫视走向全国,推出《快乐中国超级女声》节目。这种充分体现大众诉求的节目形态的亮眼推出掀起了新一轮全国娱乐节目的激烈竞争,电视第一次彻底放下身段,接近普通大众,观众不再需要仰视媒体。
(二)湖南电视娱乐节目的主要特征
后现代主义全面进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成为当下最为突出的文化景观。后现代主义特征用一句流行的口号可概括为“跨越边界,填平沟壑”。就电视释放娱乐功能而言,历来壁垒森严的高雅的综艺节目与不登大雅之堂的夜总会节目的界墙当然被推倒,以往自诩为“高级”的、“严肃”的、“纯正”的文艺晚会失去了贵族气而转向大众化。具体来说,鲜明地表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1. 边缘化的节目形态
以《超级女声》等系列节目为例,这类节目是当今电视界广为流行的“真人秀”节目,其制胜法宝就是原生态的电视形式。一位歌手能不能在第一时间让人印象深刻,迅速引起大众关注,关键在于他有没有扎实的功底和独特的音色。在初选阶段,选手们均用清唱。在卡拉OK美化人们的歌声多年后,选手们终于要用实力唱歌了。没有混响美化声音,没有升降调的方便,没有定调的基准音,没有引子、过门让你换气喘息,没有歌词字幕提示。电视直播也舍弃了灯光、舞台、音响等元素的修饰,一切都如生活本身那样,通过无修饰的清唱和直播,将参选者最原始的状态展现在观众面前。选手们或紧张或放松,或胆怯或自信,其参赛心情得以真实展现。与其他声乐比赛不同的还有评委,并不专业的评委都会用较为苛刻的个人标准和不留情面的语言直击选手软肋,这也是“秀”的重要一环。赛后各方面信息显示,评委对选手的评语引起极大争议,激起强烈的社会反响,其程度甚至超出主创人员预想。在这些酷评家把持下,绝大多数选手出尽洋相,丢尽面子,一个个面红耳赤,尴尬出局。鉴于此种状况,有人认为这不是审美,而是审“丑”。但问题不在于选手的表现是否美,现场效果是无法出自预谋的,随机发生的穿帮、失误,甚至丢人现眼比比皆是,而观众所期待的就是这种直播节目所带来的同步感、真实感和权威感。
2. 无深度的节目内容
与边缘化相伴而生的是感性增强,理性淡化,从而消解节目内容的深度。湖南电视娱乐节目林林总总、形态各异,但都是消费时代的文化商品。娱乐节目不会关心终极真理,缺乏社会批判精神,缺乏独创性。娱乐为本的媒体关注世俗的感情需要,遵循市场规律,经济冲动甚于文化冲动。如《快乐大本营》、《天天向上》、《越策越开心》等栏目,每一个环节都是纯趣味性的,其游戏环节有时是低龄化的。《仇晓的闺中密友》等节目是一串串缠绵密语,有些话题蕴蓄的伦理道德内涵常常让主持人和嘉宾都难以掌控。以警匪、言情或戏说历史人物为主打的影视剧,关心的只是情节的煽情性、挑逗性和刺激性。在只赚笑声不催人落泪的指挥棒下,这些表象所附丽的深度意义内涵都被毫不留情地剥离和剔除了。
3. 普遍化的游戏心态
湖南电视娱乐节目远离了思想重负和精神跋涉,推出的是一场场游戏与狂欢的视听盛宴,审美文化变成了娱乐,变成了一连串游戏。
“游戏”是审美文化中的一个关键词,当年席勒在提出这一概念时用以指人类所从事的感性与理性相统一的自由活动,并不同于后来那种日常世俗的理解。湖南电视节目特别强调观众的参与度,且呈现愈演愈烈之势。《超级男声》和《超级女声》所遵奉的“人人都有歌唱的权利”实际上变成了“人人都有游戏的权利”,然而,游戏满足的只是受众的当下快感,并不都是美感。湖南电视人今天导演的这一场游戏,却被雅斯贝尔斯在许多年前不幸而言中:在技术主义和实证主义统治的时代,公众的事物变成纯粹的娱乐;私事则变成刺激与疲乏的交替,以及对新奇事物的渴望;这些新奇事物就像永不止息的水流,迅速地流向遗忘之乡,没有连续性,只有消遣。
湖南电视娱乐节目正是通过对艺术形式的为所欲为,对艺术边界的横冲直撞,对大众娱乐诉求的恭迎俯就以及与市场的合谋,确立了他律的文化立场,迎合了市场的需要。可谓深得后现代之神韵。
二、湖南电视现象产生的背景
(一)实用主义的哲学基础
当代哲学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就是崇实、尚用、拜物的倾向。雅斯贝尔斯曾指出:今天,“哲学不再是一小撮人、特权分子的专利;因为只要个人迫切地反省,如何才能生活得最圆满,哲学就成了无数大众的切身之事。各个学派的哲学,只要能使人度一种哲学式的生活,它就有成立的理由。”正是在这种世俗化、生活化、感性化趋势的驱动下,实用主义成了当代哲学风头最健的思潮。
没有一定的哲学基础就没有一定的文化形式。文化的阐释系统靠哲学搭建,文化行为的根本性依据和标准靠哲学提供。当代审美文化的突出特征是娱乐性、休闲性、刺激性、装饰性、浅表性,其根本原因在哲学基础。当代审美文化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众的文化消费行为,遥控机顶盒、手机短信、网上投票等行为是受审美趣味支配的。反观湖南电视现象,其歌声、笑声中穿梭徘徊的正是“实用主义”的幽灵。无论是早期的《快乐大本营》、《玫瑰之约》,还是晚近的《天天向上》、《挑战麦克风》等节目,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对提高收视率管用、对吸引广告有效的。对广大受众而言,湖南电视娱乐节目也正为他们提供了消遣、休闲、娱情的需要,因而也是有用的。
(二)虚无主义的社会心理背景
雅斯贝尔斯曾经将人类历史分为四个时期,并将第三个时期(即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称为“轴心时代”,人类到了这一时期才形成了自己的精神轴心,开始进行哲学思考,对历史有了明确的概念,有了宗教信仰和价值体系,有了艺术和美学,力图建立社会秩序,显示了在知识和精神方面的巨大创造性。他告诉人们,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时势是历史转型时期那种旧的东西已经破除,而新的东西尚未建立的虚无状态,人类社会心理正处于从旧的轴心时代向新的轴心时代过渡的空白地带。
在被虚无主义阴云笼罩的消费时代,追求真理已经失去了原有的魅力,真理在现实面前往往抵不上有用、有趣,人们普遍重视的是“当下快感”。有用的东西才能得到人们的青睐和礼遇。理想、信念、信仰之类的字眼已不合时宜,滚滚红尘,盛行的是享乐主义、游戏心态、休闲风习。人们玩电视、玩电脑、玩电影、玩技术、玩音乐、玩人、玩深沉,一个“玩“字,道出了这个虚无世界的普遍社会心理。既然“娱乐道德”已经取代了传统道德成为热门话题,虚无主义的社会心理便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从某种意义上说,湖南电视娱乐化倾向就是由虚无主义导演的游戏与狂欢的盛宴,它以迎合的姿态逃避现实、品味世俗,与身陷虚无而不知虚无的大众深深共鸣,成为麻痹大众的致幻剂。
(三)为我所用的境外媒体文化影响
湖南电视人是“拿来主义”的急先锋。中国电视的起步较发达国家晚,无论是电视创作观念和经营思路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脉络一致,处于初步的摸索阶段。与其经过长期的缓慢摸索,不如先直接借鉴国外的先进节目形态和经营思路,在给长期封闭视听的中国观众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同时,电视人可在这一过程中以静观动,边学习先进的电视理念,边了解中国观众的观看心态,从而创造出既符合当今国际电视潮流又符合本土观众观看心理的,具有地方特色的节目。湖南电视人还意识到,模仿与创新并不矛盾,在模仿基础上的创新恰恰能给中国电视屏幕带来新意和生机。作为一个以娱乐为主打品牌的电视媒体,湖南电视台借鉴境外媒体的娱乐节目形态以娱乐资讯、真实娱乐、娱乐游戏等迅速吸引受众视听,抢占了市场先机;其后又意识到娱乐不仅是一种节目形态和生活方式,在电视节目的引导下,还会产生一种社会效应和公众话题。根据目前国际电视潮流,娱乐节目中博彩及真人秀节目大行其道,成为公众娱乐生活的主要话题,代表性节目有美国的《生存者》和英国的《阁楼》等。湖南经视的《完美假期》即模仿英国的《阁楼》,它在2002年暑期推出时几乎给湖南观众带来一个超乎想象的节目形式和全新的审美体验,一时间,欢呼声诋毁声此起彼伏,但无论如何,这一节目的出现对于本土受众来说完全是另类的电视表达,它让电视人和受众看到电视节目形态不会穷尽。
《超级男声》、《快乐中国超级女声》这两个选秀节目借鉴的节目形态是英国的《超级偶像》和法国的《明星学院》,节目的共同点都是通过演唱选拔歌手,但湖南的这两档节目对舶来的节目形态作了较大的改造,用主创人员的话来说就是“无形态的形态”、“无技巧的技巧”,整个流程的绝大部分是“原生”形态。与国外这两档节目一脉相承的都是唱歌,不同之处在于,国外是“明星”唱或唱成“明星”,初赛不播出,所以从本质上说还是“精英文化”主导。而湖南的这两档节目则重在展示初赛和淘汰赛的过程。专家把握初选,十人以后由大众通过投票决定。
两相比较,如果说国外两档节目是节目形态的胜利,那么也可以说,湖南的同类节目是情感模式的成功。湖南的节目形态操作简单,失败的风险较小。选手没有任何门槛,人人都有歌唱的权利,舒服、快乐,人们关于生存、生活状态的原始诉求在这里得到了释放,而由心而生的快乐表达权力的充分行使,本身就是一股强大的平民洪流。从心理学角度看,在人类心灵深处,存在着一种自我欣赏、反躬相思的原始情节,即自恋情节,又叫“那喀索斯情结”。自恋与焦虑相连,驱使人们产生强烈的表现欲和暴露欲,而《超级男声》等节目形态恰能满足人们的自恋需求,从选手的数量大而普遍水准不高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国外的节目追求艺术的真实,一切均在媒体意图明确的操纵与掌控之中,而湖南电视人则模仿生活的真实,如评委在初选过程中与表现特别好的和特别差的选手对话均予以直播。国外是以明星、偶像娱乐大众,明星秀给大众看,虽然其更具有主动控制力,如现场观众参与等等,但本质未改变,仍是精英文化主导,就像同是歌唱节目的央视《中国青年歌手大奖赛》等节目,这种阳春白雪型的节目总是给普通大众以高高在上的印象。可以说,湖南这类节目和央视《梦想中国》这类节目的流行,使得长期缺失的中国大众诉求在这种节目形态中找到了满足。
节目形式是该原创还是克隆,是近年来电视业界人士考虑最多的问题。近年来,由湖南卫视发起,全国电视娱乐节目克隆模仿风甚嚣尘上。有人大声疾呼要刹住这股克隆风气,盲目跟风和“千台一面”的现象将使中国电视提供给观众的是零选择,终将为观众所抛弃。也有专业人士提出,拙劣的原创比一味地克隆更可怕,在没有作市场论证和受众目标分析的情况下,无视国际影视潮流,仅凭一时兴起而自创的节目无异于一场无底牌的赌博,终归只能惨败。应该说,通过原创改进还是克隆精品来提高中国电视节目的品质,正是中国电视目前在十字路口徘徊的重要问题。
三、湖南电视现象评价
湖南电视现象是社会转型期媒介发展的必经之路,是消费时代审美文化的正常表现,是全球经济一体化时代的适者生存之道。中国电视向来稳守传媒主体立场,即传者本位,忽视电视受众和市场。如何寻求双重角度下的一种对接就是电视改革所必须面对的新课题。湖南电视娱乐类节目准确找到了受众和市场,这在中国媒体面临境外媒体挑战的时候有可资借鉴的经验。湖湘文化特有的“浩然独往,无所依傍”的精神在这里找到了最好的注脚。然而,人文精神缺失、媒介的教化功能淡化、受众想象力退化、媒介产品生命力弱化、频道专业化步履艰难,却不能不说是沉重的代价。
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和业界权威人士对湖南电视现象作过许多评介和研究,对其市场化、集团化、频道专业化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探讨,这些研究自然有其学术价值,但不足的是缺乏调查研究,止于“隔靴抓痒”。湖南广电集团内部回应社会批评的声音往往也显得就事论事,尤其是对电视的内部规律研究不够,现象罗列多,一般描述多。湖南电视成功的原因没有研究透,存在的根本问题也未能准确揭示,未来发展的思路未理清,其对中国广电事业发展的意义也缺乏研究。
本文通过对湖南电视现象的产生、发展、特征、社会基础、评价的研究,初步作了一些梳理和剖析。我们相信,以湖南电视现象为个案,审视、回顾、总结电视传媒文化作为精神产品,在生产、消费、再生产诸多环节中的规律、经验和教训,探索其未来发展的思路,这不仅对湖南广播电视的发展大有裨益,对中国广播电视应对即将到来的境外媒体的挑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责任编辑 朱 义)
[参考文献]
[1] 雅斯贝尔斯. 当代的精神处境[M]. 北京:三联书店,1992: 143-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