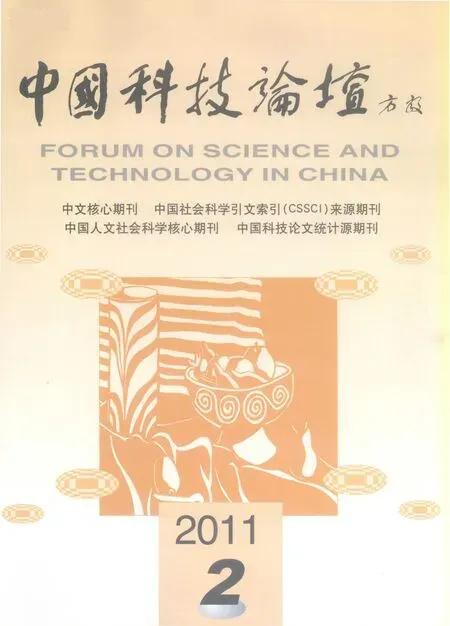绩效结构理论及其职业群体新视角:科技工作者三维绩效
张廷君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绩效结构理论及其职业群体新视角:科技工作者三维绩效
张廷君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7)
选取职业群体视角,对现有绩效结构理论进行了回顾、归类与评述,从中刻画出其内在逻辑联系与研究规律,提出伴随知识社会发展,以科技工作者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将成为未来绩效结构研究的主流。本研究在理论综述基础上,对科技工作者这一职业群体的绩效结构进行了理论探索。
绩效结构;科技工作者;三维绩效
绩效结构理论是研究个体绩效的基础。在现有研究中,学者们一般从研究的时间历程、绩效的理论内涵等角度对绩效结构理论进行梳理和综述;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以职业群体视角对绩效结构理论进行的归纳却几乎没有。然而,不同的研究对象恰恰是绩效结构划分和界定差异性的主要原因。此外,随着社会雇佣形式的不断创新与变革,组织边界渐渐模糊,打破组织框架,基于职业群体进行绩效结构研究势必成为未来绩效结构研究的重点与主流,这意味着绩效结构的研究将迎来新的视角——职业群体视角。以职业群体视角对绩效结构理论进行梳理,即是将现有绩效结构的相关研究按照不同的适用群体(研究对象)加以归类及流派划分,并寻求后续研究的契机。
1 职业群体视角下的绩效结构理论
1.1 产业工人——结果论
Munsterberg是最早从个体角度对绩效进行研究的学者之一,并将绩效界定为结果[1];Bernardin等提出绩效即工作的结果,因为工作结果与组织的战略目标、顾客满意度及所投资金的关系最为密切[2];Richard S.Williams亦持相近观点,他将绩效定义为员工在特定时间内,由特定的工作职能或活动所创造的产出记录[3]。这种以结果来衡量的绩效,也被部分学者定义为角色绩效,即满足或超过工作职责标准的数量或质量的绩效[4]。Murphy指出角色绩效是与特定工作相联系的工作职责与责任的完成[5];Welbourme等人进一步将角色绩效明确界定为“工作产出的数量和质量”[6]。
以上视绩效为结果的学术观点,较适用于组织内的产业工人,并不适用于高端员工,本研究将其整合为绩效“结果论”流派。绩效的结果论观点,经历了将绩效等同于完成任务、单一强调数量,发展为强调数量与质量统一,再到清晰界定产出结果需与特定工作相联系的进化过程。绩效结果论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与较强的操作性,但也有明显的弊端,包括导致员工忽视过程与人际因素,组织无法及时纠正偏离行为,出现决策短视,无法发挥绩效管理的监督职能等。
1.2 管理人员——行为论
随着绩效研究的深入,绩效结果论不断受到新观点的挑战。学界逐渐意识到许多工作结果并不一定是个体行为所致,可能会受到与工作无关的其他影响因素的影响[7],尤其对于组织中的管理人员更是如此,他们的工作往往无法通过定量结果加以衡量。因此,随着学界关注的研究对象从产业工人向管理人员的转移,学者们对绩效含义与结构的判定逐渐由对结果的关注转移到对工作行为的关注上[8]。本研究将此类学术观点整合命名为绩效“行为论”。
Campbell提出绩效并非行动的后果或结果,其本身就是行动,并将工作绩效定义为“由个体控制下的与组织目标相关的行为,不论这些行为是认知的、生理的、心智活动的或人际间的”[9]。这一观点同样面临着理论窘境:绩效是个体在工作中的行为和行动,但是并非所有的行为,即所有的绩效,都和产出相关[10],如何界定与规定产出不相关的那部分绩效就成了后继研究的关注焦点。Katz和Kahn更早发现了这种区别,并提出了三维分类法对职务绩效进行划分:加入组织并留在组织中;达到或超过组织对员工所规定的绩效标准;自发地进行组织规定之外的活动[4]。但碍于研究所限,Katz和Kahn并未对这一发现进行有效总结,直到Borman和Motowidlo才解决了此问题。
Borman和Motowidlo提出绩效是可以评价的、多维度的、连续的与组织目标相关的行为结构体,并在组织公民行为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OCB)的研究[11-12]基础上提出了任务绩效(Task Performance,TP) 与 关 系 绩 效(Contextual Performance,CP)二维结构理论。在此研究的基础上,Van Scotter和Motowidlo又进一步将关系绩效归类为人际促进(Interpersonal Facilitation)和工作贡献(Job Dedication)两个维度[13]。Coleman和Borman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将关系绩效再次进行分类,形成了基于行为的三维绩效模型:人际间的公民绩效(Interpers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组织内的公民绩效(Organizationgal Citizenship Behavior)、工作/任务责任感(Job/Task Citizenship Behavior)[14]。但由于关系绩效中的人际间公民绩效并不能有效区分行为对组织是否有益,Rotundo和Sackett对此进行了修正,在任务绩效-关系绩效模型下,他们将绩效明确界定为“个体所能控制的对组织目标具有贡献的行动或行为”[10]。
任务绩效与关系绩效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了高端员工的工作性质与绩效特点。但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环境变化与系统动态性日益成为现代组织的主要特征之一,任务绩效-关系绩效模型显然无法有效地解释动态变化环境中个体对新环境和工作要求的适应性问题。因此,Allworth和Hesketh指出应在任务绩效-关系绩效的基础上增加员工应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绩效(Adaptive Performance),并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适应性绩效确实独立存在于任务绩效与关系绩效之外[15]。Pulakos等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适应性绩效的结构及影响因素进行了探讨,提出了适应性绩效的8个维度:处理紧急事件或危机情境、处理工作压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处理不可确定性及不可预测性的工作情境、学习新的技术和程序、人际适应性、文化适应性以及身体适应性[16]。对于适应性绩效在绩效结构中的位置,学者们持不同观点。Hesketh和Neal把适应性绩效视为相对于任务绩效—关系绩效模型的一个独立结构,是与二者并列的第三个维度[17];也有学者认为它仅仅是对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的补充;还有学者提出适应性绩效是一个比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更为宽泛的概念,是新环境下对绩效概念的重要补充[18]。
随着该流派观点的引入,中国学者以管理人员作为研究对象开展了多项跨文化研究,力图验证该模型是否能应用于中国的组织实际,但研究结论差异较大。孙健敏、焦长泉提出中国管理者绩效的3个维度:任务绩效、个人特质绩效和人际关系绩效,其中,“个人特质绩效”是对任务-关系绩效模型的拓展[19]。王登峰、崔红则得出了包括任务指向和个人品质两个维度的中国基层领导者的工作绩效结构,同时认为就中国的党政领导干部而言,要区分他们的任务绩效和关系绩效实际上是不可能的[20]。陈亮、段兴民针对组织中层管理者工作绩效也做过类似研究,提出在中国文化条件下,组织中层管理者的任务绩效、关系绩效和适应性绩效实际上是不可分的[21]。梁开广发现,中国企业主管在评价下级“工作绩效”时,往往已包含了对关系绩效的评价[22]。樊景立在研究中则发现组织公民行为存在的文化差异,如西方人的组织公民行为维度包括了“运动精神”和“殷勤有礼”,而中国人的组织公民行为维度中包括了“人际和谐”和“保护公司资源”[23]。
绩效行为论流派的观点虽在考察员工,尤其是管理人员适应性及其对组织目标所作贡献方面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现有跨文化研究结果显示,行为论流派所提出的绩效结构模型未必适用于中国的组织特点。
1.3 知识员工——创新性行为结果论
随着知识社会的到来,结果论、行为论的适应性出现落差。一方面,结果论与行为论均忽略了研究对象本身的成长、发展和学习,另一方面,基于此的绩效管理模式也易导致绩效管理陷入只关注研究对象过去成绩与组织效能贡献,忽视其潜能提升与未来发展的误区,但“潜能发展”却恰恰是知识员工最主要的绩效特征之一。因此,在对知识员工绩效结构的研究中,学者们普遍认同,绩效结构不仅要包括任务的结果,也需包括任务所拥有的行为及素质,同时在任务的行为与结果中强调创新与学习的维度。基于此,形成了绩效结构研究中的“创新性行为结果论”。
Brumbrach的研究提出绩效包括行为与结果,行为是由从事工作的人表现出来的,将工作任务付诸实施,行为是结果的工具,其本身也是结果,是为完成工作任务所付出的脑力和体力的结果,并且能与结果分开进行判断[24]。杨杰、方俐洛和凌文铨等人也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组织雇员绩效评价的三个维度:特质评价指标、行为评价指标和结果评价指标,并建立了经由“知识、技能、能力、努力、外部条件”(KSAO)等绩效结构因素的路径分析模式[25]。仲理峰和时勘提出,当对个体的绩效进行管理时,既要考虑投入(行为),也要考虑产出(结果),绩效需包括应该做什么和如何做这两个方面[26]。田家华、张光进和姜炜在对知识员工绩效结构的研究中,基于任务绩效-关系绩效理论框架,将任务绩效进一步细化为任务绩效行为与任务绩效结果,强调绩效是行为与结果的统一,并在此基础上参照Milkovich等人的分类方法[27],将知识员工的绩效考核分为基于员工特征、工作行为和工作结果三大类[28]。
知识员工群体日益受到关注,“绩效应侧重创新与学习”的观点也随之发展起来。该观点认为,在知识社会,工作绩效不仅是对过去的追溯,更需关注未来与潜能。在行为-结果绩效结构中,应体现员工的成长、发展、创新与学习特质,这些因素决定了他们未来能做什么。London和Mone提出了学习绩效,认为学习绩效应包括参与学习的意愿、学习的效率、获得新的技能、表现出绩效的提高[29]。Scott和Bruce则建立了个体创新行为的路径模型,该模型为后来的创新绩效研究提供了研究基础。Scott和Bruce认为,创新行为是一个过程的集合,开始于问题认知、思维或方案的产生,终止于完成创新思维并应用于实践[30]。Janssen则进一步对创新行为进行了归纳,提出个体创新绩效包括三个维度:创新思维产生(Generation)、创新思维促进(Promotion)和创新思维实现(Realization)[31]。国内学者在以知识员工为对象的研究中,也逐渐开始关注绩效中创新、学习的成分,柳丽华、徐向艺提出,工作绩效除任务绩效、关系绩效外,还应包括远端绩效,即员工通过过去一段时期的工作行为所积累的能够提升组织适应性、为组织的未来继续做出贡献的能力[32]。廖建桥、龙立荣通过实证研究,提出了基于四个维度的雇员工作绩效结构:任务绩效、关系绩效、学习绩效(学习意愿、行动与结果)以及创新绩效(创新意愿、行动与结果)[33]。
绩效结构研究中的“创新性行为结果论流派”重视员工贡献于未来的潜能与素质,因此提倡将创新与学习因素融入行为-结果的绩效结构中。这一流派的观点与知识员工的绩效特征相适用。但该流派仍存在不足:创新与学习的要素特征在绩效结构中的位置及如何在行为绩效、结果绩效中得以体现均未获详细解释——这与知识员工作为一个较为宽泛的概念本身有直接的关系。
1.4 研究述评
在基于职业群体视角对现有绩效结构理论进行的流派归纳与梳理中,可看出绩效结构研究发展的脉络及未来研究的趋势。主要体现了以下特点:
首先,绩效结构的载体,经历了从一般研究到特定研究,从产业工人到高端员工的研究发展历程。早期的研究并未对研究对象进行细分,随着研究的深入及对绩效结构差异的认知,学者们开始对特定群体进行绩效结构的讨论。起初的讨论主要围绕产业工人,因此更多的研究成果是以结果作为绩效结构的唯一维度。随着工业社会的发展,以至知识社会的到来,研究者的视角逐渐从产业工人领域发展为对高端员工的关注,以对知识员工及其中的管理人员的研究居多,并形成了绩效结构研究中的“行为论”与“创新性行为结果论”流派。
其次,绩效结构的维度,经历了从单一维度向多元维度研究的拓展过程。早期,碍于研究水平以及研究对象的层次所限,学者们对绩效结构的界定主要是单一维度,即绩效是结果。随着认识的深入,对行为的考量逐步纳入绩效的结构中,行为本身的多元性特点开启了绩效结构多维研究的视野,Borman和Motowidlo[11,34]的“任务-关系绩效”成为了绩效结构多维研究的里程碑。此后,绩效结构的多维性渐成学术界的共识,学者们通过研究提出了许多具有创见性的观点,但因研究对象或视角的差异,结论各不相同。
第三,绩效结构中的侧重点,经历了从关注结果到关注创新与学习的纵深发展历程。这种变化主要源自知识社会的现实需要。知识社会是一个提倡创新的社会,知识与技术所带来的经济增长是发展之本,这决定了组织对雇员的评价将不仅关注他们当前做了什么,还应关注其创新、学习与潜能,即他们未来还能为组织带来什么利益。
综上所述,绩效结构研究的发展趋势将是以研究对象为区分形成不同的流派领域。现有研究中,学者们主要以Drucker划分的知识员工为研究对象,但知识员工中的科技研发人员与各类管理人员之间的工作特征差异较大,将二者放置一体加以研究,将造成知识员工绩效结构内部异质性突出,降低研究的严密性。因此,虽以基于工作性质划分的科技工作者群体为绩效结构研究对象的成果鲜少,但随着分工日益细化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对科技工作者绩效结构以及激励机制的研究将形成重要的研究领域。
2 职业群体视角下绩效结构研究的理论拓展:科技工作者三维绩效
随着世界科技竞争加剧,各国均以提高创新力作为提升国力与保障发展的战略重点。而科技工作者正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其关键在于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绩效。科技工作者的劳动属于复杂劳动,具有高成本与高价值性,因此对该职业群体进行的绩效结构研究已渐渐积聚,并势必基于此群体形成新的绩效结构流派,这一流派也将成为未来绩效结构研究主流。本研究将在前人理论的综述基础上,对科技工作者这一职业群体的绩效结构进行推演与探索。
2.1 科技工作者的界定及其绩效特征
对某一特定职业群体的绩效结构研究离不开对其群体界定及绩效特征的分析。本研究中的科技工作者是打破组织界限,以工作性质划分的职业群体,是从事科研创新活动的人员组成,具体为各企业、高校、研究院所以及部分政府部门研发机构中从事科技研发、科技管理的科技研究人员,以自然科学专业背景的科技工作者为研究主体,同时包括少量管理科学、社会科学专业背景的科研工作者。科技工作者与知识员工的概念范畴存在差异。Drucker首次提出知识员工的概念,认为知识员工是指“那些掌握和运用符号和概念,利用知识或信息工作的人”[35],可见,知识员工的含义远较科技工作者来得宽泛。因此,现有知识员工工作绩效特征的研究不宜随意嫁接到科技工作者群体。对科技工作者工作绩效特征的研究成果并不多。陈建安、李燕萍通过实证方法比较了知识员工中管理类和研发技术类员工绩效特征后,提出研发技术类知识员工与管理类员工相比,在工作过程上,仅仅靠观察工作行为无法预测出其工作结果;在工作结果上,技术类员工的工作结果侧重于数量考评,工作任务较难分解,个人对于工作成果的贡献往往难以精确界定和衡量[36]。
在总结借鉴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中国科技工作者工作绩效特征主要为以下四点。
(1)科技工作具有价值性与时滞性。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是科技工作的价值性所在,而科技工作者的创新活动是通过产出科研成果实现其价值的,因此,对科技工作者绩效结构的界定不能仅仅关注行为,而忽视结果绩效这一维度。另一方面,与一般劳动活动不同,科技工作者的绩效成果转化具有不确定性与时滞性,这又决定了行为绩效同样是科技工作者绩效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创新的过程既具有必然性也具有偶然性,一般来说,创新行为投入会产出创新成果,但是在付出了辛勤的努力与投入之后,却无法得到预期产出的情况也会出现,科技工作者的绩效成果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但这些未产生预期成果的投入却也不能被视为无效行为,因为科研工作需要反复论证与探索,每一次的投入无论成败都是为下一次的探索奠定研究基础;此外,创新活动的投入与产出并非接踵而至,科研创新活动的成果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获得与应用,绩效结果具时滞性。可见,只强调科技工作者的工作行为而忽视工作结果,将偏离科技工作的价值目标,有失效率;只强调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结果而忽视工作行为,又有违科技工作的客观规律,有失公平。故本研究认为行为与结果应并存于科技工作者绩效结构中。
(2)科技工作具有专业性与创新性。
与一般管理活动等其他工作不同,科技工作者所从事的科研活动本身即创造性的活动,这决定了科技工作者要实现工作目标就必须具备较强的创新潜能及专业基础,是所从事领域的专门人才,且保持学习状态,使研发能力始终处于专业前沿。因此科技工作者的工作行为与结果应重点体现创新、持续学习及潜能。本研究借鉴“创新性行为结果”流派相关观点,以参与的创新活动、创新行为投入、学习投入作为科技工作者行为绩效的衡量,以产出创新成果作为对科技工作者结果绩效的界定。
(3)科技工作具有组织承诺与专业承诺可分性。
组织中,理想的高绩效员工不仅要表现出有利于组织发展的行为绩效与结果绩效,还需具有对组织的高度认同感以及愿与组织共成长的组织承诺。前者既是对自我专业的承诺也是组织承诺,后者属于对组织的承诺。但对科技工作者而言,组织承诺与专业承诺往往可分。由于科研工作是具复杂性的高难度工作,因此对组织具有高承诺的科技工作者,并不一定能表现出高的创新行为与创新结果,另一方面,由于科研工作是自主性与专业性的工作,科技工作者进行科研投入的过程本身也是增加自我内在价值的过程,因此高行为与结果绩效的背后并不一定意味着其对组织具有高认同感,其背后既可能是利己与利他动机的良好结合,也可能单纯出于增加自我价值的利己动机,一旦有更好的组织提供更高的发展平台,离职现象就会出现,组织损失无可避免。这意味着,对组织而言,科技工作者绩效的结构不仅包括反映创新与学习的行为绩效与结果绩效,还应包括反映组织认同与感情承诺的态度绩效。
(4)科技工作的成果质量胜于数量决定了其结果绩效不宜简单叠加。
科技工作者的工作具有高复杂性,其成果表现形式也是多样的,但各成果之间亦存在着投入多寡、难度大小之分。现有研究若以具体数值对科技工作者绩效进行衡量,一般是按照绩效成果不同等级进行加权处理。刘仁义和陈士俊对现有科技工作者绩效评估常规指标体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发现科技绩效成果一般按照难度和质量进行层次等级划分[37]。可见科技工作成果不能简单叠加,应据难度与质量加权处理,以鼓励高质量的产出。
2.2 科技工作者绩效结构探索:三维绩效
根据以上理论综述与推演,本研究基于科技工作者职业群体提出新的工作绩效结构理论观点。研究认为科技工作者工作绩效应包括态度绩效、行为绩效与结果绩效三个维度,构成科技工作者三维绩效结构(见图1)。

图1 科技工作者“态度-行为-结果”三维绩效
(1)态度绩效。即反映科技工作者组织认同感、愿与组织共成长的态度强度、组织公民态度与情感承诺感等的绩效表现,包括合作态度与集体利益导向、是否与组织目标一致、在困难时期留在组织的态度意愿、对组织的认同与忠诚以及为组织利益愿意从事额外工作态度等。这些绩效表现与关系绩效不同,侧重态度与心理表达的测度,更多是通过态度测量表现出来,是行为表现未必能真实反映的内在心理与态度表现,故将之定义为“态度绩效”。
(2)行为绩效。结合“创新性行为结果论”的观点及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特点,本研究提出的科技工作者行为绩效主要指创新、学习行为,是科技工作者为形成创新成果并使之应用于实践而从事的各种创新行为以及开展的各种创新活动,同时包括为维护与增值创新能力而进行的学习及专业交流行为与活动等。这些绩效表现更多的是为产出科研最终成果而进行的活动投入与行为准备,因此将之称为“行为绩效”。
(3)结果绩效。结合“创新性行为结果论”的观点及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特点,本研究提出的科技工作者结果绩效指产出并可应用或指导实践的科技创新成果,包括获得的专利、发表的学术成果等。因反映科技工作者创新活动后的产出与结果,故命名为“结果绩效”。
在态度绩效、行为绩效、结果绩效三者关系上,由于科技工作的专业性以及对素质能力的高要求,因此科技工作者高态度绩效未必能带来高行为绩效与结果绩效,反之,由于科技工作者组织承诺与专业承诺的可分性,具高行为绩效与结果绩效的科技工作者,未必对组织具有高态度绩效,即态度绩效与行为绩效、结果绩效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科技工作者的结果绩效是行为绩效的产出和目标,行为绩效则是结果绩效的前期投入和付诸的努力,行为绩效不仅是结果绩效的工具,其本身也是一种结果,它可与结果绩效分开判断,是结果绩效的前因,但由于科技产出的时滞性,结果绩效的增长速度慢于行为绩效的增长速度。
3 结语
以职业群体视角对现有绩效结构理论进行重新梳理与综述,是一个新的尝试。本研究在文献阅读与梳理的过程中发现,国内外绩效结构研究的发展实质上是随着社会变迁,研究关注对象发生转换而不断得以推进的。随着社会发展,科技工作者群体日益成为知识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基于该职业群体的绩效结构研究将成为未来绩效结构研究的重要流派,本研究基于理论推演进行了科技工作者“态度-行为-结果”三维绩效结构的探索,这一理论探索可为科技工作者职业群体绩效研究者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发。
[1]Munsterberg Hugo.Psychology And Industrial Efficiency[M].Boston:Houghton Mifflin,1913.
[2]Bernardin H.John,Jeffrey S.Kane,Susan Ross,et al.Performance appraisal design,development,and implementation[A].In: G.Ferris,S.Rosen,D.Barnum,eds.Handbook of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Cambridge[C].Massachusetts:Blackwell,1995.402-493.
[3]Richard S.Williams.Performance Management[M].London:International Thomson Business Press,1988.93-100,173-175.
[4]Katz D,Kahn R L.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Organization[M].New York:Wiley,1978.131-134.
[5]Murphy K R,Sharella A H..Implications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nature of job performance for the validity of selection tests:Multivariate frameworks for studying test validity[J].Personnel Psychology,1997,(50):823-854.
[6]Welbourme TM.,Johnson D E.,Erez A..The role-based performance scale:Validity analysis of a theory based measure[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8,41(5):540-555.
[7]Cardy R.L,Dobbins G.H..Performance Appraisal:Alternative Perspectives[M].Ohio:South-Western,1994.
[8]Campbell JP,Ford P,et al.Development of multiple job performance measures in a representative sample of jobs [J].Personnel Psychology,1990,43(2):278-300.
[9]Campbell J.P.,McCloy R.A.,Oppler S.H.,et al.A theory of performance[A].In:Schmitt N,Borman WC,eds.Personnel Selection in Organizations[C].San Francisco:Jossey-Bass,1993.35-70.
[10]Rotundo M,Sackett P.R..The relative importance of task,citizenship,and counterproductive performance to global ratings of job performance:A policy-capturing approach[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2,87(1):66-80.
[11]Borman W.C.,Motowidlo S.J..Expanding the criterion domain to include elements of contextual performance[A].In:Schmitt N,Borman W.C.,eds.Personnel Selection in Organizations[C].SanFrancisco:Jossey-Bass Pub1ishers,l993.71-98.
[12]Smith C.A.,Organ D.W.,Near J.P..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its nature and antecedent [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83,68(4):475-480.
[13]Van Scotter J.R.,Motowidlo S.J..Interpersonal facilitation and job dedication as separate facets of contextual performance [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1996,(81):525-531.
[14]Coleman V.L.,Borman W.C..Investigating the Underlying Structure of the Citizenship Performance Domain [J].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Review,2000,(10):25-45.
[15]Hesketh B,Allworth E..Adaptive performance:Updating the criterion to cope with change [A].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cond Australian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Conference[C].Melbourne,1997.
[16]Pulakos E.D,et al..Adaptability in the workplace:Development of a taxonomy of adaptive performance[J].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0,85(4):612-624.
[17]Hesketh B.,Neal A..Technology and performance[A].In D.R.Ilgen,D.E.Pulakos,Eds.The changing nature of performance:Implication for staffing,motivation,and development[C].San Francisco,CA:Jossey-Bass,1999.21-25.
[18]张敏.适应性绩效:教师绩效结构的新发展[J].高等工程教育研究,2007,(2):103-106.
[19]孙健敏,焦长泉.对管理者工作绩效结构的探索性研究[J].人类工效学,2002,8(3):1-10.
[20]王登峰,崔红.中国基层党政领导干部的工作绩效结构[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32(1):1-8.
[21]陈亮,段兴民.基于行为的组织中层管理者工作绩效评价结构研究[J].管理工程学报,2009,23(2):44-49.
[22]Liang K.G..Fairness in Chinese of Organizations:Dissertation for PH.D[Z].Old Dominion University,1999.
[23]Farh J L.Impetus for action:a cultural analysis of justi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Chinese society [J].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1997,(42):421-444.
[24]Brumbrach,Performance Management[M].London:The Cromwell Press,1988.14-15.
[25]杨杰,方俐洛,凌文铨.绩效评价的若干问题[J].应用心理学,2000,6(2):53-58.
[26]仲理峰,时勘.绩效管理的几个基本问题[J].南开管理评论,2000,(3):15-19.
[27]George Milkovich,Jerry Newman.Compensation[M].New York:McGraw Hill,2004.
[28]田家华,张光进,姜炜.知识员工考评方法的权变选择研究:绩效特征的视角[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8(1):64-69.
[29]London M.,Mone E.M..Continuous learning[A].In: D.R.Ilgen,D.E.Pulakos,eds.The changing nature of performance:Implication for staffing,motivation,and development[C].San Francisco,CA:Jossey-Bass,1999:119-153.
[30]Scott S.G.,Bruce R.A..Determinants of innovative behavior:A path model of individual innovation in the workp lace [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1994,37(3):580-607.
[31]Janssen O.,Van Yperen N.W..Employee’s goal orientations,the quality of leader-member exchange,and the outcomes of job performance and job satisfaction[J].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4,27(3):368-384.
[32]柳丽华,徐向艺.知识型员工绩效管理模型及其优化[J].山东社会科学,2006,(5):56-58.
[33]韩翼,廖建桥,龙立荣.雇员工作绩效结构模型构建与实证研究.管理科学学报,2007,10(5):62-77.
[34]Borman W.C.,Motowidlo S.J..Task performance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The meaning for personnel selection research[J].Human Performance,1997,(10): 99-109.
[35]彼得·德鲁克.变动中的管理界[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36]陈建安,李燕萍.管理类和技术类知识员工绩效特征的实证解析[J].经济管理,2008,30(11):61-66.
[37]刘仁义,陈士俊.高校教师科技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权重[J].统计与决策,2007,(3b):135-137.
(责任编辑 胡琼静)
Theories of Performance Structure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of Occupational Groups
Zhang Tingjun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Fujian Normal University,Fuzhou 350007,China)
The paper classifies the viewpoints into different kinds based on a new perspective of occupational groups and induc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Based on it,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researches will be the mainstream of working performance struc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society and explores theoretically S&T personnel’s working performance structure.
working performance structure;S&T personnel;three-dimension performance
C931
A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决策咨询课题“科技工作者薪酬设计理论与实践”项目资助(2008ZCYJ17--A)。
2010-07-30
张廷君(1980-),女,福建福州人,管理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
——致敬殡葬工作者